范儿
海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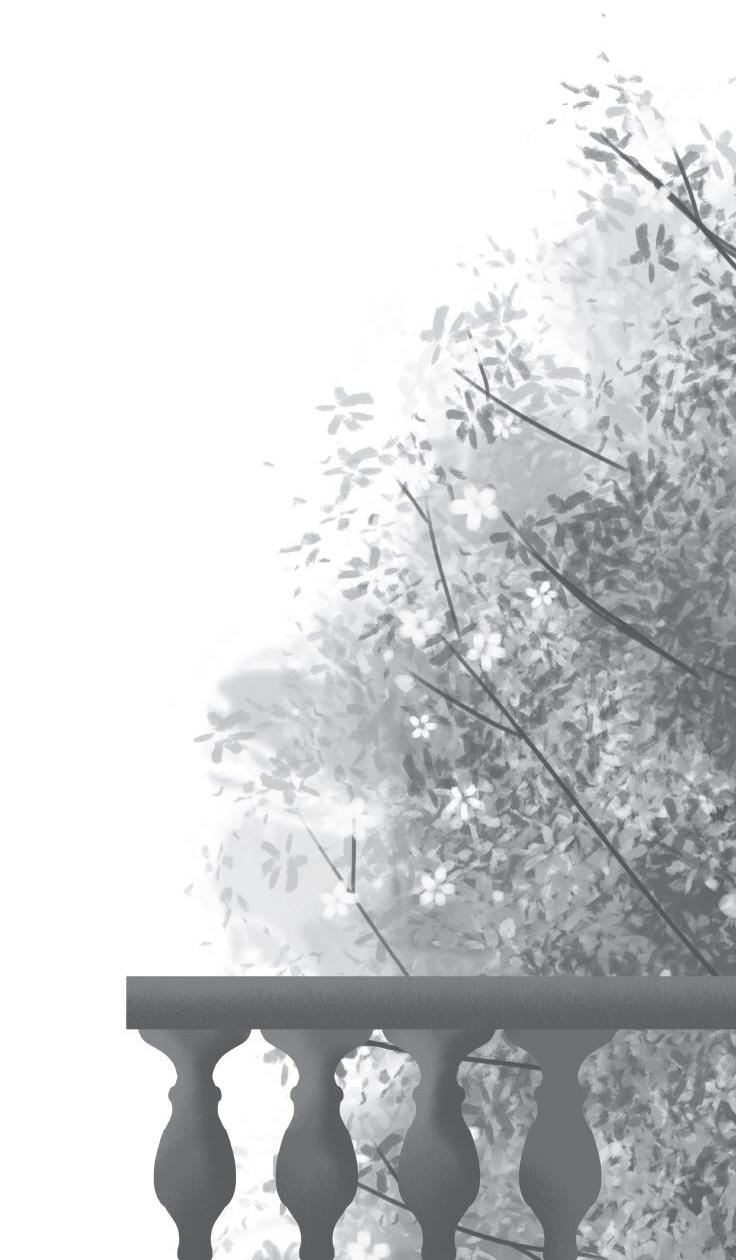
民国了,辫子剪了,不养八旗的爷们了。本来吃着祖上的功勋活得好好的,结果天塌了。
可爷们还要自己活得像个爷。卖房子卖地也要养着身上的爷气儿,爷一天是一天。
爷到了最后还得活人,爷了十几年家底子也就空了。那些个八旗贵族到末了拉黄包车的,摆小摊儿的,当用人的,五行八作干啥的也就都有了。
镶黄旗的富六爷把家里最后一个青花瓶甩给了当铺之后就走进了戏园子。台上是秋青莲的青衣戏。
秋青莲扮相好,眼神好,身段好,唱功也好。富六爷都捧了那么多年了,捧得家徒四壁,福晋也带着孩子自寻生路了。
听了一半,富六爷喝了一声彩,随手往戏台子上扔下一包响当当的银元便起身离座。台上的秋青莲看了一眼富六爷的背影继续咿咿呀呀地唱,有点走了腔调,但没人听得出来。
出了戏园子,富六爷心想,今儿算是有个善终了。富六爷不后悔。
富六爷想做点自己的事儿了。
回家后,富六爷就卖掉了仅有的两间房子,临街盘个铺子。富六爷的铺子不卖别的,只卖字卖画,都是自己写的画的。其实卖字画当街摆个摊也能,可富六爷不。爷嘛!总得有样东西撑着自己的门面。来了客人总得有个座儿,有口茶水喝,这才算体面。
富六爷从小就爱写字画画,尤其喜欢临摹董其昌的书法,倪云林的山水。家里也有过几幅真迹,不过都换了酒钱。
富六爷喜欢喝酒,怀里的锡酒壶就没空过烧刀子。一碟子酱黄瓜也是切得体体面面,一小块水豆腐也要仔仔细细撒上小葱花和精盐面儿。一天三遍酒,右手跷起兰花指捏着小酒盅,必须要有滋有味地喝下去。富六爷的话,这样才能活人。
富六爷给人写字画画落款从来不落实名,写的都是镶黄富察氏。然后盖上印章——前朝贵胄。卖字画强够维持挑费,可富六爷就喜欢这么活。
1937年秋天的一个中午,富六爷依旧在自己的铺子里用右手的兰花指捏着小酒盅,品味着烧刀子的清洌。外面的世界似乎和他无关。
门开了,秋青莲款款的身影出现在富六爷的面前,身后跟着一个日本军官打扮的小个子。
富六爷先是一怔,而后凄然一笑。
谁也没说话。富六爷继续喝酒,把烧刀子一口一口地压进了喉咙。
好一会儿,秋青莲才将几卷银元放在桌子上说,这位是横山队长……
富六爷捏着酒盅斜楞一眼说,让他自己和爷回话,又不是没长嘴。会说中国话吗?
横山用中国话说,秋小姐介绍说富先生擅长水墨丹青,家中收藏颇丰。我们山田长官也偏爱此道,尤其喜欢明清字画,听说先生手中藏有一幅董其昌的书法……
富六爷说,有过,早换酒喝了。董其昌的算什么啊,倪云林的,四王的,吴恽的家里的好东西多着呢,都卖了。不过都卖给咱自己人了,肥水也没流外人田,不可惜,自家人,谁玩不是玩啊。
横山又说,那就请先生临摹一幅董字,或者明清山水……
富六爷说,爷今儿乏了,只喝酒不作画也不写字了。
秋青莲说,六爷你就画吧,日本人惹不得的。他会……
富六爷说,他会什么啊?还能砍爷的手怎的?
横山面带愠色。
富六爷拍案而起冲着横山吼起来,给谁使脸色呢,倭寇也敢在爷面前抖威风?大清国没了也就算了,改朝换代是咱自己家常有的事儿,可你们算是哪盘菜啊?
说着富六爷换左手兰花指捏着酒盅,右手平摊在了桌子上。
横山不语,转身走了。
秋青莲看了几眼富六爷也跟了出去。
几个日本兵闖了进来。一片血光。
富六爷被砍掉了右手的四指头,手掌上只剩下了拇指,微微抽动了一下……
和别人想的不一样。
铺子没关张,几个月后富六爷还能写字画画。不过不再用笔,而是用右手剩下的拇指。
富六爷从此以拇指作书作画,书法绘画别具风骨更显苍劲有力。从此,富六爷的名声大噪。
许多年过去了,富六爷老了。人们总会看到,老六爷胸前端着右手掌,竖着的大拇指骄傲地冲着自己,倒背着左臂在街上闲逛,过往的人都会很恭敬地和六爷打招呼。
不过,这个时候的人们已经不再叫他六爷了。富六爷早就有了一个新的称呼——老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