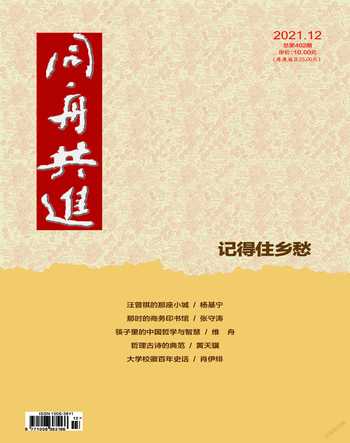陈忠实:“到《白鹿原》中找我去”
史鹏钊
白鹿原属于陕西关中,位于今天西安市城区东南方向。相传在周平王时期,“有白鹿游于此原,以是名”。自古以来,白鹿就被视为祥瑞之兽,代表着至仁至德的纯善品德。为了纪念白鹿带来福乐安康,鹿走沟、迷鹿村、鹿到坡、神鹿坊、白鹿寺等地名逐渐传开,蕴涵着当地人对这片古原的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期许。
1942年,在白鹿原北坡下的西蒋村,陈忠实出生。西蒋村,如今距西安城区虽然不足30公里,却未通公交。2017年,陈忠实先生去世一周年的那天,天气晴朗,我驾车行进在这片属于文学的土地上。忽然,一块紫底白字的路牌撞入眼帘,上面写着:“西蒋村,陈忠实故居,《白鹿原》小说创作地。”大字下面还有一行小字,记录着陈忠实的生卒年份。
这就是一位大作家名不见经传的故乡啊。这个常住人口不足300人的小村,是陈忠实呱呱坠地的地方,也是他澄净心灵、思古抚今、放飞思想、纵情写作的精神家园。直到今天,西蒋村的地理位置依然相对偏僻,如果不是陈忠实的故居,可能会更加人迹罕至。在我所到之处,三五男女一脸静然,和我一样,他们也是来走访作家的故乡吧。他们在故居大门前驻足,观而不语,流露出对陈先生的敬仰之情。
在故居左方的外墻上,写着一段节选自陈忠实散文《青海高原一株柳》的文字;右方墙壁上则印着陈忠实手书的徐霞客名句:“春随香草千年艳,人与梅花一样清。”这句诗可谓陈忠实一生真实的写照。
步入故居大院,我脑海中不禁遐想先生在这里活动的身影,又想起他在散文《原下的日子》里,曾引用白居易的诗来描述自己对故乡的情感:
宠辱忧欢不到情,任他朝市自营营。
独寻秋景城东去,白鹿原头信马行。
(《城东闲游》)
这是何等惬意,何等自在。
1957年,15岁的陈忠实上初二,他读了文学课本上赵树理的短篇小说《田寡妇看瓜》后,突然有了写作的冲动。
赵树理的作品对陈忠实影响至深。陈忠实曾说:“我这一生的全部有幸与不幸,就是从阅读《三里湾》和这篇小说的写作开始的。”半个世纪后,早已成名的陈忠实还深情地忆念到,在阅读《三里湾》后,“我随之把赵树理已经出版的小说全部借来阅读了。这时候的赵树理在我心目中已经是中国最伟大的作家”。他还讲到赵树理笔下的农村给他带来的震撼:“赵树理写农村那些事很生动,文字也很生动,情节也很生动,他写的这些事,这些生活情节,我在生活中差不多都经历过……这些东西如果能上书,能写出来文章,那么我也可能写。”
他初试牛刀,写了一篇小说《桃园风波》。这篇小说作为习作,没有发表,但老师的评价很高,那时是五级计分制,老师打了5分还嫌不够,在“5”的右上角又打了一个“+”号。从此,陈忠实走上文学之路。
1980年对于陈忠实来说,是亦喜亦悲的一年。“喜”源自一个好消息——他的短篇小说《信任》经《人民文学》转载后,在国内引起很大反响。《人民文学》编辑向前给陈忠实写信,告诉他,《信任》荣获1979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对于陈忠实来说,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他心里无比高兴。此时距离他第一次发表小说已经过去7年,这个奖项是对他7年来在文学上努力的肯定。更让他为之鼓舞的是,评委是读者,是读者以投票的方式选出最优秀的作品,说明他的作品得到全国读者的认可,奖项自然更有“含金量”。“悲”源自一个坏消息,陈忠实的妻子王翠英突然病倒了。妻子是家里的顶梁柱,她突然病倒,陈忠实的思想负担也大了起来,许多事情处于搁浅状态。
1982年底,不惑之年的陈忠实正式调入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陕西省作家协会),名正言顺地成为一名专业作家。从发表第一篇习作,称自己为业余作者,到成为专业作家的这一天,他花了整整25年。在省城里当专业作家,头衔虽然变好听了,但纷繁的环境让他无论如何也安不下心,写不出满意的作品来。于是,陈忠实决定回到白鹿原的老屋去,专心写作。
1987年8月,陈忠实到长安县查阅县志和有关党史、文史资料。一天晚上,他与《长安报》记者李东济在旅馆,一边喝酒、吃桃,一边闲聊。两人说得投机,陈忠实第一次向外人透露他要创作《白鹿原》的消息。
说着说着,陈忠实谈起自己艰难的、屡屡受挫的创作历程,感叹自己已是个年近半百的人了,“死还不是一死了之,最愧的是爱了一辈子文学,写了十几年小说,死了还没有一块可以垫头的东西呢”。关中民俗,亡者入殓,头下要有枕头,身旁还要放其他物什,这些东西,有时是由死者生前准备或安排妥当的。陈忠实说:“东济,你知道啥叫老哥一直丢心不下?就是那垫头的东西!但愿——但愿哇但愿,但愿我能给自己弄成个垫得住头的砖头或枕头哟!”(邢小利《陈忠实传》)
这时,陈忠实在中短篇小说的创作上已基本停笔半年。这种创作上“聚气”的准备,他不轻易告诉别人。即使是和他交情颇深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杂志主编何启治,他也只是透了点底,并“随即叮嘱他两点:不要告诉别人,不要催问。如同农家妇女蒸馍馍,未熟透之前是切忌揭开锅盖的”。
1988年4月1日,春暖花开,白鹿原上万物生机。酝酿已久的陈忠实在草稿本上写下第一行字:“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白鹿原》的创作正式拉开序幕。

写作的过程当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写得不顺、遇到怎么也跨不过的沟坎,烦躁乃至气馁时,陈忠实就会在夜静时分,挪一张小凳,坐在中院那破烂不堪的两幢厦屋之间,寻觅捕逮厦屋爷的呻唤。厦屋爷是陈忠实祖父的兄弟,谢世前曾住在上房和西边的厦屋里。陈忠实小时候夜半如厕时,对面窗户往往会传来厦屋爷深沉而又舒缓的呻唤声。
厦屋爷就是一个典型的关中男人,不过那时的陈忠实对这样的呻唤声不以为意,不曾想,写作《白鹿原》时,这呻唤声竟“扯开了那道朦胧的纱幕,打通了我和白嘉轩那一茬人直接对视的障碍”,让他清晰感知到“和白嘉轩、鹿三、鹿子霖们之间一直朦胧着的纱幕扯去了,他们清楚生动如活人一样走动在我的小书房里,脚步声说话声咳嗽声都可闻可辨”。这让陈忠实骤然兴奋起来,第二天,他的心境便能逐渐恢复,又能以一种沉静的心态打开稿纸。后来,作品完成后,陈忠实曾说,“我在《白鹿原》书里构思的人物和生活背景,是我厦屋爷这一茬人的生活历程”。
来过陈忠实故居的读者可能很清楚,陈忠实的写作环境其实很一般。故居里,只见眼前有两排左右对沿的关中混砖房,有父母的居室、陈忠实的居室,还有《白鹿原》创作室。创作室实际上就是个书房,在这个不大而简陋的空间里,摆放着旧时的桌椅、沙发和一张低矮的圆桌。写字台上的眼镜、稿纸和钢笔还一直摆在平时的位置。陈忠实身居陋室,胸怀天下,他就是坐在我眼前的这张圆桌旁,花了4年时光,完成《白鹿原》这部民族文化巨著。
1989年1月,《白鹿原》初稿完成,共计40万字。随后两年,陈忠实在初稿的基础上不断补充和修改,写到最后10万字时,他还曾写信给朋友李禾,说自己陷入长篇而不能解脱,并称年内一定要完成。
陈忠实一直准确无误地记着,写完《白鹿原》书稿的最后一行文字,并划上最后一个标点符号的时间,是1991年腊月廿五日(公历1992年1月29日)下午。这对他来说,是一个难忘得有点刻骨铭心的冬日下午。写完的那一瞬,他如释重负:
……是从一个太过深远的地道走到洞口,骤然扑来的亮光刺激得我承受不住而发生晕眩;又如同背负着一件重物埋头远行,走到尽头卸下负载的重物时,业已习惯的负重远行的生理和心理的平衡被打破了,反而不能承受卸载后的轻松了。(陈忠实《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
陈忠实出门散步,走到河堤的石坝上抽了一根烟,然后平静地回到小院里,为自己煮了一碗面条,他形容,“这是我几年来吃得最从容的一碗面条”。
书稿完成后,接下来就是发表了。陈忠实始终没有忘记,19年前,在自己还是一个业余作家时就开始向他约稿的何启治。两人自彼时起结下深厚友谊,多年来互相惦记,联系不断。看着自己辛苦写完的厚厚一摞书稿,2月下旬,陈忠实提笔给何启治写信,告知他这本叫做《白鹿原》的长篇小说已经写好,正在修改中,并将于3月下旬完成,他想把书稿交由何启治来发表。
何启治收到陈忠实的信后,决定派当代文学一编室的负责人高贤均、编辑洪清波一起去拿稿。3月23日一早,西安正值春雪天,陈忠实早早就安顿好生病的老母亲,步行七八里赶到远郊汽车站,再搭乘头班车进城,在火车站接两位北京来的编辑。把编辑安顿好后,陈忠实又赶回家对书稿作最后的修改。

两天后,陈忠实再次从白鹿原老家赶来,将厚厚的书稿交给了他们。中午,陈忠实请两位编辑在金家巷作协后院的家里吃午饭,妻子王翠英给客人做了一顿头茬韭菜做馅的饺子。多年后,洪清波回忆对陈家的印象:“一个副厅级的作协副主席,家里的状况可以诠释一句成语:家徒四壁……令人唏嘘。”
7月初,《当代》确定在1992年第6期至1993年第1期连载《白鹿原》。1993年6月,《白鹿原》正式出版,第一版第一印印数达1.5万册。同年,陈忠实当选陕西省作协主席。1997年12月,第四届茅盾文学奖揭晓,《白鹿原》赫然在列。陈忠实总算苦尽甘来,正如他在《白鹿原》中所写:“活着就要记住,人生最痛苦最绝望的那一刻是最难熬的一刻,但不是生命结束的最后一刻;熬过去挣过去就会开始一个重要的转折,开始一个新的輝煌历程。”
法国文豪巴尔扎克说:“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当年,在中篇小说《蓝袍先生》写成千把字时,陈忠实突然觉得,在自己生活了大半辈子的白鹿原古老南原上,陈旧而又生动的记忆如灞水般涌来,长篇小说创作的欲念瞬间打开。
如今,我也站在这原上,读着《白鹿原》,试图捕捉陈忠实所见的那幅美好的乡村图景:
田野已经改换过另一种姿容,斑斓驳杂的秋天的色彩像羽毛一样脱光褪尽荡然无存了,河川里呈现出一种喧闹之后的沉静。灌渠渠沿和井台上堆积着刚刚从田地里清除出来的包谷秆子。麦子播种几近尾声,刚刚播种不久的田块裸露着湿漉漉的泥土,早种的田地已经泛出麦苗幼叶的嫩绿……大地简洁而素雅,天空开阔而深远。(《白鹿原》)
——这是中国农村一轴多么斑斓多彩、让人过目难忘的画卷。在陈忠实的笔下,古老的渭河平原散发着勃勃生机,在字里行间给读者以心灵的震撼。如今,《白鹿原》的发行数量已超过200万册,且被改编成秦腔、话剧、舞剧、电影、电视剧等多种艺术形式,这在当代文坛上是比较罕见的。
2016年4月29日,陈忠实先生驾鹤西去,我顿时泪盈于睫。想起和先生的几次见面,情景历历在目,先生的谆谆教导铿锵有力。
斯人远去,让人无比伤感,社会各界纷纷以不同方式悼念。记得那天,我也去了省作协参加先生的告别仪式,路上一个小插曲让我难忘。

当天下午两点多,我搭出租车前往位于建国路的省作协。上了车,司机说:“你去省作协?”我说:“是。”司机说,“我知道那个地儿”,他开始和我拉话,“你是不是去吊唁陈老师?”我点点头,心里正诧异这位司机对省作协的关注。
聊了几句后,司机说自己姓陈,以前曾租赁过省作协大院的门面房,与陈忠实有过一面之交。他说,陈忠实那时上班喜欢提着一个破旧的黑色皮包,每天走到传达室,亲自取自己的报纸和信件,取了后,就夹在胳膊底下走进办公室。有一天,看到陈忠实在大院里散步,陈师傅就鼓起勇气让陈忠实给自己写几个字,陈忠实二话没说就写下了“鸿鹄凌云,气贯长虹”八个大字,还与他合了影。陈师傅觉得不好意思,就说要送点润笔费给陈忠实,陈忠实听了,言辞坚定地回绝:“你把我老汉当成啥了。”盛名之下,陈忠实依然平易近人、慈祥和蔼、淡薄名利,这让陈师傅至今念念不忘。临下车时,陈师傅叮嘱我,“去了代替我磕几个头,这是对陈老师最大的感谢和怀念”。
回望陈忠实先生的一生,无论是散文还是小说,他都写尽了农村日常的形形色色,在古老的白鹿原上,他不断坚守和突围,追求强烈的美感,每一部作品的字里行间都充溢着真实质朴、深沉灵动。他总是直抒胸臆,感天、感地、感时、感世、感人、感物,用文字呈现自己心灵的独白,在真实生活的基础上,表达超凡的生命体验和济世情怀。无论人格还是思想,他都令人崇敬和折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