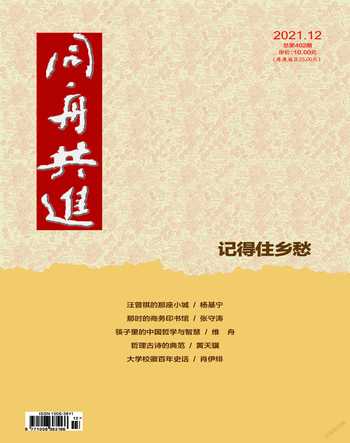老舍:点亮一盏文学的灯
于昊燕
北京城很大,老舍最牵挂的是西城小杨家胡同里的一个小院。
时至21世纪,在新街口南大街上,拓宽过的小杨家胡同口依然不起眼,向前走20多步,遇见一面墙,连着拐几个90度的硬弯,一个豁然开朗的小空场,周围分布着七八户人家。过了小空场,又是一个细而直的小胡同往北伸去。胡同的东南边是护国寺高大硬实的红墙,金刚殿挂着文物保护的牌子,殿后有一家小宾馆。出了胡同的东口向北走,不足两里路,就到了碧波荡漾的积水潭。
胡同里的人热情且善解人意,看到拿着地图、文艺青年模样的人,不待询问,就会经验丰富地指着不远处说:“8号。”8号院(原门牌号为小杨家胡同5号)的门楼早已倒塌,换了红漆的防盗门。历经百年沧桑,院内原来的房屋早已不见,但还保留着当初的格局:南北房亲密相对,院中间被挤成一条细长的过道。站在过道里仰望天空,看到的是长条的灰蓝,时而有白云与鸽群。
这个不起眼的小院子,便是作家老舍与故乡北京之间最深情的纽带。
生于北京:童年历战火
1899年2月3日傍晚,即戊戌年腊月二十三日酉时,与平时的暮色深沉大不相同,这一夜,卖糖瓜与关东糖的小摊,点着灯笼把街道照得亮堂堂的。无论是紫禁城里的皇帝,还是皇城根的平民百姓,都在热热闹闹地忙着送灶王爷上天祈求平安。
小杨家胡同住着一户舒姓人家,户主舒永寿是正红旗的护军,正在皇城值守。主妇马氏因为煤气中毒昏死在炕上,她刚生下一个脆弱的男婴。所幸这时马氏已经出嫁的大女儿不放心母亲,赶回家来,把冻得奄奄一息的小弟弟揣在怀里,才没让这个刚刚诞生的小生命夭折。
腊月二十三,民间称为“过小年”。自此日一直到除夕,年味渐浓,舒永寿为这个孩子起了一个喜庆的名字——庆春。
此时,清王朝已经到了内忧外患的末世,社会动荡,民生凋敝,舒家过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舒庆春出生后,没有母乳可吃,更请不起奶妈,马氏只好买些杨村糕干来喂养孩子。杨村糕干是用糯米和绵白糖加上茯苓粉制作而成的糕点,价格便宜,加点水搅一搅就可以成为易于吞咽的糊糊。为此,大姐夫后来还时常笑话舒庆春是糨糊喂大的孩子。
因为营养不良,舒庆春虽然活了下来,但是身体孱弱,7个月不会坐,8个月不会爬,软软的,像个棉花做的娃娃,安静地躺在炕上,到3岁都不会说话,也不怎么会走路。舒庆春没什么玩具,母亲拆洗棉被时会扯下一小块棉花,或家里偶尔吃顿白面时,给他一点揉好的白面,他就会翻来覆去地揉搓,捏成他以为形态很准确的小鸡、小鱼或其它各种东西。后来,舒庆春在南屋找到了十几个捏泥饽饽的模子,以及几个染好颜色的羊拐子(满语“嘎啦哈”,羊的膝盖骨——笔者注),这些成为了他心爱的玩具。
1900年8月,八国联军攻占北京,舒永寿防守正阳门,在巷战中受伤严重,倒在南恒裕粮店里悲惨死去。此后,全部生活重担压在马氏一人肩上,微薄的抚恤金根本无法维持生计,马氏就去给店铺的伙計、屠户们洗衣服、缝补衣服,到女校当老妈子,养活3个未成年的孩子。有时候,全家一天只能喝两顿酸豆汁和吃点用蔬菜煮成的糊糊。
马氏是个热心人,常帮穷邻居们洗三
(婴儿出生后第三日举行的沐浴仪式——编者注)、刮痧、剃头、绞脸,凡是她能做的,都有求必应。客人来了,马氏会设法弄些酒菜款待,为了体面招待客人,全家人要艰苦度日几天。遇上亲友家有喜丧事,马氏必定要穿上干干净净的大褂,拿一两串钱亲自去贺吊。
严寒的冬天过去,马氏把丈夫遗留下的几盆石榴与夹竹桃搬到院子里,花草生长得很旺盛,夹竹桃绽放着白的、粉的与玫红的花朵,让清贫而干净的小院洋溢着春的生机。马氏一生勤劳,个性坚强,爱清洁、守秩序,不怕吃亏、乐于助人,这些品行都影响了舒庆春的性格,自幼看惯的事情成了渗透在血液里的文化密码。
在刘寿绵(宗月大师)的帮助下,舒庆春进了正觉寺小学堂读书。上学后,舒庆春有了很多同学,也交了不少朋友,其中最好的朋友是歪毛儿(后来的语言学家罗常培)。两个人下午放学后就撒丫子跑到天桥,先一头扎进杂耍场子,看班主练上一通,拳脚生风,刀光剑影。
待鼓息锣停开始要赏钱时,小哥俩又一转身钻进戏园子,先听一段“苏三起解”,再来一段“水漫金山”。五彩缤纷的脸谱、金石裂帛的唱腔,伴着悠悠京胡,演尽人世间悲欢离合。日子长了,舒庆春也会哼上两句西皮、二黄之类,打上半套夹生的拳脚。老北京民间丰富多彩的艺术熏陶,牢牢印刻在舒庆春的大脑里。日后,他把这些记忆写进了《断魂枪》《方珍珠》《鼓书艺人》里。
1913年,舒庆春考入免学费、包食宿的师范学校读书,夏锡祺、张渲、方还与路鋆等4位教育家先后任过校长,他们爱生如子,教员中许多人是留学生。学校有中西风格结合的现代校舍、理化生物实验室、图书馆、劳作室,以及现代乐器等。
舒庆春在学校获得了全面的文体素质培养。他在宣讲所里演讲,在辩论会中获胜,在运动会上获徒手操、球杆体操团体第一名,还参加学校军乐队,排演讽刺话剧《袁大总统》。舒庆春像沐浴春风细雨的小树,茁壮成长,度过了充实的少年时光。
1918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被派到方家胡同小学当校长。舒庆春轻声对母亲说:以后,您可以歇一歇了!马氏说不出话来,感动得潸然泪下。

舒庆春生长于北京,这里有他的姓氏血脉、人生之根、人文之本,北京的人情风物滋养着他,没有北京,就没有老舍,如他所写:
真愿成为诗人,把一切好听好看的字都浸在自己的心血里,像杜鹃似的啼出北平的俊伟。啊!我不是诗人!我将永远道不出我的爱,一种像由音乐与图画所引起的爱。这不但辜负了北平,也对不住我自己,因为我的最初的知识与印象都得自北平,它是在我的血里,我的性格与脾气里有许多地方是这古城所赐给的。(《想北平》)
离开北京:问路倍思乡
1922年,舒庆春在燕京大学跟易文思先生学习英文。易文思同时是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校外考官,他把舒庆春介绍给在北京的伦敦传教会的伍德小姐,后者聘他为东方学院教师,任期5年。1924年9月,舒慶春飘洋过海去了英国。这是他第一次离开故乡,离开的时候,他没有回头,怕看到60多岁的老母亲依依不舍的眼神。
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中文系主任是当过宣统皇帝老师的庄士敦。这里的教学以学生需要为主,课程除了汉语、中国文学之外,还有占卜、包饺子、中医等。舒庆春与两位同事共同为灵格风语言中心编写了一套汉语教材,舒庆春以一口地道的“京片子”录制了《言语声片》,在国际上沿用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
教学之余,舒庆春还会在幽静的图书馆里阅读西方文学和历史书籍。他喜欢古希腊、古罗马文学及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也喜欢欧美近现代小说。他不断学习民主主义、人道主义和现代艺术形式,思考人生与祖国的命运。
与祖国隔得远了,思乡之情愈发浓烈,透过异域文化的视角,他对祖国的现状有了更宏阔的认识与感受,排遣不去的乡愁在他心中逐渐化为一篇篇小说。舒庆春以“老舍”为笔名创作了小说《老张的哲学》,批判现实的同时抑制不住对故乡的思念,在文中忍不住描绘:“到了德胜桥。西边一湾绿水,缓缓地从净业湖向东流来,两岸青石上几个赤足的小孩子,低着头,持着长细的竹竿钓那水里的小麦穗鱼。桥东一片荷塘,岸际围着青青的芦苇。几只白鹭,静静地立在绿荷丛中。”
舒庆春字舍予,既是把自己的姓氏拆解开来,又含有“舍我”奉献之意,他取“舍予”中的头一字,前面加上一个“老”字作为笔名。自此,文坛有了老舍。在作品中,老舍和自己过去所遇到的各种人物谈天,与家乡故里的人们拉家常,他不断写下去,又有了《赵子曰》《二马》等作品。
1930年,老舍回国后,先后在济南的齐鲁大学与青岛的山东大学任教,以教书为正职,写作为副业,创作了《黑白李》《月牙儿》等名篇。1936年,山东大学闹学潮,老舍辞了职准备只凭写作收入过日子。老舍住在青岛黄县路12号,院落幽静,一进楼门就可以看到右壁上挂满刀矛棍棒,显示出主人对武术的热爱与日常习练。
有个朋友来找老舍闲谈北平往事,朋友说,用过一个车夫,是个有心气儿的年轻人,勤俭攒钱买了一辆车,却因为遭了其它事不得已卖掉,如此三起三落,到末了还是受穷。朋友又说,也有好运气的车夫,有个被军队抓了壮丁的车夫,趁着军队换防,偷偷牵回了三匹骆驼。朋友走后,车夫与骆驼的影子仿佛一帧照片,印进了老舍的心里。

民国社会,很多没有积蓄、没有技能专长的底层人士去当车夫,老舍童年居住的小杨家胡同里就住着好几个。老舍闭上眼睛,想起北平带着尘土气息的街道、熙熙攘攘的人群、远亲近邻的面孔,渐渐浮现出一个年轻人的影子:他生长在乡间,18岁,年轻、单纯,脸和身体都结实硬棒,像一棵树。他有一个“伟大的计划”——省吃俭用一两年或三四年,自己打上一辆车,过自给自足的生活,他的名字叫祥子。
然而,军阀、官僚、特务、地痞流氓,随便一个有点权势的人,都可以把祥子以及祥子来之不易的努力成果轻易掠夺干净。老舍多么怜惜祥子的不幸,但他还是心痛而诚实地书写苦难的生活,揭示文明失范如何引发城市中的人性堕落,对病态的社会给人民带来的伤害深深忧虑。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老舍从青岛到济南,等待齐鲁大学开学。随着战事愈烈,绝不做汉奸的老舍告别妻儿,坐上最后一列开往武汉的火车。老舍为此次离别写过一首诗:
弱女痴儿不解哀,牵衣问父去何来?
话因伤别潸应泪,血若停流定是灰。
已见乡关沦水火,更堪江海逐风雷。
徘徊未忍道珍重,暮雁声低切切催。
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在汉口宣告成立,老舍被推举为总务部主任,对内总理会务,对外代表文协总会。扛着文协的旗帜,老舍从武汉到重庆,颠沛流离,贫病交加,但依然坚持国家至上的信念,他说:“我们必先对得起民族与国家;有了国家,才有文艺者,才有文艺。”
1941年春节,患了严重贫血的老舍在北碚养病,思乡情切,百感交集,他作诗《北碚辞岁》:“雾里梅花江上烟,小三峡里又新年。病中逢酒仍须醉,家在卢沟桥北边。”此时的老舍一定是想起了“那长着红酸枣的老城墙!面向着积水潭,背后是城墙,坐在石上看水中的小蝌蚪或苇叶上的嫩蜻蜓,我可以快乐地坐一天,心中完全安适,无所求也无可怕,像小儿安睡在摇篮里”。
1943年秋,老舍妻子胡絜青带着3个孩子历经千辛万苦来到重庆与老舍团聚,一家人住在北碚蔡锷路24号(今天生新村63号),算有了一个“安定”的家。胡絜青跟老舍讲述沦陷区的各种往事。那是老舍日夜牵挂的北平啊,听着妻子的讲述,他在脑海里浮现出一幅清晰的文学地图,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四世同堂》。在护国寺附近的小胡同里,以祁家四代为中心,再加上胡同里的另外几户人家,在日寇的铁蹄下,各个阶层、各色人等的荣辱浮沉、生死存亡开始上演。老舍用小人物的故事记录整个民族的脉动,记叙北平沦陷后的畸形世态,古老文化被打破后的不安、惶惑与觉醒。

抗战结束后,1946年3月,老舍和曹禺乘坐美国的运兵船“史葛将军”号从上海起程,赴美访问与讲学。年底,曹禺回国,老舍留在美国完成《四世同堂》第三部《饥荒》、长篇小说《鼓书艺人》、话剧《五虎断魂枪》、小说《唐人街》等。几十年来颠沛流离的生活,给老舍的身体埋下了许多病根。1949年4月,老舍因坐骨神经痛住院做手术,日本友人石垣绫子前去探望,说老舍病卧他乡,忧念故国之情溢于言表。
无论身在英国、美国,还是济南、青岛、武汉、重庆,老舍始终喜欢写北京的故事,故乡的一切与心灵粘合在一起,他笔下的人物大多走在德胜门—西直门—阜成门—地安门这样一个圈子里。如他所写:
一九四九年年尾,我回到故乡北京。我已经十四年没回来过了。虽然别离了这么久,我可是没有一天不想念着她。不管我在哪里,我还是拿北京作我的小说的背景,因为我闭上眼想起的北京是要比睁着眼看见的地方更亲切,更真实,更有感情的。这是真话。
重返北京:东风天地新
1949年6月,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召开在即,周恩来向远在美国的老舍发出召唤。根据周总理的指示,郭沫若、茅盾、曹禺、田汉、冯雪峰等30多人联名写了一封邀请信,经由秘密渠道送到了老舍手中。老舍收信后立即整装返回。
1949年底,他终于回到了阔别14年的故乡,他西装革履,拄着拐杖,心里却惦记着去胡同口吃碗炒肝儿。回国后,老舍被任命为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并当选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主席。在征得周总理同意后,老舍请他在美国的出版代理人寄回500美元版税,换成100匹布,买下了东城区迺兹府丰盛胡同10号(今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的一所小院。修缮之后,老舍与家人于1950年4月搬了进去,安居于此。
这是一座普通的北京旧式小院。1954年春,老舍在小院里亲手栽下两棵柿子树,每到秋天,树上结满火红的柿子,小院因而得名“丹柿小院”。丹柿小院里种满花草,菊花、昙花、山影、令箭、荷花、银星海棠……绿树成荫,花木葱茏,微风吹过,花香四溢。
丹柿小院附近有个三皇庙,民间又叫“瞎子庙”,盲人们落脚在此,靠庙宇遮风挡雨。老舍在街头经常遇到這些盲人,他们穿得很破旧,一群人相互拉扯着走,一手拿竹竿探路,一手拿乐器,由一个明眼小孩引路。这支衣衫褴褛的队伍引起了老舍的注意,老舍跟他们搭话:“解放了,大伙儿觉着怎么样?”一位年长的盲人回答:“我们也翻身了,都高兴!街面上没人再敢欺负我们了。”可是,盲人们又说没人算命了,生计成了问题。老舍的心隐隐作痛,他深知简单的接济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给他们提供就业门路,才能给他们有尊严的生存之路。

回到市文联,老舍郑重地和大家协商:“北京有好几百盲人,靠算命过活已经不行了,我们来管管他们吧,别叫他们挨饿受冻!”大家经过商议,觉得可以让盲人们学习新思想、适应新社会,掌握谋生的技能,有文艺特长的盲人学习新文艺,没有文艺特长的盲人则安排到工厂上班。老舍给市政府打报告,聂荣臻市长完全同意他的报告,还下拨了一笔专款,请市文委书记、市文联副主席李伯钊担任盲人培训班的组织者。
1950年底,盲人文艺学习班正式开课,老舍自掏腰包,买了许多乐器,并率先登台讲课,他还请来作家赵树理、北大教授罗常培来讲课。老舍到北京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请他们为盲艺人写新段子,自己也熬夜为盲人们写歌,编排适合他们演唱的曲目。一年后,一部分盲艺人组成盲人文艺工作队,到各地巡回演出;另一部分盲艺人被分配到专业文工团当伴奏演员;没有任何文艺特长的盲人则被安排到北京城的橡胶厂、皮革厂、纸袋厂、纸箱厂、印刷厂、服装城上班。经过老舍一番奔波,北京市几百名盲人终于成为自食其力者,一家老小的衣食有了着落,搬出了三皇庙,住进了灯市口西街条件好得多的房子里,他们脸上荡漾起了开心的笑容。
老舍又一次进入创作高峰阶段,写出了《茶馆》《龙须沟》《正红旗下》等经典佳作。此后,老舍再也没有长时间离开故乡——这清洁、明亮、美丽的北京。如他所写:“我爱北京的新工厂、新建筑、新道路、新公园、新学校、新市场……北京的确是宝地了!”
老舍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生于北京,长于北京,走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牵挂的都是北京,他像爱母亲一样深爱北京。老舍的文学创作多以北京城为背景,使用精粹的北京话,描写北京市民的平常人生,揭示北京文化的心理结构。北京城孕育了人民作家老舍,老舍为北京城点亮了一盏文学的灯,用作品为故乡增添了无穷的文化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