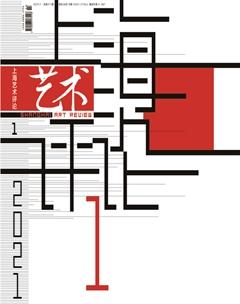寂寞的探索者
毛时安
我们已经习惯于用一个固定的视角、一种不变的色彩来处理我们面对的艺术现象文化现象。尤其是当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充满着喧哗、热闹的时代。画家方增先也被各种热闹包围着,特别是作为“新浙派人物画”的开创者、奠基人、推动者,他成就卓著,声名煊赫。而且作为美术教育家,他桃李满天下,影响深远,不乏人数庞大的艺术追随者。但我总觉得,他内心有着不为人知的寂寞和清冷。
2007年5月,上海美术馆举办《跋涉者—方增先艺术回顾展》。这是方先生一生首次有系统成规模的大型回顾性展览。二百来件展品,几乎囊括了他一生的所有重要作品,包括他最为影响深远成为中国画人物画代表作的《粒粒皆辛苦》《说红书》《艳阳天》插图和获齐白石奖的《母亲》,还有素描、手稿、书法,照片、文献,布满了偌大的一楼展厅。而那几件耳熟能详的画作前更是观者如堵人头攒动。南北两堵大墙,南墙《家乡板凳龙》,北面是铺满整面大墙的《祭天》。我在两件作品前面久久驻足。《家乡板凳龙》的翻江倒海,《祭天》的万马奔腾,那种画面上压倒一切的磅礴气势,内在的澎湃涌动的激情,让你有透不过气来的强大的窒息感。我注意到,除了少数人,大多数观众在此两幅画前只是一晃而过。
当天下午举办画展研讨会。研讨会几乎云集了当今中国美术评论界的大多数重要和著名的美术评论家。发言气氛很热烈,大家集中评价了方先生对浙派人物画的开拓和贡献。我觉得,忽视方先生浙派人物画的开创之功,固然是不对的。但把他被定格乃至固化为浙派人物画的创始人、代表画家,而忽略了他晚近更漫长的艺术追求,也是不全面的。事实上,诚如他自己所言:“浙派写实人物画从它出生那天即1955年算起,到‘文革1966年,前后仅十年时间” (见《方增先图文回忆录》26页)。即使再延伸到1974年影响巨大的《金光大道》插图,则前后20年。算到2007年,其后还有43年。浙派人物画,应该是他漫长绘画生涯中的一段重要但并不是最长的艺术旅途。其实,大家心目中的“浙派”,方先生将素描与水墨有机整合,从而为中国人物画开辟了新的路径,已写进美术史,被美术界所公认,方增先更在乎美术界对他晚年全新艺术追求的看法。会上,我就方增先晚近的人物画创新、探索、实践,做了题为“走向浑茫”的发言并在当年6月整理成同名评论。当天晚上,方先生妻子、雕塑家卢琪辉打电话给我说,老方听了你的发言很感动,觉得你特别理解他,是他的知音,老方要给你画一张画。我知道,方先生是极少赠画的,而且年事也高。回答,心领了,但不必这样的。卢大姐说,老方说一定要画的。不过时间不好确定,要看他身体。没想到,大约初秋的一个晚上,卢大姐乘车亲自上门送画,不但装裱好,而且配了非常端庄的镜框。画的是杜甫的《宿府》诗意图。四尺对开,三分之二是画面,三分之一是行草书写在洒金纸上的《宿府》全诗:
清秋幕府井梧寒,独宿江城蜡炬残。
永夜角声悲自语,中天月色好谁看?
风尘荏苒音书绝,关塞萧条行路难。
已忍伶俜十年事,强移栖息一枝安。
画中间,杜甫一人上身微微前倾,头扎浅蓝灰的巾帕,清癯的面容,眼帘低垂,一钩残月高悬夜幕,几片枯叶在抖索。外轮廓和脸部均线描,身躯变形,上长下短,用浅蓝灰层层渲染。诗和画都透出一股凄清寥落之感。其实这不是艺术家第一次画《宿府》。早在2004年他已作过130cm×80cm的《杜甫〈宿府〉诗意图》。因为尺幅大小不同,构图略有变化,其他相类。在他画册中,这是极少几件占据整页篇幅的作品。可见,艺术家对老杜此诗的情有独钟和对这件作品的重视。画边有画家自写的说明文字:“安史之乱,使杜甫经历了各种忧患。我想画一个处在孤寂中的人,朦胧夜色中,半轮残月,照映着一个孤独的灵魂。”(见《方增先图文回忆录》261页)
就我观察,方先生作为新浙派人物画创始人、上海美协主席、上海美术馆馆长一直忙碌着、热闹着。特别是他开创的早期浙派人物画,几十年来从者如云,但作为一个大师级的画家,他晚年的创作实践和探索是寂寞的。很少有人走进他的内心,去理解、响应他艺术世界中正在发生的一切。老杜此诗作于764年。诗人受成都府尹兼剑南节度使严武赏识,在其府中任参谋。家住郊外浣花溪。交通不便,遂常住府内,却不被幕僚理解,甚至妒忌、排挤,内心深为寂寞。清秋、独宿、井梧寒、悲自语、好谁看、音书绝、行路难、蜡炬残、永夜角声、中天月色……诗人这些词语游荡着的那颗“孤独的灵魂”激起了画家内心的强烈的共情。
画家的这种孤独和寂寞,来自两个方面。一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被外来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包围,传统国画不被理解的危机感。他回顾《帐篷里的笑声》遭遇,“现代艺术的冲击已經开始,对西方形式的追求是一片叫好声,而写实人物画没有再引人注意了,此画当然也无人理睬,此时连写生人物画像也没有一个画刊要用。”(《回顾录》24页)。在后来的《方增先口述历史》中他再次旧事重提。为此,他反复接触、走进现代艺术,甚至“冒风险决策”举办上海双年展(详见《口述历史》228页)。“对西方的现代或前卫,我想穷追到底,犹如呵壁天问”(《回顾录》28页)。二是在西方现代艺术的强大冲击下,有几千年传统的中国画何处去?突围的路在哪里?他迷惘、彷徨、忧思,然后探索、寻找。他说,“长期以来,一种危机感压迫着中国画家苦苦地思索一个问题:未来的中国画会是什么个样子?而人物画家对这个问题思索得更多,因为危机的压力也更大” (《口述历史》226页)。他不是那种以浮夸张扬自己,到处宣传自己艺术宣言而艺术上无所作为的人。他是一个深切意识到中国画危机,自觉意识去担当中国画走向未来的先行者,切切实实埋头苦干的艺术家,就像50年代他曾经实践过的那样。他有雄心和豪情,“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能自强不息,不断地生存发展,自立于世,它的文化也自然随着发展。中国画也必然随着中华民族相始终”(《自述历史》226页)。为此,他不惜当一个艺术的“苦行僧”:“在我身上除了苦行僧那样的路以外,我不可能去幻想此外的非分的可能性……我是那种在乱草泥泞中寻找一条小路的人”(《回顾录》26页)。在我心目中,他像一个艺术的“殉道者”。艺术是他虔诚的信仰,头上的星空。很少有艺术家像他那样寡言少语,却拥有汹涌澎湃翻江倒海的内心。
他是学院培养出来的画家。对于艺术本体和艺术历史有着长期的思考,有着锲而不舍的学术上的追求。他80年代开始的人物画创作实践,不是被动盲目的被大潮挟裹的结果,而是带着强烈中国本土艺术家主体思考的性质。正是在广泛接触西方现当代艺术后,他豁然开朗,“在我大体了解了前卫艺术状态后,我忽然了悟我画中国画还是应回到中国画本体中去”(《回顾录》28页)。
他的艺术实践同时包含了形而下的笔墨形式、语言的探索和形而上的对生存、信念以及对自己情感世界的开掘。就艺术语言而言,有几条:一是重新发现、开掘线条当代功能。 “用书法去画画”,“把笔线搞得好点”。具体是他90年代初用具有石刻味的线条画了一批脱离了写实而变形的白描古装人物。(参见《书法与国画》,原载2004年第6期《上海艺术家》)他在书法上下了苦功夫。一次,我去看望他,他送了我一本自己书写的《草书兰亭集序》。二是,大規模尝试把山水画积墨法引进人物画造型之中,增强人物和画面的厚重和苍凉。三是人物造型的团块化。他后期的笔下人物,大体都有着大山一般巍峨甚至粗看臃肿的体态造型。团块造型稳定、磅礴、大气,使他笔下那些普通人拥有了某种纪念碑式庄重、崇高和不朽。我以为,方先生人物造型图式团块化处理灵感,是来自他夫人雕塑家卢琪辉的长期的艺术影响。方增先晚年的人物画,离开大众的审美趣味越来越远。他不在乎世俗的爱好与否,没有媚俗讨人喜欢的美丽、好看、漂亮,也不在乎能否为眼下短期的某种社会功利服务,完全服从内心情感的召唤。即使“人民”这个我们已经司空见惯的概念,他也有了从个人生命经历和情感体验出发而获得的全新的理解。所以,他后来日益重、大、黑、丑的人物画,在国画界响应、追随、学习的艺术家,实际上是很少、很少的。画家自己清醒地意识到, “《母亲》在笔墨上有肌理的处理,人性的夸张,有焦虑的表达,有强悍野性的抒情。我在母亲形象处理上,大大夸大了体积,并有猛鸷一样的愕视,我开始向世俗认为‘丑的方向发展”(《回顾录》27页)。今天我们回溯80年代,中国国画突围的主流是以色彩来补救丰富强化水墨的视觉冲击力,以构成来打破中国画的传统布局。而方先生是极少数往回走,在传统武库中寻找发掘艺术创新资源,继续往前走,推动中国画人物画与现代审美对接的艺术家。对于一个功成名就的艺术家来说,这是一种壮士断腕的勇者之行!这种独特的审美境界的孤独寂寞,就如柳宗元看到的那个小石潭,“其境过清,不可久居”,同行者、赏识者寥寥,令人感慨。对于这种不惜孤独求败的追求的理解,是需要时间来消化的。
方增先晚年形而下的夸张变形的写实图式的背后则是他形而上的超乎日常生活经验的玄思。关于积墨法,方先生的体会是“笔墨的混沌积加,不但画面上出现空前的厚重感,而且有一种苦涩深沉的气质……所以,人物运用积墨,不止是形体的厚重,更在于心情的沉郁”(见《回顾录》28页,参见《回顾录》295页《积墨法》)。由此可见,有时形式即内容。笔墨形式创新的动力来自内容的需要和思考。积墨法,是形而下的技术,但它同时又是形而上的超验的哲思。特别是对于方增先这样的艺术家来说,积墨法实际上变成了“有意味的形式”,语言即思想,形式即内容。具体有三个取向。
一是对生存、生命本体的精神思考。从1985年到1992年,他和妻子卢琪辉将一切“置之度外”,七赴甘南藏区。61岁时登上三座海拔4000多米的雪峰。正是在藏区与藏民的接触交流,使他“逐渐在‘苦恼中找到了‘亮光”,感受到了“杭州、上海无法感受到的生活底蕴,雄浑、粗犷、悍朴,那一个个悲天悯人的场景”(《口述历史》225页)。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民族大家庭。各兄弟民族之间有文化的融合和互补。正是在藏族同胞身上,他找到了一种现代人失落已久的形而上的精神性本源性的存在,“他们在四五千公尺的高寒中与天地共同生存的伟大的精神本质,他们淳朴、纯真、不在乎任何艰难,他们不但可爱而且是可敬的。因为现实生活中纯真的人越来越少,敢于在恶劣环境中与天地共呼吸,这更了不起。如果世界上的人都这样那该多好,而现实中到处是危机和欺诈,到处是钱和势的张扬,到处是利益的追逐和掠夺”(《回顾录》24页)。他们把艰难险阻,生死考验,“活成了一道彩虹”,他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人性的光芒”(《口述历史》262页)。他诘问自己:“坐禅可以悟道,我的水墨也能悟出‘道吗?”(《回顾录》296页)他试图以一种形而上的虔诚信念,疗救现代人沉浸物欲的麻痹的灵魂,让灵魂从现实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祭天》的灵感来自1984年画家目睹玛曲藏区4000多米高山上藏民祭天的场景。现场的壮观深深震撼了他。前后酝酿构思20多年。2007年我久久驻足在这张宽1250cm、高200cm的大画前,只见群马四蹄生风,向着前方发疯般不惜一切的狂奔,烽烟滚滚,马上的藏民的皮袍被疾风撩起,他们全身心的投入,狂放到似乎忘记了自己的存在,完全与骏马雪山蓝天草原融为一体。画面强大的飓风般的动势,似乎把我也席卷而去,不至今夕何年,身在何处。在方先生笔下持续不断出现的藏民形象,手摇经筒、皮肤黝黑的藏族老妪(《大山的回忆》2002),行色匆匆走在街上,伟岸、雄武的藏族男子(《行行复行行》2002),还有宽袍大袖的藏族舞者(《草原祝酒歌》1997),他们黝黑的皮肤,脸上刻着的褶皱深藏着岁月的沧桑,无不倾注了他对人性的严肃思考。我想,方增先不是在画画,而是在用自己的艺术生命构筑一座现代人必需的精神家园。
二是对乡野童年生活的咀嚼回味,用“过去”对冲“现在”。他深情地说:“家乡有稻草的香味,使人感到分外亲切。经历战争,背井离乡,动荡不安,回头看,觉得家乡的日子过得特别慢,不像现在岁月如梭。”(《口述历史》27页)。他给自己自传起的题目就是“从山坳坳里来”。在《放牧》(2001)、《天籁随风》(2001)、《清泉随风远》(2001)中,农家孩子和大地清风老牛友爱无间,浑然一体,就像一曲曲乡村的童年歌谣。在我眼里,方先生本质上是一位终生裤脚上沾着泥土味的文人画家。1999年他搬出闹市,移居水乡松江,自建新房。他在不大的院落里挖了一口池塘,放上了一张渔网。两座小楼间有小桥沟通,来自家乡的巨石搁在房中。一派田园气息。其中最能体现他内心温情的就是《家乡板凳龙》(2002)。这是江浙汉民族元宵节的祭天,也是他儿时参加并且留下深刻记忆的民俗风情(《口述历史》25页)。随着时代的演进,年轻人的外出务工,他遗憾地发现“长者心中的美好回忆,成为历史长河中惊鸿一瞥”。为此,他幽默地把几代农民成群集中到板凳龙起舞的欢快场景中,凝聚成一块硕大无比的“山石”。吹唢呐,提灯笼,敲大镲,老人释放着残留着的旧梦,新人举着手里的塑料饮瓶引颈畅饮,在一片欢腾中流露出画家对现实世界发展矛盾的一丝淡淡而深刻的伤感和忧思。《家乡板凳龙》,他前后构图就有“一二十次之多”,一度找不到有希望的构图(《回顾录》241页),两个月在痛苦中挣扎,连续三次生病(《回顾录》297页)。这些画只有用心去细读,才能在他对于故乡和童年的发自内心的缅怀和心血满满、积满浓重黑色墨块的画面中,捕足到画家心的热烈、沉重的搏动!
三是《母亲》成功以后,1991年,他以线描的形式语言画了苏东坡、辛弃疾、陆游、孟浩然、龚自珍、杜甫……一批古代文人。他们人格高尚,诗格高贵,且“多为悲剧性格,忧愤”。诚如画家自己所云,“契合一种主题中心追求”。在一定程度上,这些人物也是画家的夫子自道。
这种有着形而上精神追求,哪怕是自己尚未完全清醒意识到的真正有情怀的艺术家,都会因为得不到热切的呼应,而产生范仲淹感慨的“微斯人,吾谁与归”孤独寂寞,哪怕他时时被热闹和光环包围着。
晚年方增先向着大地、山川、农民、藏胞,一泻千里地尽情倾诉着甚至发泄着自己内心长期积压、急欲吐露的思想和情感。《祭天》《祭山神》《家乡板凳龙》,还有那些文人先贤,体现了一个伟大画家的精神高度。笔墨追随着精神自由而无拘无束地舞蹈,每一根线条都像吴带当风那么随风起舞,那么兴之所至的尽兴。每一团墨块,都是一团乌亮煤块,在幽暗中燃烧、闪光。它们像江河里的浪头,千姿百态,高低起落,似乎并不在意目的和方向,但最后都朝着大海的方向,朝着一种精神的东方奔涌。
这是一个欢快的向上的时代,是五味杂陈的时代,也是一个浅阅读浅思考的时代,对于真正有自己艺术、文化思考和追求的艺术家来说,这又经常是一个寂寞而少人去艰苦理解的时代。方增先是我们这个时代寂寞的先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