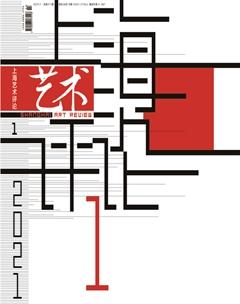寻找扶贫题材戏曲创作的内生力量
秋实
对于戏曲创作者而言,扶贫题材是热点,也是难点。从近年涌现的扶贫题材剧目数量来看,它的热度有增无减,且涉及的剧团之多、覆盖的剧种之广,远在同期其他题材之上,然而这一炙手可热的题材却让不少剧作家望而却步。究其原因,多在于面对短时间内大量涌现的“同题”创作,要实现扶贫题材的“内化”,寻找到独特的切入视角,使之从众多同类题材作品中脱颖而出,即使于那些成熟的剧作家而言,也并非轻而易举的事。
“内化”题材,是扶贫题材戏曲创作的必经之路
扶贫,首先是个社会学层面的概念,其次才是戏曲创作的一个题材类型。作为社会学概念的“扶贫”,其内涵和外延无疑是复杂而开阔的,它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伦理等多个方面,是国家政策层面大力推动并致力解决的宏大的社会命题。作为戏曲题材类型的“扶贫”,同样具有广阔的能指空间,但戏曲舞台的特殊性,要求剧作家必须把这种广阔的“能指”转换为具体的“所指”,换言之,剧作家要用明确的“所指”将观众引向扶贫题材深层的能指空间,通过作品主旨内涵的建构,引导观众对社会、时代及人生进行更为深刻的思考,让他们在收获审美享受的同时,得到心灵的启迪和升华。而这个过程,即是剧作家将作为社会学概念的“扶贫”转化为戏曲题材的过程,是剧作家对社会现象或生活素材进行“内化”后的再表达,它是扶贫题材戏曲创作的必经环节。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反思近年来涌现的扶贫题材戏曲创作出现“模式化”症结的根本原因,正是在于一些剧作者忽视了对扶贫题材的“内化”,没有把“好的”材料转化为“我的”材料,不能透过生活的表象去探索生活的本质,难以形成自己对扶贫攻坚这一社会现象的独到判断及认识,更不用说以此为标准指导自己对扶贫素材的发掘、鉴别和提炼,使得“扶贫”这一本应开阔的社会学概念在戏曲舞台上呈现出“路径相同、人物相似、结果一致、缺少悬念”的整体面貌。
在越剧《山海情深》中,我们是可以看出剧作者对扶贫问题的独到见解的。首先,编剧提炼出“山”与“海”两个重要意象,一边是代表乡土文明的“山”,一边是代表城市文明的“海”,试图打破“扶贫者”与“被扶贫者”的二元矛盾结构,将“扶贫”的内涵提升到两种文明之间的碰撞与融合,展现了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由“旧”入“新”的必然历程,以及这种历史必然性下人们心灵的阵痛;其次,编剧试图挖掘两种文明之间及其内部的深层矛盾,超越“经济扶贫”的单一向度,引导人们关注“经济扶贫”背后“被扶贫者”精神与情感世界之“贫”与“困”,拓展了扶贫题材的内涵与外延。以上两个方面,无疑是对扶贫题材进行“内化”的结果,剧作者不仅关注到生产方式落后、男性劳动力匮乏给山区经济发展带来恶性循环的表象,更敏感地捕捉到这种表象背后隐匿的沉重的情感及人伦危机,以蒋大海、蒋蔚等为代表的扶贫工作者,他们面对的不仅仅是山区经济的复苏、产业的振兴,更是对当地传统文化的抢救和道德体系的重构。可以说,剧中的“扶贫”,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一般“扶贫戏”片面追求经济效应的模式,它对社会转型时期乡土文化撕裂与阵痛的触及,是敏锐而深刻的。剧作家将自己对“为什么扶贫”“如何扶贫”的思考,集中表现在人们追求富足生活与渴望家庭圆满这一对本不该成为矛盾的矛盾之上,它的产生、发展和解决,能够折射出深刻的社会命题,体现了作为社会学概念的“扶贫”的广阔能指空间。这样的矛盾设置,无疑是充满戏剧性且能够以小见大的。頗为遗憾的是,虽然剧作者通过题材的“内化”,揭示出“扶贫”表象之下的深层矛盾,但从《山海情深》的首演本来看,这对矛盾常常淹没在蒋大海、蒋蔚的父女积怨以及龙阿婆、应花的婆媳误会等次要矛盾之中;或者说,剧中的次要矛盾没有紧紧围绕主要矛盾来铺陈,导致主题表达在一定程度上被分散和冲淡。因而,在剧本下一步的修改提升中,剧作者不妨对这些次要矛盾作适当的删改,使全剧的核心冲突能够更加集中、叙事节奏更加紧凑,让观众能够随着“山”与“海”由碰撞走向融合的过程,深刻地体味城镇化进程中的世道人心和时代阵痛。
写活人物,是扶贫题材戏曲创作深入人心的关键
任何一部戏剧作品都包含了题材、主旨、人物、语言等诸多要素,观众自然希望其中每一项都能在作品中得以完美的呈现。然而,十全十美是不可能的,一部具体的作品,总会或多或少地存在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通常情况下,观众对于这些瑕疵具有一定的包容度,但这种包容建立在一个重要的前提之上,即作品所塑造的人物必须是鲜活且可信的。倘若人物形象树立不起来,这个作品就很难说服观众而获得成功。同样地,“扶贫戏”要打动观众、深入人心,必须依靠活生生的人物形象。他们是剧作的灵魂,反映时代特征、记录历史进程必须依靠他们,传递情感、感染观众也必须依靠他们。当下许多“扶贫戏”之所以吸引不了观众,与这些作品塑造人物形象的模式化、套路化有很大关系。没有立体的人物作为载体,不管剧作者对扶贫问题的思考多么深刻,也只能成为一句空谈。借用威廉·阿契尔的观点:“有生命的剧本和没有生命的剧本的差别,就在于前者是人物支配着情节,而后者是情节支配着人物。”在扶贫题材的戏曲创作中,要把人物写活,其关键并不在于编写的情节是多么的曲折和传奇,而在于透过戏剧性的事件,挖掘历史车轮之下人性深层的冲突,并将这种冲突融入具体的人物行动逻辑,在人与自我、与他人、与时代的多重关系中,赋予扶贫主题以深刻的内涵。
越剧《山海情深》的人物形象可分为三个类型:第一类是以蒋大海、蒋蔚等为代表的扶贫工作者;第二类是以应花、滕娲、龙阿婆等为代表的山区留守女性;第三类是以根强、梁宝等为代表的外出务工的山区男性。这三类人物的命运都与时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因“扶贫”而聚合,也因“扶贫”而彰显出不同的个性;即使在同一类型的人物内部,不同人物之间也因“扶贫”而存在迥然的差异。剧作家对不同类型或同一类型人物个性差异的描写力求客观,没有对人物进行褒贬评价,而是试图以“扶贫”为背景,去描摹不同人物在时代浪潮中的心路历程,聚焦他们在这种不可阻挡的历史进程中的较量与和解。比如,剧作家对蒋氏父女两代人的刻画,他们一个是深扎基层的扶贫干部,一个是年轻有为的竹编技术人员,二人在矛盾重重的表象之下,怀揣着带领山区群众脱贫致富的共同理想,而这个理想逐步实现的过程,也是父女二人由对抗走向和解的过程。剧作家对苗寨女性群像的刻画,同样采用了这种矛盾分析法。她们乐观开朗的表象之下,都藏着思念外出务工亲人的苦涩,但她们对待扶贫的不同态度,又让她们彼此产生分歧,随着竹编产业在一次次挫折中逐渐壮大,她们也走上了同心协力壮大竹编合作社的道路。而以根强、梁宝为代表的苗寨外出务工众男子,在剧中更像是一个具有象征意味的符号,他们在前四场戏中是存在于苗寨女子期冀中的“未出场”人物,寄托了留守女人们对美好爱情和幸福生活的向往,脱贫之日,亦即他们的回归之日。在这三个人物类型中,剧作者对代表“扶贫者”的蒋氏父女以及代表“被扶贫者”的苗寨留守女性进行了重点刻画,尤其着重构建了蒋大海、蒋蔚父女以及龙阿婆、应花婆媳两组人物关系。蒋大海、蒋蔚这对父女人物关系的设置很巧妙,它既象征着扶贫责任在两代人肩上的延续,也为父女二人在扶贫观念上的分歧作好了铺垫。然而,剧作者没有将父女二人矛盾的根源归结于扶贫观念的不同,而是过多地着墨于父女二人因母亲去世而产生的个人积怨,这样的矛盾是游离于脱贫主题之外的,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人物行动的必然性。同样地,应花、龙阿婆象征了苗寨两代人对经济产业结构调整的态度,龙阿婆是长者、智者也是保守者,应花年轻、聪慧又有一颗开放包容的心,这样的人物关系设置本应很有戏,但剧作者过多地渲染婆媳之间的苦情、悲情,尤其是龙阿婆这样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不惜违背自己做人原则,佯装恶毒逼走儿媳妇,其行为动机于情于理都不符合现实逻辑,不仅贬损了这位本应出彩的人物形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作品的理性思考。此外,应花这个人物应该是全剧的“戏眼”,她生长于苗寨,却对蒋氏父女的竹编产业项目最为理解和包容;她经历苦难,却依然坚信幸福可以靠自己双手得来。可以说,她的身上集中了“山”的质朴与“海”的开阔,最能体现时代阵痛之下人的复杂性,也最能代表扶贫过程中“被扶贫者”之中的内生力量,她值得也应该被剧作者作为重点人物来刻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