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藏广府戏曲俗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兼论文献在海外的流播与价值*
徐巧越
广府戏曲俗曲是岭南文化的瑰宝。然而,受中国传统文学理念的影响,粤剧、木鱼书与粤讴等在清代被本地文人视作“不登大雅之堂”的淫曲小道。直至民国初年,仍有广东的院校认为粤曲俗乐“形骸放浪,无益学业,尤荡人心”(1)转引自程美宝《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香港:三联书店2018年,第320页。原文为《训令第581号:禁止男女学生不得共同演剧及演习戏曲俗乐曲》,载于《广东教育公报》,1928年12月第1卷第6期,第88-89页。1928年,时任省立肇庆师范学校校长的梁赞燊致函广东省教育厅,建议禁止学校排演粤曲粤剧。,禁止学生吟唱。此类文献因不入品流的文学地位,长期未得到学者士绅与藏书家的重视,历经时代的推移与社会的变迁,许多版本在国内已不易见得。幸运的是,广州自古是中国的重要对外贸易大港,早期赴华的英国传教士、商人与外交官大多驻扎在粤港澳地区。因此,广府曲籍伴随西人的迁移与学术交流,得以散藏于英伦的公藏机构。
自1990年代,国际交流日益便利,愈来愈多的中外学者前赴英国寻访中国俗文学文献,并发现了数量可观的粤剧、木鱼书、南音、龙舟歌与粤讴。21世纪以来,随着《广州大典》与“海外藏珍稀戏曲俗曲文献汇萃与研究”等项目的启动与推进,散落在海外的广府曲类文献重新回归学界视野。但是,对比敦煌遗书与传统“四部”古籍的整理,英藏粤剧与粤语说唱文献的访查、编目与研究至今未成体系。本文在追溯此类汉籍流播历程的基础上,总结广府曲籍与英国汉学发展之间的联系,对已有的研究情况做一个梳理与回顾,以之为例,进一步探讨今后英藏广府俗文学总目编撰、学术研究的发展方向与扩展空间。
一
广府曲籍的西传,最早可追溯至17世纪。在1630年代,劳德大主教(William Laud)采购了一批汉籍赠予牛津大学,以此扶持母校的东方学研究,其中包括木鱼书《新刊全本绣像花笺记残页》。这是最早流传至海外的粤语说唱歌本。
1711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澳门建立首个贸易点,与中国的联系也日渐频繁。据《明清宫藏中西商贸易档案》的记载,康熙五十四年(1715)至乾隆十四年(1749)间,仅由广州入口的英国船舰便有43艘(2)该数据引自万朝林、范金民《清代开海初期中西贸易探微》,《中国经济史研究》2019年第4期。,数量列居西欧各国之首。伴随贸易规模的扩大,英国人络绎不绝的来到广东。但因清廷明令禁止夷商购买汉籍,他们的采购受到限制,在本土收集的书籍零散芜杂。
19世纪以前,驻华英人大多不认识中文,他们在搜罗典籍时充满了随意性。在马戛尔尼与阿美士德使团赴华谈判相继碰壁后,英国政府逐渐认识到发展汉学研究对开拓中国市场的必要性。因此,该时期的传教士、外交官与商人开始有目的、有针对性的搜集汉籍,以此增加对中国语言文化和社会习俗的了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藏书家是翻译通事托马斯·曼宁(Thomas Manning)与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他们分别在政府与教会的资助下前赴广东,并在当地采购了大量汉籍,包含数量可观的木鱼书、粤讴与马头调。他们之所以会搜集此类广府俗曲文献,不仅是为了学习当地语言,更希望从这些风俗读本中认知本土的民俗、礼节与文化。曼宁曾在信函中向友人坦言,他下定决心学习汉语,是为了全面认识中国的历史文化与风俗制度(3)这封1807年的手稿信件现藏于英国皇家亚洲学会,编号为TM-4-5(Draft letter from Thomas Manning to Joseph Banks)。;马礼逊也曾写道:“重要的不是仅掌握这种语言里的几个词的知识,而是要了解中国人的性格和情感”(4)[英]艾丽莎·马礼逊:《马礼逊回忆录》下,顾长声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第216页。。此二人是首批系统搜集中国典籍的英国学人,在他们逝世后,其汉籍辗转为图书馆所藏,为早期英国汉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自19世纪30年代,东方学研究渐成风气,英国涌现出众多学术机构,各界名流慷慨的将私藏的东方器物与书籍赠予公家收藏机构。英国学者赫尔(John Fowler Hull)逝世后,其家属将他生前收集的东方藏书全部捐赠给大英博物院,其中便有一批数量可观的汉籍。(5)T.G.“Memoir of Mr.John Fowler Hull”, The Oriental Herald, 1829,Volume 20, No.63, p.310.在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成立初期,小斯当东爵士(George Thomas Staunton)为筹建图书馆,捐赠了2610册书籍(其中有136种为汉籍)(6)Stuart Simmonds, Simon Digby, The Royal Astatic Society: Its History and Treasure, Published for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by E.J.Brill/Leiden&London,1979,p.40.,更不遗余力的游说志同道合的亲友慷慨解囊。因此,该学会的中文藏书不乏英国权贵馈赠的广府俗曲唱本,譬如,稀见木鱼书《锦像边月》便是首任明斯特伯爵菲茨克拉伦斯(George Augustus Frederick FitzClarence)的捐赠。赫尔与菲茨克拉虽从未踏上过中国的土地,但他们都曾在印度任职,汉籍也由该处获得。同理,印度事务部图书馆保存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东方典籍,囊括了丹桂堂等广府书坊刊刻的书,这批藏书现归至大英图书馆管理。鉴于印度在中西往来间所扮演的特殊角色,不少中国书籍经由南亚中转,传至欧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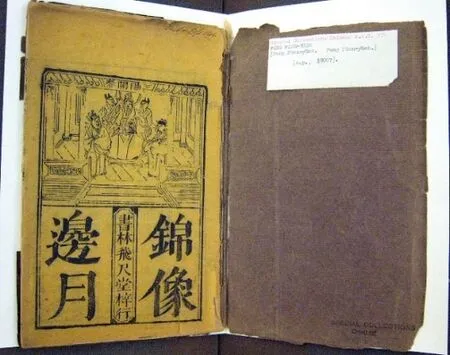
图1 菲茨克拉伦斯旧藏《锦像边月》木鱼书,现藏于利兹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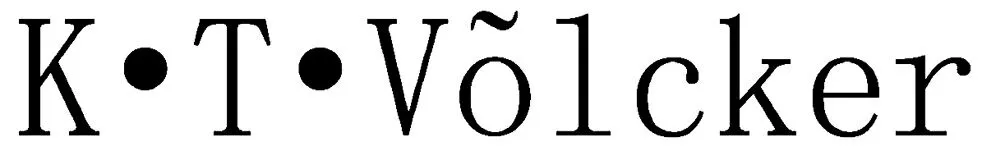
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牛津与剑桥大学先后开设汉学课程,东方研究学院成立,英国汉学开始摆脱为政治、商业与宗教服务的功利性宗旨,走向独立研究。但因社会漠不关心的态度,英国汉学长期滞后于欧陆。为了扭转这一局面,英国政府在1947年与1961年发布了《斯卡伯勒报告》(The Scarborough Report)与《海特报告》(The Hayter Report)。这两份政府报告都主张发展东方学,极大地推进了中国学研究:众多英国高校不仅增设汉学教职与相关课程,更利用政府拨款大规模采购书籍,扩充中文馆藏。1949年,在政府经费的资助下,剑桥大学的汉学教授哈隆(Gustava Haloun)前赴广州、澳门和香港采购书籍。同期,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等机构也通过香港的图书中介购买了一批汉籍。因为这批书籍大多由粤港澳地区获得,当中有相当数量的广府俗曲唱本。在改革开放以前,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汉学家与书商大多前赴港澳与东南亚等华人聚集之地选购汉籍。这些地区聚居众多粤籍居民或华裔,所以有大量的广府俗文学作品流通于市,经由采购者之手,流入英国的高校与学术机构。

图2-图4 英藏广府曲类文献上的书商印章与标签,分别为:吉隆坡大成书庄、新加坡亚基书局与香港交流图书公司
20世纪下半叶,龙彼得(Piet van der Loon)继承哈隆的衣钵,为扩充英国高校的中文藏书立下汗马功劳。他对中国地方戏曲与宗教民俗有较深的研究,并多次赴中国、日本与泰国等地进行田野调查,搜集俗曲唱本。龙彼得逝世后,其藏书为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所收藏,其中有626种粤剧与487种木鱼书、龙舟歌与南音唱本,给攻读与从事中国研究的学人提供了充足的文献资料,也保留下一批在中国本土已不易寻得的稀见版本。
广府曲籍的西传历程是英国汉学史的一个侧影,记录了中英文化交流的发展。在20世纪以前,广府戏曲、俗曲文献随传教士、外交官与图书中介的活动而流入欧洲,主要通过捐赠、采购与馆方移交的方式,为英国的公共图书馆所收藏。20世纪以后,英国汉学于政府扶持下进入兴盛时期,高校的中文馆藏得到扩充,大批广府俗文学文献得以入藏。同时,部分英国学人因研究兴趣所致,其私人藏书也有数量可观的粤语唱本。新世纪以来,中英两国的文化与学术交流愈加密切,汉籍流播途径变得多样化,为进一步的跨文化互动与融合打下了扎实的文献基础。
二
为了比较清楚地回顾与展现英国藏广府戏曲俗曲的编目状况,现将已有的成果按年代大致分作三个阶段,总结不同时期的著录特色,并对重要的书目进行评介。
(一)19世纪至20世纪初:西式目录与“文体错位”
在这一时期,英国学人尝试着以西式的学科体系对成规模的东方藏书进行分类。由于中西目录学体例的差异,早期西人甚少会在汉籍书目中编排小说或戏曲的专类,有关俗文学作品的著录也未成体系。至20世纪初,戏曲、说唱还会被归入历史、诗歌或小说的范畴,对它们的界定仍未形成固定标准。此类“文体错位”于广府曲籍的著录中亦频繁可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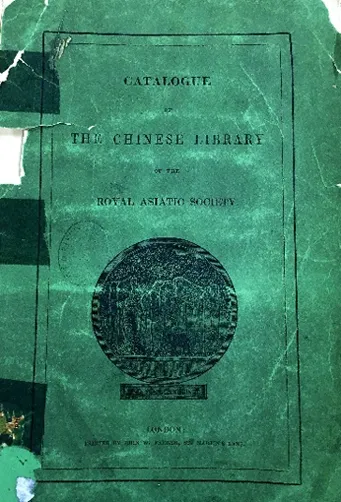
图5 1838年《皇家亚洲学会中文图书馆目录》封面 (8)1963年,皇家亚洲学会的中文藏书被移交至利兹大学,基德与霍尔特目录所著录的汉籍,现为布莱泽度图书馆(Brotherton Library, University of Leeds)的中文特藏。
最早明确载录广府曲类文献的是《马礼逊手稿目录》(Morrison’s Manuscript Catalogue),这份目录是传教士马礼逊在1823年冬季乘船回国途中所编撰的藏书清单,依题名首个汉字的偏旁为序,著录一千余种汉籍,其中提及《花笺记》与30卷木鱼书。他较为准确的将木鱼书描述为“ballad”(民谣),却将享有“第八才子书”美誉的《花笺》歌本定义为“a low novel”(低俗小说),用两种文本范畴去定义同一类说唱文体。
伦敦大学的基德教授(Samuel Kidd)于1838年为皇家亚洲学会编订了首部中文书目。这部《皇家亚洲学会中文图书馆目录》(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Library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依据康拉德·格斯纳(Conrad Gessner)《世界书目》(Bibliotheca Universalis)的条例,分21类著录242种中文藏书,题名以Pidgin English标注,每条都附有简单的介绍。基德把《海瑞传》与《缀白裘》分别归入“律法类”(Jurisprudence)与“诗歌类”(Poetry),《花笺记》则被划入“小说类”(works of fiction)。在1889年,翟理斯(Herbert A.Giles)据约翰·霍尔特(Henry F.Holt)增补的目录稿本,修订《皇家亚洲学会图书馆藏中文稿本目录》(A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Manuscripts in the Library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此书目不分类,总计著录562种汉籍,题名为汉语,在基德书目的基础上补充了作者、年份、卷册等版本信息。霍尔特借鉴了基德的分类,把木鱼书定义为小说,还误把《花笺记》的点评者写作金圣叹。
罗伯特·道格拉斯(Robert Kennaway Douglas)在1877年与1903年出版了《大英博物馆馆藏中文刻本、写本、绘本目录》(Catalogue of Chinese Printed Books, Manuscripts and Drawings in the Library of the British Museum)及其补目。此二部均为汉英双语的中文书目,参照欧洲方式,依作者署称字母排序,著录格式为题名、作者、卷数、年份与出版地点,没有关于具体版本信息的描述。其中,大部分的粤剧与粤语说唱都被著录为“Drama”“Dramatic tale”或“Play”,亦有部分木鱼书与民谣被归为“小说”。譬如,木鱼书《花笺记》即被定义为“Novel”,龙舟歌《赌仔卖女》与民歌《四季莲花》均被译为“Story”。
虽然,钟戴苍在点评时,将《花笺记》定位为“歌本小说”,概括其“叙事”与“诗韵”的双重特征。如果把木鱼书与俗曲说唱片面的视作“小说”或“故事”,虽突出叙事性的文体特质,却未能表现出韵律性与表演性。早期西式目录中的“文体错位”与“文体混淆”,反映近代西人对中国民间文学文化的认识偏差,也体现了中西文体观念与文学传统的差异。
(二)20世纪中叶至20世纪末:外籍学者编撰的专类目录
在20世纪上旬,郑振铎与柳存仁等学人在欧洲游学时,发现了数种广东唱本。但是,他们只是在考察古典小说或戏曲汉籍时,偶然注意到这些版本珍稀的文献,未开展系统的调查。直至1960年代,外籍学者才开启了针对海外所藏广东俗文学的寻访与著录。日本学者波多野太郎与鸟居久靖分别就所见木鱼书进行了编目(9)详见波多野太郎的《道情·弹词·木鱼书》(上、中、下),《横滨市立大学纪要》1969年第21期、1970年第22期、1977年第28期与鸟居久靖的《馆藏广州俗曲书目》,《天理图书馆报》1970年第45期。。德裔学者艾伯华(Wolfram Eberhard)的《广东唱本提要》(1972)详细著录德国巴伐利亚图书馆所藏的38种木鱼书。日本学人稻叶明子、金文京与渡边浩司据多年的实地走访调查,编订《木鱼书目录》(1995)。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Boris Riftin)发表的《俄罗斯所藏广东俗文学刊本书录》(1994)、《德国所藏广东俗文学刊本书录》(1995)等文章,补充了前人书目的遗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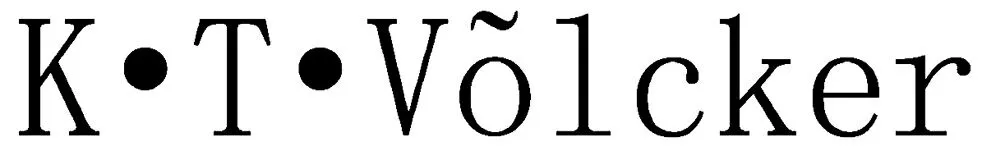
此前,关于英藏广府曲类文献的著录都散见于各类西式中文书目,对具体版本的描述也较为简略。专类目录的编撰开拓了域外汉籍研究的新领域,让更多的海内外学者注意到散落在英国的岭南曲籍,给后人的寻访与调查留下了宝贵的线索。
(三)21世纪以后:新世纪的细化整理
21世纪以来,随着科技的发展与国际交流的日益便利,中外学者在海外俗文学汉籍的搜集、编目与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对英国所藏广府曲类文献的整理也得到极大的推进。
一方面,网络目录展现了馆藏汉籍的概貌,为寻访提供了指南。牛津大学率先公布中文古籍的电子目录(Serica),该目由中文部主管何大伟(David Helliwell)编撰,依据中国传统的“四部法”对馆藏的汉籍进行分类,其中包括 “粤剧剧本”与“广州木鱼书”的专类细目(10)网络地址为:http://serica.bodleian.ox.ac.uk/,访问日期:2021年2月26日。。稍晚,部分开设中国学研究的高等学府紧随其后,在官网公布中文藏书目录。电子目录主要以公布检索书号为主,著录的版本信息较为简略,但也方便了学人的实地访查。另一方面,针对地方戏与俗曲说唱的编目逐渐形成专业的范式。近年来,有关广府曲类文献的著录愈加细化,譬如,同时标注出版者与藏板信息,说明藏板转用与拼板刊印的现象。笔者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访学期间,逐册翻阅该校图书馆的木鱼书、龙舟歌与民歌,依据目验所得之文献,编成《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藏广府方言唱本目录》(《戏曲与俗文学研究》第三辑)。除常规的版本信息,该目还增加唱词的首尾四句,以此规避“同名异本”与“异名同本”混淆的讹误。
然而,大部分英国图书馆依旧缺乏专业的中文管理人员,馆藏汉籍有待系统的编目整理,导致不少文献尘封于图书馆的角落,影响了对其价值的发掘和利用。自道格拉斯目录出版,大英博物院的中文藏书虽有所扩充,并于1973年与英国多家公共藏书机构合并成立大英图书馆(British Library),却再无编撰可展现馆藏汉籍全貌的新书目;而马礼逊旧藏的30卷广府唱本,因未得到亚非学院图书馆的编目,如今已无索书号可供寻其踪迹。总而言之,英藏汉籍的编目之路,任重而道远,亟需专业的学者投身于此项事业。
三
20世纪90年代起,因域外汉籍与中国俗文学研究的兴起,愈来愈多的学者都将目光投射向散落在海外的小说、戏曲与说唱文献。纵观近三十年来对英国所藏广府曲类文献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文献介绍
早在20世纪中叶,柳存仁在《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对大英图书馆与皇家亚洲学会馆藏的《花笺记》进行简略的介绍,但未进行详细的论述与研究。至1990年代,中外学者对各英国图书馆所藏的广府曲本文献开展了系统而全面的介绍。
李福清的《新发现的广东俗曲书录》对亚非学院馆藏的广府唱本做了详细的介绍,并载录21种马礼逊旧藏广府说唱曲本。魏安(Andrew West)在编撰《马礼逊藏书目录》时,未将30卷广府唱本纳入其中,李福清的文章及时记录了这批稀见唱本的具体版本面貌,留下了珍贵的信息。进入21世纪后,崔蕴华的《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藏中国唱本述略》(《图书馆论坛》2015年第3期)与《大英图书馆藏中国唱本述要》(《文化遗产》2015年第6期)展现了这两个图书馆所藏中国民间唱本的概貌,对版本珍稀的富贵堂《八排走兵火母女失散》、攀桂堂《唐明皇游月殿》等广府说唱与《和番》《辕门斩子》等粤剧剧本做了重点介绍。
(二)版本考证
英藏广府戏曲俗曲文献数量可观,不乏稀见的版本,是准确认识其文体诞生、发展及其艺术体式演变的关键材料,对考察清代社会境况与出版生态亦有重要意义。
《花笺记》素有“第八才子书”之美誉,郑振铎在《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中国小说与戏曲》便提及法图所藏的康熙序刊本,引起学界的关注。据统计,英国的图书馆藏有6种版本的《花笺记》,均为国内不易见到的孤本与珍本,故早期有关广府曲类文献的考证与研究,大多围绕此作展开。1995年,李福清在牛津大学作文献调查时发现了《新刊全本绣像花笺记残页》,他考辩出此书为明刊本。稍晚,梁培炽的《海外所见〈花笺记〉版本及其国际影响》与杨宝霖的《〈花笺记〉研究》(《东莞理工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梳理了该作品的版本体系,都论及三种英藏版本与汤姆斯(Peter Perring Thoms)的英译本,梁氏更对李氏的“牛津残本为明版”的说法提出质疑。(11)梁培炽:《榕荫论稿》,北京:作家出版社1999年,第23-25页。笔者的《〈花笺记〉在英国的收藏与接受》(《图书馆论坛》2019年第4期)通过版本比勘,印证了李福清的推断,把木鱼书诞生年代推前至明末,并从文本流变,管窥了岭南民间出版业在清代的经营生态。除《花笺》歌本的考证论著,另有《〈二荷花史〉研究》(《文献》2020年第5期)一文,将英藏华翰堂原本与其他版本进行比对,掌握“第九才子书”的文本流变历程,论证此作与巴伐利亚图书馆藏木鱼书孤本《小青记》之间的互文性。
在粤剧方面,周丹杰的博士论文《粤剧剧本的著录与研究》(2018年)不仅考证出大英图书馆藏的20种粤剧是出版年代最早剧本,更利用这批文献详实的考溯了粤剧唱腔板式的源流与发展。
(三)重要藏书家研究
汉籍藏书家的生平经历与学术研究是域外汉籍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收藏活动既是汉籍在海外流通的关键途径,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片段。
在欧洲汉学界,龙彼得是名声卓著的汉籍藏书家,其收藏以闽粤地方戏本与唱本为大宗。李光真的《守护中国民俗的汉学家——龙彼得》(《当西方遇见东方》,1991)以访谈的形式展示了龙彼得早年收集俗曲文献的经历。潘培忠的《龙彼得对闽粤俗文学的研究与贡献》(《文化遗产》2019年第2期)总结了这位汉学家的研究成果,探讨他对闽粤俗文学文献的整理与贡献,并就其收藏中的稀见粤剧、木鱼书与龙舟歌文献的版本情况作介绍与考辩。
综上,现有成果主要考察了大英图书馆与南部三所高校的馆藏,重点考辩知名作品的文本源流与版本情况,并对龙彼得的购藏与学术作了总结性评述。然而,英国还有许多汉籍藏书机构值得关注,更不乏有待深入挖掘的稀见版本与作品;文献本体研究之外,尚可结合档案、书信与报刊等资料,多维度探讨中英文化的交流与互动。英藏广府戏曲文献研究仍存在极大的拓展空间,如能对这批资料加以更好的利用,既可弥补已有研究的空白,也能开掘中国俗文学、广府文学在海外传播研究的学术领域。
四
自2005年以来,《广州大典》在全球范围广泛征集广州文献典籍,其曲类汇编已在2019年出版,影印了海内外24家单位与个人所藏的1589种粤语说唱与粤剧粤曲文献,打破地域空间的限制,为广府曲艺与戏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但整体而言,海内外学界对散藏于英国的岭南曲籍,认识与研讨都比较有限。基于当代研究条件下的英藏广府曲本研究,至少应该囊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编撰完备的总目
目录既是寻访文献的指引,也是揭示书籍及其内涵学术历史性秩序的基础。英国的汉籍收藏机构较为分散,受政策的影响,各馆的中文藏书情况亦有调整;此外,广府曲艺的内部文学系统繁杂,此前的馆藏书目对粤剧与粤语说唱的著录多有偏差,没有凸显版本差异。亟需编撰一部完备的英藏广府曲学文献总目,以明晰的分类、文献的勾稽,方便读者的检索与使用。
在笔者看来,总目的编撰应系统搜罗广府曲籍,涵盖各类文体的多种刊印形式。同时,通过细致化的分类、排序与著录,展示版本间的特性与共性。在“戏曲”与“说唱”两大文献类型之下,将分类细化至最小的条目,突出各文体的特质。排序应以卷端题名为序,一书存两种及以上版本者,均係于最早版本之下。除著录题名、作者、批校者、出版者、藏板、行款、首尾两句与收藏机构等信息,将钤印、夹带信函、题签笔记与国内同版本文献的存藏情况一并载入,并根据不同的文体作相应调整。譬如,粤剧剧本的条目尚应包括戏班、演出者声腔与脚色安排等信息。
在编撰总目的基础上,再谈珍稀版本的具体考证和研究,既可避免遗漏,展现英藏此类文献的概貌,亦能凸显文献自身的相对位置与价值。
(二)跨文本的互文性问题
以往的研究多以单个作品的文本分析与版本考证为主,甚少注意到广府俗文学内部的密切联系。实则,小说、粤剧、木鱼书、龙舟歌互有化用与模仿,同类文体的作品间亦有交流与借鉴,共同编织出一张交互作用的民间文学网络,存在着跨文本的互文性。
随着海外稀见藏本的发现,俗文学之间的互动也渐渐得到显现。因此,如要全面探析广府戏曲与曲艺的文学价值、社会文化与历史文明,必须要打破个体作品的界限,进行跨文本、跨文体研究。譬如,诸如《海瑞奇案》《刘晨采药》等木鱼书均改编自同题材的古典小说或戏曲,粤剧《二荷找珠》与龙舟歌的同名作品均由《二荷花史》中“白莲乔装卖珠女”的反串情节翻演而来,而《西番宝蝶》《朝上莺歌》等木鱼歌本均借鉴与化用了《花笺记》的唱词。这类叙事元素的渗透、再生与传播是中国俗文学生命力盎然的重要源泉。
除此以外,尚可从方言词汇与文化典故,深入探讨清代粤语的发展与风俗制度的演化,以小见大,全方位展示广府文学与文化的特质。
(三)书籍流播史
书籍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域外汉籍的流通是中国文学文化在海外传播与接受的关键途径。作为最早开放通商的口岸,广东是西学东渐的前沿地区,岭南曲类文献在海外的流传亦是近代汉籍流播的缩影。又因英国与香港在近代的密切联系,该国存藏的广府曲籍在种类与数量方面,都要远胜于欧陆的图书馆。通过追寻这批藏书的来源、递藏,对不同阶段的流通特色作梳理总结,以它们的流散勾连汉学家的学术活动与图书馆的发展历程,将其置于世界文化交流与碰撞的研究范域之中,展示中英文化交流史与广州口岸史的不同角度。
(四)接受史研究
首任港督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1795-1890)在谈及英国汉学的发展时曾说:“我以为在处理那些只能被少数人理解鉴赏的高深学问之前,更重要的是,先着手翻译历史、宗教、道德、习俗、文学等方面的著作。”(12)[英]德庇时:《英国汉学起源与发展——19世纪上半叶》,王仁芳译,朱政惠主编《海外中国学评论》第2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57页。的确,对比艰深晦涩的经史之学,通俗易懂、情节生动的俗文学作品更易为19世纪的英国汉学家所接受。
鉴于广州口岸的特殊历史地位,早期英人所接触的俗文学汉籍多为广府刊本,他们的中国纪闻与游记也不乏描述粤剧表演与街头技艺的文字。《中国评论》(The China Review)1872年7月第1卷第1期刊载了英人在香港同兴剧院观看粤剧《阿兰卖猪》的记录与感想;19世纪至20世纪初,汤姆斯与包令爵士(John Bowring)将《花笺记》译成英文,斯坦顿(William Stanton)出版英译本粤剧集;金文泰(Cecil Clementi)、赖宝勤(K.P.Whitaker)和语言学家莫里斯(Peter M.Morris)在不同时期译介了粤讴作品。这些对广府戏曲与俗曲的介绍、翻译与研究的著述数量繁多,是英国汉学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系统梳理英人的相关论著,从西方学术的立场、视角与方法,重新审视广府曲艺的文化内涵与艺术价值,丰富英国汉学史的内涵,为当下的广府俗文学研究提供借鉴。
余 论
得益于珠三角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广府刊刻的书籍较早便通过海运传至域外,粤语戏曲与俗曲也由此流散于世界各地。虽然,法国、德国、荷兰、俄罗斯、丹麦、捷克与葡萄牙等欧洲诸国的图书馆也保存了相当数量的广府曲籍,但它们大多为早期旅华商人、外交官或皇室贵族的私人藏品,部分藏书更于战火中佚失(13)德国柏林国立图书馆的卡尔·阿连德(Carl Arendt)旧藏中国民间俗曲唱本在二战中全部损毁,其中便包括卡尔在广东收集的木鱼书与龙舟歌。,整体收藏呈零散杂糅之状。相较之下,英国图书馆的广府曲类藏书既包含了各界名流的馈赠,也有大量曲籍是馆方利用政府拨款在不同阶段批量采购所得,体系较完善,更不乏孤本与珍本。因此,英国所藏广府戏曲俗曲文献不仅在数量上名列欧洲榜首,更涵盖各年代的不同刊本,文体多样,题材丰富,既可弥补中国俗文学内部的叙事谱系,也为深入探讨粤剧与广府说唱的发展历程与艺术范式提供了充沛的文献资料。
自20世纪初,前辈学人通过不懈的努力,在域外汉籍的诸多方面做出了不凡的成绩。相对而言,英藏广府曲类文献的调查、编目、整理与研究仍需不断推进,让更多庋藏英伦的遗珍重回学界视野,有针对性的探析此前未为关注的稀见版本,结合多元化的研究方法与学术理论,籍此推动文学、史学、语言学与民俗学等既有研究的发展。
本文在追溯广府曲籍西传历程的基础上,对英藏此类文献的编目与研究进行归纳总结,并试图探讨未来可拓展的学术空间,抛砖引玉,以期打开广府俗文学研究的新局面。
——粤语·女独·伴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