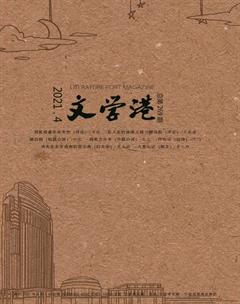一日
樊中泳
人总会在不经意间模糊了真实和幻想,就像这样一个美好的早晨。走廊窗棂下一列阳光,整齐划一地犹如哨兵,门旁的雨伞上,刹那攒动出一个壁虎;路过女生宿舍楼下,麻雀和那些常年昏睡的老狗也正在晨曦中散步。突然间,发现每天走一遍的小路旁,那些草都郁郁葱葱了,而阳光此时则犹如一个画家,躲在云后面,在地上晕出一片片金黄。那柏油马路的黑,倾诉着这片土地的安谧,鳞次栉比的不仅仅是高楼,更是树木和生灵。走进7-11,买了一份早餐,你可以边吃边走,没有人来打扰,服务员的微笑会让你心满意足;一直到图书馆前的树林里,松鼠来觊觎手中的饭团,你大可以分享它一点,只是它却倏地不知道去哪了。我没有太多的留恋,这样的情形时常在东海校园里发生,有时候甚至让我遗忘了怀念为何物,因为近在咫尺,触手可及,却可能在离去后常常神游与此,感叹不已。这片犹如乔托笔下的上帝之城,在一千米外的路斯易教堂顶端被神庇佑着,那些文理大道上来来往往的人,似乎都在赞颂着上帝的垂青和荣光。而我,放慢了匆匆的脚步,用心神去感触每一寸的柔软和细腻,然后心慢慢飘回到那一天的台北,这样的感受是何其相似,何其相似。
有时候,脱离了现实的誊写,你就会进入一种高亢的精神状态,语词和情绪被血液和气味充斥在一起,就像不同宿主的病毒与病毒之间的融合,锻造出生命最原始也最复杂的形象。肉眼和平凡的视角是永远不会体味这样的存在方式,只会被其看似无理性的外表给恫吓并且持械做出无谓的保护姿态,而那团熊熊燃烧的火焰下的这一个人,不会过于理会寻常逻辑下的因果律,仅仅是微笑,仅仅是散发着热和光。很多人称这样的感受叫自由,却更多的人迷失在自由下的迷茫之中而对自由嗤之以鼻;却不明了,常识下大维度的世界是何其的贫乏和单调。那些沉浸在景色与网络羡慕声中的魂灵,完全没有感知到我们存在的哪怕最简单的道理——那些最美的景色,那些最耀眼的夕阳,那些最妄意的旋转和月光下肃穆礼堂旁的吟唱,就是这个道理的最佳阐释,那是我们活下去的理由,因为每当回头,我们都会觉得自己曾经自由,曾经与最爱的人一起,自由。
如果选择一种最好的方式去记录台北,或许就是时间。当某一次不经意间听说艋舺是台北的发源,回忆起那些钮承泽镜头下的台北往事,那些黑白的镜头,氤氲的庙宇和褶皱着却笑吟吟的脸庞,一时间浮上了心头。我不过是在前一天设计了一个剧本,做了几份道具,而一切的展开,其实都是时间和心意。在台北车站,我们不期而遇,同样的等待,一样的欣喜与疲惫,都被某种特殊的情绪抵消掉了。而最完美的一天,从下一站龙山寺开始。
中国的文化孕育了某种庙宇中心论,尽管如今庙宇已非城市的中心,却永远是艋舺的中心,时间的中心。龙山寺的独特魅力,在于台湾本土繁芜的宗教结构,当我们还在疑惑如何掷筊与求签的时候,其實各路神明已经对我们微笑过了。如果说庙宇有什么特别,我说不出,或许这一切要在记忆里找吧,因为远处的剥皮寮也只徒有其表了。那些最真实的存在,或许只能从路上黑黢黢的本地人的脸庞上去猜测了。闲适,安逸,老人家的来来往往,预示着这个破落贵族的持续不破的气性,恰处在这个小岛最繁华的城市边缘。这样再合适不过了,回忆和过去总是美好的,哪怕它如今再低调,也代表了一个过去,一个开端。而我们的下一站,就是代表了现代和过去的交织点,西门町。这是第三次来西门町了,发现西门町的呈现方式,是讲述。当镜头里那个女孩为父母长辈讲述这样一个六十余年的商业中心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了时间的绵久和亲情的感召力。再次路过台北车站,我们匆匆用镜头记录一些别离和相遇,内心或许泛起涟漪,却谁也没有提起。
台大或许是一个憩息之地。太阳匆匆跑过了最高点,然后朝着人们飞袭,让眼睛上流的汗去交换最美的晕染,而风也渐渐盘起,在地上的落叶中回旋着,在空上沙沙地回旋着;台大之于我们,两个行走的路人,是短暂的停留,比西门町和台北车站更值得停留,那是一种自由的味道,无论以何种方式,开始酝酿和扩散。作为台湾的最高学府,却看不到什么高楼,也没有其他学校里充斥着的摩托的轰鸣。椰林大道就像好客的主人,在不经意间回头的时候,让你感到温暖。我们都没有机会读台大,作为外人,会觉得有点破旧,有一点不符身价。却发现其实我们都是错了,那些进出图书馆的学生脸上的微笑,还有手里的书,都是力量无穷的,连给我们拍照片的外国帅哥,都让我们感受到一种细致和周到。兴致是被一颗弹力球引起的,这一点我与他不一样,只是会去怀疑,是否这唤起内心童真的一面摄影机有无记录。人最真的莫过于童年,敢爱敢恨,哪怕不招人喜欢,却自得其乐。如今的我们,哪怕周身黄金,名满四海,却总是束手束脚,何况我们更多的是被内心的期待所束缚。小小的一颗弹力球威力如此,或许是连她都没有注意到的。我们俩其实都喜欢学校,徜徉,夕阳,椰林,还有自行车的铃声。说不定会在某个角落邂逅,或者会在某本书中获得解放,一切皆有可能,相比于门口熙熙攘攘的公馆夜市,水源市场,在路边喝着五十岚聊天的时候,我们的心或许还在台大的校园内,幻想着一切最美好的青春和走过的路。
台湾人夸台湾,最多的一个词语就是自由。他们并不知道自由的维度,精神状态,政治权利,自由的限度和可能的形式,他们只是说自由,八里电信店里偶遇的女孩子这么说,莱尔富的店长这么说,花莲民宿老板这么说,郭老师这么说,台湾的同学介绍的时候也这么说。每个人都有一种自由,我也有。这种自由曾经弥漫在淡水码头金色的夕阳之下,曾经流连在淡水中学最深的巷子之内,还有路小雨的家;曾经驰骋在南部最蔚蓝的太平洋和印度洋的交界处,吞噬了风的猛烈与不羁;曾经旋转在高雄最黑暗的夜中,闪烁在城市之眼的最高点;也曾吟游在清境古堡的山巅,化作最炽烈的热雨,温暖每一片迷惘而落寞人的心田。它出现在宜兰的海滩之上,黑色的沙砾,流逝指尖;也曾飞翔在杨梅山头的速降坡,用淡水河的歌声召唤,一个疲惫而兴奋的骑车人;它与神翩翩起舞在大肚山山麓,也与日月共舞在岛中心的潭水之间,以及阿里山高山族人的歌声之中。它这样的来去匆匆,这样的若隐若现,我们或许会感激,或许会忽略,无论如何,时间那么久,最后只留下了感觉。而当这一切在自由广场又被唤醒的时候,突然意识到我们来到了圣地,来到了这一切的渊源。
夕阳打在中央大剧院檐角,散落了自由广场一地,踩着光晕的碎片,没有牵手,我们默默地前进着。或许是黄昏应了心境,她说:下次你来台湾的时候,每一个地方,都会想起我。眼前的景吞噬了无意义的言语,那些广场上升腾的鸽子的背影,自由在广场上散步,我没有回答,脑海中却蓦然回想——清境被一片树叶惊吓到扔掉了佛珠,风吹砂速降坡害怕得差点攥下我的裤带;是在名统九楼吃完饭一起看照片,走出来的时候忽然看到了海;是在逢甲夜市嫉妒到拒绝吃熊手刈包,又在邀请吃洋槐冻的时候被同等拒绝;是来台第一次见到时候的欣喜与胆小,语无伦次在台北到罗东火车上的故作镇静;是在宜兰民宿里默默地心中扼死襁褓,写下最无助的谢谢你;是在八里码头大声喊,操,终于到了,又在淡江大学图书馆门口的板凳上与小天使一起等待;在台中沿路偶遇一席人,惊说这世上真有缘分;是每一次的微笑,是每一次的拒绝,是我的疯癫还有你的眼,是你的欲说还休和我的死皮赖脸。夕阳慢慢落下,慢慢在我们身上落下,我的回忆被这一片抓不住的宽阔击碎。不敢触碰,不敢说,任风吹去,吹成一片。在人生最美好的季节,遇到彼此,融化在台湾的每一个角落,最真诚的交谈,最真挚的追逐,最投入地去爱,最努力地去改变。在这青春的最后岁月,遇见了最好的记忆,遇见了自由。
夕阳还燃烧在天边,而月亮则升起在另一边。这夜与日,天与地的交织,太美丽。两旁的大戏剧院和大音乐厅升腾起了红色,让这一片深蓝和金黄的交织更加炽烈。广场上的旗帜,慢慢下降,那一队士兵,渐渐消失。留下人们的笑言和默语,留下天上的那片云,慢慢散去。我会记得,爱与被爱,怀念的过去和憧憬的未来,都在这一刻停止。你只要在自由广场上飞奔,跳跃,欢笑,旋转,甩发,牵手,登高,歌唱,自由便无处不在。当爱与自由在广场上被黄昏融为一体,那些最浅显的执着和最无意味的言语都成了嘲讽的对象。没有人在意这样的时刻是否说出了我爱你,或者相拥相吻,只要见证着自由广场一段日落和中正纪念堂上月亮的初升就足以迷醉一整晚。那些错过的,遗憾的,曾经的,未来的,失去的,拥有的,都被日月同在锻造成了一块碑,插在内心最柔软的地方。于是,剧本被设计了,然后被遗忘了,场景出现了,然后被揉进了最习惯的行为方式之中。那就是自由了。
或许还要留下最后的诗。太紧张。《The Rose》是我第一首推荐给她的歌吧貌似。没想到我竟然就在这里唱了。
Some say love, it is a river,
That drown the tender reeds;
Some say love, it is a razor,
That leaves the soul to bleed;
Some say love is a hunger,
An endless aching need;
I say love it is a flower,
And you it's only seed.
……
她的名字,就是此刻或者未來不变的回忆,或许会在记忆里浓墨重彩,或许刹那芳华。
或许,以后学会不去纠缠那些逝去的时光的时候,当你回头时,我还在自由广场,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