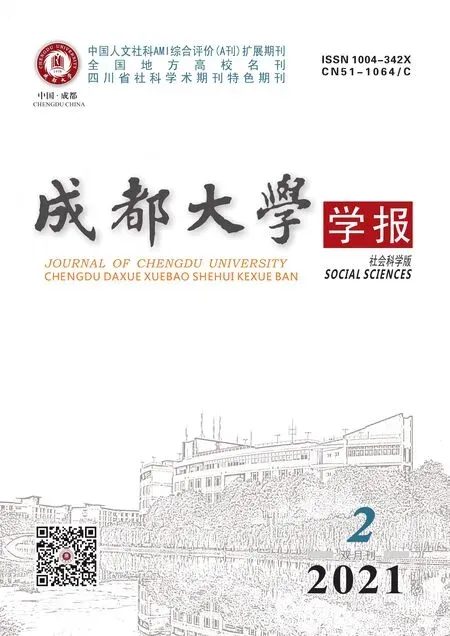如何读一首现代诗?*
——以朱湘《雨景》分析为例
张桃洲
(首都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048)
如何读一首现代诗?这应该是一件见仁见智的事。就笔者的阅读习惯而言,读一首诗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细读”(close reading),这并非一般性的赏析,也不是一种随意的蜻蜓点水式的读后感,而是进入诗作的文本内部,对其词句、语调等内在“肌理”进行剖析;它要采用瑞士文论家乔治·布莱(George Poulet)所说的“我思”[1]的方式,让思绪在诗的文本里走动,揣摩、跟踪语词的流脉和气息。另一方面是把作品放在它产生时的历史语境中,放到作者本人创作的总体格局里,即不是孤立、抽象、封闭地对一首诗进行读解,而是尽量把它上下左右周边的关系、因素引进来,也就是增强它生成的“历史感”和“方位感”,以便更清晰地把握它的构成和线索。那么,是不是每首诗的阅读都亦步亦趋遵照这样的步骤——先条分缕析地从词句入手把它剖析得“体无完肤”,再由文本扩散开去、勾连相关背景进行解说,最后收拢起来回到诗作本身、聚焦于其主题意蕴等?似乎也未必。现代诗的一个特点是:每一首诗就是这“一首”,从内容到形式、从主题到结构,是自成一体的,也是不可复制的。因此同样地,读一首现代诗就有读这首诗的独特方式,也许可以相互借鉴,但不能完全照搬读其他诗的办法,比如读冯至的《蛇》和读周作人的《小河》的方法是不一样的。
下面笔者通过分析朱湘的一首短诗《雨景》,进一步阐明自己关于读现代诗的一点想法。全诗如下:
雨景
朱 湘
我心爱的雨景也多着呀:
春夜梦回时窗前的淅沥;
急雨点打上蕉叶的声音;
雾一般拂着人脸的雨丝;
从电光中泼下来的雷雨——
但将雨时的天我最爱了。
它虽然是灰色的却透明;
它蕴着一种无声的期待。
并且从云气中,不知哪里,
飘来了一声清脆的鸟啼。
1924年11月22日
(原载《草莽集》,开明书店1927年版)
这首《雨景》被认为是朱湘的代表作,虽然篇幅短小,但在朱湘诗作以至20世纪20年代新诗中占有特殊的位置。众所周知,20世纪20年代仍然属于新诗的草创期,新诗自诞生之初直至20世纪20年代中期,一直遭受着“浅白”“不定形”等指责;不过随着徐志摩、闻一多、朱湘、冯至等的出现,新诗创作及其形象发生了很大改观,一个显著的体现是语言趋于纯熟、形式上也逐渐“成型”。这是新诗寻求“艺术”的结果,诗人们在语言的锤炼、形式的锻造方面,做了很多努力,极大地丰富了现代汉语的表现力,让现代汉语显出自身的特性和美感。也就是说,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新诗创作中开始出现周作人在20世纪20年代初所期待的“美文”的苗头了。周作人当时引入并倡导这个概念,实际上就是想呼唤现代汉语的书写能力。朱湘的诗也汇入了那股寻求“艺术”的潮流中。
梳理20世纪20年代中期新诗的基本情形,对于理解《雨景》的语言、形式特点很重要。只要看看当时徐志摩、闻一多的诗学主张(徐志摩:“我们觉悟了诗是艺术……一首诗应是一个有生机的整体……字句是身体的外形,音节是血脉,‘诗感’或原动的诗意是心脏的跳动,有它才有血脉的流转。”[2]闻一多:“我更不能明了若没有形式艺术怎能存在!……我们要打破一个固定的形式,目的是要得到许多变异的形式罢了。”[3]),就能够领悟那场由他们发起、朱湘也参与其中的新诗“形式”运动的意义了。朱湘很推崇早逝的诗人刘梦苇,认为后者是“新诗形式运动的总先锋”[4],当然他本人的诗歌很大程度上是践行了那场运动的一些理念的,在他所说的音韵、诗行、诗章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雨景》正是朱湘探索和实践的一个突出例子。尽管这首只有10行的小诗看起来语句清浅、诗意透明,似乎没什么值得深究的地方,但仔细分析还是可以理出不少东西的。这里,在细读这首诗之前,还需要稍微了解一下朱湘这个人。也许人们对这位英年早逝(1904—1933)的诗人的生平、求学、工作经历等并不陌生,流传最广的大概是他充满悲剧性而又颇具浪漫色彩的生命结局(据说他是在上海往南京的轮船上吟诵着海涅的诗歌跃入江中的)。他的诗歌成就毋庸置疑:一方面,他出版了《夏天》《草莽集》等多部诗集,是1920年代尝试和深化“新格律诗”的重要诗人;另一方面,他有很高的诗学理论素养,他的《中书集》里有多篇诗评,显示了他对新诗及诗人的独到眼光和精辟洞见;此外,他还翻译了不少外国诗人的作品。不过,我格外留意的是朱湘的其他两个方面:一个是他的性格,孤僻、桀骜不驯、耿直甚至“急躁”,是人们对他性格的描述;另一个是他在工作、生活特别是家庭中的窘境,涉及人际关系、亲情、经济等诸种因素。这两方面对于全面了解朱湘这个人是不可或缺的。
由上所述我们也许不难产生一种直观的印象,就是觉得朱湘的人生中充满了紧张感,他可谓命途多舛,生活中不时伴随着挫折、冲突和压抑。然而,通观他的诗歌写作和翻译,还有他的散文和诗学论评,全然不见一丝因受苦而滋生怨愤的印迹,也没有各种矛盾、困窘所导致的“一团糟”(无序)场景,相反地,其作品的“文字之优美精致,情调之从容宁静”[5],令人赞叹不已。尤其是他的诗歌作品,行句严整、语调柔和,既有《摇篮歌》的深情款款,又有《采莲曲》的摇曳多姿。由此,在他的人、生活和诗之间,就呈现出某种“张力”甚至强烈的“反差”。这正是沈从文论及朱湘时指出的:“作者在生活一方面,所显出的焦躁,是中国诗人中所没有的焦躁,然而由诗歌认识这人,却平静到使人吃惊。”[6]对于这一点有必要再细说一下。
按照一般设想,一则朱湘的脾气比较“暴烈”,与人略有不合就翻脸(从他求学到工作,这方面的事例比较多,其中他和“新月派”同人之间的纠葛,兼有私人恩怨和诗学观念分歧的成分①);再则他的个人境遇、家庭生活算不上顺畅、愉悦,在多重压力下难免会生出焦灼感和厌烦感——如此一个写作者,很可能他写出的作品要么充满了焦躁不安或灰暗低沉的意绪,要么满纸是饱含着忿懑乃至戾气的文字。这样的设想有其合理之处,因为一个作家很难不把他的个性、人生体验、生活态度、与周围环境的复杂关系,以及他的憧憬、失落、焦虑等情绪(特别是给其带来重大影响的负面因素),投射到他的写作中去。可是,我们在朱湘的诗里很少看到刻意渲染的阴霾。这并不是说他的写作完全抹去了尖锐的东西,他的诗里也多次言及“虚空”、死亡,喟叹人生晚景的凄凉(《残灰》),甚至鞭挞“丑恶”(《热情》:“我们发出流星的白羽箭,∕射死丑的蟾蜍,恶的天狗。∕我们挥彗星的篠帚扫除,∕拏南箕撮去一切的污朽”)、嘲讽“虚伪”(《扪心》:“最可悲的是∕众生已把虚伪遗忘;∕他们忘了台下有人牵线,∕自家是傀儡登场”),但他所抒发的并非一己之怨,而且没有让自己的情绪损害诗歌语言、形式的完整和饱满——其间隐然包含了某种“形式的政治”的“偏执”。②
这里有一个疑问:内心焦灼的作者是否必然会创作表现剧烈冲撞的作品(如陀思妥耶夫斯基)?诚然,富有个性,甚至有一点“怪癖”的人,其思想习性、行为风格多少会影响其文字表达方式,使之或绵密纤细(如普鲁斯特)、或艰涩迂回(如克尔凯戈尔)。但这种“正向”的关联不是绝对的,因此“痛苦的作者写出的作品必然是痛苦的”这个推论或预设是需要商榷的。当然,也可以反过来追问:一个在生活中充满紧张感的作者,被要求非常从容地写作,或者希望他的作品是舒缓、流畅的,其难度是否会加倍?这个问题其实也不会有定论。之所以如此反复辨析,是为了指明,朱湘的性格、生活境遇和诗歌创作之间的“张力”,是不应回避而是值得考量的(显然也不必过分强调)。在很多评述里,朱湘的诗歌被比较笼统地视为具有唯美倾向③,倘若比照朱湘的性格和生活,就会感觉他的唯美追求确实非常鲜明——无论在诗歌创作还是翻译、评论上④。最终,他就如同英国诗人奥登(W.H.Auden)悼念爱尔兰诗人叶芝(W.B.Yeats)的诗中所描述的那样:“靠耕耘一片诗田∕把诅咒变为葡萄园。”⑤
不过,说到朱湘诗歌的来源,实际上除了西方浪漫主义诗歌之外,还有中国古典诗词、民间文艺等。比如他的名作《采莲曲》,其标题就来自中国古代的乐府诗,诗篇中谣曲式的“一唱三叹”的韵律、活泼轻快的调子,也不是单纯取法于中国或西方诗歌的某一流派,而是博采众长(包括民歌的因子)、融会贯通,显得极为自如,从而拓展了1920年代“新格律诗”泛泛追求的词句的匀称和音节的和谐。可见,他对各种诗学资源的吸取是十分自主的,因此他诗歌的唯美倾向就不是单一的,至少还包含了古典诗歌的情致。
为了介绍《雨景》的相关背景,笔者在前面扩展开去讲了朱湘的性格、生活境况和他的诗学观念等,这样的迂回还是很有必要的。由此,我们进入这首诗的文本内部就有可以参考的坐标系了。那么,如何进入这首诗的文本?第一步当然是看标题——《雨景》,这个标题提示读者它应该是一首写景的诗。从题材类型来说,“写景”在中国的诗歌传统里是非常普遍的,每个人阅读视野里相关作品应该不少(“大漠孤火烟直,长河落日圆”“枯藤老树昏鸦”,不胜枚举),对于写景的诗如何写景、具有什么样的形态,可能会形成一个预期,总想到“情景交融”“寓情于景”“一切景语皆情语”之类,在古典诗歌里基本上形成了套路。可是,对于现代诗来说,如何写景是另外一个问题。在新诗的初期阶段,胡适《谈新诗》提出了“具体的写法”的主张,认为新诗要写一些具体可感的景和物,不过他以及同时期康白情等写景、写物的诗都比较简单。而到了朱湘的《雨景》这里,新诗写景的面貌就开始出现变化了。此外,这首诗写的是“雨”之景,雨在诗里也是一个常见的书写对象。在古典诗歌里,大自然中的风霜雨雪、季节里的春夏秋冬,相关的诗作可谓不计其数,写雨的诗非常多。面对强大的古诗传统和显得“俗滥”的“雨”这个题材,新诗如何以自己的方式处理并且显出“新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进一步说,早期新诗写景、写物要是有了自己的特色,也是为新诗的立足乃至地位的稳固作出贡献。就此而言,《雨景》处在早期新诗写景的一个重要“节点”上。
需要说明的是,《雨景》在收入《草莽集》之前还有一个版本(见于朱湘给梁宗岱的信中),兹录如下[7]26-27:
我所心爱的雨景也多着哪:
午夜梦回时忽闻的淅沥;
爽的,如轻纱拂面的毛雨;
夏晚雨晴时的灿烂日落;
以至充满了“不可测”的雷雨——
但欲雨的阴天我最爱了:
它清如王摩诘的五言律诗,
它是一块凉润的灰壁,
并且从寥廓的云气中,
不知是哪里,时飘来一声鸟啼。
不难看出两个版本之间的差别还是很大的:修改后没有分节、句子更凝练整齐、用词更富现代色彩等,最重要的是改换了“它蕴着一种无声的期待”这句。当然,对二者还可以做更细致的对比分析,但这里暂且搁置,将讨论的重心放在修改后的文本上。先整体上浏览这个改过的文本就会发现,它虽然取消了原有的分节,但仍然包含了两个明显的段落(或层次):以第五行中的破折号为界线,前后各5行分别构成了第一、二个段落(或层次);然后,两个段落里如果进一步细分的话,各自还会有更小的层次。划分如下:

第一个段落写“心爱的雨景”,由首句直接点明,第一行代表一个小层次,后面并列的四行是另一个小层次。“我心爱的雨景也多着呀”,开门见山引出后面四行对“心爱的雨景”进行具体说明或描绘——“春夜梦回时窗前的淅沥”“急雨点打上蕉叶的声音”“雾一般拂着人脸的雨丝”“从电光中泼下来的雷雨”,这四行呈现了不同的雨景,描画了四种雨的声音和样态。那么,这是雨的古典表达还是现代表达呢?诚然,字里行间洋溢着古典的氛围(“春夜梦回”“雨打芭蕉”),但透出更多的是现代的气息,因为这四行诗的句法是很现代的:倘若采用古诗整饬的句式,这四行诗的句子结构可能会完全相同,但事实上这四行诗的句子结构是富于变化的——既有“淅沥”的雨滴,又有“打上蕉叶”的“急雨点”,还有“雾一般拂着人脸的雨丝”,以及“从电光中泼下来的雷雨”,每一种雨的形态的描写在表达方式上是各异的,前面两种侧重于听觉、后两种侧重于视觉。这正是现代诗的个性化的表达,调动了视觉(“从电光中泼下来”)、听觉(“淅沥”)、触觉(“雾一般拂着人脸”)等感觉方式(还有“急雨点打上蕉叶的声音”是视觉和听觉的融合)。需要留意的是,为调动这些感觉,“雾一般”比喻句和“拂”“泼”两个动词的运用,增强了形象感和感染力。可以说,这一段落所写的“雨景”是形态各异的,其表达方式也各不相同,给读者唤起的感受是很不一样的。
诗人在呈现不同“雨景”之后留下了一个悬念:接下来会写什么呢?第二个段落没有继续写雨景,而是忽然转入了“将雨时的天”。“但将雨时的天我最爱了”,这句诗的首字是一个“但”,体现的是一种转折,是在上个段落“我心爱的雨景也多着呀”中“多着呀”的基础上的转折和提升,这就使得上个段落的五行全部构成了一种铺垫,即它们是为“但……”的现身做准备的。一个“但”字,表明诗的重心和指向都要发生转变了,这一句的语调格外值得揣摩,从“我心爱”到“我最爱”,其中包含了一种程度的强调。紧接着的两句是对“将雨时的天”的说明:“它虽然是灰色的却透明∕它蕴着一种无声的期待”。跟前面对雨景的描绘一样,前一句颇具画面感,令人脑海里浮现出一幅灰色而透明的天空下风雨欲来却宁静的景象,那应该是在生活中较常见的。这两行诗都用了“它……”的句式,看起来并列在一起很对称,但实际上它们不是对称的:前一句是有形的(“灰色”“透明”),后一句是无形、不可见的(“无声的期待”)。重要的是,“它蕴着一种无声的期待”,“蕴着”和“无声的期待”本身,预示了诗意进一步展开的可能,于是随后出现了两句:“并且从云气中,不知哪里,∕飘来了一声清脆的鸟啼”,诗就在这里戛然而止了。
至此可以看到,在第一个段落和第二个段落之间以及第二个段落内部,诗意是处于不断蓄积和递进的状态的。到全诗最后戛然而止时,“一声清脆的鸟啼”——最重要的事物出场了,给人以石破天惊的感觉。这一声鸟啼既打破了景致的静止格局,又改变了“无声”“期待”的心理状态。不妨将两个段落的景物转换及心理变化图示如下:
“雨景”(“心爱”)→“将雨时的天”(“最爱”)
∟“无声的期待”
→“清脆的鸟啼”
虽然第二个段落里,由“并且”连接的两个小层次之间,也许只是一种较“弱”的、非直接的递进关系,但由于“清脆的鸟啼”及其效应(“鸟鸣山更幽”)十分明显,它的出现不仅将前面的“雨景”迅速变为背景,而且扩展了“无声的期待”的心理空间。这样,全诗更像是一种“扬(放)—抑(收)—扬(放)”的精心架构:率先展示的四类恣肆的“雨景”实则仅是铺垫,它们聚集的情感(“心爱”)被收束在“最爱”(对于“将雨时的天”)之下,然后在“无声的期待”中映衬出“清脆的鸟啼”的现身,最后的重心落在“鸟啼”上。当然“鸟啼”也可被看作“雨景”的一部分,或者说它是另一种意义的“雨景”——鸟儿展翅翱翔的身影隐匿在视线之外,只闻其声不见其形——如此则深化了标题“雨景”的含义。
以上是对《雨景》所做的层次分析,是一种整体结构上的把握。就形式而言,这首诗尽管外形是严整的,但各个句子结构又是变化的,每一行的句式都不一样。另外,它的形式特征还有三个方面需要进一步探究:其一是语气,其二是音韵,其三是标点符号。
首先来看这首诗的语气,主要是两处值得留意,分别是每一个段落的首行,即第一行和第六行。先看“我心爱的雨景也多着呀”这一句,倘若换一个说法“我心爱的雨景也很多”,意思似乎没有太大改变,但语气就很不一样了。需要细细品味的正是“多着呀”中的“呀”,这个语气词决不是可有可无的,也不是随随便便就用的。可以体会一下,“呀”这个轻柔的词念出来,是不是带来一种清新、欢快甚至是喜悦的感觉呢?上文曾提及朱湘个性刚烈、急躁的一面,但这个“呀”字显出他温和、轻松、洒脱的姿态,也反映出他内心的单纯与朴直,与苦大仇深、愁容扑面、浑身戾气、满腹牢骚一点也不沾边。同样,第六行“但将雨时的天我最爱了”(作为承上启下的一句)中的“了”字也值得揣摩。这个语气词也绝非可有可无,倘若去掉这个“了”字(变为“但将雨时的天我最爱”),或者改成“但将雨时的天是我的最爱”“但我最爱将雨时的天”,意思可能差不多,但这几句跟原文之间的语气差别很大,无疑都不及原文,原文里的微妙气息、味道在改写的句子中荡然无存。这两个“不起眼”的语气词的运用,也引发思考:一位诗人如何更准确、更有效、更细致入微地传达自己的意绪?在朱湘这里,他对情感的表达使用的不是“我好喜欢”“我好悲伤”或者“我很愤怒啊”“我很孤独啊”这样直抒胸臆(有时难免空洞)的方式,而是一些委婉的、层次丰富的句子,并加入了能够贴合人感受的语气。通过对比可知,在诗中如果情绪的表达只是一种直来直去的呐喊,那么其感染力将大打折扣。
有必要指出,像“呀”“了”这样的助词和虚词,在古典诗歌里是难以入诗成为诗语的,但在现代诗里得到了广泛运用,原因是它们在细化时态、增强语气、引申意味等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语气和语调是现代诗中必不可少的“调节器”,正如俄国文论家巴赫金(M.Bakhtin)所描述的:“生动的语调仿佛把话语引出了其语言界限之外”[8],也就是语调能够激发语言的“弦外之音”。从“呀”“了”的使用也可以知晓,《雨景》中对词语的选用是十分讲究的。前面已经提到了“拂”“泼”“但”“蕴”等,还有一字或可一提,就是“飘来了一声清脆的鸟啼”中的“飘”。“飘来了”其实是“传来了”之意,但二者的区别是明显的,一个“飘”字,更能传达“鸟啼”的飘逸、轻盈。
其次是这首诗的音韵。作为“新格律诗”的实践者,朱湘非常重视诗的音韵。虽说朱湘自称《雨景》为非“自觉”的“无韵体”[7]120,后来一些研究者也跟着说它没有用韵,但这首诗其实还是使用了脚韵的,并且它们还协助着诗意的进展。该诗的一个基本脚韵是“i”韵(“淅沥”“雨丝”“哪里”“鸟啼”),此外还有“in”韵(“声音”“透明”)、“ai”韵(“最爱”“期待”)。“i”韵在声音上的特点是趋于“闭合”,音质上比较纤弱、轻柔,不如“an”“ang”这样的韵敞亮、有力。由于“i”韵的闭合,它在情感的传达上比较收敛、抑制,不像“an”“ang”韵那么张扬、奔放。如果把这个用韵特点与前面分析过的诗句语气联系起来,就能够体味诗中情绪更细微的地方:一方面如上所述,“我心爱的雨景也多着呀”“将雨时的天我最爱了”这两句的语气所释放的情绪,应该是十分单纯而欣悦的;但另一方面,此诗的主要脚韵“i”韵,又给人一种收束、克制的感觉,这似乎暗示了,《雨景》里的情绪也许并非一种纯然的欢快,而是夹杂了一点淡淡的忧郁的因子。这大概也是陈梦家曾指出《雨景》“在阴晦中启示着他的意义”[9]的缘由吧。不过,总体而言朱湘在诗里并未刻意渲染这种情绪,毋宁说他是借助“i”韵,避免了诗中的欢快之情流于夸饰甚至泛滥。
再次是这首诗里标点符号的使用。在现代诗中,标点符号并非必需,其使用与否没有一定之规,一般根据诗人的习惯和诗作的具体情形而定。如果一些诗作使用了标点符号,就应该予以一定的关注,不能无视它们的存在。《雨景》里的标点符号似乎格外费了心思,短短十行却用了多种标点符号(冒号、分号、破折号、逗号、句号),显得十分丰富,并且每一种标点符号都有各自的功用。比如第一句“我心爱的雨景也多着呀:”末尾的冒号,很显然起到了提示后面内容的作用;第五句“从电光中泼下来的雷雨——”末尾的破折号,就像一道“分水岭”一样隔开了前后两个段落,也起到了一种提示、启下的作用;第二、三、四、七句的末尾运用了分号,使分号前后的句子之间构成了一种并列、彼此呼应的关系。还有一处特别值得留意:这首诗的10行中有9行是单句,另外的一行(第九行)——“并且从云气中,不知哪里”,是由两个短语构成的,二者之间是一个逗号,这个逗号的用与不用、用后的意味,值得细细品评。与此相似的可以举一个著名的例子,戴望舒的四行短诗《萧红墓畔口占》的第三行“我等待着,长夜漫漫”也是这样,两句中间用了一个逗号。其实,“并且从云气中,不知哪里”和“我等待着,长夜漫漫”各自中间的逗号也可以去掉,从语义来说没有太大的改变和损失,但使用之后产生了很不一样的效果——主要在语气和语感上。如同乐曲里的休止符,两个诗句中间的逗号起到的是语气停顿的作用。为什么要停顿一下?停顿带来了一次间歇,一小段时间的空白,其间隐含着某种情绪的蓄积,酝酿着语气的转换,是语气稍作停驻后即将延展的前奏。如果将这两句诗轻声诵读出来,就能体会到其语感的微妙。顺便指出,“并且从云气中,不知哪里”这两个前置状语,在句法上应该是受到了“欧化”的影响。
前面进行的主要是《雨景》形式层面的分析,这种略显琐碎的分析意在表明,一首看似简单、“透明”的诗作也有繁复的内在“纹理”,需要仔细的辨察和适当的解读路径。不过到这里为止,我们没有对《雨景》一诗的主题进行阐释。谈到这首诗的主题,最直截了当地说就是写“雨景”(既有“我心爱的雨景”,又有“我最爱”的“将雨时的天”——也是“雨景”的一部分),同时写“雨景”连接着的个人情绪。虽然这似乎仍然没有脱离“景语”“情语”“寓情于景”的套路,但如前所述,此诗在写“景”抒“情”的方式上跟古诗大相径庭。倘若深究下去,就会发现有两个物象的意蕴主导着全诗的主题:一个“将雨时的天”,另一个是最后一行里的“鸟啼”。
这两个在诗中格外醒目的物象,上文已有所分析。“将雨时的天”是在四种“雨景”的烘托下出现的,是诗人笔锋一转、抑中带扬的产物;“将雨时的天”和“鸟啼”都与“无声的期待”具有某种关联:“将雨时的天”“蕴着”“无声的期待”,在“无声的期待”中迎来了“清脆的鸟鸣”;那“将雨时的天”大概寄寓着诗人对于人生的憧憬,而在以往的研究中,“鸟啼”的内涵受到更多的关注。“鸟啼”无疑是整首诗的诗眼,是展现全诗主题的核心。当然,“鸟啼”的分量尽管很重,但不必对其内涵进行“过度诠释”。比如,有人联系《雨景》的写作时间是1924年冬天,就引入英国诗人雪莱(P.B.Shelley)《西风颂》里的名句“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把“鸟啼”解释为某种社会革命即将到来的预言或象征,因为第二年(1925年)“五卅运动”就爆发了,革命的浪潮开始涌现并逐渐高涨……这样的阐释或许无可厚非,但溢出了《雨景》这首诗自身的语言形制和文本取向,也不符合朱湘本人的精神气质和诗学观念。相比之下,孙玉石先生对它的阐发更为合理:“这声音,使人得到了一种生气,一种美感,一种期待中出乎意料的获得。”[10]因此,仍然有必要将对“鸟啼”的理解和阐释限定在此诗的文本逻辑之内,注重“鸟啼”的“清脆”音质所蕴含的“美感”。《雨景》的最后两行犹如“神来之笔”,“鸟啼”可视为诗人内心的灵光乍现带来的一种情绪上的飞跃,是由宁静的欣悦和“无声的期待”生发出来的生命“天籁”。全诗的主题即止于此。
《雨景》向来被称誉为中国现代“写景诗”的杰作之一。前面说过,“写景诗”从古至今都是一种重要的诗歌类型,亦可将《雨景》置于“写景诗”的发展脉络里予以考察,其中关涉到自然(山水)、观看、物我关系等议题。按照日本理论家柄谷行人的说法,“风景是和孤独的内心状态紧密连接在一起的……只有在对周围外部的东西没有关心的‘内在的人’(inner man)那里,风景才能得以发现”[11]。当代诗人张默则认为:“咏景诗并不易写,并非一个作者把他所见到的景物一一铺陈在他的诗里就算了事……他必须努力使自己的灵视进入到他所表现的风景之中,他所看到的一花一木,一草一石,不仅是各各地站在大自然栩栩如生,尤其要把它们很轻巧地移植到作者的心灵世界里去。使它们变成作者身上的一部分,与作者的精神层面紧紧结合在一起。”⑥这些表述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雨景》中不同景致(四种“雨景”、“将雨时的天”和“鸟啼”)的意涵。此外,从《雨景》的主题层面,可看出朱湘勉力超越现实生活处境的另一向度——对于生命之“美”和“纯粹”的坚执,这应当是其“形式的政治”的延伸。或者说,此诗的形式与主题是互为表里的:以语词的锤炼和对“美感”的追寻,拒斥此前部分诗歌写作的“自白”式的粗放与狂乱。
以上就《雨景》主题所作的辨析,也是试图显示笔者关于阅读现代诗的主张:解析一首诗的终极目的不是通向一个结论式的判断,尤其是诗的主题分析,任何一首诗的主题总是多重的、开放的,不宜拘泥于某个具体的“点”上,这样阅读就表现为对诗作的聚光灯般的多维审视;进而言之,无论“简单”或复杂的诗作都有各自的读法,读诗本身是一种过程,是一种基于诗的文本的“我思”——对词语构造和生命脉动的不断感知。
注释:
①有人认为朱湘属于“新月派”,有人否认。关于二者关系的讨论,可参阅郝梦迪:《朱湘与新月诗派的关系考辨》,《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18年第1期。
②朱湘后期诗歌(收录于他身后出版的《石门集》《永言集》)中尚有一些激愤的讽喻之作,如《一个省城》《误解》《人性》《收魂》《四行》《三叠令》《回环调》《巴俚曲》《兜儿》等,值得注意的是它们在主题上趋于繁复,较朱湘以往的诗有很大不同,其中的一部分在借鉴外国诗体(triolet、ballade、rondel)方面有独特的价值,这些都需要专门讨论。
③赵毅衡说:“朱湘几乎从来不把个人情绪放到他的写作中去……为我们挽救了一个唯美的诗人。”见赵毅衡:《留学民族主义?——朱湘的留美之怒》,《文学界(专辑版)》2007年第3期。
④需要指出,朱湘的唯美追求与从戈蒂耶(G.Gautier)到王尔德(O.Wilde)的唯美主义潮流的关联并不明显(虽然他评述过王尔德的剧作《莎乐美》),而更多地源自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影响。
⑤奥登:《悼念叶芝》,见查良铮译《英国现代诗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1页。
⑥张默:《谈咏景诗》,转引自叶维廉《五官来一次紧急集合——略谈张默的旅游诗》,见张默《独钓空濛》,九歌出版社,2007年版,第3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