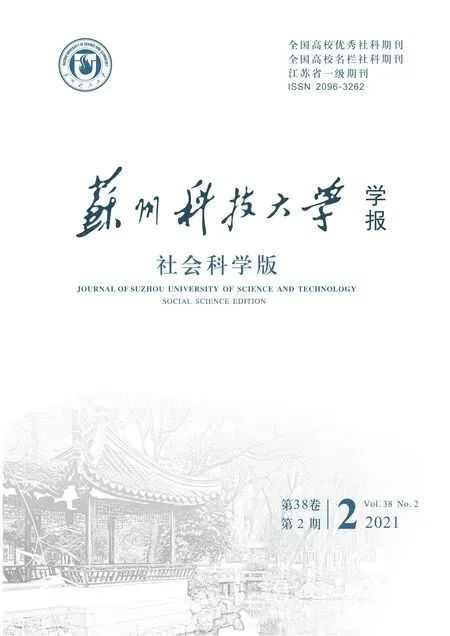《浮生六记》海外接受中的文体属性与叙事结构之争*
孟祥德
(苏州市职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苏州 215104)
沈复《浮生六记》(以下简称《浮生》)在中国典籍英译、海外传播中有着独特的地位。首先,译本多样。林语堂1935年春夏间首译《浮生》,1960年马士李(Shirley M. Black)次译,1983年白伦(Leonard Pratt)、江素惠(Chiang Su-hui)合译,2011年孙广仁(Graham Sanders)复译,共有4部不同的译本。这样一来,“既有本土译者的独译本,又有域外译者的独译本,更有中外译者的合译本”[1]。其次,译者背景不一。译者或为翻译家,或为学者,或为作家,或为汉学家。再次,译序等副文本信息丰富。既有对原作的赏析、评价,也有翻译策略的介绍等。最后,海外传播广,研究深入。截至2017年2月,全球计有上千家图书馆收藏英译本《浮生》,侧面反映出该书在海外的传播状况(见表1)。自1970年代至今,十多位海内外学者专门撰写了英文论文,探讨《浮生》的诸多问题。因此,对于这样一部作品,无论是在文学批评上,还是在翻译研究上,都有特别的价值。

表1 《浮生》各英译本国内外图书馆收藏情况
2005年,王人恩、谢志煌发表《〈浮生六记〉百年研究述评》,2006年黄强发表《〈浮生六记〉百年研究述略》,2017年梁林歆、许明武发表《国内外〈浮生六记〉英译研究:回顾与展望》,对《浮生》研究做了阶段性总结。(1)详见王人恩、谢志煌《〈浮生六记〉百年研究述评》,《甘肃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第136~144页;黄强《〈浮生六记〉百年研究述略》,《扬州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第3~8页;梁林歆、许明武《国内外〈浮生六记〉英译研究:回顾与展望》,《外语教育研究》2017年第4期第53~59页。然而,纵观这些研究,发现有关《浮生》海外研究的介绍缺失。“浮学”的研究现状是:国内相对热,国外相对冷;林译《浮生》热,他译《浮生》冷;国内研究国内热,国外研究国内冷。在中国文化日益“走出去”的今天,“第三只眼”——海外视角显得尤为重要。
《浮生》的海外研究有两个突出的争议点:文体属性与叙事结构。前者关乎名分,后者关乎艺术价值,二者紧密联系,息息相关。国内研究对前者也展开过系统而深入的探讨,对于后者则缺乏关注。鉴于此,很有必要将海外研究的成果介绍给国内学界,以资借鉴,以期争鸣。
一、《浮生》的文体属性之争
1.争论的意义
对《浮生》文体属性界定的意义,捷克汉学家米列娜·多列兹洛娃-维林格罗娃(Milena Doleželová-Velingerová)与其丈夫卢伯米尔·多利策尔(Lubomír Doležel)认为:“鉴于《浮生》所具有的美学与思想价值,本应该引起中国以及西方汉学足够的重视,并在中国文学史上给予应有的位置。这种忽略可能是由于很难界定其文体属性造成的,故而很难将其放入中国文学的历史潮流中。”[2]139因此,《浮生》文体归属的模糊性不仅妨碍了海内外学界对其进一步深入的研究,还会造成《浮生》出版时分类的尴尬与混乱。
但是,霍尔(Jonathan Hall)认为文体属性的意义正日益消解:“在当代西方学术界有一个有趣的、欣欣向荣的发展状况,那就是,从关注文体定义到关注文学作品内相互渗透的话语的多样性。即使是在继续将文体作为一个重要概念使用的地方,也可见这种兴趣的转向。”[3]155在“文体划分让位于对产生裂痕的话语及矛盾进行分析已成为非常普遍的认同”[3]156的情况下,“对西方读者来说,《浮生》给人印象最深的是话语杂乱堆砌,叙事欲言又止,从这一点来看,把它归类于自传而非小说,并不重要”[3]158。
正是基于对文体属性重要性的不同认识,米列娜与多利策尔结合对《浮生》叙事结构的分析,重点讨论了文体属性,霍尔则抛开其文体属性,重点讨论《浮生》的叙事结构。此外,海外学者要么默认《浮生》为自传文体,要么质疑,唯有米列娜与多利策尔系统地论证了《浮生》的文体属性。
2.争论的焦点
国内学界对于《浮生》的文体属性,历来存在分歧,难有定论。黄强指出:“至今这仍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从这部作品问世以来,研究者对其文体属性的归纳众说纷纭,如自传文、小品文、带有自传性质的散文记事杰作、自传体笔记式散文、自传、自传文学、自传体文言小说、自传体抒情小说、自传体笔记、自传体笔记小说、自传性质的小说、传记文学作品等等,各种说法都有。”[4]虽然如此,后期论争主要集中在:是散文,还是小说,还是兼而有之。例如,黄强基于《浮生》具有虚构与想象的特点,认定为自传体小说。但是杜平平反对“《浮生》为自传体小说”的结论,认为“《浮生六记》在内容上叙写真人真事真情,在创作动机上自觉为文、追忆人生经历,在叙事结构上以第一人称叙述、以抒情为结构中心,与古代小说文体有着截然的区别。因此,《浮生六记》是古代散文作品,并且有着明显的自传性、抒情性色彩”[5]。而倪惠颖则认为,沈复不拘泥于文体、文法,在“不离不着之间”,对自我人生进行了真实而又极富传奇色彩的个性化抒写,因此是“对散传及小说两种体裁的兼融、对骈散合一的运用”[6]。这一观点调和了散文与小说之争。
与国内不同,海外争议点聚焦于《浮生》是否为自传,并且呈现出一边倒的格局:判断《浮生》为自传文体的有9人,否定1人(米列娜、多利策尔为共同作者,故计为1人);判断为散文的3人;判断既为自传又为散文的2人;判断为非自传、非小说而为散文的1人。(见表2)
普实克是捷克著名的汉学家,也是《浮生》较早的外译者之一,1944年,他的捷克文《浮生》出版。他将《浮生》置于中国文学的发展史上,并与中国传统史学进行比较后,断言《浮生》是中国第一部文学自传:“自传文学在中国古代是极罕见的现象。直到不久前,人们还认为除了少见的一些自传性的简介,它们根本不存在。第一部文学自传在19世纪初出现时,并非按照简单的时间顺序叙述的……这在欧洲作家看来是自然的。但是这些自传的事实被分门别类组织在一起,一如司马迁的写史风格。沈复是中国第一位文学传记的作者。”[7]21他的学生米列娜、多利策尔评价道:“迄今为止,唯有普实克对该书进行了历史性解读。”[2]153遗憾的是,普实克并未系统地论述《浮生》的文体属性,仅仅指出时间顺序并非判断自传与否的标准。假如《浮生》按照时间先后顺序讲述,反而会显得毫无章法。《浮生》的顺序为中国文学所特有,符合人类回忆的方式。[7]22这一观点为宇文所安认同。

表2 海外学者关于《浮生》文体属性的判断
罗溥洛认为,《浮生》既是自传,又是古典散文;沈复的生活在他自己的时代具有代表性,但他的自传在19世纪早期的中国不具有代表性。早期的自传一般记叙的是文人士大夫的仕途经历,而沈复的自传讲述的是个人的悲欢离合,带有抒情主义、主观主义和忠实的自白,使得该书具有现代性特征。[8]98-99
宇文所安文中没有出现“自传”这一字眼,而是多处使用“回忆录”:“沈复讲述的故事是他们本该拥有的生活,但是他的讲述给人的感觉是实际的生活。这是回忆录,是一种艺术作品,而又让你感觉不到是艺术作品。”[9]103邓海伦认定《浮生》为“散文体自传”[10]108;马士李译序中使用“回忆录”3次,“自传”1次;林语堂译序中使用“自传”;孙广仁译序中认定《浮生》为“回忆录”,但是在语言风格上,认为《浮生》“语言简洁,类似于诗歌、小品文、正史的语言,而非明清时期流行的长篇小说或戏剧所使用的啰嗦的白话文”[11]viii。另外,在5篇译评中,美国汉学家白芝及P. D. H.没有提及《浮生》的文体,而《浮生》意大利语译者兰侨蒂、韩嵩文、海特均认为《浮生》是自传。
因此,在自传文体观远居上风的状况下,米列娜与多利策尔对《浮生》自传文体的否定格外显眼。他们认为《浮生》既非小说,亦非自传,而是“自白式散文”(Confessional Prose)。
3.米列娜与多利策尔的论证
米列娜是著名的捷克汉学家,是较早使用结构主义理论对中国文学进行解读的西方学者之一。为中国学界所熟知的是她编著的《从传统到现代——19至20世纪转折时期的中国小说》(TheChineseNovelattheTurnoftheCentury)。米列娜是普实克的学生,她继承了普实克关于《浮生》具有主观主义、个体主义、抒情主义等现代性特征的观点,却否定了他关于《浮生》自传体属性的论断。
米列娜与多利策尔将“自传”定义为:“它是一种文学体裁,它挑选自传的主题,并组织成对作者的生平、家庭与社会环境持续的、连贯的描述。自传的情节通常按照时间顺序组织起来。”[2]140《浮生》主题无疑基于作者生活的真实,但是具有自传元素或主题的文学作品并不等于自传。因为从结构上来说,文学主题是否虚构、是否真实、是否为自传,是次要的,文体是以主题的具体选择、组成整体结构的模式为特征的。在《浮生》中,自传主题的选择与组织不同于自传体典型的模式,该书也并未完全反映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中国文人士大夫的生活。它的中心主题是沈复夫妻之间的爱情故事。这一点,作者在开篇中即点明,“因思《关雎》冠三百篇之首,故列夫妇于首卷;余以次第及焉”[2]139-140,而在后三记中更是得以强化。
对照人物塑造与叙事主题。《浮生》的人物出场,与传统的自传差别很大。尤其芸一开始即以主角的身份出场,作者对她的生平、外表、气质、言谈举止等,进行了先直接后直接加间接再间接为主的人物刻画。而其他人物的出场则是围绕着沈复与芸的爱情主题展开的,如沈复的母亲,甚至沈复本人也退居其次。此外,《浮生》有两个截然分开并呈现层次性的主题:家庭生活主题与爱情主题。前者被压制,后者则占据主导地位,前者围绕后者展开。因此,在人物塑造与叙事主题的呈现方面,《浮生》不同于自传。[2]140-141
对照时间顺序。多数研究者之所以将《浮生》排除在自传的文体之外,是因为该书的故事情节没有按照时间顺序铺开。故此,米列娜与多利策尔将书中共计66个情节一一列出,并标注了时间,最后按照时间顺序还原。他们发现,虽然从宏观上该书抛弃了时间顺序,但是从微观上,每一记都严格遵守了时间顺序。并且,整个故事情节为循环模式,每一记的时间跨度大体相当,所不同者,不过主题与节奏而已。因此,单纯以是否遵循时间顺序为标准来确定《浮生》是否属于自传文体,是不足信的。[2]145
对照情节结构。《浮生》四记的情节安排是有意还是无心,是否遵循了某种原则,具有什么特点,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它的文体属性,而且对于它的美学和艺术价值具有决定性。单从各记的标题来看,故事情节的安排以情感为主线。为此,他们将该书中66个情节所表现的情感分成五类:乐(joyous),闲(idyllic),中性(neutral),哀(mournful),悲(tragic)。第一记16个情节中,有6乐,6闲,3中性;第二记7个情节,6闲,1乐;第三记22个情节,18悲,1哀,2中性;第四记22个情节,10中性,7闲,3乐,2哀。另外,需要说明的是,第一记中只有一个“哀”,是为沈复新婚后只身离家赴会稽赵省斋先生处继续学业,该情绪转瞬即逝;而第三记中只有一个“乐”,为沈复与芸投奔华夫人,“相见甚欢”,也是转瞬即逝的。由此可见,第一记情感主题为“闲”“乐”,第二记为“闲”,第三记为“悲”,第四记为“中性”“闲”。每一记的情节都以某一情感为主线,情感决定着情节的分配。比如,芸与憨园的交往既出现在第一记中,又出现在第三记中,前者为喜剧,后者为悲剧。所以,在情节布局上,《浮生》并非随意的,而是遵从了明显的、有目的的模式,即时间顺序让位于情感主线。这一情节结构实际上是一个“系统的、有层次的整体”。这是《浮生》最显著的特点。[2]146-151
基于以上文本之内的分析,对照《浮生》人物塑造、叙事主题、时间顺序、情节结构等特点,米列娜、多利策尔得出《浮生》属于“自白式散文”的论断。这种文体在古典文学中虽有先例,却是在现代文学中作为一种具体的、纯文学的文体而确立的。《浮生》与该文体有如下关联特征:其一,“自白式散文”对于作者或讲述者的人生、性格的形成不必进行系统的描述,而是集中于他私密生活的某些方面或某些时期。其二,“自白式散文”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对故事情节的时间刻意操纵,使之背离时间顺序,如倒叙、故事套故事,《浮生》的时间顺序让位于情感的时间模式。其三,从本质上来说,“自白式散文”倾向于第一人称的叙事形式,其优势在于既可以描述“外在的活动”,又可以描写讲述者的内在动机、情感、喜怒哀乐[2]151-152。
米列娜、多利策尔二人并未囿于文本之内,而是将这一讨论置于历史的宏观语境中。中国古典文献的确存在“自传性”的传统,如司马迁《史记》中的《太史公自序》,王充《论衡》中的《自纪》等。这些片段具有自传性,在结构与风格上也十分相似,“作者试图客观描述自己的心路历程,在事件安排上尊重时间顺序,并且使用庄重的、完全指称性的语言”,它们起到“为读者介绍其生平、家世、治学等信息,以便读者理解其观点的来龙去脉,以及写作缘由”的功能。[12]不过,《浮生》跟这一传统事实上亦无关联。直到二十世纪,中国的自传体文学才从古代史学、治学的联系中解放出来,反映在名称的使用上,从自序到自传、自述等的转变。而近代亦出现了诸如梁启超《三十自述》、胡适《四十自述》、沈从文《从文自传》等自传体文学,这些作品都是按照时间顺序客观叙述的。所以,《浮生》并非中国传统意义上的自传文体。[2]154
相反,《浮生》跟中国古典诗词、散文颇有渊源。米列娜与多利策尔认同潘麟生的观点,《浮生》堪比屈原的《离骚》,而《离骚》就是一部“诗歌体的自白”。事实上,中国古典诗词中不乏此类自白式的主题,如蔡琰、曹植、陶渊明、李白、李清照等诗人的作品。《浮生》题目本身就取自李白的“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不过,从主题、风格,尤其哲学态度上来说,《浮生》其实更像宋词。此外,散文传统如赋、笔记、游记等,也给《浮生》提供了历史的土壤,尤其是苏轼的《赤壁赋》,以第一人称表现“寄蜉蝣于天地”的情怀,以及主客之间的哲学对话,与《浮生》主题何其相似。而明清时期游记盛行,如《徐霞客游记》等个人笔记则越来越倾向主观性与情感表达,如冒襄的《影梅庵忆语》。这些痕迹在《浮生》一书中也可以找到。[2]156-158
当然,“所有这些古典文学的影响与回响,不管多么重要,都无法解释沈复作品所具有的美学品质与美学效果。《浮生》的特点是,作者将古典文学中所有主观主义与抒情主义零零星星的表现撮合在一起,消化吸收,转化成一种新的文学结构。《浮生》无疑是一曲古典诗歌的绝唱。与此同时,它开启了新的、富有现代意义的文学形式……沈复开创的这一纯文学文体——自白式散文,为古典文学所未见”[2]158。
《浮生》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分水岭。由于其浓郁的主观主义与抒情主义,一方面它脱离了自传的属性,具有现代意义;另一方面它与诗、词、赋在主题、哲学思想、风格上近似,对中国现代主观主义散文又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虽然米列娜与多利策尔否认了《浮生》的自传体属性,但《浮生》的自传体特征是不能否认的,否则其故事的真实性就容易引起人们的质疑。目前没有证据表明《浮生》完全出自沈复的杜撰。米列娜与多利策尔的贡献在于其结构主义和历史主义的分析方法与观点,国内学界关于《浮生》文体属性争论的研究,可以此为借鉴,以期获得启发。
事实上,《浮生》在文体上的模糊性正是它经久不息的魅力所在。按照西方文学的观点,从中国文学史的角度来看,《浮生》出现的时代的确不具备纯粹的自传体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处于特殊的历史时期,它不可避免地杂糅了古典与现代的各种元素,它有着自传体文学的真实性,古典诗词文赋简洁优美的语言特征,散文抒情的笔调,笔记、游记的叙事、描写与评论方式,以及小说一样的情节结构。人们从中读出了司马迁的《史记》,李白的诗歌,屈原的《离骚》,苏东坡的《赤壁赋》,徐霞客的游记,冒襄的《影梅庵忆语》,曹雪芹的《红楼梦》,等等。所以,如霍尔所言,与其关注其文体的纯粹性,倒不如关注其游离于某一文体之外的独特之处。
二、《浮生》的叙事结构
《浮生》的文本结构有一个显著的特点:从整部作品来看,没有按照时间顺序从头到尾叙事,而是六记(实存四记)各有主题,自成体系又遥相呼应。海外学者对此见仁见智,褒贬不一。
《浮生》的英译者,除了林语堂,或多或少都表达了对该书非线性叙事的不解,甚至不满。在译序中,白伦、江素惠指出该书的品质存在问题,就连沈复都承认自己不是一个明白晓畅的作者;书中多处指代不明,甚至毫无意义,有些事实则前后矛盾;该书不是我们习惯阅读的按照时间顺序讲述的故事——“我们期待有过渡的地方,沈复略之;我们期待有合理解释的地方,沈复讳之。上下句之间常孑然孤立”[13]。
孙广仁亦认为这种时间上的反复无常似乎源于各记的拼凑,而非从头到尾一气呵成,“假如我们相信沈复如他自己描述的那样,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那么他就是放任故事情节的松散了”[11]X。虽然如此,他还是肯定了沈复的叙事技巧:如果将散佚的第五记、第六记考虑在内,整部作品就达到了总体的平衡。前三记记叙沈复夫妇的悲欢离合,笔触私密而抒情;后三记记叙他的远近行迹与养生之道,笔触外露而客观。沈复的叙事技巧高度创新,他将叙事片段化,然后层层叠加。每一记内部的叙事按照时间顺序,开始于他人生的某一个节点,结束于另一个节点,叙事时间或长或短;每一记的节奏视主题而定。这一结构模仿了人类记忆的形式和行为,即有选择性的、非连续的、循环往复的,并带有情绪色彩的。这也能回答沈复为什么采用线性与片段结合的叙事结构的问题。[11]xiii-xv
出于对原作的尊重,上述译者在翻译时对叙事顺序没有任何改动,而马士李就不同了。她直接将《浮生》的四记拆分成3部分,12个章节,并对书中部分内容进行了删节,对部分情节在时间顺序上重新排列。其理由如下:对某些寺庙、景点游玩的描述大同小异,对于不熟悉这些地方的读者来说没有多少意义;部分文学评论、园艺、盆栽的细节太过专业,不会引起多数读者的兴趣;这样做可以避免时间顺序上的混乱。[14]对于马士李的做法,美国汉学家白芝认为是正当的,这样可以保证文本从始至终引人入胜[15];P. D. H.则批评这是一种“极端霸道”的做法[16];而兰乔蒂则指出:“任何时候,当我们认真考虑并着手处理如何翻译的问题时,都会听到各种不和谐的声音。于我们译者而言,应该满怀谦虚与热爱去对待每一个文本。每一处细微的改变都必须有正当的理由。而认为文本可以随意删节的观点只能是对原文的歪曲。”[17]
除了上述英译者,海外多位汉学家对《浮生》的叙事结构进行解读,其视角之独到,分析之细致,观点之新颖,值得国内研究者借鉴。
米列娜与多利策尔认为,《浮生》的情节结构匠心独具、构思精巧,并非随意的,而是遵从了明显的、有目的的模式,各记有各记的地位和功能。其基本的结构模式为:第一、二记为“闲情逸趣”;第三记为“悲剧危机”;第四记为“渐降式的宣泄”。实际上,第五、六记虽然散佚,但是根据标题猜度其内容,也可归于“渐降式的宣泄”。而第一、二记为第三记的铺陈和积累,最终指向的是第三记,第三记为全书的高潮部分。总体而言,第一、二、三记构成的是“以陈芸为中心的循环”,其情感主线为“乐、闲、悲”;第四、五、六记是“以游记为中心的循环”,其情感主线为“中性”。他们特别指出第三记与第四记的不同之处:在沈复情感的描述中有两个主角,一是陈芸,二是大自然,前者是前三记的主角,后者是第四记的主角。如果说陈芸的爱情带给沈复的是至欢至乐,至苦至悲,那么大自然带给他的则只有欢乐,或者至少是内心的平静。而第一记与第二记之间也有着微妙的区别:前者主要是动作,后者主要为描述。由此可见,作者沈复“在复杂的结构中,分与合之间尽显精妙”。除此之外,他们还指出了《浮生》在叙事上存在所谓的“情节的环扣”以及“结构与象征的伏笔”。前者的作用是将各记串联起来,后者的作用是“可以在这种闲情逸致氛围的对比中营造更为强烈的情感效果”。[2]148-151
霍尔注意到《浮生》在叙事中存在着双重的分裂:分裂的自我(沈复本人)、分裂的叙事。霍尔之所以说沈复是“分裂的自我”,是因为主人公在整篇叙事中的“自我贬抑”,甚至“自我谴责”,而同时在其关于“生活艺术、闲情逸趣、山水景色、文评艺评”等的美学评论中得以自我释放、自我表达。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第四记,因为从故事整体的时间上来说,此时沈复的父亲、陈芸都已去世,此记可以算是对前三记中某些事件的回应。此时,沈复可以放下包袱,无所顾忌地表达自己真实的情感与思想了。并且,沈复既是故事的讲述者,又是故事的主人公,这样的双重身份难以确保他是一个“言行一致的讲述者”。霍尔之所以说《浮生》是“分裂的叙事”,是因为《浮生》的篇章结构具有明显的特点——“线性叙事与叠加对照的美学评论并存”。其中,叙事的作用是与其他散漫的模式间接融为一体,互相关联,取代了显而易见的随意的断开。美学评论的作用则是取代、升华主人公在家庭的结构中被压制的欲望,该美学模式容许自我肯定,反对世俗,成为补偿主人公独立表达观点的渠道。一言以蔽之,如果说沈复对使他边缘化甚至摧毁他的封建秩序、封建礼教,在叙事中表现的是一个捍卫者,那么在美学评论中表现的就是一个叛逆者,一个无声的反抗者。前者是直白的,后者是委婉的。霍尔还特地引用《浮生》第四记中的一句话来证明这一点:“余凡事喜独出己见,不屑随人是非,即论诗品画,莫不存人珍我弃、人弃我取之意。”[3]155
宇文所安对《浮生》第二记“闲情记趣”情有独钟。他认为,第二记的独特之处在于,一是打断了叙事的直行,二是相似情节的反复出现。在第二记的描述中,沈复反复打造着自己的“小天地”,沉溺于自己的幻觉之中。文中所述的“夏蚊”“花台小草”“二虫”“素心春兰”“插瓶”“盆树”“园亭楼阁”“假山”等,就象征着这个闲情逸致的“小天地”。而沈复苦心经营的这个“小天地”屡遭外来入侵者的破坏,使他的幻觉一一破灭,如此周而复始。宇文所安认为,这符合人类记忆的特点,“在我们记忆的各个角落,隐藏着一种重复的强迫。当我们转而思考重复本身时,我们发现只有通过记忆,重复才有可能”,而“重复是过去半途而废的,不完善,不完美的印记”,任何作家都不可避免重复。[9]99-103
霍尔和孙广仁认同这一观点,并指出,这些“小天地”屡遭破坏的小事件实际上与沈复整个人生悲剧更为宏观的叙事紧密联系,揭示了悲剧的必然性。[3]164-165
罗溥洛对《浮生》结构的解读非常简略,认为该书是按照不同的话题,以传统的文人杂记的方式谋篇布局的。就其关注的话题(《浮生》中女性的角色)而言,第一记、第三记尤为重要。[8]100
邓海伦认为,《浮生》的文风简洁、含蓄,为作者隐藏自己提供了完美的载体,因为语焉不详、含糊其辞都只能逼迫读者去做无限接近作者本意的解读,这根植于中国写史采用“春秋笔法”这一传统。她赞同霍尔的观点,认为这种“线性叙事与叠加对照的美学评论并存”的结构,不仅具有艺术魅力,还为作者隐藏真实提供了心理转换的机制。[10]103-122
综上所述,《浮生》在叙事结构上具有非同寻常的考量,在很大程度上,这正是《浮生》的艺术价值所在。认识不到这一点,就很有可能对其艺术审美的完整性造成破坏,比如马士李在翻译《浮生》时对叙事结构的操纵。此外,叙事研究也成为海外“浮学”研究的重中之重。米列娜与多利策尔研究的贡献,在于从情感主题入手分析其叙事结构和叙事模式,并通过横向比较,指出其中存在的“伏笔”和“环扣”的叙事技巧或手段;霍尔的贡献,是在叙事结构中发现“线性的叙”与“片段的评”两个不同的层面及其意义;宇文所安基于人类回忆的心理机制,指出书中沈复夫妇的“小天地”屡遭破坏的重复;邓海伦从读者接受的角度,分析《浮生》复杂的叙事结构、简洁含蓄的叙事风格背后是作者对真相的刻意隐瞒,启发读者重新去解读这部作品,尤其是陈芸的“同性恋”甚至“双性恋”问题;孙广仁也是从人类记忆的特点去分析《浮生》的叙事结构的。
三、结 语
《浮生》之所以能够传播到海外,备受关注,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有其必然性。其中,文体属性的融合与模糊、叙事结构的复杂与精巧无疑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文学批评能更好地促进文学作品的传播,国内研究如此,海外研究亦如此。通过海外研究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汉语典籍外译与海外接受状况,并以此来促进国内的相关研究。新时代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时代。“走出去”可以让世界更好地倾听我们,也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聆听世界。对汉语典籍的海外研究的介绍,可以服务于我国对外形象的塑造和对外话语体系的构建,更好地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