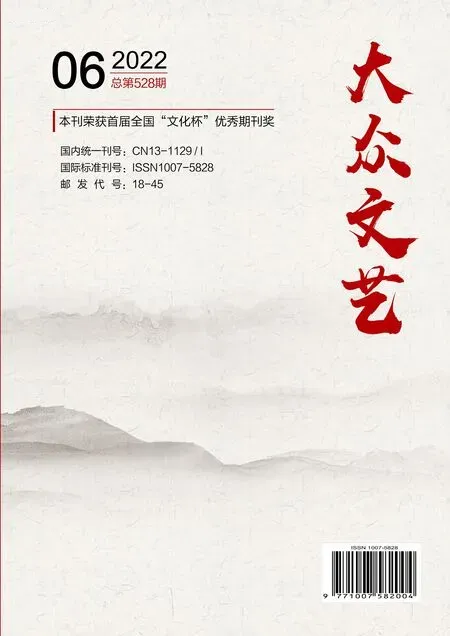《耳光》:印度女性的身份建构*
(安徽大学艺术学院,安徽合肥 230000)
21世纪的今天,尽管两性平等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女性的社会地位得到极大的提高,但人们对于陈旧观念依旧保守,女性被社会和家庭标记着身份,无法拥有独立人格。印度女性电影《耳光》围绕着“我是谁”这个核心问题,讲述了家庭主妇阿谬因为一记耳光,掀起了一场关于不同身份、不同阶层女性的觉醒与反思的故事,展现了在社会的浪潮中,女性如何实现自我身份的颠覆和重建。身份是个体与个体在交往间相互识别的标志,也是个人社会地位以及享受权利的显现。个体对自我身份的认知大多来源与所属的社会类别,在印度,男性凭借强势的性别优势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在男人的主宰下女性的身份建构便会依据他人的期望和反应不断修正,无法拥有独立个体的自由建构。因此,印度女性在长期被动的劣势下认识到不平等的体制所带来的困境,伴随着主体意识的出现,女性开始对自我身份提出质疑。
一、失语:他者凝视的女性地位
在父权制社会中,往往是男性作为观看者,女性只是被看的对象,男性作为视觉和语言的中心在社会系统里可以决定一切规则。女主人公阿谬作为完美的家庭主妇,将丈夫作为自己生活的中心,日复一日地提前早起为丈夫打理一切琐事,这些行为都符合男权制度下他者凝视的状态。“凝视”本义即是“看”,围绕着本义的扩充与外延,则有“看”与“被看”的双向视觉行为。在福柯看来,观看者可以通过“凝视”来建构自身的主体身份,而被观看者的行为和心理就会在被“凝视”的过程中受到“规训”,会被动地接受和内化观看者的价值判断。因此观看者会按照自己的审美期许对女性提出标准,使其在耳濡目染中不自觉地按照标准要求自我。
女性一直处于被男性凝视的地位,而它意味着男权统治和男权价值在整个社会中的主导性、统治性、合理性和合法性。男权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成为一切价值的尺度,在此制度下,女性被抑、被沦丧,只能成为附属的和第二性的了。被凝视的女性逐渐会在男权社会的主导下,通过满足他者的凝视来完成自身形象的认知。在现实生活中,家庭往往被看作是女人的主场,人们自然而然地将家庭的一切事务都交由女性掌管。印度作为一个传统的父权主义社会,是不会允许进入婚姻的女性离开家庭,进入社会工作的,因此被隔离于社会以外的她们,渐渐与外人脱节。电影《耳光》的主角阿谬看似在家庭中与丈夫平起平坐,而背后所呈现的仍然是女性被凝视的现状,原本身为舞蹈家的她,在婚姻的桎梏下逐渐忘却曾经知识分子的身份,丈夫潜意识地灌输她与家庭的稳定联系,剥夺了阿谬的自由与独立。被凝视的女性逐渐会在男权社会的主导下,通过满足他者的凝视来完成自身形象的认知,她们长期独自在家重复做着烦琐的劳动,却还将此作为自己重要的使命,享受着家庭的安稳生活。
在研究女性主义和凝视理论中,不可忽视的就是拉康的“镜像”理论,他认为在婴儿6-18个月间,会意识到“自我”与“他者”的概念。拉康所认为的“他者”是用象征符号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的人,如身边的亲人朋友。幼儿在“他者”的引导下,从人的镜像和他人的表情、行为中接受的一种非我的强制(或者叫“侵凌性”)投射……这种投射最终形成了作为小他者意象结果的伪自我。婴儿在成长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伪自我不需要后天的经验便可形成,因为这是长期以来人类生活的社会类别所给予他的秩序,正如男尊女卑的观念被深深刻入大多数印度人的心里,代代相传。
在长此以往的男性凝视下,许多印度女性被权力所规训,从外在的他者规训走向内化的自我凝视,逐渐成为压迫女性的合谋者。在印度社会,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根深蒂固,男权制度已经牢牢植入了每个人的心里,这一强大的他者获得了主体的认同。阿谬身边的每个人,包括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都在潜意识里接受了这个制度,认同并遵循者这个秩序。作为凝视权力下的“他者”,阿谬的母亲与婆婆都内在监视了主体伪自我的形成,两个以维系家庭为主的女性,自我服从父权秩序,恪守妇道。从小到大,母亲就用自己为了照料家庭放弃歌唱梦想的经历告诉了阿谬,女人要为了家庭放弃自我;婆婆为阿谬做自己拿手的煎饼,让阿谬重复学习为丈夫做饭的能力,亦是侧面显现婆婆将自己对秩序的践行传承给了阿谬。女性长期生活在男性主导的社会规则下,不自觉地转变成为男权发声的他者,将女性从属的地位交给了男性宰制。
要而言之,印度女性在男性的凝视下,成为父权制度的失语客体,丢失了自我身份,而拥护父权制度的印度女性在长期的规训下,从被男性凝视的受害者转化为凝视女性的他者,使印度女性在双重压迫下走向被支配、被抑制、被剥夺的地位。因此,女性被排斥在印度社会之外,完全丧失了自主意识,导致完全的身份缺失。严重的身份缺失使女性受到双重性的冲击,一方面,印度传统观念深深植入脑海中,这种影响难以割裂;另一方面,女性意识到这种他者凝视给自己带来的只有无穷的痛苦。遭遇身份危机的印度女性开始由被动转为主动,尝试反抗男性权力,夺回丧失的女性话语,客观上促进了主体意识的觉醒。
二、觉醒:女性话语与自我认同
女性意识觉醒不仅在与打破他者的凝视,更主要的是建立话语的主体性。“话语”在福柯看来不仅是概念上的语言,同时是一种社会地位,并与权力息息相关。他提出“话语承载着生产和权力,它加强权力,又损害权力,揭示权力,又削弱和阻碍权力。”影片中男女在话语权力上的不平等在女性主体觉醒前已经隐秘的显现出来:丈夫习惯性地指使阿谬为自己解决家庭的琐事,而阿谬的跳舞爱好只能在丈夫上班后,利用空闲时间去授课做回自我;当询问自己是否能学车时,被丈夫用“先学好怎么煎饼不烫伤自己”的理由搪塞过去。但同时,福柯认为的“话语”也不仅仅是思想和语言,同时也包括了身体姿态,以此延伸出了“身体话语”的概念。
身体是诸多力量(话语、体质、权力)的活动场,只有从凌乱混杂、充满歧义的身体出发,才能够找到权力与话语的轨迹。暴力是身体话语中体现权力最直接的行为,而女性常常作为暴力的承载者,更能体现出暴力的迫害与侵略。家暴是印度长期以来的陋习,正是因为男性对女性身体话语的掌控,因此对女性身体的暴力行为对于男性来说也是理所应当的,而这个身体话语已经变成了社会群体的集体无意识。当阿谬被丈夫打了一巴掌后,不仅仅是丈夫,身边的所有人潜意识里并未觉得这个行为有任何不妥,通过一个耳光后群体的无动于衷,突出了身体话语对人们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控制,表明了身体是权力所施加压力的对象。
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往往需要徘徊于顺从与抗争之间,最终掀开生活完美的虚假面纱,在目睹权力的内核后实现真正的自我觉醒。影片中阿谬觉醒的开始是在那场聚会上丈夫暴怒下的一耳光,她坚持回到自己的房间实际上也是对这个耳光所代表的外部权力的逃避,这里阿谬的心情与周围的环境呈现了一种对立,静默的耳鸣与欢乐的音乐讽刺地显现出女性在话语上的权力限制。卧室外代表的是父权势力,卧室内则是阿谬开始认真审视自我的独立空间,她曾经的婚姻幻想受到了权力的挑战。在长期的本我与自我的博弈中,阿谬回到家中尝试忘掉身体所遭受的暴力,但发现丈夫依然没有悔改之心后,毅然决定离婚。“在权力关系中,反抗是另一面,是权力关系不可消除的对立面。”男性话语在压制女性的同时也在催生着女性的反抗,这种在觉醒后所获得的自我认同让她们对女性的话语建构有了更深的理解。
在印度社会,女性总是受到各种规则的制约,需要朝着男性的标准去发展自身,因此女性对自我的认识便会造成偏差。当主体意识觉醒后,清醒的女性便开始建构自我认同,同时也意味着摆脱男权话语已经内化成内在的主要心理。女性自我认同的过程正是与传统文化观念的博弈,在自我意识觉醒后的自我认同,是阿谬改变作为女性被外界所支配的思考,即使所有人都不理解也不支持离婚,但阿谬依然坚持孤军奋战。作为女性甚至是知识分子的律师同样认为这个理由不合理,阿谬面对父权话语不再沉默,直言自己只想要尊严和幸福,为自己的女性权力勇敢发声。自此,女性明确意识到自己是独立的个体,并渴望脱离男权话语的掌控,建立属于女性的话语权力,完成自我认同也为女性建构身份奠定了基础。
三、建构:身份重建与女性书写
波伏娃在《第二性》里指出,女人并不是天生的,是一种在男人的主导下被“阉割”了的性别,在父权制下,女性的身体遭受着男性的凝视,被禁锢在家庭中;女性的思想被迫接受男权权力下的文化灌输,被剥夺话语权。当女性逐渐从男性编织的男权至上的社会权力关系的梦魇中苏醒时,女性的自我意识支配她们强烈要求挣脱男性打造的性别牢笼,从男性权威主导一切的性别关系中突围,试图重新定位自己的性别角色,重新建构自己的伦理身份。女性身份建构不仅在自我定义的改变,同时也在家庭和职业两个方面进行建构。
女性之所以成为男性附属的存在,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男性将女性桎梏于家庭之中,无法与外界有任何接触。而女性身份重建所迈出的第一步就是对家庭关系的压迫发起挑战,摆脱家庭对自己的完全控制,走出婚姻的束缚。阿谬的身份重建在走出质疑的一步便遭到了男性权力的压迫,接踵而来的谣言和意外怀孕让她一度怀疑自己的行为是否有误,但在父亲的引导下,她坚定了自己的念想,找回了属于女性的权力。在祷告会上,阿谬用自己的宣言说出了自己的心声:她不愿像自己的妈妈和婆婆一样成为深陷婚姻的家庭妇女,也不愿如身边的人那样对丈夫家暴的行为熟视无睹,阿谬用行动彻底摆脱了从属的家庭女性地位,重新建构属于自己的身份。
在集体无意识的环境下,有了第一个敢于反抗权力的打破者出现,其他被蒙蔽在幕布下的受害者也会在引领下推翻被固化的身份。婆婆在阿谬的独白下,自我的主体意识被唤醒,她告诉阿谬是父母的错,没有告诉自己的儿子不能打女人,并与丈夫放下心中的芥蒂。保姆放下了手中维克拉姆多给的工资,并在回家后因为丈夫又一次的家暴彻底爆发,用丈夫打她的方式反抗了丈夫。阿谬的自我建构为身边的弱势女性提供了反抗的标本,打破男性权力的中心地位,改变了女性沉默的被动处境。女性身份的重建不仅仅是将女性从社会的弱势地位解救出来,更主要是让女性拥有与男性平等的权利,女性不是男性的从属,更不是家庭的附庸。当女性开始脱离家庭参与到社会生活中,发现自己的能力,工作就成为女性进步的台阶。
职业是当代社会分层系统的基础因素,职业身份决定了个人的基本社会经济状态,决定了个人在社会分层系统中的大体位置,而男性和女性在职业结构中的分布状态又决定了性别分层的基本形态,职业的性别隔离是导致两性之间社会经济不平等的重要因素。职场是女性建构社会身份的重要空间,随着时代的发展,一部分受过教育的女性从家庭的桎梏中挣脱出来,积极参加到社会生活中,寻求职业上的身份认同,但不可否认的是,女性在社会中的职场选择十分限制,大多数决定权依然掌握在男性手里。影片中身为律师的奈特拉即使与男性获得了同样的社会地位,但依然在胜诉后被丈夫认为是依附于他才获得的荣誉,在以丈夫为主的男性主宰者在各种意念及感受上左右着奈特拉的思想,告诉她永远超越不了作为成功人士的律师岳父。只有女性从长期的家庭桎梏中走出来,独立的建构职业身份,才是书写自己的命运,这种过程所经历的是一个质的变化,这也真正标志着个体的进步。
事业有成的律师奈特拉一直活在律师公公的阴影下,在丈夫强迫她时也没有勇气反抗。但在得知阿谬因为一个耳光坚定离婚后,她被触动了。接手了阿谬的官司后,奈特拉向丈夫提出了离婚,结束了这段看似光鲜亮丽实则毫无波澜的婚姻,并自己创办事务所。邻居的丈夫早年去世,但她并没有因此而一蹶不振,而是自己带着女儿赚钱养家,她用自己能够媲美中产阶级的资产告诉了这个社会,女人是可以不靠男人活下去的。女性在与男权社会中的生存冲突中证明自己是独立的,获得自我价值,建构社会身份,成为与男性能力不相上下的“女强人”。这时女性的身份是主体自我的建构,并未依赖于外界,女性摆脱社会中固定化的身份建构束缚,树立以寻找自我价值为主的意识,实现了女性真正的主体身份建构。
在这条不断寻求解放的女性书写道路中,我们能体会到女性身份建构的艰难,不论是阿谬还是奈特拉,在历经一番挫折与教训之后,都幡然醒悟,脱胎换骨,实现了自我的身份建构,书写出属于女性的篇章。女性摆脱了符号化的“女性气质”,不再依靠婚姻与家庭,通过自己的努力在社会生活中取得独立的经济能力,并获得精神上的解放与自由,这不仅仅是在书写女性身份,更是在书写女性命运。女性终于挣脱被男性社会牢牢控制的命运,对自身和未来有了新的理解与顿悟,这无疑给了女性自我建构确立了一个可以追寻的目标,也为印度女性的身份书写指出了正确的方向。
四、结语
近些年印度女性电影对于女性权力的呼声越来越高,客观上促进了女性的自我觉醒与抗争,但从本质而言,并未撼动根深蒂固的男性凝视和话语剥夺,当代女性仍然很难走出他者构建自我身份的困境。在男权社会的制约下,女性身份使自己契合大众期望进行建构,电影里的印度女性身份摆脱了以往的刻板定式,开始朝独立女性迈进,主角在结尾都获得了重生,并得到了男性的尊重与支持,让观众看到了女性的未来仍有美好的希望。《耳光》相较于往年的印度女性电影,走出了女性冲破生存困境,塑造本真“自我”的第一步,但对于身份的建构却并未做到在社会中体现主体价值。当未来的印度女性不再以世俗社会的固化印象来认知自我,正视自己在社会中的困境和价值,两性平权的曙光就离我们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