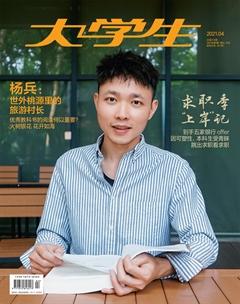母校的温暖
孙虎

去年上半年疫情暴发后,原本准备6月份毕业的我延期到12月份毕业,在这延期的半年中,我在准备毕业论文和找工作。
因为疫情,本来4月份即可见刊的文章,因为印刷停工而无法出刊。然而学院规定,必须在文章见刊后才能进行毕业答辩,这就使我在6月份毕业的打算落空,也導致我之前联系的在北京、重庆等地的工作机会不得不随之放弃。
不过,在家乡度过的数月,也让我对未来的工作计划做出了改变。原本我是打算在北京、重庆等较大的城市发展,但在和父母生活的这段时间,我发现他们已经渐渐老迈,身体经常出现小毛病,甚至在很多事情上,曾为我遮风挡雨的他们,已经不能从容应对。作为家中的独生子,我感到家人的团聚与健康,要重于自己学业与事业的微薄成绩。因此,我有了毕业后回到家乡、回到父母身边的想法。
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生产生活逐渐恢复了正常,我的学业与求职也迎来了转机。虽然未能在6月顺利毕业,但不久后我的论文就刊印了,此前所写的几篇文章也相继得到了刊物的录用回复。由于毕业日期改到了12月,即将毕业的学生只有我一人,因此导师也能抽出更多的时间来帮助我修改论文。在导师提供了很多重要的修改意见并反复辅导后,我将博士论文进行了全面的修改,最终顺利通过了答辩。
由于还面临着就业的问题,我在紧锣密鼓地准备毕业答辩的同时,还积极找着工作。从历史系博士毕业的我,主要的出路是去当高校教师、社会科学科研院所研究人员以及图书期刊编辑。这三种职业各有所长,在科研院所工作不需要承担太多的授课教学任务,可以把大量的时间用来读书科研,但这类职业与外界接触少;图书期刊编辑虽能让我拥有继续提高文章写作能力,接触更多信息的机会,但相对繁忙,要长年累月细心校阅文稿,我的眼睛之前受过伤,无法长期高强度地阅读稿件;高校教师则在两者之间,忙闲有度,在读书科研之余,还可以通过授课与学生交流。就我本身而言,高校教师是我比较倾向的选择。
不过,国内有历史学院的高校不算多,以北京为例,开设历史学院的高校只有几所。但历史学毕业的博士众多,人才济济,因此,不少历史学博士只能选择去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近现代史纲要等课程。但我是中国古代史专业出身,在历史学院工作更适合我。因此,我的选择变得愈加狭窄,主要是一些师范学校。
同时,要想去高校工作,对文章发表的要求也更苛刻,往往需要发表几篇C刊才能达到门槛。好在我博士延期的过程中,我的其他几篇文章已经陆续刊出或即将发表,这让我在找工作时有了底气。
我在网上浏览了不少招聘信息后发现,绝大多数高校都尚未开始招聘,其中就包括上半年我曾经联系过的一些高校,它们都要到来年3月才开始招聘。庆幸的是,我读本科的母校历史学院正好在招聘。我是在那里得到了历史学的真正启蒙,才逐渐对这个专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的硕士,学习北方民族史与明清史,并追随导师读取了博士。母校提供的岗位正好与我回到家乡工作的想法相契合,于是我毫不犹豫地投了简历,并迅速与学院取得联系,得知学院正好需要招聘明清史专业的教师。不过,由于当时我正在北京进行论文答辩,未能及时参加面试。
此时已经是2020年12月底,北京的疫情再次紧张,进出学校都需要提前申请。答辩结束后,我甚至未来得及与众师友话别,便匆匆离开北京回到家乡。在家自我隔离期间,我连母校的面试也无法参加。正在沮丧之中,我收到母校老师的信息,学校准备进行视频面试,面前陡然柳岸花明。虽然准备得有些仓促,好在面试过程还算比较顺利。这时,在新疆和重庆的好友也先后给我发来了他们学校招聘的信息,这些学校平台和待遇甚至更优越。由于我想回家乡的想法很强烈,再加上母校各位老师的关怀也让我倍感温暖,最终我还是决定回到家乡的母校工作。
责任编辑:曹晓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