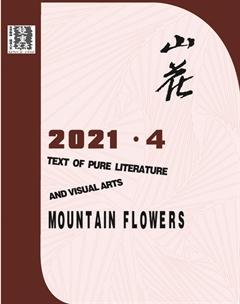愤怒的灵魂变成幸福的灵魂?
杨子
1963年8月1日,美国诗人西奥多·罗特克在朋友家泳池游泳时死于心肌梗塞。据他的中学同学和传记作者阿兰·西格描述,他将一罐薄荷朱莉酒放进冰箱,然后去扎猛子。女主人再次看到他时,他已经脸朝下浮在泳池水面上了。布勒德尔家族将泳池填土,改建为禅宗风格的岩石庭院,纪念这位去世时已在全美和欧洲赢得极高声誉的诗人。
有批评家认为,如果晚死十年,罗特克有可能问鼎诺贝尔文学奖。兰塞姆、拉尔夫·J.密尔斯等诗人、批评家将他放在与史蒂文斯、威廉斯和肯明斯并驾齐驱的位置。也有论者认为,他是二十世纪中期诗坛三领袖之一,与理查德·威尔伯和罗伯特·洛威尔比肩而立。
罗特克比威尔伯和洛威尔大十岁左右,成名却比他们晚得多,可以说他终身都在为获得承认而奋斗,否则他不会辛酸地自嘲——“我是全美国最老的年轻诗人”。
《华尔街日报》在讣告中引用了诗人的自我陈述:“我把自己看作一个爱的诗人,一个赞颂的诗人,我希望人们大声朗诵我的诗篇。”
罗特克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重要诗歌流派“深度意象主义”和“自白派”的先驱。“深度意象主义”代表性诗人之一詹姆斯·赖特是他的学生,“自白派”明星西尔维娅·普拉斯和她丈夫、英国著名诗人特德·休斯公开承认受到他的影响。美国二十世纪后期重要诗人W.S.默温、查尔斯·西密克和马克·斯特兰德同样深受他的影响。而“深度意象主义”另一位代表性诗人罗伯特·布莱的那句话——“我最终理解到诗是一种舞蹈”,听上去完全是罗特克诗歌精神的翻版。
批评他缺乏独创性的也不乏其人。有人认为“叶芝对他的影响也许是最大的。……他个人的声音从未消失过,但是他从别人那里学来的风格声音可能会更大,也更能分散人们的注意力”。有人提醒读者在阅读他的名作《一位老妇人的沉思》时应比照叶芝的“疯简诗篇”和史蒂文斯的《星期天的早晨》。
1998年,诗人罗伯特·哈斯访问密歇根大学时,回想他所知道的“密歇根风光,它的自然史和文化史”,“立刻想起两个源头——海明威的密歇根故事和罗特克的诗歌”,盛赞罗特克是“我们伟大的自然诗人之一,二十世纪最早思考自然,思考自然与人类心理关系的诗人之一”。
2005年,诗人爱德华·赫什在由他编辑、非营利出版机构“美国图书馆”推出的新版《罗特克诗选》(列入“美国诗人项目”丛书)前言中说,罗特克是“惠特曼和爱默生的值得敬重的继承人,我们具有典范意义的哲学家……二十世纪中期一位自觉继承叶芝、史蒂文斯和克兰的浪漫主义传统并将其发扬光大的诗人”。
1908年5月25日,西奥多·许布纳·罗特克(Theodore Huebner Roethke)出生于美国密歇根州萨吉诺一个德裔移民家庭。父亲是奥托·罗特克,母亲是海伦·许布纳。
三十六年前,罗特克的祖父威廉带着妻子和五个孩子从东普鲁士来到萨吉诺,成立Wm.罗特克花卉公司,建造了一座25英亩的温室,公司广告语是“密歇根最大最完美的花卉企业”。罗特克家的温室有自己的冰窖,还有一小片禁猎区。
来美国前威廉在东普鲁士,是德国总理俾斯麦的姐姐家的护林官,似乎一度也做过俾斯麦家的护林官。罗特克的外祖母掌管过俾斯麦家酒窖的钥匙。
罗特克在去世前一年给拉尔夫·J.密尔斯的一封信中提到,祖父因为他的和平主义思想挨了俾斯麦的骂,全家实际上是被逐出德国的。
一开始威廉的五个孩子都为温室工作,利益共享。威廉去世后,温室归小儿子奥托和查尔斯所有,奥托成为总管,查尔斯负责财务。
罗特克从小跟着父亲干活——在温室里(“我曾整夜待在那儿”,见《迷失的儿子》)给苗床除草,在自家土地上的原始森林里撿苔藓,在家族养护的禁猎区漫游,“那是一片采伐迹地上的次生林”。他在1953年7月30日的BBC节目中说,“我同时活在几个世界,我感到那儿属于我。最心爱的地方是禁猎区角落的一块沼泽地,苍鹭总是在那儿筑巢。”
在1962年3月23日写给拉尔夫·J.密尔斯的信中,罗特克回忆说,“那时我还是孩子,我听到欧洲人、荷兰人和比利时人不停地说,这是全美国最美的温室。我父亲成为种植玫瑰和兰花的专家。很多品种从不出售。”
小时候罗特克体弱多病,对事物有敏锐的感觉。对他来说,这座巨大的温室是“象征全部生命的标志、一个孕育生命的地方、一座人间天堂”。这个植物、花卉和虫子的王国和温室附近的大片旷野,日后成了他第二部诗集《迷失的儿子及其他诗歌》和第三部诗集《赞颂到底!》的核心意象。
1922年,一连串悲剧降临到这个家庭。父亲和伯父冲突升级,最后不得不将温室卖掉。查尔斯和奥托一开始五五分账,后来查尔斯提出他要拿利润的54%,被奥托拒绝。1923年1月25日,查尔斯开枪自杀。4月29日,奥托因癌症去世。阿兰·西格说,表面上少年罗特克没有过度悲伤,但父亲葬礼那天晚上,在家里,他到父亲座位上就坐,从此一直坐在那儿。现在他是家庭的顶梁柱了。
父亲之死和痛失温室对他产生了刻骨铭心的影响。有着普鲁士人严苛作风的家长奥托事事要求完美,儿子达不到要求就会受鄙视。这种来自父亲的威权对于罗特克幼小的心灵无疑是一种压迫,是罗特克性格孤僻、离群索居的重要原因。对父亲,罗特克既感到惊悚畏惧,又怀着崇拜和温暖的爱。没有这份温暖的爱,他不可能将那座温室称为人间天堂。这种既怕又爱的复杂感情将一次次出现在他的作品中。
在阿瑟·希尔高中读书期间,罗特克的一篇有关“少年红十字”的演讲被翻译成26种语言。他给校报撰稿,学习成绩也很好,但好成绩在同龄人眼里意味着自绝于群体。为让大家接纳自己,他加入了一个名为Beta Phi Sigma的非法兄弟会,偷喝私下售卖的威士忌。
高中毕业后,他在一家腌菜厂打了一个夏天的工。1925年9月,他遵从母亲意愿进了位于安阿伯的密歇根大学,报的是文学·法律班。入学后他加入CHI PHI兄弟会,成了高年级学生的小跟班,受尽欺凌。他们让他戴小圆帽,然后说他戴的是便壶。他从违法的酗酒中得到快乐,为自己学到新的派头,尤其是言辞粗鲁的恶棍派头感到某种替代性慰藉。
一年级时教他修辞学的卡尔顿·威尔斯教授告诉阿兰·西格,那时罗特克是一名缺乏自信、怏怏不乐、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致的学生,没朋友,不参加班里的讨论。
少有的快乐来自网球,1927年他获得校内单打亚军,大四那年和队友打进双打冠军赛准决赛。但他真正的兴趣是成为一名诗人。
1929年6月,他以优异成绩在密歇根大学毕业。
家里希望他将来做一名律师。尽管注册的是文学·法律班,但他根本没上法律课。1929年秋他进密歇根大学的法律学校读了一学期,上了一门刑法课,成绩是D。
1930年春他从法律学校退学,改读文学硕士学位。1930年秋他进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在罗伯特·希利尔和I.A.理查兹门下学习。希利尔本人也是诗人,欣赏他的诗歌,鼓励他向杂志投稿,跟他说“不肯发表这些作品的编辑一定是傻瓜”。
不幸的是,大萧条给他的家庭造成了极大压力,他不得不退学找工作,向几所大学申请职位,最后被拉斐特——宾西法尼亚州一所很小的长老会学院录取。
在拉斐特学院教书期间,他在《诗歌》《新共和》和《星期六评论》上发表了19首诗歌,创作了第一部诗集《屋门大敞》中的部分作品,与诗人路易斯·博根和斯坦利·库尼兹成为了很好的朋友。他与博根有过一段吵吵闹闹的恋情,这份恋情后来演变为持续终生的恋慕。
1935年底他在位于兰辛的密歇根州立大学短期执教。这一年的11月11日夜里,令他后半生饱受创痛的躁狂抑郁症初次发作,详情无人知晓,后来他跟人说散步时有过“神秘体验”。回到校园,他在同事办公室里大吵大闹,人们不得不为他叫了救护车。妹妹琼和两位朋友安排他住进安阿伯私立默西伍德疗养院,在那儿治疗了两个月,其间他在密歇根州立大学的职位被人取代。
恶疾缠身,但他没有绝望。他发现某种程度上这种疾病有利于写作,可以让他探索截然不同的精神状态。
1936年至1943年,前后七年,他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执教。那段时间,他在《诗歌》《新共和》《星期六评论》和《斯瓦尼评论》等杂志发表作品。
1941年,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诗集《屋门大敞》,赢得了包括奥登在内多位诗人的好评。
1943年春,他前往佛蒙特州本宁顿学院执教。
1945年底,躁狂抑郁症再次发作,他不得不接受隔离治疗。与默西伍德的温和治疗不同,这次是令他惊恐的休克疗法。
1946年,也许受到密歇根大学在《新密歇根诗歌》上发表他十首诗这件事的鼓舞,罗特克第四次申请密歇根大学教职。英语系主任路易斯·布雷沃尔德知道他进过默西伍德疗养院,没接受他的申请。幸亏这时得到一笔古根海姆研究基金,让他能够在康复期间继续诗歌创作。
没过多久,贝宁顿学院的同事写给华盛顿大学英语系主任约瑟夫·哈里森的两封推荐信起了作用,罗特克在华盛顿大学谋得了一份稳定的工作。贝宁顿学院院长在推荐信中说他是“一个极端的混合体,一个喜怒无常、行为略怪的人”,“如果华盛顿大学能容忍他古怪的性格,就能得到一个最棒的教师”。
詹姆斯·克尼斯利在罗特克班上读过半年,对他在教学上的惊人投入铭记于心。“他的热情不单单倾注在写作上,也同样倾注在教学上。他似乎是将自己倾倒出来,与学生分享他的技巧,所以他的课堂上常常有一种感触得到,甚至能够看得到的能量。”
关于他诗歌写作教学的重要性,应有学者以专文甚至专著论述,这里只需提一下他在华盛顿大学几位学生的名字,就可知道这位导师是怎样功德无量——卡洛琳·凯泽、大卫·瓦格纳、詹姆斯·赖特、理查德·雨果,后來他们都成为美国诗坛重要人物。与这些幸运的学生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罗特克一辈子将自己视为一个初学者、一个“永远的新手”,因为在写作生涯初期,他没遇到对他的写作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导师。
1950年,罗特克在纽约与威尔士诗人迪兰·托马斯结交。据说罗特克曾向系主任推荐迪兰·托马斯,被系主任拒绝。
迪兰·托马斯是罗特克生命后期非常重要的朋友。在纽约,他们一起喝酒,谈诗,一起踉踉跄跄穿过城区去看老马克斯兄弟的电影,一起逛书店,看橱窗。在罗特克眼里,迪兰·托马斯是那种“喝自己的血、吸自己的髓以抓住某种素材”的诗人。
卡洛琳·凯泽在罗特克文集《论诗与技巧》的前言中说,罗特克后期生活中有两件大事(除了抑郁症),第一件便是迪兰·托马斯的死。“这件事给了他极大的震动,使得他反复想到痛改前非。结果是,他认真地试图戒酒……”
迪兰·托马斯和罗特克都有狂饮的恶名。迪兰·托马斯死后,罗特克在怀念文章里为他正名,说只见过他喝香槟、黑啤酒和淡啤酒。罗特克死后,卡洛琳·凯泽也为他作了适度辩护,“我见过泰德喝很多酒,但难得喝醉。他的客人往往比他喝得多。”
第二件是他与贝亚特丽斯·希斯·奥康奈尔(Beatrice Heath O'Connell)的爱情。“这使他的生活安定下来,最终诞生了自叶芝以来最伟大的情诗”。
1952年12月,在纽约举办诗歌朗诵会时,罗特克与从前的学生、“黑发姑娘”贝亚特丽斯邂逅。在本宁顿学院期间,贝亚特丽斯做过他两年半的学生。
卡洛琳·凯泽说“贝亚特丽斯是个大美人”,“那么会打扮,那么安静,罕见的俊妞!所有男人都惦记!”
1953年1月3日,罗特克与贝亚特丽斯结婚,W. H.奥登和路易斯·博根分任男女傧相。
他们去欧洲度蜜月。在意大利,他们住在奥登位于伊斯基亚福里奥的私宅里。“奥登将他的房子作为新婚大礼给我们(度蜜月),让我们在那儿从冬天住到春天。”他写信告诉朋友。
这位新郎是作为美国诗坛新宠抵达欧洲的,当地媒体称他为“美国最好的诗人”,迪兰·托马斯和伊迪斯·西特维尔说他是“美国最好的年轻诗人”,奥登同样对他不吝溢美之词。
1954年,诗集《醒来》为罗特克赢得他的第一个重要奖项——普利策诗歌奖。这一年获得全国图书奖的是康拉德·艾肯,获得波林根奖的是W.H.奥登。
罗特克在西雅图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岁月(其间有过两次严重的旧病复发),教书,写下死后问世的《遥远的旷野》,不停地出门接受奖项、朗诵诗歌,直到在泳池猝然离世。
1941年,罗特克耗时十年完成的第一部诗集《屋门大敞》出版,受到《纽约客》《星期六评论》《肯庸评论》《大西洋月刊》等杂志和诗人W.H.奥登、路易斯·博根、伊沃尔·温特斯的好评。爱德华·赫什说,“非常醒目的是它简洁的抒情性,丰富的技术手段,还有机智的新玄学风格。这位刻苦创作、非常敏感的年轻诗人受到T.S.艾略特有关玄学派诗歌重要论文的指引,同时受到,乃至过于受到约翰·邓恩、乔治·赫伯特和亨利·沃恩的影响”。
对罗特克早期诗歌有影响的诗人还有威廉·布莱克、莱昂尼·亚当斯、路易斯·博根、艾米丽·狄金森、罗尔夫·汉弗莱斯、斯坦利·库尼兹以及埃莉诺·怀莉。在这份影响力名单上,威廉·布莱克或许该占首位,无论形式还是观念,布莱克都是罗特克的重要导师——后者对于儿童诗、自由诗长句和格言风格的偏爱,可能主要源自布莱克。
对于自然的热爱与崇拜是罗特克诗歌的一大特色,也是他被称为浪漫派诗人的主要原因,这一点在这部诗集里已经有许多呈现——《间歇》《淡季》《中部大风》《赞美大草原》《寒气降临》《苍鹭》《未熄之火》《田园曲》都是他亲近可触摸的有形之自然的凭证,而《夜间旅行》可以视为他后期诗歌中最重要的颂歌系列的开端,不仅仅是对于细节的全神贯注的凝视,更有俯身于这风光,全身心融入其中的宗教般的激情——
我们冲进那把双层玻璃
敲得啪啪响的大雨。
车轮震动路基上的石子,
活塞猛拉,狠推,
我到半夜都没入睡
为了凝望我深爱的土地。
1948年3月,《迷失的儿子及其他诗歌》出版,这是罗特克诗歌生涯的转折点。
爱德华·赫什认为罗特克的第二部诗集完成了一次重要飞跃,“毫无疑问,在他的写作生涯中最伟大的时刻是从早期抽象风格的束缚中突围,开始具备他第二部诗集中出现的自由诗的结构。第一部诗集中的自白式承诺——‘我的隐秘大声喊叫和‘我的心屋门大敞,在第二部诗集中兑现了。当他与他密歇根童年时代的沃土发生关联,他找到了自己的核心诗学。敞开的屋宇这一符号被发现,记忆,玻璃围墙,温室世界——他曾经说它是‘象征全部生命的标志、一个孕育生命的地方、一座人间天堂——所替代。”
对父亲的崇拜、热爱和畏惧以及失去父亲和温室这个“人间天堂”的悲痛,是他经久不散的丧失感的源头,躁狂抑郁症则与焦虑感和紧迫感互为源头。丧失感、焦虑感和紧迫感,是他这一时期诗歌最醒目的标识。
有关温室的诗歌在这部诗集中占据了最多篇幅,这可以视为诗人以诗歌重建人间天国的一种努力。这些诗歌在技法上已经炉火纯青,足以带领读者重回那个精神王国的现场。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这位新浪漫派身上强烈的反浪漫主义色彩。
夜里,
暗淡的月光无法穿透刷了石灰水的窗玻璃,
热度骤降,
兰花的麝香味更浓烈,
从长满苔藓的诞生地四处弥漫:
这么多贪婪婴儿!
柔软的荧光指头,
唇瓣非死非活,
放荡的幽灵般的大嘴
在呼吸。
——《兰花》
这是未经裁剪和后期处理的温室真面目。这样的目光显然是非浪漫主义的。
斯坦利·库尼兹对这座神奇的温室有过精准的描述,“罗特克的温室世界挤满恶毒的力量,是一片考验圣徒和英雄的土地。一个满是浮渣、霉菌、秽物、鼻涕虫般柔软的茎梗、淫猥地伸出的植物种类的地方;一个潮湿、腥臭、吞噬并且肥沃得可怕的地方。幼枝一直戏水;嫩芽爆发,光滑如鱼。我们突然就置身地下,落入水中,掉进坟墓,返回子宫,陷入无意识的泥潭;像卡利班一样被投入我们动物性的自我,忍受胎儿般的痛苦。”
《迷失的儿子》是这部诗集中最引人注目的作品,是罗特克诗歌揭示身心创痛、技法上趋于复杂和多声部的开端之作,也正是在这首诗里,集中涌现了日后将一再发出回声的这个多棱镜般的灵魂,以及他诗歌技法的多个面向。
—— 一个失去人间天堂的迷失者的形象:
告诉我:
我上哪条路;
我出哪扇门,
去何处,走向谁?
——对于父母的复杂情感:
太阳反对我,
月亮拒绝我。
……
雨有父亲吗?所有洞穴里全是冰。这儿只有雪。
我冷。我冷彻骨髓。父母取笑我。
我父亲是畏惧,畏惧老爸。
他的目光令石头枯竭。
然后蒸汽来了。
管子砰砰响。
热气在植物幼芽上急匆匆旋转。
站好!站好!
爸爸来了!
——与自然万物的接通:
蜗牛啊,蜗牛,在前方给我照明,
鸟儿啊,用温柔的悲鸣送我回家,
虫子啊,理解我。
这是我陷入困厄的时光。
——神秘事物的突出地位:
坐在空荡荡的屋里,
看阴影在那儿爬,
在那儿抓。
一只苍蝇飞过。
声音,突破寂静。
说着什么。
以蜘蛛或扑打
窗帘的飞蛾的形态现身。
……
披着猫皮
拱著美洲鳗的脊背,
长满膘的身子打滚,——
它就这样触摸。
——对于光明和生机勃勃生命力的渴求和信任:
光在辽阔的旷野上传送;
持续传送。
野草不再摇曳。
心灵穿过晴朗的天空,
寂静无声,绝非形单影只。
是光吗?
是内心的光吗?
是光芒深处的光吗?
变得活跃的寂静,
还是寂静吗?
一种生机勃勃的可理喻的精灵
曾带给你欢乐。
它将再度莅临。
安静。
等吧。
——对于童谣、民间文学和潜意识的大力开掘和意识流手法的实验:
它像耗子吗?
比耗子大。
比腿小
不止一个鼻子,
就在水下
它像平常一样游着。
软得像老鼠?
会皱鼻子吗?
能踮着脚尖
跑到屋里来?
可以说,这首诗是打开罗特克位于灵肉交接处那个神秘世界的一把至为关键的钥匙。
在《迷失的儿子及其他诗歌》中,罗特克的写作变得复杂,似乎一下打开了一个神秘的宇宙——不是三言两语就能交待清楚的世界,而是“问题比答案还多的王国”。这里有强烈的内心独白的色彩,有朝向无意识深处的挖掘。早期的清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近乎不知所云的内心的声音。
罗特克和他的密友迪兰·托马斯都被认为是弗洛伊德的忠实信徒。人们想当然地以为他们都是左手放着弗洛伊德的大作,右手写自己的诗歌。在罗特克生命的最后一年,有位格贝尔小姐为完成有关罗特克诗歌中“弗洛伊德信徒和基督徒情感之融合”这一主题的硕士论文写信给他,希望他给出他的诗歌受到“弗洛伊德作品或观念之影响的正式说法”。罗特克回信表示爱莫能助,“坦率地说弗洛伊德的书我读得很少。另一方面,我的几个爱幻想的朋友在维也纳人那儿做过心理分析,我得说我从他们喋喋不休说起的疗效里携取了某些观点……另一方面,我早就认识纽约的艾斯勒和伦敦的霍弗这些杰出的心理分析师,他们的大部分谈话至少受到弗洛伊德的影响。但我遇见这些人是在我完成这些你可能认为它们‘弗洛伊德色彩的诗歌很久以后……我读过一点荣格的《探索灵魂的现代人》,还是那句话,最近才读的。”
路易斯·博根是最了解罗特克的朋友之一,她知道这罕见的着魔绝非病理上的癫狂和技艺上的失控。她认为在《迷失的儿子》这首长诗里,罗特克“一头扎进潜意识的池塘,提取各种湿冷、无定形的材料。他经常使用格言、谚语、咒语和打油诗的语言来构造……《迷失的儿子》是在意识的完全操控下完成的。它的效果像所有受到控制的艺术一样,是在诗人的驾驭之中的……”
随后的作品走得更远,读者也将在诗人意志的强力中习惯他古怪的表达——那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却不可阐释的古怪。很多时候,读者只好沿着他力量的剧烈弧线被抛射到极度陌生的空间里。
1951年出版的《赞颂到底!》是他最具实验色彩的作品,其中一些作品尽管嵌入了自传碎片,却有着浓烈的梦魇色彩,令人如入迷宫——这些自传性碎片完全不足以成为认知他的路标。
小猫用脚
咬东西;
爸爸妈妈
有更多牙。
坐在摇椅
下边玩耍
直到母牛
全都下了小牛。
这是《你敲门,门就为你大开》第一、二小节,读来犹如谜语。张子清教授在有关罗特克的论述中提到,诗中的“脚”代表阳物,第二节说的是父母孕育新生命。这里的语感和意识状态完全是一个对成人世界一无所知的懵懂孩子的,而这恰恰是罗特克想要的那种生命的史前状态。
《我需要,我需要》的最初四行同样近乎婴儿的原始意识——
深碟子。盛海鱼。
我吃不到我母亲。
呼!我熟悉汤匙。
它与我嘴巴搭档。
丹尼尔·霍夫曼认为这一节说的是孩子的断奶。他认为在《众城门哪!请让开!》《哦,哄我安静,哄我安静吧》和《迷失的儿子》等作品中,罗特克“似乎直截了当地处理意识的原型,就像荣格给它们下的定义一样”。
在罗特克写作最晦涩的这个时期,他迷恋的或许并非某些人臆想的精神分析学说。1952年1月他写信给肯尼斯·伯克,回顾了自己的教学生涯,希望教学和写作可以互补。他渴望大量其他领域的阅读以弥补自己的短板,“我已经相当‘熟悉英语诗歌……但在哲学、历史和科学方面有那么多东西我想要探寻……诗歌方面,目前我已经如我所愿拓展了个人神话。我想让过去派上更大的用场。对我来说,这意味着广泛的阅读尤其是深深地沉浸在柏拉图哲学的传统里,沉浸在斯宾诺莎、康德、布拉德雷和柏格森这样的哲学家身上……我希望用我自己的方式吸收他们。目前——我渴望阅读——而非写作。我想得到哥伦比亚或纽约公共那样的大图书馆的资源。我相信作为一个作家我会呈现出一种完全不同的风格……”
第二年,完全不同的风格来了。1953年9月出版的《醒来:诗选1933-1953》收入了《屋门大敞》部分作品、《迷失的儿子及其他诗歌》大部分和整本《赞颂到底》,其中最重要的是新作《写给约翰·戴维斯爵士的四首诗》,而另一首新作《老妇人冬日絮语》无疑是下一部诗集《说给风听》中组诗《一位老妇人的沉思》的前奏。
斯坦利·库尼兹在回忆文章里提到《写给约翰·戴维斯爵士的四首诗》的来历,“……他让我选点东西读给他听。我拿起约翰·戴维斯爵士那首被人忽视的伊丽莎白时代杰作《乐队》,一首不知为何他从未发现的诗,尽管他在诗歌方面有着广泛的涉猎。我记得他对这清澈音乐的反应是何等强烈。与这首诗的邂逅,加上他對于叶芝诗歌的迷恋——凌驾于一切之上的节奏令他陶醉——使他能够创作出动人的组诗《写给约翰·戴维斯爵士的四首诗》,为他后期诗歌确定所要采用的韵律。”
我需要一个地方歌唱,我需要舞厅,
我已允诺我的耳朵
我将歌唱,啸叫,与熊一同奔跑跳跃。
……
我试着把自己的身影投向月亮,
这时我的血液跳跃,伴着一首无字歌。
……
是啊,我对舞蹈着了魔……
……
欢乐比狗跳得快。管它呢!管它呢!
我回吻她,却唤醒一个幽灵。
——《写给约翰·戴维斯爵士的四首诗》第一首《舞蹈》
罗特克在《论“个性”》一文里回忆了这件作品的诞生。
“我深陷于一个诗人特殊的愁苦里:一个略显漫长的枯竭期。那是1952年,我44岁,我想我完蛋了。那时我一个人住在华盛顿爱德蒙兹一个大房子里。我一读再读——不是叶芝,而是罗利和约翰·戴维斯爵士……
“突然,薄暮时分,那首《舞蹈》从天而降,并且倏地自动结束——大约三十分钟,也许将近一小时,全部完成。我感到,我清楚,我成了。我走来走去,我哭泣;我跪下——在我写出我很清楚是好诗的作品后我总是跪下。但在同一时刻,上帝作证,我真切地意识到一种神灵的存在——仿佛叶芝本人就在那间屋里。一种恐怖的体验,因为它至少持续了半个小时。那间屋子,我再说一遍,充满了一种超自然的存在:那些特殊的墙似乎在闪光。我为欢乐而哭泣。我终于再次成为另一位。他,他们——逝去的诗人——与我融为一体。”
他说这是他最深邃的生命体验之一,不接受别人的任何阐释。
或许,罗特克的“欢乐颂”(前边提到,他对自己的定位是“一个爱的诗人,一个赞颂的诗人”)正是始于这首有关宇宙与人之舞蹈以及人之情欲及其升华的颂歌。他多多少少开始清除郁积于心中的罪孽感和对于死亡的畏惧,不可抑制的向下、向黑暗,扭转为向上、向光明。这一转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从一团漆黑和可怕的阴湿中,从他强迫症般地自认为的堕落中,从无休止地向内的精神活动中,从笼罩他全身心的悲观中来,因此更有力量。
伴随这种精神上的转折的,是诗艺的嬗变——他开始告别前两部诗集中的晦涩与拒绝阐释,努力转向清澈与透明。
1957年秋,罗特克出版了包括43首新作的诗集《说给风听》,其中有著名的情诗《我认识一个女人》、纪念叶芝的《垂死之人》和纪念母亲(三年前去世)的《一位老妇人的沉思》。这部诗集获得了1959年两大诗歌奖——波林根诗歌奖和国家图书奖(他的密友库尼兹摘取了这一年的普利策诗歌奖),此外还获得了埃德娜·圣·文森特·密莱奖、朗维尤基金奖和太平洋西北作家奖。年近五十,罗特克成为当之无愧的重要诗人。
在《说给风听》的第二辑“情诗”里,罗特克将爱情提升至生命核心的位置。贝亚特丽斯或许是反浪漫主义和反讽的二十世纪诗歌中最接近天使的原型之一。毫无疑问,她是诗人抵抗内心黑暗和罪恶感、迈向欢乐和光明的重要驱动力——罗特克对上天这份恩赐的回报是奉献一系列卓越的情诗。
她将这旷野变成闪光的海洋;
我像孩子一样在火焰和流水中嬉戏,
在大海雪白的泡沫上东倒西歪;
像一根湿透的原木,我在火焰中歌唱。
在那个最后的瞬间,在永恒的边界,
我遇见爱情,我进入我自己。
——《梦》
但他仍然是肉身凡胎,满足的肉体仍然不能与灵魂统一,仍然在冰与火之间摇摆。
我们从未逃出肉体。年轻时,谁做到了?
一朵火焰自动跳跃:我认识那火焰。
某种狂热救了我们。而我是不是狂热得太久?
灵魂知道肉体必然枯萎。
梦不过是令人想起她面孔的一个瞬间。
她将我从冰变成火,从火变成冰。
……
我已识破能识破的所有欲望;
当我独自陷在声音和烈焰的中心
我为我像的那个东西哭泣。
——《爱用警句的男子》
圆满的爱情并未让他完全进入光明世界,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疾病作祟,也正因为疾病的阴影,他的情诗乃至这部诗集的整体调性,仍有不可清除的黑暗阴郁的一面。或许在他的潜意识里,爱与生死密不可分,爱使他从孱弱变得强壮,与此同时,他越是身陷爱的极乐,越是感觉到死亡的逼近。
第四辑《垂死之人》和第五辑《一位老妇的沉思》显示出诗人在努力跨越生死大限、走向复活这一重要时刻(“此刻”)的摇摆和突破的意志。
在《垂死之人》中,“我”已经意识到,“所有的色欲之爱都是在坟头起舞”,所以“我焚毁肉身”:
我掉转目光望着
别的身影而不是她的
此刻,窗戶一片模糊。
在最可怕的我的欲望之夜,
我敢怀疑一切,
我会把同样的事情再来一遍。
谁在打门?
他的到来是可以期待的。
“别的身影”就是即将到来的“他”?这个“他”是作为“肉”的另一极的“灵”,还是他将成为的那个复活的自我?
在复杂的冥想中,这复活的自我有着强烈的梦魇色彩,置身于亡灵的氛围:
陷入垂死的光,
我想象新生的自我。
我的双手变成蹄子。
我穿着从未穿过的
铅制的衣服。
……
一个亡魂从失去知觉的大脑里出来
摸索我的窗台:抱怨将来的新生!
背后那家伙不是我朋友;
搭在我肩上的手变成动物的犄角。
他想起父亲。父亲在垂死之际,同样掉转目光,望着别的身影——
我眼看父亲光着身子,正在缩小;
他转过脸去:那儿另有一人,
走在边缘,喋喋不休,无所畏惧。
他像一只鸟,颤栗在无鸟的天空,
敢用目光盯住任何地方。
他听见群鸟歌唱,这是他诗歌中与舞蹈并置、反复出现的一个意象,象征着生命的欢乐:
哦,远方亲切的旷野,我听见你的鸟群,
它们歌唱,它们歌唱……
这首诗的最后部分是对生命意志力的赞颂,是对灵魂出窍般融入宇宙获得新生的神往,是对无边虚空的蔑视——
顶点的边缘依然令人胆寒;
在光的尽头就连想象
也无法获胜:他敢于活着
不再做一只鸟,却依然拍动翅膀
对抗广袤的虚空。
有关他的作品笼罩在艾略特和叶芝阴影之下的说法让他感到巨大的压迫。在1959年6月12日写给拉尔夫·J.密尔斯的信里,他任郁积的怒火狂泻,几乎失态——
早在接触艾略特和叶芝之前我接触的是他们的前辈诗人;实际上,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两位我都拒斥……所以“老妇人诗篇”第一首中更松散的诗行里的某种东西貌似与艾略特接近而实际上也许脱胎自惠特曼,技法上他对艾略特影响很大——而艾略特,据我所知,从未承认这一点——哦,他永远故作风雅:只提但丁、法国人、詹姆斯一世时期作家,等等等等……
……而当叶芝的历史抒情诗似乎压倒我的时候,如果我没在更私人的抒情诗和情诗方面超越他,那我就死定了。所以我说斯诺德格拉斯是该死的耳聋的笨蛋,居然在我那些情诗中看到叶芝:仔细听听四部分组成的《说给风听》中的节奏——难道那是叶芝的调子吗?……
至于“老妇人诗篇”,我是想:第一,创造一个角色,对她来说这样一种节奏是土生土长的;让她能够作为一个戏剧角色而不仅仅是我本人。《四个四重奏》中的那个艾略特是陈腐的,他在精神上是陈腐的,老头子……我的老妇人陈腐吗?见鬼去吧她是这样的:她不屈不挠,她勇敢,她明白生命……第二,艾略特不仅陈腐,作为神秘主义者他还是骗子……
W.H.奥登最亲密朋友之一泰克拉·比安基尼告诉我,在伊斯基亚海滩上,威斯坦说起他一度担心我和叶芝太像,现在他放心了,因为我已经超越了他(指叶芝——本文作者注),胜过了他,走在了他前边……
1963年,罗特克完成诗集《遥远的旷野》后猝然离世。贝亚特丽斯承担了整理书稿的工作,库尼兹联络出版事宜。1964年《遥远的旷野》出版,1965年获全国图书奖。这一年获普利策诗歌奖的是“自白派”诗人约翰·贝里曼的《梦歌77首》。
《遥远的旷野》中最耀眼的是由六首长诗构成的《北美组诗》。可以说,这组作品可靠地宣告,罗特克终于在生命最后时刻抵达了精神和诗艺的巅峰。爱德华·赫什说,“在忍受了如此多的痛苦之后,罗特克拥抱了一个幸福的精灵,完成了最终的转换,获得了足可安慰的自我承认,生命的安慰……”
他曾将自己归入快乐诗人的行列,“不管这些诗歌里有多少胡言乱语,不管它们多么杂乱无章,多么黑暗,充斥了多少废物,我仍将自己算作快乐诗人中的一员。”现在他终于成为一个大放光明的快乐的诗人。
爱德华·赫什认为,《北美组诗》“有意识地回应了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他引用‘东库克中的——‘老人应该做个探险家吗?——然后贡献了一个作为智慧原始派艺术家的美国诗人的意见,‘我要做个印第安人。/奥格拉拉部?/还是易洛魁部吧。鉴于艾略特是自中西部向东,走向新英格兰,最终返回英格兰,罗特克反其道而行之,一路向西,自密歇根奔向达科他、落基山脉和靠近太平洋的西北。他将自己置于惠特曼的阴影下,受惠特曼精神统辖,呈献了一份热烈的自由诗的美洲大陆目录。”
在生命的最后阶段,罗特克融入宇宙万物、进入真正的灵魂状态的信念更坚定,所以才会有《渴望》中第二节和第三节的一连七个“我要”——
我要在更远处;我要比月亮更遥远,
……
我要听懂鱼儿,变黑的鲑鱼,发疯的旅鼠,
舞蹈的孩子,和胀大的花朵说了什么。
……
我要忘掉令人恼火的方言,所有的恶意歪曲和憎恨;
我要相信我的痛苦:平静地望着玫瑰生长;
我要喜欢我的双手,嗖嗖响的树枝,改变阵形的密集的鸟儿;
我渴望仪式中心不朽的宁静;
我要做小溪,夏末在巨大的布满条纹的岩石间迂回前进;
我要做一片叶子,我会爱所有的叶子,爱这芬芳无序终有一死的生命,
……
此刻,他变成另一个生命,或许就是他聚精会神冥想凝望的那个生命。尼采那句谶语——“凝视深渊过久,深渊终将回报以凝视”是他一生最传神的写照,他真的被深渊吸附纠缠了一辈子,但在生命最后时刻,他竟然跨了过去!
我,地狱归来朗声大笑的人,
变成另一个东西;
我的目光延展到比最远浪花更远的地方;
我迷失方向,发现自己在长河里;
又一次我被抱住;
而我紧抱住世界。
——《长河》
不知道《再一次,跳起圆舞》是贝亚特丽斯、库尼兹还是罗特克本人放在了这部诗集的最后,无论是谁的编排,都可以说是最好的编排,在这首十二行的短诗里,罗特克的生命,罗特克的“欢乐颂”升至喜悦的穹顶——
如今我最喜欢我那
与鸟儿,与不朽的树叶,
与游鱼,与搜寻的蜗牛,
还有改变一切的看相伴的生命;
我与威廉·布莱克共舞
为了热爱,为了热爱;
万物归一,
当我们舞着,舞着,舞着。
参考资料:
Theodore Roethke,Selected Poems,New York,The Library of America,Edward Hirsch,editor,2005
Theodore Roethke,On Poetry and Craft,Washington,Copper Canyon Press,2001
Selected Letters Of Theodore Roethke,Seattle &London,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Ralph J.Mills,editor,1968
Stanley Kunitz on Theodore Roethke,Originally published in Crossroads,Spring 2002
(https://poetrysociety.org/features/tributes/stanley-kunitz-on-theodore-roethke)
Linda Robinson Walker,Theodore Roethke:Michigans poet, Michigan Today,summer 2001
張子清《二十世纪美国诗歌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
(美)丹尼尔·霍夫曼主编《美国当代文学》,中国文艺联合出版公司,1984
郑敏编译《美国当代诗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