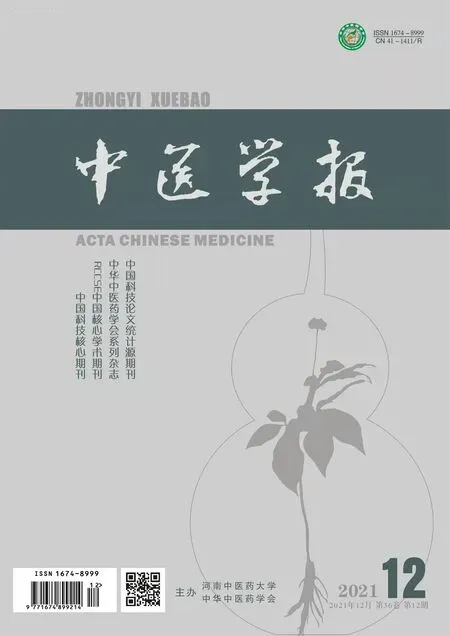基于病机“拐点”探讨乙肝后肝硬化的证治*
张红陶,钟玉梅,浦琼华,廖华君
1.溧阳市人民医院,江苏 溧阳 213300; 2.南方医科大学,广东 广州 510515; 3.无锡市锡山人民医院,江苏 无锡 214000
肝硬化是一种由不同病因长期作用于肝脏引起的慢性、进行性、弥漫性肝病。其病理基础为在肝细胞广泛坏死基础上产生肝脏纤维组织弥漫性增生,并形成再生结节和假小叶,若病变继续发展,晚期可出现肝硬化腹水、上消化道出血、肝性脑病、肝肾综合征等多种并发症。肝硬化作为“肝炎-肝硬化-肝癌”三部曲中重要的一环,对其早中期的及时干预与治疗尤为关键。我国由病毒性肝炎导致的肝硬化居于肝病首位。乙肝后肝硬化在早期肝纤维化阶段若治疗及时恰当,其病程往往可逆。
未病先防、既病防变、已病防传,此为中医“治未病”三大核心思想。从病程进展方面看,慢性肝炎迁延不愈,反复发作,日久必然导致肝纤维化、肝硬化。肝硬化早期阶段,肝功能尚处于代偿期,病情尚未十分严重,若及时诊治,尚有回旋余地。若任病情继续发展,至肝功能处于失代偿期,发为癥积,土虚木贼,便为难治[1]。根据笔者多年临证经验总结,以及联系近现代医家治疗乙肝后肝硬化的经验教训发现,在乙肝后肝硬化的病程进展中,存在一个短暂时期的病机“拐点”,即此病的病机转变,在此“拐点”前,较为易治,肝硬化病程可逆;在此“拐点”后,较为难治,肝硬化不可逆。
1 病机“拐点”概述
中医之道,不论刺法或是方药,治疗疾病均非常讲究时机的正确把握。中医认为,治病犹如弯弓射箭,真正知“道”的上工,于最恰当时将箭射出,间不容发,可正中病所;不知“道”的下工,空有弓箭,却不知应该何时出手,扣而不发,往往错失良机[2]。诚如《素问·离合真邪论》云:“知其可取如发机,不知其取如扣椎。故曰知机道者,不可挂以发,不知机者,扣之不发,此之谓也。”此外,病机与战机具有相似点,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战机亦是间不容发。因此,古人谈到:“兵法曰:无迎逢逢之气,无击堂堂之阵。刺法曰:无刺熇熇之热,无刺漉漉之汗,无刺浑浑之脉”,皆为对“战机”“病机”审时度势的充分认识。人体玄冥幽微,疾病纷繁复杂,病机更是变化万端,病机进展一般包括由表入里、由浅入深、从阳入阴、从热转寒、由实转虚等不同的情况,然表里之隙、阴阳之间、寒热之隔、虚实之化,中间必然存在病机之“拐点”。倘若医者可以抓住关键点,运用医疗手段予以干预,仿庖丁解牛法,以“无厚入有间”,则可截断病情的进展。如此,则病邪难以再行深入,医者掌握病机之关键,疾病有望向愈。
乙肝后肝硬化多因延续慢性肝炎之势而成。因此,该病在早期阶段,尚属病在气、在阳,为无形之邪;至后期阶段,则属病在血、在阴,为有形之邪。《黄帝内经》云:“阳化气,阴成形”。此文虽为阐述宇宙、天地、万物、阴阳之理而设,然乙肝后肝硬化的病理进展亦与此理相通。病在早期,为肝脏功能失调,病位偏表,未及血分,故曰其病属阳;延至晚期,肝脏之形质出现异常,病位偏里,已入血分,故曰其病属阴。所以,其病机进展实为由阳入阴之过程,病在阳,其病易治;病及阴,其病难调。医者贵在细察精详,见微知著,能准确捕捉到其病机之“拐点”,及早干预,已病防传。
2 病机“拐点”基本证治
慢性乙型肝炎是一个慢性病变发展过程,众多医家认为其与湿热、疫毒等邪气紧密相关。湿热毒邪蕴于中焦,内熏肝胆,伏于血分是慢性乙型肝炎的基本病机。其病位可累及肝、脾、肾,湿热、气虚、气郁、血瘀等病邪均可涉及,其中“湿热之邪”被认为是病机的关键[3]。因此,清热利湿、清肝利胆的治则在慢性乙型肝炎的治疗中始终贯穿[4]。若慢性乙型肝炎病情进一步进展,则发展为肝纤维化、肝硬化,湿热瘀毒、肝失条达、肝郁脾虚、肝肾阴虚、脾肾阳虚、痰瘀作祟为其病机[5]。其在早期阶段,病机及临床表现与慢性乙型肝炎相较并无明显差异,患者大多表现为面色黄暗,纳呆,不欲饮食,腹胀,四肢乏力,头昏沉,精神倦怠,右胁下不适,大便成形或溏薄,舌淡红,苔黄腻,脉弦濡等,故以清热利湿、解毒化浊、疏肝健脾为治疗大法,预后良好。若患者年老体衰,病情迁延不愈,或起居调养不慎,或治疗不当,病情进一步恶化,及至肝硬化后期,病机进展为脾肾阳虚,或肝肾阴虚,或瘀血内结,患者大多表现为面色晦黯无泽,肝掌,目黄浑浊无神,脾大,胁肋刺痛,腰膝酸软,形瘦,或腹满如鼓,四肢无力,舌下络脉曲张,脉弦硬或细微。此时脏气衰微,瘀血内结,正虚邪盛,故为难治,预后较差。
通过细致的临床观察以及根据众多肝病名家的临床经验总结,笔者发现,此病在进展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个较为短暂的病机“拐点”。在“拐点”前,其病属阳,位于气分,尚为易治;在“拐点”后,其病属阴,位于血分,其病难治。在“拐点”时期的患者大多表现为神情倦怠,面色暗黄,腹部满闷,夜间加重,两胁痞满,胸胁下胀满支结或刺痛,或腰背疼痛,四肢末端麻木、发凉,小便利,大便溏薄,大便每日二、三行或三、四行,舌苔白润或白腻不化,脉弦缓,沉取无力。值此病机“拐点”的时期(从阳入阴、从热转寒、由气入血),伤寒名家刘渡舟先生认为,此时最宜运用柴胡桂枝干姜汤,以疏泄少阳之郁热,温化太阴寒湿,扼制病发趋势,扭转病情转归,实有力挽狂澜之功,用之恰当,则有神出鬼没,能使人死里逃生之神效[6]。《伤寒论》第147条云:“伤寒五六日,已发汗而复下之,胸胁满微结,小便不利,渴而不呕,但头汗出,往来寒热,心烦者,此为未解也,柴胡桂枝干姜汤主之”,此方主治少阳胆热、太阴脾寒、三焦水气不利之证。方中柴胡用量重达半斤,与黄芩三两相配,剂量比为83,契合《河图》“三八东方木”的寓意,取其疏泄肝胆之功;干姜、甘草,辛甘化阳,主入脾阳,散太阴之寒湿;牡蛎软坚散结,佐柴胡、黄芩散肝胆郁结,主治胁下痞硬、胀满;桂枝合干姜、甘草,通阳化饮,以行三焦;瓜萎根生津清热。诸药合用,共奏清胆温脾、化气利水之功。
3 病机“拐点”分类证治
3.1 由热转寒予柴胡桂枝干姜汤合理中汤乙肝后肝硬化早期一般会延续慢性乙型肝炎的病机,初起即为肝胆气郁,湿热困脾,随着病情进展,气郁时间过久,终致因耗气而导致气虚;湿邪困阻阳气日久,终致戕伐阳气而虚寒内生[7]。因此,乙肝后肝硬化患者,初起往往表现出湿热相合,胶着不爽,气机郁滞之症状,口干口渴,口中黏腻,头部昏沉,有如物裹,肢体倦怠,手足心热,面部油腻如垢,大便黏滞臭秽,小便偏黄,舌苔黄腻,脉濡数等。及至病机“拐点”时期,若患者出现面色偏暗少泽,四肢末端发凉,口淡不渴,腹胀不减,减后又胀,大便溏薄或夹有未消化食物,大便每日数次,舌苔白润或白腻不化,脉弦缓,沉取无力等症状,病机则有由热转寒之趋势。立足六经辨证,此时实为病从少阳转入太阴之机,亦为三阳转三阴之门户。所以,治疗不宜过于寒凉,而宜从温燥、温化入手,诚如叶天士所言“湿热一去,阳亦衰微矣”。因此,方选柴胡桂枝干姜汤合理中汤(干姜、党参、炒白术、炙甘草)化裁,其中加重干姜剂量,令太阴得温,阴寒消散;人参、炒白术补益脾土,健中燥湿。若患者阳虚累及脾肾,则宜选柴胡桂枝干姜汤合附子理中汤,取附子纯阳大热,走而不守,通行十二经,暖肾温脾,直达中下二焦[8]。
3.2 由气入血予柴胡桂枝干姜汤合旋复花汤不论是在慢性乙型肝炎时期,抑或是乙肝后肝硬化初期,病机大多涉及肝气郁滞,气郁日久必然导致血瘀。因此,有学者提出,化瘀法必须贯穿于肝硬化治疗始终。然而,化瘀法具有行气化瘀、消积化瘀、通络化瘀、温通化瘀、凉解散瘀、峻下逐瘀、散结破瘀等多种类型,若选择不当,不仅于病无益,且戕害机体正气,导致邪盛正衰。因此,化瘀法的选择应当审慎。一般而言,乙肝后肝硬化初期,宜选用行气化瘀、凉解散瘀法;乙肝后肝硬化的后期,则宜选用消积化瘀、散结破瘀等法。当病至病机“拐点”时期,病机出现从阳转阴、从热转寒、由气入血的变化特点,患者表现为腹部胀满滞闷,夜间加重,两胁痞满,胸胁下胀满或刺痛,舌质紫,舌下络脉曲张,脉象弦涩欠畅等特点,此时宜选活血通络、温通化瘀法,令络脉瘀滞得解,不致陷入血结之弊。《临证指南医案》云:“初病在经,久痛入络,以经主气,络主血”。因此,此时不宜过早破血逐瘀,以免损伤正气,而宜稍行瘀滞,通络化瘀,方选柴胡桂枝干姜汤合旋复花汤(旋复花、茜草、葱白)。方中旋复花善通肝经,疏肝活血,下气散结;茜草为治肝着要药,功可化瘀通络;葱白通阳散结;诸药共成活血通络,化瘀散结之剂[9]。若络脉瘀滞较重,则可加入丝瓜络、红花、土鳖虫、制鳖甲等通络之品,轻用即可,不必重剂。
4 验案举隅
张某,男,68岁。2018年8月3日初诊。主诉:反复胁下胀闷不适10余年,加重3周。患者10余年前诊断为慢性乙型肝炎,1年前诊断为肝硬化,期间给予抗病毒、护肝等治疗。刻诊:患者面色黄暗油腻,两胁下胀闷不适,偶有刺痛感,夜间为甚,口苦口干,心烦,喜饮温水,大便每日2~3次,便质稀溏,偏黏,小便可,舌淡红,苔重度白腻而干,舌下络脉曲张,舌两侧少量瘀点,脉弦缓,沉取力弱。腹部超声示:肝硬化。血生化示: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42 U·L-1,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49 U·L-1,总胆红素26 μmol·L-1,γ-谷氨酰氨基转移酶 78 U·L-1。诊断:乙肝后肝硬化。证型:胆热脾寒,瘀血阻络。治法:清胆温脾,活血通络。方剂:柴胡桂枝干姜汤合旋覆花汤。用药:柴胡15 g,桂枝 10 g,黄芩5 g,干姜5 g,生牡蛎(先煎)25 g,制鳖甲(先煎)25 g,酒大黄5 g,苍术 15 g,旋覆花10 g,茜草15 g,葱白3茎,炙甘草5 g。7剂,每日1剂,每日2次。二诊(2018年8月10日),前药服至第5剂,自诉胁下胀闷刺痛好转,大便稀溏明显改善,便质已不黏,口不苦,纳眠可,舌淡红,苔腻减轻,脉弦缓,沉取不足。效不更方,前方继服14剂,随访诸证明显改善。
按:患者慢性乙型肝炎病史较长,迁延不愈,日久肝脾同病,气血瘀滞,进展为肝硬化。患者口干口苦,心烦,胁下胀闷,此为肝胆气郁失疏,胆火内郁;大便稀溏,质黏,喜饮温水,苔白腻而干,为太阴脾阳亏虚,运化失职;胁下偶有刺痛感,舌下络脉曲张,舌两侧少量瘀点,为血脉瘀滞,络脉不通。此时正为疾病从阳转阴、由热转寒、由气入血的病机“拐点”关键时期,故予柴胡桂枝干姜汤合旋复花汤疏肝行气、清胆温脾、活血通络,加苍术以增强其运脾化湿之功;加制鳖甲、酒大黄以增强其化瘀软坚之力。诸药合用,少阳、太阴同治,行气、活血兼顾,故可截断病情由阳入阴之传变,改善患者预后,疗效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