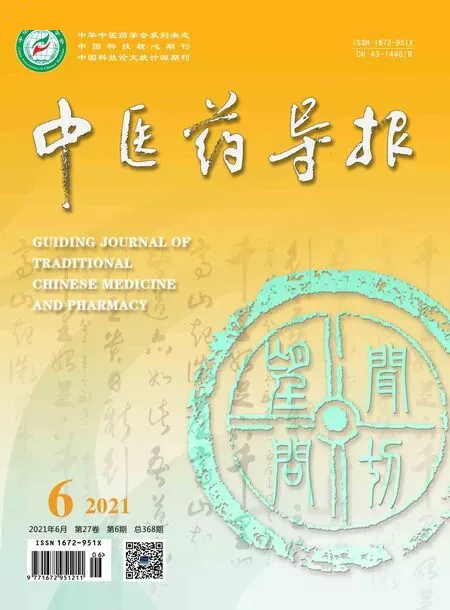秦敏运用岭南飞针疗法治疗焦虑障碍学术经验撷要*
黄春梅,陈韵龙,秦 敏
(1.广州中医药大学,广东 广州 510405;2.广东省第二中医院,广东 广州 510095)
焦虑障碍,即焦虑症,是临床上最常见的精神障碍疾病之一[1]。全球12.5%~16.7%人口患焦虑障碍,该病终身患病率最高可达28.8%[2-3]。目前以心理及药物为主的干预治疗效果一般,常伴高复发率、药物依赖及多种副作用[4]。当前,针刺治疗焦虑障碍已广泛应用[5],其疗效明确,未见明显不良反应报道,治疗成本低。但焦虑障碍患者通常伴随痛觉阈下降[6],针刺带来的疼痛可能加重焦虑症状,直接影响针刺效果。而岭南飞针疗法在进针速度上占明显优势,尤能减轻“过皮”时的疼痛感[7]。因此,岭南飞针疗法可提高针刺疗效。秦敏教授,硕士生导师,广州市首批中医优秀临床人才,全国第四批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继承人,现任广东省临床医学学会岭南飞针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秦敏教授从医三十余载,统筹施用岭南飞针疗法之“理、法、方、术”,在临床中治疗脑病、小儿脑瘫、顽固性失眠及精神类疾病经验丰富[8-10]。笔者师从秦敏教授,有幸长期跟师学习,兹以本文简介岭南飞针疗法,并着重总结秦敏教授运用岭南飞针疗法治疗焦虑障碍的学术思想和临证经验,以嗣同道。
1 岭南飞针的创新
“飞针”,又称“跑马针”“摘针”,在岭南针灸流派之中广受推崇[11]。随着岭南针灸学在明清时期迅速发展,岭南飞针疗法也应运而生。秦敏师从国家级名老中医“飞针博导”张家维学习、传承与发展岭南飞针疗法。在传统飞针选穴的基础上,以中医整体观为理,打通任督二脉为法,对头部、腹部、背部进行分区,创新演化出岭南飞针疗法“腹针、头皮针、围刺针”三大飞针系列[12],现已纳入广州市第七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
2 诊疗思想
焦虑障碍在现代医学中可细分为广泛性焦虑障碍与惊恐障碍。传统中医学无此病名,根据临床表现,可归入“郁证”“脏躁”“心悸”“怔忡”等范畴[13-14]。本病病因病机较为复杂,但总的病机属七情内伤致脏腑气机紊乱,经脉失调,肝郁胆滞,久而阴阳失衡、神气失养[15]。从岭南飞针疗法之“理、法、方、术”解读,将更充分认识该病。
2.1 岭南飞针疗法之理 秦敏提出,岭南飞针疗法之理论是从中医整体观入论。秦敏认为脏腑、组织和器官均各有其生理功能,这些功能又都是人体整体活动的组成部分,这就决定了人体内部的整体统一性[16],人体的组织、器官及其功能都归属于以五脏为核心的5个系统中。就情志的产生来说,《黄帝内经》提到:“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志”,说明情志原本是五脏五气的正常产物。一旦情志过极,则脏腑受累,影响气机,从而导致情志病的产生。崔爱军等[17]研究也发现,阴性性格的人,情绪稳定性差,更容易出现焦虑状态。因此,秦敏强调,情志失调是导致焦虑障碍的直接病因。
秦敏指出,焦虑障碍不仅与五脏相关,同时要注重脏与脏、脏与腑之间的整体关系与相互影响。《黄帝内经》云:“悲哀愁忧则心动,心动则五脏六腑皆摇摆。”明言七情伤心,则牵一发而动全身,五脏六腑均受累。由于焦虑障碍患者具有烦躁易怒、紧张担忧、思绪不宁、心神不安、恐惧等临床特点,与“肝志为怒”“肺志为忧”“脾志为思”“肾志为恐”相吻合,且情志失调伤及五脏后更易加重情志异常的症状,故从整体观的角度下分析,本病病理具有相互影响的特点,需要医者把握病机变化,方可司外揣内,参表知里,辨证论治。
2.2 岭南飞针疗法之法
2.2.1 打通任督二脉 目前对焦虑障碍的研究多集中在从脏腑角度理解,鲜见从经脉角度立论。秦敏经过多年研究发现,任督二脉在治疗焦虑障碍疗效显著。由于任督二脉上分布较多脏腑俞募穴和经脉交会穴,可将各脏腑对应的经脉有机关联;同时任脉和督脉分别位于腹背正中线上,一前一后,阴降阳升,经气交贯。因此,调节任督可调整脏腑阴阳气血,正如《奇经八脉考》言:“任督二脉,人身之子午也,乃丹家阳火阴符,升降之道,坎水离火。”故临床上若能精准把握任督二脉的选穴规律,从而打通任督二脉,诸疾可除。所谓打通,即针刺任督二脉及其周围腧穴调畅气血,充实精气,令任督二脉得以贯通,使机体达到阴平阳秘。
同时,秦敏指出,脑为元神之府,是元神所寄之所,而五脏之神、魂、魄、意、志皆为元神所化分,又由元神所主宰,脑神调摄失控,则情志乃乱,病从中生。故治疗情志失调之患,重在调神。肾为先天之本,肾中藏精可通脑生髓,肾气旺盛,则脑髓充满,神机灵敏。而督脉与脑、髓、肾关系密切,督脉贯行脊里,循腰络肾,上入脑络,作为背部气血游溢的通路与大脑直接相连,“督脉者,起于下极之俞……入属于脑”[18]。故督脉能反映脑、髓、肾生理病理变化,针刺督脉能整体调节脑、髓、肾的功能,有助于调整元神紊乱,从而调节情志,为焦虑障碍的治疗找准靶心。
2.2.2 辨虚实,明补泻 秦敏指出,需明确病情虚实,方能针刺补泻进行治疗。对于病初者,一般以实证居多,其特点为肝郁胆滞化热,经络失调;对于病久者,属虚证较多,其特点为阴阳失调,神气失养。
秦敏认为,凡七情情志过极,皆引起气机失调,日久升降失常,发为郁病。五脏六腑中,肝主疏泄,可调畅一身之气,气为血之帅,气行则血畅,气血平和,邪无从生。而胆与肝互为表里,《黄帝内经》:“胆足少阳之脉……是动则病……是为阳厥”“阳气者,因暴折而难决,故善怒也,病名曰阳厥”,可见焦虑烦躁主要是肝胆疏泄失常,阳气郁而化热邪,故在初期重视疏肝调气,泻胆散邪,一可防气血运行不畅,二可防郁热伤阴,扰动心神。而对于病久者,中医有“久病必虚”之说。当疾病持久未愈,由于致病素的作用,机体的阴阳消长将失去相对的平衡,造成阴阳失调,而阴阳互根互用,长此以往,易致阴阳两虚,神气衰微。而督脉为“阳脉之海”,总督全身阳经;任脉为“阴脉之海”,总任全身阴经,且任督同源,主一身之阴阳,任督调则气血畅、百脉和,失则气血闭、百脉乱,故在后期应重视“调任督”“调神气”。
2.3 岭南飞针疗法之方
2.3.1 理正散邪腹针方 对于病初者,选用“理正散邪腹针”。该针方是秦敏岭南飞针疗法腹针系列中一类偏泻针方,穴位选任脉及位于腹部其他经脉的特定穴。秦敏教授认为,凡郁皆在中焦,中焦是大部分脏腑集中于人身中间的部位,刺激腹部穴位,可激发脏腑气血以调整人体阴阳,恢复阴阳相对平衡。另外,十二正经中循行经过腹部的经脉有胃经、脾经、肾经及肝经,而肝属木,主疏泄,肾属水,主润下,脾为中土以灌四傍。故针刺腹部四条经脉腧穴,实际是调整“木-土-水”轴。对于具有肝胆郁滞,易贼脾胃,以及肝火易伤阴特点的焦虑障碍一病十分合适。
“理正散邪腹针”包含的穴位分理正与散邪两部分,理正部分取巨阙、三脘、京门,散邪部分取章门、期门、日月。方义:巨阙属任脉,为心之募穴,具有补心安神、理气宽胸的作用;三脘属任脉,为上脘、中脘、下脘三穴合称,根据“上主纳、中主化、下主出”的特点,三脘如上焦、中焦、下焦在腹部的缩影,且中脘为胃之募穴,八会穴之腑会,三脘同用,具有补中、和胃、理气之功。京门属胆经,为肾之募穴,具有利胆补肾的作用。章门、期门同属肝经,章门脾之募穴与八会穴之脏会,《针灸大成》曰:“善怒……少气,郁然不得息……章门主之”。期门、章门、京门三穴合用具有疏肝利胆、健脾理气的功效,既含散邪之意,又不失理正之义。临床中用于治疗胸胁疼痛、烦躁易怒均具很好疗效。日月属胆经,为胆之募穴,《针灸大成》记载:“太息善悲……日月主之”,故日月可泻胆郁,散邪气。诸穴合用,共奏疏肝调气、泻胆散邪之功。操作方面,按岭南飞针手法入针后,理正部分行补法或平补平泻法,散邪部分行泻法或平补平泻法。另外,秦敏教授指出:若患者体质有明显偏向,则不可拘泥于腹针,应结合体针随证加减,增强疗效。如痰火扰神,加内庭、曲池、丰隆;火盛伤阴者,加行间、太溪、三阴交;气滞血瘀者,加膻中、血海、膈俞等。
2.3.2 太阳夹督围刺针方、安神醒脑头皮针方 病久者,着重运用“太阳夹督围刺针”及“安神醒脑头皮针”进行治疗。
太阳夹督围刺针方,是秦敏根据多年临床经验创立的,以督脉穴位为主,结合脏腑背俞穴,采用多针、斜刺、一针透三穴的方式治疗疾病的针法[12]。其理论依据来源于《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中记载的“故善用针者,从阴引阳,从阳引阴”。秦敏教授在传统夹脊针基础上对分区进行改良和优化,把背部划分为上焦区(后发际至第七胸椎)、中焦区(第七胸椎至第十二胸椎)及下焦区(第一腰椎至骶尾部),“三针”为一组,根据不同疾病选择相应区域进行施针。针对焦虑障碍病久患者,秦敏教授常将三区联合运用,并配以任脉补益气血穴位,取大椎、肺俞、身柱、厥阴俞、神道、心俞、筋缩、肝俞、中枢、胆俞、脊中、脾俞、悬枢、三焦俞、命门、肾俞、关元俞、气海俞等。操作方面,一般按岭南飞针手法入针后,行平补平泻法。通过针刺任督二脉之穴,使患者最终达到“阴平阳秘、精神乃治”。
安神醒脑头皮针方是通过针刺人体头皮下(腱膜下层)组织中的特定刺激点(区、带、腧穴)来治疗相关疾病[19]。《内经》指出“头者,精明之府”“是故休惕思虑者则伤神”,因此调神在调节焦虑障碍的地位十分重要。头部包含奇恒之腑的大脑,头部气血直接滋养脑中元神。秦敏将头部划分为四大治疗区(阳明区、厥阴区、少阳区、太阳区)[19]。同样以“三针”为一组,治疗相关脏腑及经络病证。对于焦虑障碍患者,秦敏教授常用阳明区、厥阴区、少阳区。(1)阳明区穴位包括眉冲、曲差、印堂、太阳诸穴。与传统头皮针额区可主治精神异常类疾病的思路基本一致。(2)厥阴区包括百会、四神聪、四神聪旁开1寸诸穴。由于肝经循行经过头部并与督脉汇合于巅顶,故此区域藏调督理肝之义,安神效果较佳。另外,头为诸阳之会,《素问》曰:“阳气者,精则养神”。直接刺激头部最高位的顶区,可直接调整阳气,濡养神气。(3)少阳区包括率谷,率谷左右旁开0.5寸诸穴。就经脉循行来看,此区隶属少阳,有利胆安神之意。操作上按岭南飞针手法入针后,留针30 min。
秦敏指出,临床上所遇患者可能存在虚实夹杂的情况。故必要时,可联合“理正散邪腹针”同用,以扶正祛邪,补虚泻实。
3 岭南飞针疗法之术
岭南飞针较传统飞针不同在于其不仅强调速度快,而且角度宽、深度大。包括“一拍、二推、三旋转”的注射式、“一旋、二翻、三点头”的飞行旋转式,以及“一压,二提,三旋转”的指压式[12]。3种方式均需先找到准确刺激点或穴区,后对双手及穴区严密消毒。取1.5寸规格针灸针,用右手的拇指、示指捏持针柄或针柄与针身交界处,中指抵住针身,并且将针身稍向下压,露出针尖0.2~0.3寸,使针体与针刺部位呈10°~15°。
(1)注射式。①“一拍”:腕背屈后,突然手腕掌屈,靠刺手腕关节的力量将针拍进针刺部位。②“二推”:随即三指持针向前推进,使进针1.2~1.5寸,推进过程中中指要对针尖部有一定压力,以确保针身能进入帽状腱膜下层。③“三旋转”:最后拇指向前、示指向后搓动针柄,使针顺时针旋转,旋转速度约为150转/min。必要时可在进针后用拇指、示指夹持针柄快速旋转,频率为250~300次/min。
(2)飞行旋转式。①“一旋”:拇指先向前捻转搓动少许,示指、中指向后捻转搓动少许,使针始终处于旋转状态,且保持掌心向上;②“二翻”:随后前臂外展外旋,且保持拇指外展、示指与中指内收状态,突然挥动前臂,使前臂内收内旋,手腕迅速向下翻转,使掌心向下;③“三点头”:同时刺手的拇指内收,示指、中指同时相应外展,此时,针体便迅速转动(旋转速度约200转/min),当针处于快速旋转,并抵达穴位时,通过腕力、指力将旋转的针弹刺入穴内。
(3)指压式。①“一压”:然后拇指、示指用力将针压人穴位内。②“二提”:中指抵住穴旁皮肤,拇指、示指捏持针柄,将针向外提出0.2~0.3寸;③“三旋转”:最后拇指向前、示指向后搓动针柄,使针顺时针旋转,旋转速度约150转/min。
岭南飞针手法操作关键在于手指的挫力、手指的弹力、手腕的翻转力、手臂的挥动力,其中手腕的翻转力为其精要,飞针时使用极具特色的翻腕旋转手法把针快速无痛地刺进身体治疗部位,达到打通任督、理畅三焦、调整阴阳的目的。
4 验案举隅
4.1 病案1患者,女,48岁,2018年4月27日初诊,主诉:焦虑伴失眠1年余,加重1个月。患者1年前无明显诱因出现心烦、焦虑,未予重视,后焦虑情绪加重,入夜时常难以入睡,眠浅,易惊醒,每日睡眠时间不足3 h,甚则彻夜难眠。刻诊:精神焦虑,不欲言语,易惊慌,体质量较前明显下降,时有耳鸣、头晕,纳差,小便尚调,大便难解,舌胖大,苔白,脉细弱。西医诊断:焦虑性失眠;中医诊断:不寐(心脾两虚证)。治以健脾益气、养心安神。针灸处方,(1)安神醒脑头皮针:以岭南飞针头皮针厥阴区、阳明区、少阳区为主,取穴为百会、四神聪、四神聪旁开1寸、眉冲、头维(双)、太阳(双)、承灵(双)、率谷(双);(2)太阳夹督围刺针:以岭南飞针围刺针上焦、中焦区为主,取穴为厥阴俞、神道、心俞、肝俞、中枢、脾俞、各穴及其左右旁开1.5寸;(3)辨证配穴:神门(双)、内关(双)、足三里(双)、梁丘(双)、太溪(双)。按岭南飞针手法入针后行补法,每次留针20 min,12次为1个疗程。针灸6次。
2诊:2018年5月7日,患者诉焦睡眠较前改善,可睡4~6 h,焦虑情绪明显减轻,偶有心慌、头晕,遂继续予针灸治疗6次。患者诉可一觉睡至天亮,未见入睡困难及紧张焦虑情绪。
4.2 病案2患者,男,38岁,2018年11月2日初诊。主诉:情绪紧张伴头晕2周。患者平素脾气急躁,嗜烟酒,2周前与朋友外出就餐时与他人发生争执,回家后出现情绪不宁,烦躁,头晕头痛,面红耳赤,胸胁胀痛,自饮菊花茶后,症状稍改善。刻诊:情绪激动、急躁不耐烦,声音洪亮,面红目稍赤,胸胁胀痛,口干口苦,时有耳鸣,小便黄赤,大便干结难解,舌红,苔黄腻,脉弦数。西医诊断:焦虑障碍;中医诊断:郁证(肝郁化火证)。治以清肝泻火,理气畅中。针灸处方,(1)理正散邪腹针:以岭南飞针腹针中、上焦区为主,取穴为巨阙、三脘、各穴及其旁开1.5寸、京门、章门、期门、日月;(2)安神醒脑头皮针:以岭南飞针头皮针厥阴区、少阳区为主,取穴为四神聪、百会、安眠(双)、印堂、太阳(双)、悬厘(双)、率谷(双);(3)辨证配穴:合谷(双)、曲池(双)、太冲(双)、行间(双)。按岭南飞针手法入针后行泻法,每次留针20 min,12次为1个疗程。针灸6次。
2诊:2018年11月22日,患者自觉烦躁情绪明显减轻,胸胁胀痛缓解,无头晕头痛,继续予6次针灸治疗,经针灸1个疗程后患者症状明显缓解,后无复诊。
5 小结与展望
焦虑障碍属中医情志病范畴,与西医有限的治疗效果相比,目前研究表明针灸治疗广泛性焦虑障碍呈现出疗效好、副作用少的优势[5]。由于针刺“过皮”时难以避免因手法不娴熟导致的疼痛,而飞针快捷、灵活、无痛更易被患者所接受。秦敏教授在传统中医“理法方药”的基础上提出“理、法、方、术”:以中医整体观为理,打通任督二脉为法,三大飞针系列为处方,3种不同的飞针手法为术,构成岭南飞针整体治疗体系。在治疗焦虑障碍中,对病程不同的患者应鉴别虚实,辨证施针。一般认为实证患者多见肝郁、胆滞、经络阻滞,故治以“理正散邪腹针”,以求疏肝理气、泻胆散邪。虚证患者多见阴阳失调,神气失养,故治以“太阳夹督围刺针”“安神醒脑头皮针”,以达阴平阳秘。
目前,对针灸治疗焦虑障碍的机制研究仍缺乏明确的证据,同时质量控制存在一定缺陷,如缺少随访,难以判断针灸治疗该病预后的情况[4],这均是今后亟需完善和发展的方向。焦虑障碍依然是临床难题,但秦敏教授岭南飞针疗法对该病的疗效已在临床上得到验证,值得推广。同时,对岭南飞针疗法治疗焦虑障碍的治法组方进行优化,亦是今后我们进一步关注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