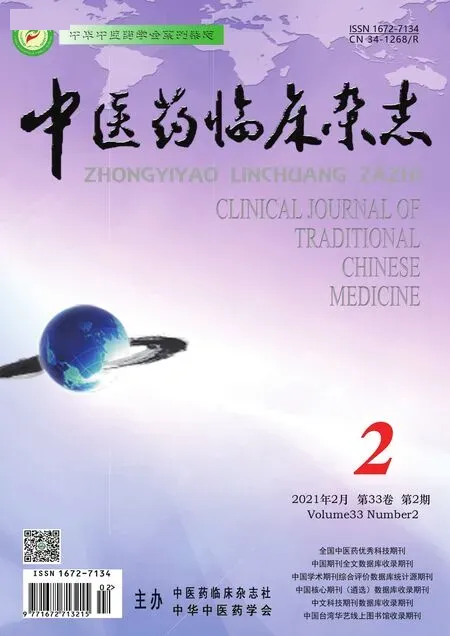徐春甫温补“脾胃元气”治未病的研究与探讨*
安徽中医药大学 安徽合肥 230038
先祖于千百年前便提出“上工救其萌芽”“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的思想,古籍经典中对于养生防病的记载也数见不鲜。随着新时代科技和信息的发展,人们生活模式和生存环境的转换,亚健康状态成为现今社会普遍现象,WHO 估计全球 70% 的人群处于亚健康状态[1],而大众对于更高更优生活质量的迫切需求,推动着治未病的理念思想与临床实践居于日趋重要的低位。徐春甫作为汪机的再传弟子,私淑李东垣[2],将汪李二家之温补培元和顾护中州脾胃之思想进行了有机的融合[3]。徐老尊丹溪之“与其求疗于有病之后,不若摄养于无疾之先”的理念,将养生思想贯穿于疾病的预防、诊断、治疗、调养的全过程。笔者将对徐氏推崇治病防病必须保重脾胃元气等方面进行论述,若有不正之处,敬请斧正。
阐发“脾胃元气”学说
“元气”一词首见于《难经》,将其认为是生命的原动力[4]。金元之补脾大家李东垣十分重视元气,并对其进行了相应的阐述和发挥,但矛盾的将元气、胃气视为同类[5]。后世医家徐春甫循李东垣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的观点,在先祖汪机的影响下,形成了温养气血、培补元气为特色的学术思想,成为新安固本培元的中坚力量[6]。他将脾胃与元气两词创造性地进行了组合,提出了“脾胃元气”这一组合词汇,实际上是阐述了后天脾胃在人体脱离母身之后,能禀谷气化生气血充养先天元气的观点,笔者将其认为是继承徐老该观点的罗周彦,并将其论述发展成“元气有先后天之分”理论中的后天元气。
1 承东垣之脾胃学说
徐春甫私淑李东垣,将李氏“脾胃之气既伤而元气亦不能充,而诸病之所由生也”之论认为是“诚医道之大幸也”。在《古今医统大全·脾胃门》中论述道:“春甫研读东垣诸论,详明《内经》论百病皆由上中下三焦元气虚惫及形气两虚而变生”,将其发挥为脾胃不足,则不能上输而散布精微以充实全身上下,继而三焦元气不足,百病而横生。徐春甫继承李东垣之脾胃学说,认为五脏六腑皆主于脾胃,“脾主中土,主生万物,虽具坤静之德,而有乾健之运”。自称临床治病之所以有较高的造诣并得到大家的信任便是深谙脾胃元气之妙,即所谓“超凡脱俗,极登万仞,探本穷源,深得脾胃元气之妙,故投之所向,无不如意。”[7]
2 治病重查脾胃虚实
徐春甫在《翼医通考·医道》中论述:“观今世医者多不工于脾胃,只用反治之法攻击疾病以治其标。”指责当下医生不明白脾胃的重要性,只懂反治之法。时下追逐名利,劳思伤脾而治病者居多,病之八九都为元气不足,治诸病以胃气为先,主虚则客邪不退。在《脾胃门》中指出:“胃气虚者,攻之则胃气益弱,反不能行其药力,病所自如”,“胃气实者,虽有病,不攻自愈故中医用药亦尝效焉,观夫藜藿野人,尝病不药自愈可知”。古云:“治病不查脾胃之实,不足以为太医。”目前,在临床上治病查脾胃虚实有广泛的实用性和适用价值[8]。
3 论“五脏之脾胃病”
《五脏别论篇》指出:“胃者,水谷之海,六腑之大源也”,《玉机真脏论篇第十九》中也记载了“五藏者皆禀气于胃,胃者,五脏之本也”,论述了脾胃与五脏六腑之间的联系。脾居中央而灌四旁,荣养气血,徐氏认为脾胃元气不足,不禀谷气濡养其他四脏,则其之类可因此而衍生百病,而调和脾胃可安和五脏。《脾胃门》治法中“脾胃为十二经脉之海,脾胃既虚,十二经脉之邪不一而出”以及其中提出的“肝之脾胃病、心之脾胃病、肺之脾胃病、肾之脾胃病”都一一强调了脾胃病变可以影响诸脏,故其他四脏的疾病,可以从脾胃调治入手。换而言之,调理脾胃可以安和五脏,治“治脾胃病兼治各经。
新安温补培元法
自汪机以降,擅用参、术、芪调和营卫、温补脾胃阳气[9];孙一奎作为汪机的再传弟子,重以温补下元,强调脾肾同治,在前者的基础上益以姜、附培先后天之本、固脾肾元气并举并治,创状元(原)汤和状元(原)丸;此后以汪机众多的弟子门生们为主体的新安温补培元法蔚然形成[10]。徐春甫作为汪机之徒汪宦之弟子,承先祖之衣钵,从东垣之学,将温补的思想糅合于调补顾护中州脾胃上,强调“治病不查脾胃,不足以为太医”;认为“人之有生,以脾胃为主。脾胃健盛,则恒无病”[11],认为疾病的产生是由于脾胃失健,脾胃健则百病除,其“阳虚则恶寒,用参芪之类,甚或加附子以行参芪之功”便是对于先祖温补大法的承袭与发展。《素问·刺法论篇第七十二》:“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强调了正胜而邪无所害,病无由而生。新安温补培元法意在用人参、黄芪、白术等甘温益胃之品,养血和营[12],补气实卫,补益后天之本脾,滋气血生化之源,内濡五脏六腑,外资形体官窍;充实先天五脏阴阳之本肾,培补元阴元阳,振奋人体之防御抗病之正气;从而达到先后之本俱实、形体健硕、筋骨劲强、邪不能害的目的,与前者有异曲同工之妙。
治未病之特色
中医自古将“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作为衡量“上医”的标准,也将其认为是医学的最高境界。徐春甫在《翼医通考·补遗》中陈述:“圣人治未病不治已病,非谓已病而不治,亦非谓已病不能治。盖治未病,在谨厥始、防厥微以治之,则成功者多而受害者少也。”而且,徐春甫的治未病论是和脾胃观相结合、相联系的,他认为“人之有生,以脾胃为主。脾胃健盛,则恒无病”,在临证善温补脾胃,培补中气,充养元气。就养生防病中的未病先防、已病防变、愈后防复发展为未病培元、已病保元、愈后复元[13]。
1 未病先防——未病培元
未病先防,即在无疾的健康人或处于疾病和健康的“亚健康”人[14]尚未发生疾患之前,便对机体采取前瞻性的保护和调养,培补元气,使形体正气充盛,不为病邪所害。简而言之,要掌握健康的主动权,在病变未产生之前就加以调治[15]。
徐氏在《医统·凡例》提出来防患于未然的观点:“论养生导引,诚古人治未病之方。今惟待病而求药,殊不知善摄生者譬犹曲突徙薪,自无焚燎之患。”在对于髭发衰白的治法上强调“必于四八之年先备滋益之药,不待于既衰之后用之。”认为髭发黑美须服神仙六子丸补脾资肾,保和气血。此外,徐氏将大健脾养胃丸推为医家之主药,认为其久服强中,百病不生,有是言:“大健脾养胃丸十二味,大补脾胃虚损,久服元气充畅,百病消除而益寿”[16]。徐氏承“五脏者皆禀气于胃”、“百病皆由脾胃而衰”思想,阐发五脏皆有脾胃之气、脾胃之病,提出“五脏之脾胃病”,肝、心、肺、肾四脏皆需脾胃的营养濡润,脾胃病可以影响诸脏,脾胃调和则五脏安和。观世人“禀气薄弱,兼劳役名利之场,甚至蹈水火而不知恤,耽酒色以竭其真”,病之十有八九为元气不足,徐老惧世人因劳倦思虑、恼怒饥饱、酒色湿热寝以伤脾胃,脾不能运精微之气,胃失所基,制大健脾养胃丸以健脾保元,防脾胃虚则俱病。
2 已病防变——已病保元
已病防变指在疾病发生之后,进行早期的诊断和治疗挫其于轻浅萌芽之时,防微而杜渐,以及防止疾病再进一步的发展与传变,大致可概括为已病早治与病后防变。[17]
《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善治者治皮毛”,强调了疾病早期诊断治疗的重要性,徐春甫批评世人“病形未著,不加慎防,直待病势已著,而后求医以治之”,评述张仲景《伤寒论》:“观其少阳证小柴胡汤用人参,则防邪气之入三阴,或恐脾胃稍虚,邪乘而入,必用人参、甘草固脾胃以充中气,是外伤未尝不内因也”,指出张仲景虽以治外伤为专,但深知脾胃元气之旨。而徐氏在各科病症的治疗上也注重先调护脾胃而后攻伐[18],在《医统·水肿门》对于脾虚不能制水一证以实脾土为本利小便为标,补中行湿要先施,认为“当以参、术补脾,使脾气得实则自健,用二陈汤加人参、苍术为主,佐以黄芩、麦门冬、炒栀子制肝木。”指出诸家治水肿,只知导利小便。《医统.肺痿证》论曰:“脉数虚者,大抵久咳伤肺,元气渐虚……即成肺痿。治法宜补血、调肺气、清金。虚者用人参清肺汤之类”。肺病日久逐伤元气,徐氏深谙此理,虚证治疗用人参培补脾胃元气生金先固本,在论调气清金之治。其又评述张元素之枳术丸言“白术甘温补脾胃之元气,枳实泄心下之痞闷,且白术倍于枳实,是先补其虚,而后化其所伤,不峻利而反增真气”,诸上例证无不一一证实徐氏先补后攻以防变的思想。
3 愈后防复——愈后复元
愈后防复,即在病情稳定或病愈之后,要注意预防疾病复发及可能造成的后遗症[19]。
《伤寒论》中有录:“病人脉已解,而日暮微烦,以病新瘥,人强与谷,脾胃气尚弱,不能消谷,故令微烦,损谷则愈”,该阶段为疾病的恢复期,主要特点是脾胃虚弱,气血虚惫,应稍稍饮食,徐徐恢复脾胃之健运功能,进而扶助正气,待气血来复。徐春甫在《脾胃证歌》归纳为:“杂病各随调理法,要皆以元气为先”,徐氏在《老老余编》中记载的药粥方有46 首之多,以“雌鸡粥”、藿菜羹、“鸡子索饼”等食疗方为代表的多个药饵方,均可用于年老素虚,病后体弱之气血虚劳,以补虚培元[20]。同时,在疾病稳定期,以补土复元为先,《古今医统大全》论曰:“肺喘,喘后肺虚吐痰,均宜用人参、黄芪补之”。此外,徐氏认为张元素就病虽愈但脾胃受损,元气受伤而将白术改为枳实剂量2 倍之枳术丸犹感不足,认为“白术一味健脾尚不能成功,又加枳实消导,其功益缓”,改原方丸粒为易于消化的“汤滴小丸”,缓复脾胃功能。正如《倦怠嗜卧门》“若是脾胃俱虚,饮食进少,形气衰弱,常倦怠者,当大补脾胃以滋其化源,而克伐消导之剂则不可轻用轻犯也,久久滋补,脾胃一健,而精神斯足矣,何倦怠之有哉”所言。
小 结
徐春甫继承前人之经验,结合自身的临床实践,汇一生心血之结晶,提出的“治病不查脾胃之实不足以为太医”、“调和脾胃为医中之王道”等新的学术观点,治病防病多建立于温补脾胃元气,善用白术、人参和黄芪,而形成的调理脾胃的临床用药风格,丰富和完善了脾胃学说,充实了新安医学的学术思想。他凝炼毕生精力的培固脾胃元气——“未病培元”“已病保元”“愈后复元”,于病前、病中亦或是病后阶段,不管是在营养和药物作用来看,都具有无可取代的地位,对于当代养生防病治病方面有着颇为丰厚的临床指导价值[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