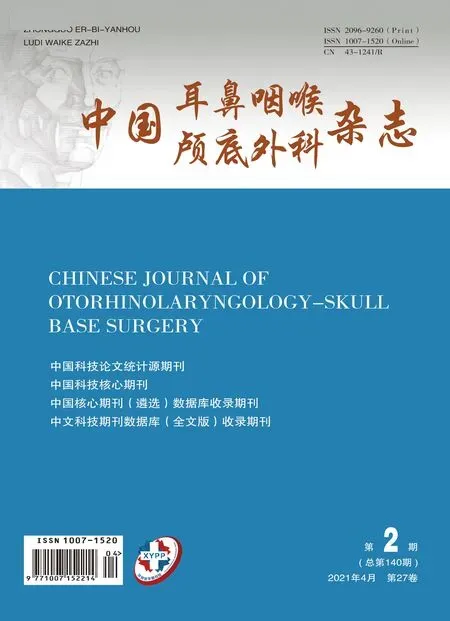鼻内翻性乳头状瘤发生发展机制的研究进展
李芊颖,陈合新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耳鼻咽喉科医院,广东 广州 510080)
鼻内翻性乳头状瘤(nasal inverted papilloma,NIP)是鼻腔鼻窦中一种良性上皮源性肿瘤,主要临床病理特征是易复发、易恶变、易局部侵犯且伴骨质破坏。NIP约占鼻乳头状瘤的70%,占全部鼻腔鼻窦肿瘤的0.5%~4%,其恶变率大约为10%[1]。人群中,NIP患病率为0.2/105~0.6/105,男女比例为3∶1~5∶1[2],主要发病人群为中老年男性(30~70岁多见,平均50岁)。NIP在鼻腔中发生于鼻腔外侧与鼻中隔,主要侵犯上颌窦与筛窦;临床主要症状为鼻塞、脓血涕、头痛及嗅觉异常等。目前,手术对肿瘤组织的完整切除是治疗NIP的主要手段,但术后仍有较高的复发率与恶变率[3]。目前NIP的发病、复发及恶变的相关机制没有综合性的分析和总结,本文将对NIP的发病机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初步的总结与介绍。
1 NIP中病毒表达及其影响
1.1 NIP中病毒感染检测率及影响因素
上个世纪80年代,Syrjänen等[4]第一次在恶变的NIP组织中发现人乳头状瘤病毒(human papilloma virus,HPV)DNA片段后,病毒感染被认为是NIP发生发展、复发、恶变的重要影响因素。然而到目前为止,HPV在NIP中的作用还尚未明确,且国内外报导的NIP组织中HPV病毒检测阳性率范围极大(0%~100%)[5-8]。对于高危型的HPV和低危型HPV在NIP发展和恶变过程中的作用仍存在很多争议,没有明确的说法。不同研究所得的结果均有较大的差异,有的认为高危型HPV与NIP的恶变有关,主要存在于NIP相关的鳞状细胞癌(squamous cell carcinoma,SCC)中;然而低危型HPV主要存在于NIP病例。还有的学者认为,低危型HPV主要是诱导NIP的发生,然而待被感染的上皮细胞被覆盖后即出现HPV逃逸现象,即出现HPV(-)。而在恶变的NIP中的高危型HPV的检测可能与上皮化生后HPV继发感染有关[9]。EB病毒(Epstein Barr virus,EBV)是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的病原体,与鼻咽癌、儿童淋巴瘤有密切关系。有学者提出EBV可能也是影响NIP发生发展的主要因素,但目前国内外研究对NIP中EBV感染证据的报道说法不一,有的认为EBV感染与NIP关系不大,然而Nukpook等却认为在泰国的东北部的人群中,NIP伴随亚急性炎症、急性炎症和不典型增生的病例中均有发现EBV,且认为EBV与NIP的发生和恶变有关,但该研究的人群比较局限,且伴不典型增生的NIP样本例数较少,其并没有进一步探讨其相关机制。仍没有明确的发病机制能说明EBV在NIP中的作用[10-11]。
针对NIP组织内HPV的不同检测率,国内有学者提出主要可能受到研究标本、检测方法、检测标本数目以及其他可能的环境、人口等因素影响[12]。早期研究标本类型多为石蜡包埋蜡块组织,时代久远的蜡块组织可造成HPV DNA不同程度的降解,或增加非特异性检测结果;同样,早期实验方法多为原位杂交或免疫组化[13],相对于聚合酶链反应(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PCR)和病毒基因的高通量测序等技术,早期检测手段具有更高的不稳定与不精确性;除此之外,人口的地理分布差异、人种及生活饮食习惯的不同、NIP的组织异型增生程度不同及对E5、E6和E7基因产物的变化的了解等对病毒感染的结果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1.2 病毒感染参与NIP发生发展及恶变过程的主要机制
HPV在NIP中的作用过程主要通过其相关癌蛋白与相应肿瘤相关基因的相互作用来启动NIP的发展以及恶变。高危型HPV E6癌蛋白可通过作用于TP53基因而促进肿瘤的发生,E6/UBE3A (E6-AP)泛素连接酶复合物以TP53为靶点进行泛素化及蛋白的降解;高危型HPV E6癌蛋白也可通过激活端粒酶的活性(TERT)从而改变细胞正常粘附与异常增殖状态[14]。高危型HPV E7癌蛋白则可通过阻止视网膜母细胞瘤抑制蛋白(retinoblastoma inhibitory protein,RIP)与转录因子E2F的结合而促进细胞周期进展,启动癌变过程。E2F可刺激肿瘤抑制因子p16INK4A的激活,形成D型细胞周期蛋白复合物,导致次级磷酸化的RIP肿瘤抑制因子的积累及触发细胞周期G1期的停滞[15]。然而在肿瘤细胞中p16INK4A的过表达的发生并不仅仅依赖于HPV的调控,还有其他原因可以导致p16INK4A的过表达,而且不依赖于HPV的调控[16]。低危型HPV E7癌蛋白则不能诱导p16INK4A的相关表达而不能进一步导致癌变反应[17]。主要通过HPV E5 癌蛋白增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EGFR)的活化,引起有丝分裂增强,导致上皮细胞不受调控从而导致增殖及肿瘤的发生[18]。
除HPV病毒癌蛋白对肿瘤组织的直接致瘤作用外,有学者提出HPV病毒可通过增加pAkt和磷酸化的S6核糖体蛋白(Akt/mTOR信号通路)促进NIP中肿瘤细胞增殖,但具体作用机制暂不明确[19]。
虽然有研究认为NIP恶变后HPV的感染率显著增加,但NIP恶变与病毒感染之间的因果关系并未得到确认,有研究指出HPV的作用机制主要是通过其病毒蛋白与肿瘤抑制因子的相互作用在NIP的发生、恶变和复发中起作用,然而也有多项研究均指出NIP良性与恶变组织中检测到的p53与p16INK4A的表达与HPV的感染无明显相关性。因此,针对与p16INK4A在NIP中的相关上游和下游作用机制的研究和Akt信号通路在NIP中的作用可能对后续的HPV在NIP中的作用机制起一定的指导作用。
2 NIP中常见基因表达的改变及主要作用
NIP恶变后,可形成相应部位鳞癌、腺癌、黏液表皮样癌、未分化癌、小细胞癌等。其中,鳞癌是最常见恶变类型[20]。NIP的恶性转化可能与许多非HPV相关机制有关。Udager等[21]首次提出在NIP和NIP相关的SCC中,EGFR突变的检测率分别为88%和77%,进一步检测EGFR突变类型发现都存在EGFR外显子19和外显子20,但EGFR外显子20突变最常见。并发现NIP和NIP相关SCC中发现了同样的EGFR基因突变类型,也进一步证明了NIP与恶变后的NIP相关的SCC之间的生物学关系。Udager等[22]的后续研究还发现HPV(+)和EGFR基因突变在NIP和NIP相关的SCC中对立存在,且HPV感染多为低危型HPV。研究发现在肺癌中EGFR激酶结构域突变的分子靶向治疗已经取得了明确的治疗成果,如今在NIP和NIP的相关SCC中也发现了EGFR基因突变的存在,且认为其在NIP的发生、恶变过程中起一定的作用,EGFR可作为NIP恶变后的相关靶点治疗方向。Sasaki等[23]在对比EGFR突变在头颈部肿瘤之间的光谱,发现EGFR突变特定存在于NIP和NIP相关的SCC中,在其余头颈部肿瘤中均未见EGFR突变的存在。对EGFR家族的基因受体和配体在NIP和NIP相关的SCC中的表达进一步研究发现,NIP组的ErbB1和ErbB2的mRNA和蛋白表达水平在正常组、NIP组和NIP恶变组中逐级递增,且其表达水平与NIP发育不良的程度呈正相关[24]。Sahnane等[25]发现存在EGFR突变的NIP样本更不易恶变且无进展生存期较存在野生型EGFR样本长,且认为LINE-1低甲基化是NIP预后不佳的标志。
除此之外,Yasukawa等[26]提出NIP、NIP伴不典型增生、NIP相关鳞癌3组标本中基因突变数目明显递增,且三者最主要差异突变基因分别为KRAS、APC、STK11。与此相反的是,TP53虽然是最常见基因突变类型,但在三者之间并无明显表达差异。Wang等[27]首次发现在大部分的NIP样本中程序性细胞死亡因子4(programmed cell death factor 4,PCDF4)的mRNA和蛋白表达水平均下降,且其表达水平与NIP的Krouse分期有关,然而PCDF4的mRNA和蛋白在正常的组织样本中过表达,阐述了PCDF4在NIP的癌前病变中的可能作用。Wang等[28]研究中FoxM1肿瘤基因在NIP和NIP相关的SCC中过表达,mRNA和蛋白水平均显著上调相较于正常对照组,与其在NIP和NIP相关的SCC的组织学分级有关。证明了FoxM1在NIP和NIP的恶变过程中起重要作用。
尽管有多项研究都认为野生型EGFR在NIP的发生、恶变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然而其具体机制仍不明确。但对NIP和NIP恶变肿瘤中的EGFR下游机制的研究,例如:MAPK、PI3K/ATK/mTOR信号通路的进一步研究,能为EGFR在NIP中的可能作用机制提供一定的基因学证据。相关的肿瘤基因和肿瘤抑制因子的进一步研究对后续NIP作用机制的阐明起重要作用。
3 肿瘤局部炎症微环境在NIP发生发展中的作用
国内外学者认为肿瘤局部慢性炎症也是NIP发生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主要论据有以下几点:①NIP的发展与鼻息肉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他们均起源于中鼻道,且NIP常常伴有鼻息肉的发生,且认为严重的炎症环境可以导致鼻息肉发生过程中的细胞周期失调,导致NIP的发生[29];②有学者认为,持续的炎症感染会导致中性粒细胞胞外诱捕器(neutrophil extracellular traps,NETs)的形成,且NETs是唤醒休眠癌细胞中必要的结构,NETs相关的蛋白酶包括中性粒细胞弹性蛋白酶和基质金属蛋白酶(matrix metalloproteinases,MMP)[30]。且有研究表明MMP是组织重塑过程中的一类关键酶,且在NIP增生的固有层与相邻的非增生固有层相比,可见到MMP-9炎症细胞显著增高,MMP-9的细胞重塑作用和MMP-9在NETs中的唤醒休眠癌细胞的作用可能是导致NIP发生、发展的因素之一[31];③Lou等[32]发现在NIP和相关的恶变肿瘤中CD4+T细胞、CD8+T细胞、Foxp3+Treg细胞相对于正常对照组显著增高,并且其受到CCR4/CCL22信号趋化和募集Treg细胞至肿瘤组织处;④Zhao等[33]进一步研究发现NIP肿瘤组织局部存在有大量炎症细胞浸润,且主要浸润细胞类型包括嗜酸性粒细胞、嗜中性粒细胞、巨噬细胞、CD4+T细胞、CD8+T细胞,其中嗜中性粒细胞是NIP的主要类型。NIP的体积占位可导致鼻窦鼻腔引流障碍,加重慢性炎症发展;肿瘤局部慢性炎症可为微生物的生长或肿瘤生长因子/介质的表达创造有利的微环境,导致组织重塑至异型增生,从而进一步促进肿瘤发展。
除此之外,Chiu等[34-35]在NIP肿瘤基底部发现骨质存在不同程度的骨炎及骨裂缝。Liang等[36]认为肿瘤局部组织内的炎症细胞与炎症介质可加重肿瘤附着处骨炎,从而出现骨膜水肿、骨质缺损、编织骨形成等系列骨质改变,最终导致肿瘤向根基部骨质侵入性生长,进而影响术中对肿物的完整切除,造成肿瘤残存。
虽然明确在NIP组织中有炎症微环境的存在,且也发现很多炎症因子和炎症细胞在NIP组织中的变化,然而炎症微环境在NIP中的作用机制尚未清楚。明确NIP中的Treg细胞等炎症细胞的相关调控因素的改变,将进一步加深对NIP发生和恶变的认识。
4 环境污染物与NIP发生发展的关系
环境因素对许多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均有影响,在NIP中环境影响因素也起重要的作用。Ahamed 等[37-38]认为工作生活环境中的重金属(例如:铜、锌、锂、镉等)游离离子、金属复合物、金属颗粒或难溶性化合物的形式通过呼吸道进入人体,具有一定致癌性。除此之外,人体内的金属毒素也可通过医源性或遗传性途径得到进一步积累,造成组织器官的损伤。金属硫蛋白(metallothioneins,MTs)是细胞内一种富含硫醇的重金属结合蛋白,它可通过结合微量金属离子,进行细胞内金属离子的重新分配,从而避免金属细胞毒性。Starska等[39]在NIP局部组织中进行MT2A基因核心启动子区域的-5A/G(rs28366003)单核苷酸多态性进行检测,发现该基因的多态性可明显影响NIP组织中的MT2A基因的表达及体内铜与镉金属的含量,从而影响该肿瘤的进程。而且职业接触有机溶剂也是影响NIP发生的影响因素之一[40]。
5 其他与NIP复发相关影响因素
NIP在鼻腔鼻窦内的根基部和对周围组织的侵犯范围也会影响到NIP术后的复发。国外有学者[41]认为肿瘤根部附着于前组鼻窦,尤其是前内侧角区域(例如:上颌窦、蝶窦)处的肿瘤会影响术中操作,造成术后残留,由于累及上颌窦内侧壁肿物较易残留,且易复发,孔祥春等[42]进行相关临床实验研究,对比鼻内镜和泪前隐窝入路不同的手术方式对于NIP复发的影响,发现泪前隐窝入路行NIP切除治疗相比于普通鼻内镜切除,复发率、术后并发症、术后恢复时间和对鼻腔功能的保留,泪前隐窝入路效果更佳,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同时,术中切除范围应超过肿物边缘5 mm以上,保证肿物的完整切除。除此之外,Katori等[43]提出肿瘤上皮鳞状化生及角化过度、上皮有丝分裂指数升高、不伴发炎性息肉及上皮中非整倍体细胞数量增多均为影响NIP复发的重要因素。
手术路径与治疗方式的选择也是影响NIP复发的重要因素。多项研究指出:NIP手术方式中,内镜手术后复发率明显低于开放性手术或联合路径手术;且目前认为如病变累及上颌窦内侧壁,泪前隐窝入路行NIP切除可减少术后复发的几率;初次手术对肿瘤的完整切除后,肿瘤复发率明显低于多次肿瘤切除手术患者;肿瘤根基部广泛分布患者复发率明显高于根基部局限性患者。因此,NIP的复发主要与术后肿瘤残余有关[44-45]。
此外,NIP复发与恶化相关表达的蛋白,例如:Ki-67、survivin蛋白、Bcl-2、Wnt蛋白、CCAAT、C/EBPs、C/EBPα、CK10蛋白、E-cadherin、β-catenin及PLUNG等均可作为有一定价值的参考指标,但上述蛋白在NIP发生发展中参与的具体作用暂不明确[41]。
NIP属于鼻腔鼻窦的良性肿瘤,虽然目前有较多发病机制研究,但均不明确且缺少足够的实验验证。在以后NIP的发生发展研究中,除了需要扩大标本量,还需尽快建立NIP的原代肿瘤上皮细胞系,以方便进行更多的功能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