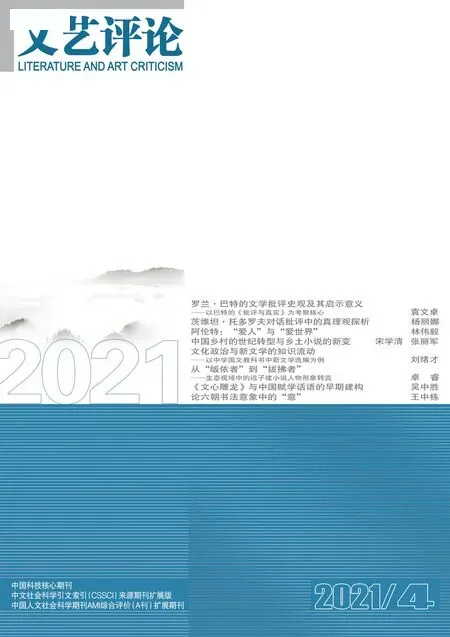新时代中国军事题材电影的叙事美学
○李梦雅
中国军事题材电影发展至今,在形式建构和主题表达上经历了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建国后,“十七年”时期,通过塑造国家英雄形象,讴歌和赞美革命热情,宣扬爱国主义精神和集体主义价值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革命历史事件以战争史诗片类型搬上银幕。特别是近十年来,军事题材电影从宏观表现“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转向意义涵盖面更为广泛的“爱国主义”精神,通过更加平民化的叙事视角,弘扬主流价值观、展现民族气节、塑造英雄形象、彰显中国精神。在新时代背景下,这一类型电影如何适应新时代语境、如何创新表现形式,还有广阔的探索空间。
新时代中国军事题材电影,大多取材于我国真实发生的军事事件,影片展现的故事是既定事实,属于非虚构文艺创作范畴。观众在走进电影院之前,一部分人往往带着“已知”的自信,对电影的展现方式有着更多的要求与期待。这种要求与期待常常建立在事实的不可更改性与演绎处理的独特性基础之上。既要求电影内容不脱离基本史实,保有“非虚构”的内核;又期待情节处理手段“非套路化”,呈现出电影所特有的多样性与震撼性的表达,从而获得新鲜的审美感受。面对这种双重要求,在一个结局既定、因果关系明确的战争史实面前,仍然能给观众造成过程的紧张感和结局的悬疑感,这就需要对影片的叙事形式进行精心的建构。并且,通过精心的形式建构,能更好地为影片的主题服务,从而完成此类型电影所承担的对事件意义的演绎和升华。
一、故事情节的非线性建构:主体性与对话性的互溶
改编自真实事件的军事题材电影,如前所言,一些观众观影前,对“事件”的主要内容可能“已知”,因此不同于其他剧情片。对于不属于“非虚构”的剧情片,观众根据不断涌现的情节,就能逐渐在心中自我建构。其中的情节就像是一块块拼图板块(或者是填空补充的材料),随着故事的进程,拼图逐渐完整,直至放映结束,故事被完全建构;甚至有些拼接的意义,在观众事后的体味或相互讨论中才得以实现。早期的“非虚构”军事题材电影,惯用此种叙事结构,在一定程度削减了剧情的冲突与观众的新鲜感。当下,军事题材电影更加注重在情节建构上,将真实事件的发展进程重新打乱或引入新视角,突破传统处理手法,使影片尊重历史真实,高于事件真实,产生更具艺术性的表达,提高了影片的可看性。
电影《金刚川》,通过“复调式”结构,将一段真实故事进行拆解、组合,分离出一个个情节,通过精巧的安排和设置,最终形成犹如精密、严谨数学结构的模型,给予观众一个“不同其他”审美对象。“复调式”一词来自于俄罗斯文学理论家巴赫金,他在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提出,其在小说中表现主人公心理动因时,形成了类似于音乐中一个“复调”,即几个“声部”同时发展、交叉进行。《金刚川》的叙事结构,将多条情节线进行有机建构,相互之间的主体性与对话性在起伏交叉中实现互溶,这就是巴赫金所说的“复调式”结构。
《金刚川》围绕“桥”这一关键点,将内容拆解为三个核心事件,分别是工兵连(包括高福来预备连)不断抢修建桥,护桥炮兵班与敌军地空对战,志愿军战士渡江。三个核心事件又被结构为四个单元,一是“士兵”,二是“对手”,三是“高炮班”,四是“桥”。四个单元并不是完全平行的结构模式。“士兵”、“对手”、“高炮班”在多线进行中,如一首乐曲的多个声部波浪式起伏,其任务分别是炸桥、守桥、过桥。第四单元“桥”,始终贯穿其间,构成“复调式”结构的主旋律,一直游走到乐曲最终章,形成高潮。情绪的累积、情感的爆发、主题的升华,都在那一刻得以实现。这样的结构设计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闭合,成功展现和升华了一个复杂的意义主体——与一场战争相关、内涵丰富的事件。
在前三个单元的多线索叙事中,对情节的选择和安排显得尤为重要。当三条情节线都在叙述同一时空故事时,就需要谨慎、精准地安排情节的“故意缺失”与互文,使看似孤立的三条线避免简单堆砌,形成相互补充映衬,达到由量而质的飞跃,形成内在闭合逻辑的系统结构模型,并在保证每条线索的独立性与主体性、对话性与对比性互渗互溶的前提下,产生共同印证主旨的效果。
“士兵”单元讲述的是志愿军需要在指定时间通过金刚川,准时到达指定地点的故事。其中高福来所带领的步兵连接到团部新命令,协助工兵连、高炮班,守住并保证大部队通行的交通咽喉——桥。影片特意选取了步兵连李班长这一人物,并安排其在后续单元中的特定情节里多次出现。例如在高炮班点亮照明弹自我暴露的情节中,反复出现李班长在河对岸山上作为“目击者”的画面。这种将人物在多条情节线反复出现的设置,使剧中人物成为“旁观者”,在三条情节线发展中出现一个参照点。而参照点的恰当存在,使影片的复调式结构更加趋向闭合状态,实现情节线之间的对比性和有机关联性;同时,让观众更容易、更清晰地完成了复杂剧情影像的“拼图”。
而在“对手”单元和“高炮班”单元情节线的叙事上,则是形成了一种对话性的结构。他们在各自的立场和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对事件的认知、情感的反应、情绪的演变,都能看到影片对战争的认识以及对人性的探索。“高炮班”单元中,导演将“民族激情”与“一般人性”相融合,在歌颂抗美援朝的民族激情中,融入高炮班战友的情谊;“对手”单元中,在美军飞行员“机械执行任务”中加入“队友”死亡前后的情绪变化。这种“对话”的镜头结构,传达了对战争中人的关注、对人性的揭示,流露出人文关怀的温情底色。其中“高炮班”单元,可以说是“复调”中冲出的“高音乐句”,通过描写高炮班几个普通人物,折射出志愿军战士不屈的民族精神和高昂的英雄主义。随着一个又一个人物的壮烈牺牲,影片中激昂情绪与悲壮气氛被一次又一次被推进,观众受到情感冲击,崇高感油然而生。这种通过书写小人物展现宏大历史事件的叙事方式,将“个体”与“历史”巧妙“互溶”,不露痕迹地将“导演主体激情、主流意识形态所指和电影观众心理缝合在一起”。①
第四单元“桥”,作为复调式结构的“最终章”,使整部影片的情感、立意、主题都被推向颠峰:中国军人用“血肉之躯”筑起一座“人桥”。疲惫不堪、伤痕累累、牙关紧咬、神情刚毅的群像,充斥着随时一冲云霄的无穷张力;具有石雕质感的影像群体,用足以让侵略者胆寒的钢铁般的事实,诠释着“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导演在这段镜头语言的运用上,充分挖掘了组合镜头的叙事和表意功能,最大程度地将特写镜头与长镜头进行有机排列组合,不断烘托渲染令人动容的悲壮氛围,“强制性”地将观众代入剧情,使观众在不知不觉中与影像所展示的时空“缝合”为一体,完成影像对观众的“询唤”过程。
同样,《八佰》也采用了非线性叙事结构,通过一江之隔的租界与四方仓库“同时性”事件,展现出淞沪战争之时,“八百壮士”舍生忘死、顽强抗击日军的悲壮历史事件。这两条情节线在不断交织中,逐渐增强联系性与交融性,不断深入挖掘两者之间在场景、事件、情境、情感等方面的对比、映照、相融直至共生的关系。
影片开头,一位老者以旁白的方式出场,娓娓道出小时候在苏州河畔对岸,亲眼目睹四行仓库里“八百壮士”与日军鏖战四天的壮烈场景。以普通人视角引入剧情,使市民与战士成为了“同时性”事件的见证者与参与者。随着剧情深入,两条情节线逐渐清晰显现出来。在一段悠扬的美声歌唱中,镜头缓缓展现一江之隔的两地:一边是已和日方持续激战三月之久,兵源骤减、装备紧缺,形势严峻、危机重重,仅剩420余人孤军驻守的四方仓库;另一边是沦陷上海中的租界,那里一片“太平盛世”,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市民们苟且地闲适且自由着的生活场景,仿佛战争之外的“海市蜃楼”,让人不由想起杜牧“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诗句。一静一动、一明一暗,形成强烈对比。士兵们在安静的夜晚出神地遥望对岸,发生在战场和租界的两条情节线在他们无比期待的眼神中逐渐交融,更加衬托出战争的残酷与悲壮。
后续剧情在两条情节线的不断铺陈与交汇中不断推进,随着时间的推移,两者间的交织愈发紧密。第一日,租界中的人开始关注对面战事,有市民使用望远镜不断观察对面发生的状况,他对战事的关注受到了妻子的不解与埋怨。此时的租界市民就和他一样处于一种观望状态,面对近在咫尺的灾难,他们以受到租界保护的侥幸心理自我安慰,自欺欺人地将自己置身于外。
当日军向四方仓库释放的“气体”扩散到租界时,市民开始疯狂逃散,平静的生活被彻底打乱。“气体”成为将两岸命运捆绑的“媒介”,使两条情节线开始关联。夜色降临,士兵端午偶然发现可以通过地下水道游至对岸逃走,却意外碰到日本人正潜水偷袭仓库,租界市民也同时发现,紧急打开探照灯提醒四方仓库守军。这一情节触发了两个空间位置间的枢纽,使两条情节线开始形成完全共时性的发展;租界中的人们已从旁观者转换成战争的参与者,市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御侮勇气被激发。
第二日开始,战事逐渐白热化,日军从正面向四方仓库发起猛烈的攻击。在激烈的战争场面中,多次插入租界群体对战事关注的画面,情节线开始密集交织,不断烘托出关联性的紧张氛围。因武器装备不够精良,士兵只能选择牺牲自我。一个个士兵身绑炸弹,毫无畏惧一跃而下,炸开日军的铁板阵队,将剧情推到最高潮。对岸的市民一个个驻足而立,悠闲自在的情绪被压抑悲痛所替代。亲眼目睹舍生忘死的壮烈场面,极大触动了国人内心深处的爱国情怀,租界市民的情感完成了重大转折,租界的情节线开始以一种积极参与的方式推进叙事——三位大学生冒险泅渡主动投身战争、翻译官深入战场记录真实影像、女学生冒死送去旗帜、赌场小混混牺牲自我送出电话线等等。
最后一日,士兵接到命令趁夜过桥撤进租界,两条情节线最终汇聚在一起,此时租界市民和士兵,同命运共呼吸。士兵在日军的枪林炮雨中冲锋陷阵、伤亡惨重,与一张张充满担心、痛心的市民脸部特写形成交织,最大化呈现出极具悲壮性的场面。影片的结尾,市民们伸出双手迎接士兵的一段写意镜头,将民族大义尽情展示,士兵主体性与两岸群体对话性得到了更为深层次的交融。
二、全知性到限制性认知层级的转换:思想性与悬疑感并存
“情节提供故事内容范围的尺度拿捏,于是就形成了认知层级(hierarchy of knowledge)之分,使每部电影都不同。”②根据故事情节,在全知叙述到限制性叙述的范围之间,选择适宜的认知层级并进行良好的转换,能够帮助一部影片更好地进行叙事表达与内容呈现。早期的军事题材电影包括当下部分宏大历史题材的军事题材电影,如《建国大业》《建军大业》《建党伟业》《百团大战》等,都是以全知叙述的方式讲述历史事件,使观众以一种“上帝”视角参与叙事,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悬疑性。这种全知叙述方式通过全景展现历史事件发展进程,勾勒群像式人物影像,凸显出事件的重大性与庄重性,但当多部电影都讲述同一事件时,难免产生同质化的问题,造成人物形象单一、事件发生既定、情节设置雷同的现象,从而使观众产生视觉审美疲劳。
新时期军事题材电影在对故事内容的呈现方面注重避免同质化的叙述方式,较好地利用了不同认知层级的叙事特点,给既定的历史事件注入了“紧张”和“悬疑”,丰富了影片的视听效果,并且通过多个限制性视角的对话,提高了影片的思想性和观赏性。
《金刚川》中的“士兵”单元,通过运用认知层级从全知性叙事到限制性叙事的转换,较好得将战争中全景式描写和个人限制性视角进行结合,在营造悬疑感的同时,凸显出“士兵”这一普通人物视域下的战争亲历感,在让观众身临其境的同时,也强调了小人物在历史事件的存在感和不可或缺性。单元开头以全知性叙述的方式,依次交代了影片的“核心事件”和主要人物,情节不断从一个人物转换到另一个人物,逐渐勾勒出“事件”的起因、时间、地点。这样的叙述策略,使观众在影片的开头就对故事背景、矛盾焦点有总领性的了解与认知。接下来,影片选择了三个人为作为本单元的主要人物,分别是邓超饰演的连长、李九霄饰演的班长和邱天饰演的女通讯员。其中班长作为“士兵”的代表性人物,与剧中其他单元的人物产生了观看与被观看的关系。例如他接到命令带着通讯工具爬到山坡上观察敌情时,全程目击了美国军机轰炸木桥以及高炮班和美国空军对战的场景。士兵目击事件的影像主要落脚于李班长的主观视角,属于限制性叙述。例如当他作为相当距离外的“目击者”时,在电影镜头中,“目击者”视线所及的两个炮位的画面是模糊不清的,观众与目击者的视线相重合,因此也是模糊不清的,这就产生了“悬疑”。这样的安排处理,目的就是让观众产生期待的心理效应,引导其参与剧情发展,产生悬疑效果。这种悬疑感一直持续到第三单元“高炮班”,当我们看到两个射击位的正面镜头与李班长的目击镜头组接时,悬疑得到解密,观众的期待心理也得到满足。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影片中唯一的女性角色——女通讯员,通过她的通讯内容,向观众进行了间接的全景展示;同时这一人物形象也代表了当时众多赴朝女兵,是一个更深远的全景暗示。
而《红海行动》则是将这种认知层级的转换运用于单个人物身上,通过个人事件的限制性叙述,完成和国家事件全知性描述的融合。影片巧妙使用了士兵石头随身携带的“糖”,作为限制性叙事元素串联事件的发展,给激烈且残酷的战争场景注入了一丝温情,也更加凸显出中国海军在保护国民人身安全时的英勇无畏。
“蛟龙突击队”在接到命令做准备之时,“糖”第一次出现,队友偷吃了一颗,被石头发现数量不对,交待了糖对于他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仅仅一分多钟的限制性情节插入,给观众留下一丝疑惑,“糖”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一情节激发出观众的期待。
在事件的不断发展中,影片特意多次将“糖”这一限制性叙述重复多次,并透露,因为石头小时候总被母亲打,吃糖就不会觉得疼,所以总喜欢在战斗时候吃糖。“糖”这一物品在观众脑海中不断增加记忆点,从而累积出大量的悬疑感,当悬疑感被在无限放大到临界值时,观众的期待值被无限拉满,全片最高潮也随之来临。“蛟龙突击队”在最终对战中异常激烈,石头在枪战交锋中壮烈牺牲,女兵佟莉抱着奄奄一息的他失声痛哭。临死前的两人关于“吃糖”的对话,无疑将限制性叙述的情绪累积推到顶峰,给人以强烈的情感冲击,成为了影片的一大泪点。
佟莉:“没事,石头。没事。”
石头:“好疼啊。”
佟莉:“吃糖,吃糖不疼。你不是说过,你说过吃糖不疼,你说过吃糖不疼。”
“吃糖,吃糖,吃糖。快,吃糖不疼,我们回家了,回家了。”
当石头咽下一颗糖后,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佟莉紧紧搂住他,爆发出了最后一句话“石头,不疼了,咱们回家了。”
“糖”在这种限制性叙事形式中,已不再仅仅是物品本身的意义,而是一种象征性符号,增加了影片的艺术思想深度。“糖”承载了对亲情的渴望、与战友的惺惺相惜。影片特意将“糖”这一意象反复出现,并不断强化这一意象,表现了当今中国军人既有柔软细腻、至情至深的情感,又有铮铮铁汉甘于奉献、舍生忘死的精神品质,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与立体。
这种对叙事范围的限制性处理,在《金刚川》“对手”单元中,为军事题材电影开拓出不一样的叙事视角和观影感受,创新性地选取了美军飞行员的个体限制性叙述,从敌军视角展现了轰炸木桥及与高炮班对战的场景。这一单元中对美军飞行员的刻画,争议、诟病较多。有人说画蛇添足,有人说美军形象虚假且做作,有人说影响影片的整体立意等等。笔者认为,这一视角的加入对于整部影片来说,不仅有利于影片结构的完整性,而且能使主题立意更好地表达和升华。此前绝大多数的中国军事题材电影都回避了对于敌军视角的描写,即使涉及也是进行了模糊化处理,形成了敌我双方二元对立的叙事策略。并且在对敌军形象的勾画上带有教条的立场色彩,人物形象大多是残暴、缺乏人性甚至是愚蠢透顶的。这种“脸谱化”的处理方式,使影片对战争中人性的表达无法深入。正如李英桃在《女性主义和平学》一书中所言:“具体丰富的人际关系转变成抽象的国家关系。以主权国家为中心的国际关系理论带来的最大悲剧就是使原本以人性为基础的人际关系转变成以抽象的国家利益为基础的‘国际冷血算计’,原本互不相识、毫无瓜葛的两个人,仅仅因为分属两个相互敌对的国家,便成了针锋相对、你死我活的敌人。人的生命在抽象的国家利益面前丧失了价值。”③
因此,新时期军事题材电影中敌军视角的加入,使电影的思想内涵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将原本二元对立的双方转换成二元统一的矛盾共同体,建构起一种一体化的叙事策略。这种策略非但没有弱化战士们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还通过不同意义主体之间的对比性对话,凸显了中国一直以来所奉行的维护和平与正义的国际主义精神。
三、主客观认知深度的结合:个体意识与集体理念的统一
认知深度是“剧情深入角色人物的心理状况程度”,有主观和客观之分,也正是热耐特所提出的“视觉聚焦”中的“内视觉聚焦”与“零视觉聚焦”。④新时期军事题材电影相较于以往,增加了许多“内视觉聚焦”的刻画,通过主观镜头深入人物内心世界,渲染出个人情绪表达的感性氛围。在现实且理性的战争事件中,主观情绪的表达凸显出个体力量与个体感受的重要性,给残酷且严肃的战争题材增添了人文关怀。
电影《金刚川》将“内视觉”与“零视觉”相结合,通过人物主客观视角的不断切换,将个体意识与集体理念通过巧妙置换实现了统一,从而形成小爱与大爱相融相生的情感互动,奠定了“小人物”折射“大背景”的叙事风格。影片在“对手”与“高炮班”单元中,就将属于不同立场之下的敌我双方,在同一个叙事时空下,以个人“内视觉”为切入点,建构起一种彰显人性的主题表达。
敌军视角是选取了一位名叫希尔·安德鲁的美军飞行员,开场用一系列客观镜头呈现出带有浓郁西部色彩的美国士兵形象:牛仔帽、敞开的座舱盖、《圣经》“启示录”的诵读等等。接下来一连串美国飞行员的主观镜头,展现出其个人对于轰炸的快感和处于优势的自得,即使是在看到桥被一次次修好的时候,在不可思议的感叹和完不成任务的愤怒之余,还是表现出掌握空中优势的自信和嚣张。然而他的形象并不是一成不变,随着“事件”的推进发展,驱使他进行轰炸任务的内在动因发生了改变。在一个主观镜头展现队友被击落之后,人物形象从单一、平面的任务执行者演变成个人为兄弟情谊而战的复仇者。这种复仇催使他与高炮班进行了无数次的正面交锋。美国飞行员的个体意识,与其背后的集体理念又是统一的。而这种疯狂的统一,反向凸显了高炮班士兵们的英勇无畏。同时美国飞行员队友之间的情谊与第三单元中高炮班张飞、关磊的战友情,在“复调式”结构中形成了一种对话性,呈现出在不同立场和价值观之下的交锋中也不乏人类的共通情感,表现了残酷战争中的人文因素,扩大了观众在观影时达到共情的效果。
志愿军视角选取的是高炮班的士兵们,主要集中于书写高炮排长张飞与班长关磊之间的战友情谊,他们之间的情感关系正如上文所说,与第二单元中的美国空军之间的情谊形成了一种互文性,展现出在同一战争时空下,不同国家、不同立场下士兵共同具有的友情和赴死精神。并且在这种互文性的对话上,两方视角有着差异性的情感表达。在张飞与关磊的情感关系表达上,除了有类似于美国士兵之间兄弟友情的小爱之外,更多折射出抗美援朝战士们团结斗争的友谊和不畏牺牲、舍生忘死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这种将小爱与大爱相融相生的情感表达,进一步凸显了牺牲精神的深厚源泉,增大了引发情感共鸣的可能性。尤其是在张飞得知关磊选择暴露自己保全隐藏炮位而牺牲之后,毅然决然地发射五发曳光弹并下令点火,暴露自己,誓与敌机决一死战时,更是如此。对于张飞这一段的画面描写,镜头语言充满了浪漫主义的暴力美学风格,当他被炸伤只剩下一条胳膊和一条腿时,画面使用了大量的大背光、暖灯源光线处理,渲染出压抑、悲愤的气氛;高仰拍的视角,刻画出平时木讷低调的张飞英勇伟岸的身影,加上面部特写镜头组接,形成了电影画面特有的感染力。宛如被鲜血染红的天空、血淋淋的断腿断臂、痛苦扭曲的面部表情等一系列画面,直白地表现了战争的残酷,通过浪漫化的镜头处理表现出一种感人的悲壮、一种神性的力量、一种人性的光辉,使观众直面逼真、壮烈的战争场面的时候,还能感受到为民族国家牺牲“小我”的大义善良、人性温情。正是这样的一种处理方式,一定程度上弱化、消解了影片中战争场面的暴力与血腥,摆脱了直接简单呈现战争残酷的一般框架。在释放暴力的同时,将低级的感官刺激转化为由伟大牺牲精神引发的崇高感。
个人意识与集体理念的统一,在《战狼2》中也有所体现。影片通过叙述一桩国际事件,体现现代中国军人的责任与价值;借助刻画中国军人形象,树立国家形象,并实现中国价值观的国际化传播。电影以冷峰的“内视觉”回忆构建起个人层面的激励事件,冷峰之所以在离开特种队之后,选择前往非洲工作,是因为未婚妻在出任务时被杀害,他因个人原因前去调查,为妻报仇。当撤侨任务的国家层面事件出现时,冷锋身上肩负起了家国双重使命,他主动请缨加入作战,营救困于非洲战乱地区的同胞。影片将杀害未婚妻的凶手设置为阻碍营救任务的雇佣兵头目“老爹”,巧妙得将个人恩怨与国家使命进行了链接与交融,缝合了商业片与主旋律电影间的“裂隙”,有助于进行主流价值观的输出与传播。冷锋对未婚妻的“内视觉”回忆在影片中多次出现,用闪回的形式不断累积他选择留下来帮助撤侨的内在动因,使得情节发展更具有合理性,也更有助于激发观众观影感受中的个人情绪,增加贴近性与代入感。
但有争议的是,当下中国军事题材电影在对战争场面的客观描写上确实存在些许暴力倾向,如《金刚川》《战狼2》《八佰》等对于肉体牺牲充满血腥氛围的表达,是否适宜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审美接受;这种具有好莱坞式的暴力美学倾向,对于偏好中庸含蓄、内敛克制的中国式审美习惯,影像与观众之间的传达与接受是否能够实现顺利对接……这些问题,在后续观影评价的反馈中,确实存在因观影者的审美感受差异而出现不同看法。“事件”的残酷性,是战争本身的规定性,因此作为“非虚构”的艺术表达,不应该抹杀“事件的本质”。不能因为有人怕辣,就让辣椒从市场上下架。当然,军事题材电影能否在国际化传播与本土化表达之间找到合适的对接口,实现良好的艺术转码,可以作为一个探讨的范畴。
结语
新时期中国军事题材电影,如《金刚川》《八佰》《红海行动》《战狼2》等影片在新时代语境下,作了新的尝试和探索。这些电影在叙事形式上不断进行解构与重建,通过故事情节的非线性建构,达到人物主体性与对话性的互溶,使情节线交叉互叠带来的冲击力最大化;通过全知性与限制性认知层级之间的恰当转换,在加大悬疑感的同时,挖掘和提升影片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通过将个体意识与集体理念的置换融合,从而更好进行主流意识形态的植入与传播。但任何尝试都不可能完美,此类型电影多少还存在一些问题,如结构逻辑的严密性、人物形象塑造的丰满性、细节刻画的真实性、影像试听表达留白等,永远有探索余地、尝试创新不会中断。
当下,中国军事题材类型片结构创新,如何承载起战争内容本身的立意表达;如何通过对战争内涵的不断解构与重构,深入挖掘其思想性;如何达到“非虚构”影视的真实性与艺术性的有机融合;如何更好地表达、弘扬主旋律;如何更好地把满足观众审美需求与价值观传播紧密缝合,将是这一类型电影面临的重要课题。
注释
①李道新《中国电影文化史(1950—2004)》[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07页。
②[美]大卫·波德维尔、克莉丝汀·汤普森《电影艺术:形式与风格,曾伟祯译》[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版,第107页。
③李英桃《女性主义和平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9页。
④[加]安德烈·戈德罗、[加]弗朗索瓦·若斯特《什么是电影叙事学》[M],刘云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1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