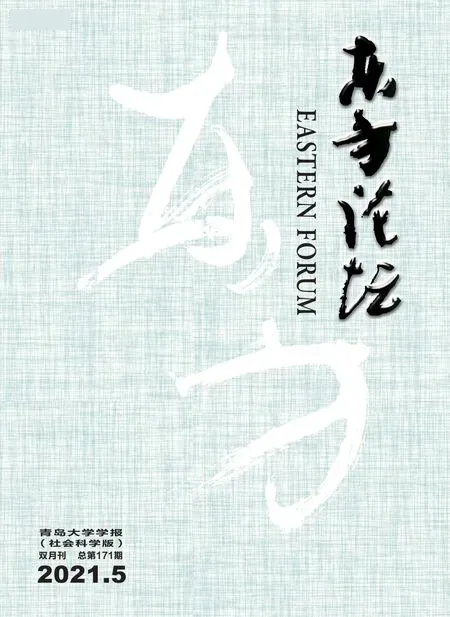重庆谈判的后续演进
王 令 金
青岛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本人曾于《东方论坛》2020年第2期发表了《重庆谈判综论》一文,论述了重庆谈判的时代背景、事前邀约、谈判经过、结果分析、矛盾根源及历史价值等问题。当时囿于篇幅和资料,对一些相关问题没有进行论述。为使学界同仁更加全面地了解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特对重庆谈判结束后国共两党继续进行谈判及其结局作些概述。
一
重庆谈判签署“双十协定”后,共产党方面继续留周恩来、王若飞等以原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为基地与国民党方面周旋。参与重庆谈判的张治中、邵力子等协同共产党方面的代表致力于“双十协定”的贯彻落实之中。
众所周知,“双十协定”的核心内容是确定了和平建国方针,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理性解决政治纷争,荡涤社会污垢,促进人类文明。所以,贯彻落实这一协定的首要举措,就是遏制内战,维护和平。然而,早在重庆谈判期间,国内局部地区已处于硝烟弥漫、杀声震天之中,突出表现在山西上党地区。从1945年9月10日至10月12日,山西上党地区的人民解放军在刘伯承、邓小平的指挥下回击阎锡山部队的进攻,歼敌35000多人,击毙国民党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俘虏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等高级军官20多人,使阎锡山损失总兵力1/3。这次战役是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军队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较量,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气焰,但同时也加重了内战爆发的局势。其时,张治中正忙于解决新疆“伊宁事件”。①1944年11月7日,伊宁维吾尔、哈萨克等少数民族群众,因不堪忍受军阀盛世才的压迫,发生了革命暴动,消灭了国民党驻军。随后,占领了伊犁、塔城、阿山(今阿勒泰)三个专区,并于1945年初建立革命政府。抗日战争胜利后,三区革命运动继续发展。国民党政府迫于压力,派出以张治中为首的代表团于1945年9月15日飞抵迪化(今乌鲁木齐),与三区革命政府代表进行谈判。几经谈判,至1946年6月6日,伊宁事件和平解决。他心情十分焦灼:一方面,痛感伊宁事件棘手,双方商谈进行迟缓;一方面,国共军事冲突升级,大有演成内战之势。11月,国民党在重庆筹备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对共作战问题,各战区高级将领齐集重庆。当此之际,张治中写了一封万言书,托国民党驻迪化第八战区副长官郭寄峤带去转呈蒋介石。信中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对中共问题主张采取政治方式和平解决,而不能再度陷入战争。他痛陈八年抗战之苦——沦陷区人民既遭受了日寇的践踏,又历尽了伪军的压迫,民穷财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即使大后方民众,亦以物价过高,负担过重,一般生活备感痛苦,徒以大敌当前,不能不尽最大之坚忍,以期待胜利之来临;眼下,抗战胜利结束,全国人民祈求和平,恢复正常生活秩序。如果战争再度爆发,人民又要生灵涂炭,这当然是违背民意之举。所以,站在政府的立场上,感到于心不忍。故今日人民之厌恶战争,渴望和平,将汇为不可遏止之时代巨流,可不待烦言而喻者。以今日之国军士气与态度而论,亦不能继续作战。各将领在钧座之前,或不敢显然作厌战之表示,甚至有自告奋勇,坚持以武力解决中共者,然以职所接触之若干将领中,其不愿战争之心理,甚为普遍;且今日多数之国军,实亦不能作战。吾党革命,历五十余年之苦斗,千百万先烈流鲜血,抛头颅,以获取革命政权,至今日始奠定建国之初基,方冀黾勉从事于亿万斯年基业之缔造,绝不能轻率从事,作孤注之一掷。必推广老成谋国之心,期立于永远不败之地。②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北京:华文出版社,2014年,第528—529页。张治中的劝诫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集中体现为国共双方停战的呼声越来越高。
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签订《停战协定》,成立了张群(国民政府方面的代表)③因蒋介石等不及,先派张群同周恩来、马歇尔谈判停战问题。1946年1月2日,张治中自新疆启程,经酒泉、兰州,至6日到达重庆。同月底,张治中代替张群。、周恩来(中国共产党方面的代表)、马歇尔(美国总统特使,亦即美国政府方面的代表)组成的军事三人小组,专门研究国共两党领导的军队之整编统编问题。同时,在北平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由国民党人郑介民、共产党人叶剑英、美国人罗伯逊三人组成,作为军事三人小组议事的执行机关。从2月14日至25日,军事三人小组进行正式会议和会外协商,最终在重庆上清寺尧庐签订了《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其中规定:全国陆军应为一零八师,每师人数不得超过一万四千人,在此数内,由中共部队编成者计十八个师。本协定公布后十二个月内,国民政府应将九十师以外之各部队复员,中共应将十八师以外之各部队复员,复员应立即开始,并大致每月裁减总复员人数十二分之一。④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第532、533页。为使方案得到实施,军事三人小组乘专机到各地(北平、张家口、集宁、归绥、太原、济南、新乡、徐州、武汉等地)进行检查。3月4日下午,到达延安,受到中共中央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以及数千群众的欢迎。对此,张治中风趣地说:“你们将来写历史的时候,不要忘记‘张治中三到延安’这一笔!”。⑤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第540页。这是张治中第三次到延安。前两次分别是1945年接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和谈判结束后送毛泽东回延安。
在张治中为和平建国东奔西忙的同时,邵力子也在致力于和平大业。1945年12月19日,在周恩来举办的宴会上,邵力子说:“和平建国是我们两党的共同心愿,也是全国人民多年来的愿望。我们国共两党早就应该团结起来,避免内战,共同建设我们的国家。”①舒风:《周恩来与邵力子》,北京:华文出版社,2001年,第188页。1946年1月12日,邵力子在政治协商会议上向与会代表们报告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经过。他说:“本人始终相信双方都有诚意解决问题,其尚未能让步之点,因各有其不能让步的立场,但决非始终不能互让解决。”②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重庆谈判纪实》,重庆:重庆出版社,1983年,第362页。此言表明,邵力子对和平建国抱有信心和希望。
然而,事态发展出乎意料。1946年6月,国民党悍然撕毁“双十协定”和政协协议,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发动了全面内战。对于国民党的倒行逆施,邵力子感到愤慨。同年11月,国民党召集包办“国民大会”,遭到广大人民的强烈反对,中国共产党拒绝派代表参加,邵力子也拒绝参加本次会议,表明了自己的严正态度。后来,随着内战范围不断扩大,国民党关闭了和谈大门。1947年2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派军警包围了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的办事处,并限期在3月5日前撤离全部人员。对此,周恩来打电报给蒋介石,厉言:“阁下业已决心内战到底,不惜以最后破裂关死一切和谈之门”“请阁下以正式公函通知我方驻京代表董必武,须延长撤退期限至三月底。”③舒风:《周恩来与邵力子》,第201页。3月7日上午,董必武率领上海、南京两地工作人员由南京乘飞机返回延安,邵力子、张治中等怀着悲愤,到机场送行,并致保重。至此,国共两党谈判陷入停滞状态。
综上可见,在重庆谈判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内,张治中、邵力子一直代表着追求和平的势力同中国共产党及全国人民一道争取和平。然而,一意孤行的蒋介石却违背民心,置人民的生命安危于不顾,发动内战。
二
经过两年多的战争较量,蒋介石集团连连败退,非但江北保不住,而且江南也岌岌可危。于是,不得不重新抛出和谈烟幕。
当此之际,1948年12月30日,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1949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一些重要媒体进行了转载。此文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将要“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④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75页。由此,向国民党当局释放了强硬的信号。1949年1月1日,蒋介石发表了《新年文告》,乞求和平。声称:“我惟有对我的领导无方引咎自责,有负国民负托之重,实不胜其惭惶悚栗。”“只要共党一有和平的诚意,能作确切的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⑤魏宏运:《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5),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23、724页。蒋介石还气壮如牛地表示:“我始终持有必胜之信念,而最后也必能达到成功的境迂。”“正义是决胜的力量,公理终必胜过暴力。”⑥魏宏运:《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5),第725页。1月21日上午,蒋介石召集会议,宣布:“在目前情况下,我个人非引退不可,让德邻(李宗仁,字德邻——笔者注)兄依法执行总统职权,与中共进行和谈”。⑦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下),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91页。第二天,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了李宗仁接任总统的文告。蒋介石宣布下野后,回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老家操控国民党政权。对此,蒋介石的私人医生熊丸回忆道:“蒋先生下野后,在溪口仍以总裁身份见客”“在溪口期间,张治中(文白)曾来见总裁,李宗仁也曾托人带信,希望总裁出国”。①熊丸:《蒋介石私人医生回忆录》,北京:团结出版社,2010年,第66、69页。
李宗仁上台后,开始着手谋划与中国共产党方面和谈。2月8日,李宗仁到达上海,经过与各方面协商,决定成立“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成员包括颜惠庆、章士钊、江庸三人,另外,邵力子以私人身份参与其中。此代表团的使命就是“敲开和平之门”。2月13日上午,“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成员自龙华机场乘中航专机,经青岛,去往北平。14日下午抵达北平,到机场欢迎的有北平市市长叶剑英的代表王拓、副市长徐冰等人。当晚,邵力子等四位老人被安置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15日上午,叶剑英前去看望四位老人。在北平期间,邵力子等与中共方面董必武、聂荣臻、薄一波和刚起义的傅作义、邓宝珊,以及民主人士、科技文化艺术界的代表,广泛接触,交流想法。邵力子表示:现在全国人民终日盼望的就是停止战争,实现和平。我这次来北平是谋求和平的,希望和平障碍能够迅速扫除。我不代表任何方面,仅仅是传递江南人民的心愿,他们日夜企盼和平。②舒风:《周恩来与邵力子》,第220页。22日,邵力子、颜惠庆、章士钊、江庸、傅作义、邓宝珊等人先乘飞机去石家庄落脚。他们到达石家庄短暂逗留后,转乘汽车奔波至西柏坡(当时属于河北省建屏县,后划归河北省平山县)。他们到达西柏坡后,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接见。24日上午,毛泽东和周恩来再一次与上海代表团的代表举行会谈,达成秘密(约定只能告知李宗仁)协议,内容包括八个方面,择其要者:其一,中国共产党和南京国民政府各派同等数量的代表出席谈判;其二,谈判地点选在石家庄或北平;其三,谈判内容以中国共产党方面1949年1月14日发表的声明中所提出的八条为基础;其四,谈判方式绝对秘密,并且速议速决;等等。③舒风:《周恩来与邵力子》,第224—225页。同日下午,代表团一行由李维汉陪同乘车到石家庄乘飞机,再回北平。27日上午,代表团一行乘飞机离开北平,中午抵达南京。3月2日,飞返上海。24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了“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成员有邵力子(任首席代表)、张治中、黄绍竑、章士钊、李蒸。28日,又增加刘斐为代表。由于邵力子坚辞首席代表,后改由张治中担任。
4月1日,“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六位成员和屈武、李俊龙、金山、刘仲容四位顾问以及卢郁文、余湛邦、张丰胄三位秘书长、秘书等20余人,乘中央航空公司“空中行宫”号(俗称“天王”号)专机飞抵北平,下榻六国饭店。当日晚上6点,中国共产党方面的代表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聂荣臻等设宴招待代表团一行,并初步交换和谈意见。④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第574页。从4月2日到12日,双方代表采取一对一的方式交换意见。周恩来对张治中,叶剑英对黄绍竑,林伯渠对章士钊,李维汉对邵力子,聂荣臻对李蒸,林彪对刘斐。⑤莫志斌:《张治中传》,北京:团结出版社,2000年,第352页。在交换意见当中,有些取得了一致,有些分歧较大。这期间,自4月8日起,毛泽东在北平香山双清别墅(此时,中共中央领导人及办公机关已于3月底迁至此地)分别约见各位代表谈话。13日,周恩来将《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交给张治中,并通知当晚9点在中南海勤政殿开会讨论。会议首先由周恩来对《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作了概括的说明,然后张治中把不可能接受的各点逐一提出,指出愿就中共所提草案再加研究,并提出了修正案。他诚恳地表示:“我今天在中共代表团诸位先生面前,不想说什么恭维的话,但我愿意唤起各位先生的注意,今后国家的责任,是落到了你们的肩膀上。国民党的政权当然是完了,今后的国民党或者再经过一番改造后,做中共一个友党。目前则我们以至诚至敬之心,希望中共能从此领导国家,达到独立、自由和民主的目标,并建设国家,臻于富强康乐之境。”①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第591—592页。14日晚上,张治中把经过研究修改的修正案交给周恩来,并和周恩来谈了很久。15日早晨,各代表复与中共代表分别交谈,希望能够找到一线解决的希望,但收效甚微。晚上7点,中共方面将最后定稿的内容包括“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中华民国宪法》及一切法统”“改编南京国民政府的一切武装力量”“没收官僚资本企业”“废除封建土地所有权制度”“废除南京国民政府所订立的一切外交条约、协定”“维持地方治安和正常社会生产”的《国内和平协定》②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51—1456页。送给张治中,并定于当晚9点仍在勤政殿举行第二次会议。届时,会议由周恩来先把定稿修正之点加以说明,然后郑重提出渡江问题,并且再三说明,这是最终定稿,不可变动。在4月20日以前,南京政府若同意上述协定,就立即签字;否则,人民解放军就马上过江!以上内容,对于国民党方面来说,如同下达了“通牒书”。既然如此,“大家表示只有接受这个《国内和平协定》为是。并决定在16日派黄绍竑代表和屈武顾问带了文件回南京去,劝告李、何接受。”③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第605页。至20日深夜,张治中收到南京政府李、何(即李宗仁、何应钦)电报。内称:“纵观中共所提之协定全文,其基本精神所在,不啻为征服者对被征服者之处置。以解除兄弟阋墙之争端者,竟基于帝国受降之形式;且复限期答复,形同最后通牒,则又视和谈之开端,为战争之前夕;政府方面纵令甘心屈辱予以签署,窃恐畏于此种狭隘与威压作用,刺激士气民心,同深悲愤;不特各项条款,非政府之能力所能保证执行,而由此引起之恶劣影响与后果,亦决非政府能力所能挽救。”“希望中共方面,确认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之原则,对此项协定之基本精神与内容,重新预以考虑。”“极盼能即日成立临时停战协定,借以表示双方谋取真正和平之决心与诚意,俾和谈得以顺利进行。”④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第605—606、607页。显然,南京政府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21日上午9时,南京方面代表团把李、何复电抄送中共,并请再加考虑。此举为时已晚,于事无补了。之前,即20日午夜,毛泽东、朱德联名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各野战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和南方各游击区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奋勇前进,逮捕一切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⑤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51页。随之,发起了渡江战役。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在西起江西湖口东至江苏江阴长达500多公里的战线上强力渡江。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宣告了国民党政权的覆灭。
三
谈判破裂后,张治中召集代表团开会,商量何时回返南京问题。邵力子当即表示坚决不回南京了,张治中表示要回南京“复命”,其他代表犹豫不决。4月19日,邵力子的夫人傅学文已搭乘飞机抵达北平。⑥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和平老人邵力子》,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第247页。24日,张治中的夫人洪希厚和子女也被接到北平。⑦舒风:《周恩来与邵力子》,第247页。由此,滞留北平的南京政府代表团全体成员均留北平。黄绍竑回南京后与政府闹翻,飞往香港。9月上旬,由香港转赴青岛,再去北平。屈武回南京后也与政府不合,回到新疆继续投入促成新疆和平解放工作,并作出了重要贡献。张治中、邵力子为争取国内和平走南穿北、劳苦功高,分别赢得了“和平将军”“和平老人”称号,在人们心目中享有很高威望。
重庆谈判达成的协议难以实施和“北平和谈”最终破裂,究其主要原因,确系蒋介石一贯坚持反共立场使然。向之论者指出:“蒋介石对国内社会的成员,采取兼容并包的办法,举凡北洋政府的遗老、已褫夺兵权的军阀、社会名流、重要绅商,或在他的政府里担任名誉上或实际上的职务,或被他推崇而拥有优厚的社会地位。但是,他对于共产党党人及左翼作家则毫不假借。并且于1927年的宁汉分裂开始,极力排共。”①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黄仁宇全集,第六册),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471页。诚然如此。早在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表面上对毛泽东一行礼貌有加,而内心里却用最不堪的字眼形容对方。在蒋氏的日记中可屡屡见到类似的记载。诸如,1945年9月9日写道:“抗战虽胜,而革命并未成功;第三国际政策未败,共匪未清,则革命不能曰成也。勉乎哉!”9月17日写道:“共匪诚不可与言矣!”9月24日写道:“共匪在日本未投降前之阴谋,拟将全部沦陷区归其所有,并以沦陷区民选政府名义召集人民代表大会,以对抗我国民大会。阴毒极矣!”10月11日写道:“今晨8时,约毛泽东早餐后,余再与之恳切对谈……彼去后,散步林园一周毕,记事,批阅公文,甚叹共党之不可与同群也。”②张秀章:《蒋介石日记揭秘》(下),北京:团结出版社,2007年,第741、743、745页。通过以上几则日记,可以看出,(1)蒋氏把灭掉“共匪”看作是“革命成功”的标志;(2)蒋氏对中共存有高度的戒备之心;(3)蒋氏不可能与中共“精诚合作”。因此,重庆谈判结束后,在执行“双十协定”问题上,蒋氏大打折扣。蒋氏对中共的敌意态度始终没有改变,在其日记中仍然用“共匪”称呼中共。诸如,1946年1月17日记有“今共匪仍在各省积极向我国军侵犯”;1月19日记有“共匪自13日停战令以后,反在华北发动攻势”。③张秀章:《蒋介石日记揭秘》(下),第747、748页。另外,蒋氏把共产党视作天敌,拒不让步。在1946年1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近日心神痛悔交集。乃知往日对共党宽容之误事也”;在同年4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唯有美方坚持积极协助我政府之政策,方能达成消极‘容共’之目的。若仍采取过去对共党怀柔与妥协之方针,则将贻误大计,必至根本失败而后已。”④张秀章:《蒋介石日记揭秘》(下),第749、754页。既然如此,蒋氏显然是想与中共势不两立,战斗到底!直到1949年春天,国民党败局已定、李宗仁当局策划北平和谈之时,蒋氏仍然坚持其顽固立场,认为“李宗仁和谈方案,其中心条件,无异于协同共匪消灭国军之基础耳。”⑤张秀章:《蒋介石日记揭秘》(下),第777页。在北平和谈期间,蒋氏认为“共匪对政府代表所提修正条件二十四款,真是无条件的投降处分之条件。其前文叙述战争责任问题数条,更不堪言状矣。黄绍竑、邵力子等居然接受转达,是诚无耻之极者之所为,可痛。”⑥张秀章:《蒋介石日记揭秘》(下),第778页。当北平和谈破裂之后,李宗仁集团负隅顽抗,蒋氏倒认为“中华民国生机与国民革命之复兴,亦即在于此也。”⑦张秀章:《蒋介石日记揭秘》(下),第778页。其实,仅是幻想而已。
再则,在北平和谈中,双方所执条件可谓大相径庭,几乎没有谈拢的可能。事前,蒋介石对和平的基础提出了五条原则,即“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犯,民主宪政不由此而破坏;中华民国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最低生活水准”。①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下),第687页。针对“战犯求和”,毛泽东提出了八项和谈条件,即“(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利。”②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389页。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方面还公布了一批战犯名单,有43人之多。其中,蒋介石位居第一,李宗仁位居第二,白崇禧位居第三,后续者有孔祥熙、宋子文、孙科、陈立夫、陈诚等。③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下),第687页。显然,上列战犯均不能逃脱历史罪责,应严加惩办。在此形势下,战犯们不会轻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相反,他们要凭借江南半壁河山负隅顽抗。那么,其对立面一方中国共产党,只能大义凛然,歼灭敌人。在大难临头之际,李宗仁似乎不像蒋介石那么顽固,对中共作了些原则性的让步,但其提出的五项条件与中共方面的条件亦距离颇大。诸如:“一、政府同意通过政治方法解决一切国家问题。二、各方指派一正式代表团,立即恢复和谈。三、和谈时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四、今后国家重建工作按下列原则进行,即组成民主政府,平均分配财富,军队国有化,全体人民自由生活。五、今后与外国的事务,按照民族平等、互相有利的原则进行。”④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下),第702页。然而,李宗仁的狡黠,模糊不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人的慧眼。所以,一旦中国共产党方面采取反制,而李宗仁就很快陷入泥潭。鉴于上述各方条件相距太大,所以,各方代表团无论如何,均难超脱逾越各方首脑划定的界限。既然如此,和谈破裂就可想而知了。
时光流逝,江河依旧;回顾往事,感知当下。谈判以实力为基础,以诚信为原则,坚守正义,恪守诺言,各尽其责,方可有成;不然,空耗时光,劳民伤财,徒以破裂为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