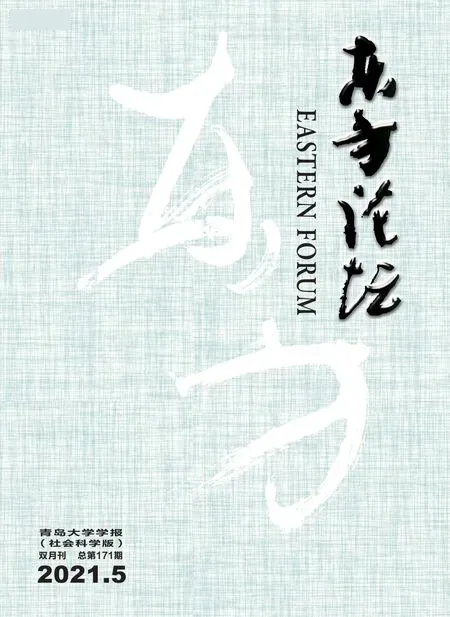《大唐西域记》与比较文学
王 汝 良
青岛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大唐西域记》是玄奘求法归来后所撰的一部内蕴丰富、影响深远的作品,是东方文化史上的一部经典之作;比较文学则是一门探究本土与异域、自我与他者的文学关系和文化关系的学科,跨越性、开放性是其主要特征。以比较文学的视阈对《大唐西域记》进行观照和研究,有助于更好地发掘这部东方文化经典的深邃意蕴,突显其学术价值,同时,也可为拓展和深化比较文学的学术空间提供一个范例。
一
比较文学研究的基本特征是跨学科、跨文化、跨语言和跨民族,而作为研究对象的《大唐西域记》本身即具有鲜明突出的上述四个特点,是一部典型的比较文学研究文本。
在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中,《大唐西域记》被列入史部地理类。它基本以作者玄奘的游踪为序,对七世纪及以前南亚、中亚、西亚以及现中国新疆境内诸地区(其中亲历110国,得之传闻28国,另加附带述及的12国,共150国)的历史地理状况进行了相对客观的记载和描述,成为上述地区史地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如:卷一对中亚素叶水城(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以南的阿克·贝希姆遗址)、呾逻私城(今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江布尔城)和卷十二对波谜罗川(今帕米尔谷地)的描述,均为迄今所见的最早汉文记载。英印殖民政府时期,考古调查局局长、考古学家坎宁安(A. Cunningham)在对印度鹿野苑、大菩提寺、那烂陀寺等遗址进行发掘的过程中,最为倚重的即为英译版《大唐西域记》,其中,在重建大菩提寺时,在寺址方位、建筑图案和使用材料的选择上都参考了《大唐西域记》。《大唐西域记》问世后不久即入典佛藏,对佛教研究来说,《大唐西域记》可视为一部隐性存在的糅合佛教史实与传奇,既有学术性又有普及性的西域佛教史著作。它记载了大量的佛本生、佛传故事,诸菩萨、罗汉传奇,护法名王、著名论师故事,佛教的重大活动和佛教圣迹等。其中,对七世纪及以前大、小乘的分布和传播情况以及佛教内外论争(内部的如大、小乘之间,大乘空、有宗之间及其他各派别之间,外部的是指同印度教、耆那教、祆教等的冲突)的记载,学术史价值极高。此外,作品中多处提到婆罗门教、耆那教、祆教的情况,甚至涉及密教和印度民间宗教怛特罗教,是中古期东方宗教研究的宝贵参考。《大唐西域记》还提供了大量的民俗学研究资料。如:卷一屈支国、卷十二佉沙国的“扁头”习俗,卷一、卷二的“嚼齿木”习俗,卷二印度人不食牛肉、葱、蒜,“涂牛粪为净”,卷十一“西女国”的独特婚配,卷十二妇人“首冠木角”习俗等。在文学领域,《大唐西域记》的价值也已越来越引起重视,系列研究成果陆续出现。总之,《大唐西域记》蕴涵丰富,在史地、宗教、民俗、文学等学科领域均有重要的价值,且这些价值本身就是相互关联、密不可分的。如:卷七所记载的“烈士池”传说,产生于印度历史上三大宗教的共同中心婆罗痆斯城,又具有佛教、怛特罗教(印度民间宗教)的宗教背景,还牵涉到是否渗透道教因素的探讨。同时,该传说采用了东方故事文学习用的“框架式”结构,又属典型的口头叙事文学作品,既实现了对印度“活态文学”的保存,又在中国、日本、朝鲜的传播过程中发生了重要的变异。如此,史地、宗教、民俗、文学和文化交流等诸多因素交融互渗,这一个案便是《大唐西域记》跨学科特性的典型体现。
玄奘出身于儒学世家,自幼“备通经典,而爱古尚贤。非雅正之籍不观;非圣哲之风不习”①慧立、彦悰著,孙毓棠、谢方点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5页。,儒学修养深厚。出家后,聪悟勤勉,笃志向佛,经国内南北游学、遍访名师,奠定了深厚的佛学根基。他从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出发,到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回到长安,行经中国内地、边疆,中亚,西亚和南亚等广大地区,对沿途各地佛教和其他宗教的分布情况进行了实地考察。在印度期间,他访名寺、从名师,精研佛典,勇于论辩,成为名扬五印的佛教论师,被尊为“大乘天”和“解脱天”。归国后开宗立派,创立法相唯识宗,并培养了包括日本、朝鲜、西域僧人在内的诸多佛教人才。同时,组织译场,翻译经书,创立翻译理论,开一代新译之风,也曾将《道德经》和《大乘起信论》翻汉为梵。如此,玄奘是一个多元文化的体验者、记录者和创造者,《大唐西域记》便是以上多元文化交流历史的客观体现。前已述及,佛教文化是《大唐西域记》所关注的重中之重。玄奘往返西域途中,所遇到的“外道”中,最大的一支当属婆罗门教。婆罗门教宣扬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婆罗门至上,佛教作为婆罗门教的对立面发展起来,力倡相依缘起、不杀生、众生平等,与婆罗门教针锋相对。这种冲突和斗争在《大唐西域记》中有着大量体现,如卷八所记马鸣菩萨摧伏鬼辩婆罗门,卷十所记龙猛菩萨战胜提婆外道等。《大唐西域记》对印度本土的另外一种传统宗教——耆那教也有记述,如卷三记僧诃补罗国的白衣外道,“其徒苦行,昼夜精勤,不遑宁息。本师所说之法,多窃佛经之义,随类设法,拟则轨仪,大者为苾刍,小者称沙弥,威仪律行,颇同僧法。唯留少发,加之露形,或有所服,白色为异。据斯流别,稍用区分。其天师像,窃类如来,衣服为差,相好无异”①玄奘、辩机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704页。,不但对该宗教的精修苦行、衣着仪法予以记述,还重点指出此宗教与佛教的相类之处②玄奘此处意指耆那教在教义和仪轨等方面模仿佛教,实际上,耆那教起源和兴起的时间要早于佛教。。在玄奘西行的七世纪,祆教(即琐罗亚斯德教)在中亚、西亚有广泛信众,《大唐西域记》中也多次出现关于该教的信息,如卷八记如来摧伏事火外道迦叶波三兄弟所奉祀的火龙(祆教崇拜火神,此火龙即祆教的象征),卷六提到舍利子降伏外道六师③也称为六师外道,即中印度境内的六个主要外道学派,分别为富兰那师、末伽梨师、删阇夜师、阿耆多翅舍师、迦鸠驮师和尼犍陀师(即耆那教中兴祖师)。外,还以“日旦流光,天祠之影不蔽精舍;日将落照,精舍之阴遂覆天祠”这一现象,形象地描述佛教与祆教的相争,结果是佛教精舍所留下的阴影始终盖过天祠,寓意十分显明。此外,玄奘本生长于儒学之家,儒家文化的痕迹在《大唐西域记》中也随处可见,如《序》中对南亚文化的“躁烈”“异术”,西亚文化的“无礼义”“重财贿”和北方游牧文化的“天资犷暴”“情忍杀戮”给予的排斥或批判,突显出以礼义、中庸为特征的儒家文化观;再如:卷一对窣利地区粟特商业文化评价道,“风俗浇讹,多行诡诈,大抵贪求,父子计利,财多为贵,良贱无差”④玄奘、辩机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第704页。,实际上也是潜意识地在以儒家的义利观进行对照。总之,佛教文化、印度教文化、耆那教文化、祆教文化、儒家文化等或显或隐、或共存或相斗地融于《大唐西域记》中,成就了其鲜明的跨文化特色。
《大唐西域记》也是一部典型的跨语言文本。文本中所直接涉及的有梵文,间接涉及的则有中亚、西亚等语言文字,如在卷二“印度总述”中,对印度的称谓进行解释时说,“详夫天竺之称,异议纠纷,旧云身毒,或曰贤豆,今从正音,宜云印度。印度之人,随地称国,殊方异俗,遥举总名,语其所美,谓之印度”⑤玄奘、辩机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第161页。。在该处,玄奘列出古代中国人对印度的几种称谓“身毒”“天竺”“贤豆”“印度”,集中关涉到梵文经中亚、西亚语言转译至中文的复杂情况。身毒,源于印度河的梵文形式Sindhu,后在波斯语中发生音变,中国古代音译为“身毒”。天竺、贤豆,来源皆与身毒相同,前者始于《后汉书》,自东汉至唐期间被中土僧俗广泛接受。玄奘认识到印度的诸多汉译名称“异议纠纷”,选择“正音”(即梵文)翻译定名为“印度”。印度,自《大唐西域记》中出现后,一直被中国人沿用至今。实际上,在古代南亚次大陆地区,是没有一个“总名”之类的称呼的,“印度”这个称谓同样来源于梵文Sindhu一词,该词在波斯语中发生音变后被西域地区的广大民族采为印度的国名,后以西域语言为媒介译为汉语中的“印度”。⑥参见玄奘、辩机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第162—163页;钱文忠:《“印度”的古代汉语译名及其来源》,见《中国文化》第4期;徐真友:《也谈古代印度汉名》,载《正观杂志》第17期,2001年6月25日。此外,对中国人普遍使用的“观音”“观世音”概念,玄奘在《大唐西域记》卷三中也重点做了辨正,认为以前的汉语翻译“光世音”“观世音”或“观世自在”都是不准确的,正确的译法应为“观自在”。《大唐西域记》在涉及其他国名、地名、人名时,也经常随之出现玄奘自身的注解“讹也”,正如他在“序论”中所言:“然则佛兴西方,法流东国,通译音讹,方言语谬,音讹则义失,语谬则理乖。故曰:‘必也正名乎’,贵无乖谬也。”①玄奘、辩机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第43页。他认为以前的说法不准确,按照梵文正音来看,只有他的说法才是准确的。实质上,这是出于西域语言转译和通过梵文直译所造成的不一致,并非以前的译法都是错误的。②这不仅属于语言学问题,而且对于研究佛教是直接从印度传往中国还是经由西域而传入,有着重要的意义。《大唐西域记》还对中亚与南亚语言的关系进行了记载,如卷一阿耆尼国“文字取则印度,微有增损”③玄奘、辩机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第48页。,屈支国“文字取则印度,粗有改变”④玄奘、辩机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第54页。,跋禄迦国的文字则“同屈支国,语言少异”⑤玄奘、辩机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第66页。,见出当时中亚语言接受南亚语言影响的历史事实。窣利地区“自素叶水城至羯霜那国,地名窣利,人亦谓焉。文字语言,即随称矣。字源简略,本二十余言,转而相生,其流浸广。粗有书记,竖读其文,递相传授,师资无替”⑥玄奘、辩机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第72页。,则是对粟特文的命名来源、字母数量、书写方式、流传途径等的详尽介绍。此外,《大唐西域记》文本用中文写成,属较为典雅的中古汉语,学界已有一系列针对《大唐西域记》的语言学研究的成果问世。除汉文文本外,中国境内也有《大唐西域记》藏译本(清,贡布加)存世。19世纪以来,随着东方学的兴起,《大唐西域记》先后被翻译成多国文字,西文译本主要有法译本(S. Julien,1857—1858年)、俄译本(Klassosky,1862年)、英译本(S. Beal,1884年;T. Watters,1904—1905年)等。在日本,也有堀谦德(1912年)、小野玄妙(1936年)、足立喜六(1942—1943年)、水谷真成(1971年)、野村耀昌(1983年)等多个译本存世。2015年,中印学者合作完成的《大唐西域记》印地语译本出版,为印度学者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总之,《大唐西域记》本身体现出突出的跨语言因素,目前学界对这部文本进行的跨语言研究也已具备深厚基础。
玄奘西行的七世纪,近代民族国家还未形成,所以,《大唐西域记》中“随地称国”,即以居民聚居之地作为形式上的行政单位,每一聚居之地的“国”民基本上都属同一民族。玄奘每到一地,均会留意该地的人种、史地、风俗、宗教、物候等情况,这可以两个跨民族的视角来进行分析。一是当时中国(唐朝)境内诸民族与生活在中亚、南亚、西亚等地区的诸民族之间,也就是中华民族与外族之间。二是中国(唐朝)境内中原民族与边疆少数民族之间。对于前者,《大唐西域记》中所涉及的对中亚民族(大致今中亚五国范畴)的记述非常丰富珍贵,如卷一对窣利地区“昭武九姓”国的记载等。玄奘西行时期,该地区隶属西突厥的统治和控制之下,所以在此意义上,《大唐西域记》也涉及中原农耕民族和域外游牧民族的关系问题。《大唐西域记》所记南亚最详,今印度、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孟加拉国、阿富汗、尼泊尔等,均有详略不一的记载,印度自然最为重要,特别是卷二“印度总述”,对印度的释名、疆域、数量、岁时、邑居、衣饰、馔食、文字、教育、佛教、族姓、兵术、刑法、敬仪、病死、赋税、物产等一一进行专题介绍,再基本按行经次序,对北印度、中印度、东印度、南印度、西印度依次进行记述,它可视为中古印度诸族的一部小型百科全书。对斯里兰卡,则在卷十一以两则传说的形式予以关注,同东晋《法显传》的记载相对照,对研究中国与斯里兰卡的古代文化交往,尤为珍贵。《大唐西域记》对西亚民族亦有涉及,如卷十一所记“波剌斯国”,玄奘虽未涉其地,仍以听闻的形式对波斯的都城、物候、生产方式、物产、习俗、语言、工艺、赋税、宗教等予以详述;再如卷十二所记“汉日天种”传说,也以文学的形式还原了中古期中原民族与波斯民族的文化交往关系,并已被探险家斯坦因的考古探险活动所证实。《大唐西域记》对于近东和欧洲也有记载,如卷十一记“拂懔国”,为中古波斯语、粟特语From、Hrum和Porum之音译,均为Rum(罗马)之讹音,即东罗马帝国。此外,比较文学研究不一定要跨国界,对于多民族国家,“凡是不同民族的文学的比较研究都应归入比较文学”①杨周翰:《镜子和七巧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70页。,这就是后一个跨民族视角。的确,对于单一民族国家来说,比较文学仅指涉本民族与域外民族之间的文学和文化关系,但对于像中国、印度这样的多民族国家来说,比较文学的跨民族研究还应体现于同一国境之内的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学和文化关系。在此意义上,《大唐西域记》又是一部典型范本,它对中国境内民族(中原汉民族和边疆少数民族,含新疆、甘肃和西藏等)的记载详致且真实,成为研究七世纪及以前汉民族和少数民族关系的珍贵文献,如卷十二对养蚕丝织技术如何传入瞿萨旦那国(今新疆和田)以传说的形式进行了记载,同卷“朅盘陁国”所记“汉日天种”传说则是内地汉族与边疆塔吉克族之间文化交往的体现。
二
《大唐西域记》符合比较文学的典型特征,自然,也适用于运用比较文学的视野和方法对其进行研究。这不但有助于拓宽《大唐西域记》的研究视野,丰富和更新其研究路径,也有助于更好地发掘其深邃意蕴,突显其学术价值。
影响研究,是比较文学最为传统的研究范式,主要以一国文学对另一国文学的影响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对此范式予以适当拓宽,可从纵横两个向度对《大唐西域记》进行影响研究。纵向上,《大唐西域记》既有对六朝文学(文体、叙事模式等)的继承和创新,又对后世文学(《玄怪录》《续玄怪录》《酉阳杂俎》《朝野佥载》《独异志》《大唐新语》《西游记》《聊斋志异》等)产生或显或隐的影响,后者在原型、题材、情节等方面曾对前者进行直接借用或稍加改编,值得认真予以发掘、整理和研究,如对于《大唐西域记》与《西游记》,胡适先生曾考证二者之间“有点小关系”②胡适:《西游记考证》,见《中国章回小说考证》,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21页。,认为本为历史真实的玄奘取经故事,经过《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这一重要的中介(“西游记的祖宗”),到明时终于演变成百回本《西游记》。薛克翘先生则在此基础上,对两部文本间存在的若干处间接影响进行了考辨③薛克翘:《〈西域记〉与〈西游记〉》,《南亚研究》1994年第4期。。横向上,一方面,作为中国文学文本,《大唐西域记》含有诸多异域文学特别是南亚文学因素,成为研究七世纪及以前中国文学与异域文学互动交流关系的典型范本,如季羡林先生认为《大唐西域记》中记载的佛本生故事影响了中国月兔传说的产生。他认为,“印度文学传入中国应该追到远古的时代去。那时候的所谓文学只是口头文学,还没有写成书籍,内容主要是寓言和神话。从公元前1000多年的《梨俱吠陀》起,印度人就相信,月亮里面有兔子……”,并以梵文的词汇为证,阐明中国的月中有兔传说正是来源于印度的月兔传说,而传播的途径则包括《大唐西域记》的记载,“唐朝的和尚玄奘还在印度婆罗痆斯国(今贝拿勒斯)看到一个三兽窣堵波,是纪念兔王梵身供养天帝释的”①季羡林:《印度文学在中国》,《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第121—122页。学界对这一观点存在争议,如钟敬文、叶舒宪等。。另一方面,这些异域文学因素(如诸多异域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又以中国文学为中介对整个东亚文学产生深远影响,如日本平安时代末期的说话集《今昔物语集》,大正时期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和近代作家井上靖的思想和创作,朝鲜王朝中期文人许筠的《南宫先生传》等,都曾深受《大唐西域记》的影响。一个具体的例子是,卷七所记载的“烈士池”故事,这个本源于印度民间的传说,经《大唐西域记》传播至中国,又传播至日本、朝鲜,形成了东亚文化圈的一个独特题材,从中可梳理出“印度→中国→日本、朝鲜”这一清晰的传播脉络,传播期间也发生了一些改编和变异,成为贯通四国文学和南亚、东亚两大文化圈的典型范例。此外,《大唐西域记》中所记载的诸多故事,或由故事的叙述者玄奘亲历,或原本在故事的发生地口耳相传,经玄奘亲闻后,再经《大唐西域记》以文本的形式留存下来,先在中国,后在整个东亚文化圈内进行传播。从传播的方式上看,“这些印度流传的佛教故事进入中国为人所知,通过的是文本经典传译之外的另一条途径:记录口述的途径”②陈引驰:《佛教文学》,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年,第60页。,较之于传统的影响和传播途径,这是一种值得关注的新的有益补充。陈引驰在《中古文学与佛教》中单辟一节《中印文化交流之口语途径》,对佛教故事经口传方式传入中土进行了梳理,并着重强调了《大唐西域记》的作用:“以现存文献而言,唐代高僧玄奘的《大唐西域记》自属第一等之列,记录西行求法过程中口传叙事最为丰赡的。”③陈引驰:《中古文学与佛教》,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411页。
平行研究,也是一种传统的比较文学研究方法,旨在对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民族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异同比较。如何认识和把握比较对象之间的可比性,成为比较文学平行研究的关键问题。“可比性是一种内在的价值”④陈惇、孙景尧、谢天振主编:《比较文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58页。,对这种内在价值的发掘和研究,成为平行研究的主要目标。宗教文学(佛教文学)是《大唐西域记》的主要文学属性,与《大唐西域记》最具可比性、适合进行平行比较研究的当属基督教文学和道教文学。钱锺书先生曾在《管锥编》中对《大唐西域记》卷七所记载的“烈士池”故事之主题与道教和基督教进行对比:“扑杀儿子,以试道念坚否,则葛洪书早有……西方中世纪苦行僧侣试其徒,亦或命之抛所生呱呱赤子于深沼中。”⑤钱锺书:《管锥编》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655页。《旧约》中亚伯拉罕燔祭献子,同样是类似的主题表现。英国学者Samuel Beal 在翻译《大唐西域记》的过程中,也曾将其中的几个具体故事与西方基督教文学进行比较,同样也曾将卷七中所记载的“烈士”经受魔娆这一情节与《新约》中基督布道前经受魔鬼诱惑这一事件进行比较。若从僧传文学视角出发,《大唐西域记》还适合用来与西方使徒文学进行平行比较:就文本本身而言,一为求取佛教真知而践行丝路的真实记录,一为播撒基督信仰而四方奔走的精彩图绘,二者之间最为共通的,是它们的作者笃求信仰、勇于开拓、锲而不舍、百折不挠的精神,这正是通过平行研究所体现出的“内在的价值”。以上是横向对比的情况,若同样对平行研究的范畴进行适度拓宽,将本国作品一并纳入,可与《大唐西域记》进行纵向比较的作品众多,视角更为多元。如将东晋《法显传》与《大唐西域记》进行对比:前者较为简略质朴,后者相对丰富详赡;前者纪实性、情感性兼具,后者纪实性强、情感表现较为隐晦;前者作于印度佛教的兴盛期,后者作于印度佛教已呈衰落的时期;将二者对于佛陀生平、佛典结集、大小乘的分布等信息记载进行比较对照,更有助于理顺七世纪之前印度佛教史发展的线索,辨清一些争议性问题。将《大唐西域记》与此后的义净所作《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进行对比,印度佛教史、中印文化交流史的线索会更加清晰,如《大唐西域记》和《南海寄归内法传》都对印度那烂陀寺进行了详细描述,这二者描述的结合,便几乎是七世纪时这座印度最大学术中心的全貌;对于印度各方面的总体介绍,《大唐西域记》更为全面、系统,文学性也更强,但《南海寄归内法传》在若干领域的记载或评价更为专业和冷静,如对于“印度”之定名的真正原因,对于七世纪印度佛教戒律、印度医药的实际状况,《南海寄归内法传》的记载都更为精审。此外,《大唐西域记》与慧超所作《往五天竺国行传》的可比性,曾经受到韩国学者林基中的关注研究,他分别以叙事式旅行记和抒情式旅行记来定位这两部作品,并就两部作品在叙事文学中的位置进行比较研究。①林基中:《关于〈大唐西域记〉和〈往五天竺国传〉的文学特性》,文英译,《韩国学论文集》1994年第2期。
形象学研究,以一国文学中的异国形象为研究对象,对本土与异域、自我与他者的关系进行互动研究。发源于西方的形象学理论,同样可以为东方文学研究提供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和切入角度,《大唐西域记》研究便属此列。《大唐西域记》属于“东方人看东方”,并不适宜于比较文学形象学的“意识形态——乌托邦”模式,但恰由于此,实现了对“西方人看东方”或“东方人看西方”时固有之二元对立观念的解构,非常适宜作为东方民族彼此之间进行形象学研究的范本。《大唐西域记》中的印度形象研究,就是对七世纪及以前中印文化关系的一种形象化、立体化描述。一方面,它对于印度史地、政治、风俗、物候的描述是相对准确和符合当时印度历史文化现实的,对于认识印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它对于印度佛教人物形象的描述,则亦真亦幻,纪实性、虚幻性相间,从中不仅可以梳理出七世纪及以前印度佛教发展史的一般脉络,而且可以见出玄奘这个形象塑造者的主体情感倾向,如对于佛陀,除本生故事外,《大唐西域记》中对其一生的活动记载得颇为详细,从出生、出家、悟道、传道、涅槃,经过整理后可以得出一完整的佛传经历,亦即早期佛传文学的“八相成道”。作品中对佛弟子的着墨也不少,如神通第一的目连,智慧第一的舍利弗,密行第一的罗怙罗,头陀第一的大迦叶波,多闻第一的阿难,等等。其中,卷九对大迦叶波寂灭经过的记载甚为详致,同卷记阿难为止息两国相争打仗而自分己身;卷六所记罗怙罗神迹传说,重点对其品尝乳粥却沉吟长叹,突出其“悲众生福祐渐薄”,感慨“今之淳乳,不及古之淡水”②玄奘、辩机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第554页。,令人唏嘘。《大唐西域记》还记载了诸多印度佛教史上的著名论师,如戒贤、觉贤、胜军、如意、世友、世亲、无著、众贤、提婆、马鸣、龙猛、德慧、童授、马胜、清辩等,或论述其意志之坚定,或着重其法力之高超,或渲染其摧伏外道之精彩,或突显其威仪之自在和雅,既可补印度佛教史之缺,又见出玄奘对佛国诸圣的崇仰。反观作品中的外道,或自诩“学艺多能,恐腹拆裂”故而“腹锢铜鍱”③玄奘、辩机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第810页。,或不抵女色诱惑从而“宴坐入定,心驰外境,栖林则乌鸟嘤啭,临池乃鱼鳖喧声,情散心乱,失神废定”④玄奘、辩机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第704页。,或因谤佛而陷地狱大坑,或以火坑、毒食加害佛陀而终遭失败,既体现佛教与外道斗争之激烈,又见出玄奘对于外道邪说的不齿和对佛门正教的信心。在作品中,玄奘还曾着重称道那些“沉浮事外,逍遥事表,宠辱不惊,声问以远,君王雅尚,莫能屈迹”①玄奘、辩机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第192页。的印度古代知识分子,也曾专门对一沙门拒绝王者之邀时表现出的高蹈之志予以赞叹,“物有所宜,志有所在。幽林薮泽,情之所赏,高堂邃宇,非我攸闻”②玄奘、辩机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第1019页。。这自然是对当时印度知识人的客观写照,却更是玄奘自己心声的流露,这是因为当代形象学研究已将关注重心由传统形象学研究所关注的“他者”转向“自我”,在此意义上,从玄奘笔下的这些古代印度知识分子身上,更多地看到了玄奘自身③玄奘求法归来后曾先后两次拒绝唐太宗让其弃缁还俗、入仕辅佐的劝诱。,这自然是对玄奘研究和《大唐西域记》研究的促进。
变异学研究,是由中国学者创立、近年兴起的比较文学理论,要旨在于对文学作品在跨语际、跨文明的传播交流和相互阐发的过程中呈现出来的变异现象进行研究。作为一部跨文化、跨语言特征鲜明的作品,《大唐西域记》中适宜进行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的主题、题材等也有不少。仍以卷七所载“烈士池”传说为例,这个源于印度民间传说的题材,在不同地域和不同时期,均发生了不小的主题变异。从横向来看,这个“烈士池”传说,在印度仅是单纯的宗教劝诫:为了达到更高深的修行境界,必须弃绝一切贪爱;修行一定要有恒心和毅力,抵抗住各种形式的魔娆,否则终致功亏一篑。该传说到了唐传奇作者和明清小说作家的笔下,却渗透进浓重的道德说教因素:修身需谨慎,勿结交不义之人;持家需勤俭,否则定会荡尽家财、人皆见弃;改过自新,浪子回头金不换,等等。这正是中印之间伦理和宗教两种不同文化传统的形象表现。从纵向来看,“烈士池”传说和后世杜子春故事的创作主旨,在中古时期以宗教劝诫或伦理说教为主,到了芥川龙之介为代表的近现代文人的笔下,却被赋予了崭新的人文内涵,这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背负沉重包袱的传统东方社会向近现代文明的迈进。再如卷三所记载的阿育王太子拘浪拏的故事,在主体情节上同汉译《阿育王传》和《阿育王经》差别不大,但玄奘并未完全被《阿育王传》或《阿育王经》的原故事框架所束缚,而是在叙述中加入了自己的主观改编创造,更为鲜明地突显了继母的阴损歹毒和阿育王的过而能改、爱民如子,最后以大团圆结局结束:原《阿育王传》和《阿育王经》中,太子虽最终沉冤昭雪,但并未双眼复明;部分汉译故事中虽然出现双眼复明这一情节,但太子最终还是死去了。上述变异,正是在不同的文学和文化传统下产生。一方面,它实现了从原历史题材、宗教题材到文学题材这一学科领域的跨越,为这个印度故事提供了阐释的空间,在此意义上,《大唐西域记》的文学价值得以突显;另一方面,它实现了从印度作者到中国作者这一创作主体的转变,经玄奘这个儒释结合的创作主体对故事情节和结局的主观改编,满足了中国读者的审美心理和价值需求。从故事情节上看,《大唐西域记》此处对阿育王过错的刻意淡化和对其贤君形象的有意凸显,可视为对它的第一个潜在读者——唐太宗所进行的委婉劝谏,不应忘记,《大唐西域记》是玄奘奉敕而作。从故事结局上看,作品中玄奘对故事结局所进行的果断处理,善恶有报、先悲后欢、先离后合、始困终亨,这一对“团圆之趣”的追求,更鲜明地体现出儒家文化接受群体的价值期待。
三
《大唐西域记》与比较文学是相互成就的。以比较文学的视野和方法对《大唐西域记》为代表的作品(如《法显传》 《南海寄归内法传》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往五天竺国行传》《唐大和上东征传》等)进行研究,有助于扩展和深化比较文学的学术空间,促进学科发展。具体体现在文学、文化和文明几个层面。
《大唐西域记》具有宗教文学和丝路文学双重定位。《大唐西域记》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之所以以往并未受到重视和研究,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其文学归属和学科属性的模糊和不确定。就文学归属来说,目前对《大唐西域记》的基本认识主要有游记、行记、传记、报告文学、新闻文学、回忆录等。以上归类认识,各有其归类理由和一定程度的合理性,但均有缺憾:或者因视角单一而无法兼顾《大唐西域记》的其他文体性质,或者归类间互有重叠而身份难辨,从而对《大唐西域记》的文学价值造成遮蔽。打开视野和思路,跳出文体认识的局限,从《大唐西域记》深湛的宗教性内涵和多样的文学表现这两方面的有机结合出发,将其归入佛教文学这一大的范畴,是一个较为合适的选择。①参见王汝良:《〈大唐西域记〉的文学归属》,《南亚东南亚研究》2021年第2期。就如姜振昌研究《野草》提供的启示:在诗歌和散文两种文体的“似与不似”交融中更能看清其“艺术特征”。②姜振昌:《“以诗为文”与鲁迅〈野草〉文体的艺术特征》,《鲁迅研究月刊》2021年第4期。就学科属性来说,将这类佛教文学作品归入中国文学、东方文学都有合理性,但针对其跨学科(宗教与文学)、跨文化(中国传统入世文化与印度出世文化)、跨语言(梵文、巴利文、中文等)、跨民族(中印诸民族为主)特征,其最为恰当的学科归属当为比较文学。这样处理,在兼顾《大唐西域记》的跨越性特征、突显其价值的同时,可为数量众多的同类作品找到一个共同的归属,也为比较文学拓展出新的研究空间。同时,《大唐西域记》人文意蕴较为丰富,如伦理观念、生态意识、警示意义、求真精神、理想主义、开放心胸等,将它归入宗教文学,并非是要回归传统的宗教性解读,而是要对其宗教性内涵中有益于当下、有益人的资源进行着重发掘、整理和研究,实现其现代意义和价值。如《大唐西域记》所记载的众多护生故事,从宗教的角度看,无非是佛教众生平等意识和慈悲理念的体现;跳出宗教认识的圈子,以现代生态学视角对这些故事进行解读,便可得到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超前反思和解构。对这些源于宗教传统却富蕴人文启示的珍贵资源进行系统发掘、整理和研究,有助于实现比较文学的学科创新。丝路文学,则是在新丝绸之路研究的大背景下赋予《大唐西域记》的新的文学定位。丝路文学,即丝绸之路文学的简称,是近年日趋热络的一个概念,相应地,丝路文学研究也逐渐成为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但对丝路文学的内涵和外延、具体分类、意义价值和学科归属等,目前的理解仍较为模糊,具体实践过程中也各行其是,并未形成一个有相对凝聚力的学术场域。我们的理解是:丝路文学是以丝绸之路的时空背景为依托,展现丝路景观、表现丝路精神、体现丝路文化交流的中外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具体说来,丝路景观指丝路沿线的史地文化、宗教艺术、风土人情等。丝路精神指在丝路上奔波往返的商人、使者、僧人们所表现出的开拓精神、开放意识和坚韧品格。③参见王汝良:《丝绸之路文学正义》,《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11月11日。显然,丝路文学也是典型的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文学和文化现象,需要一门具备兼容性和开放性特征的学科来吸纳它,比较文学是其最为合适的归属。玄奘是七世纪沙漠丝路和草原丝路的亲践者,虽未经海上航行,却也对南亚次大陆东、西、南三面海岸的著名丝路景观进行了详致地描述。对照以上诸要素,《大唐西域记》属于丝路文学的典范之作;对《大唐西域记》为代表的丝路文学的研究,也必将为比较文学拓展出新的研究空间,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比较文学的研究属于文化交流的范畴”①季羡林:《比较文学与文化交流》,见《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14页。,《大唐西域记》既是客观的文化交流记载,又体现主观的文化认同。作品所客观记载的中国与西域各国的佛教文化交流,中国的桃、梨等传入印度,中国桑蚕丝织技术西传,隋唐时期的粟特社会经济状况,等等,均已成为中外文化关系史研究的重要课题。玄奘自身也是一个成功的文化使者,他与高昌王麴文泰、西突厥可汗、北印度戒日王、东印度拘摩罗王的交往,现代视角下则是一次次颇为精彩的文化外交活动,这些,大多被真实和形象地记载在《大唐西域记》中②玄奘西行时,高昌等西域小国尚未内附,待他返归时,这些地区已归为唐朝的西州,故《大唐西域记》首篇从阿耆尼国记起。但玄奘与高昌王的交往、在其他西域小国的活动情况,均在《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有详尽记载。。总之,玄奘是沟通七世纪东方三大文化圈的和平使者,《大唐西域记》则是中古中国与南亚、中亚、西亚文化关系的珍贵历史记忆,是对前现代中外文化关系史研究的独特文献。然而,经典作品的价值,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减损,反而会在新的时代、新的历史语境下,经过新的阐释,激发出新的更为丰富的意蕴,实现其现实意义。客观来看,当下的“一带一路”建设并非一帆风顺,在与南亚、中亚、西亚等国的合作中均遇到一些困难,其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认同的缺失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每个人都有多种认同,它们可能会互相竞争或彼此强化,如亲缘关系的、职业的、文化的、体制的、地域的、教育的、党派的、意识形态的及其他的认同。……这些广泛的文明认同意味着更深刻地意识到文明之间的差异以及必须保护‘我们’区别于‘他们’的那些特性”③[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108—109页。,美国学者亨廷顿的观点虽饱受争议,但他对于文化认同之重要性的认识却相当深刻和超前。就“一带一路”沿线来说,玄奘求法所行经的七世纪之南亚、中亚和西亚诸国,有一个最为显明的文化认同力量——佛教,这在《大唐西域记》中体现得最为突出。但七世纪以后,伴随伊斯兰教的兴起和扩张,西亚、中亚国家相继脱离佛教信仰,转而接受伊斯兰信仰;即便是在佛教信仰深厚的南亚,也有大量的信众接受伊斯兰教。这样,伊斯兰教、祆教、佛教等信仰交杂共存,不时发生摩擦、冲突甚至战争。在这样的背景下,以中国为主导的“一带一路”倡议难免会遭受一定程度的误解、拒绝甚至敌视。在这方面,《大唐西域记》为代表的西行求法作品可以有所作为,对这些作品中所涉及古代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佛教历史、社会状况进行整理和研究,能够唤醒他们的共同历史记忆;对古代求法僧们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和平出使活动进行研究和推荐,也可以使人们认识到,古代丝绸之路是一条和平之路,现实中的新丝绸之路也未必是威胁,可以放下戒备,积极参与。这样,可以为当下的“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一定的文化认同和情感凝聚作用,实现比较文学研究的现实关怀。
《大唐西域记》本身是玄奘进行文明探异的结晶,也成为东西方学者进行学术交流、文明对话的有效中介。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中的“文明”,是指“具有相同文化传承(包括信仰体系、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的社会共同体”④曹顺庆主编:《比较文学学》,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84页。。在此意义上,玄奘的行迹跨越中国、中亚、西亚、南亚等几大文明区域,《大唐西域记》便是中古期东方文明体系内部之间异质因素沟通与交流的客观结晶。19世纪以来,伴随着东方学的兴起,一批西方学者、探险家相继将《大唐西域记》视为认识东方文明、考察东方文明的重要参考,《大唐西域记》也逐渐成为东西两大文明体系之间进行对话的桥梁。法国学者儒莲(S. Julien)、英国学者比尔(S. Beal)和沃特斯(T. Watters)对《大唐西域记》均有翻译和研究,英籍匈牙利探险家斯坦因(A. Stein)、英国考古学家坎宁安(A. Cunningham)、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 Pelliot)、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P.W. Richthofen)等,在对东方进行实地考察时都曾倚重和借助《大唐西域记》。在对《大唐西域记》的研究过程中,章巽、范祥雍、季羡林、薛克翘、王邦维等中国学者,堀谦德、足立喜六、水谷真成等日本学者,以及塔帕尔(R. Thapar)、古普塔(D.K. Gupta)、乔希(L. Joshi)、高善必(D.D. Kosambi)、马宗达(R.C. Majumdar)、阿里(S.A. Ali)等印度学者,都曾不同程度地学习和借鉴过这些西方学者的成果。应特别指出的是,西方学者对《大唐西域记》注重书斋研究与田野考察相结合,为东方学者更新传统研究思维和研究方法带来了一定的启示,如冯其庸先生曾为确认玄奘东归入境路线,多次进行田野考察,登上帕米尔高原,寻访公主堡方位,亲闻朅盘陀故事,确定玄奘东归山口;后又深入罗布泊、楼兰、白龙堆、玉门关,验证玄奘回归长安的最后路段。近年来,一些现代学者也根据《大唐西域记》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的记载,多次自发组织起重走玄奘之路的考察活动。东方学者在对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进行借鉴的同时,也在努力进行超越,如距离《大唐西域记》的两个现有英译本(译者分别为比尔和沃特斯)问世已有一个多世纪,译本中的一些不当或瑕疵陆续显现,为此,中国学者刘建正在为完成一个新的《大唐西域记》英译本而努力。总之,面对《大唐西域记》这一文明探异活动的结晶,西方的东方学者最早使用科学方法对其进行译介研究和实践应用,中国、日本和印度学者则充分利用语言文化等天然优势将《大唐西域记》研究推向纵深。面对这一共同的研究对象,中外学者的研究将实现资料共享、方法互鉴、视角补充,这也是《大唐西域记》带给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