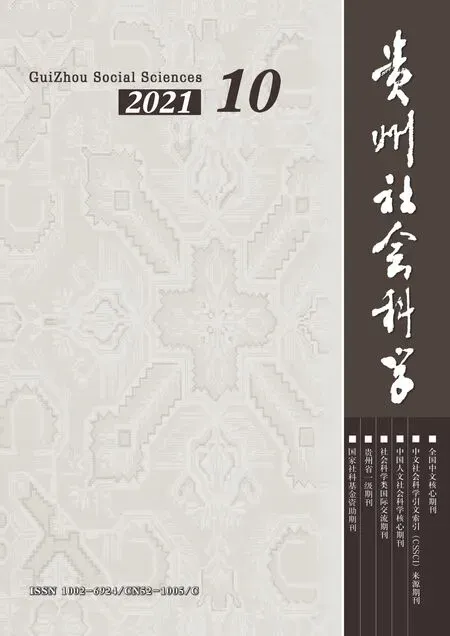汉学视阈下的明清女性诗词“疾病”书写
殷晓燕
(西南民族大学,四川 成都 610041)
明清之际,融“病”入“情”的主题逐渐从女性诗词中的罕见操作,演变为特有的“写作倾向”,女性不再把“生病”作为一种负累并开始享受其带来的生命体验,甚至以此激发创作的灵感。但由此也使私密化的女性身体与情感因诗歌的“公共属性”而走向公开化,使得传统女性以诗词为媒介的个人空间不断得以扩大。
因“疾病”主题的另类化,引起了汉学家的极大研究兴趣,如方秀洁、孙康宜等人,均对此领域有所涉猎。她们通过对“明清妇女著作数据库”的大量援引对比,特别是将相关女性创作的“疾病”诗作与男性创作的同类题材诗歌并举比较,发现同样在对“疾病”进行表达、却存在着性别化的差异。女性诗人利用日常“疾病”所具有的潜力构建出一另类空间,并使其成为一个充满创造性和想象力的存在,打破了人们寻常对“疾病”的厌恶与排斥。
一、援“疾病”入题的女性诗词
至明清之时,女性诗人以井喷式激增方式出现,她们援生活情境入诗词,使人们得以观察此阶段女性的日常。对此现象,方秀洁提出,“研究明清妇女史及女性文化的学者已形成一种共识,即从17世纪起,为数众多的才女闺媛将写诗作为自我再现的一种手段。身为女性,她们努力探寻着在日常生活中抒写自身生命体验的可能,并付诸实践。”[1]21其时,女性写作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文化实践,已与闺秀士人的日常生活相融合。而孙康宜也在研究中发现,至明清之时,女诗人的关注点已从以往传统女性诗词的“闺怨”和“弃妇”题材,转移到了对日常生活的亲身体验,将个人观察到的情景与灵感写入诗歌,无论是刺绣、纺织、缝纫、烹饪,还是养花、抚育子女,所有与生活有关的家务都能入诗,此也成为明清妇女诗词的新现象[2]79-80。在这其中,有一类主题尤为突出,即与“疾病”相关,或是对“病况”的描写。
女性在诗词中对生病经验的描述,属于主观的记录,因个人感觉不同各有差异,在创作诗词时,会不自觉对感觉进行夸大。实际上,“疾病”或“生病”,已经成为一种媒介,使才女们进入到写作的状态,它激发了女性身体健康时所没有的感悟,严重时甚至可能产生绝望等情绪,对于需要激情的创作状态来说,无疑是极为难得的媒介物。方秀洁曾言,“诗歌已成为一种手段,将生病的情境转换为某种可以富有创造性的状态,映射出作者自己的审美观照与精神感悟。”[1]23从此角度而言,无怪乎才女们对待“疾病”似乎并不十分排斥,反而欣然接受,甚至因疾病而导致的死亡,也显得没那么恐惧了。
方秀洁研究所用的文献资源,主要来自于“明清妇女著作”(Ming Qing Women’s Writings)数据库在2006年以前所收录的文献,该数据库可以提供诗题的关键词检索,却并未提供全文检索,只能检出题目中出现“病”或者“疾”等字样的相关词汇,却无法检索内容中涉及对疾病描写的诗文。而在各种女性诗集中约有450首诗的标题含有“病”字,具体分布于几种不同类型的诗词出版物中,其中部分出自于33种女性作者诗集或别集,大部分作品是以“诗”的形式写成的,可见“诗”是最重要的一种写作形式,对女性而言尤其如是;部分出自于8种合刻或汇刻,它们也可以被视为一系列或一组各自独立命名的别集;还有出自于8种大型女性诗歌总集,包括王端淑出版于1667年的《名媛诗纬》、恽珠分别在1831年出版的《国朝闺秀正始集》以及1836年续编完成的《国朝闺秀正始续集》,都是由女性诗人完成编纂的。综合以上信息与数据,可得出一定的结论,“首先,数据库中收录的46种别集中有33种包含了与疾病相关的诗作,这意味着样本中有四分之三的女诗人写过这类诗歌,并在刻印诗集时加以收录。其次,考虑到篇幅大小与编纂时间的不同,男性编选的5部大型女性诗歌总集较少收录有关疾病的诗作:其中3部晚明时期的总集所选篇目相同,都收录了少量明以前女性的诗作,6首左右明代女诗人的作品;清代的两部总集,均只收录了一首此类诗作。”有趣的是,与男性编者相比,女性选家在编纂作品时,对有关以“疾病”为主题的诗歌收录的数量要多一些,如王端淑编纂的《名媛诗纬》,将28首与疾病有关的诗作收录其中;恽珠编辑的《国朝闺秀正始集》及《续集》,收有42首与疾病相关的女性诗作。这种差异的造成,与编者因性别不同而产生的审美趣味异同无疑有关。比如,作为女性编者的恽珠即特别看重女性对于日常闺阁生活经验的再现,“疾病”显然是日常生活的一种。从编选范围来看,男性编者更着眼于时间的维度,而女性编者则关注于共时性与当代性的作品。如王端淑和恽珠编纂的总集,主要是明代和清代的作品,也证明了采用这一题材写诗的女性作者数量明显较之前增多。在袁枚(1716—1798)亲自为女弟子编纂的《随园女弟子诗选》中,收录的与疾病相关的诗作数量是18首,仅次于《正始集》与《名媛诗纬》,证明了18世纪晚期对以此类题材进行写作的兴趣在不断增长,尤其是女性诗人对此类主题的兴趣度。正如方秀洁所说,“这些诗作的反复收录,同样证明了对这一题材的兴趣在总体上得到了增强,也说明女性对疾病的感受成为她们日常生活中重要的生理、心理以及文学经验。”[1]25而这种体验,甚至比其他的成长、闺乐、相思、哀怨、被弃的感觉来得更为直观、更加痛彻心扉。
二、以“疾病”为题的诗歌性别化
在创作以“疾病”为主题的诗歌时,女性的优雅与良好教养,使她们对疾病的具体症状不能做详细描述,只能以一些意思模糊的词语来指称疾病,例如“小病”“新病”“春病”等。一般来说,女性遭受的往往是突发性疾病、或反复发作的慢性病,这多发生在身娇体弱的大家闺秀身上、或与妇科相关的病症,甚至因病毒感染、缠足等都可能引起相应的细菌感染,导致许多女性深受疾病缠身之苦,在文学描写时,自然感同身受、体验有加,更能写出颇具感染力的诗歌作品。根据方秀洁的统计,一些诗题中会有规律地使用带有“病”字的词汇。如“病中:处于患病状态(136首);病起:病人身体感觉良好,可以离开病床——已处于康复阶段;但在极少的情况下,指病人在病中强支病体而起(84首);卧病/病卧:因病卧床(分别为20首和5首);病怀:病中感怀(17首);病后:已经痊愈,与病起相近(10首);小病:病情不甚严重(6首)。”[1]27还有一些词语,在诗题中出现得不是那么频繁,但出现了不止一次,比如,“病久/久病”“病况”“病愈”“病坐”“扶病”“述病”“病危”“病革”等。也有一些词汇仅仅在题目中出现过一次,如“善病”“病魔”等。为了表现“病”的主题,这些语汇最为常见的构成方式就是由“病”与其他字词相结合,包括方位-时间指示词,如中、后、久;描述身体姿态的动词,如起、卧、坐,以及表示所思所感的词,如怀。在方秀洁看来,这些题目会极大地促使读者关注与疾病有关的写作时间结构,如病中、病后。无论是在病中还是病后写诗,“写诗似乎能使她们获得一种不同于常规经验的对时间、情感,以及其他感受方式的认知。换言之,通过写诗,围绕着对疾病的体验,一个暂时脱离社会规范、责任与等级约束的空间向女性敞开。”[1]28在局囿于闺阁的女性有限的认知中,疾病是对她们身体的深入了解,它原本是一个自在的状态,但“疾病”的存在却激发了它的活力,使得才女们不得不正面面对它,并去与它相知相伴,可以说是在女性家庭、伴侣之外所开启的又一认知世界。
与男性相比,女性诗歌对病的描写更为含蓄,而男性则显得较为直接甚至“粗俗”,因为生病不仅限于女性,同样也会发生在男性作家身上。如袁枚的诗集中,就有51首在题目中显示与疾病有关,而“病中”与“病起”则频繁出现,说明是在病中或康复中写作的。男性并不避讳说明自己所患的是何种具体的病,从他们的诗题中所包含的具体疾病的种类,就可以看到诸如腹泻(疴)、疥、痔、病目,或较为常见的病足或足疾。在他们的游历生活中,也常会记录旅途中患病的经历。古代男子为参加科考、增加学识、外地上任等,多需离家远行,交通的不便造成他们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路上,条件的艰苦与恶劣极易造成身体不适,随之疾病就会找上门来;长途跋涉,又令足疾多患,妨碍出行,故引起的忧虑、多思便出现在了诗题之中。袁枚诗歌创作主张“性灵”说,提倡诗歌创作中的真情自然流露,即个人性情、特质与写作的契合,亦即独抒“性灵”。故而他在诗中描述自己的身体状况就不足为奇了。除了前面所提到的几种病症,他还在诗中写了疟、痁、癣、足疮、齿疾、齿痛、腹疾等病症,并经常对这些病症加以详细描述。特别是在其人生的最后几年里,因年老体衰,备受痢症折磨,而他的描写也愈加坦率,甚至显示出他在此方面的幽默“恶”趣味。如他作于81岁时的《病起作》:
道是膳饮多滞留,须用将军破坚阵。果如触犯天屎星,暴下农田千亩粪。
渐渐胸膈得舒展,五浆三馈才能咽。[3]
有趣的是,袁枚竟将治疗过程比作军事行动,并用了农事活动加以比喻,诗中如“屎”、“粪”等词,粗俗不堪,虽然病况描写很真实,但对有教养的女性而言,显然不能作如此之说。女性一般也会说明自己得了何种疾病,但诗题往往用“疾”而非“病”字。这些词语包括“瘵疾”“肺疾”“肝疾”“喘疾”“咯血疾”“咳疾”“奇疾”等,但出乎意料的是,仅有一例提到“足疾”。这与文化传统之中,将女性的缠足视为女性的性感地带有关,既然女子缠足已经被缠脚布层层严实包裹,被具有恋物癖的男性将它当成性感对象,自然属于女性的隐私部位,不被轻易示人。所以,无论男女,很少会写关于缠足的诗。即使有写,“描写和提及的方式都是间接的或是高度艺术化的。”(1)“明清妇女著作数据库”只收录了三首此类诗歌,且均为词作,分别为:储慧(主要生活于19世纪)《少年游·美人足》,见其《哦月楼诗余》(小檀栾室汇刻本);沈彩(生于1752)《望江南·戏咏缠足》二首,见其《春雨楼稿》(小檀栾室汇刻本)。沈彩在其第一首诗中表现了对缠足难得的批判态度,方秀洁对此曾作过讨论,见其著作Herself an Author: Gender, Agency, and Writing in Late Imperial China,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8。
陈蕴莲(约1810-1860年),有一首提及足疾的诗作《足疾未瘳闷极遣怀索外子和》:
如同明镜绝红弘,展卷人疑诵法华。独坐深闺谁是伴,半床诗史数瓶花。[4]
诗人在诗题中提及主题为“足疾”,诗文中却并无涉及到足疾的内容,反而表现出面对疾病的超然态度。原本女性活动的范围就有限,如今又被足疾所束缚,不过陈蕴莲没表现出任何的抑郁难过,反而告诉丈夫,正是由于学识、作诗和单纯的审美愉悦令她获得了超脱。从上可以看出,虽然女性因性别、教养、传统等原因,不会也不愿在诗中以粗鄙的字词表现疾病的状况,但在面对疾病所带来的麻烦时,女性与男性相比却又似乎更为洒脱。对此,方秀洁作如此认知,“由于日常生活中的性别体验不同,男女对疾病体验的再现也因此语境的不同而产生差异。男性经常将疾病视为一种令人沮丧的阻碍,影响了他们对诸多目标的追求以及离家的意愿——不论是为了求学、参加科考、经商,还是寻友访胜。与之相对,女性更多地固守于家庭内部的生活之中,她们经常将患病的体验描述为对另一种时空的体验。”[1]31-32应该说,这既是女性的幸也是她们的不幸,常年固守家庭的常态化,使她们在受到疾病入侵时,生活范围似乎并未受到影响,因此能够比男性更快地接受因疾病带来的不便,甚至有些女性因此获得了较多的充裕时间,并因免受繁琐家务的干扰而沾沾自喜。
三、因“疾病”引起的女性审美化
因疾病带来的虚弱、纤弱、柔弱等特质,与女性气质是十分吻合的。所以,“疾病被解释成一种具有‘女性’特征的符号,在艺术与文学作品之中不断被审美化。”[1]32甚至,女性会将与“疾病”联系在一起的“柔弱”视为与女性特质相对应的表征。从宋代开始,对女性形体的审美逐渐从唐代的丰硕、健美,演变为纤细、娇弱的飘逸,明清文人小说与笔记中的悲剧女主角往往体现出了这一点(2)《红楼梦》中林黛玉纤弱而具才情的美人形象深入人心,冒襄在《影梅庵忆语》中追忆了脱籍为妾、后又因病早亡的董小宛;史震林《西青散记》则记载了身染疟寒的“农家”女诗人贺双卿;沈复《浮生六记》则叙写了自己患病多年的妻子陈芸。蔡九迪(Judith Zeitlin)认为,这一时期日益被过度强调女性性别特征是蒲松龄笔下纤柔女鬼的原型,见“Embodying the Disembodied: Representations of Ghosts and the Feminine”, 载于Writing Wome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d. Kang-ISun Chang and Ellen Widmer ,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是以不少女性将此类女性形象视为理想的目标、模仿的对象,纷相效之[5]。
其实,这并不难理解,女为悦己者容,女性的妆容、发饰的走向与男性的喜恶相关,身材纤纤的弱质女子更能引起男性的怜惜,更易成为男性文人笔下叙写之对象。在《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中收录的一百家词集中,共有50种词集收录了60首与疾病相关的词作(词题中均用了“病”或“疾”字),除此之外,在一些题画词中也再现了疾病的审美化倾向,如《生查子·杨妃病齿图》《减兰·题扶病刺图为黄古渔玉琨悼亡作》及《琐窗寒·题汤德媛寒闺病趣图》等。
比如,方秀洁认为,19世纪中期的吴尚熹即在一首寄调《蝶恋花(闺病)·云鬓蓬松钗欲坠》的词中,将病情作了审美化处理,完成了对疾病合乎情理的带有女性特质的再现。
云鬓蓬松钗欲坠。日过纱窗,独自恹恹睡。一线情丝常似醉。身嫞半拥红鸳被。
脸际销红眉锁翠。无语沉吟,总似多情泪。一缕尖风侵绣被。镜儿偏晓人憔悴。
首先,吴尚熹以《闺病》为题,将疾病体验地点设定在闺阁之中;其次,词题指明作品属于“咏物”的文体,进而将“具有女性化特质的疾病”纳入了“物”的范畴。对于“词”这种文体,方秀洁认为,“虽然词的源起和流变都带有‘男性’特征,但时至晚明,‘女性凝视’已经通过女性对于同性之谊及思慕之情(但未必就是同性恋情)的表达得以确立。”[1]33晚明的陆卿子、徐媛和清代的吴藻皆是明证,她们的词作都呈现出女性视角,表达了与交谊之好的同性的情感,甚至吴藻一度被认为是“同性恋”。吴尚熹的《闺病》,显然并非为某一特定女性所作,也无明显的表达女性情谊之背景,词中女性的身体与其性别特征已被物化,并带有词体所特有的香艳气息。该词用了非常感性的语言对女性化特质疾病进行描写,词中女子因身体不适,表现出了柔弱迷人的倦怠之感,她满面愁苦却妆痕犹在;她渴望有人相伴,却只有明镜,在闺房这个封闭的世界中,从镜中见证着她在情感与身体上的颓败。方秀洁认为,此词并没有对病中人物的主观感受详加描述,而是对病中人物进行了物化,异乎寻常地排除了“个人情感”。“这种‘客观’取向,集中体现了疾病可被感受到的女性化特质,而这一特质又再次被赋予了相思的意味。如果诗化再现可被视为一种“展演艺术”(performative art),这首词正为此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例证。”[1]34
四、对“疾病”体验的女性书写
与男性相比,女性诗人的写作更易于真情流露,对“疾病”主题的描写自然不会“无病呻吟”,而是在经历真实痛苦、虚弱、抑郁甚至厌世的基础之上,书写出患病时的身体或精神状态,所用的写作范式也被方秀洁称为“非虚构性”书写,“她们书写的是真实的而非虚构的生活体验。换言之,与其说将疾病当作一种修辞意象,不如说借助描述模仿性元素,这些诗留下了个人经历的轨迹,尽管对疾病性质的表达受制于妇仪和文学再现所要求的婉转用词与结构方式。”[1]34
在疾病主题的表达上,性别仿佛失去了差异,男性诗人也罕见地采用了非虚构式写法,和对政治的委婉以及“男扮女装”式表达完全不同。疾病主题的诗歌也成为衡量道德的标尺,它会使诗人在患病之际反映出最真实的心声。如杜甫关于“疾病”主题的诗歌就非常多,宋代文人方回曾在其编选点评的律诗选集《瀛奎律髓》中,把杜甫以“疾病”为主题的诗歌单独列出。首先选录的是杜甫的两首《老病》与《耳聋》诗。虽然杜甫诗歌以包罗万象而著称,但其描写疾病的诗歌却大都真实地记录了他病中飘泊、异地而居,病痛与衰老使他难以实现自己的雄心斗志。明代文人江盈科曾这样评价道:“杜少陵是固穷之士,平生无大得意事,中间兵戈乱离,饥寒老病,皆其实历,而所阅苦楚,都于诗中写出。”[6]方回在为杜甫此类“疾病”律诗作序时则说:“疾病呻吟之人所必有也,白乐天有云:‘刘公干卧病瘴浦,谢康乐卧病临川,咸有篇章。’盖娱忧纾怨,是以见士君子之操焉。”[7]根据统计,杜甫以“疾病”为主题的诗歌数量颇为丰硕,统其流亡飘泊、艰难困苦的一生,他共创作了167首疾病诗,这些诗中出现了种种与疾病相关的词语,皆带有“疾”“病”等字眼,例如齿疾、老病、老疾、贫疾;肺病、病肺、消渴、病渴;风病、耳聋、病脚、心弱等等,从身体不同部位充分展现了诗人身体羸弱并遭遇疾病缠身不胜唏嘘的状况。就是在这种病多体虚的情况之下,诗人依然喊出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呐喊,显现出一个充满爱国热情的知识分子的道德形象。
在西方汉学家看来,中国的诗学传统中有“非虚构性”的表征,宇文所安通过他的专著《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TraditionalChinesePoetryandPoetics),以中西学的对比研究,提出他的中国诗学有“非虚构性”传统观点,他说:“在中国的诗学传统中,诗歌通常会被认为是‘非虚构性’(Nonfictional)的,它的叙述则被认为是真实的,否则以隐喻式的解读方式是无法发现其意义的。”[8]34为证明其说,宇文所安把杜甫的诗歌《旅夜书怀》与英国诗人华兹华斯的诗歌《在西敏寺桥上》进行了文本分析,并提出,虽然《在西敏桥上》有具体的时间(1802年9月3日)、地点在西敏寺桥头来写伦敦,涵盖了伦敦的船舶、剧院、高塔、教堂等,但宇文所安依然认为,诗中具体的指向具有超时空性的,它并非指向具体的伦敦,也非让人们关注具体的情景,而应引向词语的言外之意;细读杜甫的《旅夜书怀》:“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宇文所安认为,该诗中描写的景物实与诗人心理之间有一种微妙的联系,这种联系并非指向现实世界之外,也非抽象概念和意义的表达。据此他总结出此诗并非“虚构”,“它应是对历史的一种体验,对世界的遭遇并作出解释和反应的人类意识,是一种独特的、事实性的描述。”[8]15即使我们排除掉宇文所安对两首诗情与景的分析,杜甫在诗中提到了“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再联系中国诗歌中的借景抒情、情景交融的书写传统,“老病”的描述实已反映出杜甫对自身情况的真实反映。
与杜甫、袁枚等男性诗人直接以与“疾病”名词点出生病的状况不同,女性对疾病的体验则显得诗意得多,更多了些婉曲、料峭之意,似在饱受病痛折磨的体验中更能令人怜惜。因她们往往不直接说出疾病的名称,不对疾病的状况进行描述,既不敢如杜甫般直言“疟病餐巴水,疮痍老蜀都。”(《哭台州郑司户苏少监》);也不似他所写“为吾谢贾公,病肺卧江沱。”(《别唐十五诫,因寄礼部贾侍郎》)之直接。在对“疾病”的描写中,杜甫病称、病症、病况以及引起的体衰、乏力等影响都加以陈述,如类似“高秋苏肺气,白发自能梳。药饵憎加减,门庭闷扫除。”(《秋清》)诸如此类还有很多,毕竟杜甫诗集中共有一百多首与疾病有关的诗歌。
而女性诗人对病症的书写范式则是这样的,如清代才女严永华《秋夜病怀》:
莲漏沉沉夜色阑,金炉香烬药烟残。经年善病腰围减,宽尽罗衣不耐寒。
对所患何病只字未提,但“药”“病”“减”“不耐”等字已经隐喻指向,由于病症所造成的消瘦,令女子在漫漫长夜中,更加不耐寒冷以致无法入睡,加重了身体的敏锐感官,令其情绪亦加低落。其他才女所写的类似诗句:
“已拼病骨争花瘦。”(杨蕴辉《春夜病中作》)
“瘦骨支离新病后,单衣冷薄嫩寒初。”(杨蕴辉《秋窗病起有感》)
“愁中病骨恐难苏。”(李源《病》)
“拼将瘦骨寒。”(单氏《月夜病中偶成》)
“骨瘦凉先透。”(姚静芬《早秋病起》)
可见,在对病情的描写上,女性更倾向于用“病”“瘦”“寒”“不耐”等抽象化的词语来指代感官体验,而非对具体病症进行描写。此既出于女性性别本身的矜持,又与女性含蓄、内敛的性情有关。虽然用一种更为写实的手法,去描写其他的感官体验的尝试较为少见,但在晚清之时却出现了更多以书写疾病为主题的个人体诗歌,方秀洁认为,这种变化,可能与文学及社会领域发生的更广泛的话语发展有关,还需要做进一步更深入的讨论[1]36。
晚清多产的女诗人以及维新人士薛绍徽(1866—1911),写于1897年的诗歌《海病》,记录了她乘坐海船从福州前往上海的航程:
乘舟出沧海,昼夜心轣辘。热血触肺肝,如转千钧轴。委顿复瞑眩,拥衾作蜷伏。有时坠枕惊,乡梦未由熟。有时喷珠玑,淋漓泻飞瀑。口梗舌将枯,禁方学辟谷。乃知行路难,欲作歧途哭。入江风力定,侵晨起栉沐。日影映船舷,江南烟绿树。
晚清之时,女性乘船出行已经不是新鲜事了,许多闺秀都曾随着丈夫、儿子或父亲,去各地赴任。所以,她们经常会留下诗篇记录行程中某些时刻,自然包括旅途中患病的经历与体验。薛绍徽的《海病》,描述了从福州到上海一路海运航程所遭受的煎熬,特别是对于晕船所带来的不适,诸如心悸、眩晕、呕吐等,都详细描述了其中的一些细节。如“有时喷珠玑,淋漓泻飞瀑”等句子所显示的,虽然看上去比明清早期的女性要直白了很多,但依然用诗歌意象指代了那些污秽的部分,这与袁枚在诗中直接说排泄的比喻正好相反,但仍可看出薛绍徽对疾病的诗歌写法,已经偏离了女性诗学的传统,不再模糊、朦胧、隐喻,而是更接近于男性诗学传统。此次航行,虽病得厉害,薛绍徽依然写了近十二首记病诗,在一首《病喘》的长诗中,她试图解释自己病情加重的原因,并记录了发病时的各种症状,但最终还是采取了豁达的态度来对待死亡。
五、因“疾病”书写的生命顿悟
在方秀洁的研究中,她认为对疾病的体验与对疾病体验的记录,其含义会随着女性生命的不同阶段而改变。女性生命的转折来自于出嫁之前、婚后生活与寡居阶段,每一次的改变都是生命中重大的震动。除了生育孩子为身体生理机能造成重塑外,剩下的就是患病能充分体验到身体的变化了。而雅好文学的女性,感官体验更为灵敏,因疾病激发的情绪反应自然较一般女性要深沉得多,更易于在诗歌中有所反映。如庄盘珠所作《病起》一诗:
昼漏每从闲处永,新诗反向病中添。
此乃庄盘珠(1796—1829)在此联中所表达的诗学女性对疾病的态度,缺少了外出求学、游历、入仕经历的女性,患病的体验反而促进了女性诗歌创作能力的增长。对健康的女性来说,疾病是她们人生中不多见的生命体验,患病期间,身体某个部位尖锐的痛楚、酸胀的难受,都令她们有了崭新的感官与情感体验。虽然精神可能萎靡不振,但感官带来的灵感却随之增长,她们有了全新的生命感受,自然就想用诗歌的形式将创意记录下来,诗歌的形成更加自然与水到渠成。如陈蕴莲《病中》:
病魔欲去尚恹恹,书卷纵横尘满奁。开尽好花花未绣,新诗赢得箧中添。
诗中呈现了女子病中无心梳妆,因此错过了美好时光,因病使得刺绣未能完成,但病中却完成了新诗的创作,也许这是患病所带来的值得慰藉的事情。与袁枚的《又病》不同,他在病中是“暂远”诗书,陈蕴莲则是病中完成了诗歌创作。这既与陈蕴莲尚在年轻阶段、袁枚已年老有关,又与疾病给予年轻女子的新奇体验有关。
金逸(1770—1794),袁枚最具才情的女弟子之一,方秀洁认为“她写诗的热情几乎与她缠绵不去的病情一样长久。”[1]45例如,金逸曾在病中为好友郭麐写过一首诗,郭麐为此作诗回赠,其中就有“赖有诗篇能过日,不然病骨奈三年”,可谓金逸人生的真实写照[9]。这恰好也反映出,“由于能够发挥女性艺术与知识才能的途径极其有限,疾病对于提高女性的创造能力的作用不能低估。”[1]45实际上这也正是封建旧时代女性的悲哀,长期囿于闺阁,无论是格局、眼界还是世界均被受限,生命中唯一的另类体验只能来自于“疾病”,反而造就了诗歌创作中的新奇。
对于男性来说,阻碍他们人生发展、扩大其生命范畴的疾病,在女性的病中书写里,却显出某种心灵上的宁静与平和。汪端(1793—1839),在其《初冬病中作》中写道:“年来悟得安心法,习静无如病里闲。”梦月则在其诗《病中咏》中,对女性特质进行了充分的探讨,而这种特质,传统上被认为是和女性的患病状态以及闺阁的空间位置相关的。
不觉指纤嫌尘重,那知肩瘦讶衣长。心虚淡嚼诗书味,室静频闻翰墨香。
琴怪出弦音自古,诗清下笔句多狂。病中滋味得真趣,物外幽闲细细尝。
可以说疾病并未使女诗人堕入情绪的悲伤,也并未因此抑郁不止,反而“咀嚼”着诗书的墨香,将自己从日常生活的琐累中超脱了出来,沉浸到精神的提升中,她从“病中滋味”受到启发,因而收获了“真趣”,当意到深入下笔成诗时,更能提升诗句的意境,得到与琴音相得益彰的“狂言”,这无疑是她患病经历的意外收获,令精神上得到“物外幽闲”的超脱。
在方秀洁看来,即使女性诗人仍生活在现实生活中,但疾病的体验却能将之升华为一种特殊的体验,能够将诗人带离凡俗而进入精神层面,这对女性是一种较大的吸引,故使她们能够坦然面对疾病,甚至有一点点期待存在。如多病的江珠(1736—1795),在患病期间,仍表现出对精神生活的强烈向往,“病力渐能通道力,睡魔时欲敌诗魔”(《病中遣兴》)。当睡魔因病魔之因来袭时,对诗魔的追寻仍是她的精神念力。有趣的是,明清才女们不但没将生病视作一件令人烦恼的事情,反而“把生病视为莫大的福气;因为处处感到自己的虚弱,于是便找到放弃各种家务的藉口。”[2]76正是疾病给了她们以机会,让她们可有多余的时间回到自我世界,甚至为此衍生出诸多创作的灵感。通过生病的生命体验,无论是生理、心理、身体、还是情感,都发生了变化,使得她们对人生、对归途都有了新的感悟,自然会成为她们诗词写作的对象。如一位名为李丽媖的女子就常为自己生病而感到庆幸,曾在诗中写道:“不为读书耽雅趣,那能与病结清欢。”(《晚晴簃诗汇》)孙康宜认为,“把病中读书之乐看成一种‘清欢’,实是明清才女的一大发明。”[2]76
生病对女性来说,还有一个好处即可以暂时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可以短暂地从侍奉长辈、照料夫君、抚育幼儿中解脱,她们终于有一段静静的闲暇时间,可以去思考人生、去体味情感、去感受因病菌入侵身体而产生的异样体验。正如方秀洁所说,一些女性会在生病期间,引发对人世沧桑与存在本质的深思;爱好文学的女性,则会利用这段时间进行阅读、写作和其他富有创造力的智力活动[1]47。这恰好印证了事物具有正反两面的辩证哲学观,同时也让人们意识到,与男性文人相比,“词(笔者按含诗)对于她们,已不仅仅是单纯的情感载体,也是值得用心对待的‘美的形式’。”[10]
综上,疾病主题进入女性文学范畴,并成为她们所喜爱描写的主题,实为女性开创了一个新的空间。从审美客体到生命体验的主体,具有女性气质的疾病,以各种方式在女性诗歌中得到体现。此类主题在女性诗人笔下的盛行,构建了不同的写作样式,同时也为女性在生活与诗学中创建了另一个空间。此空间的构建既是女性生活与创作的结合,也是女性诗学由个人私密情感向公共领域的进一步拓展,扩大了其生命的外延与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