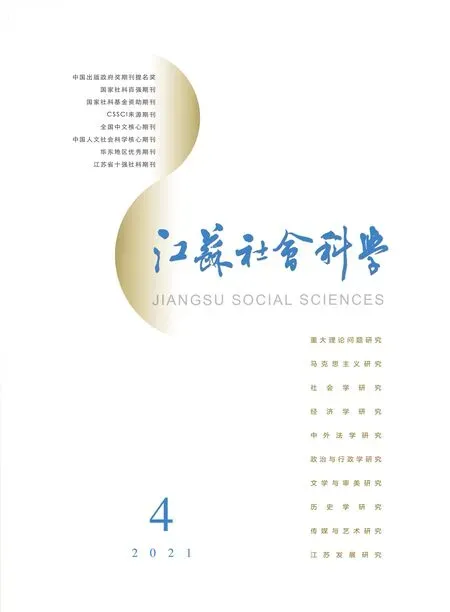论家事司法正义
—— 以家事司法实体正义为视角
刘 敏
内容提要 不同于普通民事司法正义,家事司法正义是一种特殊的司法正义。家事司法正义特殊性的根源在于家事司法价值的特殊性以及家庭法上的家事正义的特殊性。家事司法正义具有特殊的考量因素,它至少包括三个方面内容:在满足当事人多元利益需求基础上依法公正妥善处理家事争议是家事司法正义的基本考量因素;实现未成年子女利益最大化是家事司法正义的首要考量因素;维护家庭和谐是家事司法正义的应有考量因素。在家事司法过程中,为实现家事司法正义,我国有必要利用家事诉讼、家事调解、婚姻家庭咨询、心理咨询和治疗等四种机制处理家事案件。
引 言
在全球家事司法改革的背景下,我国自2010年起也展开了家事司法改革,这一改革首先从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开始,并从局部推向全国[1]早在2010年,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就选择了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等6家基层人民法院和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家事审判方式改革试点。从2015年9月开始,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选取了南宁、柳州等6个市的10个基层法院开展家事审判方式改革试点。2016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开展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决定自2016年6月1日起在全国118家基层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开展为期两年的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试点工作。在改革试点两年期限届满以后,2018年7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总结试点工作的基础上又颁布了《关于进一步深化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意见(试行)》,决定在全国法院系统进一步深化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随着家事司法改革的深入推进,我国未来还将进行家事诉讼制度改革。家事司法改革的终极价值目标是实现家事司法正义,然而,由于家庭法上的正义或曰家事正义不完全等同于普通财产法上的正义[1]婚姻家庭法的价值不完全等同于普通财产法的价值,夏吟兰教授曾对婚姻家庭法的伦理价值做了深入研究。参见夏吟兰:《论婚姻家庭法在民法典体系中的相对独立性》,《法学论坛》2014年第4期。,因此,家事司法正义的考量因素不完全等同于普通民事司法正义或曰普通的财产型诉讼正义的考量因素。进行家事司法改革,首先必须在理论上把握家事司法正义的特殊性,厘清家事司法正义的特殊考量因素。如果不能在理论上正确把握家事司法正义的特殊性并厘清其特殊考量因素,家事司法改革、家事诉讼立法以及家事司法程序运行难免会出现偏差。限于篇幅,本文主要从家事司法实体正义视角研究家事司法正义特殊性根源、家事司法正义的特殊考量因素以及实现家事司法正义的特殊机制,以求教学界同仁。
一、家事司法正义特殊性的根源
不同于普通财产型诉讼,家事司法价值所涉主体具有多元性;不同于普通财产法上的正义价值,家庭法上的家事正义具有特殊性。家事司法价值的特殊性以及家事正义的特殊性决定了家事司法正义的特殊性,质言之,家事司法正义的特殊性的根源在于家事司法价值的特殊性以及家事正义的特殊性。
(一)家事司法价值的特殊性
家事司法正义属于司法价值范畴,作为法律价值的司法价值具有哲学上价值的一般属性。在哲学上,价值是一个主客体之间需要与满足需要的关系范畴,马克思曾经指出:“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06页。价值是指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积极意义。价值具有客观性和主体性,价值的客观性指的是作为外部世界的客体对主体所具有的积极意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价值的主体性指的是价值取决于一定主体对客体的需要。司法价值也具有客观性和主体性。司法价值的客观性,即,不管主体是否意识到司法价值的存在,它们都是客观存在的;司法价值的主体性,即,司法价值取决于主体对司法的需要,取决于司法制度能否满足主体的需要以及满足程度的大小[3]有关法的价值客观性和主体性的详细论述,参见吕世伦、公丕祥主编:《现代理论法学原理》,安徽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5—67页。。在我国,家事司法包括身份关系诉讼、与身份关系有关的财产关系诉讼以及包括未成年子女的抚养、监护、探望等在内的家事非讼程序。对于普通民事司法而言,司法所涉及的利益主体往往就是民事案件当事人本身,法院的裁判只对民事案件当事人发生效力、产生影响。而家事司法涉及的利益主体往往是多元的,这些利益主体包括家事案件当事人、与家事案件相关的未成年子女以及家事案件当事人所在的家庭。家事案件当事人作为家事司法的利益主体没有任何争议,那么,与家事案件相关的未成年子女以及家事案件当事人所在的家庭为什么也是家事司法的利益主体呢?这是因为,虽然未成年子女在涉及未成年子女抚养的离婚诉讼、变更抚养关系诉讼、探望权诉讼等家事司法中不是案件当事人,但判决会对他们的日常生活产生直接的影响。因此,在讨论家事司法价值的时候,不能将未成年子女排除在家事司法的利益主体之外。家庭是由一定范围内的亲属所构成的社会生活单位。法律上的家庭是共同生活的、其成员间互享法定权利、互负法定义务的亲属团体[4]参见杨大文主编:《婚姻家庭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页。。现代家庭具有实现未成年人的初步社会化、提供情感支持和相互陪伴、救助保障等社会功能[5]参见〔美〕戴维·波普诺:《社会学》,李强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13页。。
在家事司法中,法院对离婚案件、抚养案件、赡养案件、继承案件、探望权案件等家事案件的处理对家庭成员产生直接影响。家事案件处理得好,可以维护家庭关系和谐,生活在家庭中的家庭成员感到幸福美满;家事案件处理不好,通过诉讼反而加大了家事案件当事人之间的冲突,给家庭成员带来痛苦、烦恼甚至怨恨。因此,在讨论家事司法价值的时候,不能将案件所涉的家庭排除在家事司法的利益主体之外。可见,与普通民事司法价值只取决于案件当事人的需要不同,家事司法价值不仅取决于家事案件当事人的需要,还取决于案件所涉及的未成年子女的需要和案件所涉家庭的需要。家事司法的利益主体具有多元性,家事司法价值取决于满足多元主体的利益需求以及满足程度的大小。
(二)家事正义的特殊性
家事司法固然具有自身内在的目的性价值,例如,给予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程序保障等。然而,家事司法还具有外在的工具性价值,家事司法的工具性价值在于实现家庭法上的家事正义(access to family justice)。家事正义的特殊性决定了家事司法正义具有特殊性。家事正义的特殊性在于:
第一,家事正义不仅关注财产利益,而且关注情感等非财产利益或曰精神利益。在人类思想史上,关于正义有不同的定义,而正义的核心乃在于每个人获得其应得的东西。古罗马《查士丁尼皇帝钦定法学阶梯》就指出,正义是指给予每个人他应得的部分的这种坚定而恒久的愿望[1]参见〔古罗马〕查士丁尼:《法学总论——法学阶梯》,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5页。。在美国法学家博登海默看来,给予每个人以其应得的东西的意愿乃是正义概念的一个重要的和普遍有效的组成部分。没有这个要素,正义就不可能在社会中盛兴[2]参见〔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64页。。这些正义观主要是从物质层面来探讨正义问题的。就此而言,法律正义指的是人与人之间权利、义务的一种合理分配关系。财产法上的正义关注的是财产权利和义务的合理分配关系。而由于家庭法上当事人的利益需求具有多样性,不但有财产利益需求,还有非财产利益需求,如维护感情和亲情等精神利益需求等,因此,家庭法上的正义不能仅仅理解为财产性权利义务的合理分配关系,它还关注家庭成员之间的亲情等情感利益需要。例如,我国《民法典》第1043 条第2 款规定,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互相关爱;家庭成员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这些内容是《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一般规定的内容,因而成为婚姻家庭法的基本准则。杨立新教授指出,维护亲属亲情,要求亲属之间必须按照亲情的基本需要,确定亲属之间在精神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并将这个准则作为判断身份行为的标准[3]参见杨立新:《家事法》,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11页。。法律是正义的体现,《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对维护亲属间亲情的规定体现了婚姻家庭法对正义追求的特殊性。
第二,家事正义追求的是实质正义。实质正义区别于形式的正义,形式的正义往往与平等联系在一起。美国著名哲学家罗尔斯(John Rawls)指出,如果我们把正义看作一种平等,那么,形式的正义就意味着法律和制度应平等地(即以同样的方式)适用于属于它们所界定的阶层的人[4]参见〔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4页。。然而,由于平等本身难以真正做到,因此,这种形式上的正义可能会导致实质的非正义。诚如英国著名道德哲学家西季维克(Henry Sidgwick)所指出的,法律的执行可能是平等的,但可能是不公正的[5]cf. Henry Sidgwick, The Methods of Ethics, The Jefferson Adams Library of Moral Philosophy, 2011, p.192.。家庭法律领域存在妇女、未成年子女、老年人等特殊群体,这些群体属于社会弱势群体,应当予以特殊保护。我国婚姻家庭法律制度体现了对这些弱势群体的特殊保护,特别是强调对未成年人利益的特殊保护[6]例如,我国《民法典》第1044条规定,收养应当遵循最有利于被收养人的原则,保障被收养人和收养人的合法权益。《民法典》第1084条第3款规定,已满两周岁的子女,父母双方对抚养问题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双方的具体情况,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判决。。这正是家庭法上的家事正义追求实质正义的表现。第三,家事正义不仅关注家庭成员个人利益,而且关注家庭团体利益;不仅关注家庭成员的个人利益,而且关注家庭团体利益,这是家庭法所追求的正义价值区别于普通财产法所追求的正义价值的重要表现。虽然家庭法也将权利义务的合理分配作为正义的内在要求,但家庭法对权利义务的规定不同于普通财产法。家庭法属于身份法的范畴,家庭法调整身份关系以及与身份关系有关的财产关系。家庭法中的身份关系具有浓厚的伦理性,家庭法调整与身份关系有关的财产关系的目的在于实现亲属共同生活的需要和家庭经济职能,因而也具有浓厚的伦理性[1]参见薛宁兰:《婚姻家庭法定位及其伦理内涵》,《江淮论坛》2015年第6期。。基于婚姻家庭的伦理要求,家庭法对权利义务的规定具有以下特殊性:(1)家庭法更强调权利义务的同一性,家庭法上的身份权利往往同时又是义务。例如,对子女的抚养权,实际上也是抚养义务。(2)家庭法制定大量义务性法律规范来规范夫妻和家庭成员的行为。(3)家庭法上的权利义务往往不具有对价性。家庭生活一方面表现为互助、温情、扶助和传承,另一方面表现为义务、约束和责任[2]参见丁慧:《再论中国亲属法的立法价值选择——在〈民法典〉起草和制定的语境下》,《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基于亲属身份关系产生的权利义务不具有对价性,一方履行了义务,并不能向对方主张权利,或者说,一方履行义务并不以对方履行义务为前提。例如,子女履行赡养义务,并不以父母曾履行抚养义务为前提,而只考虑受赡养的父母的需要。家庭法对权利义务分配规定的特殊性,反映了家庭法不像普通财产法那样追求个人正义,最大限度地保护个人利益;家庭法的立法理念是人格独立下的团体主义,在保障个人利益的同时要维护婚姻家庭关系和谐稳定,实现婚姻家庭的功能[3]参见夏吟兰:《论婚姻家庭法在民法典体系中的相对独立性》,《法学论坛》2014年第4期。。现代家庭法在维护个人利益实现个人幸福的同时,还要维护家庭和谐,这是家庭法上正义的要求。
二、家事司法正义的特殊考量因素
家事司法价值和家事正义的特殊性决定了家事司法正义具有特殊的考量因素。家事司法正义的特殊考量因素至少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内容:在满足家事案件当事人多元利益需求基础上依法公正妥善处理当事人之间的家事争议;实现未成年子女利益最大化;维护家庭和谐[4]这里说家事司法正义考量因素至少包括三个方面,因为除了这三个方面考量因素外,家事司法正义还有其他考量因素,例如,对妇女和老年人的合法权益进行特殊保护也是家事司法正义的考量因素。而在对弱势群体的特殊保护中,维护未成年子女利益,实现未成年子女利益最大化显得更为突出。因此,本文在对家事司法正义考量因素的研究中着重考量未成年子女利益最大化。。
(一)在满足家事案件当事人多元利益需求基础上依法公正妥善处理当事人之间的家事争议:家事司法正义的基本考量因素
家事案件是法院处理的家庭成员之间的民事案件,与普通民事案件相比,家事案件具有特殊性。家事案件的特殊性主要有:第一,伦理性。家事纠纷是婚姻家庭法所调整的婚姻关系和家庭关系发生的争议,而婚姻家庭关系是以两性结合和血缘联系而形成的社会关系,它是人类社会最基本、最原始的、充满人伦色彩的社会关系。家事案件当事人即婚姻家庭关系主体不同于商品经济交往中理性的经济人,婚姻家庭关系主体之间不存在商品经济交往中的等价有偿关系,他们之间存在广泛的伦理关系,夫妻恩爱、父慈子孝、兄弟姐妹相亲相爱、尊老爱幼都是相传已久的中国家庭伦理,这些家庭伦理是中国的传统美德,也是现代婚姻家庭法的基本伦理要求。家事案件的发生意味着家事案件的当事人一方有违婚姻家庭法上的伦理要求[5]我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有许多伦理规范,例如: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家庭成员间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夫妻有互相扶养的义务,一方不履行扶养义务时,需要扶养的一方,有要求对方付给扶养费的权利。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有负担能力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对于父母已经死亡或父母无力抚养的未成年孙子女、外孙子女,有抚养的义务;有负担能力的孙子女、外孙子女,对于子女已经死亡或子女无力赡养的祖父母、外祖父母,有赡养的义务。有负担能力的兄、姐,对于父母已经死亡或父母无力抚养的未成年的弟、妹,有扶养的义务;由兄、姐扶养长大的有负担能力的弟、妹,对于缺乏劳动能力又缺乏生活来源的兄、姐,有扶养的义务。。第二,情感性。家事案件的当事人往往是家庭成员,在社会学上,家庭关系是一种初级关系,这种初级关系是个人的、情感的、不容置换的关系,尽管初级关系中的人员不必总是情深义重,但他们的交往是充满情感的交流。在离婚诉讼导致的家庭解体而使儿童失去父或母的情况下,初级关系中个体都会遭受巨大的痛苦[1]参见〔美〕戴维·波普诺:《社会学》,李强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3—194页。。家庭成员之间存在着血缘关系,存在着亲情和感情。在发生争议的基础法律关系背后隐藏着的这些血缘关系、亲情关系是割不断的,家事案件表面上是法律争议,但在法律争议背后存在复杂的情感冲突、情感恩怨。一旦弄清并消除了案件背后的情感冲突,法院对家事案件的处理往往比较顺畅。第三,隐私性。家事案件是家庭内部事件,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家丑不可外扬”的传统,家事案件当事人包括案件所涉及的未成年子女多不愿意让他人知晓其或其所涉的诉讼情况。另外,家事案件中难免涉及个人情感、生理等方面的隐私,这些隐私需要予以保护。第四,人际关系的持续性。家事案件当事人之间往往存在长期的、持续的人际关系,如在赡养案件、扶养案件、抚养案件中,法院判决被告履行赡养义务、扶养义务或者抚养义务后,赡养、扶养、抚养并不是一天就能完成的。在离婚诉讼中,即使婚姻解体了,当事人还会在探望子女等方面存在长期的关系或联系。诚如美国学者所指出的,家庭关系所面对的通常是持续和互相依存的关系,即使在家庭解体的时候也是如此,这些案件中当事人之间仍然存在持续的经济和子女抚养方面的关系[2]参见〔美〕斯蒂芬·B.戈尔德堡、弗兰克·E.A.桑德、南茜·H.罗杰斯、塞拉·伦道夫·科尔:《纠纷解决——谈判、调解和其他机制》,蔡彦敏、曾宇、刘晶晶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69页。。
家事案件的特殊性意味着家事案件当事人具有多元的利益需求,除了身份利益、财产利益之外,家事案件当事人还有保护其隐私等人格利益需要以及希望弥合亲情、修复感情等情感利益需求。家事纠纷的发生意味着家事正义在实现过程中发生了扭曲,家事正义所关注的财产利益以及情感等非财产利益得不到充分实现,家事案件当事人在家庭生活中感受不到家事正义。家事案件当事人诉诸司法,就是希望通过法院对家事纠纷案件的处理,重新实现家事正义。家事正义是家事司法的价值目标,家事司法正义的考量因素应当以家事正义为重要内容。因此,衡量家事司法正义的标准在于法院在满足当事人多元利益需求基础上依法公正妥善处理家事案件。在满足当事人多元利益需求基础上依法公正妥善处理家事案件是家事司法正义的基本考量因素。最高人民法院对家事司法正义的这一基本考量因素予以了认可。2016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开展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要求人民法院改变工作理念,适应家事案件特点,全面保护当事人的身份利益、财产利益、人格利益、安全利益和情感利益,切实满足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
(二)实现未成年子女利益最大化:家事司法正义的首要考量因素
在涉及未成年子女利益的离婚案件、变更抚养关系案件、探望权案件、监护案件等家事案件中,未成年子女不是案件当事人,他们既不是原告或者被告,也不是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或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但这些案件都与未成年子女利益有关。在这些案件中,未成年子女实际上是程序关系人,家事司法不能不关注未成年子女的利益需求。未成年人是国家和社会的未来,保护未成年人就是保护国家和社会的未来;未成年人心智尚未成熟,需要特殊保护、优先保护。在家事司法中,给予未成年子女特殊优先保护,实现未成年子女利益最大化,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内在要求[3]有学者对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为什么符合社会公平正义要求,从社会功利主义、儿童本位主义、博爱主义等方面做了论述。参见何海澜:《善待儿童: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及其在教育、家庭、刑事制度中的运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16年版,第167—171页。。我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贯彻了未成年子女利益最大化原则,例如:《民法典》第1044条规定,收养应当遵循最有利于被收养人的原则,保障被收养人和收养人的合法权益。《民法典》第1084条规定,离婚后,不满两周岁的子女,以由母亲直接抚养为原则;已满两周岁的子女,父母双方对抚养问题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双方的具体情况,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判决。可见,在家事司法中实现未成年子女利益最大化是家事正义的要求。
在家事司法过程中实现未成年子女利益最大化是《儿童权利公约》的要求。《儿童权利公约》第3条规定,关于儿童的一切行为,不论是由公私社会福利机构、法院、行政当局或立法机构执行,均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首要考虑。按照《儿童权利公约》第1条的规定,儿童系指不满18岁的任何人。《儿童权利公约》中的儿童实际上就是我国的未成年人,本文使用“未成年人”替代“儿童”的表述。《儿童权利公约》确立了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或曰未成年人最佳利益原则。1991年12月29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关于批准〈儿童权利公约〉的决定》,《儿童权利公约》于1992年4月2日对我国生效。至此,《儿童权利公约》所确立的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在我国发生法律效力。在涉及未成年人利益的立法、行政、司法活动中,都应坚持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而且必须将实现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作为首要考虑。家事司法涉及未成年子女利益,家事司法应当贯彻未成年子女利益最大化原则,并且将实现未成年子女利益最大化作为首要考虑。唯有如此,才能体现家事正义和家事司法正义的精神。为了实现家事司法正义,我国人民法院在对涉及未成年子女的家事案件进行判决或者调解时,应当将未成年子女利益最大化作为判决或者调解的首要考虑。
何为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儿童权利公约》的监督机构——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在其第62届会议(2013年1月14日至2月1日)上通过的第14号一般性意见中强调,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包含三个层面内容。首先它是一项实质性权利。当审视不同层面的利益时,未成年人有权将他或她的最大利益列为一种首要的评判和考虑,且每当涉及某一未成年人、一组明确或不明确指定的未成年人,或一般未成年人的决定时,都得保障这项权利。其次,它是基本的解释性法律原则。如果一项法律条款可做出两种以上的解释,则应选择最有效实现未成年人最大利益的解释。再次,它是一项行事规则。每当做出一项将会影响到某一具体未成年人、一组明确和不明确指定的未成年人或一般未成年人的决定时,该决定进程就必须包括对此决定可能对所涉未成年人或诸位未成年人所带来(正面或负面)影响的评判。对未成年人最大利益的评判和确定必须具备程序性的保障[1]参见Committee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ren, "General Comment No.14 (2013) on the Right of the Child to Have His or Her Best Interests Taken as a Primary Consideration (art.3, para.1)", 联合国人权机构网,https://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RC%2fC%2fGC%2f14&Lang=en。。为规范法院处理有关未成年人利益家事案件的自由裁量权,一些国家和地区在法律中对家事案件中未成年子女利益最大化的判断标准做出规定。如《美国统一结婚离婚法》第402条规定,判断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的考量因素包括:(1)父母一方或者父母双方有监护子女的意愿;(2)子女对监护人的意愿;(3)子女与父母双方或者一方,与兄弟姐妹或与任何对其最佳利益有重大关联的其他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或影响;(4)子女对家庭、学校、社区的适应性;(5)所有相关人员的身心健康[2]参见〔美〕哈里·D.格劳斯、大卫·D.梅耶:《美国家庭法精要》,陈苇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第138页。。《奥地利普通民法典》对是否符合子女福祉规定了12项判断标准,该法第138条规定,凡与未成年子女有关的事务,特别是关于未成年子女的照护和个人来往方面,均属于子女福祉的范畴,应予以重点考虑,并尽可能予以妥善处理。特别是,在判断子女福祉时,应将下列各项作为重要标准:(1)对子女予以合理的照护,特别是在营养、医疗保健和住房方面予以充分的照顾,并对子女进行耐心细致的教育;(2)培养和塑造子女高尚道德情操,促进和保护子女身心健康;(3)父母对子女的尊重和宽容;(4)促进子女的体质、能力、兴趣和发展机会;(5)充分考虑子女的意见,顾及子女的能力和形成意见的能力;(6)避免违反子女意愿而采取措施或变更已采取的措施,以确保不对子女造成损害;(7)不使子女遭受不法侵害或暴力,不使子女卷入其重要关系人(指在心灵上、心理上对子女产生影响的人)遭受不法侵害或暴力;(8)不使子女遭受不法诱骗、拘禁或其他损害;(9)子女与父母双方、重要关系人间可靠交往,以及子女与这些人的信赖关系;(10)不使子女在心理上产生忠诚冲突和犯罪感;(11)保护子女的权利、请求权和利益;(12)子女、父母和周围其他人的生活条件[1]参见戴永盛译:《奥地利普通民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8—19页。。借鉴域外的立法经验,并汲取我国的司法实践经验,在家事司法中,在判断未成年子女利益最大化的时候,既要考虑未成年子女以往、现在的生活状况、又要考虑未成年子女未来的生活状况;既要考虑父母的职业状况、经济状况、生活状况,又要考虑父母的身心健康状况以及道德品质状况;既要考虑未成年子女与父母的情感关系,又要考虑未成年子女与兄弟姐妹之间的情感关系;既要考虑父母的愿望,更要考虑未成年子女的意愿;既要考虑未成年子女的意愿,又要考虑未成年子女的年龄和心智状况;既要考虑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健康成长,又要考虑未来未成年子女道德、人格等方面的全面发展。总之,人民法院在对涉及未成年子女利益的案件进行判决或者调解时,应当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平衡各种利益,综合考量各种因素,将实现未成年子女利益最大化作为判决或者调解的首要考量因素,从而实现家事司法正义[2]为实现未成年子女利益最大化,在家事司法程序上要求做到以下几点:第一,法院应当将未成年子女作为独立的个体或者说权利主体对待。尽管在家事司法程序中未成年子女不一定是诉讼主体,不是案件当事人,然而,法院仍然应当将案件所涉及的未成年子女作为独立的个体或者说权利主体对待,尊重未成年子女的权利。第二,保障未成年子女的意见表达权。既然未成年子女是独立的个体,未成年子女对于涉及其自身的事项具有一定自治权。具体来说,达到一定年龄和具备一定心智的、有意见表达能力的未成年子女,对于家事司法过程中涉及他的事项有自我决定的权利。未成年子女自己的意见和主张在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判断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在决定涉及未成年子女的事项时,未成年子女有意见表达权,国家要给予未成年子女提供充分发表自己意见的机会,法院要根据未成年子女的年龄智力状况,听取未成年子女的意见。为保障未成年子女的意见表达权,立法上有必要建立未成年子女利益代表人制度、家事调查员制度。第三,法院应当对家事诉讼中父母等成年人所进行的涉及未成年子女利益的诉讼行为进行限制和监督。在未成年子女不是家事案件当事人的情况下,当事人对未成年子女的事项进行处分、安排时,法院应当进行监督,以确保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例如,离婚案件当事人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达成和解协议时,法院应当审查协议是否符合未成年子女利益最大化。。
(三)维护家庭和谐:家事司法正义的应有考量因素
在家庭法的正义目标下,和谐、稳定的家庭关系使得家庭成员的人格发展具有更大空间,个人权利也能得到尊重和保护,最终达到家庭每个成员都幸福[3]参见曹贤信:《亲属法的伦理性及其限度研究》,群众出版社2012年版,第82页。。维护家庭和谐是我国婚姻家庭法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我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在“一般规定”中明确将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作为家庭成员行为的基本准则和婚姻家庭法的立法价值追求。
维护家庭和谐是我国婚姻家庭法的价值取向,是家事正义的基本内容,当然也是我国家事司法的价值追求。在我国家事司法过程中,法院应当贯彻家庭本位原则,着力维护家庭和谐,努力维护和谐的家庭关系。我国法律实务界专家指出,家事审判与一般的民事审判不同,并不是严格遵循审判程序、分清对与错、厘定是与非就可以实现实体正义的。家事审判的核心要义是通过人际关系调整,尽量维持血缘人伦关系和婚姻家庭的和谐稳定[4]参见刘冠华主编:《家事审判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19年版,第74页。。家事司法维护家庭和谐,能够有效实现家事正义。第一,家事司法维护家庭和谐,可以促使家事司法所做出的给付判决或者达成的调解协议能够得到顺利履行,使得权利人真正感受到家事司法正义。第二,家事司法维护家庭和谐包括离异家庭的和谐,可以促使离婚诉讼当事人无论是否判决离婚都能够和谐相处。对于有未成年子女的离婚诉讼而言,即使判决离婚,也能为离婚诉讼当事人双方在日后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探望方面提供良好的合作基础。未成年子女健康成长需要和谐的家庭环境,问题少年往往出现在不和谐的家庭。家事司法维护家庭和谐,可以促使未成年子女健康成长,实现家事司法正义所追求的未成年子女利益最大化。第三,家事司法维护家庭和谐,可以促使老年人老有所养,安度晚年幸福生活,从而实现家事正义。将维护家庭和谐作为家事司法正义的考量因素,也符合我国传统家庭文化的要求。我国自古以来特别强调家庭和谐,素有“家和万事兴”的说法,家和文化是传统家庭文化的精髓,这一家和文化保留至今,并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在域外,许多国家和地区也将家庭和谐、家庭和睦作为家事司法程序的立法目的和家事司法正义的追求。比如,日本的《家事审判法》第1条规定:“本法以个人尊严和男女实质上的平等为基本,以维持家庭和睦和健全亲属共同生活作为宗旨。”
三、家事司法正义的实现机制
家事司法正义考量因素的特殊性决定了家事司法正义的实现机制具有特殊性。家事司法正义的特殊性决定了一元化的诉讼机制有时不能完全实现家事司法正义。在家事司法过程中,为实现家事司法正义,我国有必要利用家事诉讼、家事调解、婚姻家庭咨询、心理咨询和治疗等四种机制处理家事案件。
(一)家事诉讼机制
在家事纠纷发生以后,当事人有权诉诸法院,请求法院公正审判以解决其纠纷。家事案件的特殊性决定了法院对家事案件处理需遵循特殊的诉讼制度[1]这是由程序相称原理决定的,程序的设计与运行应当遵循程序相称原理。所谓程序相称原理就是指程序的设计与运行应当与所处理的案件性质、争议金额、争议事项的重要性、复杂程序等因素相适应,由此使得案件得到妥当处理。参见刘敏:《原理与制度:民事诉讼法修订研究》,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29页。,这一特殊的诉讼制度就是家事诉讼制度。家事诉讼制度在基本原则、程序制度和程序规则等方面都不完全等同于普通的民事诉讼制度。例如,家事诉讼中限制适用辩论主义,有些类型的家事案件甚至要适用职权探知主义;家事诉讼中限制适用审判公开原则;家事诉讼中实行当事人本人到庭原则;在家事诉讼过程中,要实行家事调查员制度、家事案件回访制度、离婚冷静期制度,在未成年子女利益与其法定代理人利益冲突等情况下,要建立和落实未成年子女利益代表人制度。为实现家事司法正义,许多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专门的家事诉讼法,在家事诉讼过程中适用特殊的家事诉讼机制。在我国,实现家事司法正义、家事审判同样需要遵循特殊的家事诉讼制度,适用特殊的家事诉讼机制[2]为实现家事司法正义,我国有必要制定《家事诉讼法》。关于制定《家事诉讼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参见刘敏、陈爱武:《〈中华人民共和国家事诉讼法〉建议稿及立法理由书》,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1—26页。。
(二)家事调解机制
法院对家事案件的调解即家事调解也是实现家事司法正义的途径,甚至是更妥当的途径。这是因为家事案件具有情感性,当事人具有情感需求,家事调解可以减少审判程序的对立和冲突,为当事人双方提供沟通交流的平台,促使当事人消除对立,捐弃前嫌,展望未来,达成和解,满足情感利益需求;家事调解过程也是人际关系调整的过程,家事调解有利于维护当事人之间的亲情;家事案件具有隐私性,当事人有保护隐私权的需求,家事调解可以避免纠纷解决过程和结果向社会公开,从而能够保护当事人隐私权。相对于审判而言,家事调解更有助于促进家庭和谐,这是因为判决只是为了终了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冲突,而调解则可以帮助当事人双方达成协议、实现合作,修复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从而实现家庭和谐。正因为家事调解在实现家事司法正义过程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不同国家和地区都非常重视家事调解,甚至将家事调解作为家事诉讼的前置程序。例如,日本的《家事事件程序法》设有专编规定家事调解程序,对于可进行调解的家事案件,当事人首先应当向家事法院申请调解。在我国,为实现家事司法正义,必须重视发挥家事调解机制的作用。家事调解机制除了包括诉讼程序在内的法院家事调解机制外,还包括独立于诉讼程序的诉前法院家事调解机制。
(三)婚姻家庭咨询机制
婚姻家庭咨询也是实现家事司法正义的重要机制。诉诸法院的家事争议表面上是法律争议,背后有可能是情感冲突、人际关系冲突。实现家事司法正义,不仅要在法律上处理当事人之间的法律争议,还要利用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等知识帮助当事人处理好情感冲突、人际关系冲突。为此,在家事司法过程中,为当事人提供婚姻家庭咨询显得特别重要。婚姻家庭咨询包括对离婚双方当事人的情感咨询、提供夫妻关系调适的咨询与辅导、提供家庭成员人际关系调适的咨询与辅导、帮助当事人排解各种婚姻和家庭危机、提供父母自我教育及亲子教育咨询与辅导等。在域外,不少国家和地区设立了婚姻家庭咨询制度。例如,奥地利《非讼事件程序法》第107条规定,在离婚诉讼中,法官可以为了子女的福祉命令采取相关措施,包括命令夫妻接受家庭咨询、父母咨询或教育上的咨询[1]关于奥地利家事诉讼中离婚咨询的详细内容,参见陶建国:《家事诉讼比较研究——以子女利益保护为主要视角》,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60—64页。。在家事司法过程中为当事人提供婚姻家庭咨询,不一定由法官亲自进行,法官可以委托或者转介有关机构或者个人为当事人提供婚姻家庭咨询。
(四)心理咨询与治疗机制
除了上述机制之外,心理咨询与治疗也是实现家事司法正义的重要机制。美国有学者指出,鉴于家庭进入法院系统的复杂性,法律补救措施在缺乏额外服务时往往无效。家事法院必须提供一系列社会服务,有效解决与家庭相关的社会和心理问题[2]cf. Barbara A. Babb, Judith D. Moran, Caring for Families in Court:An Essential Approach to Family Justice, Routledge,2019, p.27.。也有学者认为,通过召集跨学科的第三方处理儿童和家庭的问题,能最好地实现家事正义[3]cf. Peter Salem, Michael Saini, "A Survey of Beliefs and Priorities About Access to Justice of Family Law: The Search for A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Family Court Review, vol.55, no.1, p.122.。家事争议往往是由当事人之间的人际关系冲突引起的,解决家事争议,需要解决当事人之间的人际关系冲突,而当事人之间人际关系冲突的背后原因有可能是当事人心理上的原因,或者说当事人的心理状态出了问题,不能理性客观地看待自己和客观世界。因此,处理好家事案件,实现家事司法正义,需要利用心理学等专业知识,为当事人提供心理咨询、心理疏导、心理治疗等心理服务,帮助当事人解决心理上的问题。山东省武城县人民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时,在法庭调查阶段要求当事人双方互相列出对方主要优点以及婚后对方让自己感动的事[4]参见陈晓静、吴广辉、阚东广、祖振:《紧扣家事特性,建构“武城模式”》,刘敏主编:《当代中国的家事司法改革——地方实践与经验》,法律出版社2020 年版,第117 页。。这一做法表明,法官实际上在充当心理治疗师进行家庭心理治疗[5]家庭治疗是将治疗的对象从个人转向家庭,用系统的观点看待个人的问题的一种心理治疗。参见徐汉明、盛晓春主编:《家庭治疗——理论与实践》,人民卫生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当然,对当事人进行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并不一定由法官自己亲自进行,法官也可以委托或者转介有关机构和个人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