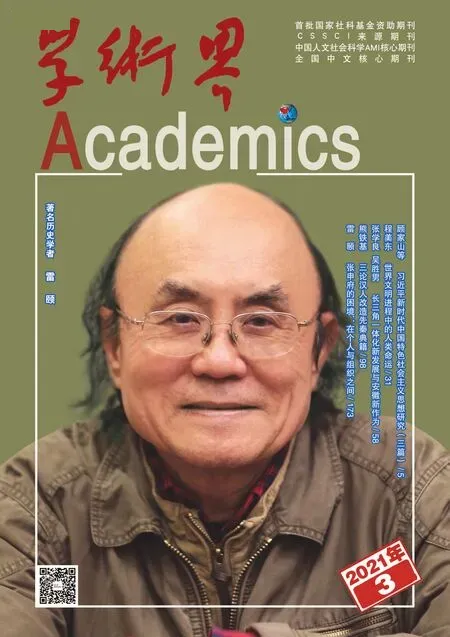张申府的困境:在个人与组织之间
雷 颐
(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 北京 100006)
在大故迭起、风云激荡的中国近现代史上,张申府是位非常独特的人物。在近代中国科学思潮、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引进、传播和发展中,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黄埔军校的筹建、民盟的成立等重大政治活动,但又长期被政治所冷落;他介绍周恩来、朱德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列宁布尔什维克党建原则在中国最早的介绍、宣传者之一,强调无产阶级政党“铁的组织纪律性”,自己却又因一言不合而退出共产党。他是五四知识分子中最早转向共产主义者之一,也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位,因此对他的研究,也会使人们加深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尤其是从“新文化”转向共产主义那一代知识分子思想、心灵的理解。
一、求真、求善与共产主义
张申府(1893—1986,名崧年,以字行)出生在河北献县,其父为清末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民国时期的众议员等职。
1913年,张申府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但他却又对哲学深感兴趣,于是几年间在数学与哲学间“摇摆不定”“变来变去”。1917年毕业后虽留校任数学助教,但依然难舍哲学,而且在哲学上似乎用功更勤。正是这种“文理交修”的背景,影响了他以后的思想发展与学术方向。
这期间,正是新思潮在北大孕育发动之时,身处其中、思想敏锐的张申府深受时代精神震动,常常探讨哲学、政治、社会及人生等方方面面的重大问题。不久,他便成为《新青年》的经常撰稿人之一,其后又任该刊编委。他还曾参与学生启蒙团体“新潮社”的成立活动。在一系列文章中,他首次向国人介绍了罗素等许多西方现代进步思想家。这期间,他与李大钊、陈独秀关系密切,并于1918年和李大钊一同创办了《每周评论》,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风云人物之一。
在张申府的思想中,“求真”的科学与“求善”的道德是内在相通,互相发明的。“科学规律”加深了他对社会主义思想的信念,“社会主义”又使他对“科学”的价值备加推崇。将“真”与“善”统一起来,是他的理想目标。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科学”虽具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新思想的宣传者中只有极少数是研究“科学”的,而张申府便是这极少数之一。作为数学系学生,他具有某种“得天独厚”的优势,立即敏锐地感到世纪初以罗素为代表的分析哲学、数理逻辑学在思想史上蕴含的巨大革命意义,并深为这种哲学的清晰、精密及高度技术性所吸引折服。因此,他并不是空洞地宣传“科学”,而是脚踏实地、终生不辍地译介、研究罗素的思想和分析哲学,为“科学的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作了开拓性工作。
大约在1914年,张申府在北大图书馆偶然读到罗素的《我们的外界知识》一书即被其吸引,由此对罗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罗素的数理逻辑理论更是推崇备至。他在《新青年》上称颂罗素“是现代世界至极伟大的数理哲学家,是于近世在科学思想的发展上开一新时期的一种最高妙的新学〈即数理逻辑(名学),也叫记号逻辑或逻辑斯蒂科Logistic〉很有创发而且集大成的”。〔1〕他认为数理逻辑的产生是哲学“科学化”的重要标志,更证明了哲学及所有人文学科不仅应该,而且能够“科学化”。
在推崇罗素哲学的同时,他又接受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他虽然看到了二者的差异,却不认为有本质的不同,而认为二者因本质相同能够“结合”、互补:“解析是要根据科学的,是反对承认不变的本体的玄学的。唯物也正如此。此二者相通之点。”“解析的第一步工夫固在言辞文字上,但也是要切实如实的。唯物则尤要脚踏实地,实事求是。这又是二者相同的地方,解析之极致可使一切学问统一于一,这一点至少也是唯物之所从同。以此种种,最近世界哲学界里两个最有生气的主潮是可以合于一的;而且合一,乃始两益。而且合一,乃合辩证之理。在理想上,将来的世界哲学实应是一种解析的辩证唯物论。”〔2〕而二者的不同反可“互补”而共臻完善。逻辑解析“偏重于分”,辩证唯物“侧重于全”;“解析末流之弊是割裂破碎”,“辩证唯物之弊则是笼统漠忽”,但由于二者有共同的基础,“解析与唯物,实正相补”。总之,“解析与唯物,这是西方方兴的趋势。两势会归,必然于人类思想的改造,世界状态的变更,均大有所成就,夫岂止于解决些哲学的问题而已?”〔3〕这最后的问题,颇能反映张申府等人对“科学”“科学哲学”如此推崇的最终关注之所在。他们最终关怀的并不是科学、哲学及知识本身,而是人生、社会,是“世界状态的变更”。
张申府认为,科学的“求真”与人类社会的“求善”是统一不可分的,因为“科学是器,器无善恶”,所以需要一种价值观念的引导。他设想以“仁”作为引导“科学法”的价值体系,“今日世界的问题是如何把仁的生活,与科学或与由科学而生的工业,融合在一起。”〔4〕“在吾意,真即是自然,自然即是真:即真即自然,美善视此。”〔5〕“求真”的意义在于“求善”,“求善”的路径在于“求真”,社会主义便是“善”,是“仁的生活”的体现。因此他充满热情的介绍、宣传社会主义学说。思想上开始将共产主义与其他种种社会主义划清界线:“主张社会主义而不主张共产主义只是不要精华罢了”。〔6〕
真、善、仁的统一,是他转向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现实世界贫富悬殊巨大,使他强烈感觉到世界的不公,接受了阶级斗争学说。接受阶级斗争学说,主张社会主义革命就理所当然。在李大钊的直接影响下,他开始转向共产主义,译介了一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章,积极参与实际政治活动。1920年初,他参与了组建中国共产党的筹备活动;在“南陈北李”间奔走串联。同年10月,与李大钊创建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并将张国焘发展进来。
1920年末,他遵照陈独秀的指示来到巴黎,在赴法勤工俭学学生中发展共产党员。在此,他介绍周恩来入党,组成中共旅法小组;不久又与周恩来一起将正在探求新路的朱德发展入党。1924年初春,张申府回国来到广州,参与黄埔军校的筹建,任政治部副主任,蒋介石的英、德文翻译。正是由于张申府的极力推荐,周恩来回国不久便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之职。
张申府认为,主张“劳工”“劳农”翻身革命的社会主义便是“善”与“仁”的体现。1920年,他一篇文章的题目就是《打破现状、才有进步》。这篇短文不到千字,主旨是“大家如果肯去想,能够想出一个比现在好得世界来,更奋力以创造之,他没有不发见的”。他强调这个观念“对于农工劳动,尤其是对的”,因为没有劳动就没有世界,“人的世界一天没劳动,一天就会消灭。既然如此,当然劳动愿意人世怎么样,就应怎么样”。〔7〕两年后,他更强调:“人人都讲高洁,谁与浑身煤黑的人握手?人人都讲高洁,谁去掘煤掏屎?人人都讲高洁,谁作产婆收生?人人都讲高洁,谁向民间去,谁与群众合伙?又哪是民间?又谁是群众?又谁对盗贼娼妓一洒同情之泪?”所以:“不但要想作先觉,更要作先锋,更要作先驱。什么是?就是踏险的马前卒。”〔8〕他引用了罗素新近的一段话:“吾们现在最要紧的是大家都感着非有此一事——革命——不可。无此一事,吾们都无活路。不是吾们无活路,凡好人都无活路。不是凡好人都无活路,凡应当有活路的人都无活路。”他未注明罗素此话典出何处,但无论他的引用是否准确,对罗素的理解是否正确,一战后世界知识界普遍左倾,同情各地革命、尤其是俄国革命却是不争的事实,这一切都加强了张对革命的认同。而且,他比罗素更进一步,“阶级论”色彩更加鲜明,罗素泛指“凡好人”“应当有活路的人”,张申府则具体强调:“最应当有活路的人就是劳农。劳农是社会的基础。没有他们,别人都不能活。但是现在怎样?别人都活的过份了,劳农自己却迫得绝了路!”〔9〕
二、阶级论与“无产阶级专政”
从阶级论出发而认同、投身社会主义革命,必然会面临一个问题:革命后国家的性质、如何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此时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出版未久,他从中找到了答案,并深深折服。《国家与革命》是“阶级论”国家观的奠基之作,将国家定义为“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既然如此,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不仅势所必至,而且理所当然。
1921年张申府在巴黎积极发展共产党组织时,给陈独秀的信中说到法后感到欧洲一时无望,寄希望于东方,“最好的希望是中俄之联合”。他认为中国改造的程序是革命、“开明专制”。他解释说,此处所谓“开明专制”是“劳农专政”,因为“以今日中国之一般知识阶级而言代议政治,讲选举地,纯粹是欺人之谈”,“政治上事切忌客气”,要学习列宁,“能认事实是列宁一大长处”。〔10〕一年后,他在给陈独秀的信中说,自己近来多读了列宁的著作,如《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张根据法文、英文本分别译为《共产主义之孩子病》《左派共产主义——一个孩子病》),称《国家与革命》“最富学理的价值”。这些著作使他“益感动”,尤其是“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为扫清压制者,被压迫者之先锋组织为治者阶级。’”“又说,‘养成些有经验有影响的党的领袖是一件很烦难的事,但无此,无产阶级专政与‘其意志之一致’只是空话。”他进一步明确解释说,自己主张“正式的提倡总还是‘劳农专政’、‘无产阶级专政’”,但又恐此词“徒惹反感”,故曾用“开明专制”只是一种策略。“今日的共产主义者大都晓得无产阶级专政并非无产阶级群众全体的专政,只是少数先锋少数前驱的专政,只是少数有充分阶级自觉的无产者的专政。”〔11〕“寻常战争,不能无先锋;阶级战争又怎能缺了先锋?劳动阶级的这种先锋便是共产党,有了这个机关,乃有了指路的。有了这个机关,本阶级较进步的分子乃可领着全体群众,鼓舞而进。”〔12〕“社会是万恶之成就者。人性是罪恶之教唆者。吾们只有:革社会之命;调理人之性。”〔13〕“我的根本主张是废国灭产,绝婚姻。”“对于社会主义自然要绝对的信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之间,更没有第三者……现在摆在眼前的,已只有共产主义与资本帝国主义两条路。”“吾想创造的少年中国,乃是无产阶级的少年中国。”〔14〕而且,“只由无产阶级的专政,建立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安定才能重得,秩序与进步才能再望。”“这个变更,必须是革命性质的;必须以非宪的手段抓住权力;必须以强力扑灭反革命。”〔15〕
张对列宁国家学说的介绍虽然简略,却非常准确,抓住其核心、实质:革命后打破、废除代议政治、选举政治,“以非宪的手段”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并非由全体无产者来实行,而是由其“前驱”“先锋”,即党来实行;在党组织中,“有经验有影响的党的领袖”作用至关重要。这些文章、通信,是中国最早介绍列宁“阶级论”国家学说、介绍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论述之一。随后几十年,“阶级论”国家观与社会现实互动,在思想界影响遽增,在现代中国最后取代了“契约论”国家观;“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成为中国社会最重要的政治话语。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对现代中国影响之巨大、深刻、久远不必多说,作为首倡者之一,张申府的作用确实非同小可。
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张申府分析、透视问题的主要“透镜”。这种视角,使他完全否定改革,坚决主张革命,极其重视、强调共产党的决定性作用。
1922年,在共产国际指导下,中共提出了与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的观点。张申府对此表示赞同,但又用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共产党的终极目的等提醒说:“但我们也不能不明白告诉大家,而请大家切记:那种办法究竟不是共产党的终极目的,那种办法究竟不是一种手段,而且也不是像无产阶级专政一样的,共产革命的普遍的必然手段。只不过处像现在中国情势之下,不得不取的一种特殊手段。采取这种手段的时候,必须牢牢记住:自己的——必须牢牢记住:自己的正手段,乃是劳动会议式的无产阶级专政,自己的本目的乃是生产共有,分配共管,无阶级、无国、无家、无政府的共产社会。更要不忘为一种行动,与终级目的不同的党派有,结成统一前敌时,必须保持住自己组织的独立!必须得机即把自己的终极目的向大众标示!”〔16〕
1922年5月中旬,由张申府“五四新文化运动”时的“战友”胡适起草,经蔡元培等16人联合签署的题为《我们的政治主张》在胡适主编的《努力周刊》第二期上发表。他们希望军阀从善,由“好人”组成政府便可实现政治清明。所以“主张”认为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应该以“好政府”作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中共领导人、与张申府有“师兼友”关系的李大钊对此表示支持,且是16位联合签署者之一。但张申府却发表《胡适等之政治主张与我们》一文,公开表示坚决反对。开篇第一句就充满斗争的火药味:“胡适蔡元培也公然发表政治主张了!”然后,他从四个方面批驳“好人政府”:“第一,一个人或一阶级的政治主张,总是为其人,其阶级自身的生活利害而发。”胡适等16人多是大学校长、主任、教师、医学博士等,都是“知识阶级的人”,所以他们的政治主张是为了知识阶级。“可是至于一般小民,至于农工,生活如何,则犹难必,不但不能必其利,至少一部分必且要适得其反。根本原因即在士绅与农工生活方法不同。知识阶级历来是资本阶级(靠资本生活的)的附庸,必不敢过于得罪资本阶级,利害如何能与农工小民相容,晓得这个,职业非大学校长、大学教员、医学博士的人,如也要生活得安,还非出来自作主张不可。你们如但能助人呐喊,你们必落得百劫不复!”简言之,不同阶级不可能有共同的政治主张,知识分子只是“皮上之毛”(这是知识分子“皮毛论”最早论述之一,此论后来影响深远),主张体制内改革的精英阶级其最终目的仍是为了本阶级的利益,劳农阶级只有自己起来革命。如果劳农阶级也支持精英阶级的改革主张,结果是本阶级将“百劫不复”。第二,就算胡适等主张的“好政府”真能实现,也不过如美、英、法、日、德的政府一样。然而,“在这等政府之下,劳动阶级(靠自家劳动生活的)养活人而治于人的人,还不是同样的生活不能得安”?第三,胡适主张的“好人”“优秀的人”,其实,今日并无多少“好人”“优秀分子”。第四,中国今天真正的“好人”“优秀分子”就是中国共产党,所以:“我们并不立时主张什么好政府。我们主张即刻要有的只是一个共产党,公开的共产党,强有力的共产党,极有训练的共产党,万众一心的共产党。”通过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才可能有真正的好政府。因为“共产党是劳动阶级的代表,是劳动阶级的先驱,是要使人人都得其所的,是不许一人逾其分的。共产党主张的,因此绝不是少数人的利害。共产党的人必须是劳动阶级或同化于劳动阶级的。必须有死也不改的信仰,必须了然于同阶级人彼此利害的共同,且认除此共同的利害,别无利害。必须对于现世的恶,誓死不相容。这样的人,中国是有的,必须由这样的人,当仁不让,造成强固的共产党,中国事乃有可为”。〔17〕
列宁学说使他认识到,一个强有力的共产党是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而“强有力”的关键又在严格的纪律,这是“今日共产党之真谛”:俄国十月革命之所以成功、德国革命之所以失败,就在于一有强有力的共产党、一无强有力的共产党。而强有力的真谛就在纪律:“有纪律,有共产党;无纪律,无共产党。共产党之所以强在此,共产党之能成功在此。”“有这种纪律才有那样力量,有这种纪律,才能坚苦卓绝,未成功时,既饱尝监禁流放之味;成功以后,又把天灾人祸战胜。”“没有纪律,不能坚固,不能精神贯一,一个共产党形体不坚固,精神不贯一,又岂有能成功之理?”“一个组织,精神不贯一,万万不能强有力,数目虽多,只同散沙。”“真正的共产党是一点不苟且的,是一点不姑息的,不但显然不忠,或违犯纪律的党员,为其所不容。便是一个党员,居重要职位,而作事不得法,或见解不当,也必逐无疑。”“总而言之,纪律是共产党之魂的。失此,共产党是不能活的;不懂得这个的人,不配加入共产党,更不配组织共产党。”他进一步从阶级论说明这种纪律性并非易事:“寻常出身小有产阶级而未改其心习的人,非但不能以此自律,亦且不敢以此律人。这种的人,本来不配组织共产党。就令一旦组织,也只徒冒其名。”〔18〕此话写于中共成立刚满一年之时,但其基本精神、原则却与后来中共日益成熟的“党建理论”相当一致。在这个意义上,他是中国共产党“党建理论”的奠基者之一。
在五四时期科学思潮在中国的传播、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兴起、中国共产党成立过程中,张申府都作出了突出贡献。
三、组织与个人
然而,一个人理论上认识、论述、强调一个政党严格的纪律性,并不意味着实践中能适应、遵守其“铁的纪律性”。1925年初,他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四大”时,因讨论党的纲领和国共合作问题与人争执而负气提出退党。他不反对国共合作,但更强调共产党保持独立性。如前所述,早在1922年他就提醒说:“请大家切记:那种办法究竟不是共产党的终极目的,那种办法究竟不是一种手段”,“只不过处像现在中国情势之下,不得不取的一种特殊手段”。“更要不忘为一种行动,与终级目的不同的党派有,结成统一前敌时,必须保持住自己组织的独立!必须得机即把自己的终极目的向大众标示!”〔19〕
在“四大”会场上他仍坚持此观点,与人激烈争论,但他的主张未得到多数人赞同。几十年后他回忆说自己的主张“招致冷笑,认为幼稚幼想。当时那种轻蔑的态度,使我感到极端难堪”,因此激动地说:“同意我的观点,我就留下来,不同意,我就滚蛋。”最后他拍桌子说:“你们如果执意这样,我就退出这个党!”说完就摔门而去,“摔门而出时周恩来正在门外。周追上他说:你讲得很好,我赞同你的观点,但退党的事还请你慎重”。周劝他不要退党,李大钊、赵世炎等也反复劝说挽留。但他仍执意持“在党外来帮助党工作”的立场,与李、赵说定:“以后在党外仍当与党配合工作,一定永远同党保持友谊关系,以免在党内因意见分歧,发生龃龉,反而多所妨碍。”〔20〕
退出中共之后,他以教学、著述为生,但仍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罗素思想。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张申府更是全身心投入抗战工作,与共产党合作密切。1939年11月末,为进一步团结与联合各党派力量,以沈钧儒、张申府为首的救国会、国社党、职教社、青年党、第三党、乡建派及无党派人士在重庆青年会餐厅聚会,正式成立了“统一建国同志会”。它的成立,为后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奠定了基础。1941年11月,作为民盟前身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基础上公开成立。1942年春,以沈钧儒、张申府为首的救国会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使民盟团结成为“三党三派”的政治联盟。1944年9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张申府被选为中央常委兼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还兼华北总支负责人。
在抗战中,张申府与共产党的关系更加密切,思想上更加接近。抗战结束,国共之争开始,他的话语系统与政治思想明显与共产党基本一致。他认为今日的时代有三个特点:革命的,人民的,科学的。〔21〕他与中共一样,坚决批判“第三条道路”“中间路线”:“其实所谓中间路线(共左国右,自居中间),或第三路线(国一共二,自居第三),只是一个幻想,只是一个欺骗。”“就令想像有一条中间路线,也无人能走。”〔22〕今日的知识分子要“认识时代,跟得上时代,进而推进时代”,要“重视人民,与人民合拍,为人民服务”。“时代的出路,国家的出路,人民的出路,也就是顺应时代、随顺人民、革命前进的出路,就是今日知识分子的出路,当前唯一可能的活路。”〔23〕“过去一切自外于人民的,超乎人民而上之的,当都跑在人民怀里,伏在人民脚下,不但真乐于为人民服务,而且对人民深爱在心。”“不待言,人民就是老百姓,就是一般人或普通人,就是无权无势者,就是被统治者,就是劳苦大众,就是贫贱愚者,就是一切一向被压迫、被剥削、被侵略者,被别人瞧不起者。”〔24〕1948年夏秋,针对共产党在政治、军事上已占优势,部分知识分子“感到恐慌”、怕被“清算”,张申府专门写了《知识分子们,人民在需要你!》一文,呼吁知识分子认清形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在可说,就是还自己的债”,知识分子要“自觉不赖债”,“只要你站得住,挺得起,并不赖债,怕什么清算?”“与其怕人清算,那就诚不如先自己清算清算自己!”〔25〕
然而,在共产党节节胜利、即将发动淮海战役时,张申府却发表《呼吁和平》一文,要求双方停战:“‘兵犹火也’。‘佳兵不祥’。不论什么方面,如果不管眼前人民的切身遭受,而只求一个不尽可知、不必可靠的将来,那不过是一种不仁也不必智的冒险。”“无论如何,作战于一国之内,不管胜也罢,败也罢,遭受死伤的,遭受涂炭牺牲的,既是同一祖宗的子孙,穷兵黩武,总要不得,总不应该。凡真为人民的,就令不得已而事内战,也必反对内战。不管胜败,总必哀矜勿喜。”〔26〕
此文一出,自然受到胜利在望的共产党及民盟左派领导人的强烈批判,张申府被开除出他参与创建的民盟。
这篇文章说明,话语系统和政治思想变得与共产党几乎一样的张申府,在思想核心深处仍相信理性的力量,相信并希望理性使政治由暴力的变成理性的:“力即是理必须变成理即是力。”〔27〕这篇文章虽未明言,却反映出罗素、罗曼·罗兰等人道主义、和平主义对他的深刻影响。关键时刻,这些影响就会表现出来。而且,发表如此重要的文章,他没有考虑到自己作为民盟中央常委兼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还兼华北总支负责人的身份,并未与“组织”商量,认为这只是个人观点与愿望的表达。
许多年后,在回忆1925年中共“四大”时自己一时负气退出自己参与创立的共产党时,张申府自我反省、批判道:“由于小资产阶级的习性未除,不能在党内奋斗争取,竟而错误地决定自己退出,造成一生大错!”〔28〕
确实,张申府身上始终有着浓重的文人气质,即所谓“小资产阶级的习性”。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之一,他最早介绍、宣传列宁的“铁的组织纪律性”,在实践中却难以适应,因“一言不合”而执意退党,表现出一种“合则即,不合则离”的精神特性。也因这种“小资产阶级的习性”,才会认为自己在关键时刻发表一篇政论文章只是代表个人,这是个人的权利,并不代表自己身在其中、且担任相当领导职位的“组织”的观点。
他所面临的个人与组织的矛盾,有深刻的思想渊源。这是一部分深受新文化运动影响的知识分子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并参加共产党后所面临的严重矛盾。从戊戌维新起,在引进中国的新文化、新思想中,个人主义、个性解放是重要内容。
梁启超早就强调:“凡人所以为人者有二大要件:一曰生命,二曰权利。二者缺一,时乃非人。”“今日欲言独立,当先言个人之独立,乃能言全体之独立”,“为我也,利己也,中国古意以为恶德者也。是果恶德乎?”“天下之道德法律,未有不自立而立者也。……故人而无利己之思想者,则必放弃其权利,弛掷其责任,而终至于无以自立。”“盖西国政治之基础在于民权,而民权之巩固由于国民竞争权利寸步不肯稍让。即以人人不拔一毫之心,以自利者利天下。观于此,然后知中国人号称利己心重者,实则非真利己也。苟其真利己,何以他人剥夺己之权利,握制己之生命,而恬然安之,恬然让之,曾不以为意也。”在他们的话语论述中,个人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因此一反中国轻视个人、抹杀个性的传统,大力提倡被视为大逆不道的个人主义,启发人们为做一个真正的人而战斗。他们甚至还从中国古代哲学中为个人主义找出论据,“昔中国杨朱以为我立教,曰:‘人人不拔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吾昔甚疑其言,甚恶其言”,〔29〕而今却认为:“一部分之权利,合之即为全体之权利;一私人之权利思想,积之即为一国家之权利思想。故欲养成此思想,必自个人始。人之皆不肯损一毫,则亦谁复敢撄他人之锋而损其一毫者,故曰天下治矣,非虚言也。”〔30〕
激进的革命派刊物《浙江潮》发表未署作者名的“公私篇”,以现代公权私权分界理论严厉分析、批判中国传统的“公”的观念,强调:“人人不欲私其国,而君主乃得独私其国矣!”“盖私之一念,由天赋而非人为者也。”“人人有自私自利之心,于专制君主则不便甚。”文章充满激情地大声疾呼:“自私自利一念,磅礴郁积于人人之脑灵、之心胸,宁为自由死,必不肯生息于异种人压制之下为之力也。可爱哉私也!”西语曰:‘人生之大患,莫不患于不自助而望人之助我,不自利而望人之利我。’”〔31〕《河南》杂志发表文章认为法国革命是18世纪欧洲启蒙思潮的产物,而启蒙思潮的特色就是理性主义与个人自由主义,并十分干脆地说:“佛郎西革命之精神,一言蔽之曰:重视我之一字,张我之权能于无限尔。易言之曰:个人之自觉尔。”〔32〕
决心“血荐轩辕”的青年鲁迅以西方哲学、文学思想为个人主义张目:“个人一语,入中国未三四年,号称识时之士,务引以为大诟,苟被其谥,与民贼同。意者未遑深知明察,而迷误为害人利己之意也欤?夷考其实,至不然矣……久浴文化,则渐悟人类之尊严;既知自我,则顿识个性之价值;加以往之习惯坠地,崇信荡摇,则自觉之精神,自一转而为极端之主我。且社会民主之倾向,势亦大张,凡个人者,即社会一份子,夷隆实陷,是为指归,使天下人人归于一致,社会之内,荡无高卑。”提出“非物质”“重个人”。蔑视群众,鼓吹“超人”哲学的唯意志论哲学家尼采,骄傲地认为“只有最孤独的人才是最强有力的人”的戏剧家易卜生,都曾经给他们极大的精神力量。他们服膺尼采的学说,推崇易卜生的思想,力图最大程度地振奋人的精神。存在主义哲学的先驱,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的学说也被介绍进来。鲁迅写道:“丹麦哲人契尔开迦尔(即克尔凯郭尔)则愤发疾呼,谓惟发挥个性,为至高之道德,而顾瞻他事,胥无益焉。”〔33〕
《游学译编》1903年发表的“教育泛论”一文,明确提出应把个人主义作为教育的纲领。此文强调“贵我”是从事教育者不可不知的两大主义之一,因为“人人有应得之权利,人人有应得之义务”是“颠扑不破之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者也”,并进一步论证个人能自由行使自己的权利、对自己行为负责才是道德的来源。而且,就权利来源而言,不是“全体”决定、重于“个人”,而是“个人”重于、决定“全体”:“个人之权利,即全体权利之一分子也,一人失其权利,则全体之权利已失一分矣”;如果个人失权互相牵连,结果是“全体之权利,遂荡尽无余矣”。文章还以宗教、学术、社会、国家的发展为例,说明“其所以变迁发达之故,无不基于人类利己之一心”。个人主义的重要一点是个人独立,文章认为这才是教育的宗旨:“人而无独立之精神,是之谓奴隶。任教育者,而不能养成国民独立之精神,是之谓奴隶教育。以教育为己任者,安可不知此意也!”强调个人主义、独立精神是教育的宗旨,必然与中国奉为金科玉律的传统儒家教育思想发生冲突,作者批判说:“古来儒者立说,无不以利己为人道之大戒,此不近人情之言也。剥丧人权,阻碍进步,实为人道之蟊贼,而奉为圭臬,无敢或逾。”〔34〕
五四运动中,“同一营垒”的新文化运动先锋们发生了分裂,其中一部分转向了共产主义,但他们身上,不能不带有强烈的“新文化”印记。
张申府是“新文化”的重要成员,如前所述,深受罗素思想的影响。他在介绍罗素的哲学思想、社会观点时,对罗素的“个人主义”亦极赞赏:“他(罗素,笔者注)最重视个人,个人的自由,小团的自治,与他哲学里的重视个体与主张绝对多元,实不无关。”〔35〕在张申府的思想中,“个人”与“集体”的矛盾一直十分尖锐,无法真正解脱。所以,他认为社会问题的核心是“群与己,少与多”的关系问题,“过顾社会则碍个人,过重小己亦妨社会。”〔36〕张申府的理想社会、理想的个人与组织的关系,是个人与社会、组织的和谐统一。“如何可以自由?自由在个人主义。如何得个人主义?得个人主义在知有人,亦不知有人。知有人,不以己害人。不知有人,不以人碍己。个人主义之极致,即是大同之极致。大同之极致,即是个人主义之极致。故此个人主义为大同个人主义。解群己之纠者,在于是。”〔37〕其实,这“大同个人主义”毕竟只是一种美好而苍白的空想,恰恰反映了中国“新式知识分子”的伦理困境。一方面,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他们无法完全接受西方近代“个人主义”取向;另一方面,他们又无法忍受中国传统的“集体主义”取向。而如何才能实现理想的“大同个人主义”呢?张申府只能寄希望于人类的理性:“解决此问题自宜更循人性而审选群制。巴甫洛夫的制约反射之律,于此实大有助益……换辞来说,人生必须由科学的进展,人性的认识,社会的改制,教育的更新,以达于仁之境。”〔38〕他认为通过诸如条件反射学说便能“科学地”认识人的本性,可以据此作出理性的选择,造成群己和谐的合理社会。如何处理“群己”关系,是他困惑不已、深感痛苦、反复思考的问题。
在1925年执意退党时,不知他是否想起自己三年前写的这段话:“总而言之,纪律是共产党之魂的。失此,共产党是不能活的;不懂得这个的人,不配加入共产党,更不配组织共产党。”“寻常出身小有产阶级而未改其心习的人,非但不能以此自律,亦且不敢以此律人。这种的人,本来不配组织共产党。就令一旦组织,也只徒冒其名。”〔39〕
从个人经历可以看出,这一问题对他有着特殊的意义。作为深受罗素、罗曼·罗兰等人的哲学和社会思想影响的新文化运动先锋之一,他对以个性独立、个性发展为核心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观念一直有着深深的眷恋之情;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译介者、信仰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之一和列宁建党学说的服膺者、宣传者,他对以集体主义为目标的大同境界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又始终怀有深深的崇敬之意。
这种内在的矛盾和紧张,也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内在矛盾和紧张。对加入到中国共产党队伍中的知识分子来说,这种内在的矛盾、冲突更为尖锐、激烈。
注释:
〔1〕〔5〕〔35〕张申府:“罗素”,《新青年》第八卷第二号,1920年10月。
〔2〕〔3〕张申府:“现代哲学的主潮”,《清华周刊》第四十二卷第八期,1934年12月17日。
〔4〕张申府:“所思·一一九”“所思·一一八”,《所思》,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第67、68页。
〔6〕张申府:“各地劳动运动现状”,《晨报》1921年11月10日。
〔7〕张申府:“打破现状,才有进步”,《劳动界》第六册,1920年9月。
〔8〕张申府:“英国共产党与劳动党”,《先驱》第三期,1922年3月。
〔9〕〔11〕张申府:“巴黎通信”,《新青年》第九卷第六号,1922年7月。
〔10〕张申府:“英法共产党——中国改造”,《新青年》第九卷第三号,1921年7月。
〔12〕〔18〕〔39〕张申府:“今日共产党之真谛何在”,《少年》第二号,1922年9月。
〔13〕赤(即张申府,笔者注):“个人不负罪恶责任”,《新青年》第九卷第六号,1922年7月。
〔14〕“编辑室杂记”,《新青年》第九卷第六号。
〔15〕赤:“共产主义之界说”,《新青年》第九卷第六号。
〔16〕〔19〕R(即张申府,笔者注):“中国共产党与其目前政策”,《少年》第二号,1922年9月。
〔17〕张申府:“胡适等之政治主张与我们”,《少年》第三期,1922年10月。
〔20〕〔28〕张申府:《所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第102-103页。张尊超、刘黄:“回忆伯父张申府先生”,《张申府、张岱年研究集刊》(第2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84-385页。
〔21〕张申府:“青年往何处去?”,《天琴》第三、四期,1948年6月15日。
〔22〕〔23〕张申府:“论中国的出路”,《中国建设》第六卷第四期,1948年7月1日。
〔24〕张申府:“知识分子与新的文明”,《中国建设》第六卷第五期,1948年8月1日。
〔25〕张申府:“知识分子们,人民在需要你!”,《北大半月刊》1948年8月5日。
〔26〕张申府:“呼吁和平”,《观察》第五卷第九期,1948年。
〔27〕〔38〕张申府:“续所思·二六”,《所思》,第159页。
〔29〕梁启超:“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清议报》第82、84期,《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第13-14页。
〔30〕梁启超:“新民说”,《新民丛报》第1、3,6、7、8、10、11期,《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第132页。
〔31〕“公私篇”,《浙江潮》第1期,《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第492-496页。
〔32〕旒其:“兴国精神之史曜”,《河南》第4期,《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三卷,第299-301页。
〔33〕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6-54页。
〔34〕“教育泛论”,《游学译编》第9期,《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第400-404页。
〔36〕张申府:“续所思·二六”“续所思·二七”,《所思》,第159、160页。
〔37〕张申府:“所思·二十”,《所思》,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