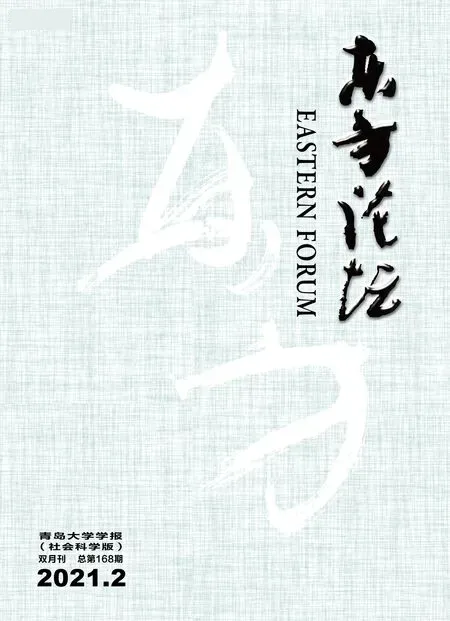怨恨与区隔
——论张资平与无产阶级文学的相遇
徐仲佳
上海财经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443
张资平被郭沫若看作“真正会写小说者”a陶晶孙:《创造三年》,《风雨谈》1944年第9期。。陶晶孙虽然对张资平小说的通俗性不以为然,但也不得不承认,“资平的通俗小说最能深入一般青年”b陶晶孙:《创造社还有几个人》,《一般》第1卷第1期,1944年2月1日。,是当年新文学阵营中爱情小说创作的名家。不过,在此后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叙事中,张资平的地位却并没有显示出他在历史现场中的占位。遍览当下通行的文学史著,没有哪一种将他单列章节进行叙述。c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杰成印书局,1933年)在第五章用了比郭沫若、郁达夫稍多的篇幅来介绍张资平的小说创作(第152—156页),这与之后文学史著的三者定位是不同的。文学史叙事受现实强制性权力文化逻辑的支配。张资平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地位除了受到文学史叙事支配性力量的影响之外,多年文学场域行动主体的怨恨心态也不能忽视。
怨恨是一种由于现代平等观传播所导致的“生存性价值比较的紧张情态”,即一种在体性的把自身与他者加以比较的社会化心理结构。在与他者比较中,比较者感受到的生存性的伤害、生存性的隐忍和生存性的无能感使怨恨得以积累。处于传统与现代、中与西的双重“现代化焦虑”的中国,这种怨恨心态表现得尤为突出。有人甚至认为中国的现代历史就是一部怨恨心态大显现的历史。a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362—364页。当然,这种怨恨心态也不可能不影响到文学史的叙事,换言之,怨恨心态可以看作是中国现代文学史叙事的深层心理动因之一。
我们选择张资平作为文学史叙事中的个案来考察,其原因在于,不仅张资平在历史现场的自我区隔与被区隔均蕴涵着怨恨,而且在其后的文学史叙事中,作为文学史叙事的支配性力量中也不乏怨恨的影子。通过这一个案,我们有可能对文学史的叙事秘密做一揭示,而这种揭示对于我们清醒地认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事有着相当的意义。
一
文学史的叙事权力首先表现为一种分类原则,即以合法叙事主体的评价系统来区隔文学史中出现的作家作品的优劣、地位的高下,或者经典化之,或者妖魔化之,或者使之湮没在史料的烟海中,最终形成一幅与合法叙事主体评价系统相适应的感知图式。中国现代文学史叙事的分类原则与叙事主体的怨恨心态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文学史叙事权力的区隔、分类不可避免地蕴涵着叙事者的怨恨情绪。它常常采取两种价值取向:贬低被比较者的价值,或者提出一种不同于被比较者的价值的价值观。
历史现场的行动主体的怨恨情绪会直接影响到后来的历史叙述。创造社诸君是现代作家中怨恨情绪最突出的一群。这一点在他们的自叙传性(包括自传性)作品中有鲜明的体现。他们常常借助自叙传的叙事发泄怨恨情绪,进行自我区隔。张资平在创造社中的怨恨情绪并不是最浓厚的,但也并不例外。他的自传性的作品主要有《脱了轨道的星球》《资平自传(从黄龙到五色)》《我的创作经过》《曙新期的创造社》等。除此之外,他的小说也常常带有自叙传色彩。这除了指像郁达夫小说中那些比较显明的作家个人的经历(他的一部分小说也可以看作是自叙传小说,如早期的《冲积期化石》《一班冗员的生活》《植树节》、后期的《兵荒》《冰河时代》《新红A字》等)之外,还指他的小说中借人物之口发泄出来的作者对社会的认知,有时甚至是以叙述者面目直接出现的作者对现实社会世界的议论、评价。从他的这些自叙性的叙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张资平被怨恨情绪所支配的自我区隔、分类。
张资平一直自称是一颗“脱了轨道的星球”:“社会在激烈的变动着,革命的潮流也在蓬勃的高涨着。我是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但对于时代和环境,仍然是漠不相关,只在过病态的生活,每天也只在怨天尤人,……(我)是像一颗没有轨道的暗星,完全无目的地,只在天空中乱碰乱撞……”b张资平:《脱了轨道的星球》,上海:现代书局,1931年,第205—206页。这是张资平在他年近四十的时候对自己前期生活的一段回忆,也不妨看作是他对自己一生的评价,因为他对自己之后的生涯的评价依然是“彗星的行踪”。虽然“彗星”已经有了一定的轨道,但是它依然是与其它行星相异。这种自我定位有功成名就之后的自得,但更明显的是与其他作家进行区隔的自觉。张资平把自我区隔的原因归结为“性的苦闷和经济的压迫”a张资平:《脱了轨道的星球》,第206页。。事实上,造成传主在叙事中自我区隔的不是这种苦闷和压迫,而是由此而积累的怨恨。长期的怨恨积累沉淀在传主的内心深处成为他深层价值秩序中不可磨灭的结构性因素,进而形成了叙事主体的认知图式和评价系统。从张资平的自传中,我们看到他经历坎坷:幼年丧母,又无兄弟姊妹可以依恃。他虽然出生在一个“灯火夜深书有味,墨花晨润字生香”的“书香人家”,但是却没有能力像同时代的其他作家例如郭沫若、郁达夫那样自由求学,只能靠自己的努力挣扎出来。虽然他的“知识欲很强,也努力读书,不幸的是因境遇所迫,失掉了学习普通科学的权利。回想起来我当时是何等可怜的一个学生啊!想进五年的完全中学的余裕都没有啊”b张资平:《资平自传(从黄龙到五色)》,上海:第一出版社,1934年,第72页。!因此,他所走过的求学路:公孚当私塾、廖屋岗私塾、广益中西学堂、东山初级师范、广东高等巡警学堂都是所谓的“偏途出身”。这种“偏途出身”肯定不是他自己所愿,更要受到正人君子们的鄙视。就连张资平的堂兄张耀仪、十三伯父都曾经鄙视他不能“循正规出身”,更不要说其他士人的态度了。这种生存性价值比较的体验正是张资平怨恨心态积累的最初动因:生存性的伤害、生存性的隐忍和生存性的无能感这三个怨恨心态形成的必要条件,张资平在20岁之前(考取赴日留学的时候)都体验到了。所以,当他在对自己的这段历史进行叙述时,他内心深处压抑已久的怨恨一定会喷薄而出。这种怨恨心态对于身处现代中国的作家以及后来的文学史家来说并不陌生。例如新青年社诸君在与复古势力进行论争时就拒绝对话与协商:“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c陈独秀:《通信(胡适—陈独秀)》,《新青年》第3卷第3号,1917年5月1日。创造社诸君1921年走上文坛时,也是显示出一副“打架”的态势;1928年的革命文学论争中,更是充塞着横扫一切的暴戾之气;……甚至鲁迅先生在20年后回忆自己进入江南水师学堂时,也还耿耿于正人君子的“奚落”与“排斥”。d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15页
张资平的怨恨直接地表现在他与他所身处的社会世界、其他作家的区隔上。他的自传只涉及到他三十岁以前的经历,所以他的自我区隔更多的是表现在他的小说中,尤其是1928年以后他置身于革命文学与商业大潮中所写的小说中。张资平的怨恨常常表现为通过贬低被比较者的价值来自我区隔。例如,他在《植树节》中通过人物V之口表达了对当时一些“朋友”们的不满:“我身边是没有一个银元的积蓄,由学校领来三分之一五分之一的工资仅仅把一家四五口的生活维持过去。但朋友们说他生活费这样省俭,一定有些积蓄了。他觉得朋友们未免过于自私自利了。因为他们只爱说自己穷,不准其他的人说穷。啊!除非研究无产阶级的社会学者实地的来调查我这一家的生活出去报告后才有人信我的穷吧。算了算了。没有人知我,没有人知道我的穷也算了。我以后不再道穷道苦了。若不会死,我决意用我的精力和体力去挣两个钱,日后妻子也不至于流为乞丐。还是这样决定主意的好,不要再唱高调了。”e张资平:《植树节》,上海:新宇宙书店出版部,1929年,第3—4页。V的朋友的“自私自利”“唱高调”与V的节俭、平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对比不妨看作张资平与现实中某些朋友之间的区隔。不过,此时张资平在小说中的自我区隔还是比较有节制的,他的评价和认知图式与小说主人公的性格、遭际、身份都还比较契合,批判的矛头更多时候也是针对着不平等的社会制度。他把自己想象为一个社会制度的批判者,现存社会世界则被贬低为虚伪、不公、丑恶。所以,在他的以建构新的性道德为主要目的的性爱小说中,他常常使那些服膺着新的性道德的主人公自觉地把自己对爱的追求与社会制度的虚伪、不良对立起来,使他们的这一行为带有强烈的政治意义。a参见徐仲佳:《新道德的描摹与建构——张资平性爱小说新探》,《中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1期。当这些小说中的主人公因为欲爱不得而对阻碍着他们的恋爱的社会世界发泄着怨恨的时候,张资平的影子一定也附在他们身上。
1928年,张资平到了上海。随着生活境遇的变化,张资平开始试图融进革命文学的浪潮中。在1920年代中期,“革命文学”一词包容甚广,不仅有无产阶级文学、也有无政府主义文学和国民革命文学。革命文学论争的一个功绩是使得无产阶级文学成为“革命文学”的主流内涵。张资平是较早受到无产阶级文学观影响的作家之一:“我原是习自然科学的人,中途出家改习文学已经十二分吃力。对于革命理论及普罗列搭利亚文艺理论至1927年春才略略知道。”b张资平:《编后并答辩》,《乐群月刊》第1卷第2期,1928年10月。这段叙述写于1928年,张资平已来到上海,身处无产阶级文学漩涡之中。不过,1927年他便翻译了日本的藤森成吉的《无产阶级文艺论》,连载于《革命军日报》(武汉)。该书(实是全书之绪论)比较简略论及了布哈林、托洛斯基、卢那察尔斯基等的无产阶级文学理论。到上海后,张资平明确地趋向于无产阶级文学,有意识地表示要转变方向:“论我的作品截至一九二六年冬止写《最后的幸福》后就没有再写那一类的作品了。无论从前发表过如何浪漫的作品,只要今后能够转换方向向前进。”c张资平:《编后并答辩》,《乐群月刊》第1卷第2期,1928年10月。他的《柘榴花》(1928)、《青春》(1929)、《长途》(1929)、《明珠与黑炭》(1929)等都是以恋爱来传达革命的理念,是当时常见的“革命+恋爱”叙述模式。恋爱小说本来就是张资平在文学场域中占位的主要资本,新的性道德建构以及对礼教秩序的抨击是他恋爱小说写作实践的功能目标。因此,张资平自称转向之后的这些作品基本上就是在他所熟悉的恋爱叙事基础上黏贴革命故事。当时,进入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大多是借道日本而来,张资平利用自己熟悉日语和日本文化的资本,在这一时期翻译了一些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理论和作品;他创办的乐群书店也出版了很多宣扬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科学书籍;他所编辑的《乐群》杂志也发表了许多“可以冠之以‘普罗文学’”的作品。d颜敏:《在金钱与政治的漩涡中——张资平评传》,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89页。从上述表现来看,张资平在当时风起云涌的革命文学浪潮中有其一席之地。
即使在这样的情形下,张资平的自我区隔意识还是很明显。其原因是在无产阶级文学的浪潮中,张资平并没有真正被容纳进去,他被区隔在普罗文学之外。此时的“革命+恋爱”的小说模式已经发生了变异。早期(张闻天《旅途》,1924)的革命与恋爱的同等地位已经转变为革命对恋爱的支配。因此,他被一些普罗文学家定位为:自然主义的、多产的、多角恋爱的、善于写肉感的、小布尔乔亚的(或者指称他为布尔乔亚的,这有时意指他的稿酬收入特别的多,有时意指他的非革命性或反革命性)小说家。张资平的自我区隔主要表现在对上述这些评价、分类的反驳或解释。他在声明转向的同时也与一些革命文学的倡导者拉开了距离:“有一种人常摆革命文学家的脸孔,而明于责人暗于责己,对于革命理论又没有十分的研究,只爱瞎批评人,这种人名为革命,其实是停顿。”a张资平:《编后并答辩》,《乐群月刊》第1卷第2期,1928年10月。当倡导革命文学的新锐李初梨宣扬“今后写创作,应当是使它成为马克斯主义通俗教科书”时,张资平虽然没有在表面公开质疑,但是他却在内心里感到“似有斟酌的必要”b张资平:《读〈创造社〉》,见史秉慧编:《张资平评传》,上海:现代书局,1932年,第152页。。1929—1930年,随着无产阶级文学的阶级论色彩越来越鲜明,张资平的“转向”小说以及他的文化商人的身份开始逐渐被以左翼文学的倡导者从正统的无产阶级文学中彻底区隔出来。张资平此时的自我区隔可以视为对左翼文学理论家对他进行区隔、分类的一种应激性反应。这种反应最直接的结果是张资平与创造社出版部分道扬镳。在此之后,张资平的自我区隔变得更加激烈,他的评价系统和认知图式变得更加极端。在《天孙之女》(1930)中,他的女主人公甚至这样嘲讽所谓的革命者(丘景山):
算了吧!像你们那样今天写什么同在一条文艺战线,明天说获得了普罗意识,让你写一百年文章也达不到革命成功的目的。……算了吧!不要再去丢丑了!革命的先觉者为革命努力十余年,为革命的牺牲也极大,结果还得了反革命之罪名,你们只写了一二篇似是而非的革命理论文章,讲演了一二回肤浅不堪的文艺理论,便赶上革命先觉者,比革命先觉者更加革命了?我真不敢相信!你还是每天晚上跟我去跳舞场吧。你不是也喜欢玩麻雀吗?我也可以请两个朋友来,凑凑脚天天和你在家里搓麻雀。c张资平:《天孙之女》,上海:文艺书局,1931年,第330—331页。
熟悉这一段历史的人可以敏锐地发现,小说中的这一段人物语言蕴涵着对无产阶级文学倡导者的怨恨。怨恨情绪在论争双方的表达中都不鲜见,问题是,张资平的怨恨放置在小说这一文体中,溢出了必要的文学限度。他让这段话出自一个日本舞女之口,显然是超出了人物的生活逻辑,使之成为作者思想的传声筒。类似的突破文体规范的超表述在张资平这一时期的小说中经常出现。这表明,张资平的怨恨情绪已经扭曲了他的写作行为,其被文坛所遗弃就是必然的。
当然,超出文体规范限度的写作并不足以完全抹杀作家在后来文学史叙事中的有效性,作家作为文学实践主体合法性被剥夺,才有可能使这一有效性消失。抗战时期,张资平落水当汉奸不仅意味着人格有亏,也意味着张资平作为文学史叙事对象的合法性无形中被取消。从此,他的自我叙事很难再进入文学史叙事的视野。他只能成为文学史叙事中的他者,成为“经验教训”和“人生失败的标本”。正像张资平在新中国成立后写的一份交代材料所总结:“总之,我是当时社会的象征,受了多方面的攻打,终未能获得志同道合的朋友,因我风来随风,雨来随雨,是我性格上最大的缺点……我是人生失败者,偷生苟活明哲保身,但终归失败。”d鄂基瑞、王锦园:《张资平——人生的失败者》,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68页。
从“脱了轨道的星球”到“彗星的行迹”再到“人生失败者”,张资平的自我叙事可以说充满了悲剧性。在这一变化历程中,强制性权力通过作家的怨恨、区隔完成了作家在文学史中的自我叙事。
二
作家的自我叙事并不能自然而然地具有文学史叙事的合法性。他在文学史中的地位主要是由文学史的叙述者以文学评估的方式进行区隔、分类所决定的。文学评估是一个综合性过程,是由不同现实领域中极不相同的评价所组成。这些评价联系着“客观地置根于社会意识的结构和发展形式”a[德]朔贝尔:《文学的历史性是文学史的难题》,见[德]瑙曼等著、张大灿编:《作品、文学史与读者》,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第217页。、不同世界观、不同关系系统,它们的目的是使被评价者具有“实际的意义”b[德]瑙曼:《作品与文学史》,见[德]瑙曼等著、张大灿编:《作品、文学史与读者》,第192页。。也就是说,文学评估所反映的是文学史叙事语境中现实强制性权力的认知图式与评价系统。另一方面,作家的文学场域占位也深刻地影响着后来的文学史叙事。1933年的《申报·自由谈》的“腰斩”事件是影响张资平在文学史叙述的地位的一次巨大变化。它不仅改变了张资平的文学场域占位,也是左翼阵营的一次重要的区隔行动。在这一过程中,区隔者与被区隔者都显示出比较明显的怨恨情绪。
张资平在早期创造社中以小说创作见长,“是真正小说家”。这是当时创造社成员的公意。它主要是指张资平小说文体的成熟性、通俗性。c参见陶晶孙:《记创造社》,见丁景唐选编:《陶晶孙选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240页。因此,在1929年之前,时人笔下的张资平通常被视为创造社的元老、自然主义的代表、一个为青年读者所欢迎的、善于写恋爱小说的小说家。他在小说中对现存制度的批判、对教会的鄙夷、对灵肉一致爱情观的向往以及新道德的建构意识等怨恨心理的显现契合了当时读者的阅读期待。因此,当时的评论者是把张资平归为新文学中成功作家之列的。1926年一位署名默之的批评者这样评论他:张资平氏的“性欲描写虽有些挑拨性,却是不像同社的郁达夫氏来得露骨。用笔的简净,在当代作家中,笔端的无滞气,措词的无累语,恐怕要推氏为数一数二的人了。”d默之:《张资平氏的恋爱小说》,见史秉慧编:《张资平评传》,第31页。郁达夫也认为“在目下中国的小说家里头,结构最严整的,总要推他(张资平)了”e达夫:《尾声》,《创造月刊》第1卷第1期,1926年2月。。即使到了1930年代,一些批评者在评价他的时候也还认同这一点。1932年4月日本《改造》杂志特刊的特别号最新世界人名辞典这样介绍他:“……以自然主义的手腕描写恋爱,在中国新文坛中无有能及之者。名著《苔莉》、《最后的幸福》,描写的深刻,与技巧的熟练,尤为显然。”f李长之:《张资平恋爱小说的考察》,郜元宝、李书编:《李长之批评文集》,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年,第204页。李长之也对张资平做了类似的批评:“他恰抓着现在青年婚姻问题的时代。他一点也没特意挑拨,他写的是性爱的悲剧,他的成功在于自然主义派的技巧,他的失败在有时对自然主义的作风偶尔放弃。”g李长之:《张资平恋爱小说的考察》,见《李长之批评文集》,第234页。史秉慧认为:“张资平先生写恋爱小说的精神是值得我们佩服的。”“他颇能获得多数的少男少女的读者,而在两性的关系方面曾发生不少的影响。……他不仅是一个写实主义者,而且是颇有自然主义的风味。他从生理方面去刻画性的态度和描写人性中的丑恶,是颇值得赞许的。”h史秉慧:《张资平评传·序》,《张资平评传》,第2页。在这其中虽不无溢美之词,但张资平作为一个成功的小说家被叙述则毫无疑义。
张资平被文学场域贬抑主要是出现在围绕着无产阶级文学这一信仰的话语权争夺中,其中也包含着文学场域的占位斗争。1920年代中期开始的“革命文学”论争可以看作是以后期创造社、太阳社为核心的一批文坛后起之秀的一次文学信仰话语权和文学场域位置的争夺行动。“后期创造社名义上是一个‘同人文学社团’,其实已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革命文化组织”。而且共产党在革命文学论争的早期(不晚于1928年2月底)就直接干预这一论争,指示论争的矛头不要指向鲁迅。a参见林伟民:《中国左翼文学思潮》,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95、97页。但是在论争中,这些后起之秀仍然彻底否定了“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传统及其代表作家,把他们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这其中的原因除了冠冕堂皇的主义之争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后来者准备取而代之的占位意识。怨恨情绪的积聚在这些后来者的内心深处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即后来所谓宗派主义情绪是也。作为创造社成员之一的王独清的观察是有道理的:“创造社一向几个中心份子都有一种倾向,便是对于新进份子加入的防制,表面上虽然是取公开的态度,其实却总是无形地维持着几个中心份子底小组织的。”b王独清:《创造社》,见史秉慧编:《张资平评传》,第120页。这些后起之秀的生存性压抑体验成为他们怨恨积累的温床。他们在论争中所提出的“普罗列塔利亚”“普罗文学”“意德沃罗基”“新兴文学”“革命文学”等新名词、新标准在某种程度上恰是他们怨恨心理的显现:通过提出“一种不同于被比较者的价值的价值观,以取代自身无力获得的价值实质。”c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第364页。正是借助于“普罗列塔利亚”“普罗文学”这一新的信仰,他们试图建立一种新的认知图式和评价系统。这些文坛的后起之秀把自己与使他们产生生存性伤害感、无能感的那些新文学的先驱区隔开来。同时,他们又在这一新的评价系统中,贬低那些给他们带来压抑、屈辱的生存性体验的文坛先驱。冯乃超在《文化批判》创刊号上发表的《艺术与社会生活》是一个很好的代表。它除了指出新兴艺术的方向要有“严正的革命理论和科学的人生观作基础”这一空泛的口号之外,文章的主要内容是在抱怨“现在中国文坛的情况,堕落到无聊与沉滞的深渊”,否定以叶圣陶、鲁迅、郁达夫、张资平为代表的新文学创作,把他们贬低为“厌世家”“落伍者”。
张资平虽然在1928年就开始宣布要转向,但他的转向并没有得到无产阶级文学倡导者的认同,反而被贬低进一个已经落伍、被否定的价值系统。对他的评价主要包括“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鲁迅语)、布尔乔亚的、“商人化的”。这些都是与新的标准、新的认知图式相区隔的定位。例如,钱杏邨认为:“张资平先生转换方向初期的创作,若严格地说来,是不能令我们满意的。他还没有把握住普罗的阶级的意识。……他还是站在进步的小市民的立场上在发着牢骚,他并没有站在新的立场上来说话。”d钱杏邨:《张资平的恋爱小说》,《阿英全集》第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3年,第139页。鲁迅虽然并没有看过多少张资平的小说,但他仍然对张资平的转向加以嘲讽,并把他的小说学提炼成“△”。e参见鲁迅:《张资平氏的“小说学”》,《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30—231页。而张资平的自动脱离创造社出版部,创办乐群书店、出版《乐群》杂志、参加“第三党”等自我区隔行为又在某种程度上加重了这种怨恨心理的积聚。一些打着革命文学旗号的批评者甚至不惜以人身攻击这种低劣的贬低、区隔手段来发泄怨恨。署名许由的文章以鄙夷不屑的口吻称张资平“实在的做起商人来了”,指摘张资平千字十元叫卖自己书稿的发行权。f参见许由:《张资平与乐群书店》,史秉慧编:《张资平评传》,上海:现代书局,1932年,第93—94页。而署名皮凡的作者则讥笑千字十元的稿酬使得张资平“近来吃得十分肥涨”,“渐渐踏进布尔乔亚的坛池里去了”a皮凡:《〈红雾〉之检讨》,史秉慧编:《张资平评传》,第110页。。这种恶劣的评价和区隔在当时应该并不鲜见,以至于史秉慧在编选《张资平评传》中的批评文章时,忍不住在序中对这一情况表示不满:“他的稿费虽然每千字能够卖到十块钱,但以这点来攻击一个作家,抹杀一个作家,我想这是错了。”b史秉慧编:《张资平评传》,第2页。
1930年代的上海文学场域虽然受到多种力量的制约,呈现出一定程度上的权力结构多元性,但是,党派力量的有意识参与,使得文学场域的占位斗争不可能不受其影响。发动《申报·自由谈》“腰斩张资平”事件的黎烈文虽然没有什么党派色彩,但他有意识地借助所谓读者这一强制性权力施行的“腰斩”行动却不能不受到当时文学场域占位斗争的影响。《时代与爱的歧路》算是一部比较典型的张资平转向后的小说:多角恋爱与革命的纠葛、借助主人公之口发泄作者对革命文学以及现实人事的偏见。这部小说有许多弱点,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正如同时代人章克标所说,当时的普通读者是不可能出来反对这一小说的。读者云云,只是编辑者在行使强制性权力的“遁词”“饰词”。c章克标:《创造社“四大金刚”》,《文苑草木》,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第6—7页。粹公当年认为这一事件是左翼文学在清理门户。此说虽不乏挑拨之嫌,但至少说明了事件中现实权力运作的一部分真相d粹公:《张资平挤出〈自由谈〉》,《社会新闻》第3卷第13期,1933年5月9日。:张资平的被“腰斩”的原因恐怕与他小说中对当时无产阶级文学的不满、对革命的偏见有着很大的关系。虽然张资平也打着革命文学的幌子,但他的确站在了与无产阶级文学的作家相对峙的一面。“腰斩”事件虽非“左联”主导,但黎烈文所受左翼文人的影响是明显的。他的价值判断有趋向于无产阶级文学的一面。另外,如上所述,张资平在1930年代初与无产阶级文学的自我区隔叙事变成了无聊的谩骂,为时人所不齿e例如署名激厉的文章《评“脱了轨道的星球”》(1931)中就认为,“张氏最大的谬误……他都是随着个人的意识来对于现在社会,对于他所认为对象的人物,作一种比‘讽刺’更明显的谩骂”。见史秉慧编:《张资平评传》,第78页。再如鲁迅在与黎烈文的信中也提到,“张公资平之战法”好似“吾乡之下劣无赖,与人打架,好用粪帚,足令勇士却步”。见《鲁迅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94页。。时人对张资平的不齿,不仅包括他在小说创作中“好用粪帚”,也包括他迎合读者市场的带有模式化、复制性的生存方式。前者越出了小说的文体规范,损害了文学的独立性,使文学成为人身攻击的工具;后者则冒犯了文学场域的“颠倒的经济学”逻辑,将精英文学的生产逻辑等同于通俗文学的生产逻辑。当时的上海文学场域是多元的,与左翼文人联系更紧密的黎烈文既不能容忍张资平对革命的诋毁,又不满意于他对文学独立性和“颠倒的经济学”逻辑的冒犯而“腰斩”之,就可以理解了。所以,张资平从此不“再有刊物上的生命”f鲁迅:《致黎烈文》,《鲁迅全集》第12卷,第194页。主要是指经此一役,张资平实际上已经被排除于无产阶级文学和精英文学之列。这显然是当时左翼文学阵营的一种区隔行为。
在文学的现场,对作家的评价、分类也许是多元的,但是文学史的叙述却常常是简约化的。现实强制性权力通过叙述主体的评价系统来决定文学史材料的选择,同时通过对这些材料的有意识的“误读”来体现强制性权力的现实需要。后来的文学史叙事在涉及到这一“腰斩”事件时主要是一种胜利者的叙事。它所显示的必然是胜利者的认知与评价体系。“腰斩”事件所蕴涵的怨恨情绪也有意无意地渗透进历史的叙述中。怨恨作为一种现代情绪,蕴蓄着弱者的“无能”感。这种无能感逃避了对自我肯定性价值的正视。a[德]马克斯·舍勒:《道德建构中的怨恨》,罗悌伦译,刘小枫校,见[德]马克斯·舍勒:《价值的颠覆》,罗悌伦、林克、曹卫东译,刘小枫校,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70—71页。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现代文学史叙事中怨恨情绪的存在意味着独立的文学史叙事规范尚未真正建立起来。1980年代中期以来重写文学史的诸种努力在摆脱旧有文学史叙事规范的同时,对文学史实所蕴涵的怨恨情绪没有给予充分的关注和清理。我想,今后的文学史叙事应该有此自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