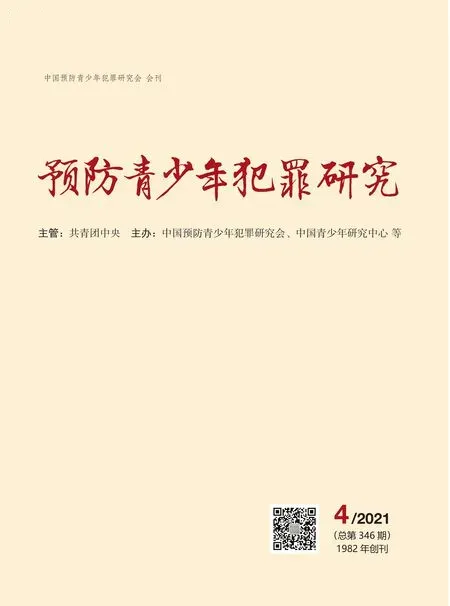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检察公益诉讼保护之“公共利益”探究
苏 青 陈本正
2020年10月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章专章规定了对未成年人的“网络保护”,以应对网络信息时代出现的新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问题。其中第72条规定了处理未成年人信息必须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并规定了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更正、删除权。同时,在第七章“司法保护”第105条、106条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对未成年人案件的监督权、对侵犯未成年人权益案件的支持、监督起诉权以及对“涉及公共利益”的侵犯未成年人权益案件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利。可以说,对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检察公益诉讼保护已有了法律依据。2021年3月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检察院对某知名短视频公司提起侵犯儿童个人信息民事公益诉讼案作为首例儿童个人信息检察公益诉讼保护案例,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检察公益诉讼保护须基于对《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06条之“涉及公共利益”的合理解释,而对“公共利益”的解读需基于一定的公共利益观,进行对公共利益的一般判断与规范判断。
一、我国检察公益诉讼中“公共利益”的扩张
公益诉讼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之后为许多国家所借鉴和移植。基于不同国家文化、法律制度及所面临的现实问题的不同,各国公益诉讼制度的发展呈现不同的特征。但总体而言,西方国家的公益诉讼之价值主要体现在对社会边缘群体的权利保护,且以私益救济为主要模式。①参见梁鸿飞:《检察公益诉讼:法理检视与改革前瞻》,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9年第5期。我国从1996年“中国公益诉讼第一人”丘某状告电信部门到2011年云南省首例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宣判,公益诉讼的初始形态以私权利主体或社会组织等为维护公共利益而发起的诉讼活动为主。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生态环境、食品药品、消费者权益及国有资产等领域的违法犯罪问题凸显,但其“公益侵害性”使传统的法律救济与惩处机制难见成效。同样,处于弱势地位的私权利主体作为“公益维护者”的维权行为,面对大量的公益侵害行为,也是杯水车薪。相应地,随着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深化,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再次被强调,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建设与实践探索也逐步推进。
以我国《宪法》规定的“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为基本依据,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2015年5月中央深改组通过了《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改革试点方案》,对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目标原则、试点案件范围、诉讼参加人、诉前程序、提起诉讼、诉讼请求等内容作了规定。2015年7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公益诉讼试点工作的决定》,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国有资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食品药品安全等领域开展提起公益诉讼试点。2016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人民法院审理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案件试点工作实施办法》,对人民法院受理人民检察院提起民事和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的范围、案件管辖、案件当事人、调解、撤诉、审理规则等方面进行了规定。自2017年7月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全面实施以来,截至2020年7月1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公益诉讼案件31万件;诉前程序案件27万余件,其中向行政机关发出诉前检察建议26万余件、发出民事公益诉讼公告1万余件;提起诉讼1万余件。①参见闫晶晶:《检察公益诉讼全面实施三周年办案31万余件》,《检察日报》2020年7月9日。
对于检察公益诉讼制度,虽然有《宪法》作为基本依据,《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等也有相关规定,但总体而言,当前法律只是为推行检察公益诉讼提供了抽象的、原则性的指引,缺乏具体、可操作的规则。实践中,基本以前述《试点方案》、《授权决定》及《实施办法》为根据推进检察公益诉讼工作。因而,法律供给严重不足是当前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存在的突出问题,导致实践中对于检察机关的法律地位、公益诉讼具体法律适用、调查取证权、诉前程序操作等各方面均存在争议。②参见高洁:《检察公益诉讼制度若干问题思考》,载《法治研究》2021年第1期。作者提出应当制定《公益诉讼法》,构建“合力”保护公共利益的诉讼构造,拓展案件范围,细化公益诉讼规则,推进中国特色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的科学发展。此外,《授权决定》对检察公益诉讼的范围采取了明确列举加“等外规定”的形式,意味着除了列举的四大领域,仍有拓展检察公益诉讼范围的空间和可能。而“等外”条款的适用首先是基于对“公共利益”的合理解释。
在西方国家利益理论的发展中,公共利益脱离出国家利益的范畴成为一个独立且重要的利益单元,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个人利益相对“泾渭分明”的划分也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基础之一。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利益的多元化、复杂化,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国家利益作为独立的利益单元,相互之间的边界越来越模糊,“公共利益”的表现形式与范畴也呈现多元化、扩大化的特征。个人、集体、国家本身就不是能够截然区分的范畴。在现代信息社会中,公众对国家、社会事务的信息获取与参与度空前提高,不能忽视典型的个人利益可能因其对社会道德观念或秩序的冲击而呈现出突出的公共利益特征。譬如在“于欢案”中,社会公众对“辱母”情节的高度关注与案件本身在现代刑法语境下的评价存在的严重脱节,使我们不得不反思道德层面的公共利益几乎完全被剥离出现代法学体系及理论是否合理。③关于本案中民意、情理、法理的冲突及对判决的分析,参见梁治平:《“辱母”难题 · 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情——法关系》,载《中国法律评论》2017年第4期。此外,2020年12月杭州郎某等涉嫌诽谤罪自诉转公诉案中,原本典型的侵害个人名誉权的诽谤案件,因捏造的诽谤信息在网络空间迅速传播、扩散,检察机关认为其不仅侵害了被害人的人格权,而且给社会公众造成在网络空间的不安全感,适用《刑法》第246条第二款的例外情形,以“严重危害社会秩序”为由启动了公诉程序。①本案案情介绍及相关探讨参见车浩:《杭州诽谤案为何能转为公诉》,载《检察日报》2020年12月30日;樊崇义:《诽谤罪之自诉转公诉程序衔接——评杭州郎某、何某涉嫌诽谤犯罪案》,载《检察日报》2020年12月27日等。可见,无论是对传统的伦理道德价值的维护,还是应对新时代产生的新的社会秩序问题,亦或是对其他具有“公共性”特征领域的特殊保护,“公共利益”范畴的扩张已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
二、侵犯未成年人个人信息行为之“公共利益”侵害性
我国自上而下的检察公益诉讼制度本质上是利用公权力来保护公共利益,而公权力保护模式本身就意味着其扩张是有限度的,否则会导致公权与私权的紧张关系。公共利益的保护需要公权力、社会组织、特殊群体代表及个人等多方社会力量的参与和多元保护机制的构建。检察公益诉讼只是保护公共利益最有力的手段,故而其范围应当限于有公权力介入保护之必要性的特殊领域的公共利益。而未成年人权益无论是从各国法律体系还是从实践来看,都是需要进行特殊保护的特殊领域。在我国推进检察公益诉讼的过程中,应当将其纳入“等外公共利益”范畴。我国2020年修订并于2021年6月1日起施行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均强调对未成年人权益的国家保护,《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了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权与公益诉讼。②如《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00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部门应当依法履行职责,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第106条规定:“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相关组织和个人未代为提起诉讼的,人民检察院可以督促、支持其提起诉讼;涉及公共利益的,人民检察院有权提起公益诉讼”。法律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侵犯未成年人权益案件的督促、支持提起诉讼制度,体现了国家积极启用公权力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基本态度。提起检察公益诉讼,虽然有“涉及公共利益的”作为限定条件,但立法明确将涉及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案件纳入前述《授权决定》的“等外条款”范围,解决了涉及公共利益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适用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的法律依据问题。在信息网络时代,侵犯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案件迭出,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个人信息从“私益”向“公共利益”的扩展及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特殊性使侵犯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案件凸显出公共利益侵害性,因而具有通过检察公益诉讼保护的必要性。
(一)个人信息的特殊性:从“私益”向“公共利益”的扩展
传统社会的个人信息与隐私具有天然的联系,甚至可以将二者作同等理解并以保护隐私权的法律制度来保护个人信息。然而在信息时代,个人信息已突破隐私权的核心范畴而体现出多元的价值与属性。顺应时代需求,欧洲国家将个人信息与隐私区分,通过统一立法对个人信息的收集、储存、处理作出规定,譬如《德国联邦个人资料保护法》以一般人格权为基础保护个人信息,以信息主体的权利为核心对个人信息的收集、处理和利用进行规范。③参见 Marion Baston- Vogt. der sachliche Schutzbereich des zivilrechtlichen allgemeine Persönlichkeitsrechts [M].Mohr Siebeck, 1997: 107。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则通过扩展隐私及隐私权的外延来保护个人信息,譬如美国《隐私法》规定了对个人信息的保护规则。④Daniel J. Solove & Paul M. Schwartz, Information Privacy Law , Wolters Kluwer, 2009: 2.我国应对互联网背景下产生的侵犯个人信息安全问题,最早是在《刑法》中增设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罪名。随后此类侵权及犯罪问题日益突出,相关的研究也日益丰富和成熟。2020年5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人格权编”第六章设专章规定了“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从个人信息的界定、个人信息的处理原则及限制、免责事由、个人信息决定权、个人信息安全等全面规定了对个人信息的民法保护,同时也体现出我国立法对隐私权和个人信息的“二元保护”模式。①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32至1039条。可见在信息时代,个人信息具有区别于隐私权的特殊性基本已成为现代法治国家的共识。
个人信息的特殊性不仅体现在民法语境下与隐私权的相对独立性,也体现在互联网背景下,因信息主体的不特定性、信息聚合衍生的新法益以及信息处理的快速、广泛等特征而呈现出的个人信息从“私法益”向“公法益”扩展的趋势。据统计,截至2021年3月,已有24个省级人大常委会通过支持检察公益诉讼的决定或决议,其中大部分都包括授权检察机关办理个人信息保护等领域公益诉讼案件。譬如2019年11月,上海市宝山区检察院对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案件同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杭州、广州、深圳等地也对多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提起公益诉讼,并积极通过与各部门及学界的合作,推进涉网络、大数据案件公益诉讼的研究。②参见杜洋:“公益诉讼破解互联网侵害个人信息治理难题”,载《法治日报》3月24日。http://www.legaldaily.com.cn/IT/content/2021-04/01/content_8465318.htm.最后访问日期2021年4月23日。而在学界,早在2007年就有学者认识到个人信息的多重价值属性,主张在信息时代,个人信息不仅体现为作为人格权的隐私,还体现具有商业价值的财产权属性。对个人信息进行确权应该根据其体现的价值而定,当其维护主体人格利益时,应该给予其人格权的保护;当其维护主体财产利益时,就应该给予其财产权保护。③参见刘德良:《个人信息的财产权保护》,载《法学研究》2007年第3期。也有学者明确提出应当确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之法益的“公共性”,主张将该罪规定在《刑法》分则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中。④参见皮勇、王肃之:《大数据环境下侵犯个人信息犯罪的法益和危害行为问题》,载《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可见,个人信息在信息时代具有明显地从作为人格权的“私益”向涉及公共利益的“公益性”扩展的特征。
(二)未成年人个人信息:“公共利益”的凸显与检察公益诉讼保护的必要性
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因其特殊性,在立法、司法上均和成年人予以区别对待。2021年《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了保护未成年人的“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并在第五章设专章规定对未成年人的“网络保护”,其中就包括对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保护。例如第72条规定了处理未成年人信息的原则及处理儿童信息须征得其父母或监护人同意的规则,同时规定对未成年人信息的更正、删除权。而对于不满14周岁的儿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于2019年发布了《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其中规定了儿童个人信息处理的基本原则,要求处理儿童个人信息应当以显著、清晰的方式告知儿童监护人,并应当征得儿童监护人的同意,同时规定运营者应当设置专门的儿童个人信息保护规则和用户协议,并指定专人负责儿童个人信息保护。从国外立法和实践来看,国家对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保护力度也远高于成年人。例如,美国1998年的《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Children's Online Privacy Protection Act of 1998,COPPA)规定了网络运营者针对 13 岁以下儿童信息收集与处理的基本规则,如要求制定隐私政策、通知并征得儿童父母的可验证的同意、应父母要求终止向儿童提供服务及儿童家长的审查权、删除权、拒绝收集及使用权等。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第8条同样引入了“父母同意”制度( Parental consent) ,明确规定网络服务的提供者在收集、使用或处理未满 16 周岁的儿童的个人网络信息前,需要获得父母的同意或者授权,并规定成员国可以设定不低于 13 岁的年龄门槛。⑤参见张继红、尹菡:《数字时代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21年第2期。
2019年抖音国际版短视频应用TikTok因违反美国COPPA而被处以570万美元的高额罚款案引起了国内对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的广泛关注。①FTC称TikTok要求用户提供电子邮件地址、电话号码、用户名、姓名、个人简介和头像等资料,用户号默认是公开的,且并未对儿童个人信息采取特殊保护措施,违反COPPA规定的“家长同意”规则。参见周扬、张忠:《从抖音被罚案审视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基于合规视角》, https://www.sohu.com/a/299763657_99955893,搜狐网2019年3月7日,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4月23日。较之于美国等西方国家,我国法律制度和实践对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保护尚为薄弱,故而对TikTok遭美国天价罚款的事件起初在国内引起的是一种“错愕”反应,因为网络平台收集、处理未成年人信息已成常态,且并没有因此受到规制或处罚的先例。COPPA对儿童隐私的强制保护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在互联网背景下,对不特定多数儿童个人信息的保护已然不是通过私力救济所能实现的,其权力属性也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公益性”,因而有政府强制保护的必要。相对于迅速发展的数字经济,我国法律呈现一定的滞后性,尤其是对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已具有迫切的现实需求,亟待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与出台。2020年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设专章规定对未成年人的“网络保护”,便是对这种现实需求的回应。在此背景下,2021年3月,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检察院对某知名短视频公司提起侵犯儿童个人信息民事公益诉讼案,成为全国首个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案件,并入选2021年4月2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检察机关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②参见最高人民检察院网上发布厅:“最高检发布检察机关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斩断个人信息侵权与电信网络诈骗之间的利益链条”, https://www.spp.gov.cn/xwfbh/wsfbt/202104/t20210422_516357.shtml#1,2021年4月22日,最后访问日期2021年4月27日。国内外的立法与实践已说明未成年人个人信息凸显出“公共利益”属性,具有国家强制保护的必要性。
可以说,将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纳入我国自上而下、带有明显的“公益性”特征的检察公益诉讼保护范围是必然且必要的。在信息时代背景下,对个人信息的收集、处理通常都具有对象的不特定或多数性,这是个人信息成为“公共利益”的前提和基础。未成年人这一主体的特殊性不仅在于其因认识和意志能力、责任能力的欠缺而导致的对个人信息自主权的缺失或弱化,因而具有给予特殊保护的必要性,同样在于,国家和社会保护未成年人权益、保证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本身就是一项涉及社会健康发展的“公共利益”。当然,《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06条“涉及公共利益的,人民检察院有权提起公益诉讼”之“公共利益”仍需相对具体、明确的判断标准,避免“公共利益”的虚化或泛化。只有设置具体的判断规则,才能避免《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规定成为一纸空文,或者因泛化的“公共利益”而使检察权成为无处不在的“威胁”。从“公共利益”的一般概念与范畴出发,结合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特殊性,可以大致设定侵犯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案件之“公共利益侵害性”的判断规则。
三、侵害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案件之“公共利益侵害性”的判断
(一)“公共利益”的基本判断标准
如果说我国早期由个人或社会组织为维护特定群体利益而发起的公益诉讼,在基本目的和价值上比较接近于西方国家的公益诉讼,那么从2014年起,由中央推动的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建设与实践探索,已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英美等西方国家的公益诉讼之初衷主要在于对弱势群体的权益保护,虽然其后扩展到生态环境、食品药品、消费者权益、行业垄断等各个领域,但并未改变其私益救济的基本底色。而我国经由顶层设计而出的公益诉讼制度是纯粹的“公益模式”,③参见巩固:《美国原告资格演变及对公民诉讼的影响解析》,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7年第4期。即借助公权力推动对公共利益的保护。同时,“公共利益”在不同国家因不同的“公共利益观”,亦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西方公共利益观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高度发达以及国家与社会分离的基础之上的,而我国公共利益观则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义利观’基础之上的,这种‘义利观’在社会转型期呈现出复杂多样的现实情景。”①高志宏:《公共利益观的当代法治意蕴及其实现路径》,载《政法论坛》2020年第2期。因而,现阶段我国对公共利益的认识尚处于模糊、杂乱的状态,公共利益理论的不成熟一方面导致公共利益被过多过分强调甚至成为公权力扩张、以公谋私的借口或手段,另一方面切实关乎民生的公共利益被泛化、虚化,无法在制度与实践中得到有效保护。发展我国的公共利益理论,应当立足于我国传统的公共利益观与政治、文化背景,结合现实需求,为公共利益划定合理的内涵与外延边界。纵观之,我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一贯强调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及家族利益的重要性,这也是我国公共利益观及公益诉讼制度建设天然地与国家公权力具有密切关联性的内在原因。
学界对公共利益有不同的理解,或者可以说,为“公共利益”寻求明确的内涵和外延的努力基本都是徒劳的。在德国公法学界的“公共利益”理论中,有“地域说”“人数说”和“综合说”之争,其中“综合说”为主流观点。“综合说”主张公共利益是指“不特定多数人”所享有的利益,其中,“特定”还是“不特定”,“多数”还是“少数”,都是相对一个特定的圈子而言的,同时,这个“圈子”是一个相对的、动态的概念。②参见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上册),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82-186页。从我国传统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公共利益观出发,结合西方国家多元、动态的公共利益判断标准,我们认为,可以将“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作为公共利益之基本特征来判断个案是否涉及公共利益。就我国检察公益诉讼保护之“公共利益”而言,如果说《授权决定》所列举的国有资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带有明显的“国家利益”特征,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则更具“集体利益”之特征。借鉴西方国家源于弱势群体利益保护的“不特定多数人利益”理论,结合我国检察公益诉讼向个人信息保护等新领域的拓展,可以预判我国的“公共利益”也将逐步走向“多元化”道路,公共利益中的个人利益尤其是弱势群体利益色彩将逐渐凸显。
将“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作为“公共利益”判断的基本标准,可以使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特殊领域或特殊群体中的(即前述德国公共利益理论中的“圈子”)的个人利益之集合均有被解释为“公共利益”的可能性。以侵害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案件为例,是否“涉及公共利益”而能被纳入检察公益诉讼保护范围,首先便要判断是否侵害了“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美国的COPPA及我国《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将儿童个人信息保护限定于“在线”或“网络保护”,且主要内容集中在对网络运营者相关义务和责任的确定。这意味着“在线”或“网络”环境下儿童个人信息具有其特殊性:一方面,在线或网络环境下的儿童个人信息案件具有“涉众型”,即侵害的是不特定多数儿童的利益;另一方面,儿童这一特殊弱势群体面对网络运营者,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显然形成鲜明的“强弱”对比。可见,儿童个人信息在对象和权益方面均属于作为“公共利益”保护的范围。在符合此项一般判断的前提下,判断个案是否“涉及公共利益”,应当结合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制度,对“公共利益”进行规范判断。
(二)侵害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案件“公共利益侵害性”的规范判断
“公共利益”的多元性、动态性决定针对不同领域、不同群体,对于是否涉及公共利益,可能有不同的判断标准。推进检察公益诉讼应当时刻警惕公权力的不当扩张,而法律便是划定国家公权力界限的最有效的手段。因而在个案中,判断是否符合“公共利益”标准,应当建立在相对完善的法律制度的基础之上。也即,是否侵害公共利益需要有更明确的判断标准,而非以“公共利益观”或一般性的公共利益判断标准进行抽象推定。“公共利益”从一般性判断标准到法律领域的判断,应当是一个从抽象到具体、从非规范性判断到规范性判断的过程。而规范性判断便是在一般判断的基础上,设定相对明确的法律规则,作为法律赋予“公共利益”的规范内涵。具体到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是否涉及“公共利益”,应当在符合公共利益之一般判断标准的前提下,进行规范判断:即是否被法律、法规或有效的规范性文件作为特殊保护的对象或领域,以及个案中相关主体有无违反具体的信息保护义务的行为。以前述某知名短视频公司侵犯儿童个人信息民事公益诉讼案为例,在一般性判断标准下,该案符合侵害“不特定多数人利益”之基本标准;在规范标准下,亦有《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为依据。短视频公司未尽到《规定》中的儿童个人信息保护义务,检察机关便有权提起公益诉讼。
因此,在符合“不特定多数人利益”基本标准的前提下,对于侵害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案件进行检察公益诉讼保护,应当在建构和完善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机制的基础上逐步推进,才能使“公共利益”的判断具有规范性。《民法典》《网络安全法》《刑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等规范性文件,以及已提上立法议程的《个人信息保护法》,都是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检察公益诉讼保护的规范依据。但具体到个案判断,虽然上述法律、法规等均有相关规定,但除了《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都为抽象、一般性规定,无法为个案中判断是否“涉及公共利益”提供直接参考。因此可以说,当前法律背景下,对14周岁以下儿童的个人信息保护尚有规范性判断依据,而针对14至16周岁的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案件,尚需推进专门的保护机制。同样地,虽然实践中已有数例个人信息检察公益诉讼保护的案例,但在《个人信息法》及相关法律规定尚未出台的背景下,这些案例只能说是“有益的实践探索”。“实践先行”有助于推进相关制度建设,但严格来讲,当前实践中对“公共利益”的理解和判断仍停留在一般性、抽象性判断的层面。要实现检察公益诉讼之“公共利益”判断的具体化、规范化,还有赖于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
以现有法律及相关规范性文件为基础,应当建构分层次、分类型的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法律机制。对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特殊保护主要与未成年人的信息自决权有关。虽然在大数据时代,对个人信息及由个人信息聚合而成的大数据的性质与权属问题尚有很多争议,但个人信息的保护应当首先承认信息主体的信息自决权,避免过于强调数据的经济价值而忽略对个人权利的保护。未成年人权益历来就需要国家以“家长主义”的立场进行特殊保护,具体到其个人信息,同样需要根据未成年人对与其个人信息相关的行为之性质、后果等的认识和决定能力为依据,合理掌握公权力保护的限度。未成年人的信息自决权与其年龄直接相关,而不同年龄段的个人信息保护范围也应进行区别对待。《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充分借鉴和参考了美国COPPA的相关原则和制度,对14周岁以下儿童的个人信息保护,尤其是对网络运营者的信息保护义务及规则规定的较为详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72条也针对14周岁以下儿童的个人信息处理作了专门规定。①《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确立了处理、收集儿童个人信息须充分告知、监护人同意,以及信息的更正、删除权等基本规则,并规定了“网信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对网络运营者是否遵循儿童个人信息保护规定的监督、检查职责。《未成年人保护法》第72条规定:“处理不满十四周岁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应当征得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同意,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但从实践来看,当前许多网络平台没有对14周岁以下儿童与14-18周岁未成年人进行区别保护,儿童个人信息保护的实践效果欠佳。我们认为,应当沿用《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对14周岁以下的儿童进行“一刀切”式强制保护,在信息保护范围及保护模式上都应当与14至18周岁的未成年人及成年人进行区分。譬如在信息保护范围上,除了当前立法通常采用的“身份可识别信息”外,应当一般性地禁止收集和处理儿童照片、视频、生日、学籍、家庭住址等可能与身份识别无关的信息;在信息处理上,应当禁止利用儿童信息进行商业目的的用户画像;在保护模式上,采取国家强制保护模式,即通过一般性禁止条款和“家长有效同意”的除外规定,划定儿童个人信息处理的清晰法律界限。同时,应当推进专门针对儿童的网络产品建设,划定特定范围的网络运营者必须提供符合法律要求的“儿童版”网络产品。违反强制性义务者即可判定符合《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06条规定之“涉及公共利益”的规范标准,人民检察院有权启动公益诉讼保护。
14至18周岁的未成年人在法律上一般认定其具有一定的行为能力与责任能力,从个人信息保护的角度,同样可以推定其具有一定的信息自决权。《未成年人保护法》第76条在网络直播领域将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与16-18周岁的未成年人进行了区分,从我国《民法典》、《刑法》等基本法律中也可以看出,对未成年人责任能力有多层划分的必要性。因此我们认为,对14-18周岁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保护有必要再分层,对14-16周岁与16-18周岁采取不同的保护模式。如果说14周岁以下儿童完全没有信息自主权,14-16周岁未成年人可以推定具有有限的信息自主权,可以将“家长有效同意”作为一般性要求,探索家长同意的可行方法与规则。16-18周岁未成年人则可以推定原则上具有信息自主权,一般采取与成年人个人信息同等的保护措施。但为了防止未成年人接触网络不良信息、网络沉迷等问题,应当遵循《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章“网络保护”的各项规定,落实对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特殊保护责任,如第73条规定的对未成年人隐私信息的积极保护义务等。①《 未成年人保护法》第73条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发现未成年人通过网络发布私密信息的,应当及时提示,并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同样,应当推进“未成年人版本”网络产品的开发、应用,并在特定领域作为法律强制性要求。在个人信息保护范围上,对14-18周岁未成年人个人信息可以沿用当前立法普遍采取的“身份可识别性”标准,并采取较为灵活的保护模式。
四、结语
信息网络时代个人信息体现出多重价值与多元属性,实践中已有对侵害个人信息案件启动检查监督或检察公益诉讼的案例。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特殊性更是凸显其“涉及公共利益”的特征,许多案件中都体现出检察公益诉讼保护的必要性。但我国自上而下的检察公益诉讼动用国家公权力保护“公共利益”,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何为“公共利益”,或者说“公共利益”的判断标准是什么。具体到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06条之“涉及公共利益”的判断应当有相对明确、规范的标准,而非停留在一般、抽象的观念判断层面。“公共利益”难以取得一个统一的概念,“不特定多数人利益说”具有相当的涵盖性和包容性,可以在我国公共利益观下将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与特殊领域的个人利益纳入其中,为检察公益诉讼提供一般性的理论依据。但检察公益诉讼的启动应当对“公共利益”作进一步的规范判断,即“公共利益”的判断应当有具体的规范性依据。《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了包括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在内的未成年人权益检察公益诉讼的基本法律依据,但“涉及公共利益”的判断仍有赖于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法律法规的进一步完善。国家网信办2019年发布的《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对儿童个人信息保护作了较为详尽的规定,在此基础上,可以对未成年人个人信息进行再划分,针对不同年龄段的未成年人设定不同的保护规则和义务。这样,将违反强制性保护规则的行为推定为符合“涉及公共利益”的规范标准,使“公共利益”从抽象、一般性判断走向具体、明确的规范判断,为检察公益诉讼的启动提供相对明确的判断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