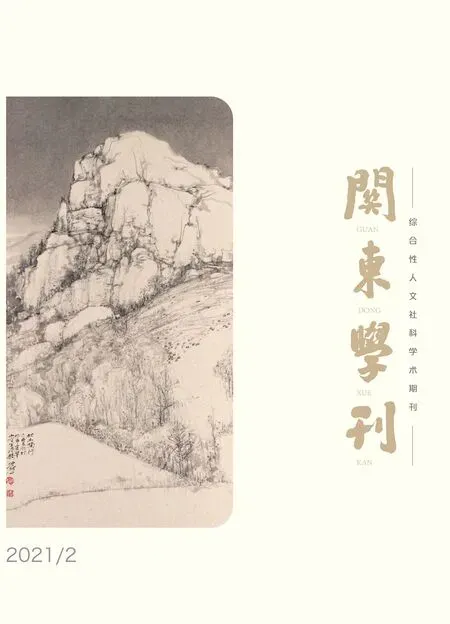从“图像载体”到“影像见证”
——试析幻灯片作为媒介的功用沿革
原平方 梁欣彤
1922年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中说明了其弃医从文的缘由。早年在日本学医时,在微生物课上观看老师播放的、用于消磨“多余光阴”的幻灯片。幻灯片呈现着关于日俄战争的景象,“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彩。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示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被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鉴赏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幻灯片中,国人“麻木的神情”直接而真实地展现在鲁迅面前,从而对其产生刺激,激发其萌生放弃医学转而从文以治疗国人“精神”的念头。此后鲁迅先生在另一篇文章《藤野先生》中也有对于此事的记述。“幻灯片事件”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源”事件,而触发该事件的那张“幻灯片”实际上被影像与历史赋予了“符号性”的意义。应该说,幻灯片作为一种传播媒介,其价值与所载影像及呈现方式密切相关,同时其功能的变迁围绕技术的发展和普及而进行,具有明显的技术偏向性。
一、宣教:新技术初现阶段的原始功能
在探讨幻灯片的功用之前,我们需要对“幻灯片”进行一定的限定。狭义的“幻灯片”定义了幻灯片的物理性质,指的是一种“影片”,即正片、菲林,一般有135和120两种规格,用来冲印或放大相片;而广义的“幻灯片”代表了用于幻灯机放映的“照片”,也就是一种图像媒介。本文所探讨的“幻灯片”则主要基于后者的定义。
探讨幻灯片的功用不得不提到放映幻灯片的装置——幻灯机。幻灯机最初其实是传教士的传教工具。1654年,在德国的犹太籍人基夏尔的记录中第一次提及了幻灯机的发明,幻灯机利用凸透镜成像原理,将图像放大投影于银幕上。早期的幻灯片使用玻璃制成,依靠人工绘制。幻灯机作为传教工具,主要的作用在于将幻灯片中所绘制的有关宗教内容的“画”进行放大展示,便于配合传教的宣讲内容。恰如传播学者麦克卢汉关于媒介的阐释,“媒介即是信息”,什么样的媒介传递什么样的信息,因此幻灯片在传教活动中承担了“图像”的功能。“幻灯片”即是“图像”,“图像”即是“宗教宣扬的信息”,这一阶段的幻灯片主要发挥了宣教功能。
实际上,“幻灯片”的宣教功能也是伴随着新的传播技术诞生的。传教士对于“宣教功能”的需求催生了幻灯机的发明,同时使幻灯片作为一种媒介开始出现。新传播技术产生在早期的社会环境之下,而初现阶段的新兴技术也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正如“幻灯”技术因传教需要而诞生,作为一种新传播技术的“幻灯”技术早期亦被少数占据较高社会地位及技术能力的“传教士”所掌握,其发挥的功能也因此主要以“传教”为主。同理,随着技术的诞生到普及,社会知识阶层始终掌握接触新兴技术的“先机”,此后的幻灯片功能自然成为这一阶层宣传阶层理念、传扬知识内涵的“工具”。
虽然幻灯片随传播技术的发展几经变迁,但是宣扬、教化功能作为“幻灯片”的初始功用仍然是幻灯片的主要功能之一,并延续至今。如在前文中援引的“幻灯片事件”中,幻灯片实际上是课堂上的教学工具,用于“显示微生物的形状”,使之更为清晰直接准确地传授给学生。又如19世纪英国流行的一种演讲形式,“每套幻灯片必须有附带文字形式的讲义,演讲者不仅要放映幻灯片,还要朗读并解说”(1)菅原庆乃:《声音和文字:为“理解”电影的媒体史初探》,《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甚至在今天,传统幻灯片作为一种图像呈现形式,与计算机结合成为被广泛使用的PowerPoint(PPT),在当今的教学活动中依旧发挥着重要作用。由此可见,宣教是幻灯片技术诞生的基本动力,也是幻灯片作为一种媒介最重要的职能。
二、娱乐:传播技术普及下的衍生功能
美国传播学者尼尔·波兹曼在关于“电视”作为媒介对于社会认知、文化结构等产生决定性作用的论述中认为,“文字信息”使人们保持思考的习惯,而“图像”相较于“文字”更为直接,甚至“无需质疑”地向人们传递信息,使人们逐渐失去“思考”的过程,从而开始习惯于直接“理解”。也就是说,对“知识”的获取需求,被“趣味的吸引”代替。“阐释年代开始逐渐逝去,另一个时代出现的早期迹象已经显现。这个新的时代就是娱乐业时代。”(2)[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章艳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同时,波兹曼还认为在电视媒介的影响之下,“教学已成为一种娱乐活动”,为教学所制作的“活动影像”,其教学目的已然不足以覆盖其宣教功能。幻灯片作为影像媒介的作用虽不同于“电视媒介”,但两者均携带着“图像”的属性功能——趣味性带来的娱乐功用。
在鲁迅先生的“幻灯片事件”中,对其产生精神刺激的幻灯片的播放缘由在于消耗“多余的光阴”,显然该“幻灯片”所产生的效果远远不是“娱乐”,但出于“娱乐”的目的而呈现的事实则不可否认。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幻灯片的确具备一定的娱乐功能,“寓教于乐”即是早期幻灯片娱乐功用的集中体现。“1885年11月的上海,教育家颜永京举办了一场幻灯演讲会。这场幻灯演讲会的主题被定为:模拟环绕世界一周。该幻灯演讲会中,放映了英国、德国、日本等国的风景名胜幻灯片。该演讲会结束后大获好评,后来还举行了延长公演。”(3)菅原庆乃、郑炀:《“理解”的娱乐——电影说明完成史考》,《当代电影》2018年第1期。这是在19世纪末上海举办的,与英国流行的演讲形式基本类似的幻灯演讲会。该幻灯演讲会是一场以“理解”为初衷的娱乐盛会:各国风物近乎分毫毕现地以幻灯的形式一张张在观众面前展示,同时现场配以生动的解说。其从形式到内容所呈现的新颖特征足以吸引大部分受众的注意力,同时其“声”与“画”的默契配合很大程度上提升了观众获取信息的趣味体验感,从而发挥了巨大的娱乐功效。
精美的“画片”展示佐以丰富有趣的内容演说,让人联想到一种曾经流行于我国的民间艺术——拉洋片。就幻灯片的此种呈现方式来看,二者异曲同工。而相较“拉洋片”这种艺术形式,幻灯片的娱乐功能更为显著。“洋片又称西洋景,是旧时跑江湖耍玩艺儿的一种。拉洋片需要有一个特质的木箱子,这个木箱子里装着绘制好的图片,人们要用凸透镜来看。洋片的分类有很多,有自然风光,也有人物故事。过去在城市游乐场所、农村庙会,多有从事拉洋营生的人,伴随着富有节奏的锣鼓声,画上的人物景物与悠扬的唱词相结合,别有一番滋味。”(4)李玉川:《拉洋片》,《光彩》1996年第12期。“拉洋片”的展示利用了与“幻灯片”相似的原理,虽然从物理属性来看,“洋片”与“幻灯片”存在性质上的不同,但从呈现形式上看,“拉洋片”这种文艺形式,甚至可以拟称为“透过木箱观看的幻灯片”。从“图像”媒介的角度出发,两者本质上具有相同的功能。可“拉洋片”是一种纯然出于娱乐目的的图像呈现形式。在这种形式当中,“前所未见”的画面是通过猎奇心理吸引受众的手段;曲折离奇而充满故事性的讲演内容,既使受众便于理解“画片”,更增加了受众观看“洋片”的趣味性;富有节奏的“伴奏”、生动多样的“唱腔”均是为了给受众提供更好的观看“洋片”的体验感。“洋片”通过综合性的呈现方式,调动“图像”以引发受众的情感反应。“从形式上看,画片的人物、故事、环境、气氛、色彩、动作,生动逼真。而且在音乐、演唱的配合下,观众的情绪始终被画面所吸引。”(5)刘建勋:《陕甘宁边区的艺术轻骑——新洋片》,《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1期。受众通过观看“洋片”在感性上获得了巨大的愉悦,其作用更甚于理性的“信息”获取,其娱乐功能格外显现。
毋庸置疑,幻灯片所表现出的“娱乐”功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幻灯技术普及发展的一种典型表现。以此看来,作为一种传播技术的“幻灯片”是从早期的被少数阶层所掌握逐渐普及到社会的各个层面。随着幻灯技术的普遍传播,其与“戏剧”“演说”及具有一定审美及趣味性的“图像”艺术等结合使幻灯片自身也衍生出了与其承载内容相关的“娱乐”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幻灯片作为一种与“图像”相关的媒介,其发展受到“图像”传播技术发展的影响,“图像”传播技术的升级也表现在幻灯片的功能转变中。不难看出,“幻灯片”的功能与“拉洋片”所发生的功效有某种类似之处,而以此种形式呈现的“幻灯片”,或者说“幻灯片的播放”,已经初具早期“电影”的雏形。
三、纽带:传播技术升级过程中的过渡功能
关于“图像”的媒介演变是由“静态影像”到“活动影像”的传播技术升级。在传播技术的升级过程中,受众对“图像”的理解接受也相应发生了转变,即从对画报、照片此种“静态影像”的理解到对电影这种“活动影像”的接受,“幻灯片”充当了两者间的纽带,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从19世纪末我国上海的“电影接受史”或可考证幻灯片发挥“过渡”作用的端倪。“在上海,电影接受不仅有游戏性的单线脉络,游戏与文化交错的理性空间也是电影的基盘,不过这样交错混杂的空间却先于电影而出现,它在幻灯片的放映中已然诞生。在这样兼具文化和娱乐的混杂空间里,上海电影‘重视理解’的美学方向也悄然扎根。”在同治皇帝的国丧期间,任何娱乐形式均被禁止,戏剧舞台无戏可“演”便引进了幻灯,从此开启了上海的幻灯放映时代。
如前文所述,上海所举办的幻灯演讲会也佐证了初期的幻灯放映虽是以“知识获取”为主要目的,但却发挥了一部分早期电影的娱乐功能。“1895年,上海格致书院开始举办幻灯讲座,第二年讲座拟定六个主题,内容包括‘芝加哥世博会’‘动物学’等方面。每个演讲兼有娱乐性质的幻灯片作为助兴。”(6)菅原庆乃、郑炀:《“理解”的娱乐——电影说明完成史考》,《当代电影》2018年第1期。在这些讲座的“闲暇”时间里,娱乐性的幻灯片再一次成为“主角”,这说明以教育为目的的幻灯放映,与十年前同在上海、由颜永京举办的幻灯演讲会有着相似的功用。这无疑在很大程度上为文化与娱乐融合奠定了基础。
同一时间,用于演讲会的幻灯机开始在上海各大剧院普及开来。在科学杂志《格致汇编》上出现了向剧场、大讲堂出售幻灯机的商业广告。“这些‘戏迷’群体与科学杂志的读者多多少少会有重叠。科学杂志的读者,也就成为了后来电影的潜在观众。幻灯作为‘理解’娱乐的科学展出为受众所接受,也恰是以‘理解’为内核,其成为孕育上海电影观赏美学的摇篮。”(7)菅原庆乃、郑炀:《“理解”的娱乐——电影说明完成史考》,《当代电影》2018年第1期。也就是说,不同于单纯的“静态图像”,“幻灯片”成组连续的出现,让静态的图像出现了活动的趋势,加之现场解说的配合,幻灯片所呈现的图像虽未“活动”起来,但其连续的动态“信息”已经产生。受众接受并开始理解这种图像呈现方式所释出的信息,从而开始习惯于此种状态的图像阐释方式,因此,当真正的“动态影像”——电影出现后,受众对电影的“接受”与“理解”近乎无碍。可以说,幻灯片在受众接受由“静态图像”向“动态影像”发展的过程中充当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纽带。而幻灯片的这种“纽带”功能,也在“影像”媒介技术升级的过程中发挥了较强的过渡作用。
四、史料与艺术品:传播技术升级后的剩余功能
随着传播技术的升级,比幻灯技术更为先进的“图像”技术不断出现,同时,幻灯技术也有一定程度的升级,幻灯片所具有的更为本质的功能作用也更为突出。幻灯片其本质为一种影像,而影像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客观存在的反映与对事实的真实记录。因此,传播技术的革新在信息生产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在19世纪中叶,伴随着赛璐璐胶卷的出现,幻灯片迎来了新的生产方式——照相移片法。用这种方法生产幻灯片,意味着幻灯片不再是单纯的图像描绘,因为人工绘制的图像即使再精准也终究不能称之为“真实”,但照相移片法使幻灯片开始具有真实记录与反映客观现实的功能,甚至可以作为一种历史的“证明”。
关于传统幻灯片发展最终形态的记述有这样一段文字:“边框由硬纸板制成,起固定作用,表面多以白色出现,一方面统一美观,一方面便于将注释、名称等文字符号落于其上,更加明显。幻灯片的主要部分以透明塑料胶片为材质,将绘画、文字等印刷其上,更有高级品类,把照片等影像如相机胶片一般印制其上,让观者身临其境。”(8)福雨:《收藏光影之色》,《北京纪事》2020年第12期。从我国幻灯片的发展轨迹来看,“其道路跨越了我国比较重要的几个阶段,全民卫生运动、学习英雄事迹、中国动画片典型风格发展、城市标志性建筑崛起……可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幻灯片成为一种大众所接受的载体,记录、见证、传播着光阴的记忆。例如一部名为《看中国》的系列幻灯片,在这部系列幻灯片中,不仅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壮丽山河与风俗人情,还展现了当时的民生状态,更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中国经济民生的发展轨迹。再如一部北京幻灯片厂出品、主题为《吴作仁画选》的系列幻灯片,文字介绍独立成册,与幻灯片的作品展示相辅相成,观者既可领略画家风采,又可详细了解作品背后丰富的信息。几十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再次走进幻灯片的世界,也如参阅历史,或如曾经的青葱岁月重新来过”。(9)福雨:《收藏光影之色》,《北京纪事》2020年第12期。照片是客观世界的真实影像,其被印制在幻灯片上并经由幻灯机投影播放,便完成了对所记录的“历史真实”的客观再现。
不可忽略的是,当幻灯片开始与“照片”产生连接,幻灯片与摄影艺术之间也就存在了必然的联系。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影像艺术家们尝试使用幻灯片来进行艺术创作,摄影艺术家用幻灯片的标准来审视摄影艺术与他们自身以及他们所处的时代之间的关系。在不同光影条件之下,幻灯片所呈现的“照片”与被拍摄物体本身产生了微妙差别,这激发着摄影艺术家利用幻灯片与摄影技术不断进行试验与尝试,发掘幻灯片在视觉艺术领域的可能性。“我想要呈现的东西介于静止与移动的影像之间,我想将这两者之间的空间呈现出来,我实验性的运用移动的影像和运动中拍摄到的影像,并探索通过全景影像(幻灯片)、语言和声音呈现非线性的叙述结构。幻灯片是可以做到在空间中延伸的,方法是让照相机和胶卷做同步运动。影像虽然是静止不动的,但是却包含了照相机、胶卷、拍摄对象随时间先后运动的踪迹。”(10)西格纳·哈曼、周岚:《在静止与移动的影像之间:摄影幻灯片》,《装饰》2007年第12期。摄影师西格纳·哈曼即利用幻灯片进行了这样的艺术尝试。所以,当幻灯片与摄影技术发生关联,其所承担的功能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而这种变化本质上由传播技术的变迁所引发。幻灯片成为“真实再现”的载体,承担了“记忆”的作用,其作为一种“史料”的功用凸显;同时,艺术创造对幻灯片的运用也激发出幻灯片的“图像艺术”价值,这实际上是传播技术升级后幻灯技术所提供的主要功用。幻灯片被升级后的“图像”传播技术所“取代”,其所承担的主要功能变为传播技术升级后的“图像”媒介的“剩余价值”。
五、幻灯片作为传播技术融合的当代功能
计算机的诞生让电子科技充斥整个现代社会。20世纪80年代,企业家罗伯特·加斯金斯意识到了幻灯片商业化的价值。传统幻灯片与现代计算机技术相结合,诞生了如今广为人知的PowerPoint(PPT),即电子幻灯片,也称演示文稿。电子幻灯片通过与幻灯机类似的投影仪进行投影展示,与传统幻灯片的呈现方式几乎无异,但其放映装置的运转动力全然不同,所展示的幻灯片内容也较传统幻灯片更为丰富多元。在融媒体时代,各种媒介均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特征,电子幻灯片发展到今天也具有了一定的融合媒介特征。如今的电子幻灯片所呈现的内容除了传统的文字、图像以外,还包括视频、音频等多种媒介内容。唯一不变的是,电子幻灯片的放映过程仍然离不开解说者的演说。在大部分场景下,电子幻灯片仍呈现出一种“展示”与“解说”的功能。其实,这恰恰也是在融媒体背景下电子幻灯片体现出的最为主要也最重要的功用。
总之,幻灯片在传播技术发展的进程中,以“图像”作为媒介发挥了宣教、娱乐、记录等功能。同时,在与不同技术相融合的过程中,幻灯片也保持并完善和健全了原有的功用,并且发展出诸如艺术创作等新兴功能。由此可见,幻灯片的功能沿革具有典型的技术偏向性。换言之,传播技术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助推并决定着幻灯片功能的变迁,也使得幻灯片成为媒介发展史中一个不可忽略的有机组成部分。
——一种电影考古学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