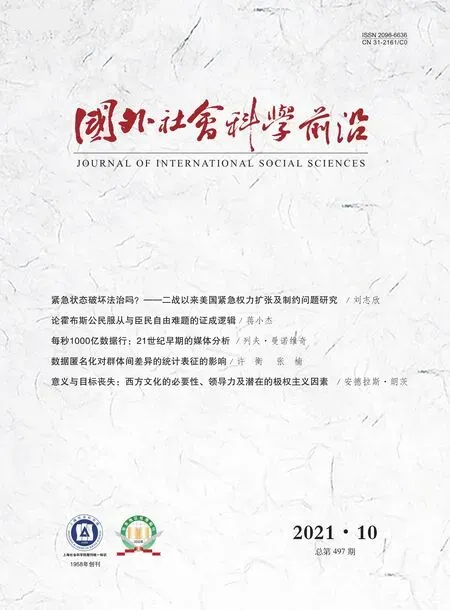沃格林人性秩序基本原理之源:灵魂秩序、城邦秩序与正义秩序
王红曼
埃里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1901—1985)是20世纪一位重要的政治哲学家。在20世纪50年代初,他提出了“新政治科学”的基本原则与研究方法,力图重建政治科学的普遍原理。从世界政治史和政治观念史的双重维度,他考察了人类的诸种“政治秩序”。这种政治秩序是对古希腊政治学传统的回归,同时呈现出人类政治现代性诞生的清晰线索。对沃格林来说,他的任务就是在“历史的长流中辨察出人类用以规范他们个人和社会生存之秩序的符号形式”。1[美]埃里克•沃格林:《以色列与启示》(秩序与历史 卷一),霍伟岸、叶颖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2页。其目的是重新发现真理,以作为对现代危机的补救之道。所以,他认为自己写作《秩序与历史》“是对人类在社会与历史中生存秩序的哲学探究”。1[美]埃里克•沃格林:《以色列与启示》(秩序与历史 卷一),霍伟岸、叶颖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25、2页。在沃格林看来, 政治科学在每个时代都面临的首要问题是:什么是秩序?因此,“历史”的本质所在就是“为秩序真理而战”!2[美]埃里克•沃格林:《以色列与启示》(秩序与历史 卷一),霍伟岸、叶颖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25、2页。他写道:“自从有文字记录以来,处在历史中的人便希冀理解自身的人性,并希冀根据所获洞见塑造有秩序的生活。”3Eric Voegelin, Equivalences of Experience and Symbolization in History, The Collected Works of Eric Voegelin, vol.12,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16.正如沃格林的主要代表作《秩序与历史》的标题,尤其是最后一卷的副标题——“寻求秩序”(In Search of Order)所示,寻求秩序是沃格林通过其学术研究想要达成的目的。4叶颖:《论埃里克•沃格林“新政治科学”的逻辑起点》,《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那么,“秩序”奠基于何处呢?在沃格林的所有著作中,始终贯穿着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的新阐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政治“秩序”哲学,是奠基于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两位哲学家古典政治秩序理论的理解之上。对沃格林而言,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话语体系,是有灵魂者对于实在秩序的探究,这也是组织成了希腊知识模式的基本特征。因此,他根据两位哲学家所处的古希腊城邦的社会本性和依据他们的相关文本,分别考察了灵魂秩序、城邦秩序、正义秩序,从而阐述了他们的古典政治哲学体系里所蕴含着的人性科学的基本原理和核心内容。力图表明在历史—政治进程中,他们是人类秩序的探索者,是古典政治秩序的奠定人,他们致力于阐释实在秩序的结构,进而探究能够将世间万物存在着的普遍联系归之为一般性的原则。而这些一般性的原则是构成沃格林政治哲学的基础。因此,准确地把握沃格林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古典政治秩序理论的理解,既可使我们找准在当代语境中理解沃格林政治哲学的学理路径,又能让我们明白在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框架中对古典政治秩序源头的追溯性阐释意义。
一、灵魂秩序
沃格林将“秩序”作为自己学术研究的核心问题,倾其一生追索人类重建秩序的可能。这一努力曾被概括为“重演柏拉图对雅典危机的反应”5[美]埃里克•沃格林:《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秩序与历史 卷三),刘曙辉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5页。。于是,沃格林宣布自己处于“柏拉图的立场”,并试图成为“现代柏拉图”。他要求自己从柏拉图那里承传哲学范式,并在他自己的生命和工作中得到彰显。他公开、明确的姿态就是以真理为业,并抵制腐败的哲人和教师。6[美]埃利斯•桑多兹:《沃格林革命:传记性引论》,徐志跃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12年,第289页。沃格林认为自己与柏拉图当时的处境相似。柏拉图当时的“处境”是身处于与雅典腐败的批判性对立之中,是一个“失序”的时代。社会危机的经验,对柏拉图的历史意识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一危机继马拉松和埃斯库罗斯的雅典“大觉醒”之后发生,在修昔底德的散记或报道(Syngraphe)中得到公正的表达,并在对苏格拉底的司法谋杀中达到最糟糕的地步。与以色列启示所创造的历史形式不同,希腊历史形式唯独是逐渐建立的。其最大的清晰性之实现,乃是经由对失序的经验和理解,该失序标志着希腊文明一个阶段的终结。16[美]埃利斯•桑多兹:《沃格林革命:传记性引论》,徐志跃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12年,第118~150、147页。因此,柏拉图的哲学体系,用沃格林的话来说,就是“身历无序之经验,去追问真正的秩序”。2[美]埃里克•沃格林:《城邦的世界》(秩序与历史 卷二),陈周旺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3、4页。在《秩序与历史》第一卷的导言中,他写道:“朝向真理的运动,始于人意识到自己生存于非真理之中。”3[美]埃里克•沃格林:《以色列与启示》(秩序与历史 卷一),霍伟岸、叶颖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25页。在此意义上,柏拉图遂成为一切真正哲学努力的典范。而沃格林则是将这种希腊经验的基本结构,用来作为建构自己新政治科学体系的主题。由此可见,沃格林是将柏拉图的哲学理解为“自身努力的一个先声”。4[美]埃里克•沃格林:《城邦的世界》(秩序与历史 卷二),陈周旺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3、4页。
沃格林强调,“正是柏拉图发现了‘人类学原则’,根据此原则,城邦是大写的人,与神话的宇宙论原则(社会是小写的宇宙)之间存在着张力。”5[美]埃里克•沃格林:《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秩序与历史 卷三),刘曙辉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2、121、328、4页。秩序与失序是灵魂最重要的境况。正是灵魂的秩序与失序,在生存辩证法中孕生和反省着社会之秩序和失序,同时反映出在历史过程的节律中,人与存在真理是合拍还是偏离。正是柏拉图以其抵抗他所在时代的社会失序之举,发现了“社会的实质是人的心”,“社会可以摧毁一个人的灵魂,因为社会的失序是其成员心中的病”。灵魂的“疾病”被柏拉图指称为灵魂对存在真理的无知。建议的救治方法是通过皈依,“摆正人与上帝的关系”,让“‘整个灵魂’从对上帝真理的无知,从对不定游移的事物的意见,转向存在的知识”。6[美]埃利斯•桑多兹:《沃格林革命:传记性引论》,徐志跃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12年,第118~150、147页。沃格林认为,《国家篇》尽管是作为关于个人正义生活的对话而开始,事实上,也可把它看成为对社会中秩序和失序的探究。7[美]埃里克•沃格林:《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秩序与历史 卷三),刘曙辉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2、121、328、4页。
沃格林一再强调,哲学起源于井然有序的灵魂有意识地对抗周遭社会的失序。他坚持认为,这对于恰当地理解希腊哲学是根本的。所以,他说,“柏拉图政治学的重要经验是时代意识。”8[美]埃里克•沃格林:《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秩序与历史 卷三),刘曙辉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2、121、328、4页。这种时代意识,也就是历史意识,致使柏拉图并不打算提出“一种人的哲学”,而是具体地“探究人的灵魂,灵魂的真正秩序最终依赖于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即爱智慧(sophon)”。9Eric Voegelin, The New Science of Politics, with a new foreword by Dante Germino, 1952;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p. 61; The New Science Of Politics, The Collected Works of Eric Voegelin, vol. 15,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2000.因此,沃格林在《秩序与历史》的第一卷(出版于1956年),就开始提醒人们尤其应该铭记柏拉图,因为柏拉图的哲学代表的即是秩序本身。随后在《秩序与历史》的第二卷中,沃格林向我们呈现出这样一个柏拉图——他远非一个与经验现实没有联系的理想主义者,而是一个“精神的现实主义者”。沃格林含蓄地写道,“现代阐释者把柏拉图对精神改革的迫切吁求理解成‘理想政制’(ideal constitution)的理性蓝图是一个不幸的误解。”《国家篇》应该被解读成“以哲学家的精神权威”向雅典人发出的一个吁求。10[美]埃里克•沃格林:《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秩序与历史 卷三),刘曙辉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2、121、328、4页。
按照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的构想,社会的真正秩序依赖单个人的真正秩序;真正的个人秩序又进而依赖灵魂的建构;而灵魂的建构,其有序或无序,是透过某些经验而得以看见的,这样的经验在一个敏感的人为了神性智慧而充满爱意地求索实在的过程中得到象征化。于是,“上帝是尺度”是决定性的,所以,人类学原则又被柏拉图以“神学原则”所补充。1[美]埃利斯•桑多兹:《沃格林革命:传记性引论》,徐志跃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12年,第118~119页。因为,柏拉图对其当下的实在始终保持着敏锐的开放性,并经由观察宇宙秩序通过灵魂而对自身变得明晰起来。除了那个由生成又衰亡的万物构成的过程之外,实在还包含更多的内容——宇宙是神圣的,而在流变与持续的节律之上,兴起了被称为“人”的那样一个东西,这种神性实在能够在他心灵中变成神的显现。
到了亚里士多德那里,他早期仿于老师柏拉图的文采,其中的对话篇《灵魂论》大体承袭了柏拉图的《斐多篇》中的有关于灵魂的观念和思想。2[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灵魂论及其他》,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2、44页。因此,亚里士多德的人性理论即是通过苏格拉底—柏拉图揭示出来的灵魂秩序作为经验基础。3[美]埃里克•沃格林:《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秩序与历史 卷三),刘曙辉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398、348、397页。他在《灵魂论》开篇就写道“研究灵魂是一个困难问题,却具有崇高价值”。4[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灵魂论及其他》,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2、44页。但是,在《灵魂论》中,他对灵魂的研究更多是从自然科学角度展开探究。对灵魂与政治秩序之间关系的讨论则是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他主张,“政治家对灵魂本性更需要了解。”5[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32、22页。但是,和柏拉图相比,他的灵魂论更具实践性。他说:“灵魂的善是最恰当意义上的、最真实的善。而灵魂的活动也应当归属于灵魂。”6[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32、22页。沃格林认为,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开始把政治学定义为人类行为的科学。7[美]埃里克•沃格林:《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秩序与历史 卷三),刘曙辉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398、348、397页。并且,“人的善是灵魂与自身卓越相一致的功能。”所以,在沃格林看来,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科学原则,主要是为了确定人的行为科学中“什么是至善”,而人的至善本性对于体制秩序和社会秩序提供了何种秩序经验?所以,亚里士多德始终致力于探索人性完美秩序的条件,提出了著名的政治理论,即人性秩序是构成社会秩序的基石;换言之,“政治社会是人性实现的领域。”8[美]埃里克•沃格林:《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秩序与历史 卷三),刘曙辉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398、348、397页。
关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灵魂秩序论,沃格林写道:
“事实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式的分析恰恰就是肇始于对存在的这种真正洞见,而绝对不是肇始于对自身之可能性的思考。可以说,正是这种对于存在的洞见激发了这个分析的过程本身。在政治科学的奠立之中,一个关键性的事件就是达到这样一种哲学认识:此世之中可觉察的存在之各层面被一种超越的存在之源及其秩序所逾越。而这个洞见本身是以人的灵性灵魂走向超验的神圣这一场真实运动为根基的。正是对存在之超世本源的爱的体验之中,在对智慧的热爱之中,在对善与美的欲爱之中,人成为了哲学家。正是从这些体验之中产生出了存在之秩序的意象。” 9[美]埃里克•沃格林:《没有约束的现代性》,张新樟、刘景联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3~24页。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当灵魂向超验领域开敞时,人认识到了“存在之秩序”,从而产生敬畏。随着灵魂的觉醒,随着对存在之秩序的确认,人开始追问正义,开始向流俗和偏见宣战。10陶杨华:《现代性的兴起与主权的政治想象——关于身份政治的哲学思考》,《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0年第5期。可见,沃格林表明了古典政治哲学是如何兴起的——希腊思想家运用心灵的智慧创造了根据井然有序的灵魂对实在做出新的解释。
二、城邦秩序
沃格林认为,“如果我们想了解城邦的结构,我们必须了解进入城邦构成中的人性。”1[美]埃里克•沃格林:《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秩序与历史 卷三),刘曙辉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397、146、149、149、55~56、144、147、51页。正如柏拉图所言,城邦乃是一个大写的人。因此,柏拉图认为,人的灵魂秩序的发现是哲学家探求的任务。沃格林认为,“当柏拉图提出将哲学家灵魂的秩序作为城邦中秩序‘本性’的标准时,他并没有超出经验观察。相反,他使用了我们仅有的经验知识。只有当城邦的秩序‘被使用神的范式的画家’描绘时,城邦才会处于幸福的状态。那个‘画家’是爱智者(philosophos),通过与神的秩序(theios kosmios)的联系,在人被允许的尺度上,他自己已经变得有秩序而且如同神灵。”2[美]埃里克•沃格林:《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秩序与历史 卷三),刘曙辉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397、146、149、149、55~56、144、147、51页。由此可见,在柏拉图的政治思想中,城邦谱系的建构从一开始就以最好的神谱风格开始,也就是从由秩序来协调的基本力量格局开始。3[美]埃里克•沃格林:《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秩序与历史 卷三),刘曙辉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397、146、149、149、55~56、144、147、51页。在柏拉图哲学语境下,神的秩序就是宇宙秩序、智慧秩序、正义秩序,这些秩序一旦进入哲学家的心灵,即会赋予哲学家灵魂秩序,哲学家再将这种灵魂秩序用来治理城邦,城邦的政制才会有良好的秩序。因此,柏拉图认为“哲学家的城邦是美好的或美丽的城邦”。4[美]埃里克•沃格林:《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秩序与历史 卷三),刘曙辉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397、146、149、149、55~56、144、147、51页。因此,柏拉图被迫宣布,“只有崇拜正确的哲学能够使人们识别出城邦和个人生活中正确的东西。”沃格林写道:这种思想到了《法律篇》时,达到了最高潮,即智慧秩序成为了类似于宇宙秩序的东西。5[美]埃里克•沃格林:《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秩序与历史 卷三),刘曙辉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397、146、149、149、55~56、144、147、51页。
沃格林对希腊城邦历史意识的重构,典型地体现在他对柏拉图《国家篇》解读的意义上。在他看来,《国家篇》就是探索“什么是好的城邦?”他认为,这是一种认知的探究,“为了实现建立好城邦的目标,建立者必须知道什么是好城邦,必须拥有找到好城邦的方法。”他写道,“柏拉图对目标的阐明开始于《国家篇》这个领域的分析。”6[美]埃里克•沃格林:《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秩序与历史 卷三),刘曙辉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397、146、149、149、55~56、144、147、51页。在《国家篇》里,柏拉图探究了人的品质与城邦的政制之间的关系。当柏拉图谈到好城邦是“根据本性建立的城邦”时,他所意指的含义变得更加明确。在《申辩篇》《高尔吉亚篇》以及在后来的对话作品——如《政治家》《蒂迈欧篇》《法律篇》中,“本性上”的秩序是城邦秩序的秩序理论以更大的强度占据柏拉图的思想。7[美]埃里克•沃格林:《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秩序与历史 卷三),刘曙辉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397、146、149、149、55~56、144、147、51页。换言之,柏拉图主张,人的灵魂秩序是构成城邦秩序的基础。
同样,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体系中,在《天象论》《形而上学》《政治学》中依次可见理智与精神洞见的循环,以及对“成熟的人的权威”的沉思。8[美]埃里克•沃格林:《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秩序与历史 卷三),刘曙辉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397、146、149、149、55~56、144、147、51页。在继承柏拉图思想的基础上,他认为“最好城邦的特征,即‘标准’,与城邦的本性紧密相连,因为最好的城邦是本性得到完美实现的城邦。”在《政治学》第二卷中,他提供了从城邦本性的探究到城邦完美实现研究的转变。在《政治学》的结构中,第三卷占据中心地位,在卷首提出了一个核心问题:“城邦到底是什么?”随着问题的思考与展开,他回答:城邦是公民的大众。”亚里士多德的目标就是要寻求城邦,因为它是“政治家和立法者活动”的目标。在沃格林看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城邦秩序建构原则,已经发生转变,9即标志着从观念论向实在论的转变。但是,仅仅拥有理性秩序的法律,就是政治秩序的保障吗?事实上,在《法律篇》全书中,柏拉图处处讨论人的灵魂需要神性的参与。沃格林在一定程度上对亚里士多德的这一转变进行了批判。尤其是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他通过使体制成为秩序的形式来缩减自己的经验观察。沃格林写道,“亚里士多德对城邦本性的探究,不是朝社会及其结构的历史进程定位,而是朝城邦的最好秩序定位。尽管亚里士多德承认他最好城邦的类型适应成熟人社会的历史条件,但是他仍然坚持他的范式表达了城邦的本质。”因为亚里士多德认为,“立法者需要这种实在的彻底的经验知识。”1
沃格林为何特别强调亚里士多德“成熟的人”的德性对于城邦秩序的重要性。在识读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关于“政治正义”的表述时,沃格林具体解释了他所理解的“成熟的人”即“明智者”(phronimos)的德性。2[美]埃里克•沃格林:《记忆:历史与政治理论》,朱成明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57~164页。这意味着,“成熟的人”的德性最终体现为在历史的具体生存处境中践行正确的言行。虽然沃格林用了“成熟”来理解spoudaios,但是我们应该说,所谓的“成熟”意味着智性正确地追求“高尚”并践行高尚的正确。否则,一个人无论智性或超越意识有多高,都谈不上生存德性方面的成熟。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完全可以把spoudaios译为“高尚之人”。3刘小枫:《从“轴心时代”到“天下时代”——论沃格林<天下时代>中的核心问题》,《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然而,怎么样才能算是一个“高尚之人”呢?可以说,关于人的完善,亚里士多德看到了柏拉图所看到的,而且看到的比他更多。然而,由于人的完善并不是自明的,也不易通过明确的证明来得到解说,所以,在《尼各马可伦理学》里,亚里士多德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什么是人的善?于是,作为苏格拉底—柏拉图实践哲学的典型追随者,他把政治哲学继续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如果说亚里士多德是“政治科学的奠基者”,那么,这是“因为他是道德德性的发现者”。4Leo Strauss, The City and Ma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8, p. 27.在亚里士多德那里,道德德性是为行动提供适当原则的;这些原则是正义和美的。5[美]伯格:《尼各马可伦理学义疏——亚里士多德与苏格拉底的对话》,柯小刚译,华夏出版社,2011年,第6页。因此,特别有意思的是,沃格林将《秩序与历史》的第三卷取名为《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全书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柏拉图;第二个部分是亚里士多德,然而,在本卷的第二部分一开始的第七章的标题却是“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意在表明他们之间有承继关系的同时,也表明亚里士多德在某种程度上对柏拉图的超越。沃格林写道:
一旦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灵魂秩序与城邦秩序被创造和阐明,结果可以作为学说来传播。我们现在知道什么是“最好的”,这种知识可以设想“准绳”或“标准”的形式,……这些标准来自柏拉图的标准。亚里士多德知道“理论生活”是“最好的”,所以城邦是“最好的”,其中可以实现理论生活的幸福。城邦幸福与人的幸福一致。通过标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与柏拉图的政治学连在一起,这种连接从未破裂。然而,柏拉图的问题得到修改。对于柏拉图而言,形式是超验的,他的问题是理念通过哲学家及其圈子的心灵在历史现实中的化身的问题。对于亚里士多德而言,形式内在于现实之中,城邦的本质以与动物或蔬菜的本质一样的方式内在于现实之中;然而,政治生存同动物或蔬菜的生存区别开来,因为理性的人类行为是实现城邦本质中的一个因素。6[美]埃里克•沃格林:《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秩序与历史 卷三),刘曙辉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378、336~337页。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沃格林认为,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和《政治学》是对柏拉图政治思想发展的延续,同时也是《法律篇》的老师。因为,在沃格林看来,柏拉图是“好城邦的建立者”,而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城邦是一种内在——世界的实体,政治科学是城邦本质最大化实现的艺术。”1[美]埃里克•沃格林:《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秩序与历史 卷三),刘曙辉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337、368、369、397、62~63、74、75页。可以说,亚里士多德对沃格林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甚至可以说,他是一位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政治科学家”。
在沃格林看来,希腊人和罗马人比起先知、犹太人和基督徒,对秩序共存的问题知道更多,也更为敏感。2[美]埃里克•沃格林:《城邦的世界》(秩序与历史 卷二),陈周旺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81页。因此,亚里士多德对“人性与政治”的解释,意味着真正有美德的人就是“真正成熟的人”。这样的人对于城邦秩序的构建有重要意义。所以,沃格林认为,“亚里士多德的建构总的来说忠于柏拉图的人类学原则,如在《国家篇》中,城邦的美德与人的美德平行发展。因此,城邦的勇敢、正义和智慧,与允许我们说个人是正义的、智慧的或节制的品质具有相同的含义。”3[美]埃里克•沃格林:《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秩序与历史 卷三),刘曙辉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337、368、369、397、62~63、74、75页。沃格林指出,城邦的科学(即城邦的政治科学)是建立在城邦本性的基础之上。所以,城邦以最高善为目的,人的本性在城邦中找到实现,“政治社会是人性实现的领域。”4[美]埃里克•沃格林:《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秩序与历史 卷三),刘曙辉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337、368、369、397、62~63、74、75页。换言之,城邦秩序被生活于其中的人性秩序历史地构建。
三、正义秩序
在希腊哲学的古典意识中,正义秩序是一个核心概念,并具有绝对的确定性。柏拉图的《高尔吉亚篇》《国家篇》《斐德罗篇》《政治家篇》《蒂迈欧篇》《克里底亚篇》和《法律篇》等作品,始终贯穿着对“正义秩序”的哲学思考。在《秩序与历史》第三卷第一章,沃格林在确定苏格拉底审判的中心问题时,写道:“秩序神圣的再生力量由苏格拉底传给了柏拉图。”而苏格拉底灵魂的象征力量即是正义秩序。在沃格林看来,苏格拉底的戏剧是柏拉图创造的一种象征形式,作为交流和扩展由其主角建立的智慧秩序的手段,这是埃斯库罗斯和柏拉图对社会和灵魂的理解方式。他们认为,社会是灵魂的秩序,灵魂是社会的力量秩序。灵魂秩序是社会秩序的源泉,两种秩序的建构是相同的。强调苏格拉底悲剧力量冲突的秩序观念,是智慧和正义的胜利。正义秩序的表达是通过苏格拉底之死的力量流入对话。因此,沃格林说:“在《斐多篇》中,死亡成为治愈地球上患病灵魂的净化力量。”5[美]埃里克•沃格林:《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秩序与历史 卷三),刘曙辉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337、368、369、397、62~63、74、75页。
到了《高尔吉亚篇》,柏拉图直接“向腐败社会宣战”。6[美]埃里克•沃格林:《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秩序与历史 卷三),刘曙辉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337、368、369、397、62~63、74、75页。通过同代人对所列话题的态度,柏拉图描述出他们的特征。这些话题,主要是:修辞的功能、正义的问题、关于做不义的事情和忍受不义哪个更好的问题、不义灵魂的命运。沃格林认为,柏拉图这部作品的主题就是生存问题,尤其是“生存的正直”问题,目的是要提醒我们,“在一个颓废的社会,荒谬的知识分子是精神的敌人,有足够的能力从身体上去谋杀精神的代表。”7[美]埃里克•沃格林:《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秩序与历史 卷三),刘曙辉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337、368、369、397、62~63、74、75页。在《高尔吉亚篇》中,波吕斯对苏格拉底的嘲笑暗示出他个人的可耻是人性的尺度。1[美]埃里克•沃格林:《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秩序与历史 卷三),刘曙辉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77、90、107、114、115、121页。因此,通过对话, 柏拉图揭示“做不义之事而不遭受惩罚最糟糕。”腐败秩序即是不正义。正义秩序是一种自然法则,它来源于宇宙秩序。沃格林评价说:“《高尔吉亚篇》的神话是柏拉图最早关于秩序与历史哲学的诗歌。他实际上是在讲述‘真理’。”2[美]埃里克•沃格林:《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秩序与历史 卷三),刘曙辉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77、90、107、114、115、121页。
因此,对于柏拉图来说,人与社会的正当秩序是善在历史现实中的具体化。在《国家篇》的开场白中,有关于“老一代的正义”“中生代的正义”“智者的正义”,即通过不同年龄段的人与苏格拉底的对话,从而展开探究正义与正当秩序的本性。在《国家篇》中,他毫不妥协地坚称,“灵魂过着他们曾经为自己选择的生活。”柏拉图的理由是,“当他认识到让灵魂堕落并使它更不正义的生活方式是坏的,而将灵魂向上引至更高的正义状态的生活方式是好的,他就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当一个人向下走到冥府,他必须带着一种坚定的信念:生活的质量必须由它能在灵魂中发展正义美德的适当性来判断。”因此,在《国家篇》中,柏拉图声称:要想知道正义这类具体的理念,必须知道善的理念。3[美]埃里克•沃格林:《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秩序与历史 卷三),刘曙辉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77、90、107、114、115、121页。同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也是持同样观点:“选择比行为更能判断一个人的品质。”4[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64~65页。沃格林对此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写道:
在《国家篇》中,柏拉图使用了通过阐明善恶来指明道路的概念对子。他的哲学并不是存在于社会真空之中,而是与智者相反。正义不是被抽象定义的,而是与不正义所采取的具体形式相对。城邦的正当秩序不是作为“理想状态”被呈现,正当秩序的要素是在与周围社会中失序要素的具体对立中发展起来的。灵魂中美德的形式在与灵魂中失序的诸多形式的对立中生长。5[美]埃里克•沃格林:《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秩序与历史 卷三),刘曙辉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77、90、107、114、115、121页。
沃格林认为,在柏拉图所有的概念对子中,第一对概念涉及正义与不正义的本质。比如:灵魂中的正义和不正义是身体上的健康和疾病;健康被定义为身体各部分之间自然秩序的确立;疾病被定义为各部分之间支配和从属的自然秩序的扰乱;灵魂的各个部分都履行各自的职能,不干涉其他部分的职能,以这样一种方式在灵魂中确立自然秩序被叫做正义;更广泛地来说,美德是灵魂的健康、美和康乐;邪恶是灵魂的疾病、丑和虚弱。在沃格林看来,柏拉图倾向于将正义的含义缩小到灵魂和城邦的正当秩序,而技艺层面的劳动分工只是正义的一个形态,是“正义的影子”。6[美]埃里克•沃格林:《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秩序与历史 卷三),刘曙辉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77、90、107、114、115、121页。沃格林明确表态:“如果人们想理解柏拉图的秩序科学,他必须很好地理解紧凑意义上的‘哲学家’术语的含义,即在它出现于抵制行为的时刻的含义。社会的实质是心灵,这一洞见产生于哲学家对摧毁他灵魂的社会的抵制。社会能够摧毁人的灵魂,因为社会的失序是其成员心灵上的疾病。哲学家在自身灵魂中体验到的疾病是强加在他身上的周围社会心灵中的疾病。因此,灵魂中健康和疾病的诊断同时也是社会中秩序与失序的诊断。”7[美]埃里克•沃格林:《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秩序与历史 卷三),刘曙辉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77、90、107、114、115、121页。
根据沃格林的分析,《国家篇》将灵魂投射在社会的背景之上;《蒂迈欧篇》将灵魂投射在更大的宇宙背景之上。在《国家篇》中,心灵为城邦提供秩序模型;在《蒂迈欧篇》中,心灵为宇宙提供秩序模型。关于柏拉图的秩序科学,在沃格林看来,“存在的领域现在被心灵渗透到它们的极限。就形而上学的建构而言,没有一个宇宙角落可以留给物质主义者作为在原则上否定心灵秩序的立足点。宇宙秩序与城邦秩序和人的秩序一起变得具有相同本质。”1[美]埃里克•沃格林:《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秩序与历史 卷三),刘曙辉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232~233、298~299、317、341~356、364、368、369、397页。
沃格林认为,在《法律篇》的第一部分,柏拉图表达了将他与智者时代分离开来的一句话标志着秩序科学的开端,这句话就是:“对我们而言,神是万物的尺度,是真的尺度;如他们所说,更是人的尺度。”在沃格林看来,柏拉图这句话是对普罗泰戈拉“人是万物的尺度”有意的对立。沃格林写道:“柏拉图仔细地澄清了两个原则之间的对立。他求助于一句古老的谚语:神将一切开端和结尾都掌握在自己手中。他直线地向目的地前进,如他的本性一样;正义女神一直在他身边,准备惩罚那些不服从神的法令的人。那些想和谐生活的人将紧密地、谦逊地跟随在正义女神的序列中。”在《法律篇》第二部分中,人的心灵得到安置。心灵是人身上最神圣的部分,其等级高于身体善和物质善的见解是人在其中把自己“比作‘神的行为’的第一个条件。人必须在灵魂中建立节制和正义的真正秩序;然后他必须将这些原则应用于个人生活的秩序、共同体的内在秩序以及与城邦中的陌生人和外邦的关系”。2[美]埃里克•沃格林:《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秩序与历史 卷三),刘曙辉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232~233、298~299、317、341~356、364、368、369、397页。
到了亚里士多德时期,沃格林说:“作为柏拉图—苏格拉底意义上的生活方式,哲学已经塑造了亚里士多德的灵魂,痕迹是抹不掉的。”3[美]埃里克•沃格林:《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秩序与历史 卷三),刘曙辉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232~233、298~299、317、341~356、364、368、369、397页。《政治学》和《尼各马可伦理学》充分地说明了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是有理论和实践(phronesis)4希腊文Phronesis,汉译为明智、实践智慧等。两种政治智慧的。这两种智慧都以人的善和人的美德为原则,美德是性格的一种品质,这种品质通过教导和实践被反复灌输直至它成为一种习惯。拥有卓越品质的人在过度与不足之间选择中道的习惯,就会养成正义、节制、勇敢、慷慨、庄严和好脾气。因此,在沃格林看来,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智慧和实践智慧都包含有一个“审慎科学”,这种审慎科学可以按照逻各斯制定行动原则(例如中道),审慎科学可以发展为对现实中逻各斯的阐述。一个人如果是审慎的,那么他就会对其所做的选择有一个平衡判断。真正有美德的人是《尼各马可伦理学》意义上的成熟的人。人的善是灵魂与自身卓越相一致的功能。5[美]埃里克•沃格林:《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秩序与历史 卷三),刘曙辉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232~233、298~299、317、341~356、364、368、369、397页。所以,沃格林说:“在亚里士多德的描述点上,他谈到了人与人之间秩序的最终来源。社会的人的秩序是通过人参与神圣的理智创造的社会中的正义秩序而被实现,并且在某种纯理智秩序的潜能将在居于社会的人的灵魂中被实现。正义最终被建立在理智和友爱的基础上。”6[美]埃里克•沃格林:《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秩序与历史 卷三),刘曙辉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232~233、298~299、317、341~356、364、368、369、397页。
亚里士多德的正义秩序是建立在对“人性与政治”的解释基础之上,意味着真正有美德的人就是“真正成熟的人”。这样的人对于正义秩序的构建有重要意义。所以,沃格林认为,“亚里士多德的建构总的来说忠于柏拉图的人类学原则,如在《国家篇》中,城邦的美德与人的美德平行发展。因此,城邦的勇敢、正义和智慧,与允许我们说个人是正义的、智慧的或节制的品质具有相同的含义。”7沃格林意在说明,正义秩序与城邦的科学(即城邦的政治科学)是建立在人性秩序的基础之上。所以,城邦以最高善为目的,人的本性在城邦中找到实现,“政治社会是人性实现的领域。”8[美]埃里克•沃格林:《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秩序与历史 卷三),刘曙辉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232~233、298~299、317、341~356、364、368、369、397页。换言之,正义秩序被生活于其中的人的灵魂秩序历史地构建。所以,沃格林写道:
在我们对社会秩序的前科学式参与中,在我们关于对错、正义与否的前科学经验中,我们会感到自己有一股渴望,以求深入到对秩序的根源及其效力的理论性理解之中,我们也许会在努力过程中得出这样的理论,即关于人类秩序的正义取决于这一秩序参与到柏拉图的善,或亚里士多德的努斯(Nous),或斯多葛的逻各斯,或托马斯的永恒理性之中。
四、结 语
在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古典政治秩序理论的历史分析中,沃格林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理论洞见。更确切地说,是一位杰出思想家对西方文明如何导致现代性的诊断。蕴含在沃格林新政治科学原则中的古典政治秩序的主要内容与基本逻辑,不仅是一种基于普遍人性的政治理论,更是基于更广泛、更深刻的历史理解。因此,沃格林说:“人在政治社会中的存在是历史性的存在,一种政治理论若要能洞悉其理念的话,就必然是一种具有历史性的理论。”1Eric Voegelin, The New Science of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2, p. 1.在沃格林政治哲学语境下,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古典政治秩序所包含的灵魂秩序、城邦秩序和正义秩序,是奠基在对“人的秩序”的理解之上,是对古典政治治理理论的一种哲学与历史的回应。沃格林的目的,是要提醒我们不要忘记古典政治哲学中的宇宙秩序、心灵秩序与政治秩序之间的关系。只有获得对宇宙神圣秩序的理解——这包括对我们的(理性)自我的理解,我们才会获得对政治科学的新的理解。这也是沃格林提出“重建政治科学”的本质涵义。他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秩序科学的认识,不仅“映衬出一个出色而细腻的心灵,展示出很少几位学者可以匹敌的学问”。2[美]埃利斯•桑多兹:《沃格林革命:传记性引论》,徐志跃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12年,第24、152页。同时,也是他提醒我们恢复圆满人性的重要性。毕竟,对人性的回归,是哲学的使命。正如沃格林所说:“人心秩序就是哲学本身。”3[美]埃利斯•桑多兹:《沃格林革命:传记性引论》,徐志跃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12年,第24、1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