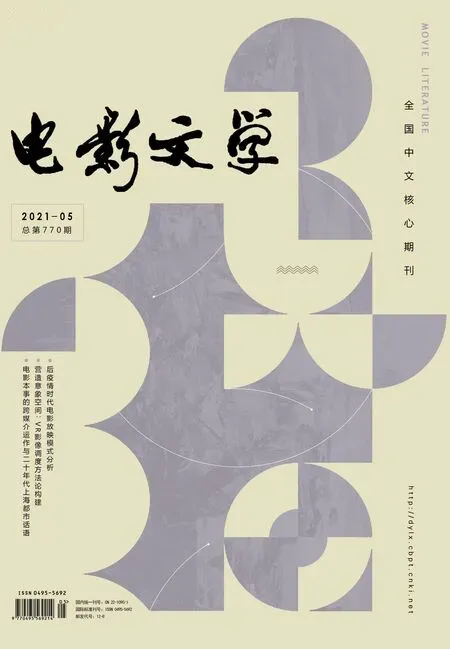影片中的“对位阅读”
——论迪士尼真人版电影《花木兰》中的文化矛盾
邓春霞/Deng Chun Xia
继2020年9月4日真人版电影《花木兰》在流媒体平台“Disney+”上上线后,11日,这部被国人期待已久的迪士尼公主片也终于在中国大陆上映。然而比之于迪士尼公司此前的真人版电影,如《爱丽丝梦游仙境》(2010)、《灰姑娘》(2015)、《美女与野兽》(2017)和《克里斯托弗·罗宾》(2018)等,此次《花木兰》在国内的票房和口碑等都不算好。虽然前期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资本,但它的豆瓣评分仅5.0分,甚至一度跌至4.8分,远低于其同名动画片(7.9的评分)。“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究竟木兰与木兰之间有着怎样的差异?又是何者造成了此种差异?本文试以爱德华·萨义德理论中的“对位阅读”法进行解读。
一、主题的对位
如当代理论家萨义德在其著作《文化与帝国主义》中所言:“没有任何人有认识论上的优势,能够不受当前关系所附带的利益与牵扯的羁绊而对世界做出判断、评价和解释。”任何文化文本的创作是如此,真人版《花木兰》的呈现也是如此,即使它改编于1998年的同名动画片,即使它的最初原型终究始于中国北朝的《木兰辞》,但它早已与当初的木兰相去甚远了。
诚然,从南北朝至今,我国历史上关于“花木兰”的改编与重塑几乎从未停止。如近几十年来的影视作品就有:杨丽菁饰《天地奇英花木兰》(1996)、陈妙瑛饰《花木兰》(1998)、袁咏仪饰《花木兰》(1999)、赵薇饰《花木兰》(2009)、侯梦瑶饰《花木兰传奇》(2013)和刘戴恩饰《小戏骨花木兰》(2017)等多个版本,且她们也都是真人饰演。那么为何《花木兰》(2020)就遭到了国内众多观众的“口诛笔伐”呢?是演员刘亦菲演技不到位吗?也并非如此。的确,如重庆师范大学贺滟波女士所言,受近年来数字化语境的影响,“花木兰”这一传统文化符号在文本的再生产过程中遭到了当代人的解构与戏谑,从而使木兰的形象有了矮化和世俗化的趋势。但在从北朝至今的1000多年的木兰形象传播史中,经由《木兰辞》和《雌木兰替父从军》(徐渭明杂剧)等文学文本的稳定传承,人们对木兰形象的接受早已形成了这样一种相对稳固的基本审美倾向:替父从军的“花”家姑娘木兰是能文能武、讲求忠孝,最终还乡结婚的,“家”(家族)与“国”始终是其文本的核心,甚至在明以后,“国”隐隐还有赶超“家”的趋势。
表面看来,迪士尼真人版《花木兰》的确没有脱离木兰“姓花+能文能武+替父从军+忠+孝+还乡/结婚”这个基本主题,但正如牛马易头、表里不一,影片中西方资本主义式的文化思维模式早已渗透其中。也正如知乎审美类话题活跃回答者思妤的揶揄:这片不应该叫《花木兰》,应该叫《凤凰传奇》(如图1),讲述的是一代气功大师花木兰的故事。

图1 来自知乎思妤
的确,《花木兰》(2020)在影片中预设了一个重要的前提——“气”,不被世俗所容的“气”。剧中的反派仙娘/女巫(巩俐饰)正是因为拥有不被世俗所承认的“气”而被流亡,只有柔然王愿意给予她容身之地,所以她才被迫加入了步利可汗的队伍之中,甚至不惜成为他的专属奴隶(the slave),忍受他的指使。但单于的下属对于“气”本身还是既畏惧不安又惶恐惊骇的,因而当得知女巫(他者心中的女巫)的存在时,他们都对首领单于与女巫合作表示出强烈的担忧与抗议,纷纷要求处死她(虽然伯里汗压下了争议)。而木兰也曾因幼时展示出了“气”而被家族邻里引以为耻(影片开场的木兰抓鸡),遂而相见媒婆失败;木兰的父亲也每每告诉木兰,她的“气”是不可展示于人前的,需要掩藏起来。因而在军营训练期间,当木兰与洪辉(安柚鑫饰)比武中无意展露出了“气”时,她迎来了围观士兵们诧异的眼神及背后的议论,木兰自己也后悔不已,暗自埋怨自己的冲动。但纵观中国文化史,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并无对“气”文化无法容忍的设定。早在先秦时期,“气”在中国就独受青睐,且数千年以来也一直沿用不衰。如春秋战国时期,“气”就已经有了理论基石:“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四十二章)和“吹呴呼吸,吐故纳新”(《庄子·刻意》)等。秦以后,也有韩愈的“气盛言宜”论、徐上瀛《溪山琴况》之“气”和谢赫的“气韵生动”等,“气”在文、乐、书、画方面都得到了广泛的传承与发展。而明清以来,由于武侠小说的广泛发展,中国对于“气”的推崇更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相比之下,西方历史文化中,虽然也有“气”的存在(如阿那克西美尼的物质一元论等),但唯独中国文化中的“气”是贯穿古今,且覆盖各个领域的。因而,一定程度而言,“气”—气功—功夫,成了中国的代名词。也如《原创在气》中所言,“气”由此成为一个探寻中华民族精神品质、审美心理、思维模式和理论形态的重要侧面。
“文学文本一方面影响了那些没有到过殖民地的人关于殖民的想象,另一方面又激发了殖民者的探索热情,他们在先前文本的参照下对新的殖民地进行构想。”如果说《花木兰》是那块殖民地,迪士尼公司就是背后的那个殖民者。因而虽然《花木兰》(2020,妮基·卡罗执导)与《花木兰》(1998,巴里·库克执导)并非同一导演,且导演妮基·卡罗身为女性,极易带有女性主义色彩,但在西方帝国主义式的文化侵蚀下,他们哪怕没到过殖民地,但在文学文本陈陈相因又互相指涉的先在语境中,导演与编剧们都明里暗里地参与或肯定了这个先见的殖民主义逻辑。何况,《花木兰》(2020)皇城的取景就在中国湖北的襄阳唐城影视基地,她们不可能对中国文化毫无了解。虽然,影片的末尾,木兰最终洗去了耻辱,成为花家的英雄,但这个荣耀也早已在接替仙娘时(片末仙娘为救木兰而死)成为西方文化中的附庸。此时的木兰,是西方女权主义式的拥有史诗般成长史的木兰,而非中国式的以家国情怀为内核的木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国“大我”几乎全被西方好莱坞式的“宏大”“小我”解构了。木兰成了披着中国外衣,却拥有西方意识的木兰,是西化的木兰传奇。
二、鹰与雪崩的对位
“文学是一种感觉结构,它并不是单纯的,而是复合的、混合的。”在对《花木兰》(1998)的改编中,其殖民意识也在有意识或是无意识地影响着迪士尼影业和好莱坞公司。1998—2020,真人版《花木兰》删去了大量的内容(意象),如影片中最具立体感的两个形象:“小神龙”木须和“好运”蟋蟀等,但其有选择性地保留下来的几个因素,如“鹰”与“雪”,它们又何尝不是西方意识形态的化身?
在对1998年版《花木兰》进行改编时,《花木兰》(2020)的编剧们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地保留了“鹰”这一意象,并且比之于前者影片中背景板似的存在,真人版《花木兰》中的“鹰”的功能也得到了扩大,它成为不可忽视的“反派”——仙娘/女巫的化身。但不同于鹰在中华文化中的精神象征——国家/民族的振兴、腾飞和崛起(如国产电影《半条棉被》(2020)片末中鹰的使用),西方文化中的鹰总是与战争相关联。西方文化的源头,古罗马人就认为鹰是“朱庇特之鸟”,是他们的代表,因而他们的军旗就是鹰旗;在希腊神话中,鹰也是众神之王宙斯的传令鸟,是力量与勇敢的标志。后来的很多欧洲民族正是继承了这个传统,所以才把鹰视为其力量与实力的象征。中国近代时事漫画《时局图》中,或许也由此选取了鹰来指代美国。而这也正如长于用动物表现人性的英国诗人泰德·休斯(二战期间曾在英国皇家空军服役)“Hawk
Roosting
”(《栖息的鹰》)中的描写:Or fly up,and revolve it all slowly-
I kill where I please because it is all mine.
There is no sophistry in my body:
My manners are tearing off heads-
“或高高飞起,使天地慢慢盘旋/我生来喜欢杀戮/因为绝对权力,无须辩解/我的习性就是扯下他人的脑袋”,《花木兰》(2020)中的鹰也是夹杂着其殖民主义思维的,它是主战方的代表,是战争的象征。而“Hawk Roosting”正是主战之鹰的一个缩影,它以世界的统治者自居,它是“权力意志”(尼采)的象征,因而它总能轻易挑起战争,又能冷眼审视死亡的世界。《花木兰》(2020)中的鹰正是如此,因而它成了女巫(巩俐饰)的翅膀,它成了女巫的化身,它一面为战争助力,一面又睥睨一切,它支配着死亡。甚至它最后的死亡也并非其被动的结果,化鹰为凤,它完成了自己的一次转换。
除此之外,为突出木兰的聪明才智,《花木兰》(2020)和《花木兰》(1998)中也都运用了不少篇幅来描写雪崩这一场景。1998年版《花木兰》中,木兰正是透过剑中反射出来的光影看到了远处匈奴军背后的雪山山顶,从而利用留下来的最后一颗炮弹,击中了雪山,引起大量雪体崩塌,暂时将匈奴军消灭。而在2020年版《花木兰》中,这一场景的篇幅虽然得到了扩大,但也是由于木兰巧妙地利用了雪山,引发了“雪流沙”,才转危为安。而有意思的是:因中国古代“边塞”(相对而言)的战争之地大都集中在居庸关(今北京市昌平县境内)、玉门关(今甘肃省敦煌县西北)、嘉峪关(今甘肃省嘉峪关市西)、阳关(今甘肃省敦煌县西南)、潼关(今陕西省潼关县北)等关塞扼要地区,都是形势险要之地,因而附近并未有能够轻易引发雪崩的雪山,且中国的战争记录史及雪崩史中也没有类似“战争引起雪崩”的史实记录。同时,根据《花木兰的史实与传说考》中的考证,《木兰辞》中提供的行军路线和战争地点等,都与北魏征伐柔然的战争状况,即《北史·蠕蠕传》中的史料记载十分相近,因而根据这些有力的佐证,其战争之地就在云中(今内蒙托克托县东北)、盛乐(今内蒙和林格尔西北)、黑山(今内蒙呼市东南杀虎山)、溧水(克鲁伦河)、菟园水(今蒙古国图音河)、燕然山(今蒙古国杭爱山)等地区,但在《木兰辞》与《北史·蠕蠕传》以及其他史料记载中,它们对雪崩都只字未提。
而与此相反,炮击雪崩的这一场景反而与一战中的一幕景象不谋而合。如《雪崩的主要案例》中的记载:“双方经常有意用大炮轰击积雪的山坡,制造人工雪崩来杀伤敌人。”(李杰卿的《一场雪崩埋葬意、奥两个师》和王淼的《被一场雪崩瓦解的战役》中也有类似的文字记录)一战期间(1916年12月),奥匈帝国与意大利的战争中,就有超过50万(人数有争议,也有说2万~8万)的意大利士兵死在了阿尔卑斯山上,而引发雪山爆发的原因正是战争开火时双方强烈的炮击。虽然这一说法也遭到了军事专家们的反驳(根据当时大炮的射程和积雪量考虑),但如果连一战期间都不会轻易触发雪崩,那生活在北魏时期公元424—449年的花木兰所在的北魏军又如何能做到呢?且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唐中后期我国古代炼丹家才通过炼丹术提取出了火药(文字记载见孙思邈《丹经》),火药开始运用于军事则是唐朝末年(豫章的一场战争),直至宋朝年间才广泛用于战争。那处于冷兵器时代的北魏军的大炮又从何而来呢?“文学文本塑造着殖民想象,而这意识形态就像空气,每一个作家都在其中呼吸而不自觉。”文学也在以某种方式支持、表现和巩固着其对外的文本扩张,因而虽然“花木兰”是中国IP化,但迪士尼的编剧劳伦·海尼克、里克·杰法等人都是基于对欧美文化的了解,从而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并未对中国文化做过多考量。他们在雪崩场景的呈现上是如此,在影片语言的使用上也是如此,这种理所当然的思维习惯构成了《花木兰》(2020)的语言与文化实践的重要部分,也正因如此,《花木兰》中的语言对话遭到了众多学者的诟病。
三、音乐及叙事的对位
萨义德曾表示:“我们生活的世界不仅有商品,还有再现,再现——包括它的生产、流通、历史和阐释——是文化的真正元素,并且这种再现与帝国语境、政治语境紧密相连。”尽管从导演的确定,到演员选角,再到影片的拍摄和宣传等,迪士尼影业都花费了巨大的精力,但就音乐性和叙事性而言,《花木兰》(2020)甚至难以与动画版《花木兰》比拟,20多年后,文化殖民意识形态下的偏见与戏谑还是潜藏其中。
迪士尼影片中的一个显著优势,也即动画版《花木兰》(1998)中的一个显著优势——音乐性,并未在真人版《花木兰》中得以表现。在国语动画版《花木兰》中,五首插曲的使用是促进动画故事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如第一首《荣誉》(王曼丽、叶蓓、白永欣主唱):“想要让自己能为家族带来那荣誉,就应该要端庄……男子出征战场,孩子女人扶养……”就真切地表达了木兰在见媒婆前,家族其他成员给她梳妆打扮时的要求与期望,她们希望木兰能够找到一个好的婆家,为家族争光。第二首《沉思》(叶蓓演唱)是木兰相见媒婆失败后发出的感慨:“为什么我却不能够成为好新娘,伤了所有的人……”可见,此时的木兰也是受家族婚配思维影响的,正是因为毁了家族成员对她的期待,因而木兰也在究竟是做真情的自我还是做压抑的自我之间痛苦地徘徊着,此时她对自己的“信仰”也产生了怀疑,对家族的愧疚感伴随其中。但当在目睹父亲接到应征入伍的消息独自在祠堂练剑摔倒、父母灯下分别的场景时,木兰愈加坚定了自己的决心,要替父从军,要换一种方式为家族赢得荣光。第三首《自己》(李玟演唱)是木兰思想逐渐成熟的转换。初到军营的木兰在面对军营里参差不齐的新兵、样式各异的训练方式以及对李翔的感情时,是产生怀疑的,“看着波光中清晰的倒影,是另一个自己,它属于我最真实的表情”,经过倒影中的反思,木兰才愈加坚定自己的理想与信念,她想要做真实的自己,想要向世界呈现更有力量、更有勇气的生命,于是她放下了情与爱,开始专心训练,最终成为各项训练中的佼佼者。……诚然,动画片《花木兰》中也在极力地宣传着其西方思维的价值观,如“我只希望她是好厨娘,牛肉、猪肉、鸡肉”、“我气喘如牛快断气,西方极乐等我光临”等,无论是思维还是用语上,当时的迪士尼影业都是停留在对中国的刻板印象上的,它也始终在向我们灌输着其意识形态。但起码在叙事的连贯性上,它是相对完整的,五首音乐的使用,使得故事层层递进、环环相扣,从而构成了故事情节的完善性,使得影片线索的进展合情合理,有据可依。
如西方媒体Boulder Weekly的评论,《花木兰》(2020)中存在“很多无幽默的动作戏,也没有歌”。的确,迪士尼总裁肖恩·贝利(Sean Bailey)和《花木兰》导演妮基·卡罗(Niki Caro)都看到了中国市场对于迪士尼本身的重要性,从而对大量的中国元素进行了文化杂糅和文化挪用,但因受其潜在的殖民意识影响(对自身文化的过度认同以及对他者文化的固定印象及否定),他们不愿意也并未从根本上对中国文化进行理解,并且文化的自豪感使得他们把其本身的艺术特色也忽略了。动画版《花木兰》的插曲都是迪士尼音乐译文下的表达,那么现今中国是否有对位的《花木兰》音乐之作呢?事实上,2018年《经典咏流传》(第三期)和2020年中秋晚会上尚雯婕演唱的《木兰诗》正是中国人眼中的木兰形象的一个缩影,是当代中国音乐人对“花木兰”的一种解读与表达。从孩童诵诗,到民间器乐大鼓、唢呐(突出)(明代武将戚继光曾把唢呐用于军乐之中)、古筝、古琴的使用,再到小花木兰们(孩童女子表演)用摇滚元素演唱的河南豫剧《木兰诗》的选段,加之尚雯婕独特的嗓音(别具气势感):“行万里,赴戎机,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这首歌把木兰的刚柔并济都完美地演绎了出来。其中,尚雯婕也加入了众多个人对花木兰的理解,她是注重突出“谁说女子不如男”这一文化特性的,因而在主题上《木兰诗》(尚雯婕演唱)与真人版《花木兰》也有极大的同一性。但遗憾的是,《花木兰》(2020)并未使用音乐来表达,也并未借鉴尚雯婕等中国音乐人对于木兰的看法。
“刘亦菲作为主角魅力十足,但剧本没有给她足够的深度以及合作的意义”。离开音乐,迪士尼公司仿佛已不会叙事,《花木兰》(2020)在叙事上也愈加显得空洞与无力。如武打戏的使用。木兰在训练时武力值和体力值都是首屈一指的,但等到真正上战场时,她的武力值却极速下降,难以阻挡士兵们的任意一击(身受刀伤,从而被赶离军营),而在柔然王的箭远远射来时,她也眼睁睁地看着箭到了女巫的身上而毫无反击的意思,仿佛之前的训练都是花架子。且影片花了大量的时间与场景描写木兰战前的经历,却并未突出她替父从军的情感原因。动画版《花木兰》中,木兰雨中沉思,深思熟虑后用刀断发,临行前再次看望熟睡中父母的容颜,夜半换装骑马而出,奶奶受到感应夜半惊醒,父母半夜发现留书,追出雨中摔倒,沉思后不再追去,转而变成奶奶在祠堂前求助列祖列宗,列祖列宗显灵交谈……都是十分细腻的。再如梅花的使用。片头木兰儿时与父亲在梅花树下的交谈,父亲对她的期望,再到木兰不为封赏,重回故乡,与父亲再次梅花树下谈心,李翔前来求亲,正好突出了其“梅花香自苦寒来”的主题。这些细腻的情感在真人版《花木兰》中都被忽略了。而这也正印证了影片人韩浩月的一句影评:“好莱坞成熟的编剧模式、迪士尼成熟的公主片模式,这一次没有成功用到《花木兰》里,甚至连流水化作业水平都没达到。”可见,虽然20年来,中国的经济实力壮大了,但对于中国本身,迪士尼虽存在一定的敬畏,但受其殖民主义思维的影响,他们并不愿意主动去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而是迫于市场因素,不得已而为之。20年过去了,他们对于中国演员的形象也始终停留在“能打”这一层面,对东方的偏见与刻板印象始终夹杂其中。
“在市场条件下,文化资本的运作是整个社会活动的重要方面。对文化资本的控制和媒体的掌控,决定着社会的基本文化倾向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取向。”真人版《花木兰》也并非一无是处。但在被文化资本覆盖的市场机制下,萨义德的“对位阅读”法为我们开辟了一个新的寻找他者的视野,在这一对位解读中,容易被淹没的被文化殖民者的声音重新被挖掘了出来。而除此之外,我们也须保持警惕,避免中国/西方二元对立的话语模式,超越文学的狭隘性与地方主义,在当代的超克中,把文学批评及影视批评放到统一的、整体的批评体系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