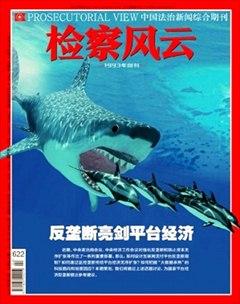异质现象
陆其国

想起写这篇文章,缘于一本人物传记中讲述的一则真实故事。故事主人公L先生是位著名民主人士,曾被错划为“右派”。L先生死于1965年。他无妻无儿无女,所以死后由弟弟和侄子赶来继承他的全部财产。那些财产除了数百美元、少量黄金,另外就是一些青花瓷器和名人字画,L先生专门收藏齐白石的画。其弟弟和侄子把L先生的书捐给了他所属的组织,独独没有理会他的骨灰,便抬腿走人。
1983年,由L先生供养读完大学的侄子趁赴京出差,前往探望传记作者的老母亲。谈话间他告诉老人,他现在是万元户了。前不久他挑了十八幅齐白石的画卖给省博物馆,得到三万元。传记作者这时写道,母亲送走客人,哀叹不已,说她要是有三万元钱就好了,就可以留住L先生的藏畫了。你看,两人一样都提到三万元,但他们所想迥然不同。一个哪怕有血缘关系,但看到的只是利益,少有亲情;一个和L先生尽管没有血缘关系,但她更看重自己全家和L先生的生前交谊和友情,留住L先生的藏画,就是留住他曾经的音容笑貌,就是对他最好的纪念。这就是同样为人,面对三万元所产生的异质。
这类异质现象,今天似乎并不少见。就以写作来说,有人任什么都可以拣到篮里都是菜,轻佻为文,轻率发表,然后以创作丰富自许。而有人哪怕写篇千字文,也要打磨多时,甚至更长时间,这才拿去发表。后者所求不在文章长短和数量,而是思想。近日,作家莫言出版新著《晚熟的人》,他说获诺奖后“这八年来,尽管发表的作品不多,但是我一直在写作,花费在案头上的准备工作远比写这本新书的时间要多”。这就是一样在写作,不同的写作者身上所凸显出的异质。
由此联想开去,忽然让人情不自禁打了个寒噤。因为在当今社会,这样的异质现象,竟早已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了。谓予不信,就以和每一个家庭关系最密切的教育来说吧。一样身为老师,一样站在神圣的讲坛上,有的老师可以真正做到诲人不倦、奉献所有、问心无愧地浇花育人;可也有这样的所谓老师,不恪守理应为学生答疑解惑的职业道德,在课堂上讲一半藏一半。学生如要听“详细分解”,那就得在校外“开小灶”——当然,你得另缴听课费。这就是一样的老师不一样的异质。再如,一样都是肩负救死扶伤神圣使命的医生,他们在从事这份崇高的职业前,应该都宣读过尽人皆知的希波克拉底誓言。就是在这样的岗位上,许多医生确实做到待病人如家人、如亲人;很多时候,为了服务患者、抢救病人,他们尽自己的一切努力和可能,把救死扶伤做到极致,有的还为此付出健康的代价。可是也不乏有些医生,别说医德,甚至还缺德。他们可以为贪图一己私利(比如索要红包、回扣),完全漠视患者利益及病人痛苦乃至生命健康。如此冷血,彰显的就是一样的医生身上不一样的异质。
当然,说起异质现象,有一个群体肯定绕不过去,那就是都声称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大小官员。都说自己是“人民公仆”,都高喊“为人民服务”,结果有的言行一致、名副其实,老百姓交口称赞,赢得好口碑;有的却贪赃枉法、贪污腐化,其所做事情与自己高调标榜的,完全是南辕北辙。且听某高官,在东窗事发前称,廉洁是一种幸福,做清官是大智慧。说的是不是很好听?可就是这样的高官,终因其所做坏事、恶事,最后被送上历史的审判台。这就是他们和言行一致“为人民服务”的公仆们不一样的异质。
图:付业兴 编辑:黄灵 yeshzhwu@fox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