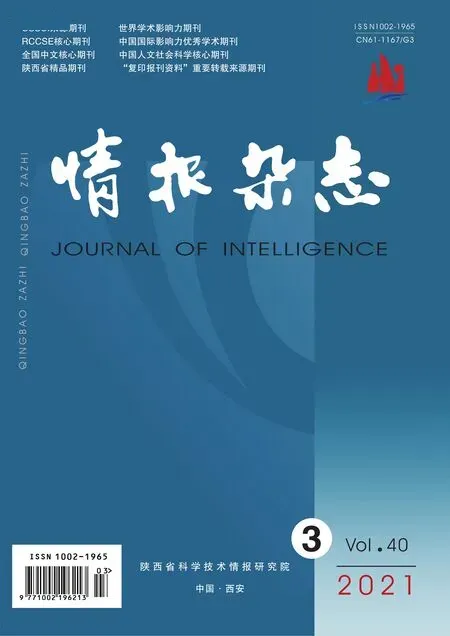美国网络空间安全的安全叙述建构
——基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话语分析(1987-2017)
王守都
(南京大学 南京 210023)
The Construction of Security Narrative of U.S. Cyberspace Security: A Discourse Analysis ofU.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1987-2017)
Wang Shoudu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Abstract:[Purpose/Significance]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and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every domain of human life has been closely linked with cyberspace, and cyberspace security is gradually topping the agenda of U.S. national security.[Method/Process]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security narrative, it employs 17 copies ofU.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as research materials, takes the approach of discourse analysis, and further explores the construction of security narrative of U.S. cyberspace security. [Result/Conclusion]Under such premise, it generalizes three principal features and underlying dynamics of security narrative of U.S. cyberspace security, and combined with the aforesaid features, makes prospect of future arena in which the power game of great powers takes place.
Keywords:cyberspace security;security narrative;U.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 discourse analysis; techno-nationalism
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以信息通信技术为核心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席卷全球。如今人类社会正处于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所预言的“第三波浪潮”的信息时代之中。以互联网及其相关衍生技术应用为核心的信息通信技术,已经渗透美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生活等领域,网络空间安全已经愈发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重要议题。匈牙利布达佩斯的国立公共服务大学的科瓦克斯(LszlKovcs)在《作为国家安全基石的国家网络安全》一文中指出,拥有更加先进的数字经济与社会的国家更易受到来自网络空间的威胁[1]。 美国作为现代互联网技术的开创者、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的弄潮儿,以及未来智能数字应用的引领者,在与网络空间相关的安全关切、治理规范、制度构建、技术研发等领域具有相较其他国家行为体而言更为深厚的历史经验以及更加扎实的实践基础。与此同时,美国也相较于其他国家更早地意识并感受到来自网络空间的安全威胁。网络空间中国家实力的较量与信息的掌握能力息息相关,实体物理世界中的大国权力博弈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中也在不断的循环上演。
美国作为现代互联网的创造者以及信息通信技术的业内领头羊,其面临的来自网络空间的安全形势相较于其他国家来说更为严峻。牛津大学数字伦理实验室主任卢西亚洛·弗洛里迪(Luciano Floridi)指出,“新技术的产生不断塑造着人类对于人性本身以及其在宇宙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思考与认知”[2]。以互联网及其相关应用为核心的信息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在便利美国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的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在不断塑造人类对于网络空间的具体认知。与此同时,网络空间安全(cyberspace security)也日益成为美国决策层在国家安全制定和规划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个难以回避的议题,关于网络空间安全的安全叙述架构的研究也兼具理论及政策意义。本文旨在借助安全叙述的理论框架,通过话语分析探究有关美国网络空间安全的安全叙述的建构历程与具体特征,并对于其深层动因做出尝试性阐述。
1 安全战略、安全叙述与文本选择
在《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安全被认为是一种“免受危险或者威胁的自由状态”,而在《韦伯斯特辞典》中,安全既包括主观上的不存在恐惧、焦虑以及担忧的心理状态,也包括不受任何伤害的物理状态,是一种包含主客关系的理解。奥利·维夫(Ole Waever)则认为安全是超越一切所建立的政治规则以及政治结构的一种途径,是一种所有政治之上的特殊政治[3]。因此,安全既可以被视作是一种目的,也可以被视作一种手段,其行为主体既可以是生物,也可以是具体存在于自然界的任何物质。在国际政治的话语体系当中,安全问题是行为体之间一定关系的产物,是主观认知与客观状态的综合产物[4],并且对于安全关系的不同的解释则最终导致形成了不同的安全观念[5]。 作为哥本哈根学派的代表之一,维夫将“安全即言语行为”作为安全化理论的理论基石,认为安全化的施动者通过对于某一种威胁来源的宣布将一些议题政治化并提升到安全领域,并通过这种方法为国家行为体实施相应的安全措施提供合法性以及必要性[6]。所以对于安全的认知并不能简单停留在指代客观存在的威胁这一表象,而应该将其理解为一种通过话语、框定以及叙述等言语行为所建构出的主体间认知。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建构主义、哥本哈根学派、后结构主义和女性主义、批判安全研究等非传统安全研究的兴起,基于政治文本的话语分析成为国际政治以及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种崭新的研究方法。对于政治文本的话语分析的主要理论依据在于人类倾向于依托叙述作为理解世界并赋予其意义的主要方式,对于政治话语的考量也广泛地依赖于叙述模式。琳娜·汉森(Lene Hansen)对于非传统安全研究的话语分析方式进行了梳理,认为通过文本解读而确认的基本话语的主要价值在于提供了一种有力的分析视角,并且至少可以通过文本解读(methodology of reading)以及话语识别(methodology of identifying discourse)的方法进行话语分析操作[7]。 本文将在此理论基础之上,界定出分析美国网络空间安全的安全叙述的研究框架。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安全叙述包含三种基本要素。第一种要素包括“事件、角色以及背景”,包含了主要叙述主体以及主体所存在的地理、社会及制度空间。第二种要素包括“事件序列”,即将事件按照时间连续域进行排列。第三种要素是“因果关系”,该要素所包含的因果归因存在于绝大部分的政治叙述之中[8]。 在有关美国网络空间安全的安全叙述的研究当中,美国这一国家行为体作为安全叙述的主体,在一定的连续时间域内通过构建特殊安全话语,构成连接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安全叙述。鉴于安全叙述本身所具有的时空特质与动态属性,美国作为叙述主体在某一时期内通过言语行为所呈现的安全话语建构,缺乏长时段的时间域连续性,因此需要综合中时段的系列政治文本加以梳理,方能形成具有时间跨度的安全叙述分析。
上述关于安全的理论及概念延伸进一步拓展了安全议题的研究范围,并为连接安全叙述与安全战略搭建了理论桥梁。“安全”作为一种“自我指涉”(self-referential)的话语实践,通过“言语行为”加以构建。这种关于安全的定义标准是依托于具有文本性的语言机制,叙述行为主体将常规政治领域提升到安全领域,其主要方式就是建构存在性威胁的话语[9]。 叙述与安全化的实践过程紧密相关。一条完整的叙事逻辑链包括话语含义、角色(行为体),以及情节主线,而安全叙述则是在此基础之上增加(或引导)一种特殊的政治以及安全目标[10]。关于安全战略的经典定义,往往聚焦于传统安全对于权力、军事实力等物质能力的关注。例如,根据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1997年出版的《军事用语及相关术语》的界定,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指的是“为达到巩固国家安全目标而发展、运用和协调国力的各部分(包括外交、经济、军事和信息等)的政策组合”。这种传统的关于安全战略的定义过于关注物质能力,但是忽略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战略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有关未来故事的叙事假设[11]。尤其是国家行为体的安全战略,其安全导向与政治目的尤为明显。例如,在《撰写安全:美国外交政策及身份政治》一书中,戴维·坎贝尔(David Campbell)指出所谓的危险不仅仅是一种客观的条件,还是一种行为主体对于威胁的评估。这种衡量是主观理解的结果,而叙述则构成了这一理解过程的核心[12]。对于安全战略中所包含的语言以及话语使用的具体分析能够反映出战略叙述者所面临的客观威胁以及构建出的安全状态。例如菲尔克劳福(Fairclough)认为语言“与现实的联系是主动(而非被动)的”[13], 帕克(Parker)也认为语言“不仅描述着社会世界,并且将其分门别类,(并)将种种现象引入大众视野”[14]。因此,当具体战略发生转变之时,安全叙述会在目标行为体脑海中形成新的安全现实,而在此过程当中涉及到具体的话语使用。综上,安全叙述与安全战略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叙述行为体通过言语行为构建出一种综合客观危险以及主观威胁的“安全”,并借助安全叙述达成特定的安全以及政治目标。如果叙述行为体是国家,那么这种安全叙述就构成了国家安全战略的叙述基础,因为安全叙述不仅建构了基本的威胁来源,还通过话语选择及叙述方式对于达成特定安全及政治目标的手段做出规划。
结合上述考量,本文在进行话语分析的文本的选择方面,主要考虑具有代表性的官方文件。经过整理筛选后发现,《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是非常合适的文本选择。首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作为一种首要文本(primary texts)[15], 集中体现了现任政府对于当前国际局势以及美国所面临的主要威胁的基本认知,反映了美国作为叙述主体在构建安全叙述时候的基本利益诉求。其次,《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系列文本满足安全叙述对于连续时间域的动态需求。根据1986年美国国防部出台的《戈德华特-尼科尔斯重组法案》中第603条的具体要求[16],时任美国总统需要每年向国会提交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以阐明美国的国家安全诉求以及具体战略要求。自罗纳德·里根总统正式发布第一份《美国国家安全》报告以来,截至2020年,美国自里根总统至特朗普前后六任总统共发布17篇《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对于这一系列报告的历时性梳理满足了安全叙述对于“事件序列”的基本要求。
在确定分析文本之后,需要整合17篇《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形成语料库。在整合之后的语料库之中,本文将遴选出与网络空间安全相关的代表性话语(discourse)并进行词频分析[17]。学界关于话语的选择性建构已有诸多研究,涉及的社科领域包含政治学、语言学、传媒学、政治心理学、认知心理学等多学科。例如,一些学者将话语构建理解为一种议程设定(agenda-setting),并突出其所引发的框定效应(framing effect)[18]。也有学者在研究框定效应的基础之上,对于政治偏好的形成进行理论分析[19]。话语作为建构安全叙述的燃料,不仅连接了叙述者身份认知以及安全现实,还可以将其罗列于时间序列之中以窥视安全叙述的建构演进。需要指出的是,具体每一篇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关于网络空间安全的安全话语的使用不尽相同,因此可以通过对于这一系列报告整合而成的语料库进行的分析而梳理出不同时间点上关于网络空间安全的安全话语建构的差异与连续性,并进一步厘清其安全叙述逻辑。
2 基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网络空间安全话语分析
对于安全叙述的分析需要结合具体的安全话语并结合时间序列,因此对于安全话语的梳理与分析是安全叙述分析的基础。在安全话语的筛选及分析方面,首先需要明确的是“网络空间”是一个具有双重属性的二元公域。网络空间是一个具有技术属性的物理域,其主要特征就是利用电子以及电磁频谱,利用相互连接的网络以及信息通讯技术来进行信息的创造、修改、储存、处理。同时,网络空间又是具有社会属性的国际公域,全球所有的国家行为体以及非国家行为体在实体物理空间的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具体活动,均映射在这一公域当中[20]。 美国军方将网络空间定义为“超级战略领域”(uber-strategic domain),并且美国陆军战争学院的战略研究所(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US Army War College)曾召集一批从事战略研究以及军用网络技术的专家进行圆桌讨论,他们最终给出“网络空间”的定义是:网络空间是人造的全球战略领域,也是衡量国家行为体权力的一个维度,还是在信息环境中(包括相互依赖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网络以及由个人或者组织使用或生产的常驻数据)增加权力维度的一种方式。因此,与网络空间安全相关的安全话语既包括与网络空间及其相关衍生应用息息相关的技术属性话语,也包括涉及政治、军事等领域的社会属性话语。此外,与“威胁”“攻击”“安全”“危险”等类似语义的安全话语也需要纳入话语分析的考虑范畴。此外,本文在进行词频分析的过程中,将带有相同限定词的名词词组加以区分,同时也将以名词形式单独呈现的部分加以保留。例如在分析“computer”相关词条时,“computer crime”或者“computer attack”中的“computer”不会计入以单独名词形式出现的“computer”的频数记录当中。同时对于不同词形的名词及词组(如cyber-security以及cybersecurity),本文在进行词频分析的时候也采取了单独处理的方式。这种方式可以增加话语分析的精确程度,同时将尽可能多的安全话语及其频数加以记录。本文经过筛选以及词频分析,汇总并制成了17篇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与网络空间安全相关的安全话语及出现频数的列表,详见表1:

表1 1987-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网络空间安全相关的安全话语及出现频数列表
根据上述词频分析表,本文首先得出下述基本分析结果。
第一,美国政府对于网络空间安全的基本认知,经历了从技术领域、经济领域、社会领域、军事领域到政治领域的演变。这一演变从安全话语的变化可以看出。从1987年里根总统的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直到克林顿政府时期1997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10年跨度,包含9份国家安全战略),围绕网络空间安全的安全话语使用完全是围绕技术出口展开,例如里根(1987年,1988年)和老布什(1991年,1993年)的国家安全战略中诸如“计算机技术及软件”“超级计算机技术”“超级计算机技术出口控制”这些话语的使用。自克林顿政府开始,有关经济领域、社会领域、军事领域、政治领域的相关话语开始系统性出现,诸如“市场信息系统”(1994年,1995年,1996年,1997年,1998年,1999年,2000年)、“军事及商用信息系统”(1995年,1996年)、“信息/网络基础设施”(1994年,1995年,1996年,1997年,1998年,1999年,2000年,2010年,2015年,2017年)、“计算机/网络攻击”(1998年,1999年,2000年,2010年,2015年,2017年)、“网络安全”(1999年,2000年,2010年,2015年,2017年)、“网络空间”(1999年,2010年,2015年,2017年)。
第二,网络空间安全在美国国家安全众多议程中的优先程度也在逐年上升,逐步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核心关注领域。1994年之前的6篇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涉及网络空间安全话语的出现频数不超过5次,甚至克林顿之前的5篇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有关计算机技术及出口管制的话语出现的频数只有一次(老布什1990年的战略报告甚至通篇都没有相关安全话语)。克林顿时期的7篇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所包含的相关安全话语的种类及频数都出现大幅上涨。在克林顿政府时期1998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整篇战略报告相关的话语频数达到34。到了2017年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中,涉及网络空间安全话语非常之多(共64处),几乎全篇遍布网络空间安全相关的安全话语。相关安全话语频数的增加,反映了网络空间安全在美国国家安全议题讨论中重要性的逐渐升高。
第三,与网络空间安全相关的安全话语在历届政府中既表现其变化,也表现出一定的传承。里根与老布什时期采用的安全话语只包括“计算机”“超级计算机技术”及“超级计算机技术出口管制”。克林顿时期仍然延续了“计算机”的话语使用,并且扩展了其范围(“计算机入侵”“计算机相关犯罪”“计算机黑客”),但是也出现了克林顿政府时期特殊的安全话语,诸如“信息基础设施”“信息安全”“信息能力”,并且这些安全话语的使用延续整个克林顿政府时期。1998年报告中首次出现关于“cyber”的使用,例如“cyber-crime”“cyber-attack”,2000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首次出现了“cybersecurity”以及“information/cyber security”的用法。对于“cyber”及其衍生话语的使用是克林顿政府为后续历任政府留下的话语遗产。小布什时期由于恐怖主义使得美国国家安全重心转向国内,网络空间安全相关话语无论是种类还是频数都大幅减少。奥巴马时期对于网络空间安全的重视程度显著加强,在延续克林顿政府对于“信息基础设施”安全话语的基础上,开始使用“网络空间”的安全话语,并且贯穿整个奥巴马政府的网络空间政策。特朗普政府在延续奥巴马时期“网络空间”的话语基础之上,增加了诸如“网络威胁”“网络赋能的经济战争”“意识形态信息运动”等威胁性导向极强、富有进攻色彩的安全话语,形成了特朗普政府时期网络空间安全相关话语的基本特质。
3 基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网络空间安全关切梳理
本小节将简要回顾17份安全战略文件的简要内容以及核心安全关切,并在此基础之上展开话语分析,并为后续研究提供基本的叙述背景。
囿于冷战时期的国际体系两极格局的结构性张力,里根时期的两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意识形态宣传意味浓重。1987年1月的安全战略报告在开篇就强调“对我们的国民、朋友以及世界上为民主而奋斗的人而言,美国就是自由、和平以及繁荣的象征”[21]。冷战时期美国的核心利益,就是确保美国作为一个独立自由之国,其价值观与制度完好不受侵犯;美国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维护世界的安全以及稳定,确保美国利益免受重大威胁;巩固美国的联盟关系。1987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并未涉及对于网络空间安全的探讨,但是在两处提及了在情报政策和计算机技术方面相对于苏联的优势:一处是在谈及苏联公共外交以及宣传力度时提出美国的政治以及情报战略要做出相应的回应,另一处是在讨论美国国防政策的时候,报告指出美国的计算机技术以及软件方面的技术优势可以转化为在军事战争中的胜势,并且要强化相关技术的信息保密,增强美国的反情报以及安全反制措施。1988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继续强调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四大支柱,即恢复军事实力、振兴经济实力、重塑国际声誉、增强国民信心。报告指出,上述美国国家利益与战略目标来源于美国持久的价值观念。此外,报告还谈及了军事技术革命对于军事战略能力以及战略认知的塑造,并且相较于苏联,美国及西方在信息自由流通方面的优势有助于美国及其盟友在超级计算机技术领域这一重要战略资产方面的进一步开发[22]。由于里根政府时期推行的“星球大战”计划,该报告在对美国国家空间(太空)政策(U.S. National Space Policy)的描述中,针对空间技术的应用以及苏美争霸着墨颇多。
老布什政府时期的3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出台于苏联解体前后。里根时期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关于美苏争霸的主题被美国政府对于新世纪的国际体系的展望所取代。在来自苏联的掣肘分崩离析之后,美国在国家安全战略中开始进一步思考如何领导世界的问题:“我们(美国)的价值观是我们的过去与未来、内政与外交、实力和目的之间的纽带……我们不仅要守护我们的公民,捍卫我们的利益,更要创建一个新的世界使我们的基本价值观光耀四方”[23]。在1991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防止扩散”(Stemming Proliferation)这一部分,报告列出了包括核武器、生化武器、以及超级计算机等尖端军事技术的技术扩散问题,并认为美国政府应该强化当前不扩散的条约基础,扩大不扩散多边机制的成员,并提出新的不扩散倡议。1993年1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美国在全球大转型时期必须抓住机遇领导世界,并且在“不扩散”(Nonproliferation)这一部分重申对于超级计算机技术以及其他敏感技术的出口控制[24]。
威廉·杰斐逊·克林顿时期共出台7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是截止特朗普总统之前在任期内发布最多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总统。克林顿时期战略报告一改里根和老布什时期报告的通用题目《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开始推陈出新,以新的命名方式来强调时任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偏好。1994、1995、1996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题目为《关于参与和扩张的国家安全战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Engagement and Enlargement),1997、1998、1999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题目为《新世纪的国家安全战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for a New Century),2000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题目为《全球时代的国家安全战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for a Global Age)。1994、1995、1996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认为冷战的结束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的安全重心:共产主义扩张的阴影已然消散,美国需要面对诸如种族冲突、恐怖主义、能源安全、核武器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人口的迅速增长等问题开始削弱美国以及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稳定,是美国目前所面对的主要安全挑战[25]。值得指出的是,1996年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首次提出了“国家安全应急准备”(National Security Emergency Preparedness)的初步概念,认为美国应该全力防止遭受诸如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对于信息系统的威胁、以及自然灾害的影响,一旦出现上述紧急情况,必须要确保国家制度以及基础设施的保全、保证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存美国式的生活之道[26]。1997、1998、1999年的国家安全战略开始面向新世纪。具体在网络空间安全与治理领域,1997年5月发布的安全战略在“有组织的国际犯罪”(International Organized Crime)方面,将大规模国际诈骗和公款挪用、伪造、以及对于手机和银行的计算机入侵视为金融犯罪的范畴。在1998年10月发布的安全战略中首次出现“cyber”的用词,具体出现在“增强国内外安全”(Enhancing Security at Home and Abroad)大标题之下。报告指出,通过国际网络对于美国国家信息基础设施进行的网络犯罪或者战略性的信息攻击是美国安全面临的新的挑战[27]。1999年12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在讨论有关基础设施保护以及提高出口控制这两个方面的时候首次提出了“信息安全”(information security)的概念[28]。此外,同样在讨论有关基础设施保护的部分,报告还首次出现“网络安全”(cyber-security)的用词,但是具体的语境是“训练网络安全的从业人员”。“网络空间”(cyberspace)的概念也首次出现,具体用于描述“美国比任何国家都更加依赖网络空间”。2000年的《全球时代的国家安全战略》首次将“信息/网络安全”(information/cyber security)提上了国家安全战略的议程,并开始用“网络安全”(cyber security)替换之前的“信息安全”,并明确表示该战略作为美国第一部网络安全战略(first-ever national strategy for cybersecurity)使美国已经深刻地认识到,在全球时代,美国所面临的威胁不仅仅来自于已然确定的敌人以及致命的武器,还来自网络空间以及其他领域[29]。
乔治·沃克·布什在任时期共发布了两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2002年10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是在“9.11”事件发生一周年之时发布的。放眼全篇报告,“恐怖”成为该战略报告的主题。在对2002年的战略报告进行词频分析之后,全文共出现14处“terror”,33处“terrorists”,29处“terrorism”,14处“terrorist”[30]。小布什时期的首份国家安全报告在高举人权大旗的同时,呼吁世界各国共同参与反恐联合行动、缓解区域矛盾。全文并未出现任何有关“cyber”“computer”或者与网络空间安全相关的话语,只是在“转变美国的国家安全制度以应对二十一世纪的机遇与挑战”这一部分中提及了有关建立国内国外的情报预警机制的相关内容。小布什于2006年3月发布了任期内的第二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报告指出,美国必须在“恐惧”与“自信”两条路径之中择其一而行,而选择“自信之路”则意味着美国选择了领导世界追求自由贸易与开放市场。2006年的国家安全战略重申了美国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的坚定立场,并指出美国国家安全的两大支柱:推行自由、正义与人权以及领导民主国家应对时代挑战。整篇报告并未提及有关网络空间安全的内容。
贝拉克·侯赛因·奥巴马于2010年与2015年先后颁布两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2010年5月发布的战略报告11次提及“cyber”,9次提及“cyberspace”,3次提及“cybersecurity”,1次提及“cybercrime”,足见奥巴马政府对于网络空间的重视。战略报告指出:“除了应对传统战场上的敌人,如今的美国还必须准备应战诸如针对太空以及网络空间的非对称威胁”。同时,在讨论有关“加强国土安全与恢复力”的部分中,报告指出,“美国的国土安全有赖于我们共同协作,通过识别并禁止威胁,挫败敌对行为体在境内进行活动的企图,保护国家关键性基础设施以及关键资源,并确保网络空间的安全”[31]。在“保护网络空间”(Secure Cyberspace)这一部分中,报告再次指出,网络安全威胁是如今美国所面临的最为重要的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经济安全的挑战之一。网络相关技术不仅促进了美国的经济繁荣,也强化了其军事优势。但是如今,网络黑客、有组织的犯罪团体、甚至民族国家行为体都有可能从网络空间对美国造成严重威胁。2015年5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除了重申美国在安全、经济、价值观、以及国际秩序方面的利益诉求之外,还对美国在国内以及国际的网络安全任务做了规划。具体而言,在国内要求确保联邦政府网络系统的安全,不断强化关键基础设施的恢复能力、建设高标准的立法框架;在国际上要求美国在遵循国际法的前提之下协助盟友抵御针对基础设施的安全,并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长久的国际行为规范(包括知识产权保护、网络自由、对民用基础设施的尊重),强化政府与私营领域的公共责任[32]。
唐纳德·特朗普于2017年12月18日颁布任期内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这份战略报告突出“美国优先”的基本原则,分别从维护国土安全、促进经济繁荣、以实力维护和平、提高美国的影响力四个部分阐述了特朗普政府的战略构想,其中报告在“维护国土安全”以及“以实力维护和平”这两个部分对于有关网络安全问题进行了具体阐述。报告中24次出现“cyber”的词条,11次出现“cyberspace”的词条,8次出现“cyberattacks”的词条。安全战略报告强调了网络空间安全对于美国政府的重要意义,认为“美国对于网络时代的挑战与机遇的应对将会决定美国未来的繁荣与安全”[33]。报告进一步指出,网络攻击如今成为现代冲突的关键特征,美国将在必要时威慑、防御并痛击使用网络空间能力针对美国的恶意行为体。
4 美国网络空间安全叙述的基本特征与深层动因
对于17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1987-2017年)的详细梳理呈现出每一份战略报告的主要内容以及核心安全关切,并且为安全叙述的构建提供了基本背景与事件序列。在此基础之上,本文将美国政府建构出的网络空间安全话语与叙述背景和时间连续域相结合,形成完整的叙述逻辑链,对于美国政府所建构出的网络空间安全的安全叙述的特征进行进一步讨论。结合之前对于历届《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文本分析的结果,本文首先得出下述结论:
首先,美国网络空间安全的安全叙述具有历时性。美国对于网络空间安全相关的叙述建构经历了近二十年的演变才逐渐形成现今的成熟叙述框架。美国政府对于网络空间的认知经历了从里根、老布什时期的超级计算机技术,到克林顿、小布什时期的信息安全以及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再到奥巴马和特朗普时期,最终将网络空间视作美国战略博弈的新领域,将网络及其相关技术与美国军事、经济、政治以及核心价值的安全威胁紧密相连。严格意义上而言,克林顿政府与2000年发布的《全球时代的国家安全战略》是美国政府建构网络空间安全话语及叙述的开始,因为之前的11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对于网络空间的认识尚显粗浅,主要停留在有关技术领域、经济领域的安全话语的使用层面,尚未将网络空间安全的高度提升到与美国国家政治及军事安全息息相关的统领层面。小布什时期,囿于国际安全环境的剧变以及应届政府明显的利益偏好,着重突出反恐而非网络空间安全,因此小布什时期的两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几乎没有着墨网络空间安全的相关话语。小布什政府之后的奥巴马以及特朗普政府,美国对于网络空间安全的认识进一步加深。历届美国政府结合自身对于网络空间威胁的认知以及具体的利益偏好,建构出一系列的安全话语。这些安全话语在连续时间域中的有机整合最终形成了美国网络空间安全历时性的安全叙述。
其次,美国网络空间安全的安全叙述具有延续性。克林顿政府到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无不反映了美国基本的国家利益诉求以及国家目标,即促进美国国民经济繁荣、强化美国国家军事力量构建、维护美国国际政治影响、宣扬美国国家价值的核心安全观念。这种核心安全观念奠定了美国网络空间安全相关的安全叙述的“主旋律”,具有延续性。虽然历届政府在任期内所使用的安全话语各有差异,反映出时任总统对于网络空间威胁的认知差异以及利益偏好,但是长期而言,历届美国网络空间安全的安全叙述构建依然紧紧围绕美国基本的国家利益诉求展开。美国政府通过发布国家安全战略,将美国政府及人民描述为世界的领行者,面对不同时期的敌对行为体(冷战时期的苏联、“9·11”事件之后的恐怖主义、“流氓国家”、后“9·11”时代的诸如俄罗斯、朝鲜、伊朗的“恶意行为体”),应对来自各个领域的安全威胁,仍然坚持不懈的维护美国核心价值观以及世界霸主的地位。美国政府通过这种延续性的安全叙述,不仅将自己建构成引领世界抵抗邪恶势力的正义战士,而且还向国内民众以及其他国家行为体宣扬立场、传播信心。
最后,美国网络空间安全的安全叙述具有引导性。美国政府通过国家安全战略这种安全叙述的方式,将来自网络空间的对于美国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生活等领域的种种威胁逐一呈现。在安全叙述过程中,美国政府所率先创造并使用的安全话语,诸如“网络空间”“网络威胁”“信息基础设施”等,在安全战略报告的“听者”的主观印象中植入可达性建构体(construct of accessibility)[34],使得“听者”在下次听到类似话语时很容易唤起记忆并产生认同感。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潜在“听者”,既包括美国国内政府部门及普罗大众,亦包括全球范围内的其他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美国政府通过建构网络空间安全的安全话语及叙述,将美国所面临的安全威胁放大为全世界所面临的共同威胁,这种“放大效应”在有关恐怖主义以及网络空间安全这两项安全议题上尤为明显。通过建构网络空间安全的安全叙述,美国不仅为国内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对网络空间的安全威胁做出规划和调整,同时也引导国际上其他国家及非国家行为体在网络空间安全领域的概念界定以及议程设定,并进而掌握国际网络空间安全及治理的话语权。
美国网络空间安全叙述建构是由美国国家安全观念及战略传统所持续驱动的。美国国家安全观念及战略传统作为一种非物质力量,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以及网络空间安全叙述奠定了具有长久延续性的基本框架,深刻地影响着其安全目标的制定以及基本方向的规划与调适。美国安全观念以及战略传统“谋求和维持绝对、全面的军事优势,追求绝对安全”[35]。这种进攻性战略文化对于威胁的认知往往基于最坏假设,并且推崇以绝对军事实力追求绝对安全。后冷战时期美国的安全观念以及战略思想对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霸权地位维护起到根本性的推动作用。美国网络空间安全叙述的构建历程及基本特征,反映了美国国家安全观念与战略传统对于不同历史背景之下美国对于来自网络空间中的威胁认知以及在网络空间之中的利益诉求。在上述安全观念以及战略传统的影响下,美国政府在网络空间中一直积极寻求绝对安全并维护其霸权地位,这不仅反映在相关网络空间安全叙述之中,也体现在长期以来美国政府对于传统及新兴信息技术的战略优势的不断追求。
5 结论与展望
本文通过对17篇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1987-2017年)的文本分析,呈现了三十年来美国在网络空间安全领域创造并使用的安全话语。安全话语的使用及变化不仅反映出美国政府对于网络空间安全基本认知所经历的从技术领域、经济领域、社会领域、军事领域到政治领域的演变,也表明网络空间安全在美国国家安全众多议程中的优先程度也在逐年上升,并且网络空间安全相关的安全话语在历届政府中也展现出其变化与传承。安全叙述与安全话语不同,具有时间维度的动态属性,本文在进行综合梳理后认为,美国网络空间安全叙述具有历时性、延续性以及引导性这三大基本特征。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美国网络空间安全的安全话语及叙述反映出美国政府的技术霸权主义以及技术民族主义倾向。美国政府深知核心技术优势对于维护美国关键的军事、政治、经济、以及核心安全观念的重要意义,因此对于其他国家行为体在某些领域的技术研发十分敏感。冷战时期,美国为了获取与苏联竞争的战略优势,在冷战时期对于苏联实施包括计算机技术在内的多方面封锁。昔日的对苏联关于计算机技术的出口管控以及如今对于中国的5G技术封锁,其维护霸权的实质并未改变。随着全球范围内的科研水平的提高,美国在一些前沿领域的技术优势已不复存在。为了维持自身霸权地位,美国政府今后可能会在国家安全战略中涉及更多的技术细节(例如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报告中所涉及的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技术名词),这些前沿的战略性技术可能成为未来大国权力博弈全新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