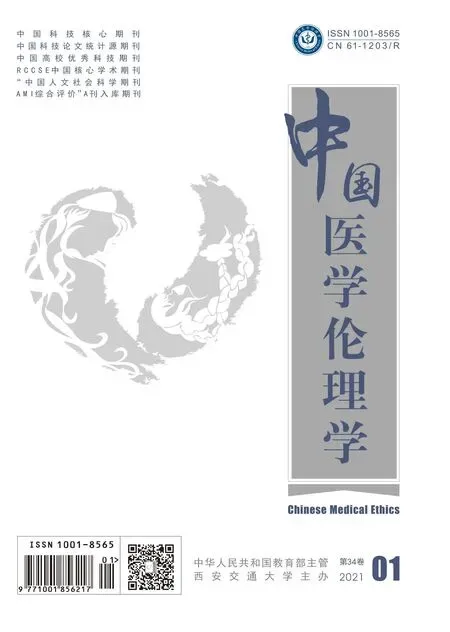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污名化解析与思考
——基于传统儒家文化视角*
贺 苗,李红英,尹 梅**,辛 军
(1 哈尔滨医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1,hemiao767@163.com;2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江苏 苏州 215000; 3 中共苏州市委党校,江苏 苏州 215000)
新冠肺炎疫情是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后,面临的一场前所未有的大灾难。在全球性、突发性的公共卫生危机中,世界各国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在全球被污名化的时代,人类的傲慢与偏见、嘲讽与指责、恐惧与推卸只会加速病毒的全球蔓延,而灾难面前人类的责任与担当、团结与合作、同理心与善意的坚持,才能护佑人类共同的福祉和安宁。本文主要以课题组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过程中的调研结果为基础,分析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所引发的污名化效应,试图从传统儒家文化视角深入反思人们在重大灾难面前的认知态度和去污名化的内在心理机制。
1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污名化调查
课题组以2020年1月发生在日本名古屋中部机场的冲突为例进行了调研,当时有乘客发现两名同班机乘客在自测体温,因担心感染新冠病毒而拒绝与其同机回沪。在回收的2663份有效问卷中,受调查者的观点存在差异,支持隔离建议的人数为365人,占13.71%;超过半数的人(1343人,占50.43%)倾向于采用综合评估的应对方式,其中认为未确诊不能判断是传染性病患的人数为155人,占5.82%;不应歧视病患的人数为306人,占11.49%;应做好个人防护的人数为246人,占9.24%;做好合理建议并希望管理部门重视的人数为248人,占9.31%。通过调查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大众还是能够比较理性看待污名化现象,避免或减少歧视,加强综合治理是大众的普遍诉求。随着全球疫情的持续蔓延,一些不怀好意的政客和媒体试图将病毒贴上地域、国家、种族的标签,致使世界各地的很多无辜者成为被攻击的对象。面对此类歧视、分裂、恐惧等污名化效应,我们需要冷静地思考在疫情时期乃至后疫情时代,现代人应如何对待可能比病毒更可怕的“心理病毒”及其在全球弥散出来的前所未有的危机与风险。
2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污名化的本质与特征
2.1 污名的本质
污名(stigma)一词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是烙印在奴隶、罪犯或叛徒等社会底层个体或群体身上的一种标记,以表明他们身上有污点,应避而远之。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Erving Goffman)在《污名——受损身份管理札记》(1963)一书中将污名理解为“受损的身份”,是一种令人耻辱、羞愧、贬低性的社会特征。污名,首先表现为对身体的歧视,即身体残障或缺陷;其次为其所在社会文化不能接受的行为,比如吸毒、酗酒等;最后是由于血统形成的对种族、民族和宗教的集体污名[1]。质言之,污名作为一种身份标签或社会建构,具有很强的价值判断,使个体或群体成为遭受社会排斥、打击的对象,在日常交往和社会情境中他们的社会身份、地位、价值受到贬损,甚至遭遇社会不公正对待的后果。此后,污名逐渐进入当代社会研究视野,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从社会学、心理学等不同视角丰富和发展污名的内涵与外延。其中,林克(Link)和费伦(Phelan)对污名概念的理解颇具影响力。他们认为,“污名是贴标签、刻板印象、隔离、地位丧失和歧视等元素的集合体”[2],这一概念清晰地概括了污名的形成机制及其后果。实际上,污名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在日常生活中造成一种社会差异[3],它将人分成常人和蒙受污名者,通过身份标签、刻板印象、社会歧视等一系列方法或手段在人与人之间潜移默化地形成一套社会分类标准。
2.2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污名化的基本特征
随着中国社会的深刻转型及世界格局的复杂动荡,由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日益严重,泛污名化现象日益凸显,在一定程度上对个体和社会大众的身心健康造成危害,甚至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发展。根据污名的内涵及本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污名效应主要呈现出如下特征:
第一,污名的内容日益泛化。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瘟疫对人类的生存构成巨大威胁。无论是历史上曾席卷整个欧洲的黑死病,还是至今仍受诟病的艾滋病,已有太多的传染病或者瘟疫因其传染性、致死性等承受着严重的污名。而新冠病毒早已跨越单纯的疾病污名,呈现出地域污名、身份污名、种族污名、交错污名等泛化趋势。不仅患者本人,还包括家属及相关人员,似乎只要和病毒沾边,就很容易使人们在社会心理产生认知偏好,形成集体的身份污名。人们日益发现人类面对的最大敌人不是病毒本身,而是导致人们彼此对立的污名。
第二,污名的方式日趋多样化。根据林克和费伦的框架,污名始于贴标签[2],在人与人之间形成区别。对于新冠肺炎患者而言,一旦确诊即意味着被贴上了“病毒”的标签,需要接受规范治疗,成为被隔离的人群,自然而然与常人划出界线。不言而喻,在疫苗尚未研制成功之前,隔离、检疫是维护公众健康的最有效的保障和举措。然而,新冠病毒的快速传染性及其前所未有的杀伤力和危害性,很容易在大众文化与心理上形成刻板印象和思维定式,不知不觉中使患病人群及相关人员陷入受孤立、受歧视、受伤害的不利境地。
从上述分析中不难发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污名,一方面,遵循常态污名内在的演化逻辑,即从贴标签形成先入为主的刻板印象,接受社会隔离,进而遭遇社会歧视;另一方面,随着人类不断迈入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由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自身特点所引发的突发污名,以及由互联网传播出现的媒介污名,使污名方式日益多元化。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大流行,其罕见的破坏性迅速引发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危机,突发污名与常态污名并存[4]。尤其是网络媒介、自媒体等信息技术催生出来的媒介污名,其传播速度快、受众范围广,造成的危害性更大。受利益驱动和博得受众眼球,部分网络媒体有意制造具有煽动性、甚至耸人听闻的不实信息,断章取义,放大污名效果。因此,在突如其来的疫情面前,不少专家、学者感慨他们不得不面临双线作战的尴尬境地,既要应付病毒的肆虐蔓延,又要应对比病毒本身还难克服的恶意造谣与污名。
第三,污名的风险日渐加剧。从全世界范围来看,新冠肺炎疫情差不多危及全球所有的国家,给人类社会带来空前灾难。病毒不断攻击社会的核心力量,夺走无数人的生命和生计,引发全球经济空前恶化。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曾指出,目前这场新冠疫情是二战以来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可能会引发一场近代历史上无可比拟的衰退[5]。这种衰退不仅表现为社会经济的全球危机或者大萧条,而且由此引发的污名风险也不断加剧。概括起来,这种风险主要表现为:一是公众或社会对某一特定个体或群体造成的身份区隔或群体标志,致使蒙受污名者被抛出正常的社会生活轨道,遭到社会排斥与孤立;二是由于公共卫生事件的突发性和不确定性,尤其像新冠病毒的传染性和高致死率,如果公众不能及时获取专业的权威的资讯,会产生极度的焦虑、惊恐、愤怒等不良情绪,一旦社会风险管理失效,极易导致社会恐慌、群体抗议、秩序重构等一系列公共卫生危机;三是公众污名伴随着自我污名不断内化,导致人的情感、心灵等精神世界严重受损。当下中国抗疫取得阶段性胜利,越来越多的患者痊愈出院,但他们仍普遍感到来自外界的压力和鄙视,导致自我评价、自我效能的贬损或降低[6],甚至产生严重的心理应激障碍。
3 儒家伦理对污名化的反思
实际上,由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污名化效应仅仅是突发公共卫生危机中的一个缩影,人类文明的历史演进始终伴随着危及人们生存的各种灾害与苦难。人类在与疾病、瘟疫、灾难一次又一次的博弈过程中,不断积累经验,获得成长,也日益加深对自然、对社会、对他人、对自身更为深刻的觉察与认知。在当下全球一体化、文化价值多元化的时代,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有价值的普世的伦理思想对于矫正人类生存的价值坐标[7],改善现代人内在精神需求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3.1 仁民爱物的宇宙观
经典儒家伦理最核心的理念莫过于“仁”,其最朴素的要求就是爱人,所谓“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实际上,儒家伦理以爱人之名,倡导一种人与人之间同类相爱的博爱思想。正如《淮南子·主术训》所言,“仁者,爱其类也。”正因为人与人同类相似相爱,才会建立联系,从而形成共同的生命情感。在当下这场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危机中,我们看到污名极大泛化,不仅仅是个体的身份建构,同时也成为一个群体、一个种族甚至一个国家集体的污名,这无疑会给蒙受污名的个人带来身心打击,引发社会恐慌,甚至对国家造成巨大损失。儒家主张人类一家、彼此相爱,其爱的基本出发点就是将他人视为自己的同类,以爱己之心爱人。质言之,儒家的爱类意识对于冲破由污名造成的身份区别、社会差异、文化纷争具有重要价值。尤其是对处于社会边缘的脆弱群体,儒家更是抱有深切的同情与悲悯。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作为一个有德性、有良知的人,要懂得同情他人,尊重、理解他人的感受与需求。在新冠疫情暴发过程中,疾病的高传染性和杀伤力,在世界各地引发一系列对脆弱群体的孤立、歧视和排斥,特别是个别国家在床位、呼吸机等医疗资源救助方面的差异政策使患有新冠肺炎的老年人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这在具有儒家传统文化浸润的中国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中国在此次疫情中采取了“应收尽收,应治尽治”的原则,对高龄的老人和年幼的儿童均施以人道主义的救护和帮扶。“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下》),这种文化精神已经远远超越儒家最初的范畴,成为深刻积淀在每个中国人的血脉之中的价值取向。
在儒家看来,爱在先后、层次上是有差别的,呈现出一个不断向外拓展生成的过程。亲亲、仁民、爱物构成了儒家差等之爱的演进序列,从爱人过渡到自然万物,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伦理观。“天人合一”是儒家思想的精髓,先贤们认为,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应敬畏天道,不可向自然过度索取,要取之有时,用之有度。“子钓而不纲(大网),弋不射宿(归宿之鸟)”(《论语·述而》)“数罟(细密的渔网)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上》)。实际上,这些朴素的话语揭示出人类对待自然万物的伟大智慧,这对于人们正确审视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经历疫情,人们真的要停下来反思现代社会面临的生态危机,不仅仅是气候变暖、土地沙化、环境污染等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利用,而且还要重视对野生动物的保护,真正从源头禁止非法猎杀、收购、运输、贩卖野生动物。从更为宽泛意义而言,本文强调去污名化是从一个延展的维度强调,人类不应盲目自大,妄图凭借现代科学技术就可以征服和控制自然。儒家经典告诉我们,“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天道与人道相通、相感、相济,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8]。无论是在疫情之中,还是在后疫情时代,我们应从本心出发,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具备爱人爱物之德性,不断体悟人在宇宙中的位置,从而营造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生存格局。
3.2 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
从本质而言,儒家提倡的仁爱思想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民生至上的基本理念。仁者爱人绝不是玄之又玄的空中楼阁,而是落在坚实的大地上,活在人与人之间的生命情感中。因此,儒家历来重视忠恕之道,将其视为推行仁爱的方法与路径。朱熹曾这样阐释,“尽己之心为忠,己已及人为恕”(《四书章句集注》)。质言之,忠恕之道将仁爱之心一以贯之的基本路径就在于将心比心,推己及人,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仔细分析,忠恕之道包含着人与人之间的双向互动,一方面它强调不伤害他人,以自己的感受去理解、同情、帮助他人;另一方面,它对自身也提出了严格要求,即你希望别人做到,自己要先做到,也就是先求诸已,然后求诸人。
实际上,儒家的忠恕之道为避免或减少污名化效应开辟一条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进而达成共识的交互体验之路。首先,在对待他人的态度上,儒家主张要竭尽所能、全心全意去帮助他人,并且这种帮扶是发自真心,而不是虚情假意,所谓“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其次,儒家强调以爱己之心爱人,先严格要求自己,再以己度人。这种以爱人之心为出发点的换位思考和同理心,实际上是消除污名效应的内在心理机制。污名者之所以被污,从本质上是对其身份或其存在状态的一种道德贬损。而儒家伦理以仁爱为核心推演出来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或者说“施于己,再施于人”的忠恕之道,对于当下来说,无疑具有启发意义。在此次疫情中,感染新冠肺炎的患者及家属在身心受到病毒侵袭的同时,也常常直接或间接地成为蒙受污名的对象,而且由病毒连带的地域污名、种族污名、国家污名已经给不同的个体或群体造成严重影响。在风险与机遇并存的全球化时代,忠恕之道内在所蕴含的将心比心、以己度人、相互关切的人生态度,以及其引发而来的社会成员之间和衷共济、求同存异、互惠共享、守望相助等思想已经成为全世界人民抵御重大疾病时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总之,人类的文明进步始终交织着与重大瘟疫、灾难的艰苦抗争。在一定意义上,人类的发展史也是一部人类不断与疾病作战、与病毒长期共存的历史。病毒不会歧视,所有人都有风险,污名也并非是某个人或群体的“专利”,而是所有人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大疫当前,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视角思考人与人、人与万物之间的关系,细细品味流淌在民族血脉中的那份情义,将人类的恻隐之心化成对人、对天地万物不竭的动力源泉,从而体悟生命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