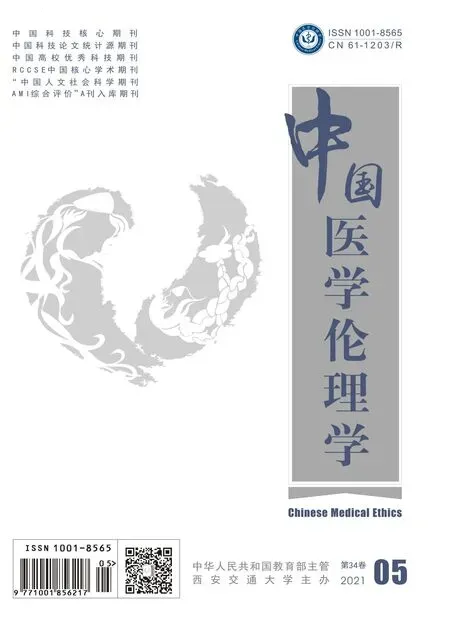发展的马克思主义道德哲学问题式下医德教育范式的转型
——医德的现实化与“践行性的道德实践能力”*
蔡 昱
(云南财经大学金融研究院,云南 昆明 650221,yucaicn@vip.sina.com)
我们当前的医德教育囿于“知性医德教育模式”,即以医学伦理学课程和医学伦理学原则为核心,着重培养学生的道德认识能力、道德判断能力和道德反思能力,忽略了对作为道德现实化的前提的“跨主体性的能力/践行性的道德实践能力”的培养,更是忽略了对作为获得此能力的前提的“超越生存性恐惧的勇气”的培养,从而造成了医学生“知旁落而无践行”的局面。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道德哲学问题式的视野下,我们当前的医德教育急需范式的转型,即从“知性医德教育模式”转变为着眼于使医德现实化的“践行性的实践性医德教育模式”。
1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包括道德哲学?
当我们探讨马克思主义道德哲学时,需要澄清一些基本问题,如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是否包含道德哲学?如果包含道德哲学,那么马克思主义道德哲学的根本特征是什么?与以往的道德哲学相比,它主要解决了什么问题?我们应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道德哲学等。
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包含道德哲学这个问题,伦理学界存在很大争议。的确,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曾像近代以来的许多哲学家那样从理论上构建系统的伦理学体系,在他们看来,道德观念与宗教及其他意识形态一样,是对社会经济基础的反映。据此,有学者就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包含道德哲学,如国外分析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的“马克思主义非道德论派”,包括艾伦·伍德、理查德·米勒、安德鲁·科利尔等。但同时,不少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对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驳。如罗德尼·佩弗指出马克思的“自由、人类共同体和自我实现”三个概念形成一种系统的道德观;凯·尼尔森认为马克思关于“道德是意识形态”的论断仅属道德社会学,而非道德认识论;德布拉·萨茨认为在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中,关于价值的观念居于核心;布伦克特则对马克思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理论作出新的理解。
不少国内学者对“马克思主义道德论”和“马克思主义非道德论”之争作出了分析和评价,在我国,公开主张“马克思主义非道德论”的学者并不多。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其他领域相比,道德哲学的研究相当薄弱并充满争议,其中也包含了对马克思主义道德哲学的质疑。
值得重视的是,我国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价值维度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道德哲学的研究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应当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界的大多数学者都承认并深入研究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价值哲学维度。他们认为,从早期到后期著作,马克思对社会历史发展的研究都是在科学考察与价值规范的统一中进行的,这是两个相互联系、缠结且不能相互取代的尺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价值维度的确认便是对马克思主义道德哲学的肯认,因而,21世纪以来,国内学界有关马克思主义道德哲学的研究产生了丰硕成果。其中,安启念的《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研究》[1]和宋希仁的《马克思恩格斯道德哲学研究》[2]等著作是标志性成果,它们都系统地整理和阐发了马克思道德哲学的理论内容。
2 马克思主义道德哲学的根本特征——马克思主义道德哲学的问题式
在我们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包含道德哲学”这一基本问题之后,我们需要解决的是“马克思主义道德哲学的根本特征”是什么。应该说,“马克思的思想并非哲学史链条上紧密咬合的一环,而是改弦更张的变音。揭示马克思思想的创新性和革命性以区分马克思哲学与传统哲学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完成的任务。对马克思这样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思想家来说,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作为新思想开启者的他。”[3]同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道德哲学建立在马克思所创立的作为哲学史的“改弦更张的变音”的彻底的实践哲学基础上,它必然具有其建立在彻底的实践哲学基础上的独特性,这是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道德哲学的基本前提。
当代西方伦理学和马克思之前的西方道德哲学是以西方传统的知识论和逻辑规范为框架而建立起来的,即它们所要解决的问题,或它们对现实世界的提问方式,也即它们的“问题式”是“道德是什么”和与之相关的“为什么”。本质上,它们都是出自“解释世界”的思维方式。显然,知道如何去做并不意味着有能力开启一个行为,由此造成的“知旁落而无践行”正是人们的常态。原因在于,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有助于人们的道德认知、道德判断和道德反思,却不能全面有效地解决道德行为在客观世界中的现实化问题。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4]。当然,改变世界必有其目的,而对于马克思,此目的就在于自由和道德的现实化(这两者是相互关联的,甚至就是同一个问题)。在此目的下,道德哲学的问题式就转变为“道德如何现实化?”由此,在此崭新的问题式和改变世界的要求下,马克思以其彻底的实践哲学使道德真正地走出了纯粹的内在性。
具体地说,马克思扬弃了康德的作为内在精神活动的实践,在作为现实的、能动的感性活动的实践的基础上创立了彻底的实践哲学,其“彻底性”在于,马克思将其全部哲学建立在以人的感性活动为基础的感性世界中,并以“改变世界”为其实践哲学的主题,由此展开了以自由与道德的现实化为目的的历史维度。进而,“马克思的伦理观是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到成熟阶段,随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才完全确立起来的,是真正表达马克思主义革命精神的伦理观”[3],其道德哲学所关注的必然是人类历史的宏大背景下道德现实化的条件及其达成。也就是说,在马克思彻底的实践哲学视域下,道德和自由不再具有康德哲学中的彼岸性,而是具有条件性。进而,在“道德如何现实化”这一总问题下,马克思的道德哲学的研究域也转变为“道德现实化的条件是什么”和“如何促成道德现实化的条件”等。在此研究域中,马克思以唯物主义历史观、共产主义理论和其政治经济学等理论讨论了“使道德现实化的外部的物质和社会条件是什么”“不同历史条件下阻碍道德现实化的外部因素是什么”和“如何促成道德现实化的外部条件”等问题。
综上,马克思主义道德哲学的问题式,即对现实世界的提问方式,是马克思主义道德哲学的根本特征。对马克思主义道德哲学的问题式的挖掘不仅可以使一些隐而未发的问题得以显化,还可以使我们更为系统地阐发马克思主义道德哲学的理论内容。
3 发展的马克思主义道德哲学问题式及“跨主体性的能力/践行性的道德实践能力”
笔者在《论西方主流伦理理论的前提错误——兼论道德无力症与冷漠症对医疗的影响》[5]一文中尝试从(笔者在之前的系列文章[6-10]中所揭示出的)作为最深层次人性的人之弱点,即“畏死的恐惧”(也即“对生存性安全感意义上的匮乏的恐惧”,也可称为“生存性恐惧”,它包括物质性和社会性两个方面)出发,重塑扎根于生命的道德基础,即道德行为就是由人的本真的生命驱动力(慈)所推动的本真的生命实践,而“生-生”式的道德关系(即相互承认与尊重对方的人格并协同创生的互为目的的属人的社会关系。在其中,每个人都不把对方当作观察、研究与利用的客体或对象,更不把对方视为可操纵的工具,而是在相互合作的过程中扩展、创化和实现双方的生命)则是人的本真的存在方式。也就是说,道德(无论是道德行为,还是道德关系)是人的本真需要,更确切地说,是人的本真存在方式的需要。同时提出,道德实践的有效性依赖于道德主体具备的“践行性的道德实践能力”。而“践行性的道德实践能力”是指区别于道德认知能力、道德判断能力和道德反思能力的,践行道德实践从而形成“生-生”式的道德关系的能力。由于生存性恐惧是人们获得践行性道德实践能力的阻力,因此,“超越畏死的恐惧的勇气”是人们可以获得“践行性的道德实践能力”从而使得道德可以现实化为“生-生”式的道德关系的前提条件。
哈贝马斯认为“‘自我’是在与‘他人’的相互关系中凸显出来的,这个词的核心意义是其主体间性,即与他人的社会关联。唯有在这种关联中,单独的人才能成为与众不同的个体而存在。”[11]。由此可见,“生-生”式的道德关系便是具有“主体间性”的社会关系。笔者在《跨主体性的能力——从“畏死的恐惧”看跨主体性何以可能》[12]一文中讨论了“主体间性何以可能”的问题。具体而言,近代哲学开创的建立于唯我论视角下的狭隘的理性原则基础上的主体性哲学的失败引发了道德危机。作为应对,胡塞尔开启了“主体间性”的研究视域,后经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和哈贝马斯等的努力而不断地丰富和发展。然而,从胡塞尔开启“主体间性”的视域到现在已有一个多世纪的时间,人类现实中的道德危机和道德滑坡却并未改善,即“主体间性”并没能成为人类生活的现实。顺此思路继续思考,我们发现之前的思想家们都忽略了作为“主、体间性”现实化的阻力的“畏死的恐惧”,它是将个体封闭于“匮乏感”“恐惧感”和“狭隘的私利下的严格的私人性”的原因。进而,由于遗漏了此“主体间性”现实化的阻力,思想家们也就忽略了与之相关的可以使“主体间性”走入客观世界的个体的“跨主体性的能力”的问题,这使得胡塞尔、海德格尔和哈贝马斯分别将“主体间性”禁锢于思维、体验和关于“如何有效地对话与协商的知识”中,即不能在客观世界中现实化。进而,个体的“跨主体性的能力”包括独立能力、通达能力、公共能力和作为其基础的“超越生存性恐惧的勇气”。显然,只有具备了“跨主体性的能力”的个体,即“跨主体性的个体”(在笔者之前的论文中,也将“跨主体性的个体”称为“超个体的个体”)才能相互结成主体间性的关系(即“生-生”式的道德关系),即可以使“主体间性”得以现实化,也即使得道德得以现实化。进而我们发现,在道德领域,“跨主体性的能力”也便是前文的“践行性的道德实践能力”,而对“跨主体性的能力/践行性的道德实践能力”及其培养的相关问题的有效探讨是回答“道德何以现实化”的基础与前提。同时,如果说(道德认知能力、判断能力和反思能力等的)“认知性的道德实践能力”是建立在康德的作为内在精神活动的道德实践的基础之上的,那么“跨主体性的能力/践行性的道德实践能力”则是建立在作为感性活动的道德实践的基础之上的。
进而我们发现,从最深层次的人性,即作为人之弱点的“畏死的恐惧”(即“生存性恐惧”)理论出发,我们可以在继承马克思的问题式(即“道德如何现实化”)的基础上,对此总问题下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领域做进一步的发展,从而将研究的问题和领域拓展到“道德现实化的内在条件是什么”,进而探讨“道德实践的动力、阻力和能力是什么”“如何强化道德实践的动力”“如何消解道德实践的阻力”“什么样的主体具有践行性的道德实践能力/“跨主体性的能力”“如何使人们获得践行性的道德实践能力/跨主体性的能力”,和更具根本性的“如何帮助人们超越生存性恐惧”等问题。
4 当前医德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和积极的探索
严格意义上,我国古代医德主要是以师承的方式传承的。随着西方医学的学院式教育方式的引进,医德教育也打破了传统的师承。当前,我国的医德教育主要吸收西方的经验,即医学院校主要通过医学伦理学课程对医学生进行医德教育。近年来,我国在医德的教育方法和教育媒介上进行了一些新的探索,如引入PBL教学法、借用微博和微信等新兴网络媒体对学生进行医德教育、倡导多学科共同参与的医德教育等,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然而,这并没有真正打破以知识化形态存在的医德教育,即主要通过对医学伦理学原则的学习和借用医学伦理原则对道德现象的解释来提高学生的道德认识能力、道德判断能力和道德反思能力等的“认知性的道德实践能力”。正如高德胜在《知性德育及其超越——现代德育困境研究》[13]一书中所认为的,这种“知性德育”把道德作为知性的研究对象而仅仅从逻辑上进行探讨,它隔离于人的道德实践,也隔离于人的真实生活。知性德育这种割裂的、知性的运行逻辑,使现代德育走向抽象、虚假的困境而不能自拔。这种知性的医德教育也使得“医德医风理论相对抽象”[14],“医德教育只是停留在整个学术范围内的探讨,没有足够的行动践行这些理论”[15]。显然,知道“道德是什么”和与之相关的“为什么”,并不意味着可以开启道德行动。也就是说,这种医德教育方式没能让学生获得可以使得道德现实化为道德实践和道德关系的“跨主体性的能力/践行性的道德实践能力”,从而使得“知旁落而无践行”。医生的“践行性的道德实践能力”的缺失造成了医疗中的“道德冷漠症”(即医生所行的是一种冷冰冰的“道德”实践)和“道德无力症”(即医生明知按照伦理原则的要求自己应该如何行动,却不能真正开启道德实践)的道德失范现象,从而造成或加剧了医患矛盾。
可喜的是,近年来我国医德教育方面出现了一些突破“知性医德教育模式”的积极探索,如郭莉萍、王一方、杨晓霖等推动的叙事医学人文教育和平行病例,王明旭、张金钟等推动的旨在提供榜样力量的(面向全国医学院校的)抗疫英模事迹的系列宣讲活动,以及刘俊荣、刘虹等推动的身体伦理。本质上,这些探索都是尝试从不同的路径提升学生的“跨主体性的能力/践行性的道德实践能力”。显然,由于问题式、问题域和根本性障碍没有显化,之前的相关研究还没有形成体系。
5 呼唤发展的马克思主义道德哲学问题式下的医德教育范式的转换
我们首先总结一下前文的论述。
第一,“马克思的伦理观是什么已经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马克思的伦理观表达的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不同于其他伦理理论的独特性”“应该说,马克思哲学的出现,得益于马克思之前的哲学史乃至思想史。但更重要的是,马克思的出现改变了历史,因为他所要做的并非是在观念的历史中加进紧密贴合的一环,而是要改变人们看待历史和观念的方式。”[3]显然,最能揭示马克思主义道德哲学的独特性的,便是其革命性的对现实世界的提问方式,即“道德如何现实化”这一问题式。在此总问题下,马克思以其唯物主义历史观、共产主义理论和政治经济学等讨论了与道德现实化的外部条件相关的诸多问题。
第二,从被前人忽略的作为道德实践的阻力,和作为人们获得“跨主体性的能力/践行性的道德实践能力”的阻力的“生存性恐惧”出发,我们可以对马克思主义道德哲学的问题式,即“道德如何现实化”这一总问题下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领域做进一步的发展,从而将研究的问题和领域拓展到“道德现实化的内在条件是什么”,进而探讨“道德实践的动力、阻力和能力是什么”“如何强化道德实践的动力”“如何消解道德实践的阻力”“什么样的主体具有践行性的道德实践能力/跨主体性的能力”“如何使人们获得践行性的道德实践能力/跨主体性的能力”,和更具根本性的“如何帮助人们超越生存性恐惧”等。
第三,虽然存在一些突破的尝试,我们当前的医德教育仍囿于“知性医德教育模式”,即以医学伦理学课程和医学伦理学原则为核心,着重培养学生的道德认识能力、道德判断能力和道德反思能力,容易造成医学生的“知旁落而无践行”的局面。
与之前的道德哲学家所倡导的道德培养的路径不同,马克思认为道德建设的根本路径是改变现实存在。从上述讨论中我们可以发现,外在的种种现实存在的改变的根本目的指向了作为内在的人的现实存在的道德能力,尤其是“跨主体性的能力/践行性的道德实践能力”这种可以启动感性的道德实践从而使得道德走出纯粹的思维性而在客观世界现实化的能力的提升。同时,马克思认为人的能力是“最大的生产力”[16],“人的能力的发展也成为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的动力和源泉所在,因为一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成果都是人类能力的对象化和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 ”[17]。显然,可以将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的能力更多地指向了建基于感性实践之上的实践能力,也就是说,改变世界之要求的现实化最终要落实到人的感性实践的实践能力的提升。由此我们发现,当前的医德教育急需范式的转型,即从“知性医德教育模式”转为着眼于使医德现实化的“践行性的实践性医德教育模式”,即在对道德认知能力、道德判断能力和道德反思能力等的“认知性的道德实践能力”的培养的基础上增加对“跨主体性的能力/践行性的道德实践能力”的培养,即“……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沉睡着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制。”[18]
进一步地,对“跨主体性的能力/践行性的道德实践能力”的培养的关键在于引导学生对“生存性恐惧”的超越,即对“超越生存性恐惧的勇气”的培养。显然,如果我们无视当代人类所面对的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现实的具体的“生存性恐惧”,则我们的道德教育便会成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批判的“道德说教”,即那些脱离于实际和隔离于人的现实生活,从而不能反映现实的人的真实需求的空洞而又无力的道德理论和道德教育。进而,只有从作为当代人类现实的“生存性恐惧”出发的,反映了当代人类的真实需求的道德教育,才是彻底的和能说服人的,才能转化为物质力量,进而才是可以“改变世界”的道德教育。
显然,对“跨主体性的能力/践行性的道德实践能力”的培养路径和对“生存性恐惧”的超越(即对“超越生存性恐惧的勇气”的培养)路径都需要系统地研究与实践。由此,我们呼唤发展的马克思主义道德哲学问题式的视域下的医德教育范式的转型,即在研究和实践上从“知性医德教育模式”转变为着眼于使医德现实化的“践行性的实践性医德教育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