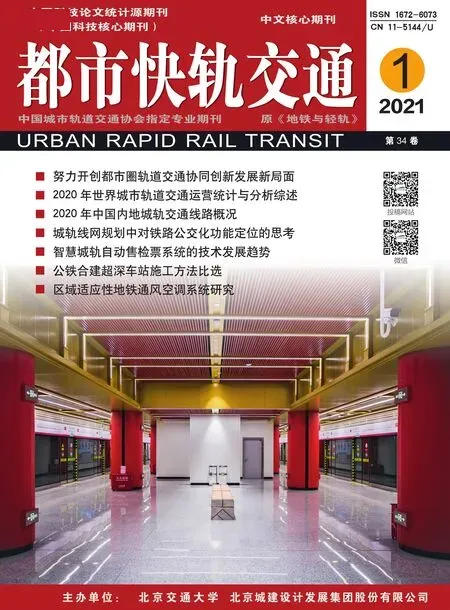智慧城轨自动售检票系统的技术发展趋势
杨承东,刘 洋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武汉 430063)
1 AFC 系统的目标和存在的问题
随着移动互联网、信息化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模的不断扩大,“智慧化”已成为轨道交通技术发展的新趋势。2020 年3 月,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发布了《中国城市轨道交通智慧城轨发展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开启了智慧城轨建设的序幕。其中,通过提升票务服务的智能化水平从而创建智慧乘客服务体系是《纲要》的重点之一。《纲要》明确了自动售检票(automatic fare collection,AFC)系统的2025 年目标:“智能售检票的实名制乘车、生物识别、无感支付、语音购票等普遍采用,各城市间乘车畅行无阻,智能票、检合一的新模式普遍应用;智慧车站的自动开关站、语音问询、信息服务、动态引导、环境调控等服务功能齐全;智能列车的信息服务温馨实用、个性化需求多样完善;紧急情况下智能管理、引导与应急疏散客流,乘客服务安全有序;智能线网运力服务精准匹配、安全、快捷、高效。”[1]
在智慧城市轨道交通发展的新形势下,自动售检票系统在系统架构、数据传输、支付方式、互联互通等方面的建设相比传统模式有着较大的差异。同时,由于国内城市轨道交通AFC 系统的建设标准不一、所处阶段不同、信息化建设进程差异较大,尤其是对智慧城轨发展形势下的AFC 系统认知程度深浅有别,导致乘客使用不便、系统改造频繁、互联互通性差等问题[2],不利于轨道交通AFC 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针对以上问题,迫切需要根据智慧城轨的AFC 系统需求,结合国内各城市AFC 系统的发展现状,总结归纳出新形势下的AFC 系统技术发展趋势,以便于长远地指导城市轨道交通线网AFC 系统的建设与运营。
2 智慧城轨对AFC 系统的需求
随着国内城市轨道交通的快速发展,网络化与智能化运营时期已经到来。在智慧城市轨道交通发展的新形势下,AFC 系统需求成为智慧乘客服务系统建设的关键制约因素,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 系统架构精简化。精简化并非是系统功能的缺失,而是在保障线网AFC 系统正常运营的情况下,结合本地的线网规模、线路建设、系统投资等因素,高效利用各种资源,实现AFC 系统架构的精简,降低建设、运营、维护成本。
2) 高峰客流及突发大客流条件下的客流数据实时监测以及客流疏导。在日常高峰客流及大客流条件下,轨道交通车站的客流拥堵已成为常态,站台乘客安全隐患亟需解决;需要通过AFC 系统终端设备实时上传客流数据,为运营管理部门动态监测和疏导客流提供决策参考。
3) 提供基于生物识别等技术的智能化、无感化票务服务。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以及生物识别技术的发展,车票已经逐渐演变为乘客乘坐轨道交通的凭证,用生物识别等技术实现智能化、无感化的票务服务是提高运营服务水平的关键。
4) 解决客流通行效率与安全防控高要求的突出矛盾。随着轨道交通线网客流的与日俱增,以及安检和反恐防范要求的提高,高峰小时客流通行受到人工安检效率低的影响,存在客流拥堵情况严重、运输能力未充分利用、乘客投诉频繁等问题,亟需探索更加智能化的安检、票检模式。
5) 基于三网融合以及城市群、都市圈发展的互联互通服务。随着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城市群的规划政策逐渐明确,市域轨道交通也成为轨道交通领域的重要发展分支之一,城市群之间的互联互通刻不容缓。在此背景下,实现城市间AFC系统的互联互通成为了迫切需求,票务服务须由单城市向城市群、都市圈演变。
6) 实名制乘车。若要有效满足上述需求,实名制乘车是关键,其中实名制是智慧乘客服务的基础支撑条件。
3 AFC 系统的技术发展趋势
结合新形势下的轨道交通AFC 系统需求以及发展现状,笔者得出AFC 系统的技术发展趋势,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精简化系统架构、交易数据实时上传、票卡虚拟化及支付多元化、安检票检一体化及乘车实名制、互联互通。
3.1 精简化系统架构
随着国内城市轨道交通的快速发展,传统AFC 系统的建设思路和系统架构基本稳定成熟,各线路一般独立建设,采用标准5 层系统架构(清分中心ACC、线路中心LCC、车站计算机SC、车站设备层SLE、票卡层)[3]。但是,这种建设模式增加了中心级设备采购、应用软件开发、维护等费用,同时也需要增加大量的电力、人力、用房等资源。考虑到多线独立建设线路中心导致运营管理的复杂程度增加,逐步衍生出多种AFC 系统架构变体,如北京采用多线共用AFC系统线路中心、南京采用区域控制中心等取代单线路中心[4-5]的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系统建设投资,节省了运营维护的工作量和人力资源,但这并未从根本上解决资源共享率低、系统扩展难度大等问题。近年来,温州市域铁路、广州地铁、郑州地铁、成都地铁、洛阳地铁等陆续将清分中心、线路中心进行整合,形成清分中心、车站、设备层、车票的4 层系统架构,不仅实现了网络化运营管理,还达到精简系统架构、高效利用资源的目的,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与此同时,随着互联网支付以及云计算技术的快速发展,基于云平台的“互联网+AFC”系统架构成为了主流建设模式。全国所有在建轨道交通的城市将互联网票务平台纳入了AFC 系统的同步建设,并实现了互联网支付功能;同时温州、郑州、成都、深圳、呼和浩特、太原、洛阳、金华、哈尔滨等城市已经明确,采用城轨云平台搭建AFC 系统[6]。
可以看出,各大城市已经不同程度地根据本地的交通状况、线网规模、运营管理需求等,对AFC 系统架构进行了灵活的调整和优化,传统的AFC 系统5层体系架构已逐步被基于云平台的“互联网+AFC”精简化系统架构所替代。
3.2 交易数据实时上传
在日常高峰客流以及大客流条件下,车站客流拥堵已成为常态。为保证车站(尤其是站台)乘客的安全,采取进站限流、增开列车以及站台客流疏导方式,已成为运营管理部门常用的客流组织手段。然而,这些客流组织手段目前大多依赖于人工,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另外,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根据各地区防疫指挥部的要求,需要通过乘客的动态出行数据进行大数据分析,从而实现更有效的客流动态管控。为此,国内轨道交通已逐步开展依据车辆称重传感器、人脸识别摄像头、售检票设备来动态监视车站站台的客流拥挤程度以及控制客流等方面的研究[7]。但是,由于客流数据并非实时上传,导致设备只能起到监视效果,在客流控制方面仍然依赖于人工与传统的管理模式,亟需通过票卡交易数据的实时上传,辅助运营管理部门进行智能化的决策。
AFC 系统交易数据主要包括单程票、储值票的进站、出站记录等,通常是间隔15 min 甚至更长时间统一采集后进行上传,而且受到传输层级较多(SLE-SCLCC-ACC 逐级上传)的影响,到客流数据解析时已产生较大的延时,难以作为动态疏导客流的数据支撑[8]。为此,各大城市已经逐步开展了AFC 系统交易数据实时上传的研究,同时结合站台人脸识别摄像头,以及车辆称重传感器的动态监测数据,实现动态的客流监测;通过提前设定的站台乘客阈值,使闸机控制进站客流,在达到阈值时告警,并提供动态客流控制手段给运营管理部门决策参考。目前,温州市域铁路的AFC 系统票卡交易数据采用“SLE-SC-ACC”3 层实时数据传输架构;广州地铁新线将传统5 层架构系统调整为票务交易数据,采用“SLE-ACC”2 层实时数据传输架构。
交易凭证数据的实时上传已成为实现车站站台客流动态监测与控制的关键制约因素,精简的交易凭证数据实时传输结构能帮助实现交易凭证数据的实时上传,可为动态、精准地控制车站客流提供数据支撑。同时,通信传输系统为AFC 系统提供大带宽、低时延的网络通道,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基础。
3.3 票卡虚拟化及支付多元化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以及生物识别技术的发展,车票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实体卡片,它演变为乘客乘坐轨道交通的实体或虚拟凭证,如手机二维码、手机蓝牙、人体生物特征等。目前,轨道交通采用互联网支付方式过闸的乘客比例正逐步提高,据不完全统计,已有17 座城市的地铁互联网过闸客运量占比达到30%以上。同时,各大城市正对生物识别过闸进一步深入挖掘,人脸识别技术已在北京、济南、深圳、郑州、天津、贵阳等城市的地铁AFC 系统中应用,全态识别技术在南宁地铁试点研究,虹膜识别技术已在福州地铁中应用。
同时,随着电子支付在轨道交通中的推广应用,AFC 系统支付方式已由单一的刷卡支付逐步发展为多元化支付[9],乘客可以任意选择使用支付宝、微信、银联云闪付等方式实现过闸与扣费。同时,随着生物识别技术在轨道交通AFC 系统的逐步应用,可通过关联乘客生物及非生物特征、身份、信用支付等信息,将各类支付方式设置为不同标签,系统根据支付标签进行乘客配对完成扣费。目前,广州地铁新线拟通过关联乘客生物及非生物特征、身份、信用支付等标签信息,使AFC 系统按需与乘客信息库进行数据交互,以实现精准的票务服务。
另外,随着央行正式发行法定数字货币并开展相应的应用试点,轨道交通将成为使用频率较高的场所之一。法定数字货币具备流通性强、安全性高、可控匿名、支付交易便捷等优点[10],其首要取代的是AFC系统现金流通类业务。法定数字货币不仅能够获得与支付宝、微信等第三方支付平台同样的支付体验,无需与商业银行接口,而且还能实现“双离线”交易,为AFC 系统实现去现金化、支付体验便捷化、收益审核精准化提供了重要的支撑。综上所述,票卡虚拟化及支付多元化从根本上克服了乘客购票、充值等带来的不便,解决了现金交易产生的运维繁杂等问题,能够减少现金交易,降低运维成本,提升乘客服务质量。
3.4 安检票检一体化及乘车实名制
随着轨道交通线网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安全防控要求的不断提高,客流通行与安检之间存在的矛盾逐渐凸显。在传统的建设模式下,票检与安检是独立运营的两个系统,通常采用先安检后票检的通行方式。由于数据信息不互通,安检与票检工作相对独立,容易引发进站客流的拥堵。为加强安检、票检的信息互通,提高安检、票检的效率和服务品质,《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规定》[11]以及《纲要》中明确提出,鼓励实行安检新模式,探索票检、安检合一的新模式。
目前,国内一线城市已逐步开展票检安检一体化方案的应用研究。上海地铁在部分站点试点“安检、票检快捷通道”进站措施,乘客可持METRO 大都会App 通过“安检、票检快捷通道”刷码进站乘车;武汉地铁开展试点研究,通过大数据采集将乘客按白、灰、黑名单进行分级,完成人脸采集的白名单乘客可通过“安检、票检快捷通道”,灰、黑名单乘客仍采用传统的安检方式。此外,郑州、西安等城市已经在进行依据人脸识别的安检票检一体化实践。
可以看出,安检票检一体化模式通过乘客身份辨识进行分流,为部分乘客提供快捷通道,能够实现精准防控、安全高效兼顾的目标,是解决客流通行和安检的突出矛盾的重要手段,也是未来安检、票检新模式的发展趋势。
然而,安检票检一体化模式需要对乘客进行精准、有效的信息采集,离不开乘车实名制。同时,随着生物识别技术在轨道交通AFC 系统的逐步应用,推行地铁乘车实名制,从而帮助构建地铁乘客信用体系,也是未来AFC 系统的研究重点。
2020 年1 月以来,全球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进入关键阶段,轨道交通运营管理部门可通过乘车实名制,达到乘客出行信息可查询、可追溯的目的,从而确定出行者中是否已有人被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或是病例的密切接触者。目前,全国多个城市实施了乘车实名制:深圳地铁线网已全面启用实名制乘车,通过构建“三户模型”实现实名制、账户制,确保乘客信息可查询、可追溯,实现对重点疑似人员的行程轨迹有效跟踪;广州地铁宣布,实行扫码实名乘车;青岛市公共交通和出租车行业实行实名制;武汉地铁采用“实名登记、亮码出行”的方式。
综上所述,安检票检一体化以及乘车实名制化,可以提高安检、票检的信息互通性,有效解决客流通行效率与安全防控之间的矛盾,能够帮助构建地铁乘客信用体系,还能在保障市民健康安全出行方面提供信息追溯渠道,这将成为未来AFC 系统行业内的研究重点和发展方向。
3.5 实现城市间的互联互通
互联互通关键解决的是乘客在轨道交通中实现“一票出行”[12]。目前,我国有两个全国性的储值票卡形式的互联互通项目,分别为住建部和交通部主导的全国一卡通互联互通项目。从票卡应用和支付方式看,有传统IC 卡支付方式、银联闪付支付方式,都已具备城市内、城市间的互联互通基础,可满足乘客市内以及城市间的出行需求,缺点是清分体系和票卡管理复杂。近年来,随着“互联网+AFC 系统”建设进程的加快,以二维码为代表的移动支付技术在轨道交通行业内发展迅速,然而二维码技术应用时缺乏统一标准,难以直接地互联互通。与此同时,随着生物识别技术的快速发展,人脸、虹膜、掌静脉、指静脉等识别技术已逐步试点应用于AFC 系统,互联互通问题也有待解决。
实名制信用消费将是未来乘车凭证互联互通的发展趋势。随着智慧地铁的建设,乘客实时信息是智慧城轨大数据应用的主要源数据之一,各个城市的地铁官方App 是为乘客提供精准服务的重要窗口,智能票务业务是地铁官方App 的主要功能,连接各个城市地铁的官方App 成为互联互通的刚需。
随着城市群的规划政策逐渐明确,实现城市群之间的互联互通工作已经刻不容缓。目前,使用“Metro大都会”App 的乘客已经可以在上海、杭州、宁波等13 个城市的轨道交通“一码”畅行;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主导的城轨易行平台已经连接了10 多个城市,旨在得到全国地铁的认同,通过后台换码的技术路线,使各个城市的地铁官方App 都能漫游到其他城市,达到乘坐地铁可互联互通的目的;金义东市域轨道交通要求金华、义乌及东阳3 个城市的“市民卡”以及交通运输部一卡通、银联云闪付、第三方支付、江浙沪一码通等,都可在金华市轨道交通领域内使用;广州地铁通过互联互通规划统一票务技术标准,初期实现广佛线网内所有票种的无障碍付费区互融互通,近期实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内的“一票通”。
由此可以看出,加强城市间的联系已成为迫切需求,实现城市间的互联互通已成必然,城市轨道交通AFC 系统规范即将发布,不同城市“互联网+AFC”系统的业务流程和数据规范将逐步标准化,百花齐放的互联互通局面正在形成。
4 结语
随着国内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的大力推进,以及云计算、电子支付、生物识别等技术在AFC 系统中的不断推广应用,AFC 系统已成为提升乘客服务质量的关键之一,其系统建设也越来越受到重视。精简化系统架构、票卡交易数据实时上传、票卡虚拟化、支付多元化、安检票检一体化、乘车实名制化、互联互通的实现,能够很好地解决投资浪费、运营管理难度大、乘客使用不便、互通性差等问题,可为智慧城轨尤其是智慧乘客服务体系的建设提供较大的研究和应用价值,有利于城市轨道交通AFC 系统的可持续性发展。此外,AFC 系统作为轨道交通的重要安全生产系统之一,其外部、内部网络均有可能受到网络攻击,导致数据丢失、信息泄密甚至是系统瘫痪,信息安全也将成为智慧城轨AFC 系统的重要建设发展方向,从而保障轨道交通AFC 系统的安全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