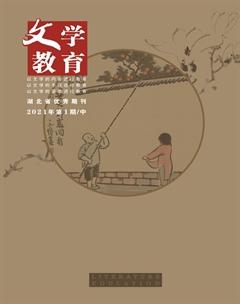《传习录》及阳明学在日译介发展
石新卉 罗琬莹
内容摘要:《传习录》作为王阳明思想的集大成之作,阳明学派的“教典”,在其东渡日本传播之时,各家翻译者或多或少会受限于学识储备、时代背景等因素,导致所编译本之间存在不可避免的理解偏差。本文旨在通过研究不同译本,探究《传习录》的在日传播历史和译介发展状况,分析阳明学所经历的日本本土化过程,为译介学的进一步发展和中华文化向世界传播提供宝贵经验。
关键词:阳明学 《传习录》 日本阳明学
《传习录》是我国古代哲学著作,由王阳明的门人弟子整理其语录和信件编撰而成。书中不但全面阐述了王阳明的思想,也体现了他辩证的授课方法,以及善于用譬、常带讥讽的语言艺术。本书是王阳明一生最重要的代表作,对研究王阳明心学思想有着重要的意义,是儒家思想中最具个性、最具争议的著作之一。
由此我们可想而知,《传习录》在登陆日本时,曾掀起过怎样的浪潮,以至于日后在明治维新中,我们仍能感受到《传习录》的影响余波。而《传习录》的传播、演化与进步,都与译介有紧密且重要的联系。
所谓译介,由字面来看,就是“翻译、介绍”的意思。翻译是促成不同民族文学间发生交集的方式之一,译者也往往与“个人媒介者”重合。通常,我们能够找到《传习录》在同一语种下的各种不同译本,而每份译本中,又因为时代背景、译者主观意见等因素,导致译文与原文意味产生或大或小的差池。
本文撰写目的在于研究《传习录》在日本不同历史时期的传播情况和其造成的社会影响,并通过研究《传习录》的不同译本,来观察在不同时期、不同社会现实影响下译介的发展演变,以期日后能够对文献翻译、译介学发展做出贡献。
一.《传习录》与阳明学传播的坎坷之路
江户时代,《传习录》同阳明学一起传入日本。当时,日本思想界正值大动荡时期。其原因一方面是日本加强了同中国和朝鲜的交流,中国先进的思想成果如洪水般涌入日本国内,大受欢迎。然而由于唐本价高,为了满足读者需求,当时书籍的和刻版多以唐本韩版为祖本,这才得以批量发行。阳明学和《传习录》本来也应走这样的道路,然而对立阵营的朱子学派捷足先登,将反阳明学的刊物输入了日本。另一方面,当时中国学术思想界也进入了阳明学反省期,《求是编》《学蔀通辩》等书籍原为反阳明学非主流,但由于尊朱子学为正统思想的李氏朝鲜反应过激,保护朱子学的护教书发行后,反而比《传习录》更早登陆日本。
因此,《传习录》与阳明学在日本从一开始就是被当做“错误的思想体系”所接纳的。但中江藤树在读完王阳明著作后,成功地吸收了阳明思想,成就了自己的思想體系。
二.江户时期《传习录》在不同译者笔下的演变与发展
1650年,中江藤树去世。其遗著出版的同时,《传习录》和刻版也随之出版。此次和刻版以1602年刊行的杨嘉猷刻本作为祖本。在随后的1652年至1653年间,《传习则言》和《王阳明先生文录抄》的和刻版也相继出版面世,至此,诠释王阳明思想的教材已基本集齐。此后,杨嘉猷和刻版的《传习录》一直占据着通行本地位,直到1712年三轮执齐所著的《标注传习录》出现为止。
师从于佐藤直方的三轮执齐本是朱子学的狂热追随者,但他在阅读《传习录》之后倒向了阳明学一边,之后更是花费十五年时间将《标注传习录》一书编撰而成。
著书时,三轮执齐的主观意见也对《标注传习录》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尽管杨嘉猷本被当做祖本,但其收录的《咏学诗》为了在朱子学徒面前吃到甜头,批评“阳明学是禅”。三轮执齐厌恶这种做法,于是便将《咏学诗》删除,重新添加了《大学问》、《略年谱》和最初的标注。此书发行后在读者中大受欢迎,确立了通行本的地位。
幕末儒学界的泰斗佐藤一齐也是《标注传习录》的追随者。1837年,他把之前一直记录在书栏位外的摘录整合成了一本书,即为《传习录栏外书》。
至此可见,江户时期的阳明学运动中,中江藤树、三轮执齐、佐藤一齐和三人所归属的门派各有千秋。可以说,作为最初和刻本祖本的杨嘉猷无注释版《传习录》、《标注传习录》和《传习录栏外书》,它们各自代表着成书时期作者之于阳明学的独到理解。
日本阳明学与中国阳明学的最大不同在于,它不像中国的阳明学那样是以时代要求为动力而产生的思想。而因为忽视了中国阳明学这一历史特质,有不少人把阳明学看作是“内心精神上的自立”、“打破既有规范秩序的良知的跃动”的学问,即认定阳明学是发挥内心主体性的学问。例如熊泽蕃山在《集义和书》中将阳明学称为“自反慎独之功”、“治心之心术”;山鹿素行在《山鹿语类》中称阳明学为“骋聪明矜意见”、“放荡”。这种看法是将中国的阳明学与日本阳明学的特质相混同的。
三.社会潮流下《传习录》与阳明学的新释义
在第三次阳明学运动中,一齐门下的后起之秀于幕末维新时期十分活跃,可以说是竭尽所能。他们成立以阳明学为基本纲领的结社,发行相关的机关杂志,加入新的资料和注解,将《传习录》重新刊行。门人们发起的阳明学运动影响深远,甚至蔓延到了明治和大正时期。这是因为在明治时期,西欧基督教文化传入,洋学夺取了学术思想界的主导权,而被认为以一己之力就能够游刃有余地与西洋舶来新思潮抗衡的人,正是拥有心学思想的王阳明。
正如三岛由纪夫在《作为革命哲学的阳明学》中所说:“在我看来,作为神秘主义的国学和能动的虚无主义的阳明学为明治维新打下了基础。”人们利用阳明学为洋学的传入和渗透铺路,又因反欧化主义风潮的出现使阳明学复兴运动应运而生。同时,日本阳明学从“心即理”中演化而出的“尊重个性”、“无惧权势”等打破旧有的理念,为维新运动培养了大批人才。以《传习录》为始的阳明学系教科书的广泛普及,也为传播阳明思想做出了卓越贡献。
明治四十一年,结城蓄堂在《阳明学》2号《儒学沿革与王阳明》中谈到:“维新之时,蹶然而起致力为国并举事功之人中多有阳明学者,此乃时势使然……王阳明以其实践为主,于文于武,概不介意生死;不论难易,对其所接触之事物必遂行而后已,此诚酷肖我士风,相距不远。”明治四十五年,亘理章三郎在《阳明学》42号中提出:“首先我们要知道阳明自身的人格是进步的。他既不墨守旧有的儒家学说,也不盲从社会风潮,专一地以其心为本,致力于日日革新……正因阳明一生以日新之志自勉直至生命的尽头,所以他的学风是活泼泼的、向上而进步的。拘泥、墨守、因循等停滞、退步的倾向都与他无缘。”
从中可以看到,原本在中国阳明学中,发挥人的道德本性这一命题是以孝悌慈为内容的;而经过代代译介发展与演变,在日本阳明学中,孝悌慈这一内容已被剔除。不知何时,它被普遍化为一般道德与一般的心,独自产生出精神上的自立与进取、变革、超脱生死、神佛、日本性、宇宙性等顺应潮流方向的新意义。
四.译者的“叛逆”与适应民族的去粗取精
谈及《传习录》及阳明学对日本发展的影响,我们可以从侧面角度观察。在20世纪20年代左右,日本阳明学研究进入低谷阶段,侧重表现大致为点状式研究,甚至对阳明学的关注仅集中于《传习录》。二三十年后,在安田二郎和岛田虔次的带动下,阳明学研究才在日本社会逐渐被重视。岛田于《中国近代四位的挫折》中提出,阳明学在中国的发展状态处于末流,那种被痛斥为社会性弊病的社会认知状态,同其传播至日本时被赐予高评价的状态不同,“甚至还被看成是明治维新的一个精神动力”。阳明学,或者在一定时期内的《传习录》,都对明治维新创造了精神上的推动条件,也为日本社会思想构建创造了辩证前进的机会。
“日本阳明学”更类似于一个因阳明学及同类文化的传播而兴起于日本社会的思想活动。在“日本阳明学”兴起的一段时间内,三宅雪岭等运动发起人根据日本近代社会思想进步的需求,撰写、编辑了关于阳明学的教育传播类小册。随着时间推移,译介水准与时俱进,这也为《传习录》和阳明心学在日本的传播发展提供了极大便利。
明治维新时期思想文化的发展,极大地活跃了人的思维,激发了译者个人意识的高度觉醒。为了促进民族觉醒和优良文化传播,译者、研究者在译介当中的“叛逆”便体现出来,他们将原版阳明学做了挑拣和切割,从中摄取对日本社会发展具有积极意义的内容,再进一步做出改动和延伸。而在日本民族传播阳明学的过程中,也有许多为了自我发展,而在原本基础上对思想理论进行虚构的情况。就好比高濑武次郎的“大凡阳明学含有两种元素,一曰事业性的,二曰枯禅性的”这一分裂阳明学正负面影响的阐述,在那个年代具有极深的政治讽刺意味。
五.结语
相比于翻译,译介更注重在文化差异之下,对一份作品进行适当的改动,让其更容易被理解和接受。因此,译介要比纯粹的翻译更多一分“叛逆”,多一分对于文学文化的研究、探讨。同样,日本间断汲取阳明学,也是选择了片面却极有特色的信息点,使用《传习录》作为其思想代表,从点推面,以便自己在日本本土环境下更好地消化阳明文化。于己而言,这的确是事半功倍的良方。
在文化传播中,叫人“接受”是第一步,随即才能够有深入的二三四步。要在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下更好地传播中国文化,对译介方面的研究定不能少。我们在深入研究本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同时,也不能忘记与其他文化之间的差异。我们需要理解、包容,并积极了解他国文化,这样才能在从事译介、传播工作时主动抓住要点,成就更多既不失中华本质特色,又便于他国理解的优秀译介作品。
参考文献
[1]松岡正剛(1936)『松岡正剛の千夜千冊』[M].岩波文庫.
[2]水野博太(2014)明治期陽明学研究の勃興——井上哲次郎『日本陽明学派之哲学』に至る過程][J].『思想史研究』、24:68-85.
[3]溝口雄三(2010)『伝習録』[M].中央公論新社.
[4]溝口雄三.孙军悦,李晓东.中国阳明学与日本阳明学[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5]吉田公平(1988)『王陽明「伝習録」を読む』[M].講談社学術文庫.
[6]吉田公平(2018)[日本近代—明治大正期の陽明学運動][M].『国際哲学研究』,7:181-188.
[7]邓红.日本阳明学与中国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52-63.
[8]王建瑞.浅谈日本阳明学对明治维新的影响[J].神州,2012,(11):26.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