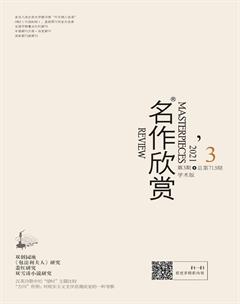“方向”所指:对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流变的一种考察
摘 要:赵树理1947年被定位为“方向”,在经历了短暂的追捧后,就饱受争议。但他从决定成为一名“文摊”作家后,就一直坚持自己的创作原则,文艺界对其评价不断发生变化。通过分析这些变化,可以探究赵树理与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之间的关系,透视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在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的流变轨迹。
关键词:现实主义文学思潮 赵树理 关系 流变
赵树理在文学史上是一个特殊的存在,1947年他被树立为解放区文学的“方向”,向着赵树理方向迈进成为当时解放区作家努力追求的目标。但属于他的黄金时代非常短暂,1949年以后赵树理依然坚持自己的创作,却遭到了严厉的批判。对赵树理的评价从赞扬到否定,绕不开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现实主义”。作为曾经被树立为“方向”的作家,赵树理的命运沉浮能够很好地折射出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变迁过程及内在理路。
一、现实主义的选择
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严重阻碍了现实主义的发展,直到主流思潮选择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种情况才有所转变。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起源于苏联,1933年11月,周扬发表了《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介绍到中国。他批评了“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过于强调作家的主观态度,将作家的世界观等同于作品的错误。周扬还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进行了解释,认为它是真实的、发展的、具有典型性的,并将革命的浪漫主义包含在其中。可以说,从一开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就带有了浪漫主义的特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出现是为了对抗“左”倾机械论,以及摆脱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其产生确实昭示着现实主义思潮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周扬的这篇文章,为现实主义思潮在我国的发展奠定了基调。虽与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相比,它更侧重于阶级性、时代性和理想性,未能彻底摆脱“左倾”的消极影响,但很大程度上起到了纠偏的作用。《讲话》的某些精神内涵也与周扬的这篇文章有异曲同工之处。
1942年,毛泽东在《讲话》中正式提出主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次年,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与《李有才板话》出版。据学界研究,赵树理并不是为了迎合《讲话》才写了这两篇小说。实际上,他一直坚持着这样的写作,甚至不被理解和重视。据杨献珍回忆,《小二黑结婚》一直未能出版,彭德怀过问后,问题才得到解决。出版后受到了人民群众的喜爱,太行区的销售量就达到了三四万册,并被多次改编为秧歌剧。但很多知识分子仍看不起这部作品,认为是“低级的通俗故事”a。可见,《讲话》发表后,仍有许多作家对大众化持有抵触态度。《讲话》所提出的精神需要不断被阐释,才能确立其地位,此时周扬发现了赵树理。赵树理的人生经历以及文学创作与《讲话》呈现出惊人的契合。创作初期,赵树理受“五四”影响至深。1925年,他来到长治师范学校读书,首先接触到的就是新文学。但是当他把新文学作品读给父亲听时,父亲却毫无兴趣。赵树理意识到了新文学与农民之间的鸿沟,于是他主动从知识分子向农民转变。“为农民写作”的思想占据上风,他决定要做一个“文摊”文学家。《讲话》要求的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确立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在赵树理这里得到了实现。
1946年,周扬在《论赵树理的创作》中给予了赵树理很高的评价:“赵树理同志的作品是文学创作上的一个重要收获,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践的一个胜利。”b周扬着重强调了赵树理小说的人物及语言,他认为过去作家们塑造的农民大多都是落后的,而赵树理塑造了积极人物的典型;赵树理使用的是群众的语言,完全符合民族形式,并且真正以平视的眼光去书写农民。周扬的这些评价,可以反映当时现实主义思潮的某些特点。20世纪40年代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继承了30年代周扬对其进行阐释时提到的特质,如典型性及阶级性。周扬认为,赵树理将人物放置于斗争的环境中,写出了阶级斗争的曲折与复杂。他还对赵树理讴歌新社会、新人物进行了肯定,其实就是为了重申《讲话》的“写光明为主”的思想。同时周扬也肯定了赵树理批判农民消极方面的做法,认为这样的描写更具教育意义。不论是《讲话》,还是周扬的评价,都体现出教育功能与民族形式是这一阶段现实主义关注的重点。而阶级性一直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所强调的,但周扬对赵树理写消极人物的肯定性评价,说明此时主流思潮对真实性还是有较为理性的认识,它的矛头指向依然是教条主义。
二、浮出地表的赵树理
如果说1946年赵树理微微崭露了头角,那么1947年他才真正浮出了历史地表。1947年,陈荒煤做了《向赵树理方向前进》的发言。“赵树理方向”被正式提出,其作品也成为衡量解放区文学创作的标尺。陈荒煤将赵树理的创作概括为:政治性强、运用大众语言和民族新形式、高度的革命功利主义。与其说这三点是赵树理小说的特点,不如说是中国共产党所希望见到的现实主义。此时的文学创作需要反映阶级斗争,需要采用民间艺术形式,还要具有革命功利主义。赵树理的小说在形式上符合此时现实主义的要求,他致力于借鉴民间资源,作品的民族化风格非常鲜明。另外,其创作带有很强的功利主义色彩,他是为农民而写作,“我在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所要写的主题”c。而《讲话》后解放区兴起的大众化更是出于教育群众、宣传革命的功利性目的,当然,在赵树理这里为政治服务可以约等于为农民服务,这时赵树理是符合《讲话》要求的。但当为政治与为农民出现矛盾时,赵树理与政策之间就会出现裂隙,这也是赵树理最终被抛弃的原因。所以陈荒煤所言赵树理小说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
陈荒煤认为赵树理揭发了地主的阴险凶毒,将地主阶级和新农民阶级两个阵营划分得非常清楚。但是赵树理的小说没有显示出如此强的政治性,《小二黑结婚》是为了批判封建势力对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的迫害,反面典型金旺是村干部;《李有才板話》是为了让人们重视土改的工作作风问题,阶级对立不是小说表现的重点;《李家庄的变迁》或许是这几部小说中最具有政治性的,但并非所有的地主都企图破坏革命,如福顺昌掌柜王安福就是一个正面形象。在革命政治叙事的背后,隐含的是民间伦理叙事。二诸葛、三仙姑等人虽是愚昧封建的代表,但赵树理是基于传统伦理对他们进行批判。《李家庄的变迁》的导火索也是外来户与本地人的矛盾,主人公铁锁遭到欺压,首要原因是外来户的身份,而非农民身份。但茅盾及郭沫若等都努力阐释小说中的阶级性与政治性,避开了赵树理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存在的差异。
或许在周扬等人看来,赵树理小说是否真的存在政治性、阶级性等特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阐释让其小说具有这些特点,以此逐渐建构他们所需要的现实主义。赵树理与《讲话》贴合的一面被强化,如向农民学习。1942年,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明确要求与群众广泛接触,从农民身上汲取有益养料。赵树理不符合《讲话》的一面则被故意遮蔽起来,如《讲话》要求文学作品反映的生活应当比实际生活更具有典型性和理想性。这种浪漫主义在赵树理的小说中并没有体现,其小说是缺乏抽象性的,所体现的也是具体问题和实际生活。这一方面反映出,当时的现实主义虽处于主流地位,但不是僵化的、绝对的,它对文学作品的控制还是较为宽松的。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讲话》之后现实主义的写真实与理想化之间还保持着一种相对平衡。这也正如温儒敏所说:“现实主义就一直在艰难地选择既不受教条主义以及其他左的思潮束缚、又能充分适应与满足革命时代要求的发展道路。”d但是它对赵树理小说中写真实和政治性不强的故意忽略,显示了现实主义越来越倾向于政治性,这对之后现实主义的发展产生了新的束缚。
三、无法弥合的分裂
其实,赵树理并不想成为文坛作家。当他被抬进庙堂时,他的悲剧也就开始了。他的创作目的其实很简单,就是描写工作中遇到的疑难之事。赵树理一直坚持自己的创作理念,当他与现实主义之间的嫌隙越来越大时,恰恰说明了现实主义在不断变化。
1948年,赵树理创作了反映土改问题的《邪不压正》。12月2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党自强《〈邪不压正〉读后感》与韩北生《读〈邪不压正〉后的感想与建议》两篇意见相左的评论文章。党文虽然肯定了小说大众语言的运用,但认为教育意义不够,忽视了党在农村变革中的决定作用。韩文则认为这篇小说在政治与艺术上都很成熟,具有很高的现实教育意义。之后《人民日报》又刊登了多篇评论文章,指出了党文的过激之处,肯定了《邪不压正》的艺术价值,但也批评了阶级性不强、人物刻画不鲜明的问题。被确立为“方向”两年,赵树理就受到质疑和批判,实际上这是对《讲话》中“写光明”的进一步强化。竹可羽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赵树理擅长展现落后的方面,却不擅长展现先进的方面。e赵树理与现实主义的分歧开始被暴露。此时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中“非文学”的因素变得愈发重要,但赵树理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1950年,赵树理因在他主编的《说说唱唱》上刊登了小说《金锁》,遭到了《文艺报》的多次批评。《金锁》被批评“侮辱”了劳动人民,但赵树理坚持认为不能将农民理想化。连续做了两次检讨后,赵树理被迫表示认识到了政治立场的重要性,但他仍未创作出完全符合政治要求的作品。随着全国政权的建立,赵树理与主流思潮之间最为贴合的部分也开始走向分裂。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建立一种积极的、理想化的现实主义,并以社会主义的立场有所选择地描写现实。赵树理的创作显然不符合这一要求。是否以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进行创作,成为衡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重要标准。这就使世界观取代艺术性,又重新开始在现实主义创作中占据首要位置,作者的阶级立场与作品的真实性再次被勾连。第二次文代会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文学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周扬、冯雪峰等人纷纷撰文要求塑造先进人物形象。而对人物进行典型化的提高和扩大,就需要对浪漫主义进行必要的融入和吸收。随着时间的发展,现实主义的政治功利性被不断地强化,越来越向着一元化发展。他们奉行了自己先前所反对的,不可谓不是一种悲哀。
这种倾向在赵树理创作了《三里湾》后,得到了进一步印证。虽然他意识到了文学作品中政治性的重要,但其作品与当时要求的现实主义仍若即若离。赵树理对人物、故事的处理仍站在民间伦理的立场上,而不是以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进行创作。所以《三里湾》虽反映的是农业合作化運动,但仍遭到了诸多批评。以周扬《评〈三里湾〉》为代表的评论认为,小说没有充分刻画先进人物,没有展示出阶级斗争的深度,尤其是对政策思想、党的领导以及两条道路的斗争表现不够深入。虽然评论不是完全否定,但所指出的恰恰是赵树理与主流思潮之间最大的差异。赵树理在谈到这部小说时,也提到自己创作中存在的缺点:重事轻人、旧的多新的少、有多少写多少。若把这三个缺点反过来,正是此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所要求的:描写英雄形象、表现积极的方面、对现实进行理想化的提纯。赵树理其实已经明白了此时的现实主义需要什么样的作品,但是他无法放弃农民的立场去迎合政权。这是赵树理的可贵之处,却也造成了他的悲剧。
“双百方针”昙花一现,政治性对现实主义的束缚略微有松动,在第三次文代会上,“两结合”的创作方法正式取代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理想性、政治性逐渐占据上风。在此期间,赵树理发表了《“锻炼锻炼”》,再次受到批评与质疑。1959年7月,《文艺报》刊登了武养的《一篇歪曲现实的小说》,抨击赵树理扭曲现实,质问他写落后的农村妇女的目的。武养的指向性非常明确,那就是赵树理所描写的现实不是理想的“现实”。由于文艺政策的调整,1962年邵荃麟在大连座谈会上提出了写“中间人物”等问题,对赵树理重新进行了肯定,赵树理的处境略有好转。这种肯定实际上是对“两结合”后现实主义日趋极端化、教条化的抨击,也是现实主义试图对日益趋紧的政治性进行的艰难反抗。但好景不长,赵树理与邵荃麟迅速因写“中间人物”遭到批评。之后赵树理虽创作了《互做鉴定》《卖烟叶》等作品,仍没有得到肯定。1966年后,现实主义文学思潮陷入了长达十余年的沉寂,直到赵树理离世。
赵树理被树立为“方向”不久,他与中国共产党所努力建构的现实主义之间的矛盾愈发突出。他虽有过短暂的挣扎,但最终还是坚持了自己的创作。所谓“赵树理方向”,重点是“方向”而不是赵树理,不是以赵树理为方向,是以“方向”为方向,没有赵树理还会有“李树理”“张树理”。作家们的创作是不会被允许脱离这个“方向”的,所以当赵树理脱离方向时,被批评就在意料之中了。现实主义在文学与政治、真实与理想之间几经挣扎,还是走上了政治化、革命化和理想化的歧路。当现实主义逐渐抛弃文学的本质特征,走向完全“独尊”的地位时,等待着它的必然是被异化的命运。
a 杨献珍:《从太行文化人座谈会到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出版》,《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3期。
b 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见黄修己:《赵树理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版,第166页。
c 赵树理:《也算经验》,见《赵树理全集(第四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208页。
d 温儒敏:《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89页。
e 竹可羽:《评〈邪不压正〉和〈传家宝〉》,《人民日报》1950年1月15日。
作 者: 范丽媛,山东师范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