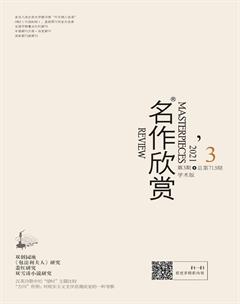近现代日本洪水神话比较研究
摘 要:从中国西南部一带流传的伏羲女娲的故事,再到日本记纪神话的国土创造故事,洪水神话作为世界神话的主题之一近年来在学术界广为人知,而与洪水神话有关的研究,也是长久的一大热点。高木敏雄、大林太良、伊藤清司、吉田敦彦这四位在日本神话研究领域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分别从文献学、语言学、民俗学、考古学等几个角度对世界洪水神话进行研究和解读,本文希望能通过对四位学者的研究进行系统的研读和分析,获得对今后洪水神话比较学习和研究中的一些启示。
关键词:洪水神话 起源 治水 比较
一、日本神话学研究的奠基和世界洪水神话的阐释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日本明治维新刚结束不久的时期,日本神话研究打破自我封闭的状态,开始将眼光放向世界,以积极的姿态与世界神话研究进行交流。作为日本神话学的奠基人和近代日本神话研究的代表学者,高木敏雄的《比较神话学》更是被尊为日本神话学的奠基之作。曾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神话研究被划分成三个里程碑,其中,第一个里程碑便是高木敏雄于1907年创作了《比较神话学》一书,标志着日本神话学的创立。a
纵观日本近现代对洪水神话的研究,大致可将洪水神话分为两类,一类是治水型神话,还有一类是起源型神话。早在1907年高木敏雄便在《比较神话学》中对日本、中国乃至世界洪水神话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关于治水神话的具体含义,高木敏雄在对中国大禹治水的故事进行解读时,曾提到大禹受尧之命,花费九年完成治水平土的伟大功绩,成了大英雄。但任何一位国民大英雄最后会像一个普通人一样迎来生命的终结,无论在天上、海底乃至深山中,其伟大功绩都会永久流传于世,成为不死的英雄神话,这是在民间传说中非常普遍。b那么根据高木敏雄的这一解读,可对治水型洪水神话作出以下定义,治水神话是指主人公完成治水且死去后其丰功伟绩仍作为传说被人们代代流传。
除了治水型洪水神话以外,起源型神话也是洪水神话的一大经典。高木敏雄通过文献的研读,对中国西南部的伏羲、希腊的丢卡里翁、北欧日耳曼的巨人尤弥尔等神话做了比较研究,对世界起源型洪水神话的特色进行了以下概括:洪水的发生代表世界的开始;洪水发生的原因是人类的堕落;除了主人公以外,所有人类都在洪水中丧命;主人公是借助船死里逃生;死里逃生后的主人公最终成为人类的祖先。c值得注意的是,世界各地的起源型洪水神话虽然大致与上述特征符合,但也会有些细微的出入,如中国西南部少数民族流传伏羲女娲的洪水神话中,二人就是借助雷公的牙齿种得的葫芦才得以获救,而大洪水发生的原因是因为伏羲女娲之父冒犯了雷公,并非是人类的堕落。
高木敏雄认为在做洪水神话比较研究时,研究中国洪水神话不能单纯因为故事内容与世界洪水神话有一些相似,便将其归类于世界洪水神话的分支内,换言之,中国洪水神话是中国纯粹的产物,是民间传说固有的财产,而比较神话学能追溯其根源。可以用自然发生说的理论,从中国的地理条件出发,认为中国天然的国土地势和数千条大河导致洪水灾害频发,从而催生了人们治水之术,这是其洪水神话的本源,而中国洪水神话的部分内容与世界洪水神话相似是因为受到了世界洪水神话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是具体是受到了怎么样的影响,是通过什么渠道受到的影响,高木敏雄的研究对这些问题仍没有一个系统和完整的解答。
二、山与海的对立与二元论的世界
上述提到,高木敏雄代表着日本神话研究的第一个里程碑,而大林太良《神话学入门》的问世,标志着日本神话研究繁荣期的到来,也代表这日本神话研究的第三个里程碑。d大林太良充分肯定了高木敏雄在日本神话研究中的地位,并对其学术成果进行了高度评价。
从神话的解释方法上可分为两大流派,其中一派认为神话与人类社会生活有着十分密切和直接的联系,主张从社会角度观察神话。而大林太良认为,这并不是解释神话的唯一办法,他认为可以从神话自身解释神话,从神话的语言本身的观察分析中可以发现神话的意义,神话的结构分析,目的就在于发现神话中蕴含的“语法”,如果仅仅把目光放在神话与人类社会的某种联系上不一定能认识到神话的本质。e
大林太良曾对自古流传于中国江南地区的故事——吴越之争和记纪神话中海幸彦和山幸彦的故事进行了比较,他主张海幸彦和山幸彦的故事起源很有可能就在中国江南地区。海幸彦和山幸彦讲述的是一个兄弟斗争的故事,哥哥海幸彦与弟弟山幸彦因鱼钩丢失一事发生争执,最后山幸彦得到了海神的帮助,用潮盈珠发动洪水淹没了海幸彦的领地,在海幸彦认输后,山幸彦又用潮干珠将洪水吸走。山幸彦和海幸彦展现的是一个具有宏达规模的二元论观念,这种观念将洪水发生的原因在海与山的对立中,这种二元论观念又与中国江南地区流传的吴越之争十分相似。
吴越指的是存在于春秋时期的吴国和越国,其中家喻户晓的“卧薪尝胆”故事便是来源于这两个国家的战争。大林太良先生认为,吴国定都有水乡之称的姑苏,与水有着密切的联系,代表海洋,而越国位于会稽山中,则代表山峰,而吴国和越国之间的战争其实就是象征着海洋和山峰之间的对抗,这一点与海幸彦和山幸彦的故事结构完全一致。f越王自称为禹的后裔,禹是中国治水型洪水神话大禹治水的主人公,传闻禹在临死前曾集各诸侯于会稽山,之后便在山中与世长辞,留下了后世祭禹的圣地,而会稽山名字也因此而得。根据吴越之争的记录,吴王爱好宫室,越国便利用这一点向吴王进献了众多美女,让其沉迷于女色无心治国。而使吴国亡国主要原因之一的西施,其故乡就在会稽山附近的苎萝村。
除此之外,在吴越之争舞台之地的中国江南地区,有一个名为钱塘江大潮的自然现象,钱塘江注入杭州湾的入海口处形成三角洲,每次涨潮海水都会逆流灌入河中,与顺流而来的河水发生碰撞。大林太良认为,这是文种和伍子胥的灵魂引起的。g伍子胥是吴国忠臣,曾劝说吴王消灭越国无果,最后被吴王下令自杀而亡,最后其尸体被扔入钱塘江中。文种是越国忠臣,最后也是被逼迫自杀,尸体埋在三峰山之下。大林太良分析指出,钱塘江大潮是伍子胥和文種灵魂相冲突,前者代指从海上发起的潮水,后者代指从山中流出的河水,这和日本海幸彦和山幸彦的二元论相符合。
三、神话的考古学与“葫芦”的讨论
前面提到,一个神话的形成是否受到影响,受到了什么影响,是通过什么渠道受到的影响,这三个问题的解答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伊藤清司在中国学术报告时曾提及,二十世纪初有部分日本神话研究家并不积极,他们认为单纯将海外某国某地的与日本神话类型相同的民间故事进行介绍和比较,对于做比较研究而言理由并不充分。若不将这些故事流传的社会背景、流传方式、与习俗和信仰的关系解释清楚,单纯将其作为比较材料,是不具备充分的学术价值的。h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吉田敦彦和伊藤清司以考古学的出土文物作为线索,试图复原绳文时代的神话故事,探寻其本源。
伊藤清司以“葫芦”为题,将中国西南部的洪水神话与日本国土创造神话,即伊邪那岐伊邪那美神话进行了比较研究。在前面已提及,葫芦是伏羲女娲二人从洪水灾害中逃生的工具,而在日本国土创造神话中,则象征着男女神相交的性行为。伊藤清司将神话中的性描写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的、具有写实意义的,另一类是比喻的、具备象征意义的。i他将日本国土创造神话归类为前者,中国西南部的洪水神话归类为后者。
在记纪神话中,国土创造的两尊神直截了当地确认了彼此“多余的东西”与“缺少的东西”之后,便互相求爱进行性交。在中国西南部的洪水神话中,伏羲女娲二人则通过占卜活动完婚,占卜的形式多种多样,有从山上往山下滚两半石磨让石磨重合的,有往空中扔出针和线令线穿过针的,也有用火生烟看烟在空中是聚还是散的……这些占卜活动虽然形式各不相同,但无一不使人联想到性行为。葫芦是女性生殖器的象征,吉田敦彦认为芦是家庭主妇在干家务活时不可缺少的容器,因此很自然会将葫芦与女性的观念联系在一起。j而性作为起源神话的母体代表着创造和诞生,国土创造神话和洪水起源神话离不开性的原因,并非是为了讲低俗之事,无论是真实的、具备写实意义,还是比喻的、具备象征意义,这些内容与创造、诞生的理念紧密结合。
日本国土创造神话和中国西南部的洪水神话之间的相似之处,不禁让人思考究竟是偶然,还是说两者之间具有某种联系,而伊藤清司从考古学的角度回答了这一问题。中国的考古工作人员在浙江省河姆渡遗址中挖掘出七千年前的与葫芦类型相似的东西,又从陕西省西安半坡遗址挖掘出了葫芦形状的陶器,这两件文物的出土说明了中国在很早以前葫芦文化就已经非常发达,而在日本,考古工作人员从属于绳文前期的福井县鸟滨一直中挖掘出了葫芦,说明绳文前期的日本已经在种植葫芦了。k伊藤清司从考古学的角度出发,通过出土的文物的印证,令人自然地认为葫芦最开始是在中国播种,之后才传入日本,而“葫芦”在神话中作为性行为的象征,也是以这样的形式从中国传入日本的,这便回答了前面提到的故事如何流传的问题,在洪水神话比较研究中具有重大的意义。
伊藤清司也对中国治水神话进行了研究和讨论,他对中国治水神话的研究侧重于对治水方式的研究,他认为禹的父亲鲧建堤阻挡河流的治水方法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违背了自然规则,而治水想要成功应该努力避免违背自然的人为因素;与此相反,禹清除了堵塞河流之物使水流畅通,其治水方法顺应了水性,所以取得了成功。除了对治水方法的讨论,伊藤清司还将记纪神话中的让国神话与治水神话做了比较研究,他认为治水神话中父亲鲧的失败与儿子禹的成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此创造出了对比性治水故事。失败的父亲更能够彰显儿子光辉的功绩,而这种结构上的特征和记纪神话的让国神话一致,在让国神话中,天之尾羽张神尾为让儿子建御雷神能前往下界,将天安河水逆上,堵塞了道路,使其他神无法前行。
四、洪水神话比较学习和研究的启示
高木敏雄从文献学、语言学和人类学的角度出发为洪水神话的研究提供了一套研究方法;大林太良主要从民俗学的角度解释和分析日本洪水神话的叙述和内容与其他地区(本论文仅列举了中国西南和江南地区)神话故事的异同;吉田敦彦和伊藤清司从考古学的角度,对不同地区神话之间的联系、传播和影响做出了进一步的解答。
通过系统地整理与学习上述四位日本学者的研究后,笔者认为对今后洪水神话比较学习和研究有以下几点启示:第一,在作比较研究时,不能将一个神话仅仅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第二,仅仅分析和归纳两个神話的异同过于表面且不具备太大意义,应该深入探讨两个不同神话之间的内外联系,如神话诞生的社会背景、传播手段、影响要素等;第三,在作比较学习和研究中探讨不同神话之间的关系时,从多角度出发,避免单一视角。在了解日本洪水神话的内容后,不难发现其内容存在着许多与中国西南、江南等地区少数民族流传的神话相似的成分,因此,对于日本洪水神话的学习与探究其根源而言,中国少数民族神话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ad 乌丙安:《日本神话学三个里程碑的主要代表人物》,《日本研究》1988年第3期。
bc 高木敏雄:《比較神話学》,博文館1904年版,第224页,第234页。
e 大林太良:《神话学入门》,林相泰、贾福水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29页。
fg 吉田敦彦:《日本神话的考古学》,唐卉、况铭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3年版,第50页,第51页。
h 伊藤清司:《中国、日本民间文学比较研究(在华学术报告集)》,辽宁大学科研处1983年,第32页。
ijk 伊藤清司:《中国古代文化与日本——伊藤清司学术论文自选集》,张正军译,云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7页,第90页,第89页。
作 者: 李皓宇,天津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日本文学。
编 辑:水涓 E-mail:shuijuan393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