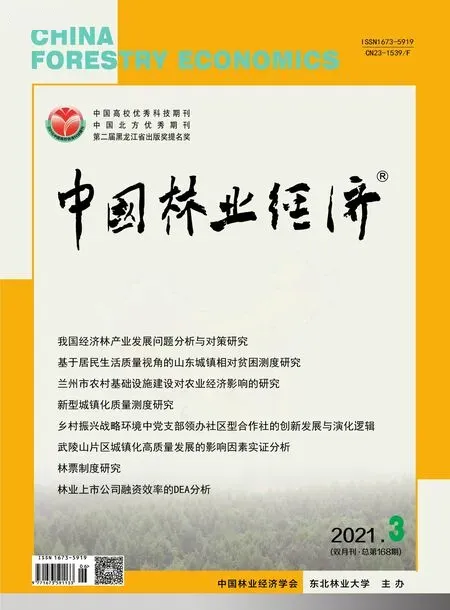森林采伐限额制度研究综述
秦添男,贾卫国
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南京210037
1984 年,《森林法》有了采伐限额制度的雏形,然而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人员、设施配备不足等问题使得采伐限额制度形同虚设。直到“八五”通知的出现,采伐限额制度得以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实施。“八五”到“九五”期间,为扭转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森林资源破坏采用全面且无差别的管理机制,但滥砍滥伐现象并未得到有效抑制。因此“十五”通知后,我国加强公益林和天然林的管理力度,放松商品林管理,按照森林类型实行分类经营管理以求改善我国森林资源不断减少的局面。目前国内外就采伐限额制度的执行效果、管理体制、限额指标设置、林农积极性等方面做出了研究。本文在对这些文献进行阅读梳理的基础上,就采伐限额制度实行的必要性、有效性、现存问题及对策进行总结分析,为未来的深入研究提供可供参考的意见。
1 采伐限额制度实现的必要性研究
1.1 采伐限额制度是必要的
主张采伐限额制度是必要的学者,主要基于以下几点原因:①采伐限额制度是我国国情和林情的需要。首先,我国人口多导致现有森林资源人均占有量少。其次,我国仍处经济发展阶段,木材市场需求量大,采伐限额制度的取消势必会造成森林资源的严重破坏[1-2]。②森林资源自身特性要求。森林资源除经济效应外还有防护、调节气候等生态社会效应,而森林经营者为自身利益最大化,势必会追求经济效益忽视森林的生态效益,因此森林资源正外部性的实行必须依靠政府干预即采伐限额制度[3],③顺应世界发展潮流的需要。美、日、德等世界绝大部分国家都实现采伐限额制度,并将其写入国家相关法律之中,可见其存在有其依据和必然性。
1.2 采伐限额制度具有不合理性
主张这种观点的学者,主要包括以下两种情况:①他们认为采伐限额制度损害了林农的合法权益,挫伤了林农的积极性甚至导致了木材市场的扭曲。有学者通过走访农户进行访谈,提出农户作为理性经济人即使没有采伐限额制度也不会滥砍滥伐的观点[4-5];②认为对商品林实行采伐限额制度是不必要的,应该只将其限定在国有林区。有学者通过对农户的走访,提出采伐限额制度与产权制度相悖,侵犯了林农的林农处置权,因此应该实行林业分类管理,对公益林进行禁伐、限伐,大胆放开非公有制商品林[6]。
2 采伐限额管理制度的有效性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采伐限额与林农采伐行为,造林管护行为以及森林蓄积量、覆盖率、面积的关系。
2.1 采伐限额与林农采伐行为
一部分学者认为会对林农采伐行为产生显著影响。这种影响主要分三种情况:①有抑制作用。有学者从产权激励理论出发,发现采伐管制使得森林资源管理强度增加,林农更难获取木材采伐权导致采伐热度及采伐量的减少[7];也有学者通过对天保工程对国有林场的林农样本进行考察发现因为禁限伐政策的实行,非法采伐现象、碳排放量及木材产量减少,林农采伐行为遭到制约,森林资源及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保护[8-9]。②无抑制作用。虽然天保工程在四川等地起到了作用但在自然保护区并未起到相同作用,这是因为自然保护区森林经营者对资源的依赖度高,刺激了拉关系、走后门和无证盗伐行为,促使管制失灵现象出现[10-11];也有学者通过实证分析提出采伐限额在带来管制强度增加的同时也使得木材市场的价格提高,寻租空间增大,因此会刺激滥砍滥伐、贿赂等手段[12];③与采伐限额的高低有关。有学者从博弈论的角度发现当处罚和监管力度较弱时林农在期望收益的刺激下会选择超额采伐。这种行为的出现可能性与期望收益大小成正比。当处罚和监管力度较强时林农短期内会选择限额采伐。由此可见处罚和监管的力度决定采伐限额制度的效果[11]。
另一部分学者认为采伐限额制度对林农采伐行为无显著影响,提出木材采伐限额制度的约束在变小,林农在采伐时会通过某些规避方式,因此采伐限额制度对林农的采伐行为并无显著影响,家庭特征因素和林地面积才是影响林农采伐行为的重要因素[14]。
2.2 采伐限额制度与林农造林管护行为
一部分学者认为采伐限额制度对造林护林行为产生了负向效果。在采伐限额制度下,林农难以达到预期收益导致投资热情降低。有学者通过案例分析对比发现,采伐限额制度极大程度抑制了森林经营者投入造林管护的时间、金钱以及劳动力,导致“只种不管”“只砍不种”及投入其他行业现象的出现。还有学者通过对农户的调查发现,受到采伐限额制度制约的林农相比于未受到制约的林农会减少高达73.8%的造林投资[16]。
另一部分学者认为采伐限额制度对造林管护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他们提出基于林木生长周期长、市场价格多变等原因,经营者更期待长期效益,因此采伐限额制度对造林管护行为的影响不大。同时造林管护行为更多的受山林依赖度、林地条件、家庭特征等非政策因素的影响,而非受制于采伐限额制度[17]。
2.3 采伐限额制度与森林蓄积量、覆盖率和面积
一部分学者认为,森林资源存量、蓄积量等逐渐增加、被破坏的森林资源得以快速恢复,这都是采伐限额制度带来的效果[18-19]。另一部分学者认为多数研究未考虑林业工程项目的影响,他们提出林业重点工程造林项目才是森林面积、覆盖率的增加的原因[20]。还有一部分学者通过对样本的计量分析发现采伐限额制度非但没有起到资源保护的作用,反而抑制了森林资源的增长。
目前学界已经从各个理论运用多种模型对制度的有效性进行了深入详细的研究,但是仍存在缺乏个案研究的情况且对于后续采伐限额强度的设置、处罚管制力度的设计缺乏更深入的探讨。现有研究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第一,对必要性的证明多数采用理论分析,缺少实证。实证多采用农户走访的方式,主观性较强,证明力较弱。第二,虽然有学者提出利用森林经营方案控制采伐等替代性制度,但是对于该制度的有效性及与采伐限额制度相比的优势性缺乏研究。
3 采伐限额制度现存问题及对策研究
3.1 编制不合理问题
目前的采伐限额编制在根据合理经营和永续利用的原则,提出年采伐指标的基础上进行的。森林资源的质量、数量和结构具有动态性,年采伐指标的制定本身就极其复杂。此外,林农为追求经济利益,忽视生态效益,夸大采伐指标的现象广泛存在,因此采伐限额编制往往与现实违背,缺乏科学性与准确性,难以实现预期目标[22]。为此有学者提出采伐指标总量要同时考虑市场需求和林农意愿;也有学者提出要区分用材林和其他林种的编制管理原则。用材林适用“消耗量低于生长量”原则,其它林种适用“合理经营、持续利用”;还有有学者提出了“伐区制定模式”和“伐区协定模式”两种指标分配方案。
3.2 制度执行率低问题
根据《森林法》规定,林政主管部门担任监督者和执行者。但“人情发证”“关系发证”的现象依旧存在。而在超伐行为发生之后,在超伐主体多与地方政府有关、超载原因多与员工工资、企业债务有关的现实背景下,司法机关往往难以执法。有学者指出,该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国家和地方财政支持不足导致技术支持不够、人员匮乏、基础设施薄弱,提出要加大资金投入力度,提高队伍素质;也有学者认为抚育方式不合理、任务不科学是抚育采伐执行率低的原因,抚育采伐率低则是导致采伐限额执行率低的原因,提出要加强抚育管理,增加抚育补贴,科学确定抚育任务;还有学者提出要加强公益林和天然商品林的监管,适当放宽人工商品林的监管;更有学者提出以采伐申报制度代替对私有林的采伐管制[22-23]。
3.3 管制失灵,超额采伐现象问题
有学者提出现有的采伐限额制度并未达到理想效果,超额采伐现象依旧存在,现有管制出现失灵的情况。管制过强是主要原因,在高管制强度下林农会试图突破现有限制。当寻租成本低于寻租收益时,林农会采用找关系、贿赂等手段,当超额指标扩大、寻租人数增加时出现失灵现象;当寻租成本高于寻租收益但无证采伐被发现可能性低时,林农为寻求经济利益冒险采伐,制度并未达到预期效果。有学者提出可以有条件的取消采伐限额制度,用经济激励制度来替代[24-26];也有学者通过断点回归分析发现山林依赖度过高是制度失效的重要原因,政府管制并非解决资源问题的最佳方式,过强管制反而会导致森林资源的破坏。政府要“简政放权”,弱化管制力度。要寻找并发展可以替代林区的产业,降低林农的山林依赖度[27];还有学者从博弈论角度出发发现林农的不遵守行为是导致制度失效的重要原因,而林农是否遵守是由政府推行制度的成本和收益决定的。生态效益补偿机制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式,要建立生态效益补偿基金,提高生态补偿的标准,特别是对公益林的补偿。完善林业税费制度,减少不合理税费,并给予税收优惠[28]。
4 评述
保护森林资源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采伐限额制度作为我国《森林法》的核心制度,其设计目的就是为了保护森林资源环境。目前我国学者就采伐限额制度的有效性、必要性及问题进行了细致的讨论。然而目前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现有研究缺乏对采伐限额强度与处罚管制强度如何设置的研究;对取消采伐限额制度的理由缺乏科学性的证明,多数采用主观性极强的农户走访方式;多数主张取消采伐限额制度的研究只论证采伐限额制度的弊端,但未提出替代性制度。即使提出替代性制度,也缺乏对其可行性的证明。未来的研究可以重点探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探讨采伐红线及处罚管理强度的设置。采伐限额的强度及处罚管制的强度会对林农采伐行为产生极大的影响已经得到证明,因此未来可以更多通过农户调查、数学模型等方式探求不同采伐红线及强度的处罚方式对林农的影响,探求最适宜的采伐红线及处罚强度的设置或探求采伐红线设置的依据等问题。
第二,替代性制度的有效性及与现有采伐限额制度的有效性评估。虽然目前有提出采伐限额制度的替代性机制,但是对于替代性机制的有效性并未进行证实,此外可以通过现有机制与替代性机制的绩效对比从而观测机制的优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