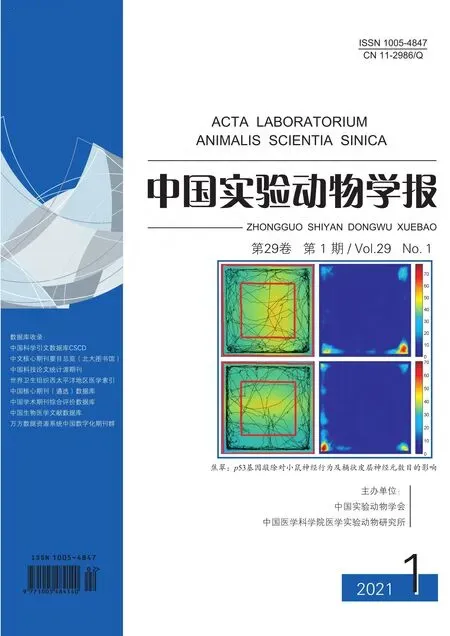白细胞介素-37 在流感病毒感染导致的重症肺炎中作用的研究进展
刘明娅戚菲菲鲍琳琳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北京协和医学院比较医学中心,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人类疾病比较医学重点实验室,新发再发传染病动物模型研究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北京市人类重大疾病实验动物模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人类疾病动物模型三级实验室,北京 100021)
流感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轻症者出现肌肉酸痛、体温升高、乏力等症状,重症时出现病毒性肺炎、继发细菌性肺炎、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常累及多种器官病变,引起心血管和神经系统症状[1]。据报道,每年因流感导致的重症病例将近数百万,因流感死亡的人数约25 ~50 万人。自20 世纪以来,世界上已有五次大规模的流感大流行,给全球经济和人民健康造成巨大损害。2009年H1N1 流感大爆发导致数万人死亡[2],并迅速在世界范围内蔓延,流感病毒导致的重症肺炎一直是流感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当前临床上的治疗方案大多是抗病毒治疗或对症救治,针对肺炎的治疗效果不理想,因此需要寻求更有效地办法来治疗流感引发的重症肺炎[3]。
1 H1N1 感染导致重症肺炎的机制
有研究表明,增加流感严重程度的关键因素是先天免疫被过度激活。先天免疫是机体抵御病毒感染的第一道防线,H1N1 病毒主要通过气溶胶进入呼吸道,进而感染机体,H1N1 病毒进入呼吸道后,呼吸道上皮细胞通过Toll 样受体(Toll-like receptors,TLR)、视黄酸诱导基因-I(retinoic acidinducible gene I, RIG-I) 受体等模式识别受体(pattern recognition receptor,PRR)识别自病毒的病原体相关分子模式(pathogen-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s,PAMP)[4],激活先天免疫反应,产生大量的促炎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主要包括干扰素-α(interferon-α,IFN-α)、肿 瘤坏 死 因 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 TNF-α )、 白 细 胞 介 素-1α(interleukin-1α, IL-1α ) 和 白 细 胞 介 素-1β(interleukin-1β,IL-1β),IFN 在流感感染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表达主要受干扰素调节因子(interferon regulatory factor,IRF) 家 族 的IRF3 和IRF7 控制。IFN-α 与其受体结合后,激活JAK/STAT 信号通路,诱导干扰素刺激基因(interferonstimulated exonuclease gene,ISG)的表达,从而发挥抗 病 毒 作 用[5]。IL-1β 与 白 细 胞 介 素-1 受 体(interleukin-1 receptor,IL-1R)结合,通过髓样分化因子(myeloid differentiation factor 88,MyD88)信号通路诱导炎症基因的表达。另一个调节免疫和炎症反应的重要细胞因子是白细胞介素-6(interleukin-6,IL-6),临床研究表明,重症流感患者外周血中IL-6 水平明显高于健康者,被认为是决定肺炎严重程度的重要细胞因子。IL-6 可在多种不同类型的免疫细胞内产生(如自然杀伤细胞、单核细胞),具有多种生物学功能[6-7]。IFN-α 和IL-1 可刺激IL-6 和许多趋化性细胞因子,如吸引嗜中性白细胞的白细胞介素8(interleukin-8,IL-8),巨噬细胞炎症蛋白(macrophage inflammatory protein,MIP)和单核细胞趋化蛋白(monocyte chemotactic protein,MCP)的产生,从而介导中性粒细胞和巨噬细胞的定向迁移[8]。此外,炎症反应的诱导和调节还受丝裂原激活蛋白激酶(mitogen activated protein kinase,MAPK)的控制,MAPKs 的活性与IL-6、趋化因子配体5(chemokine ligand 5,CCL5)和重组人趋化因子8(recombinant human C-X-C motif chemokine 8,CXCL8)的表达有关[7]。募集到肺部的免疫细胞又会分泌大量的促炎因子,这些细胞因子具有协同作用,且可以诱导自身或其他细胞因子的产生,吸引更多的巨噬细胞、树突状细胞到肺部,产生更强烈的细胞因子风暴,使炎症反应更加强烈,引发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严重者还可导致多器官功能障碍症。
临床上流感药物大多通过抗病毒作用发挥治疗效果,不能抑制机体过度免疫导致的重症炎症,目前常采用小剂量激素和抗病毒药物配伍来治疗流感引发的重症肺炎,但由于临床上激素使用剂量和副作用的影响使该疗法存在很大争议,因此当前对流感引发的重症肺炎的治疗尚无特异且有效的方法。目前全球流行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由SARS-CoV-2 病毒感染导致免疫系统的过度激活引发的细胞因子风暴综合症诱发,正严重威胁世界人民的生命健康,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亟待寻找有效平衡免疫反应与病理性细胞因子风暴的发生的治疗方案。若能找到可有效抑制细胞因子风暴产生的药物,无疑将给重症病毒性肺炎的治疗提供新的策略。
2 IL-37 生物学活性
2.1 IL-37 的抗炎作用
IL-1 家族成员中具有多种作用于局部和全身的细胞因子,在炎症引发的疾病中起到关键作用,是先天免疫和炎症反应的调节介质。IL-1 家族的大多数细胞因子具有促炎活性(如IL-1α、IL-1β、IL-6、IL-18、IL-36α、IL-33 等),部分具有抗炎作用(如IL-1Rα、IL-36Rα、IL-37、IL-38)。
IL-37 是IL-1 家族中一种具有多种生物学功能的抗炎细胞因子,具有强大的抗炎作用[9],是调节炎症反应的关键细胞因子,主要通过抑制促炎细胞因子的表达发挥作用,通过限制免疫和炎症反应的持续时间和强度,从而在感染和免疫过程中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10-13]。人IL-37 基因位于染色体2上,编码总长度为3 × 103的基因产物,并通过选择性剪接产生五种不同的亚型(IL-37a、IL-37b、IL-37c、IL-37 d 和IL-37e),研究表明,IL-37 在人体的分布具有广泛性,五种亚型在身体的不同部位表达,如淋巴结、骨髓、胸腺、肺等[14]。IL-37 的抗炎作用在诸多研究中已被证实,在人外周血单核细胞与肺上皮细胞中过表达IL-37b,细胞中的促炎因子合成被抑制,若用siRNA 干扰IL-37 的表达,促炎因子的合成增加[15]。用LPS 刺激过表达IL-37b 的小鼠巨噬细胞RAW264.7 后,IL-1α,TNF-α,IL-6,GMCSF,M-CSF 和IL-1Rα 表达水平下降[16]。在经过IL-37 处理的小鼠的脾和肺组织中,促炎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表达水平也较低[17]。另外,IL-37 在风湿性关节炎、系统性红斑狼疮、银屑病等患者中均呈高表达状态。研究表明,IL-37 通过抑制CXCL8,IL-6 和重组人S100 钙结合蛋白A7(recombinant human S100 calcium binding protein A7,S100A7)等趋化因子的产生,减轻巨噬细胞、中性粒细胞、树突状细胞的炎性浸润,避免过度炎症反应,从而起到改善银屑病的作用[18]。IL-37 在小鼠过敏性鼻炎中发挥作用,可以通过STAT6/STAT3 途径降低促炎因子的表达水平,从而抑制炎症的发生发展[19]。
2.2 IL-37 的抗病毒作用
IL-37 不仅可抑制炎症和调控免疫应答,还有一定程度的抗病毒作用。IL-37 可抑制甲型流感病毒的复制,用IL-37 处理感染流感病毒的A549 细胞,流感病毒mRNA 的复制水平下降。在甲型流感病毒患者体内发现血清中IL-37 的水平明显高于健康受试者,感染甲型流感病毒后,在细胞水平上IL-37的表达水平也明显升高[20]。IL-37 可通过调节Th17/Tregs 细胞的免疫应答抑制IL-6 的表达,促进IL-17 A 的分泌,从而改善柯萨奇病毒B3(Coxsackie viruses B3,CVB3)诱导的病毒性心肌炎[21]。IL-37还可通过抑制单核细胞炎性标志物sCD14 的水平从而在艾滋病病毒-1(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1,HIV-1)中发挥作用,研究表明,在慢性HIV-1患者体内,IL-37 表达增加,且IL-37 的表达与HIV-1储存库的大小有关[22]。
3 IL-37 的作用方式及机制
IL-37 是一种具有双重作用的细胞因子,其可通过两种不同的机制发挥抗炎作用。在细胞内,促炎因子刺激促进IL-37 前体的产生,并激活caspase-1,IL-37 前体的羧基结构域上具有caspase-1 切割位点,经切割后变成成熟形式的IL-37,成熟的IL-37与磷酸化的Smad3 结合,并转移到细胞核内,调节基因的转录[23-24]。Smad3 是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途径中的转录调节因子,通过促进IL-37b转运至细胞核而在IL-37b 的生物学效应中发挥重要作用[16]。IL-37b 与Smad3 结合进入细胞核后,抑制Toll 样受体诱导的促炎因子IL-1α、IL-1β 的产生,使其下游的NF-κB 和MAPK 信号通路激活受阻,从而抑制COX-2、IL-6、TNF 等的产生[25]。此外,还可抑制STAT1-4 的磷酸化过程,拮抗STAT1-3 炎症通路[26],通过抑制促炎信号传导级联反应,减弱先天免疫。研究发现,当使用Smad3 阻断剂抑制Smad3 后,IL-37 对炎症因子的抑制效果被阻断[27]。
IL-37 前体和成熟形式均可通过非经典的分泌途径从细胞中释放出来[28]。在细胞表面,IL-37 与IL-18Rα、IL-1R8 结合形成三联体复合物抑制IL-18的信号传导通路[29]。炎症反应发生时,IL-18 可与细胞表面的IL-18Rα 结合并招募IL-18Rβ,启动MyD88 依赖性促炎途径,当IL-37 与IL-18Rα 结合后,招募IL-1R8[30-31],由于IL-1R8 的TIR 结构域与IL-18Rβ 相比发生了突变,使其与MyD88 结合的信号传导弱或无信号传导。IL-1R8 可调节多种下游途径和信号激酶的作用,如抑制JNKs、NF-κB 和MAPK 等信号激酶的磷酸化,激活Mer-PTEN-DOK途径来传导抗炎信号,减少促炎基因表达,抑制促炎细胞因子的产生[32];通过减少琥珀酸酯的产生,抑制mTOR 的磷酸化,激活AMPK 来恢复细胞的代谢。
4 结论与展望
IL-37 广泛作用于全身的多种促炎因子,在感染性疾病、自身免疫病及肿瘤中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TNF-α、IL-6、IL-1β、MCP-1 是引起流感导致的重症肺炎患者体内细胞因子风暴发生的重要因子,而IL-37 可抑制NF-κB、MAPK 和MyD88 信号蛋白的活化,从而抑制IL-6、IL-1α、IL-1β 等促炎因子的分泌,阻止细胞因子风暴的发生发展。因此,我们猜测IL-37 可以通过抑制细胞因子风暴而在流感病毒感染导致的重症肺炎中发挥抑炎作用,但目前对于IL-37 治疗流感导致的重症肺炎的研究甚少,需进一步探讨IL-37 的生物学作用,明确研究过程中的给药时间点及时间窗,研究IL-37 在重症肺炎中发挥作用的机制,将为治疗H1N1 导致的重症肺炎提供新的治疗策略,也将为克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提供治疗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