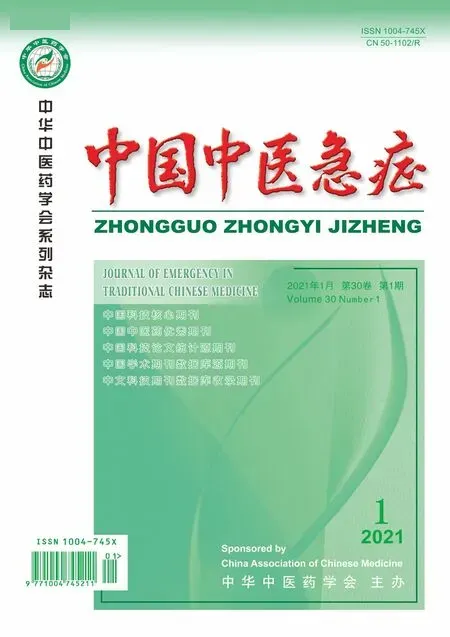脑桥中央髓鞘溶解症中医诊疗思路探讨*
郑立夫 邓慧明 文 希 唐纯志
(1.广州中医药大学,广东 广州 510405;2.广东省第二中医院,广东 广州 510095)
脑桥中央髓鞘溶解症(CPM)是渗透性脱髓鞘综合征的一种特殊类型,是目前临床上较为少见的一种急性非炎性中枢脱髓鞘性疾病[1]。CPM最早由Adams等[2]于1959年报道,病变呈对称性累及脑桥中央,影像学上可见脑桥中央横切位上圆形或蝴蝶形病灶。该病往往与严重的电解质紊乱有关,最常在迅速纠正低钠和高渗透压血症的过程中发生[3]。此外,尚有研究指出低钾血症、慢性酒精中毒、营养不良、慢性肝病等也可能是其独立诱发的因素[4-5]。该病起病常见四肢瘫痪、假性延髓性麻痹和不同程度的意识障碍等神经系统症状,与脑梗死、脑出血等较难区分,加之在临床中较为少见,容易造成漏诊和误诊,预后极差,死亡率高。目前西医治疗以预防为主,早期多采用激素冲击治疗[6],患者常常遗留有严重的生活功能障碍,治疗效果并不理想。该病中医上属危急重症,目前缺乏系统的中医治疗思路整理。本文从CPM中医病证、病因病机方面入手探讨该病的中医治法治则,并试举1例临床案例以供参考。
1 CPM的中医病名归类探讨
根据目前对该病的相关报道,CPM临床多见突发意识丧失、吞咽及构音障碍、癫痫发作、四肢麻痹、瘫痪、精神错乱等症状,其中尤以意识障碍、四肢麻痹、瘫痪为主要表现[7]。虽然当下并未有关于该病中医证型归类的文献引证,但在中医古籍中却有大量类似病症的记载可做参考,如《素问·大奇论》曰“暴厥者,不知与人言”。《灵枢·五乱》言“乱于臂胫,则为四厥;乱于头,则为厥逆,头重眩仆”。其中不难看出所载厥证有突然昏厥、意识不清的表现,与该病非常类似。另外在《灵枢·热病篇》中有“痱之为病也,身无痛者,四肢不收,智乱不堪”的记载。“痱”病为中风的一类,除患者意识改变以外,亦出现有四肢瘫痪等症状,后世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进一步指出“夫风为病,当半身不遂,或但臂不遂者,此为痹,脉微而数,中风使然”。除此之外,王冰在注解《素问·生气通天论》时指出“偏枯,半身不随”。张介宾在《类经·针刺类·刺诸风》中云“偏枯者,半身不随,风之类也”。查证偏枯,实为中风之虚证,其多见于疾病后期或虚弱体质者,以一侧肢体的偏瘫为主要临床表现。因此,该病在中医上与上述病证(厥、痱、痹)均应有较大关系。CPM早期起病时常由于严重的电解质紊乱而引发神志的突然丧失,尤以全脑性急症表现为主,或可伴有大小便失禁[8],但报道中却并未指出有肢体偏瘫或口眼歪斜的症状出现,这些症状大多在后期才逐渐产生。在流行病学上看,病例中目前未见明显年龄分段,甚或有儿童病例的报道[9],而其病因亦多与慢性饮酒、低钠血症、手术后补液、尿毒症、营养不良等容易导致人体自身机能代谢紊乱的因素相关,与中风的由外邪直中或是传统中医认为的痰瘀伏邪形成致病的情况有一定差别。如此看来,CPM早期的发病似与厥证病理病机更为吻合。正如《张氏医通·厥》所言“夫中风者,病多经络之受伤;厥逆者,直因精气之内夺”。这也从一定程度上解析了该病个别案例在治疗康复后甚或可以在症状和影像学上均完全恢复正常[9]。而CPM后期演变出肢体瘫痪、口舌禁闭等症状,应是由于“内夺”太过,或是外邪乘虚而入,造成向中风病中的喑痱、偏枯等症的转变。《素问·脉解篇》中就有“内夺而厥,则为喑痱,此肾虚也,少阴不至者,厥也”的记载,说明CPM虽然以气血运行失常导致一过性昏厥为主要病机,但在精气损伤过度,或是先天之气偏弱的情况下,损及脑髓,外邪直中,后期亦可向喑痱等他证转变,出现四肢麻痹失用的类似偏枯的现象。此时(后期)患者则可按中风偏枯论治。另外,元代医家程杏轩在《医述》中亦将“痱”“厥”并称为“痱厥”一类,并指出“肾络与胞络内绝……二络不通于下,则痱厥矣”。综上,则本病中医病名归类可分为两期,早期以厥证为主,后期则与“中风偏枯”的疾病发展有关,或可以“痱厥”统称。
2 CPM的中医病因病机分析
目前中医方面尚未有关于CPM的病因病机研究。根据当前报道[10]的病例情况,患者在发病过程中,存在早、后两期不同的病理表现,其病因病机亦可以分为两期进行辨证分析。该病早期发病时多为急症,常见意识障碍等情况,存在气血逆乱的基本病机,与厥证的生理病机比较吻合。《类经·疾病类四十六》曰“厥者,气逆也”,《景岳全书·厥逆》亦指出“厥者尽也,逆者乱也,即气血败乱之谓也”。该类疾病在早期起病多是由于患者平素生活作息不规律,或是手术、出血、酗酒、妊娠[11-13]造成津液丢失太过,耗伤五脏六腑精气,使人体内正常的气血运行失常,气机逆乱,从而可出现头痛、呕吐、肢体乏力等先兆表现。而当体内的气机混乱进一步发展,致使体内出现阴阳之气不能相续,形神不生,则会影响到患者神志,从而出现早期的昏厥症状。《诸病源候论》中则载有该病发病时的主要表现为“其状如死,犹微有息而不恒,脉尚动而形无知也”。在该病的发展中,早期的病证虽以“真气厥乱”为病理本质,当疾病进一步进展,却可以在后期向类似中风偏枯的临证表现演进,进而出现肢体乏力、瘫痪,言语噤默等症状。此期患者产生与早期不同的病理变化,主要与患者厥乱内夺后真气偏虚,损及脑髓,或受外邪直中脏腑,影响经气运行有极大关系。《诸病源候论》中将其病因病机总结为“阴阳离居,营卫不通,真气厥乱,客邪乘之”。由此可知本病与人身阴阳的严重失衡导致后期偏枯是密切相关的。《素问·脉解篇》亦载有“内夺而厥,则为喑痱,此为肾虚也,少阴不至者,厥也”。故其在后期的病理本质上除厥证的上述“真气内夺”的病机外,还可有“客邪乘之”的基本机理。而临床上,厥证的虚证者进一步加重,亦可有向脱证发展的趋势[14],从而导致该病的病死率较一般脑血管疾病为高。此时患者常常由于自身正气不足,加之气机逆乱过度,而造成正气不能维持正常抵御外邪的功能,使外邪由外直中脏腑,或是因为真气停滞,津液不生,损及脑髓,进而出现持续神昏、四肢瘫痪等,病情危急且凶险,预后较差。此期在治疗上则应注意扶阳固脱,醒脑开窍,重用甘辛养阳之品。
综上可知,该病证的中医病因病机早期以阳气亏耗,气机逆乱为主,进一步发展可出现后期真气耗夺或正虚邪中的病理表现,病性为本虚标实,早期病理层次在气,表现为气机运行紊乱,后期则可损及脏腑脑髓,尤以先天肾气及后天脾气的亏耗为主,可出现肢体废用、失神等症状。
3 CPM的中医治疗思路探讨
3.1 精准辨证,分期施治 辨证施治是中医治病的一大原则。由上面的分析可知,该病在不同阶段病因病机存在一定差异,因此中医治疗上亦应根据不同时期的病理表现辨证进行施治。结合大多数病例的报道,该病病程大致可分为先兆期、早期的气血逆乱期及后期的真气耗夺、正虚邪中期3期。1)先兆期:此时患者可见头晕、恶心、自觉乏力、表情呆滞[15]等症状,多是气血运行不畅、受阻或脏腑功能紊乱的表现,往往是诱发该病的直接因素,但并未能引起临床上的足够重视,进而病程向早期的气血逆乱进一步发展。若该期能及时进行中医对症调理,或可以阻断病情进入下一期。2)早期:当患者进入早期气血逆乱的爆发后,可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意识障碍、精神异常或肢体的抽搐[16],甚者可伴心率加快、无尿等重症表现,此时的病机为气虚不续,阴阳离乱,全身的气机处于极度紊乱的状态,此期的治疗亦是该病善后的关键。《灵枢·五色》曰“其病生于阳者,先治其外,后治其内”,该期的治疗当以扶阳固脱,醒脑开窍为主,外部可采用针刺人中、百会、三阴交、委中、内关等,辅助阳气升发的同时尽快调整患者阴阳气血的平衡,同时可配合内服中药独参汤或四味回阳饮等以固阳止脱。如若痊愈,则可继续对症调补,以降低患者复发的概率。3)后期:患者神志或可逐渐恢复,但多出现不能言语、吞咽障碍及四肢瘫痪等症状,此时根据患者正虚邪中等病机,当进一步匡扶阳气,调节神机,扶正祛邪。治疗可采用扶阳调神法,加强督脉及膀胱经穴位针刺,并调服八珍汤一类补益气血的中药进行施治,以促进患者功能康复为目的。
3.2 扶阳为主,注重调神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治病必求于本”。本病治疗过程的理法方药,均应建立在谨守本病病机的基础上。本病发病以全身的气血逆乱为主,特别是在早期起病及预后两个阶段,与人身阴阳二气的平衡密切相关。《素问·生气通天论》曰“阴平阳秘,精神乃治”,而当阴阳升降失去调和,出现“离诀”时,则“精气乃绝”。纵观本病,阳气的逆乱及亏耗可以说是贯穿病程的各个阶段,因此在整个治疗过程中,都应注意培扶患者阳气,同时加强调神的治疗。《素问·汤液醪醴论》曰“针石,道也。精神不进,志意不治,故病不可愈”。《类经·针刺类》云“医必以神,乃见无形,病必以神,血气乃行,故针以治神为首务”[17],指出了“调神”在治疗该类疾病中的重要意义。而人体“神”的存灭,亦离不开阳气的充养。督脉为阳脉之海,通过针刺督脉等穴位,能够达到激发脑部经气,调和阴阳、气血的作用[18],能从根本上改变患者的病理体质,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神者,意之守也[19]。神气的恢复得益于阳气的充养及全身气机的正常运行。据《灵枢经》所载,督脉为阳经之海,总督诸阳,起于胞中,为原气所发,所过为背部正中,恰是人身各阳脉汇集的地方[20],也是各阳经获得原气温煦以升发的场所,而行于两旁的膀胱经主一身之表,所属脏腑能司气化,与肾表里。此二经脉皆上巅络脑,针刺既能帮助全身阳气的正常升发和散布,又能开窍醒神,驱邪外出,是本病早、后两期治疗均应密切关注的两条经脉。
3.3 内外相辅,针药结合 该病的病因病机以人体全身的气机逆乱首发,进而出现中风偏枯的表现,病位牵涉到表里脏腑气血的运行,则治疗上,亦应从内外同时进行施治,对患者气机的运行进行整体调理。针灸及中药恰是中医外调内服的重要治疗手段。在治疗该病时,外部可根据本病病机,选择对阳气有升扶作用的督脉及各阳经上的穴位进行针刺,以激发局部经气。此外,各阳经经脉均抵达头部,针刺时能够同时达到调神的目的。临床上具体可采用扶阳调神法针药结合施治,该法用于治疗中风后出现气虚失神的一类患者亦常能收获良好的疗效。其针法选穴受启于石学敏院士的醒脑开窍针刺法,尤以督脉为主,结合双侧膀胱经穴位,能起到扶阳通脉,调神导气的作用,正合患者各期病机。但针刺虽能激发阳气的重新升越运行,使其回到正道,阳气的化生却尚需依靠人体肾腑元气的充养。此则需结合内服补肾益气养血一类方剂,以培补患者正气,固护阳气。《黄帝内经》亦云“阴为阳之母”,则用药应多遵养阴益阳之意,如八珍汤之属。
4 典型病例
患某,女性,35岁,职员,曾长期熬夜工作,2019年5月22日因头晕头痛,伴发热、呕吐、四肢乏力不适至当地医院住院,检验示多项电解质紊乱。住院期间患者出现昏迷,心率加快,无尿,并入住ICU支持治疗。6月21日头颅CT提示:双侧桥脑-间脑-丘脑-基底节-放射冠大面积脑梗死。7月7日查头颅MRI+MRA:桥脑异常所见,考虑CPM可能性大。至7月底患者生命体征趋稳,神志转清,但遗留四肢瘫痪、吞咽困难等症状,遂于8月2日转入本院。入院时见神清,精神疲倦,言语不能,能眨眼示意,形体偏瘦,四肢无自主活动,留置胃管注食注药,二便调,舌红,苔黄厚腻,脉细弱。查体:伸舌、张口、发音不能;四肢肌肉稍萎缩,肌张力无增高,肌力0级;双侧肱二头肌、膝反射、跟腱反射减弱。右霍夫曼征(+),双侧巴氏征(+)。血常规:WBC 6.93×109/L、PLT 421.0×109/L。血生化:K+3.2 mmol/L、Cl-94.9 mmol/L,超敏C反应蛋白、糖化血红蛋白、血浆D-二聚体、降钙素原、心酶四项、心梗三项、脑钠肽(BNP)未见异常。诊断:1)CPM;2)闭锁综合征(不完全性)。治疗采用中医扶阳调神法针药结合为主。中药取八珍汤加减。针刺选穴主选太阳经、督脉穴位,结合头皮针醒脑开窍,治疗主穴:四神针、风府、哑门、大椎、陶道、长强、身柱、中枢、命门、腰阳关、腰奇、玉枕、大柱,并结合患者病情变化随证选用膀胱经上穴位施治。每日1次,治疗2周后,患者发音、吞咽等症状改善明显,可自主张口、伸舌,左上肢可抬至额部,左手可微屈握拳,左下肢可稍平移。洼田饮水试验:5级。后患者曾再次至本院住院行上述治疗2个疗程,复查颅脑磁共振(MR)平扫+DWI+MRA:桥脑异常信号影,符合CPM,对比前片,现病灶基本软化。出院时患者肢体肌力已较前明显改善,并能自主进食流质食物。1个月后随访,患者下肢虽尚未能支撑行走,但上肢已可完成一般的自理活动,并能进行简单句子的语言交流。
按:本例患者起病时符合CPM的典型症状,转入本院时存在神倦、四肢乏力等气虚失神症状,契合本病后期治疗的病因病机,可运用扶阳调神法进行施治。治疗上,结合患者后期气血不足情况,先以中药选八珍汤调服培补患者正气。方中人参大补元气,白术、甘草实脾土,升脾阳;茯苓渗湿,利阳气生发。而阳气的运行又有赖于阴血的鼓动,故辅以四物汤活血补血。外部针刺依扶阳调神法主取督脉、膀胱经穴位以激发患者经气,取总调阳气之意。其中,四神针位于巅顶,为调神主穴,大椎为诸阳之会,主通阳复脉,风府、哑门都有驱散入脑之风邪作用,能开窍醒神,余选用督脉及膀胱经上与诸脏腑相通穴位施治,进一步加强阳气的生发。而另据《灵枢·经脉》言“足太阳膀胱经……主筋所生病”,故该针法对腰背部肌肉的松弛、乏力亦有良好的效果,有利于患者运动功能的康复[21]。诸穴合用,治疗具有调整全身五脏六腑阳气,促进气机正常运行的功效,可以帮助人体气血重新回复到正轨上,从而在短期内达到了改善患者临床症状的目的。
5 结 语
中医药对于个体特殊病证具有灵活高效的特点,运用于临床治疗危急重症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CMP作为一类临床罕见的中枢神经系统重症,其发病凶险,目前西医治疗效果欠佳。中医学认为本病以气虚气血逆乱为基本病机,治疗上应注重扶阳调神,在临床上能取得比较满意的效果,值得在临床上进一步发掘及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