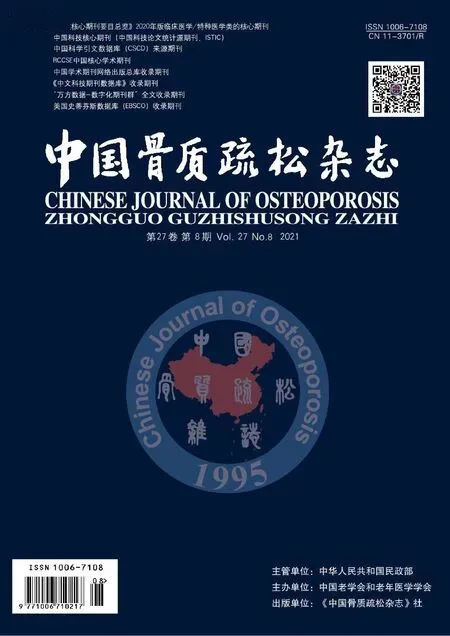全膝关节置换术后KimⅠB型股骨侧假体周围骨折的手术治疗
杨雨润 陈瀛 林朋 孙伟 刘成刚 王立强
北京中日友好医院骨科,北京 100029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剧和膝关节置换技术的普及,全膝关节置换术后假体周围骨折的发病率逐渐升高,约为0.3%~8%。其中股骨侧假体周围骨折最多见,该类患者多为高龄、重度骨质疏松者,内科合并症较多,围手术期处理难度大,对其进行治疗时要兼顾患者的全身状况以及假体周围骨折的特点。本研究回顾性分析中日友好医院骨科2015年7月至2019年7月收治的9例膝关节置换术后股骨侧假体周围骨折的病例,均采用手术治疗,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入选患者共9例,女性8例,男性1例,年龄65~92岁,平均(75.3±8.7)岁,所有患者膝关节假体类型均为骨水泥型,骨折均为闭合性、单侧的股骨侧假体周围骨折,致伤原因均为摔倒等低能量损伤,其中左侧6例,右侧3例。1例合并同侧肱骨近端骨折,1例同侧髋关节曾行动力髋螺钉内固定术。受伤至入院时间为3 ~ 24 h,平均(11.6±7.2) h。Kim分型均为ⅠB型。本研究已通过中日友好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患者均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手术方法
所有病例均采用全麻或硬膜外麻醉,患者仰卧位,使用锁定钢板者屈膝60°,不使用牵引床,通过股骨远端外侧入路完成,沿股骨轴线外侧向下延伸至股骨外侧髁,切开关节囊,暴露骨折断端,探查股骨假体稳定程度,将骨折复位,采用经皮微创的方法置入钢板,以保护局部血液供应。使用髓内钉时,将膝关节屈曲约30°,沿原切口经髌韧带或其内缘插入导针,在透视下确认导针位置无误后,逆行置入髓内钉及远近端锁钉。
1.3 围手术期处理
术前常规完善心脏彩超、下肢血管B超等检查,评估全身情况。术前30 min预防性使用抗生素,如果手术时间延长,追加1次抗生素。术后行抗感染、抗凝治疗。术后鼓励患者练习髋、膝、踝关节活动,预防下肢深静脉血栓。
1.4 随访与评价指标
术后按照医嘱于门诊进行随访,随访内容为患肢HSS膝关节评分、骨折部位疼痛视觉模拟评分(visual analogue scale,VAS)。通过骨折部位的疼痛情况和X线来判断骨折是否愈合,以HSS膝关节评分评价术后功能。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所有患者在术中均未发现假体松动,行切开或闭合复位内固定。手术时间80~130 min,平均(100.0±16.3)min,出血量100~550 mL,平均(276.7±152.1)mL,输血量0~400 mL,平均(266.7±188.6)mL。术后所有患者伤口均甲级愈合,无感染发生。术后2周拆线。
2.2 骨折愈合
9例患者均获得随访,随访时间12~36个月,平均(28±8.5)个月,骨折临床愈合率88.9%,8例达到临床愈合,骨折部位负重VAS评分0分,X线片显示骨折端对位对线良好,已愈合,内固定无移位,未见假体松动迹象;1例先取出股骨近端内固定物,后行逆行髓内钉内固定术(图1)。1例发生内固定失效,未达到临床愈合,负重VAS评分8分,术后1年随访X线显示骨折无愈合征象。
2.3 临床疗效
末次随访时所有患者膝关节活动度均为优良,伸直平均为(2.67±2.11)°,屈曲平均(94.9±10.5 )°。末次随访时HSS膝关节评分20~90分,平均(74.0±19.6)分。膝关节静息状态的疼痛VAS评分为0.52,主动活动时VAS评分为1.12,负重活动时VAS评分为1.89。
3 讨论
膝关节假体周围骨折是膝关节置换术后的严重并发症[1],随着膝关节初次置换及翻修手术的增加、患者寿命延长、骨质疏松加剧等,该并发症的发生率日益增加,在初次置换中为0.3%~2.5%,在翻修手术中为1.7%~38%[2]。由于患者高龄、合并多种内科疾病,围手术期死亡风险明显增加。多存在重度骨质疏松,全身骨量下降,骨脆性增加,关节置换术后易出现假体松动、骨溶解,加大了假体周围骨折的风险。股骨假体的存在使该类骨折不同于单纯的股骨髁上骨折,无论是进行内固定还是假体翻修,均面临相当大的难度,给骨科医生带来极大的挑战[3]。
发生膝关节假体周围骨折的危险因素包括全身及局部两方面,全身因素包括女性、高龄、合并内科疾病(如尤其神经系统疾病)、药物服用史;局部因素包括假体周围骨溶解、假体松动、关节僵硬等。另外,股骨前方皮质过度截骨过多,将使股骨远端对抗扭转的能力明显下降,是导致此类骨折的医源性因素。选择何种治疗方式取决于骨折类型、全身情况、骨质疏松程度、医生的经验等。对于假体无松动、骨折无移位的Ⅰ型骨折(Kim分型),或伤前长期卧床、内科合并症多、无法耐受手术的患者可以采用保守治疗[4],但长期制动可能导致关节僵硬、骨折对位不良、延迟愈合或不愈合,适应症非常窄。所以,对于此类骨折首选手术治疗,对骨折进行牢固的复位和固定,早期功能锻炼。本文所选病例均为假体稳定的ⅠB型(Kim分型),该类型骨折最为常见,是本文的研究对象。常用的手术方式是锁定钢板和髓内钉,研究[5-6]认为二者的疗效相似,没有绝对证据证明何种方式更好。
锁定钢板是治疗假体周围骨折的首选方案,该技术可以减少对骨膜的剥离,保护局部血运,尤其对于骨质疏松症患者,依靠其成角稳定性可以获得有效的抗拔出能力,后期具有较好的愈合率和临床效果[7-8]。该方式不受假体及骨折类型的限制,即使对于远端骨折块较小的病例,也可以进行有效固定。有学者[9]报道尽管如此,仍有骨折延迟愈合或不愈合的几率,最高可达19%,尤其股骨内侧粉碎、无法提供有效支撑时可导致内固定失效[10]。本研究中有7例患者采用了单一外侧锁定钢板固定,除1例内侧粉碎严重、内固定失效外,其余均达到骨性愈合。对于无法实现精确复位、骨折延迟愈合者,或骨折线向远延伸的Ⅲ型骨折(Su分型),有学者[11]推荐使用内、外侧双钢板固定,内侧钢板可对抗内翻应力,提供更坚强的固定,有利于早期功能锻炼。但对于多数假体周围骨折,该方式不作为首选,只推荐应用于Ⅲ型骨折(Su分型)。因此笔者认为,对于远端骨折块完整、内侧可提供支撑的病例,使用单一外侧钢板可取得良好的愈合率。严重骨质疏松、内侧粉碎无法支撑的病例,应当考虑使用双钢板,重建内侧骨质的完整性,对抗内翻应力。
逆行髓内钉治疗股骨假体周围骨折也可获得较好的疗效,髓内钉位于股骨髓腔内,具有中心固定、分散应力的特点,比锁定钢板具有力学上的优势,可获得满意的愈合率[12],但畸形愈合的发生率高于钢板[13]。本研究中有2例患者采用了该方法,利用原手术切口经髌韧带入路置入髓内钉,不直接显露骨折端,减少对骨膜的剥离。但应用髓内钉技术有严格的适应症,由于远端骨块存在骨质疏松,至少应置入2枚交锁钉,以提供足够的把持力。由于膝关节假体的存在,髓内钉仅适用于髁间开口的假体,髁间的距离应当略大于髓内钉直径,容纳更粗的髓内钉头部及尾帽。正确的进针点对髓内钉手术至关重要,假体的存在会影响进针点的选择,术前应查看假体参数,利用正侧位X线测量进针点和假体的间距[14-15]。即使进针点正确,骨质疏松导致皮质变薄、髓腔增大,也可使稳定性下降、力线恢复不良,应当尽可能使髓内钉通过峡部至小转子水平,以增加抗旋转能力[16]。股骨近端存在内固定物或人工髋关节时,禁用髓内钉,这样容易导致局部应力集中而发生骨折,需在股骨外侧加用一块钢板,跨过近端内植物。本研究中2例患者远端骨折块均较大,可以满足螺钉数的要求,其中1例既往曾行动力髋螺钉术,为避免置钉困难及应力集中,先将该内固定物取出,再行逆行髓内钉术,因股骨前弓大只通过峡部而未能达到小转子水平,也获得了临床愈合。
除了上述术式以外,也有学者报道了一些治疗方案,为重度骨质疏松合并假体周围骨折的治疗提供了新的选择。髓内钉治疗股骨干骨折时,如出现骨折不愈合,辅助外侧钢板可取得良好效果[17]。基于以上经验,有学者采用髓内钉结合外侧钢板的方法治疗假体周围骨折,综合了髓内、髓外固定的优势,增加了骨折的稳定性[18]。对于重度骨质疏松病例,也有学者提出髓腔内植入同种异体骨结合钢板的方案[19]。当假体出现松动的时候,应当采用假体翻修术。对于高龄、严重骨质疏松患者,即使假体是稳定的,也可采用翻修术,早期下地活动[20]。但该手术损伤大,术后仍有可能发生假体松动、假体周围骨折等可能,且对于高龄患者,麻醉及手术风险更高,因此行翻修术前,应该充分评估患者综合情况,通常作为假体周围骨折的最后治疗手段。
膝关节假体周围骨折有其自身特点,不同于常规的骨折内固定以及膝关节置换术,需要兼顾骨质疏松骨折的治疗理念以及关节置换原则[21]。在治疗中,笔者还有以下体会:初次行膝关节置换时,尽量多保留股骨远端骨量,减少骨折发生率。应当加强骨质疏松的治疗,预防及识别早期假体松动。对于高危人群,可以在围手术期行骨代谢指标的监测,预测假体周围骨折的发生,指导临床决策[22]。术前进行CT检查以了解假体稳定性,准备关节翻修器械,以备术中发现假体松动而行翻修术。
综上所述,由于膝关节置换术后假体周围骨折的诊治具有一定难度,因此应当采用循证医学的证据,对这类骨折进行有效的预防和正确的处理,使骨折得到可靠固定,获得满意的疗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