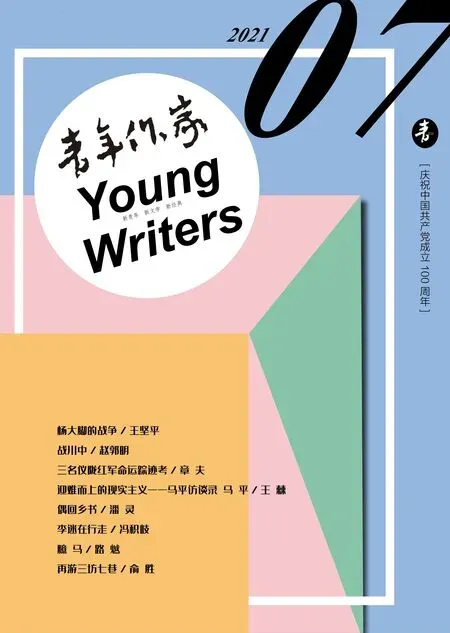心 猿
路 魆
要向不相信我的人,比如审问我的警察,或者此刻正在阅读的你,论证这段故事的真实性,已非我所能做。“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这句话只在那些见过、听过、经历过奇异之事,也行遍空想与苦痛的人身上成立。他们必须率先接受世间的残酷洗礼,以至于灵魂上无休止的折磨,才能对发生在马斯布身上的事,表现出足够的冷静,甚至能享受其中的奇妙趣味,以抵消种种不可名状的恐惧。
我从前也许不是这样的人,但在历经马斯布一事后,我就彻底地成了他们中的一个。
马斯布被送进停尸间几天后,他的母亲还没伤心多久,那天走进工作室准备收拾他的遗物,发现他竟然回来了,正坐在工作台前,继续他从前的工作:为一名死者制作蜡像。不过,她的第一反应却是以为丈夫为了安抚她的丧子之痛,夜以继日地制作了这尊马斯布的蜡像。于是,她叫丈夫过来,想表示感谢。但马斯布的父亲看见后,一脸惊恐,发誓从未制作过儿子的蜡像。他捂住妻子的眼睛,要她离开房间,还说,那只是人死后的幻影罢了,还不忘打个比方,来加强说服力——庙堂菩萨身上的颜料,风化后也会在地上留下相似的轮廓,更何况是一个在这里生活了二十多年的人?但她偏要看,就算马斯布化成灰,她都认得,而且仔细观察,那才不是什么幻影,明显是一个活人!
马斯布做蜡像的姿态跟从前无异,在雕塑泥上勾勒轮廓时运指如飞,头向前凑得很近,似要跟蜡像融为一体,连女娲造人都没他那么专注。看起来,这只是寻常日子中的一天,死神从未在他身上降临,他只是不知怎么从医院醒来,然后默默回了家,忘了跟父母打个照面。母亲缓缓地走向马斯布,伸出双手搭在他的双肩上,轻轻推了推,接着,她的手不由自主地颤了一下——啊,他的身体很凉,但不是死人的那种凉,而是透露着一丝人类的温暖。母亲相信,马斯布正在慢慢回温,要不了多久,就会跟常人无异,回归世界的怀抱。
在工作期间被打扰,总会令马斯布感到烦躁,最后,他停下手中的活计,转过头来,极其悲伤地说:“爸爸,妈妈,我已经很努力了,但还是捏不出弥留之际的人的模样。这宗委托要黄啦——你能替我向客户道歉吗?唉,我脸都丢尽了,还有什么活着的价值呢?”他失去耐心,疯了似的用十指在人头泥稿上抓出一道道划痕,两行浊泪从瞳孔扩张的眼中汩汩流出,像两个黑泉眼在冒活水,沿着遍布紫色瘢痕的脸颊滑落……
母亲明白那些紫色瘢痕是什么,心中大惊,对马斯布是个活人的事,又不那么确定了,觉得生与死的时间线应该出了什么错。但她没有把手缩回来,那是她最爱的儿子,于是安慰道:“那就不要做了,安息吧,儿子。”马斯布摇摇头说:“活着如何安息,死去又谈何安宁?要怪就怪我的鲁莽,本来安分守己,好好给动物做蜡像就行了,非要去接那宗委托。有些事啊,一旦碰了,就永远别想摆脱……”马斯布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后来,我反复猜测,到底是马斯布对死亡的无知,还是对蜡像工作的执念,驱使他能以死人的形式归来呢?答案肯定是抽象的。
此时,他父亲却一拍手掌,突然想到了一个绝妙的点子,雀跃无比,刚才受到的惊吓都忘光了。他搬来一面人高的落地镜,摆在马斯布面前,“看!看镜子!你现在是个死人啊,你自己不就是最佳的参考范本吗?!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马斯布似懂非懂地点点头,站起来要去看看镜中的自己……
母亲听完丈夫这番妄言后,不禁倒吸一口气,慌乱之下,拿起一块干结的雕塑泥,朝镜子扔过去,砸碎镜面。她一时不知如何解释,只好尴尬地说:“照什么镜子,别照!你知道,他一直没有照镜子的习惯,别为难他。”马斯布不知道父母今天为何古古怪怪的,但他不关心这些,因为只要想起那尊至今仍未能完成的蜡像,他就愁眉苦脸的,喉咙就像塞了只死耗子,舌头僵直,呼吸困难——这种异样也正是马斯布猝死前的症状——现在马斯布觉得冷、疲惫,深呼吸一口气,想走出门外,好让阳光驱除皮肤表面那种毛毛的微颤。但外面是个猩红的黄昏,白日临近覆灭。母亲想阻止儿子出去,但父亲反过来阻止母亲,说,若马斯布走在阳光下,不会变成一堆灰烬,若每个人都能看见他的实体、看见他的影子,那么,马斯布就是一个如假包换的活人。父亲想通过这种冒险的方法,证明他面前的人的真实性。
其实马斯布的奇迹早就被见证了。几个小时前,在他走回家的路上,白天的阳光那么炽烈,把他照得红光满面,街上很多人都看见了他,在短暂的惊愕过后,他们纷纷赞叹神迹降临。奇迹,真是奇迹!有人断定,此前马斯布陷入了某种神秘的假死状态,连医生都瞒过了,要不是及时醒来,说不定早已被送进焚化炉,或者泡在福尔马林液里了,可怜他父母差点就要蒙受无辜的丧子之痛。有部分好事之人还准备到医院门口集结,讨要说法,实则是想知道其中的医学奥秘。马斯布的母亲没想到事情传得这么快,逢人就说,“事情过去了,就别追究啦,”一心要隐瞒马斯布生死未明这个更大的谜团,还把马斯布关在家里,不让他露面。马斯布像只圈养在家的动物,不知道昨天,不知道明天,也不知道此时此刻到底为何活着。每当他提出要继续完成蜡像,母亲总是劝他休息。只有父亲极力怂恿他去做,去勇敢地走到阳光下,去展示身体上的神迹,“去吧,这是你的使命!”
有两件事,让马斯布的父亲感到特别自豪。第一件,无疑是马斯布继承他的工作,成了一位出色的动物蜡像师。第二件,便是马斯布的复活。他父亲这辈子都在借助蜡像形式,复活已灭绝的动物,将它们送进各地博物馆的橱窗,供人参观,让世人见识见识那些早已不在这片大地上生息的神奇动物的面目。除了制作灭绝动物蜡像,他们也接到不少制作各种濒危的、有趣的、奇特的动物蜡像工作,来代替普遍使用活体动物制作标本的不人道手法。但蜡像终究是蜡像,无论多么栩栩如生,也不过是一件注满填充物的硅胶摆件,只有逼真的外形,并无生理学的内在,在教学和科研领域上是无法跟真正的标本相比的。他没想到,第一个在真正意义上复活的竟是自己儿子,一具名副其实的活体标本,他多年来在这项工作上积下的福分,似乎得到了上天的回报。
由于种种不便,在制作灭绝动物的蜡像之前,马斯布和父亲很多时候只得到委托方提供的一张照片,如果是某种未得到公认的动物,可能只有一张在无意间抓拍留下的模糊照片作为唯一的参考,非常考验创作者的想象力。有一次,父子俩得到一张据说是渡渡鸟的真实照片,委托方希望他们能够制作出世界上最接近真实渡渡鸟的蜡像,卖给博物馆,好赚一笔钱。从照片可看出,那的确是一只拥有鸟的外形,能够在地上奔跑的动物,可是辨认程度仅止于一个虚化的影子。马斯布和父亲决定分别制作一尊蜡像,完成后再做对比。马斯布的成品像一只鸵鸟,而父亲的成品更接近于火鸡,于是他们又将鸵鸟和火鸡的形象做了结合,做出一尊稀奇古怪的鸟类蜡像。无奈之下,他们只能把这尊成品送到委托方手中,表示无能为力。委托方那时才承认,最早的照相机出现在19世纪,而渡渡鸟早在17世纪灭绝,因此不可能有人拍到渡渡鸟的照片。他这么做纯粹出于好奇心,想知道人类的想象力可以抵达什么程度,照片上的其实只是一只普通的公鸡。不过,他对马斯布父子的最终成品非常有兴趣,希望能以高价买下来,不枉他们大费周章,也算是一桩有回报的交易。但马斯布的父亲决定不卖,他从这种无中生有的虚幻形式中,看到了某种潜在的未来,以及超越常规的乐趣。最终,一尊不存在于现实的动物蜡像,成了他们的镇店之宝。它代表的是一种可能性,对此马斯布的父亲解释说:“生命演化的可能是无穷无尽的,也许它曾存在于世上,只是后来灭绝了,也可能差一点就进化成功。”
然而,马斯布父子的工作有一个巨大的缺陷。他们只做动物蜡像,从不做人物蜡像,不是因为他们不愿意,而是无法做。马斯布父子对人的五官比例、头骨轮廓和四肢尺寸,缺乏准确的把握,勾勒出来的模样基本是畸形的、丑恶的,跟他们还原动物的精湛技术比起来,失真得简直令旁人难以相信。就如先天性五音不全的人,对于再简单的歌曲,无论怎么努力发音,都无法准确走在调上。更值得琢磨的是,在现存灵长类动物蜡像的制作上,比如猴子、狒狒、猩猩等,马斯布父子的技术从不受影响。然而,当他们尝试按照人类发展的几个阶段——从南方古猿、能人、直立人到智人——这个进化模式,来逐渐过渡到现代人类蜡像的制作上时,手中勾勒的面目却总是不知不觉地、缓慢地倾向于崩塌和扭曲,始终无法突破界限。马斯布的母亲曾打趣说,父子俩的思维心智没有进化成功,是个失败的作品。吃过几轮败仗后,马斯布父子放弃了制作人物蜡像的尝试。
直到那天,马斯布鬼使神差地接下一宗奇怪的委托,制作一个“弥留之际的人”的蜡像。这是一个演化方向开始分岔的伟大事件,它直接导致了马斯布的死亡,为随后的复活以及更为奇怪的演化铺平了道路。委托人是一个跟母亲失散多年的男人,他记忆中对母亲的印象是空白的。当他终于找到母亲时,却是在她的弥留之际。母亲临终前的眼神,陌生而温柔,没有着力点,她的注视从未在他身上过久地停留,而是在四周的虚妄中飘荡。多年后相遇,他原本期待母亲能够给予他血缘上的感情冲击,感受来自生者最为炽烈的温暖,而不是双眼蒙着黑面纱,在生死边界扑朔迷离,仿佛叫她一声妈妈,就是跟死亡认祖归宗。男人感到极度困惑,依然为母亲拍下一张照片。外人绝不知道,照片上的女人微张着眼睛,她的死亡就在随后的一秒降临,在拍下照片后,她停止了呼吸。因此,每次凝视照片,男人总觉得自己站在鬼门关处,来自阴间的冷气团和来自阳间的暖气团相遇,形成一道生死的锋面,两股力量在较量,在他身体里形成波诡云谲的天气变化,时而大汗淋漓如降雨,时而寒冷砭骨似冰封。
男人向马斯布描述了这张照片给他带来的复杂情绪,希望马斯布能把他母亲处于弥留之际的模样,通过蜡像表现出来,做成一尊蜡像。理由是,他仍试图通过长久的凝视,凝视母亲最后的面容特征,搞清楚那份困惑的实质,那也是他跟孕育自己的母体之间的一个极为独特的重逢时刻。
“准确来说,”男人最后补充道,“我当时看到的不是死亡,而是死去。希望你能把握其中的区别。”
马斯布面临着两个递进式的绝对困境。其一,如前面所言,他根本无法在雕塑泥上勾勒出哪怕是一个儿童简笔画水平的人脸。其二,处于弥留之际的人,是一个正在死去的状态,而不是已经死亡,可是,他连最基础级别的固态人脸都无法表现出来,更何况要表现某种特定的、具有流动连续性的抽象状态呢?人本身的问题,超出了他在动物世界里引以为豪的想象力。凝视那位垂死女人的照片时,马斯布就意识到该困境的艰险之处,他看到一道界限,自己将永远无法逾越;它的跨度就如从猿进化至人类的时间那么宽阔,不,比后者还要更宽阔,而且,那不是时间可以衡量的;那种困境,是古猿祖先第一次被火灼伤时的惊愕,第一次用木棍戳动同类尸体却发现它只会一点点腐烂时的恐惧,第一次梦见死去的同伴后惊醒的惘然;而那道界限,则是在它们意识到火、生、死与梦境都是现实,却只能用身体去承受,无法超越这种现实的痛苦。马斯布看到了思维的顶点,他明白这一切,却义无反顾地接下这宗委托,全因他体内产生了一种全新的冲动。是的,他感受到了,那股对跨越界限的渴望,那颗贪婪而致命的企图心在搏动。头痛欲裂,极度烦躁,马斯布越来越虚弱,意志带动并快速消耗他的身体,终于在某个夜晚,他猝死在工作台前。倒下时,他的脸恰好压在雕塑泥上,此时我们悲哀地承认,那是他生前唯一制作出来的人脸泥塑。
马斯布的母亲断言,那个男人是上天特地派来夺走马斯布性命的,她亲眼看见马斯布如何一步步被击垮,却对此无能为力。他父亲不以为然,也并不出手制止,只是说:“要创造艺术,就先要成为艺术本身。要解决困境,也要先成为困境本身。做猴子,还是做人,这是个选择问题。我已老矣,但马斯布做选择的时候到了。”她不知道丈夫到底在说什么,后来不止一次指责丈夫是杀死儿子的帮凶。
外部风波逐渐平息,马斯布从解剖室消失的消息,没有传到医院高层的耳朵,但那只是时候未到。不过,有一个人绝对知晓此事,在躲起来几天后,他终于忍无可忍,悄悄找上门来。那个人就是马斯布尸体的解剖医生,亦即我本人。在决定投身动物蜡像制作事业后,马斯布就签订了遗体捐献协议,死后将自己的遗体捐献给那些好奇的眼睛,还有初生的手术刀。我就是那把手术刀,虽不是初生的,但也是锈钝的。
多年前,我为某位病人做了一次心脏手术,手术很成功,不久后却得到他自杀身亡的噩耗。病人自杀的原因,据说是心脏问题引起的长久精神紊乱。我是一个外科医生,这本不是我的职业范畴,但只要一想到我治好他的身体,却忽略了问题的真正源头——他的精神在我看不见的地方,正默默崩塌——无论同事怎么安慰我,自责的情绪并没有放过我。因为从某种角度来看,那位病人是死在我的手术刀下的,是我让他意识到,他的身体恢复健康后,精神并没有按预期随之得到拯救,而是依然承受着无绝期的痛苦。我难辞其咎,最后主动请辞,离开了医院。辞职后,我干了很多别的事情转移注意力,摄影,写作,旅行,甚至去乞力马扎罗雪山上,寻找海明威小说开头写到的那只冻死豹子的尸体……但旧日的噩梦啊,仍未离开我的脑叶,它栖息在那里,除非我死了,才会树倒猢狲散——若能这么理解的话。
那个清晨天还没亮,我辗转反侧。不知怎的,我突然跳下床,销毁了这几年拍摄的照片以及写下的手稿,决定重操旧业,披上尘封的医袍。我的行医执照依然有效。但那几年心力交瘁的生活,已经摧毁了我在外科医生这行业所要求秉持的那份理性和精确,仿佛失了焦,只能接一些不必给出精确治疗方案,或者不强制具备某种特定专业知识,更接近于文学那般性质模糊的医学工作,赚取不多的生活费。
有位非常念旧情的同行朋友,也许是出于同情,聘请我做他的助手,协助他进行尸检解剖工作。我欣然接受。与其为病入膏肓的活人做手术,现在的我宁愿摆弄一具冰冷的尸体,内心感到非常平静,甚至无动于衷。复业后,我在尸检岗位上负责第一名“病人”,正是马斯布的尸体。某日,朋友临时出差几日,要我代为检查马斯布的死因。没想到时隔多年,旧日的噩梦仍阴魂不散,我再一次失职了。如果导致一个活人死去,是我的第一次失职,那么,在解剖马斯布的过程中,我无意间让他以一种令人难以理解的状态复活了,则是我的第二次失职。当时,根据他父母关于他临死前的症状描述,我判断死因出在心脏,于是准备剖开他的胸腔,检查心脏。
然而,我悲哀地发现,持刀的手是如此笨拙,无法干脆利落地在胸腔位置划开一道切口,寻找心脏也费了不少工夫。当解剖室的窗棂射进来一道苍白的阳光,我发现马斯布的尸体已经在我手中彻底受损了,特别是心脏,它从胸腔内剥离,骨碌地掉落一旁。我无法想象自己现在的技术很可能连一个粗鲁的屠夫都不如。我简单地缝合他的胸腔,颓然坐下,决定接受失败的命运,摘下手套,走到外面打电话向朋友承认自己犯下的错。当我平复心情准备拨通电话,解剖室传来一阵器械跌落声,以及猫的叫声……肯定是从窗棂跑进来的野猫,叼走了马斯布的心脏;也肯定是那道苍白的阳光,唤醒了马斯布仅有的意志幻象;是的,肯定是的……要不然,怎么解释当我回到解剖室时,解剖台上空无一物呢?我甚至抛弃医生的科学理性,说服自己相信猫一旦靠近尸体,就会引起尸变这等民间传说的可能性。第一次失职,我的生活出现了一个黑洞。第二次失职,这个黑洞蔓延至我整个思维宇宙。我躲在家里,不敢外出,直到听闻马斯布竟然苏醒,并且已归家的消息,反复怀疑多时,才决定上门一探究竟。
马斯布的父母见我登门,欣喜得像看到了救星,同时面露难色,不知如何解释那件事。我说,事情的经过我已经清楚了。母亲说,她不是没想过给我打电话,只是考虑到签订过遗体捐献协议,害怕马斯布被抓回去,被迫变回一个死人。我请求先去见见马斯布。在房门前,他父亲神色忧虑地告诉我,马斯布刚回来时确实跟活人无异,但随着时间流逝,他变得越来越呆滞,越来越缺乏人气,现在的他只会坐着不动,发出吱吱哦哦的声音,随后打开门请我走进去。马斯布坐在床上,一尊木讷的蜡像似的,双臂已经显露出绿色的腐败血管网,散发微弱的臭味——我的第一个怀疑是,马斯布的父母忆子成狂,潜入解剖室,盗走了儿子的尸体。但当我听到马斯布的喉咙确实发出某些声音,他的双眼虽然空洞,但也更像在没有焦点地望着某处虚空时,我的内心才稍稍做出让步,认为目前的马斯布不能说真正地死了,但至少正在死去。
马斯布的父亲拿出相机,为儿子拍了一张照片,“好了,委托终于完成!医生,你还不知道吧,马斯布为了完成那项委托,把自己变成了一道完美的成品。这种献身精神只有我们艺术家才有。那么,接下来,你有什么高见呢?”
这回轮到我感到难堪了。爱伦·坡在《瓦尔德马先生病例之真相》中,写了一位医生利用催眠术,延缓一个弥留之际的人真正的死亡时间,奇迹般长达七个月,最后通过一声命令使他得以解脱,变为一摊腐液的古怪故事。我在马斯布身上看到相似的情况,也意味着,我接下来的每个操作,都极有可能决定马斯布到底是维持如今的状态,还是在下一个瞬间彻底归于极乐。但我的首要困难是,如何对他的心脏不见一事做出合理解释。
“两位……我必须承认一件事……”我鼓起勇气说,“马斯布的心脏不见了。”
跟马斯布的复活相比,一个器官消失这种事根本不值一提,他的父母没有因此生气。父亲走到马斯布跟前,突然转身握住我的手,发现什么惊人秘密似的说道:“是的!就是心脏!问题都出在心脏!”
“当然啊,这不是废话吗?”母亲说。
“不,我的意思是,”父亲继续用力握着我的手,“正所谓形具神生,只有身体完整了,灵魂才会随之产生。没有灵魂的人,跟一头猪有什么不同?我问你,蜡像跟标本的最大区别是什么?对,一个空无一物,一个五脏俱全。”
“那……”
“医生,你能给我儿子搞一个心脏来吗?”
“这……”
我当然不能为马斯布找来一个人类心脏,那不过是他父亲异想天开的论调。如果四肢无损,五脏俱全,就能达到形具神生,暗示所有标本其实仍活着,那现代生命科学未免太容易被挑战成功了。但为了缓解内心的愧疚,我假装答应他,然后出门走到菜市场,买来一个猪心。猪心跟人心非常相似,未来还有望进行异种器官移植,现在这颗猪心至少能在外观上骗过马斯布的父亲,直到他最终接受马斯布无法逃脱死亡这一个人类最大的宿命为止。
我在马斯布父母的监督下,解开他胸腔的缝合线,将猪心硬塞进他心脏的原本位置,然后缝合——所有人都能看出此举的荒谬和愚蠢,我在行医生涯里犯下了又一个将使自己颜面尽失的错误,痛苦得几乎要夺门而出。难道我要摆出一副精神科医生的姿态,向眼前这对凝神等待的父母深入分析马斯布不可能活下去的事实吗?如果这样有效,我就能从上一次事故带来的煎熬中解脱了。
然而,奇迹再次降临在马斯布身上——在我们苦苦等待近一个时辰后,他的四肢出现了明显的活动迹象,开始是一阵没有规律的抽搐,接着平复下来,最后出现带有目的性的动作:抚摸,抓挠,在地上爬行,打滚,四处嗅探,活像一只低等动物。奇迹,真是奇迹!我战栗不已。此刻支撑理智保持完整的唯一力量,反而是辞职那几年,我从写作阅读中获取的那种形而上学的纯粹情感,爱和真挚,被拓宽的抽象思维,几乎与科学背道而驰。我开始为人的血肉之躯,竟然能诞生如此抽象的精神体验而感到全新的喜悦,这是我在手术台上无论救活多少个病人都难以得到的快感。
但情况太狼狈了,显然马斯布的父母也注意到了儿子的行为的怪异之处。我不得不再次承认,我找来的不是一颗人心,而只是一颗猪心。马斯布的母亲顿时大发雷霆,骂我不仅侮辱了她儿子,那更是对我自己职业操守的极大损害,“你怎么可以拿一颗猪心来骗我们?”只有马斯布的父亲一而再再而三地从各种迹象中看到更长远的未来,马斯布能恢复活力无疑鼓舞了他的信心,不管那是一头猪还是一只鸟——如果给马斯布植入一只鸟的心脏,说不定他就能长出翅膀,在天空翱翔。他还向我们阐述,人类不过是演化历史上的一个失败作品,相比之下,猴子比我们更加适应自然环境,我们的身体是最大的弱点,我们仅能引以为豪的只有文明和智慧,如果能超越思维界限,那时人类再来自称是这个世界生死灵肉的主宰,也为时不晚。最后我还受到了威胁。马斯布的父亲声称,如果我不尽快为马斯布换上一颗人类的心脏,他就到医院告发我,告发的理由各种各样,比如说,医学伦理问题,任意一条都能让我名誉扫地,永不翻身。在此之前,只能让马斯布以猪的形式活着啦,他把家里的东西都拱翻了。
朋友出差结束回来,在听完我的描述后,觉得整件事太不可思议,以为我在为失误找借口。但当他想起我曾为一名病人的死而引咎辞职的往事时,摸摸下巴,说:“唔,你并不是那种会逃避责任的人呢……我再问你一次,你敢保证这件事千真万确,不掺一丝虚构成分?”“我拿自己的人格担保。”我回答。事情的转机,也发生在此。朋友原本是受动物园之托,解剖一头因为地盘殴斗而负伤死去的猩猩,如今猩猩的尸体正有待处理。如果我所言非虚,他倒可以帮我这个忙,把猩猩的心脏交给我。我问他,是否需要亲眼确认事情的真实性,再决定是否帮我。他拒绝了,表示不希望自己的职业理性,被某些超出他理解范畴的东西所左右,他之所以帮我,是基于对我品行的信任,而不是这件事包含多少真实成分。为了表示谢意,和秉着负责任的态度,我说我会把事情的最终结果汇报给他,他可以当聆听一个都市秘闻,聊作消遣。但朋友依然拒绝了。我似乎开始理解马斯布父亲的话,为何人类还不是世界的主宰。
猩猩心脏,是我尽最大努力能为马斯布找到的代替品,至少他的行为会更接近人类。万幸,马斯布的父母也表示接受。“养一只宠物猴,总比养一头猪要体面吧。”他母亲说。我发现,麻醉剂对马斯布根本不起效,严格来说,是对他的大脑不起效。因为现在主宰他身体的,不是大脑,也不是残余的神经反射,而是某种弥漫在他身体每个部分的存在意识,这种所谓的存在意识是非物质的、非电波的。另外,最初唤醒他的,也不过是一道从解剖室窗棂射进来的晕眩白光啊。唯一的手术时机,是趁马斯布睡着的时候。他果然睡得跟一头猪一样深沉……
换上猩猩心脏后,马斯布在醒来的第一时间,他眼睛里的光芒明显发生了变化。他像一个婴儿,不,应该说是一个灵长类幼崽那样,好奇地望着四周,对着他母亲发出嘤嘤的声音,还攀缘在高高的床脚上。他仍在最大程度上保留着动物姿态,用四肢爬行,偶尔蹲坐着,抓耳挠腮。慢慢地,在几个小时后,他开始表现出学习的冲动,模仿我们直立行走,使用汤勺和筷子进食。语言系统是发育得最为缓慢的,他只会发出尖锐的鸣叫,不过,人类婴儿至少在一岁左右才能够叫爸爸妈妈,所以我们必须耐心地等待和观察,不能妄图在一天之内,见证曾经横跨几千万年的人类进化史的发生。
但我们并没有等来令人喜悦的变化。马斯布不仅变得凶悍、狂躁,而且体表开始长出黑色粗硬的毛发,脸部骨架和五官气质,逐渐朝着一头真正的猩猩转变,我甚至不能称之为物种退化,他比民间出现的毛人更加接近古猿祖先。更糟糕的是,在我们一筹莫展之际,一群警察突然闯入,声称我们盗卖尸体,要我们立刻将其交出来。我朋友显然没有真正信任我,是他私下报了警,猩猩心脏不过是一个诱饵,为了找出我的“藏尸地点”。然而,警察进屋后,他们被眼前的景象吓坏了,谁也没想到这里并没有什么尸体,反而有一头活蹦乱跳的猩猩,向他们扑过来。大家冲出屋外,将门关紧,把那只野兽锁在里头。“报警的人怎么连人跟猩猩都分不清啊?”一个警察喘着气问,还看着我,似乎我能给出什么解释。我只是摇摇头,说道:“猩猩长得像人,不是很正常的事儿吗?”随后,渔护署人员也赶来了,说居民不得饲养猩猩作为宠物,根本没有检查那头所谓的猩猩,到底是不是猩猩,就把它抓走了。一番鸡飞狗跳的闹腾后,所有人都忘了盗卖尸体的事,整间凌乱不堪的屋里,只剩下我和马斯布的父母还处在恍惚之中,一时无法缓释。这一切好像只是来了一阵狂风扫荡,当风停后,世界只留下一地鸡毛……
一个晴日,我陪马斯布的父母去动物园参观。
在猩猩园里,有一群大同小异的猩猩。在其中,我认出了马斯布,不是因为那头猩猩的模样有多像他,我仅仅是认出了他胸腔上那道尚未愈合、在浓密的毛发之下若隐若现的解剖切痕。“你看,那头猩猩很像马斯布。”我指着那些跑来跑去的猩猩说。“猩猩当然很像人,”他父亲说,“这不就说明人是从古猿进化来的,而不是从石头蹦出来的吗?”“我倒是想养一只宠物猴呢。”他母亲的模样有点可怜。显然,他们已经忘了马斯布。我记起心猿这个词,它是古猿的别称,又指代孙悟空这个虚构角色。望着笼子里的动物,我有点呆住了。马斯布的父母催促我赶紧跟上,移步下一个园区,因为那里引进了一头濒危的白犀牛,他们打算拍些照片做参考。就在我转身离开的那个瞬间,我的眼角余光似乎看见在那群猩猩中,有一头朝我挥了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