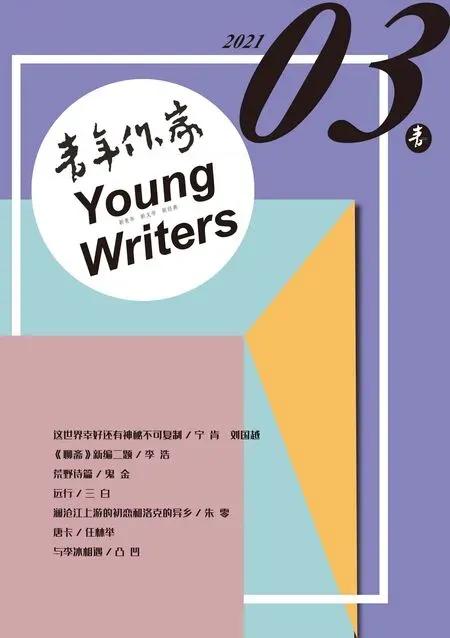献给无限生活的愉悦艺术
宋 尾
人到中年,于人生已无太多幻想了,波德莱尔所言“热情的预算”大大削减,包括幼时沉溺的神鬼之说。但我仍对未知的事物抱有敬畏,仍然相信暗示。这世上确有一些无法用科学具体分析的东西。这些难以解释的东西,被我们称为神秘。
在我看来,酒便是一种神秘。无人能清晰指明它的起源,也无法解释为何整座地球表面的先民都擅于调制这种神秘的物质,尽管它们的工艺和口味如地理和气候一样存在显明差异。但毫无疑问的是,酒在东西方都是一种悠久文化,也是一门悠久的技艺。我们国度最早出场的是黄酒,传说夏商时期一个叫仪狄的人创造了它。传说总比事实跑得更快,比历史更远,介乎于虚构和真实之间。但《诗经》有句:“十月获稻,为此春酒。”那么,这便是酒这种虚无的文化在典籍所留的痕迹,当然也可以说是文化的证物。这似乎说明,酒的历史几乎始终缠绕着人类历史,作为文明的某种象征如影相随。到秦汉时,酒已成为日常的饮品。两千多年来,很多坚固的物质包括一些顽烈的生物都遗失在时光之河,但这奇妙的液体却被一辈辈挽留下来。这倒不是什么神秘所致,而是它与人的日常生活实在是太密切不过了。酒,不单单是人类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产物,更是人的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连接的特殊渠道。有朋友说,一个人只要有两个习惯,他就不可能抑郁:一是写诗;二是喝酒。我觉得颇有道理,写诗能排泄心灵的冗余;而呼朋聚饮,则让人大量说话,自有一种疏导功能。话说回来,诗也是一种神秘。因此,由古至今,酒与诗的关联度似乎又是最高的。在没有大众媒体的时代,酒自身就是媒介(当然它现在也充分具备这个功能),诗人就是体验者、专家型记者。所以很大程度上酒是由于诗人的存在而得到记录与催化的,犹如用一种神秘来描述另一种神秘。于酒而言,蒸馏术是另一种神秘。古代成酒名称众多,或俗或雅,总跟颜色相关,比如绿酒、青酒、黄酒……直到蒸馏技术运用到酿酒工艺之内,就像一把偶然的钥匙打开了神秘之门,今人所熟识的“白酒”始才诞生。蒸馏究竟是何时融入酒酿造的,没有定论。不过,在四川宜宾,这道“转折”的缝隙却是有迹可循。据《宜宾县志》载,一千多年前,当地有一种酒,闻名远近,居于百酒之上,曰“重碧”。当时人们喜将荷叶浸泡到此酒中,因而得名。公元765 年,杜甫从乐山乘船东下,至宜宾时,当地行政长官设宴东楼,杜甫对重碧酒情有独钟,饮后即席赋诗一首:“胜绝惊身老,情忘发兴奇。坐从歌伎密,乐任主人为。重碧拈春酒,轻红擘荔枝。楼高欲愁思,横笛未休吹。”能让诗人如此兴酣,说明当时宜宾酿酒已很具风味。至宋代,宜宾手艺人在重碧酒的基础上酿制出“荔枝绿”。可见,唐宋间宜宾酒仍以碧绿为色。期间,中国白酒非常微小但也特别重要的一场转折被另一位文学大家、亦是品酒大师黄庭坚记录下来。其时,黄庭坚贬谪宜宾,如苏东坡一样,失意之人的心灵更为柔软,味觉也更为敏感。当时重碧酒仍为当地主流名酒,可黄庭坚偏偏钟情于一种私房酿制,即姚子雪麯,并为之赋诗,篇名为《安乐泉颂》——可见此酒在他心中的分量。黄庭坚为何钟爱此物?它采用蜀黍、大米、糯米、高粱、荞子等五种粮食混合酿制,成品有如“杯色争玉、白云生谷”。首先,黄庭坚描述所品饮的姚子雪麯,近乎白云和白玉,说明绿酒变“白”了;其次也佐证,至少在北宋,宜宾已掌握了蒸馏提纯的酿造技术——囿于工艺极繁复,产量极低,只能供极少数人享用。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区别于大众市场的高端白酒,出现了。如果说重碧酒是宜宾的前酒,那么被黄庭坚赞美追捧的姚子雪麯,其实就是今浓香川酒——五粮液之源流。从重碧、荔枝绿到雪麯,名称随着酒色产生了微妙转换,这种进化,便是五粮液的塑身所在,也是浓香白酒的玄奥之门。对酒这种野生的神秘物质的驯化,至此进入一层新境界。但我难免好奇于雪麯在当时的生成,那层玻璃纸是如何捅破的?就如酒的神秘本身,无法窥知。不过,我也似乎——或说是接近于——品尝到了黄庭坚当时所得到的愉悦。
酒的秘密当然藏在酒坊里。今年初秋,我随一行作家赴宜宾,出入于五粮液各车间、作坊,亲眼看见酿造的诸多工序与过程,继而感悟到,酒的神秘即为自然与人相交的神秘。走访期间,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个细节是,宜宾还保留了古老的明代酿酒作坊,并且这些作坊并非作为标本或博物馆道具,而是持续在繁衍生产,古老的作坊迄今还安然地存活在生活区域,犹如野花盛开在田野。宜宾城东,有一条老街——鼓楼街,门市兴旺,行人熙攘,五粮液最早的一座老窖池就隐于这闹市街边,门扉古色古香,左侧木楼顶上,悬一块斑驳古匾,上书“长发升”三个大字,右下侧标注着“洪武六年”,随后入眼十几个形似馒头的泥堆——它们是世上现存最古老的窖池,计有六百五十多年。古窖形态各异,长方形,四方形,刀把形,看起来没有定式,其实是古人善于运用自然,因形就势而成。如果说五粮液是有秘密的,那么,其中一点就是这个——充分尊重传统,擅用自然之法:循环。相较于六百多年的古窖池,“长发升”发酵所用酒糟的年代更为久远,工作人员介绍,五粮液用于蒸酒的母糟除靠近封窖泥的酒糟外,全都是长年累月循环使用。循环的关键是,必须保证在最初发酵中有老糟的存在。所以,“长发升”的老糟循环多少年、多少遍,已经成了一个谜,唯一能确定的是,“一定比长发升自身历史更长”。如此说来,这种循环倒是跟文学近似,文明也是如此。没什么是独自成立的,所有瞩目的事物都因站在巨人的肩上,底下不可见的沉淀和微粒,才是构成那些循环的源泉。那天在长发升我第一次品尝到了刚酿出的新酒,酒液甚至还是烫热的。它或许与宋代雪麯有所差异,但亦符合黄庭坚当时之感受:“清而不薄,厚而不浊, 甘而不哕,辛而不螯。”透过长发升,我似乎也慢慢走近了那些遗落的梦境——砖木结构的建筑,抬梁或穿斗式屋架,小青瓦覆屋;窖壁上方是缠枝花纹的木刻,抬梁上雕有凤凰与牡丹,以及“前店后厂”的整体结构。原来,古时的酒作坊就是这样子的,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酒坊就是这样式儿的,它不在庙堂也不在荒野,而在人间,它在的地方,就是人间烟火最为浓墨之处。又听说,像“长发升”这样的古酒坊在宜宾还有七处,均保存完好,且持续在酿造,蓦然间有一丝说不清的感动。这哪是酒作坊啊,这分明是活着的呼吸着的民间生活的博物馆啊,这里面不单单存储了酒的秘密和酒的历史,还是我们这共有世俗生活的一座精神遗址。
从酒坊出来,与几位朋友去了金沙江和岷江交汇处,站在黄昏的码头上,忽然,一个事实渐渐在我脑子里清晰起来。
老实说,三十年来我一直是浓香白酒的忠实拥趸,你要问我五粮液好在哪里,我只能说个一二三的。但这次来宜宾前,有朋友这样问我,你说五粮液好,那它为什么好?顿时我惘然而无法作答。此刻,站在长江的起始点,望着烟波浩渺的江水,我似乎得到了一种答案。为什么是五粮液?五粮液为什么是在这里而不在其他地方?酒,确实是一种神秘,但没有什么是无缘无故的。就像每个汉字背后都有文化和故事那样,我们所见到的五粮液已经昭示了它存在的秘密。如果要我归纳的话,首先是天时地利,两江交汇处不可复制、不可迁徙的酿造环境;其次,是未曾中断的酿造传统文化,以及六百五十多年不间断发酵的明初古窖。前者我们可归结为自然属性,后者是人为。两者缺一不可。但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人”——尊重自然和传统的酿造者。五粮液是人与自然合作共融的一件堪称完美的标本。没有一代代将酿酒视若生命的杰出匠人,也就没有精湛的技术和延绵的文化传统,更不会留下这“千年老窖万年糟”;如今,这一代的理想主义者用科技接续古老的传统工艺,使得中国白酒成为一种美妙的艺术。
在我看来,酒从诞生起就是一种喜悦的艺术。酒的使命有如火神的象征意义,是一种欢乐,是极致,是胜利后情绪的极致。我见到的五粮液酒窖,那些孜孜不倦的酿造者,则将这种传统的喜悦变为一种富于时代审美的艺术,也可以说,是这座江城献给我们无限生活的愉悦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