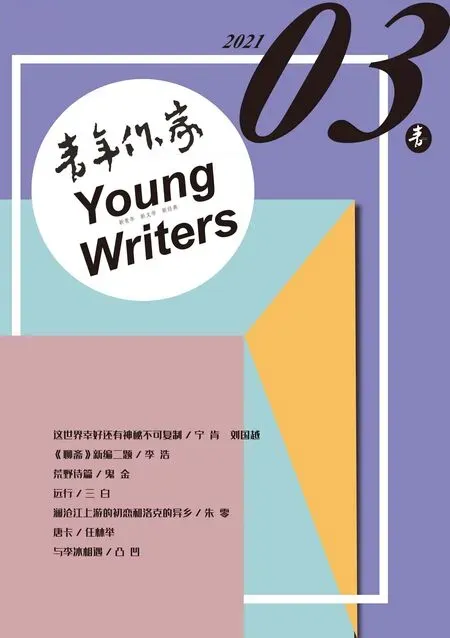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蒋 蓝
我的父亲就读于民国政府的蒲阳空军幼年学校,他有8 个弟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爷爷因是自流井盐务官员,只好带着一帮儿女来到宜宾落地。在我记忆里,叔叔们来自贡市看望大哥大嫂,一般会带来几瓶酒。酒并不都是五粮液,往往只有过年来时,才会送上一瓶。父亲就着豆腐干、油炸花生米,喝得很慢,一脸陶然。他会用筷子蘸酒让我舔……这一舔不要紧,到我可以一口气喝下一瓶酒时,父亲又后悔了。
记得我还在读小学时,过年三叔四叔来家,父亲开五粮液,杯子小了,酒满溢到桌子上。他猛然低头,舌舔不已,大口吮吸。叔叔瞠目以对,父亲笑笑说:好酒!好酒!我至今保留着叔叔送他的一盒5 瓶装的五粮液,二两一瓶,时光漫漶,舍不得喝的酒,早已蒸发殆尽。以至于我后来为父亲上坟,五粮液是必带的。不要在坟前乱洒哟,这样做他定会骂我暴殄天物。
二十多年来,因为各种会议,我去过很多酒厂参观。2004 年,我去宜宾宗场以及大捲子村采访过五六次,那里是刘文彩三姨太凌君如的老家,每次我必从五粮液厂区穿过。我在遍布浓郁酒糟味的风里穿行,很自然会想起爷爷、叔叔,以及埋首于桌的父亲。酒糟味里,有粮食的精灵在不停旋舞,不是针尖上的天使,而是踏水而行的鸟足微波凌步。奇怪的是,如今很多酒厂里闻不到酒糟气味了,别人说这是世界最先进的生产工艺所致。我不懂,只好干笑。
记得二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到五粮液酒厂与会。今年8 月的一个上午,我在这个日渐扩大的花园工厂里徜徉。天下着雨,我见到了一株黑铁一般的桃树,树上无花。我很想看看桃花,以及桃花倒映在水中的模样。我伸手触及黑得发亮的树枝,枝丫颤抖起来,竟然吐出了一树的桂花。这是我的幻觉,也许不是。
去国家文保单位“利川永作坊”参观时,也许是刚刚喝过红茶,口齿清洁敏锐,喝了一小杯72 度的原度酒,那种绵柔、不辣、清香、清冽之感,萦萦而起,宛如一股大力从涌泉直贯头顶。想起与我有一面之缘的著名学者何满子,我曾向他索要过签名本《中国酒文化》。我还知道他的习惯,毕生只喝五粮液,从不喝杂酒。他是在那种充和的美感里,回到了中国酒的深处。
我不大相信关于北纬30度上的种种附会,比如美酒传奇。诗人埃兹拉·庞德说:“我的爱人不容易遇见,就像水底的火焰。”其实,酒才是从水里萃取的带焰之火。但我相信,拥有千里浩渺岷江、剽悍的金沙江两条蔓延文化带的相聚,只有在宜宾,才能开始它的互嵌交融、对撞生成。岷江裹挟蜀山精魂,水体清冽,在汉代已能铸造闻名遐迩的蜀刀,漂洗的蜀锦才会五彩斑斓、鲜丽夺目。这是来自古蜀祖地的血脉之水,当它与携带青藏高原密码的金沙江相遇,是泥浪与清流的拥抱,是细沙与钢砂的遭遇,是阴柔与粗犷的深情相拥。此地更蕴含了古蜀治水的人文踪迹。无论是历史上“岷山导江,东别为沱”的错讹,还是厘定金沙江为长江正脉的后世,两条大江在此逐渐沉淀出一种无可替代的天造地设。
公元765 年,杜甫从嘉州乘船顺岷江到达宜宾,当地最高长官杨使君在东楼设宴,并用当时宜宾最好的名酒“重碧春”酒款待杜甫。杜甫于是写《宴戎州杨使君东楼》诗:“胜绝惊身老,情忘发兴奇。坐从歌伎密,乐任主人为。重碧拈春酒,轻红擘荔枝。楼高欲愁思,横笛未休吹。”从“歌伎密”到“重碧”,“重碧”之“碧”指青绿色,是度数高于自然发酵的蒸馏酒存放一定时间后所具备的典型酒色。“重”字是指酿造工艺上重复酿造之法,古称“重酿”。酒不醉人人自醉,真是浓得化不开。
五粮液所蕴含的五行哲学,在两条大江的强力加持下,昭示了一种伟大的美学:充实。《十三经注疏》解释说:“充实善信,使之不虚是为美人,美德之人也。充实善信而宣扬之,使有光辉,是为大人。”
奇怪的是,在琳琅满目的五粮液酒史博物馆里,竟然没有蜀人扬雄的《酒箴》。连一个字也没有提及。
在我看来,扬雄善饮,他的《酒箴》是世界上第一篇关于酒文化、酒哲学的文章。如果饮酒关乎精气神,那么《酒箴》则直捣命运。关键词是:人、酒、瓦罐、井口。翻译过来就是:你就好比一个陶制的罐子。你所处的位置,就像是悬挂在井边。虽处于高处面临深水,动一下便有危险。你肚里所装的不是酒而是凉水。你不能左右晃动,并被拴上绳悬挂在高处。一旦绳子被挂住,被井壁上的砖石碰碎,便会抛到浑浊的水中,粉身碎骨。你的用处只仅限于此,还不如装酒的皮口袋。装酒的皮袋子安装有滑稽开关,却仍是肚大如壶。尽管整天往里边装酒,人们仍会用它来装酒。它还被视为贵重之物,经常被放入皇帝出行时随从之车。它甚至还出现在皇帝和太后的深宫,在官府奔走谋求。从这一点来说,酒本身又有什么过错呢?
这就是说,你是成为瓦罐,抑或成为皮口袋呢?而在一个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当下,昔日韬光养晦的皮口袋们,现在身兼数职,当做了钱袋子。
文中提到的“鸱夷子皮”与“滑稽”,均是汉代蜀人早已使用的装酒设备以及利用虹吸原理的酒器开关。正所谓“物外烟霞为伴侣,壶中日月任婵娟”。所以啊,我喝酱香酒就容易想起“歌伎密”,而喝五粮液,我则有点正襟危坐。
现在我坐在凉亭里,斟满一杯酒,天空就向杯底凹陷下去了。我在想一些往事,想那些再也见不到的亲人,还有那个美丽绝伦、最后被活活饿死的三姨太凌君如的命运。苏轼所谓“诗酒趁年华”固然很正确,但大口痛饮的年华过去了,如今在中年时节的下午时光里,才能独自品味出一些顺滑、清冽之后的那种腮边反刍的涩味,然后是颓然。起身时分,是释然。
悄悄举杯。酒本身又有什么过错呢?“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