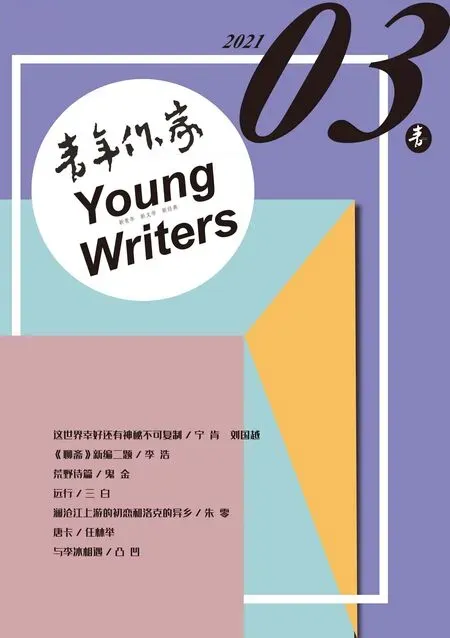城市的门
刘鹏凯
一
今年以来,我不知怎么搞的,整天神魂颠倒,萎靡不振,细想想,我发现这和我吹的萨克斯管有关,另外,还有那个可以让我发疯的小妮。
认识小妮是在一年前的某个晚上,我和朋友墨墨正在八毛街上的一家大排档吃饭,我们正袒胸露怀、酣畅淋漓地喝着扎啤,嘴里喋喋不休地说着一些不切实际的找钱计划,口气一个比一个大,好像我俩吃完这餐饭立马就会成大爷似的。其实我俩都明白,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儿。嘴上吹吹,是为了吹出一片气氛,好让自己在心里平衡一下,产生一种莫名的亢奋感,这种亢奋感会使我们说话和办事有些底气,要不然我们在特区就无法混下去。墨墨将一个冒上来的酒嗝喷出来后,显得有些兴奋。他说:三子,你要是有了钱怎么花?我说:该怎么花就怎么花。他又说:告诉你,我有钱非娶两个老婆不可。我无可奈何。我知道墨墨已经想钱想疯了,他四年前辞职和女朋友来到特区,初来闯荡的激情不几天便被坚硬的现实一扫而光,随后,女朋友也跟一家公司的老板跑了。想起这个,墨墨会立即暴跳如雷,恨不得一下子将那两个狗男女一下一下撕扯下来吃了,他愤怒的表情会让人想到台风之前的雷鸣电闪。据墨墨自己说,他以前在内地的一个美院工作,从我和他来往之后,我看他一点都不像,他连美和漂亮的概念几乎都搞不清,怎么会是美院的呢?不过,如果在美院扫扫地、提提水,随便打一个什么杂倒是有可能的。我没有问过他这类事,这是江湖规则,英雄不问出处嘛,何况他搞没搞过美术完全和我没一点关系。我们的内心都各自明白,我们不会成为朋友的,因为凭感觉完全不是一个道上的人,命里注定我们是酒肉桌上吃吃喝喝的朋友。墨墨早些时候曾自己折腾了一个什么公司,说是公司,其实也就是他和一个看起来挺妖的湖南女子,那女子我见过几次,没什么印象了,下巴上突出地长有一颗很大的痣,这个我记忆犹新,因为我有一次还摸了一下那颗痣,她十分狂躁地瞪着眼睛,一口要把我吃掉的神情。
回想起来,那天晚上很美,我不动声色地坐在那里,听着墨墨对于金钱和女人的诉说,可我并没有完全在意他的谈话,我一边喝着啤酒,一边斜睨着邻桌的一位女子。那女子头发修剪得很短,脑后却独扎一个小辫,很长地拖在背后。虽然是大热天,她却穿着一身仔衣仔裤,透过裤腿上遍布的窟窿,可以看到几块雪白的肉。这是一个很前卫的女子,令我有些心惊肉跳,她没有任何表情地坐着,不时用一只手摸摸另一只手上的手链,偶尔发出几声金子和银子撞击的响声。
这女子就是小妮。她好像意识到有人在盯她,突然一回头,碰上了我的目光,我没有预料到她会突然这样,我内心显得十分尴尬,却装出一脸镇静自若的神情,那神情很冷漠,并没有因为小妮的眼睛而惊慌失措。我记得她盯了我好一会儿,见我无任何反应,便转过头去,突然又回过头来,冲我十分友好地笑笑。
墨墨并没有注意到这些细节的变化,他只管起劲地说着他的事。我起身将椅子向那女子挪了挪,探出头问她。
就你一个?
一个。
来做什么?
和你一样。
我看着她一脸吃惊的笑容,顿时觉得自己十分可笑。都出来几年了,怎么还这样子呢?我为这句话非常恼怒自己。
八毛街在特区很繁华,几乎是不夜街,红红绿绿的灯在远处或者近处向你眨着挑逗的眼神,这是诱惑的现象。生活也越来越具有现象,人都在这种现象上奔来跑去,累得气喘吁吁,始终找不到都想得到的那个结果。
结果会以什么模样出现在每个人的面前呢?
那次晚饭后,我知道了小妮是从北京来的摇滚歌星,来了几个月了,仍旧找不到感觉。怎么会找到呢?阴柔的南方不喜欢她那份独特的粗犷。小妮为此感到很悲痛,她把这悲痛告诉了我,我便从此成了她倾诉悲痛的对象。一个人享受另—个人的幸福是幸福的,而聆听悲痛却让人牵肠挂肚,尤其是来自一个漂亮异性的悲痛。
我想帮助小妮,那是悲痛所引发的力量。
二
三年前,我手提装着可爱的萨克斯管的黑皮箱只身行进了特区,我把萨克斯的声音吹响在我前进的路上,只要路上有行人,都会被我的这种声音感染,他们驻足张望,文明地拍着双手。我靠我的这种声音站稳了自己的脚跟,我把那忧郁的声音挂在墙上,日日倾听。整整三年,我没有遗漏一天。
我慵懒地躺在床上,微眯着双眼。室外的绿树一动不动,阳光恬静地穿过玻璃,将墙推在了一边。小妮还睡着,发出细微而有节奏的呼吸,她的手随意地放在我的胸上,在静静的早上,我强烈地感受到了生命的跳动。我想推醒她,好让她也感受一下早上的阳光。但我没有这样做,我知道她对安静的东西没有兴趣,而只喜欢声嘶力竭的歌声。
我点起一支烟。
吐出的烟在阳光里变成了蓝色,它们向上盘旋着,我顺着蓝色的烟抬起目光,在云一样的烟雾中,我看到一只金黄的蟑螂静静地趴在天花板上的一个角落,它那长长的触须微微地摇晃着,如一个探雷器,机械而警醒。
这时,我脑子里十分幽默地生出了一个使我自己也感到惊讶的问题:我们的触须长在哪里?
想到这儿,我有些难过,浑身顿时疲倦无力。我伸手将电扇的功能摁到最强风,呼呼的风只一个轮回就将空中四处逃跑的烟雾赶得无影无踪。小妮似乎感到了凉意,她哼哼着向我怀里钻了一下。
小妮自从那次认识后,我们几乎天天在一块儿,大白天睡觉,晚上出来活动,小妮在我的帮助下每晚可跑三四个场,最后一个场则是跑到我所在的新彩虹酒吧,我们唯一的区别是她要跑场,因为她是歌手,而我却不同,我要为乐队伴奏,中间还要插上一段独奏,一直坚守到凌晨酒吧打烊,然后我们一道去吃夜宵,吃完夜宵我再把她送回住处,每次我回到自己住的地方总是在凌晨四点左右。几个月下来,小妮索性打的把她的东西搬到我的房里,我们从此同眠共枕、同饭共吃,丝毫没有一点响动发出。
窗外是楼房的头或者身子,参差不齐地拥挤在一齐,透过一丝缝隙,我想象着声音之外的东西,它们凝聚着,拼命地钻入我的躯体,让我逐渐从迷迷糊糊的状态中清醒过来。
小妮翻了一下身,传呼机就突然叫了起来。
是谁呼我呢?我看着那行黑色的阿拉伯数字,往往会想起一个人行走在路上的情景。我轻手轻脚下了床,将别在裤带上的手机从套里抽了出来。
三子吗。你在干吗呢?是不是还在睡觉。
我听出是墨墨的声音,拿着手机继续躺到了床上。
告诉你,晚上我们一起去总统酒店吃饭,把小妮也带上。告诉你,我刚认识了一个大老板,非常有钱,口气大得惊人,花钱也大得惊人,喂,喂,喂喂,告诉你……
别再告诉我了,那个大老板关我屁事。
怎么能这样讲话呢,告诉你,他一定要见见你,吃完饭,还准备到新彩虹听你吹萨克斯呢,够给面子吧,你就等着拿小费吧!
他怎么知道我?
我告诉他你是我的朋友,他一听很高兴,说听你吹过萨克斯,很靓。哎呀!不说了,一下子又说不清楚,晚上见面了再告诉你,记住,六点在总统见。说完,墨墨就挂上了那头的电话。
我双手将小妮搂在了怀里,心里却在想着我在昨天和今天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三
特区临海。这仅仅是一个城市的象征。
晚上,我和小妮打的赶到了总统酒店,这是一家五星级酒店,又面对大海,环境幽雅不说,单说去了那里的人临了海一坐,心情便如海一般,汹涌澎湃,涛声阵阵。
我们径自上了二楼,墨墨和那个大肚子老板早已候在饭台边,远远看去,墨墨的神态像一个小奴才。那个老板四处张望着,摆出一副派头来。这种神态我早已司空见惯,有钱的暴发户大都如此,他们会用腔调和男性说话,又会用眼神和有些妖艳的女性说话,只要他们瞄准的猎物,跑掉的自然不多,甚至有的还会自投罗网,巴不得被这些老板的眼光那么蜇一下。
在新彩虹酒吧的空间里,我不用睁眼睛,便会闻到类似的浓烈气息。
小妮跟在我的身后,一声不吭。
我们互相寒暄后开始入座,那个老板朝一个服务生轻轻挥了一下手,服务生便毕恭毕敬地走来,脚下没发出一点声响,点了菜后,又不声不响地走了。不一会儿,所点的菜几乎都上齐了。那个老板姓胡,长得慈眉善眼,一副笑眯眯的模样。他站起身来,朝我和小妮举起酒杯。
认识你很高兴,希望你们不要客气。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从现在起,我们算是一家人啦,以后若有用得着老兄的地方,只管说一声。
我没作答,只是礼貌地点点头。墨墨已开始向台上的菜发起了进攻。
这位小姐长得好靓哦!是你女朋友吗?
我点点头。小妮似乎有些不适应,慌乱地冲那老板笑了笑,随后,又用手玩着另一只手上的手链。
大家十分文明地吃完了这个长达两小时的饭局,胡老板显得异常激动,一手感激地拍着墨墨的肩头,一手又朝空中挥了一下,那个白面服务生很快又走了过来。
先生,还要点什么?
埋单。胡老板看都没正眼看一下服务生,冷冰冰地吐出这两个字。
稍等。服务生转身朝总台走去,一会儿,服务生手托收银盘又走了过来,躬身对胡老板说:
先生,一共3280 元。谢谢!
胡老板从口袋里拉出一沓人民币,数了3500 元递给那服务生说:剩下的是你的小费。
谢谢!服务生依然很礼貌,躬身退了一截路,才转身离去。
小妮的手在台下轻轻地拽了我一下。看来,她尚未碰到过这种场面。
饭后,胡老板开着自己的白色本田思域,将我和小妮以及墨墨送到了新彩虹。我们下车后,他笑容可掬地说:我办完事后,一定来捧场。
胡老板的车一溜烟消失在霓虹中了。我站在温暖如初的南风中,怀想着城市里到处乱跑的人,他们和我一样,忙着一种既看不见又摸不着的结果。
四
此刻,我不知道该怎样去面对自己。
这对于我的确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当我在拥有小妮的时候,我曾经天天都在体验失去她的痛苦,我为自己的这个设想不时地打着寒战,虽然我所处的环境不是冬天,而我常常能看见北方的大雪扑面飞来。
小妮走了。
那一段时间,我几乎丧失了所有的理智,我四处寻找小妮的影子,但最终没有。她会消失于何处呢?我猛然想起了那个大肚子的胡老板。
那晚凌晨一点,酒吧里的人逐渐地走了,我的同伴们也吆三喝四地去吃夜宵了。我和小妮没去,还有胡老板和墨墨。胡老板是后来才来的,他是一个人不声不响地进来的,我们谁也没看见,他一个人找了一个空吧台,就那么一直坐到散场。其间,有一个服务小姐曾递给我一个厚厚的红包,那是在我演奏完萨克斯之后。我来到后台,撕开红包一看,我完全惊呆了,是谁给了我一万元的小费,这是我在酒吧里从未遇到的事啊,既不留名,也不留姓,我简直到了怀疑自己的地步。我打探着台下昏暗的吧台,借着红红的烛火,我看见了一个个陌生的男女面孔,他们对我没有在脸上有任何表示。这个人是谁呢?出手如此慷慨,如此阔绰,真的会是胡老板,仅一面之缘,不像。当我看遍了吧台上所有的人,却唯独没有看到胡老板。后来得知这钱确实是胡老板叫人送给我的。那么当时他躲到哪里去了?难道还有不可告人的隐衷。
站在今天,我明白了过去的许多事理。
我们一同走出酒吧,一同钻进那辆白色的本田思域。先送走墨墨,胡老板又绕道驶上海边那条著名的情侣路,车上的音响效果很好,节奏强劲的音乐穿行在红色的夜里。
小妮很累,她靠在我的肩上,将我的手紧紧抓住,像要有什么危险发生一样。我默不作声,静静地看着窗外的物体一件一件被滑到车后,海面上黑黑的一片,遥远处,似乎有几盏渔火在莹莹闪亮,除此之外,什么也看不见了。街面上仍有小车一闪而过,同样开着音响,很大。
胡老板老练地驾驶着车,目不转睛。在快要到达我们的住所时,他忽然问:你们每天都这么忙吗?
是啊!比较特殊一点。
这么忙能找着钱吗?
不完全是为了找钱,而是为了找感觉。
我清楚我的回答对于他来说是苍白无力的。在特区,金钱是不可割舍的东西,它伴随着人们的欲望和文明,当然,这东西对于别人是无可厚非的,同样对于我,我也需要钱,可是,我精神的深处隐隐约约还藏有一个不能与人言说的秘密,这个秘密从我起程的那一天起我就怀有了,我把它悄悄地装在心间,整整三年,如同我倾听我的萨克斯的声音,我不想离断,也不想舍弃。我经常用这样的回答回答着几乎同一个问题,他们不曾理解一种声音对于一个人的影响。
我怀念过去和即将发生的声音。
胡老板显然很惊愕,他在座位上动了动肥胖的身子,然后又悄无声息。我无法看清他的表情,在运动中的暗夜里,我凭感觉能体会到他的心情,就像我可以闭上眼睛能够闻到一股气息。
白色的车终于停下了,胡老板隔着玻璃朝我和小妮挥挥手,一踩油门,就消失了。
小妮低着头,一句话不说,我觉得特别奇怪,平常她不是这个样子的,她总是有说有笑,有时还会跟你来一个恶作剧,高兴了还会唱上两句。她走在前面,背影里好像注入了从前的悲痛。
难道悲痛要再一次降临?
现在我终于明白,悲痛随时都伴随着人生,主观的或者客观的,只要是人,无一逃脱。
小妮已经离开我快半年了,半年来,我除了四处打听她的消息,就是一个人闷在屋里。屋里还是老样子,小妮走的时候,她的东西没搬走一件,我几次想从中发现踪迹,但是没有。
我已经到了绝望的境地,这不是一次离去,这简直是对我人生的一个惨重打击。我在自我折磨中虚度着每一个时光,我记不起我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我记不起自己的从前和现在到底有没有区别。我唯一记得的,小妮走的那天晚上,月亮很高、很亮。
墨墨好久不见了。
胡老板也好久不见了。
难道他们都死了,我一躺在床上就这样想。
不行,我要去找找他们,说不定他们知道小妮的下落,当我生出这个想法时,我的身上陡然出了一层厚厚的冷汗。
原来的正在复出,现在的正在消失。没有想到,我会十分痛苦地把自己关在了门外。
五
酒吧老板昨晚向我发出最后警告:如若再不老老实实上班,后果自负。三年来,我尝过被炒鱿鱼的滋味,我不想失去我目前的境况,而我现时几乎已情不自禁,我越来越颓废地幻想着自己的未来,刻骨的伤痛再次凶猛地袭击了我,就和当初倾听小妮的悲痛一般,牵肠挂肚。这会儿我多么像一位迟暮的老人,整天坐在窗前,遥想着曾经光亮的过去和风一样来到我身边的小妮。
我似乎已做好了离开这个城市的一切准备,起初的感觉已被现实无情地击溃,所有的愿望此刻都呈现出原始的灰暗,犹如黑夜中的大海。
汹涌的海水将我一点一点开始湮没。
八毛街上人来人往,街边的高楼耸立在云端。我无精打采地走在深深的楼谷里,想着一些和自己无关紧要的事,想得最多的还是小妮,我多么希望小妮会突然出现在我的视线内,和我一同走过这条繁华的街道。最终没有。
我站在一个十字路口边,不知该向哪条路走去,在以往我不会出现这种情形。那时候,我可以随便走哪条路,不管是对是错,那是因为我心底是踏实的,而今,我却不知所措,我为自己的这种踟蹰不前而懊恼不已。在一瞬间,我觉得自己老了许多,我眯着双眼,弯着腰,艰难地行走在孤独的八毛街上。
前几天,一个过去的朋友告诉我,墨墨被抓了,原因是贩毒。在我得知这个消息时,好像没有一点异常的反应。墨墨出事是在我预料之中的,他太爱钱了,几乎已到了苛求自己的地步。那个朋友说,改天我们约好去看看墨墨吧!我答应了。
当我无处可走的刹那,我决定一个人前往拘留所去看看墨墨。拘留所离市区较远,需要坐半个钟头的大巴。决定之后,我就蹿上了一辆正开来的大巴。
在昏暗潮湿的拘留所里,我见到了墨墨。他一脸的恐慌和不安,目光始终飘浮在一个捉摸不定的位置上,我实在不知道他在和我谈话的时候,能具体地看到什么。墨墨坐在我的对面,平时的一惊一乍已全然不见了,前后半个小时的会面,他根本没说一句话,为了打破这种难堪的局面,我总把话说到前头。
什么时候进来的?
两个月前。
你怎么会干这事呢?这事不该是你这种人干的。
墨墨没吱声,他将头埋得很低,我从台面上看过去,只能看到他那颗光秃秃的脑袋。他越不说话,我越不知说什么好。待在这里头,会有什么话好说呢!
静默和守望,我俩一直这么僵持着。
正在我不知说什么话题时,墨墨突然说:告诉你,我知道小妮去了哪里。
这句话如一根救命稻草,重新燃起了我内心的热望。
她现在在哪儿?你是怎么知道她的?我由于心切,步步紧逼。
说来话长,你还记得那个胡老板吗?
我一下想起了那个出手阔绰的大肚子胡老板。
记得。
小妮在他那儿。
我不想再多问下去了,我只想马上见到小妮,至于小妮为什么会在胡老板那儿,只要见到小妮,一切都会水落石出的。
我二话没说,顾不得墨墨那双乞求的目光,站起身子,朝大铁门狂奔而去。
三子哥,你不能这样走,我需要你的帮助,你一定想办法救救我,救我出去,我想回家,我不想在这个地方混了,救我一下吧,三子哥,你不能扔下我不管。墨墨大声地在我的身后哭喊着。
当我奔出门口,外面的阳光一下炙热起来,统统地聚集到了我一个人身上。我在阳光里奔跑着,我要去找胡老板,去找小妮。
盲目只会毁灭自己。那个炎热的夏季仿佛还在我的眼前晃动,漫长而又难熬。在我的眼前,到处生长着茂密的亚热带丛林,它们有高有矮,有肥有瘦,可它们没有遮挡住阳光的炎热,那束阳光似乎一直追赶着我,将我烤得焦头烂额。
我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哆嗦。
六
没有人认识我是谁。
我把我所租住的屋子翻了个底朝天,终于找到了那个胡老板的名片,上面有公司名称、电话、手机、传呼机,一应俱全,我双手捧着那张珍贵的名片,兴奋得有点喜出望外。我久久凝视着它,我在心底盘算着是先打电话好,还是先传呼他好,抑或直接打他的手机。此时此刻,我彻底体会到了什么叫天马行空。也只有在大城市里才会有这些天马行空般的人,他们每天都在不同的地方奔波着,寻找着那个共同的结果。这其中也有我。
想来想去,我打算先采取一个稳妥的方式进行,我先让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按着名片上的传呼号打了出去,当传呼小姐甜甜地问了一声您好时,我的心儿又开始狂跳不止。我很礼貌地将传呼号告诉了小姐,那小姐却说:对不起,胡先生已停机半年了。听到小姐的回答,我整个人傻呆了半天。我又立刻打去电话,没想到不但没人接,反而是一个机械的声音告诉我:对不起,对方欠交电话费,已停机。我一下惊慌起来,马上又打去手机,同样是一个机械的声音告诉了我同样的一个信息。
我瘫软下来。
几乎是同时,我清醒地意识到这是一个阴谋。
我怀揣着最后一线希望,按名片的地址找到了位于八毛街附近的一座写字楼,楼很高,当我乘电梯直达十八层楼时,我出现了从未出现过的眩晕感。
我按响门铃,我想象着多日未见的胡老板一副大腹便便的熊样,可开门的却是一位非常精瘦的先生。
你找谁?
对不起,请问胡老板在吗?
胡老板?胡老板?那人念念有词。胡老板是谁?
我赶忙拿出名片,隔着有空格的防盗门想让那人看清楚一点。说:就是这个胡老板。
对对对,有有有,是有这么一个胡老板,可他早已走了,差不多已走了半年啦。
那个阴谋已不打自招,小妮肯定是跟胡老板跑了,或者胡老板跟小妮跑了。
我站在门口哭笑不得,那个人倍感诧异,狠劲地将门摔上了。
怪谁呢?三年来我奔跑的结果出来了,这个结果让我难以置信,让别人可以笑掉大牙。我垂头丧气地走进电梯,当箭头指向下时,我又有了一种新的感受,那就是强烈的失控感。
我不想放弃自己,我要找到小妮,我一定要证实一个阴谋。
从那天起,我开始每天晚上奔跑在各种酒吧、歌舞厅,整整一个月,我未得到任何一点关于小妮的消息。
望着空空荡荡的我的房间,我黯然神伤,我咀嚼着一种来自信仰的痛苦。我留意着天花板或者四周的墙上,居然没有发现一只能够飞翔或者爬行的小动物。
七
我早些时候,已经炒了老板的鱿鱼。
我不想再光顾城市。
我背起那个落满尘埃的装着萨克斯管的黑皮箱上路了。
我倾听着一种忧伤的声音一直走向自己的心脏。
我终于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
八
一切都是那么遥不可及,我现在坐在北方一场大雪刚刚过后的冬天里,过着自由自在的居民生活。生活中原来没有故事,没有情节,没有真实,也没有虚构,它们就是它们原来的模样,谁会改变本来的生活面貌呢?
谁也不会!
北方寒夜的上空是碧蓝的,我能在那上面看清星星的错落有致,它们在现象上没有任何联系,可是,它们在结果上和生活一样,千变万化地发生着意想不到的联系。
我不会欺骗生活。
在那段似醒非醒的日子里,我最终没有找到一种叫做结果的东西,那个东西太近,又太远。现在好多了,我不想那个结果了,生活反倒显得平静如水,没有一丝悲痛会游入我的心间。
那天在街上,我看见了一个很像小妮的女子,可我始终想不起来小妮到底是谁?
是谁从门里出来又进去了呢?又是谁从门里进去又出来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