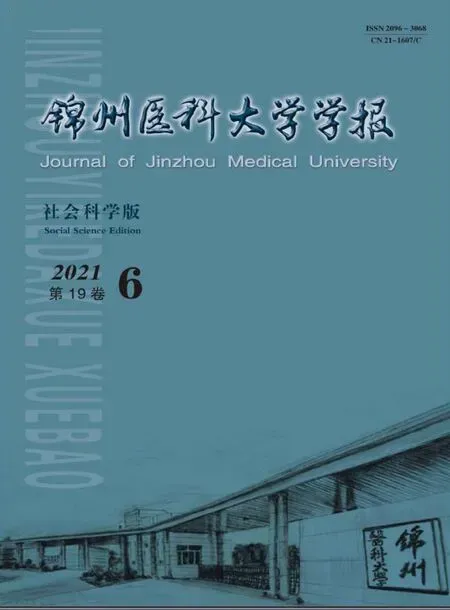姑息治疗手段的伦理考量
林珂宇,张洪江
(锦州医科大学 人文与管理学院,辽宁 锦州 121002)
姑息治疗,作为一项不常出现于大众视野的临终医疗手段,常常会引起众多伦理性非议:人们面对仅存的生命时,第一选择难道应是不予治疗,任病情肆意发展吗?姑息治疗真的可以缓解病患的痛苦吗?诸如此类的非议层出不穷,本文将针对姑息治疗所引发的典型伦理性问题进行分析,消除姑息疗法带给人们心灵的阴影,让特殊人群可以更放心地接纳姑息治疗,认同其为临终状态时的最佳医疗方式,为我国姑息治疗的发展提供伦理性解释与支持。
一、姑息治疗是否等同于放弃治疗?
一位老年妇女在2020 年新冠肺炎暴发期间,因胸背剧烈疼痛并伴有低热就诊,诊断为新冠肺炎和右肺癌IV 期(双肺、肝、骨转移)。家庭成员要求竭尽全力治疗新冠病毒,同时控制肿瘤,延长患者生命。但由于止痛药使用不规范,病人在整个治疗过程中疼痛控制不理想,出现了严重的呼吸困难、便秘、呕吐等不良反应。因病情进展,患者双侧胸水及心包积液,胸闷、气短、疼痛等症状逐渐加重,建议行姑息对症治疗。家属反对并提出:姑息治疗是否意味着放弃治疗,我们是不是离死亡更近了?
1.放弃治疗与姑息治疗的争辩。放弃治疗的定义可谓是“因人而异”,对于健康的大众人群而言,放弃治疗仅具有着简单的字面含义,放弃了治疗而已;对于患有重病的病人家属来说,放弃治疗无异于凭借着“四字箴言”收回了与病人仍可共度的零星时光;对病人而言,放弃治疗就像递出一份死亡判决,当它贸然展现在自己面前时,要带着怎样的心情去面对它,撕碎或安静地放在胸前,这更是一种极其复杂的选择。医学界认为,放弃治疗是指“在患者被确诊后,临床医师针对不可治愈的晚期患者或仅能维持呼吸心跳但生命质量极度低劣且不能恢复意识的病人,不给予人为地延长生命的治疗。[1]笔者认为,放弃治疗实则围绕着两种特殊群体展开,一种为病情可以自行好转或通过医疗干预得以治愈的病人,此时放弃医疗意味着通过医方判定且家属与患者同意终止有效的手段;另一种是对于病情严重不可治愈的患者,医方通过审慎检查判断及依据家属及患者本人要求而行使的终止治疗的行为。而姑息治疗,是一种不仅应用于临终前的治疗手段,在严重疾病的任何阶段都能起到辅助作用,即使同样需要患者的知情同意,它与放弃治疗仍有天壤之别。世界卫生组织对姑息治疗的定义修正为:通过早期鉴定并正确评估和治疗身体、心理或精神方面的疼痛和其他问题,预防和缓解痛苦,改善正在面临与威胁生命疾病有关问题的患者(成人和儿童)及其家庭的生活质量。姑息治疗在实践中遵循的核心原则为:患者的自主权,即尊重患者选择;行善,即做善事,其根本出发点要有益于患者的生存质量;非侵袭性,即治疗过程中采取伤害最小的方法;公平性,即公平地使用有限的资源。[2]放弃治疗与姑息治疗皆属为特殊群体在不同情况下的特殊手段,区别在于姑息治疗是提供缓和治疗的医治行为,而放弃治疗代表着治疗的终止。若将放弃治疗与姑息治疗同一而论,濒临绝症患者家属同意放弃抢救的行为是否等同于姑息治疗行为?对于患有慢性疾病“帕金森”的病人实施姑息治疗,难道就代表着接受了“死亡洗礼”?
那些混淆了“放弃治疗”和“姑息治疗”的人们,实际上只是不能接受死亡和生命并存的事实。唯有接受死亡是必然的结局,才能真正思考如何减轻临终病人的痛苦、如何照顾病人及家属的心情,让病人在安详中度过生命最后一刻。
2.放弃治疗与姑息治疗并非等同。首先,姑息治疗的“早期鉴定”是一种处于慢性疾病中所实施的鉴别手段,它的终极要义是尽早让患方比医生更了解自己的患病状况,让患者及家属有时间去理性思考进而做出下一步医嘱;“缓解患者的痛苦”虽在字面意义上与放弃治疗的含义有所混淆,但选择放弃治疗的患者实则承受着身体与心理的双重折磨,因为当人们处于死亡的边缘时,关注的大都是未完成的遗憾与心结,放弃治疗可能会让患者家属陷入“过早放手”与“延长痛苦”的两难境地之中,它并不能疏解患者内心的纷乱,更无法替代姑息治疗提高患者及家属的生活质量;况且,姑息治疗能够应用于病程早期,与其他旨在延长生命的治疗手段一起实施,包括化疗或放疗,从而更好地管理疾病缠人的并发症。姑息治疗还可以赋予患者精神和心理治疗的双重诊疗,为患者供给积极、乐观的生活方式,减轻终末期痛苦直至死亡。[3]于患者、于医院,通常在谈及放弃治疗或者姑息治疗手段时,大都是在其丧失“治疗价值”的情况下,放弃治疗与姑息治疗的分界线在于当患方处于失去治疗价值的状态中,是否还“有计可施”,通常在这种状态下,不代表患者就无事可做了,其实仍存在非常多的事情未完成。
在《人间世》的《中国人生死观》一集中记录了几个案例。一名年轻男子,患有恶性肿瘤并伴有骨折,经诊断无法治愈后,选择回到家附近的二级医院进行姑息治疗,直至闭上眼睛,妻子一直陪伴在他身边。在访谈中,妻子说:“他很快乐,好像没有痛苦,每天的状态都很积极,如果不是成天不工作,可能自己都忘了生病这件事。”影片并未给予案例任何评价,只是静静地记录这一切,似乎并不存在孰是孰非的问题,存在的只是每个人不同的选择。我们只能说,当患者深谙积极性治疗已对自身生命没有任何价值时,能够作出姑息治疗的决定之勇气是最值得我们赞颂的。不妨设想一下,若这位病人在了解自身病情后郁郁寡欢,拒绝一切医治行为而选择放弃治疗,他的结局和真实的结局有何不同?当死亡已成为倒计时,“放弃治疗”与“姑息治疗”将病人引向了不同的精神世界,如何抉择则需要结合实际情况具体分析,但可以肯定的是,案例中的年轻男性在临终前的心情绝对不是饱含痛苦的。
一篇香港医院管理局文章的题目与我们提出的问题不谋而合:《舒缓治疗让末期病人活得更好,积极助减身心煎熬,绝非放弃》。(姑息治疗在香港称作舒缓治疗)“谈死色变”是大多数人对死亡的普遍反应,无须羞愧,无须自责。面对死亡和病魔缠身,“活下去”成了心中唯一的明灯,而延命医疗则是临终病人最宝贵的绳索。被世界称为“近代日本预防医学之父”的日野原重明曾说:“即使每个人‘生的时刻’已经决定了‘死的必然’,但因‘讨厌死亡宁愿选择不出生’的人并不存在,死和生是不可分割的,没有生就没有死,没有死就没有生。领悟其内涵,方知生和死本质是一样的。”正是由于人们时刻怀抱着对死亡无比恐惧的心理,才会将姑息治疗“简而化之”为放弃治疗,细想果真如此。
二、“以人为手段延长垂死过程”真的符合患者的利益吗?
1.生命伦理角度的利益权衡。以晚期肿瘤病人为例,就当前医疗发展现状来看,他们是治疗无望的、要忍受病痛及治疗手段双重折磨的一类人。对于一般的家庭而言,一些人宁愿“砸锅卖铁”也选择继续医治。《孝经·开宗明义章》中阐明:“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中国的孝文化根深蒂固,亲情的纽带注定了在面对患病子女/父母时的难舍、难断、难离,有一丝希望也要尽万分努力,至于病人的意愿,可能往往会被忽视。无论晚期肿瘤患者在年轻时活得多么意气风发,治疗时往往会被折磨得毫无生命尊严可言,而病人本身对于生命的看法却通常不会受到家人的理解与尊重。家属通常会想当然地认为:他还小/年纪大了,并不懂。家属常怀着一厢情愿的爱,美其名曰“都是为了你好。”很多西方国家存在着死亡教育,有宗教信仰,有法制化的安乐死。纵使心中有千般万般不舍,也能与亲朋好友欢快地相聚一场,追忆往事,彼此告别之后悄然离去,基于社会及文化背景的差异,我们很难做到这一点。可我们真的应该反思,“一厢情愿”后的结果,是病人自己想要的吗?《Being Motal》的作者在书中提到,使用机械呼吸机、电除颤、胸外按压或在临死前入住监护室的末期肿瘤患者,其生命最后一周的质量要比不接受这些干预措施的病人差很多。姑息治疗这种不以治愈疾病为目的,而是着重考虑如何帮助患者享受当下最充分生活的治疗方式,在有效缓解疼痛的同时不仅能够保持患者头脑的清醒,还可以使患者有尊严地度过人生最后一段时间,这种绝妙的治疗方式有何不可呢?
以上一章首先出现的案例为例,该老者经受着新冠及肺癌的双重折磨,当靶向治疗效果无益时,延命治疗手段就真的符合患者及家属的利益,真的有利可循吗?现如今,延命医疗为病房普遍应用,结果不仅使病人面临无法忍受的痛苦,家人饱受煎熬的噩梦都将由此开始。在痛苦缠身的患者身上所实施的技术性干预不仅延长了其生命的长度,更是延长了其“死亡的时间”。很多患者及其家属被技术医疗的陷阱所禁锢,将仅剩的生命交给技术处理,荒诞地认为只要钱到位,技术便可挽回无可救药的现实,殊不知,对于医方和患方而言,这都是一项“西西弗斯”的工作。
不难发现,一股浓厚的“效用主义”风气常弥漫于病房,尤其是重症病房之中,几乎所有家属都会跟医生说“请一定救活我的家人”,但很少有人说“请你让我的家人舒服一些。”这与伦理学的效用主义紧密地贴合了,即行为本身的正确性根据行为结果的好坏来判断,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行为似乎并未顾及人的尊严,在康德的义务论中得以体现。康德认为,人人都拥有同等的道德尊严,最慷慨的爱国者和最吝啬的守财奴、最勇敢的英雄和最可怜的懦夫都拥有同等的尊严,当然对生命质量论而言则是两说的(在下一节会予以论证)。当代伦理学者多纳根对于康德主义原则是这样叙述的:“决不允许不把每一个人,自己或他人,当作理性动物来尊重。在医生奉患者家属之命为器官极度衰竭、仅凭借呼吸机生存的新冠患者实施冰冷无望的延命治疗时,其首要利益是延长患者的生命,但这并未考虑到患者遭受的痛苦与奄奄一息的尊严,若单从效用主义的角度去考量延命医疗,“救人”似乎是失之偏颇的。
在《流行病学》一书中,希波拉底最具代表性地提出:“对于疾病,要养成做两件事的习惯——帮助,或至少不伤害。”不伤害并不等于要无条件地维持生物性生命,也不要求启动或继续治疗而不管病人的疼痛、痛苦和不适。由此,如何合理地权衡福利与负担就显得尤为重要了。笔者建议,在被重大疾病压制的患者面前,治疗与否可以通过参考权衡过后的福利与负担来决定,即我们把受益的几率和数量与可能的负担进行权衡来分析治疗是否存在过度或无效。因为在进行大部分的医疗决策时,医方会不可避免地考虑到患方的受益期望,这导致在可能并没有实施治疗义务的情况时,进行了过度的医疗措施(常会对患方造成伤害却没有补偿效益)。美国法院曾强调,有必要通过权衡福利和负担来确定总体效益。很多时候,姑息治疗可以栖身为绝症患者的最优之选,正是因为它在尽可能地减轻患方多方面负担的同时又兼顾了患者的合理化期望。美国健康与人类服务部曾经提出了一个规则:“提供基本的营养、液体以及日常护理,是人类尊严的基石,而不是医疗判断中的一个选项。”我们需要知道,复杂又昂贵的治疗并不是义务性的,即使负担巨大,治疗也是可选择性的。
2.现代医疗科技的滥用效应——与医疗说“不”。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突飞猛进,人类对高新技术的依赖也日趋加重,当医疗技术作用于人类身体时,常常会忽略甚至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命质量与尊严,这里出现了一个吊诡现象,[4]人们既认同自然规律,认为人类终有一死,但似乎人类又无感于死亡的最终结局,在死亡面前“残喘”而放弃了活的尊严与生的意义。科技的能力与治愈性毋庸置疑,但不当地使用甚至滥用很可能令本就脆弱不堪的特殊患者们(癌症晚期、垂死患者等)更快地徘徊于死亡边缘。日野原重明先生曾说,要把医学当作一门艺术来看待,音乐也好,绘画也罢,其中蕴含的娴熟技艺皆是需要长时间持续努力才能获得提升,音乐与绘画艺术描绘了人类的情感,无论是善良、悲伤还是爱都会深深感染听到或者看到这些艺术作品的人,医疗与此类似,虽然医学发展日新月异,但也如其他科学一样,并非无所不能,现代医疗面对很多疾病时同样会束手无策,无法将患者从疾病、伤痛中彻底解放出来。研究表明,当医生作为一个“倾听者”站在患者的角度,问诊时面带诚恳的微笑,倾听患者的真实诉求,即便同样伴随着冰冷的仪器治疗,患者的疼痛和愁苦也会得到大大的减轻。中医的治疗方法讲究“望、闻、问、切”,对于患有慢性疾病及无法治愈的病人,医方若可以做到以减轻患者痛苦为期“望”、不对患者真实情况充耳不“闻”,以患者为中心,切实应对患者的“问”询以及给予患者合理化关“切”,那么以病痛为伴的患者将不再束手无策,从而也会更坦然地面对自己的疾病。鲁道夫·博灵·泰斯勒在创建圣路加国际医院时提出这样的理念:圣路加国际医院不是治疗疾病的场所,而是用爱疗愈患者痛苦的所在。任何医院都不应将全部希望寄托于高新的医疗器械上,而应以关爱为引、以全心全意治疗为依,给予患者“望”“闻”“问”“切”,更好地治愈患者的伤痛。
科技悲观主义认为,科学与技术的结合变成技术——科学,成为位居于主导社会的中心地位,但是伦理和科学问题的分离可能会使科学变得致命。笔者认为,我们应该对科学技术抱以中性态度,在科技决定经济的大时代,在我们有权利去决定如何活下去的年代,我们不再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群体,合理地运用科技,将科技与自身情况相结合,从而进行全方位的考虑,再去决定如何应用才是正解。生是偶然,死是必然。综合而言,所谓“救命”的治疗无论是在决定上还是道德上都是可选择性的。对于患者而言,真正的最佳利益绝不是无意义或无效的治疗,运用理智的头脑全方位地权衡总体利益、福利与负担以及科技与生命才是最优选择。当然,姑息治疗的实施一定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同情况区别对待。
三、姑息治疗与生命价值论的关系
如何为仅存的生命赋予意义,许多学者引入姑息治疗的手段进行分析和实施,但实践中却产生了疑问——姑息治疗难道不是对生命价值的一种慢性的泯灭吗?由此,应特别强调生命质量判断在确定延命治疗时的选择性与义务性以及可能出现的相关问题。
1.延命治疗的选择性与义务性分析。似乎,当一个人被定义为“患者”,他就理应像流水线的产物一般,接受一个又一个的治疗方案,却忘记了“患者”在成为“患者”的前后,都是一个完整的人,都有其内在的需要和人生的目标。实则,在濒临死亡的病人面前,责任不是由提供延长死亡过程的治疗义务来决定的,而是由为濒临死亡的患者提供合理的关怀义务来决定的,因此,治疗与不治疗是选择性的。治疗的选择性与义务性代表着实施一项医疗行为的强制性与非强制性,即是依据自身情况可以选择实施与否还是根据道德或法律强制实施进行。生命的存在意味着价值的存在,生命的价值论将人们引向了错误的方向——治疗对病人就是有利的,不治疗就会对病人的生命价值产生威胁。现如今,人们对于生命的价值和有质量的生命常常含糊不清,但我们需要分清的是:个人生命的质量与个人生命之于他人的价值。最常见的案例:穷苦的年轻夫妇为了拯救先天性缺陷的新生儿不惜变卖一切家当。当生命的质量与耗费的社会资源及无法承担的重担不成正比时,个人的生命质量又将价值何在?很多人可能会对此产生辩驳:怎能将神圣的生命与金钱作比较,这本身就不是对等的。正是因为它的不可比拟性,我们才需要对福利与负担进行合理化的衡量,从而限制生命质量的判断,同时避免关于个人偏好或社会价值的偏颇性说辞。患者及患者家属可以运用有限生命质量论,结合医学的判断,合理决定延命治疗是选择性的还是义务性的,以进一步决定姑息治疗的引入与否。
2.姑息治疗引出的道德滑坡问题。将姑息治疗应用于实践,极有可能引发道德滑坡等相关问题,例如,因金钱产生的医疗技术滥用问题、协助死亡抉择的滥用问题等。以开头出现的案例为模板加以极端的变化:患者家属因某些特殊情况急需用钱,而患者的伤亡保险恰好可以弥补用钱的缺口,患者家属在知晓患者命不久矣后,采用姑息治疗的方式使患者安度晚年(目的却是加速患者死亡)。在医方对详细情况不知情的前提下,对于患者家属采纳的姑息治疗意见,医方虽有帮助实施治疗的义务,但是在全部知情的情况下,医方也应当如此吗?
可见,由医生干预而引起死亡或协助死亡的实践与决策存在着被滥用的风险,这意味着家属选择性的治疗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会造成对患者生命的伤害与亵渎。在社会中,存在患病老者及先天性残疾的新生儿需要大量公共资源的现象,当社会对这些特殊人群的存在表示不屑与歧视的态度时,道德滑坡现象就更有说服力了。扪心自问,当一个新冠患者站在你面前,即便有着严密的防护措施,你愿意与他交谈或握手吗?在社会的压力下,去坚持自身的信仰与道德观念显得尤其困难。道德中反对人们直接或间接性致使他人生命受到伤害的原则,并非是一个个孤立的岛屿,他们是保护着尊重人类生命规则的一整片群岛,被孤立的岛屿越多,群岛就极其容易遭到破坏。因此,如果我们仅仅关注规则性的改变与说辞,而忽略真正意义上的态度的改变,那么固执的规则将会腐蚀掉尊重生命的一般态度。
我们常常期盼医方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促进患方福利,但我们却并未深刻地探究过福利的意义。剥丝抽茧,患方的真正利益应该出自患者还是出自患者家属,如果道德判定家属的极度自私将受到道德谴责,医方是否还应提供给患者所需的医疗救助,医生的抉择也充满了艰难。关于医疗行为道德滑坡的问题至今还没有明确的法律加以规定和限制,但“打法律擦边球”的行为一定是受到人民深深谴责的。各方面的论证都是推测性的,尽管我们不能解决这些问题,但我们可以坚定本心,道德是杆秤,应存在于每个人心中。
3.姑息治疗是生命价值的延续。“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圣治》)。古代哲学家认为,人作为生命的承载体,其存在本身就富有价值,价值是之于自身的存在,由此衍生出人性。不免有人质疑:当一个人的所作所为被他人判定为有价值时,不正可以证明人的价值是之于他人而存在的吗?即人与人之间才会产生价值。“生命权者,不受他人妨害,而对于生命之安全,享受利益之权利也”。[5]有一个很简单的说法可以推翻这一论点:一个富豪时常救济穷人,大家都认为他对社会做出了贡献,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人,突然有一天他变得一贫如洗不再有能力资助他人,他的价值性就随之消失了吗?很显然这里所体现的价值而非价值本身,可以判定他的行为对社会而言是有利的,具有社会性,即他的存在并不是道德上的强制也不是普遍性的责任,他只是出于自身能力及道德思想与觉悟而产生的行为,因此,笔者赞同价值性是人类从出生开始就被赋予的这一说法。[6]既然人自出生便具有价值,那么何种行为会对价值产生影响,一向以“医人心”著称的姑息治疗又是否会为生命价值带来不良影响呢?这里我们只讨论后者。
我国姑息治疗的发展向来比较缓慢,大多数医疗资源都集中在治愈性治疗上,仅有1%的人可以享受到姑息治疗服务,并且大多数临终关怀机构都集中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我国姑息治疗的排名虽靠后,但政府在姑息治疗的政策方面已经出现了历史性的转变,开始制定相关的政策,公众对于姑息治疗的认知情况也有了相对的提升,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之于我们国家,姑息治疗的发展是有前瞻性的,有着极大的进步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