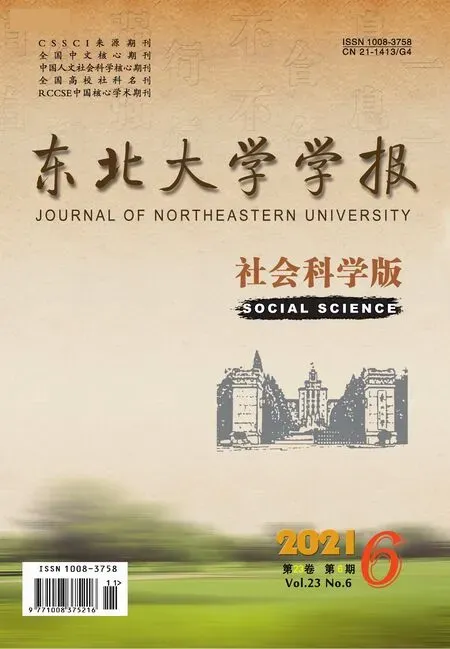从生命意识到审美观念
----论“直觉”在跨文化语境中的流变与融通
姜 智 慧
(1. 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 上海 200062; 2. 浙江外国语学院 英语语言文化学院, 浙江 杭州310023)
“直觉”一词是西方哲学中英文单词“intuition”的汉译,于20世纪初期随着伯格森的《创化论》进入中国,又经克罗齐“直觉表现论”的译介与接受,逐渐成为中国文艺美学与批评话语中的固定语词。实际上,直觉也是中国艺术的特征之一,但在西方“直觉”概念进入中国之前,中国古代文化中的直觉思维并没有固定的语词,而是以各种意义不定的单音节词如“道”“气”“清”“一”“虚”等来表示。这些语词不仅仅体现为一种认知思维方式,同时也是一种审美意识。根据“翻译之所以可能,乃是基于对不同‘语言’和‘概念’同一性之认识,不同语言和概念之间具有可通约性”[1]的说法,在中西不同语境中,直觉显然既有共通性,也有翻译的“不确定性”。“直觉”作为“intuition”的对应翻译,二者之间虽然具有共通性,但是并未充分传达“intuition”的确切内涵,也不能概括中国传统直觉思维的全部意蕴。“直觉”这一译名实际上承载了丰富的跨文化内涵,不仅实现了作为一个现代性概念与中国传统直觉思维的话语对接,同时也使得中西两种直觉思维得以融通,生成了新的意义,并牵动了一系列观念与思想的变革。“直觉”概念在现代中国从生命意识到审美观念的演变,就充分体现了这一跨文化融合的过程。
一、中西交集:对于“直觉”进入中国的考察
从词源学上考察,“intuition”一词源自拉丁文“intuicioun”,起初带有某种神学意味,意为“直接或即时的认知,精神知觉,或顿悟”(insight, direct or immediate cognition, spiritual perception);其拉丁文动词形式“intueri”,原意是“凝视,聚精会神地看”(loot at,watch over),这里的看是一种心看,而非眼看,意为“不经推理而直接感知”(to perceive directly without reasoning, to know by immediate perception)(1)本文依据的是Online Etymology Dictionary中的Intuition词条注释,参见:https:∥www.etymonline.com/search?q=intuition。。这说明“intuition”诞生之初就是某种与逻辑推理相对立的认识能力,所以安东尼·弗卢(Antony Flew)主编的《新哲学词典》[2]中把直觉定义为:Intuition----一种非推理的或直接的知识形式。该名词在哲学上可分为两种主要用法:第一,关于一个命题(proposition)的真的非推理知识;第二,关于一个非命题对象的直接知识。前者对应于西方理性哲学中的数学公理等,而后者则是指宗教、美学中如“善”“美”“绝对精神”“自由意志”“绵延”等形而上的本体概念。不论是命题对象还是非命题对象,“直觉”的对象都超越现实世界,而“直觉”便是对超越对象的直接领悟。古希腊的柏拉图将直觉视为一种对于“理念”的直接洞察和领悟能力,而亚里士多德则认为直觉是了解科学知识的原始前提,他们所开启的直觉认识论维度,影响了直觉在西方文化中的发展进路。无论是近代的笛卡尔、莱布尼兹,还是启蒙时代的康德、谢林等,都有这样一个共识:直觉是与逻辑推理相对立的、直接把握对象本质的思维形式,通过直觉所获得的知识是可靠的、不证自明的。现代的叔本华、尼采和伯格森实现了认识论和生命意识的沟通,他们认为直觉不仅能够为科学知识奠定认识论基础,也为理解一个完整的人提供认识的基础。伯格森之后,克罗齐的艺术直觉关注直觉中的美感体验,由直觉所引起的艺术创造将人带入情感的领域,通过艺术形象达到美与生命的同一。由此看来,西方文化中的直觉,大都指向外在,其目的在于通过直觉获得某种客观而确定性的知识。伯格森与克罗齐的直觉则将外在的探寻转向主体的生命与精神世界,但是其直觉的对象依然超越于人的现实感性而与某种绝对的实在相联系。
直觉思维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它涵盖了以下几种概念: 一是不经过逻辑推理与分析而达到形上境界,如老子的“涤除玄览(鉴)”[3]与庄子“心斋”[4]53“坐忘”[4]119而观“道”的直觉; 二是基于佛学思维的突如其来的瞬间感悟, 如妙悟、顿悟等; 再者便是通过亲身体验而自明自证, 基于理智并与理智并用的反身体认与反求自识,如程朱理学中“体悟”与“豁然贯通”的直觉。 中国的直觉思维将形象世界与超验意念世界连为一体, 注重反躬向内与反己体认, 体现为一种主体向内的生命感悟与审美体验, 这是和西方外向型直觉思维的最大不同。 所以,如果用“直觉”来翻译“intuition”, 就不可能达成内涵上的完全一致。“直”和“觉”在中国古代,一直是作为两个独立的单音节词被使用,如“直觉巫山暮, 兼催宋玉悲。”“建安黄初不足言, 笔端直觉无秦汉。”“风顺掠口岸,直觉市声沸。”等古诗词中, 以及《官场现形记》《好逑传》《容斋随笔》《梦中缘》中都使用过“直觉”一词, 但这些作品中的“直”与“觉”是两个词,“直”作“只是”或“直接”解,而“觉”则是“觉悟”或“感到”等意思。 “直觉”作为一个双音节词首次出现在张东荪翻译的伯格森的《创化论》中。 张东荪的“直觉”一词借鉴日译而来, 日译中的“直觉”最早出现于西周的《敬知啟蒙》(1874年), 后来被“直观”替代,一直沿用至今。 德国传教士罗存德编撰的《英华字典》(1866—1869年)中将“intuition”解释为“看见,或一见而知之、聪慧、聪明”,“直觉”的译文并未出现。 1908年的颜惠庆《英华大辞典》(第1244页)已将“intuition”翻译成“直觉”, 并将其和“天知、良知、觉知、直觉、直知、原知”等词语等同。 1911年的卫礼贤德《英华文科学字典》(第236页)和1913年的商务书馆《英华新字典》(第280页)翻译成“直觉力”, 很可能参考了1884年日本东京大学编撰的《哲学字汇》中“intuition”的译文“直觉力”[5]。 由此可见,“直觉”作为一个双音节词语确实是一个日本现代外来词汇。 根据许慎《说文解字》,“觉,寤也。 一曰发也”[6]176。 这里的“寤”和“发”都侧重于一种主观上的领悟和启发。“觉”在《佛教大词典》里是“菩提”(Bodhi)的汉译, 即知、觉察、醒悟,亦为“觉悟”的略称[7], 是对真谛的领悟, 依然侧重于人的主观意念;而“直”在《说文解字》解释为“正见也”, 徐锴注为“今十目所见是直也”[6]268, 是正视、直视之意, 即一种感官所及,“直”刚好弥补了“觉”在现实感性方面的不足。 因此, 用“直觉”一词来指代中国传统思维中以主体的现实感性为中心的内心感悟思维方式, 也不失为一种合理的翻译, 但是需要明确的是这一译名并未实现中西文化的等值。 因此,“intuition”以“直觉”译名在中国登陆, 必然会引起中西文化及其思维方式的连接、碰撞与融通。
“直觉”概念被引入中国,有其特定的历史与文化机缘。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辛亥共和,中国知识分子在寻求救亡图存的道路上经历了从技术层面到制度层面的尝试,当这些尝试一一失败之后,他们转向文化的批判。当旧的价值体系崩塌而新的文化权威没有着落之时,西方的科学(还有民主)作为新的价值依托应运而生。然而,正因为五四知识分子怀着摆脱现实困境的强烈诉求,使得科学的“底蕴一开始就超越了科学自身而改换为中国社会现代化努力的历史主题,并由知识分子对未来社会的期望参与了对它意义的重塑”[8]。科学因此超出了其本身的知识内容与价值而被赋予了更多社会与人生价值的概念意义。当时的科学主义者视科学“为云云众生所托命者”[9]和“万能必胜之利器”[10],甚至一种普遍和终极价值的委身,它能“造就新的,能主宰人生、自然的新人”[11]。这股狂热的科学主义浪潮最终触发了中国思想史上的科玄论战。张君劢于1923年2月14日以“人生观”为题的清华演讲对科学万能观发起了质疑与挑战,他认为人生观是直觉与综合的,并不受客观因果律支配,“故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绝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诸人类自身而已”[12]。以张君劢、梁启超、张东荪等为代表的人生观派从西方思想潮流变化中清醒地意识到科学理性的危机所导致的人之自由意志的丧失:“托庇科学宇下建立一种物质的、纯机械的人生观。把一切内部生活外部生活,都归到物质运动的‘必然法则’之下……于是人类的自由意志,不得不否认了,意志既不能自由,还有什么善恶的责任?”[13]在此种文化历史语境里,伯格森的生命哲学得到人生观派的垂青,伯格森的《创化论》于191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译本由张东荪参照Arthur Mitchel的英译本CreativeEvolution,并参考了金子马治与桂井当的日译本(《创造的进化》)翻译而成。
伯格森的哲学是针对西方启蒙机械论与目的论的批判。伯格森认为:“究竟观(2)此处张东荪的“究竟观”即目的论,法文finalité,英文finalism。之弊。正同于机器观。皆偏重于智慧(3)此处的“智慧”就是“理智”,法语、英文均为intelligence。耳……机器观视世界为一大机器。究竟观谓宇宙为一大计划。皆不过表示人心上互相辅翼之二趋向而已。究竟观尚有同于机器观者。则皆不承物心之本为不可预知之创化是也。”[14]43-44“物心之本为不可预知之创化”表明宇宙的本体不是固定的静体(物),而是创化,伯格森称这一过程为绵延(duration),它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伯格森是想从生命的角度来理解世界,他认为要把握“绵延”着的宇宙,必须用“直觉”取代理智。“直觉”一词,在伯格森的原著中是法文词l’ésprit ( 英译spirit),意为一种“内在的、固有的直观的能力”(cettefaculté de voir qui estimmanente à la facultéd’agir et qui jaillit),也即Arthur Mitchel的英译本中的“intuition”一词。伯格森的直觉不是空间与感觉的直觉,而是一种哲学的直觉,用伯格森自己的话来说:“哲学的直觉者,直接知识也(direct knowledge),同情也(sympathy),深入物体之内部也(one place oneself within an object)”[15]。哲学的直觉视一切物皆互相融透之整体,深入物之内部而知其变动。“所谓直觉无一定条例可言,就消极言之,则非分析也(analysis),非显微镜之辨柝毫厘也(hairsplitting),非论理上之对抗原则也(dialectic),就积极言之,则自察也(self-observation),内省也(instropection)。”[15]直觉并非站在物之对立面以既定条例与原则审查之,而是进入物之内部的体验与内省,这是直觉与理智分析的根本区别所在。但是伯格森并不完全否认逻辑之“思”的存在:“吾之所谓直觉为补足知识之手段,在知识之分别比较外,下一种深入物体内部之工夫,如是则于求真之道得之矣。”[15]伯格森以为理智法用于分析物质世界,而直觉法才能触及生命之真。由此可见,伯格森的直觉基于西方的精神土壤,并未彻底脱掉理智的基因,但是他强调“深入物体内部”的同情与内省却又与中国传统的主客共通的直觉思维有着高度契合。张东荪在《创化论》译本的序言中说到:“数千年来,东西洋之思想显然不能互相发明者,至19世纪为极。”“以伯氏之说,能补助中国哲学之乏论理性与印度哲学之太消极性。而且东西洋思想接触之介,渐为东西洋文明贯通之渠。”[14]5张东荪引进“直觉”,不仅只注意到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从而借伯格森的直觉论来弥补中国哲学之不足,显然也认识到了伯格森思想与中国文化的相通之处从而达到二者相互沟通之可能。
在张东荪引进“直觉”之前,严复已于1905年在其译著《穆勒名学》中将“intuition”翻译为“元知”,解释为“智慧之始本,一切知识,皆由此推”[16]。“元知”的译名很忠实地传达了西方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将“直觉”作为一切知识的原始前提的观点。而王国维认为日本人对于“intuition”的译文“直觉”并不非常精确,因此在其诗词美学中采用“直观”一词,王国维理解的“直观”基于叔本华意志哲学的“观”,即超越了道德律和充足理由原则的“一切真理之根本”[17],这是一种纯粹主观的超越现实世界的“观”。由此可见,严复的“元知”与王国维的“直观”都还是西方的“直觉”,与中国传统的直觉思维并无文化关联。“直觉”真正与中国传统直觉思维发生沟通与交融,是在张东荪翻译伯格森的《创化论》之后。当张东荪第一次引进“直觉”概念,并将之放在哲学认知论的维度上加以讨论,才触发了“直觉”与中国直觉思维的跨文化关联与改造,开启这一改造过程的是梁漱溟。梁漱溟基于伯格森的直觉思想,借用印度唯识论中的现量与比量概念定义直觉。他认为直觉是介于现量(感官经验)和比量(理智判断)之间的阶段,直觉的意义在于:将感觉变成一种意味、精神、趋势或者倾向。直觉得来的意味,“既不同于呆静之感觉,且亦异乎固定感知概念,实一种活形势也”[18]。梁漱溟认为孔子的思想是重直觉而反理智的,儒家的“仁”以及“良知”“良能”就是直觉.在梁漱溟看来,生活就是顺着本性、听任直觉,即儒家所说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不仅如此,梁漱溟的直觉还是一种情感表现,是人超越理智和思虑,对其所面对的周遭世界的随感而应、敏锐感通,是一种符合儒家伦理秩序之“天理”的情感。梁漱溟以直觉诠释“仁”,并发掘出了传统儒家思想中的生命意识与情感因素,与西方科学理性形成鲜明对照。他将伯格森的直觉思想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相互融合与阐发,使得直觉这一概念具有了中西文化交融的内涵,为直觉进一步演变为中国现代文艺美学中的生命意识与审美观念奠定了基础。
二、生命意识:唯情论对“生命直觉”的认识论阐释
如果说张东荪与梁漱溟等现代知识分子在“科玄论战”期间只是从社会改造以及道德重建的层面讨论直觉,那么唯情论者则从哲学认识论的维度深入发掘了传统直觉思维中蕴含的生命认知。他们从颠覆科学主义本体的基础出发,以“情”为本体来对抗心物二元的科学理性对于整体生命的割裂,认为“‘情’融合了心与物、人生与宇宙、主观与客观、精神与物质,理性只是‘情’的一部分”[19];而直觉是通向“情”本体的唯一路径。
“唯情”一词首度出现在朱谦之1922年发表的《唯情哲学之发端》一文中。1924年他的《一个唯情论者的人生观和宇宙观》由上海泰东图书出版发行,这部作品是“科玄论战”中关于情感问题讨论的进一步发展。朱谦之立“情”为世界的本体,“本体不是别的,就是人人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一点‘真情’,就是《周易》书中屡屡提起而从未经人注意的‘情’字。宇宙万物无一不为‘真情’所摄。故此大宇宙的真相,就是浑一的‘真情之流’”[20]。作为本体的“情”是每一个体先天而有、独立自在的创造冲动和生命活力。朱谦之的“真情之流”与伯格森的“宇宙之绵延”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即他们将世界视为一个统一的、动态而连续的整体,把握真情与绵延都是从生命的角度来理解世界。朱谦之从中国传统中挖掘情感思想资源:“大概《周易》千言万语,都只是‘情’字,更无其他。”[20]他认为“情”字贯穿于孔家思想,孔子 “主张孝弟为行仁根本”并非思索与安排,而是基于人心中情感的自然流露。礼乐的提倡,也不过是为了涵养性情而不是节制性情。朱谦之认为孟子的“性” 与“恻隐之心”,其实质都不过是情。所以他说唯情哲学是孔家的本来面目。但是自孟子之后,孔家的这一条真情之流在理智与道统的笼罩下断流。朱谦之希望借着他的唯情哲学,“把从孔孟以来被诸儒打断的形而上学系统,再接续起来,组织起来,而且应用到政治、伦理、教育、艺术各方面,用真情的默识方法,使宇宙生命化,物质精神化,这么一来,‘真情之流’才可完全实现了!”[20]“情”不同于静止的理,它永远在变化中,如滔滔不绝的流水一般没有间断。这活泼泼的真情之流便取代了静止的天命,它“只是个自时而然,就其自然而然所起的绵延之感,人们便发见自由了。自由没有别的,只是不绝的生命,无间的动作,不尽的绵延”[21]119。朱谦之“情”的绵延颠覆了凝固不变的“理”的秩序,也解放了“理”的秩序规定下的自由人性。
朱谦之用“情”之本体将人从科学主义所倚重的了无生气的物质世界拉回到生机勃勃的精神领域,如此一来,他就更加理直气壮地驳斥科学主义所玩弄的抽象、机械的理智思辨对人的冰冷分析,取而代之以情感为基础的“直觉”法去体悟活泼的生命。
首先,朱谦之认为直觉法与理智分析法最大的不同在于它克服了主客的对立。理智的分析法是主体站在客体外部对之作静态的剖析,而“直觉方法的好处,是能够撤毁物我之间的障壁,而由一种同情捕捉生命的内部”[22]。同时,“‘直觉’是能够脱却皮相的方法,而直接证会之;这种证会,是要置身内里去观察它”[23]335。朱谦之的直觉强调“同情”与“内里的观察”,这实际上是伯格森直觉的中国翻版。伯格森曾经将直觉称为一种直接的领悟与“共感”(sympathy)[24],弱化了西方直觉中“看”的意义,强调的是直觉融入绵延中的情感与生命体验,这与朱谦之作为“同情”的直觉在克服理智的二元对立上具有同质性。那么,主体如何能够深入到对象的生命内部?朱谦之阐发了《周易》的意象思想,“一切形象,凡我们看得见想得到的,都是‘意象’罢了”[21]142。朱谦之说:“依易理看起来,物质只有可能性,如常人自以为有质碍的空间性的物质,其实在意想中还明明是一个意象,可见物质不过意象,举目而存只有意象而已,变化而已。世间原没有物质这个东西。”[21]143将对象通过直觉转化为意象,是主体进入对象生命内部的第一步,在这一点上,朱谦之又再一次接近了伯格森。伯格森直觉的第一步,便是将物质的世界进行现象学的“悬置”存而不论,主体敞开感官所感知的只是“物象(image)”[25]。无论是朱谦之的“意象”还是伯格森的“物象”,它们都能够将主体置身于对象之中,使之成为对象的一部分,而对象通过主体的情感维系与贯通成一个具有永恒创造之力的整体。在朱谦之看来,既然一切物质都是意象,那么意象就无不在“我”的意识之内,情本体就在万千意象之中.而意象无时无刻不在流转,前后相续,真情也就在这万千意象之中流动,我们无须绞尽脑汁寻求这意象背后的本体,只需顺其自然“默而识之”,感应意象的流转变化,便能够触及到意象之中的“情”之绵延了。
其次,朱谦之的直觉是一种动态的、变动的以及肯定生命个性的认识方法。科学主义的理智分析法是外设一套恒定不变的理论框架,将变动的万物纳入预设的框架中,通过各种语言的概念企图用静止的法则来框定变化多端的实在,实际上是对于事物多样性与变化性的模糊与否定。而直觉则是能够“打破那种种界限的名字障,在大的方面,看得到宇宙总体的精神,就把虚伪的差别看轻了;在小的方面,看得到具体而微的真际,就把个性的自我看重了”[23]335。朱谦之的直觉打破了名与象的对立,超越了一切言词之名所代表的虚幻象征意义,因而也解放了概念之名对生命个性的约束,促成主体自我特性的张扬与生命(情)的自由进化。此外,“直觉法不止似辩证法,只教我们以流动、综合、进化、灭而复生,断而再续的绵延,还要引渡我们去契合那意识界绵延的本真,须知这种体验上的直觉,实使我们看到浑一不可分的时间,就是那滔滔不绝之内质的变化的绵延(duration),这自然是动和变的方法,更无疑义了”[23]335。静态的分析与理智的名言不能解析千变万化的实在,而直觉则契会流动与变化的绵延。直觉在否定亘古不变的绝对与神圣实在的同时,也是对生命个性的肯定。
更重要者,朱谦之的直觉是一种近乎本能的冲动,“根于情感的直觉,为有生俱来不学而能的东西”[23]344。但这种本能当然有别于动物的本能,它基于一种道家泛神论的信仰,即对大自然的崇拜与爱恋。作为一个泛神论者,朱谦之的信仰为直觉提供了着落之处,即如果人保持对于自然的爱恋,便能安于一种情感生活,随时体悟到身边之物中充盈流动的真情。泛神论的信仰保证了直觉“随处体认,当下即是”的特征。他在《周易哲学》中将直觉视为一种“神的智慧”:“形而上学的方法,一定要求一种神秘的直觉(mystic intuition),以神的智慧作自己的智慧,大开真情之眼,以与绝对无比不可言状的‘神’融合为一。”[21]107因为“‘神’是不靠观念和符号直接默识的,那种明了透彻的程度,用言语是说不出来的”[21]107。这种神秘直觉完全不含有理智的思,因此与伯格森的直觉区别开来。前文已经谈及,伯格森的直觉并不完全否定思的意义,与朱谦之的直觉“不学而能”不同的是,伯格森虽然认为直觉始于本能,但是也离不开后天的修养。按冯友兰的说法,伯格森的直觉是一种“智识的同情(intellectunl sympathy)”[26]。他并不主张要用直觉来代智识,也没说本能比智识好,他仅只说明我们要离开物质界而研究精神界要诉于一种生命之体验;而朱谦之在他的《历史哲学中》中并不赞成伯格森将人与智慧(理智)联系在一起。他说:“我们所有的直觉,所有不受智慧限制而了解生命的力,这才是一个心理进化的最后产物。但这种进化,却是从本能发展得来,是他种动物所没有的。”[27]直觉作为历史的基础与本能的元素,它超越了理智,落脚于情感,不需要后天的学习而与生俱来。朱谦之的直觉强调“意象” 与情的连接,饱含着情感的意象又并非科学认知所能触及,因此只能以审美感悟的方式直达。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朱谦之的直觉是一种艺术审美的生命意识。他于理智的忽视与贬抑虽不完全可取,但是在一个科学主义日益膨胀且被神话的年代,确有其现实价值和意义。他在反对科学主义的绝对化的同时,实际上也有将直觉绝对化、神秘化的倾向,这对于五四时期面临价值危机、探索启蒙之路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也在所难免。
唯情论直觉是中国传统儒家与道家情感哲学的现代重生,“儒家哲学从一开始就偏重于情感,它的知识学、认识论和意志问题都是与情感联系在一起的”[28],而道家哲学更是注重情感在体“道”中的重要意义。朱谦之将伯格森的“直觉”与中国传统哲学及文艺美学思想中的直觉思维对比关联,从唯情论哲学体系的视角赋予了“直觉”概念以学理的地位,即从一个与理智对抗的工具性概念演变成“情”本体的认识方式,成为一种带有审美经验性质的生命认知语词。唯情论的直觉是一种灵动与变化的内心体验,它与生命的创化互为前提,相辅相成,不仅是对至情真理与至善人性的探索,也是对于美之生命意象的追寻。因此,唯情论对直觉的学理阐释,为克罗齐的艺术“直觉”进入中国奠定了基础。正是克罗齐的“直觉表现论”在中国的吸收与接受,使得“直觉”概念逐渐从生命意识演变为审美观念,成为现代中国文艺美学话语中的固定与常用语词。
三、审美观念:直觉表现论对“艺术直觉”的美学阐发
“审美对象的表现性是自然属性与审美主体的主观心理相结合、相作用的结果,这个主、客体相结合相作用的过程就是艺术直觉的过程。”[29]作为生命意识的直觉也强调这种主客体之间的相互结合与作用,因此,生命直觉与艺术直觉本来就有内在的逻辑关联。直觉概念在西方发展到克罗齐,已经从对生命本体的感知过渡到对艺术本质的认识。克罗齐“直觉表现论”的引进,促进了“直觉”概念在中国的进一步转化,即从唯情论的生命认识论语词转变为作为艺术直觉的审美观念话语概念。朱光潜对克罗齐“直觉表现论”的改造与阐释,是在现代文艺美学的体系中赋予了“直觉”以具体的美学与文学批评的含义,让这一概念最终在文艺美学与文学批评的话语中得以固定。
最先向国人介绍克罗齐艺术直觉观的是朱光潜。1927年他的《欧洲三大批评学者----克罗齐》一文是国内克罗齐艺术直觉表现论的首次引介,后来的《诗论》与《文艺心理学》等著作又对之进行了更深入的跨文化阐释。在克罗齐的心灵哲学中,直觉是心灵活动的起点,即人类的整个思维进程起源于诗性的表达,亦即情感的抒发。与伯格森超越理性的直觉不同的是,克罗齐的直觉并没有越过理性成为把握世界本质的方法,他将直觉锁定在艺术的王国里,他的直觉无所不能,即直觉=表现=艺术=美。作为认知起点的直觉带有人类原始诗性的意味,它既不是感觉,也有别于推理,是基于人的被动感受力的心灵综合,是创造,是表现,是对艺术本质的探寻,甚至就是美本身。直觉是生命活动的开端,而生命的活动是从直觉到理性认知,再到行动的循环不止的运动过程。克罗齐并不否认直觉中含有概念的成分,但是蕴含在直觉中的概念已经不再是概念而是直觉的一部分。由此可见,克罗齐之所以将直觉等同于艺术,是为了让艺术(或者美)彻底摆脱理性(包括知性)的枷锁而获得独立。
那么,克罗齐的直觉到底是什么呢?他说:“在直觉中,我们不把自己认成经验的主体,拿来和外面的实在界相对立,我们只把我们的印象化为对象(外射我们的印象),无论那印象是否是关于实在。”[30]4克罗齐从精神一元论的认识论视角明确了直觉的对象是一种心灵材料,肯定了直觉就是一种纯粹的心灵综合活动,它与外在物质世界相区隔。在此基础之上,克罗齐将直觉与人的被动感受、逻辑知觉、联想活动通通划清了界限。直觉即表现,即艺术,它是人类理性思维的前提却又独立于理性、道德以及物质实践。克罗齐指出:“直觉在一个艺术作品中所见出的不是时间和空间,而是性格与个别的相貌。”[30]5克罗齐肯定直觉是一种个人的独特活动,它只是体现个别的特征和面相,因而是确定而具体的。正因为直觉的主动创造性,它也与记忆及拼接事物的联想大不相同,它是主动的,富于分辨与建构的主观能动性。正因为如此,抒情成为直觉的一个显要特征,或者说,直觉与抒情是同一的。克罗齐说:“抒情原则是意象综合的内在依据,其作用就是连贯完整地把握情感。抒情原则给与直觉以连贯性和完整性:直觉之所以是连贯的和完整的,就因为它表现了情感,而且直觉只能来自情感,基于情感。”[31]克罗齐的“直觉表现论”在西方美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为西方美学揭开了一个久被幽闭的心灵世界,也使得被启蒙理性遮蔽已久的情感通过艺术的表达得以复苏。
在中国传统学术和西方知识熏陶下的朱光潜,将克罗齐的“直觉表现论”与中国传统美学理念相融合,构建了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美学直觉论。朱光潜将直觉等同于一种纯粹的美感经验,认为美感的经验就是直觉的经验,“在美感经验中,心所以接物者只是直觉而不是知觉和概念。物所以呈现于心者是它的形象本身,而不是与它有关系的事项,如实质、成因、效用、价值等”[32]119。和克罗齐一样,朱光潜认为艺术直觉只是心灵的活动,并将直觉与知觉和概念,实际效用等完全区分开来。但是,朱光潜又认为“形象是直觉的对象,属于物,直觉是心知物的活动,属于我”[32]118-119。由此可知,朱光潜直觉的对象与“我”分属两个不同的世界,只不过通过“物”呈现于“心”之后的心知物之活动,二者交融在一起,而克罗齐的直觉从一开始就与外在世界脱离了干系,从直觉的材料(心灵感受外在之印象)到直觉活动(心灵综合)再到直觉的结果(意象的生成)都在且仅在主体的心灵中完成。因此克罗齐直觉的最大意义在于它克服了感受的被动性而具有了创造性。朱光潜基于现代心理学的直觉形象是物呈现于心的一种美感意象,它虽然和主体心灵获得了交流,但并未克服被动性,这是朱光潜的直觉与克罗齐直觉最大的不同(4)朱光潜在1948年的《克罗齐哲学述评》中纠正了自己对克罗齐直觉的误解,对此本文暂不讨论。。朱光潜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阐释克罗齐的直觉的,而“克罗齐的直觉论超出了现代经验派认识论的心理学,已把直觉视为一种创造一切的本原的心灵力量”[33]。
朱光潜的直觉与克罗齐的直觉所奠基的哲学基础显然有所不同。朱光潜是从心物二元论来阐释直觉的,在他看来,“美感经验的特征就在物我两忘,我们只有在注意不专一的时候,才能很鲜明地察觉我和物是两件事。如果心中只有一个意象,我们便不觉得我是我,物是物,把整个的心灵寄托在那个孤立绝缘的意象上,于是我和物便打成一气了”[32]123。他认为艺术直觉的产生,是观赏者和对象之间的一种情感交流,即“我”排除掉一切主观欲望与意念,对于“物”作纯粹的直观时产生的一种特殊情感,而“我”又会将这种情感移至对象,同时又将对象的姿态吸收于我,于是“我”的生命便和物的生命在这种情感的往复交流中合二为一了。作为一位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与浸润的现代知识分子,朱光潜始终不可能彻底摆脱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他接受西学也不过是在其传统知识框架之中对之进行中国化的阐释,因而也就无法真正深刻理解克罗齐基于精神一元论的直觉是与物无涉的纯粹心灵活动。朱光潜直觉的“心与物的融合”实际上是中国古典美学中“情景交融”和“天人合一”哲学认知的现代演绎。在中国传统哲学中,人从来都是自然的一部分,中国人自古强调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的沟通、默契和感应,这种思维在艺术中便体现为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的情感沟通,而促成这种情感沟通的直觉依然关联着主观世界与现实世界两端,并非克罗齐的纯粹一元精神世界。因此朱光潜的直觉并非克罗齐的纯粹表现论,而是多少带有中国传统艺术反映论的身影。
朱光潜对克罗齐直觉的阐发,还体现在对于艺术传达的不同理解中。克罗齐的艺术即直觉论中,没有艺术传达的位置。因此他的直觉表现乃是一种精神的图像,仅存在于艺术家的心灵世界,而传达已经涉及到社会物质元素,一旦和物质界相涉,就不再是艺术。克罗齐严格区分了艺术和艺术品的精神与物质之别,但是朱光潜对这一点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认为艺术家在直觉心理活动时,就已经在脑海中酝酿艺术符号(语言、线条、色彩等)的传达了,艺术的想象中本来就内涵了传达,但是这种传达需要付诸现实才能算是艺术的生成,即艺术品的生成才是艺术的完成,也即从胸中之竹到手中之竹的完成过程。这一点与克罗齐作为纯精神活动的直觉是相悖的。克罗齐的直觉并不否认语言、声音和颜色等元素,他们都是直觉的组成部分,但是这些元素并不一定非得要呈现于现实世界,他们存在于直觉的精神意象里就已满足艺术成为艺术的要求。但是朱光潜把克罗齐精神意象里的语言、色彩和线条等元素当成了艺术传达的媒介,以为艺术和媒介不可分离。朱光潜对克罗齐直觉的误读源自中西方对于语言(这里指广义的语言,包括声音、色彩和线条等艺术符号)的理解差异。朱光潜思维中的语言仅仅是表达情意的媒介手段和载体,而克罗齐的语言则是一种精神的本体逻各斯(Logos),这种先验的逻各斯本体决定了经验的语言表达。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克罗齐并不轻视艺术语言,而是强化了艺术语言的精神特质,即艺术的语言便是艺术的意义,此外不再需要别的媒介。这一点也正好体现了中国传统思维与经验世界密不可分的特征。克罗齐基于精神一元论的纯精神想象的直觉在中国是没有生存的文化精神土壤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切抽象思辨与精神想象都离不开经验世界,这也正是朱光潜无法接受克罗齐艺术排斥传达的根本原因所在。
可以这么说,正是朱光潜的跨文化转化,克罗齐的艺术直觉克服了其精神的狭隘与局限,实现了心灵感悟与现实世界的衔接。朱光潜立足于现代文艺美学的体系赋予了“直觉”以明确而清晰的理论意义,使得“直觉”从此作为中国现代文艺美学与文学批评中的固定话语而被广泛接受与使用。在朱光潜美学“直觉”的基础上,美学家邓以蛰、宗白华,以及文学批评家林语堂、梁宗岱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对“直觉”进行过更加深入的跨文化探讨,“直觉”因此逐渐演变为中国文艺美学中的显性话语概念。
四、结 语
“直觉”进入中国之后,在朱谦之和朱光潜等现代知识分子的跨文化阐释中,融合中西方直觉思维的特征,获得了新的意义。唯情论的“直觉”是对生命情感的当下体悟,是主体深入到对象内在而与之共舞的创造进化的生命意识。作为生命意识的直觉,和逻辑分析所不同的是,它不将认识对象孤立起来对待,而是将主体融入到对象之中体验其变动。而艺术直觉所强调的表现性是对象在与人的审美联系中表现出来的一种与人的观念、情趣相通的内涵。因此,作为生命意识的直觉就与艺术直觉有着内在性质的关联,艺术直觉是在生命直觉基础上的深化与具体化。“直觉”概念在中国从生命意识到审美观念的流变,始终沿着一条“情”的主线发展,它带动了中国传统哲学与文艺美学话语概念的现代转型,使得过去意义边界模糊不清的能指开始有了较为明确而清晰的所指,最终演变成现代文艺美学与文学批评中具有确定意义的话语概念。在现代中国,无论是生命直觉还是艺术直觉,无疑开辟了一条理性之外的情感启蒙之路。虽然中国对于情感直觉的讨论比西方整整晚了一个多世纪,但是两种文化在探求现代化的路径上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与五四科学理性悖反的情感直觉,正好和欧洲启蒙理性对抗的情感直觉形成了跨文化对应。而直觉从欧洲经日本旅行到中国,中国的知识分子并不是纯粹的拿来主义者,他们在对于西方直觉理解的基础上,有效地实现了两种文化的衔接与融合。与西方哲学家和美学家对于精神与理论探索不同的是,中国的唯情论哲学家和美学家们始终立足于现实,着眼于人生,坚持理论与文化发展的深度结合,认知的眼光和审美的眼光最终是为了创造生活与改造人生。在科技人工智能高度发达的今天,直觉所引发的对于生命情感的思考,依然是我们高度关注的话题。1923年张君劢在清华大学有关“人生观”的演讲中提出,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的问题,这既是中西文化的问题,也是20世纪人类文化与哲学的问题。在21世纪的今天依然是一个显性的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与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