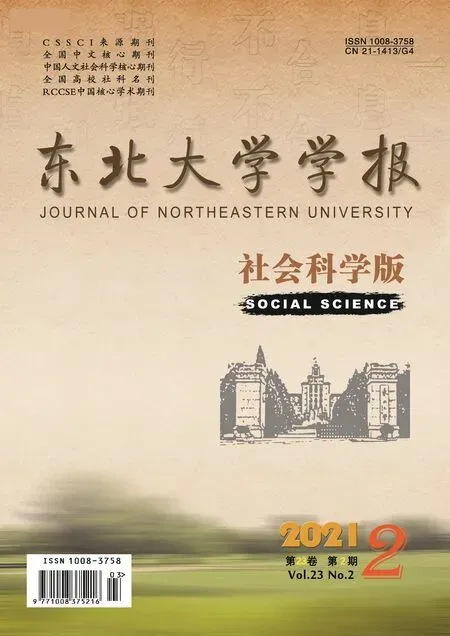当代技术伦理实现的范式转型
贾璐萌, 陈 凡
(1. 天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天津 300350;2. 东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辽宁 沈阳 110169)
世纪之交,技术伦理学界出现了一股研究范式的转向潮流,具体表现为伦理关注的对象从技术工作者和技术后果转向技术活动的内部机制和动力,伦理反思的时机从技术应用阶段拓展到技术研发阶段,伦理研究的方式从批判性反思转向经验性描述。国外学者将这种研究范式的变化概括为从“外在进路”(externalist approach)向“内在进路”(internalist approach)的转向,即技术伦理研究不再执着于站在外在于技术活动的立场上进行批判与说教,而是积极致力于深入技术发展的过程当中考察技术语境中的伦理问题[1]。这一转向进一步投射到践行技术伦理的实践活动中,影响到技术伦理实现的范式选择,从而引发了技术伦理实现范式的当代转型。
一、 技术伦理实现的内在意蕴
要了解技术伦理实现范式的当代转型,需要在对技术伦理的基本范畴有所把握的基础上,确定技术伦理实现的内涵,以此锚定其范式转型的大致图景。
就伦理一词的本意而言,其首先体现为一种关系,即人与相关现实之间的应然性关系。在充满着“人学”特性的中国传统哲学语境中,伦理主要表现为一种人伦秩序----人们依照这种人伦秩序彼此相倚相待、和谐共处;而在西方哲学的语境中,伦理起源于公共生活的需要,它可以帮助个体确定他者行动的意义及其与自身的关联,进而作为个体间的稳定关系为群体行为奠定可能性基础。技术伦理的出现同样源自人们对自身与技术这一现实事物之间的应然性关系的探索。它是在现代技术活动急剧扩张以及技术对人类生活全面渗透的背景下,对人与技术之间的应然性关系进行的哲学反思。例如,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异化”学说就是据此提出的。“异化”之说之所以成立,正是由于人与技术之间的实际关系背离了人们对两者之间的应然关系的一贯认知----技术的发展由工具上升为目的,而人类自身的存在则由目的沦为工具,此之谓“异化”。
技术伦理对于人与技术间应然关系的关注,不仅源于伦理的“关系性”本质,也是由其研究对象----技术----的特殊性导致的。随着现象学技术哲学以及STS领域在“无基础”(nonfoundational)的关系论进路中对技术的不断追问,技术调解(technological mediation)现象逐渐显露,并在社会学、心理学等多个领域引起了普遍关注[2]。根据维贝克(Peter-Paul Verbeek)的技术调解理论,技术不仅在个体对外部世界的感知中发挥着非中立性的调解作用,也参与共塑着个体的行为选择与行为方式。在最原初的意义上,这一现象意味着在人与世界的相互关系中,技术不仅作为“对象”而存在,也构成了人们认识和作用于现实世界的“中介”,因而也被国内的一些学者称为“技术中介”现象[3]。在这一现象中,传统伦理所关注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都由于技术的介入发生了变化:工业技术发展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颠覆与紧张,媒介技术的网络化扩张引起个体间关系的变化,人工智能及生物医学技术的进步使得人与技术物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等等。这些由于技术介入而引发的变革无可避免地成为技术伦理反思的主题。
在关系性维度之外,伦理还表现为伦理主体的道德特性,如“德性”“品格”“品质”等,这些德性或品格是伦理主体的身份得以确立的依据。这一维度构成了技术伦理的另一重内涵:对技术伦理主体的道德特性的探讨,并延伸到对技术伦理主体的范畴界定上。因此,技术伦理在其最初发展阶段表现为关于技术工作者----以工程师为主体----的职业伦理学。与此同时,也有学者认为,技术伦理所牵涉的“是对与技术打交道,以及对技术的后果和掌控的一种伦理反思。这种反思一方面是在具体的行为范畴之中,另一方面亦是在当前和未来人类发展过程中,以及在自然和技术、人和技术的关系改变过程中,对于技术所扮演的角色的总体思考”[4]。随着近些年来学界研究对人与物之间二元关系的超越,如拉图尔(Bruno Latour)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哈拉维(Donna Haraway)的赛博格理论、皮克林(Andrew Pickering)的冲撞理论等,更使得对技术物能否被纳入道德能动体的探讨成为技术伦理领域的热点问题。
根据以上分析,技术伦理的基本范畴既包含对人与技术间伦理关系的思考,又涉及到对技术伦理主体的界定及其道德特性的思考。这也决定了技术伦理实现的双重内涵:既体现为人与技术间的应然性关系在实践中的落实,又意味着关系双方所应扮演的角色在行动中的彰显。
二、 技术伦理实现的目的转向
在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实现”以目的及潜能的存在为前提。因此,技术伦理实现的目的转向构成了技术伦理实现范式转型的逻辑起点。
在技术伦理实现的传统范式当中,人与技术之间的应然性伦理关系主要表现为主体与客体、目的与手段的二元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无论人们是否认可技术的积极伦理价值,传统技术伦理实现的实质目的都是要捍卫人与技术之间的界线,确保技术的工具性地位始终如一,以捍卫和彰显人的主体性。例如,基于“技术异化论”的传统伦理关怀,通常致力于恢复人与技术之间的控制与被控制关系,换句话说,也就是恢复技术的工具性角色,防止工具性的技术对人的主体地位造成威胁。即使是在乐观的技术乌托邦主义者眼中,技术对于道德进步的推动也建立在其工具性的角色之上:技术对于人类需要的满足构成了技术可靠性的表现,并在伦理实现中成为人们更准确高效地达成道德目标的手段,这种对技术伦理价值的认知也因此被称为“道德工具主义”(moral instrumentalism)[5]。
然而,伴随着现代技术对人的高度趋近与介入,以及学界对二元论框架的超越,当前技术伦理实现逐渐发生了目的转向,即不再执着于捍卫人与技术之间的界线,转而追求一种人与技术的本真性共在关系。“共在”,即“与他人共在”,是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现象学中的重要概念,描述了一种把自我和他人同时显现出来的存在方式,是此在的本质规定性。在现象学技术哲学的语境下,共在关系中的“他者”主要是指与人类互动的技术,人的存在由此呈现为一种“与技术共在”的状态。在海德格尔的分析中,“共在”存在着非本真与本真两种状态。在非本真的共在状态中,自我或对他人淡漠疏离、陌如路人,或越俎代庖、代替他人“操持”,或消失于他人之中而沉沦为“常人”----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出现了混淆与失衡,由此也妨碍了自我与他人对各自此在的把握[6];“仅当共在双方都能够自由地把握自己的此在时,才谈得上本真的共在”[7]。因此,本真的共在状态意味着“自我保持了与他人的距离,达到了自我和他人之间的平衡关系;同时又能以我为主,回应他人”[8]。由此推论,人与技术的本真性共在状态也体现为一种人与技术之间的恰当距离与平衡关系。
这一伦理目的的显现是基于近年来学界对人与技术间相互关系的认定与再解读。一方面,在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中,学者们分别从后现象学技术哲学、STS等不同的进路出发,共同勾勒出人与技术相互交缠(intertwined)的状态。在由伊德(Don Ihde)开启、维贝克等人推进的后现象学技术哲学进路中,技术物不仅仅是处于既有实体(pre-given entities)之间的中介者(intermediary),其所蕴含的技术意向关系更是实体得以构建的来源和场所。由此,人的“在世之在”变成了“与技术共在的在世之在”,“技术人工物与人共同在生活场景中的相互作用构成了现实生动、有序、有效的生活世界”[9],自我、世界、技术同时在这种共在关系中显现出来。此外,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从STS视角揭示了人与技术间的互动关系:正是由于技术的折叠(fold),人类才得以跨越时间和空间而不必被拘束在最邻近的互动中,人和技术共同构成技术社会中的行动者。换言之,人与技术以“混合行动体”(hybrid agent)的形态共存于其行动所构建的网络之中[10]。这种动态的、相互交缠的状态构成了人与技术间本真性共在关系的第一重含义,即接纳人与技术的交互状态作为显现自身的方式。
另一方面,在后转向时代,对于人与技术间交互状态的解读不再局限于探讨人与技术之间的“共同”(co-)维度,更是关注起两者之间的“非共同”(non-co)维度[11]。在后现象学技术哲学对具体技术物的经验性考察中,人与技术之间的互动存在着极大的丰富性和创造空间。技术调解中的“多元稳定性”(multi-stability)现象----技术物在不同的使用情境中会呈现出多样化的意向性----说明人们总是能在对技术物的使用(appropriation)中找到与技术共存的个体化模式,以彰显出个体存在的独特性和能动性。这意味着人们对于自我及人的主体性的强调没有必要通过拒斥技术的方式进行,重要的是在于技术的互动中保持自我。在这层意义上,“非共同维度”构成了人与技术间本真性共在状态的第二重含义,即从拒斥技术转变为积极地、创造性地塑造与技术的互动方式,以彰显个体存在的独特性与建构自我的能动性。
三、 技术伦理实现的主体转化
伴随着技术伦理实现的目的转向,伦理关系双方的形象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反映在技术伦理实现中,具体表现为伦理主体由具有绝对自主性的“人”让位于人与技术交缠而成的“人—技混合体”。
传统技术伦理是一种建立在人本主义基础上的规范伦理学。这意味着在技术伦理实现的传统范式中,人类作为唯一的伦理主体,不仅被认为应当承担起与技术相关的全部伦理责任,而且也相信通过自身道德能动性的发挥就能够有效地避免技术发展的消极后果。因此,技术伦理通常被理解为技术工作者的职业伦理。当然,也有一些学者意识到了个体在面对现代技术风险时的局限性,认为技术伦理需要机制化:“技术伦理若想在现代技术活动中取得良好效果,就必须得到制度的支持。如果没有制度的支持,我们在实践当中就没有办法具体运用应用伦理的相关原则”[12]。总之,无论是面向工程师群体的伦理守则,还是围绕工程技术活动的制度安排,在技术伦理实现的传统范式当中,伦理目的的实现被完全寄托于人类的能动性发挥上,并限定在了人类道德活动的领域。
然而,随着学界对人与技术共在关系的认识逐步加深,人们开始意识到,规范伦理学所依赖的纯粹独立的“人”实际上并不存在:技术不仅参与构成了人们对于世界的认知方式与经验内容,甚至能影响人们对某种特定行动路径或行为方式的选择[13]。这使得一系列道德范畴也随之发生变化:道德决策和道德行为不再是由个体完全基于其自由意志作出的理性选择,而是在人和技术物的共同参与及互动中完成的;同样,建立在自由意志基础上的道德责任划分方式也不再适用于当下技术伦理实践的现实状况。对此,学界逐渐抛弃技术工具主义的观点,开始重新反思现代技术伦理主体的界定标准,以期能正确认识人与技术物在伦理实现活动中的角色。
目前,技术伦理主体的界定已经逐步从实体论进路转向关系论进路。在实体论进路中,行动者的伦理角色依赖于实体的某种先天属性。例如,在康德伦理学中,人类之所以能够成为伦理主体,是由于人先天具备的实践理性与善良意志。在关系论进路中,行动者的伦理角色“既不存在于客体之中,也不存在于主体之中,而是存在于两者的关系之中”[14]。沿着这一进路,人与技术物的关系以及两者在具体关系中呈现出的表观特征构成我们判断其伦理角色的关键。具体来讲,在人与技术的互动关系中,伦理角色的表观特征包括两点:自主程度与伦理意向性。在技术伦理实现的传统范式中,自主性通常表现为不受任何干扰的绝对自由,伦理意向性也是独属于人类的伦理特质。然而在人与技术的共在关系中,人与技术永远无法摆脱彼此的影响,自主性和伦理意向性只能在人与技术共同参与的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实践过程中进行具体考量,并作为人—技混合体的共有属性而存在。
根据自主程度和伦理意向性两项表征,当前技术伦理实现中的混合性伦理主体可以分为以下三种类型的行动者。
第一,操作型道德行动者。这类行动者主要指“那些自主性较低、无法进行自主道德认知和判断,而只能遵循明确的道德原则进行活动的道德行动者”[15],主要面向的是日常生活中的平凡技术物。在《何处去寻暗物质:一些平凡人工物的社会学》一文中,这类技术物被拉图尔称作是社会道德领域长期缺失的“暗物质”(missing masses)[16]。根据拉图尔的设想,设计者可以通过“授权”(delegation)将伦理规范写入技术物的“脚本”(script)中,获得授权的技术物则可以凭借其脚本作用的发挥去“规定”(description)使用者的行为,实现技术物作为操作型道德行动者的角色。
第二,功能型道德行动者。这类行动者主要面向人工智能体,“其核心特征在于自主程度的提高,具体表现为面对道德困境时,能够进行相对独立的道德认知和判断,进而主动采取有效反应”[15]。在人工智能技术领域,“道德决策和其他任何一种行动选择都是类似的”[17],是可以被论证并通过编程在算法模型中实现的。
第三,伦理型道德行动者。在弱人工智能阶段,伦理型道德行动者主要是指具有成熟认知与思维能力的人,这是由于他们能够在伦理实践中发挥更高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对于伦理型道德行动者来说,伦理是对自身存在方式的主导与塑造,而成为伦理主体意味着在与规训性权力的互动中发挥自我建构的能力,自主发展自身的倾向、需求、爱好等,其朝向的是个体存在方式的多样性与丰富性。同时,伦理型道德行动者的伦理意向性体现在对道德责任尤其是约纳斯式的非对称性责任的主动识别与承担。
四、 技术伦理实现的机制转变
技术伦理的实现机制是指在实现技术伦理目的的过程中,各方行动者及各种因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及其协调方式。鉴于技术伦理实现的目的及伦理主体的变化,技术伦理的实现机制也从外在的伦理规范转变为技术与伦理的互嵌伴随。
在技术伦理实现的传统范式中,无论是捍卫人与技术之间的界限,还是将人类认定为唯一伦理主体,其中都隐含着一种传统的伦理关怀:对人的主体性的彰显。围绕这一目标,传统范式中的实现机制将维护人的主体地位所需的条件具化为规范技术发展的准则。这些准则一方面构成了工程技术人员的职业伦理规范,另一方面被作为技术伦理评估的标准来判定新兴技术的“道德可接受性”(moral acceptability)[18],这种评估的实质是对技术是否越界的判定。然而,这种基于人的先天主体地位转化而来的技术伦理准则,通常是外在于且先在于技术物与技术实践的,从而表现出不因人与技术间的互动发展而改变的固定性与强制性。因此,传统技术伦理惯于略过对技术系统内部机制与发展动力的探讨,倾向于从技术系统的外部生成对技术发展的伦理控制力。这意味着其实现机制只能前置性地依赖工程师群体的道德自觉和伦理决策能力,或后置性地、“被动地等待技术出现问题后再去亡羊补牢”[19],因而必然遭遇技术伦理的实践有效性困境。
为了突破这一困境,学者们开始走出书斋,与其他行业群体开展跨学科合作,将技术伦理拓展到与工程相关、政策相关的领域当中。于是,在当前的技术伦理实践中,陆续出现了“技术伴随伦理”(ethics of technology accompaniment)、“建构性技术哲学”(constructive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负责任创新”(responsible innovation)和“价值敏感性设计”(value sensitive design)等理论框架和实践进路。在这些探索中,一种技术与伦理互嵌的技术伦理实现机制正逐步成型。这一实现机制既不过分强调技术对伦理道德的消极影响,也不执着于伦理对技术发展的外在规范作用,而是在着重考察人与技术互动的基础上,探讨技术的价值负荷以及伦理因素嵌入技术发展过程的可行性。具体而言,这种技术伦理实现机制可以拆解为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技术对伦理实践的调解机制,即技术调解在伦理实践中的发挥机制,也可以看作是作为人工道德行动者的技术对伦理实践的参与。如前文所述,在技术调解现象中,技术协助塑造了人们认识、解释和改造世界的实践;而在伦理实践当中,技术则可以凭借其对个体认知和行为的调解作用,参与到个体进行道德判断、作出道德决策并最终作出道德行为的全过程当中。
对于个体的道德判断而言,技术不仅可以通过信息呈现来构成人们进行道德判断的认知基础,而且还能通过知觉调解来引导人们的道德判断与决策;在个体进行道德决策的过程中,技术则可以通过影响个体道德决策过程中的理性、情感、情绪等因素,以及调整各因素发挥作用的比重,实现对个体的道德决策的调解性影响;而作为个体道德实践的最后步骤,道德行为的作出通常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干扰和阻碍。中国传统伦理学中的“知而不行”困境,以及西方伦理学中的“道德软弱”(moral weakness)现象,都是指这样一种情形:个体在作出“应该做”(ought to do)的道德判断,且具备了“如何做”(how to do)的相关知识之后,却依然由于内外因素的干扰而最终未能采取相应的道德行动[20]。对此,技术可以凭借其行为调解直接作用于使用者的身体或行为,通过引导甚至强制的方式促使其作出符合特定道德规范的行为方式。
当然,除了通过个体道德的调解机制来影响群体道德实践之外,技术调解还可以直接作用于群体道德的特殊性,凭借对群体道德共识以及群体道德行为的影响而参与到群体道德实践当中。具体来讲,技术不仅能够通过认知调解提供关于某一道德情境的解释框架,协助该情境中的行动者在此基础上达成对特定道德事件的基本认知,又能够凭借互联网等技术平台拓展公共讨论的空间,促使个体间的冲突与分歧在协商伦理的框架下得以解决,进而达成道德共识。
其二,伦理对技术发展的伴随机制,即伦理对技术发展全过程的介入与伴随,也可看作是伦理型道德能动体的人类对技术发展的治理与责任承担。“伴随”的概念来自于维贝克所提出的“技术伴随伦理”:在这样一种技术伦理框架中,伦理实践意味着要参与到技术发展的各个环节当中,去审慎地塑造并引导技术的发展[21]。
根据具体技术物的发展过程,伦理伴随机制可按照四个阶段推进:首先,以技术工作者为主导,在技术设计阶段进行伦理嵌入,让技术设计负载利益相关者的价值观,使设计实践符合特定的伦理道德考量。对于技术产品而言,就是让具体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嵌入到技术物的物理结构当中,并通过技术功能的发挥得以实现。其次,以伦理委员会为主导,在技术试验阶段进行伦理评估,通过技术伦理效应的预测与识别、伦理问题的分析与澄清,以及解决方案的开发与确定来修正和完善技术开发方案。此阶段的核心是对评估对象的道德可取性(moral desirability)进行积极分析与建构。再次,以政府部门为主导,在技术推广阶段进行伦理调适,实现技术产品的价值导向与社会价值系统的顺利融合。那些具有明确价值导向的技术产品,如环境友好型产品,它们不像其他技术产品那样有自下而上的庞大市场需求作为支撑,因此需要依靠政府自上而下的引导与推动,才能够激发市场受众的积极呼应,从而使这些技术产品的伦理潜能得以顺利实现。最后,在技术使用阶段,以使用者为主导,通过“善用”承担起对他者、对世界的责任,同时通过审慎的、创造性的使用避免沦为盲目的行动者(blind doer),建构起具有个体风格的技术使用实践,最终实现自身作为伦理型道德行动者的角色,并为人工道德行动者的角色实现、人与技术之间的本真性共在关系的落实提供实践支撑。
五、 技术伦理实现范式转型的价值取向
就技术伦理实现范式转型的三个方面来看,其体现出的价值取向有如下几点。
第一,实践旨趣。当代技术伦理实现范式转型的背后,是技术伦理研究中实践旨趣的复归。面对现实问题的日益复杂化、新自由主义下的市场导向以及社会对知识分子公共责任的吁求,技术伦理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必然遭遇存在主义危机:除非技术伦理研究能恢复其实践旨趣,回应现实问题、满足社会需求,否则就会被社会所淘汰。
对此,当代技术伦理冲出象牙塔的尝试集中体现在技术伦理实现的范式转型上。首先,技术伦理学家开始“走出学术壁龛,成为一个真正的社会行动者”[22]。作为追求实践效果的社会行动者,技术伦理学家的任务是与其他领域、非学术性的行动者进行合作,针对具体的实践问题提出建设性的、可行的解决方案,“以用于引导和改变负责技术开发、控制和使用的社会行动者的实践活动”[22]。其次,伦理的外延变得更加宽泛,它不再是硬性的约束,而是与多元的价值相关联----“在科技发展中,只要涉及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权利和/或美好生活的理念(安全、健康、福祉),都是‘伦理’问题”[23]57。因此,在转型后的技术伦理实现范式中,技术伦理所扮演的角色不再是狭隘、反馈的,而是“作为技术的塑造者之一,同其他行动者一起积极地参与技术未来的构建”[23]61。
第二,后人类主义视角。在技术伦理实现的主体转化中,无论是对伦理主体界定标准的重构,还是对技术所扮演的伦理角色的探索,都体现出了一种后人类主义的视角。与非人类主义视角不同,这种后人类主义视角的实质在于摆脱“对启蒙的挟持”(the blackmail of the enlightenment),以一种“混合的进路”(hybrid approach)超越启蒙运动以来的非此即彼的人类主义伦理框架[24]。所谓“对启蒙的挟持”,即人们只能对启蒙及其提倡的价值采取非敌即友的立场,这一立场强化了传统技术伦理中主体与客体、人与技术二分的框架。
从摆脱了挟持的后人类主义伦理视角看来,关于技术的伦理角色问题不再集中于“技术能否成为像人类那样的道德行动者”,而是去探究“技术物在具体的道德情境中扮演着何种角色”的问题;维护人类的伦理主体性并非在于否认并抗拒技术在人类存在中的地位,也非一味地将人类的存在交付于技术的调解性力量,而是要在与技术的共在关系中进行主动的参与、建构与塑造。因此,承认技术作为人工道德行动者的伦理角色并不意味着弱化人类的伦理主体性,反而在更为丰富的实践层面上扩展了人类的道德性:作为与技术共在的行动者,人类必须通过积极的行动来彰显自身存在的独特性,在具体的实践情境中塑造自身不同于技术的伦理主体性。
第三,基于责任的伦理规范。对于技术伦理实现范式的转型而言,无论是对实践旨趣的诉求,还是混合性伦理主体的建构,要想将其转化为实际的行动,都离不开基于责任的伦理规范。对责任的划分与承担,是人与技术本真性共在的伦理目的从理论走向实践的关键所在,也是技术与伦理的互嵌机制得以顺利运行的保障,因而也构成了对技术伦理主体的规范性要求。
从后人类主义视角出发,基于责任的伦理规范面向的是人与技术共同构成的混合行动者,因而,责任的划分需要在人与技术物之间进行。对于技术物而言,其对应的责任在于以合理的方式对人的认知和行为进行调解。其中,“合理”主要指在技术调解情境中应该尊重个体使用者的意愿与偏好,保留个体在其中发挥自我独特性和创造性的空间,以避免个体消失于由技术调解的规训性权力所造成“群体”中,沦为集体的、匿名的“常人”。由于技术调解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技术的设计与使用实践,因此其负责的方式主要表现为被动的承担,是基于设计者授权与使用者解读的既定伦理角色的呈现。与此相对,人类行动者在伦理责任的识别与承担中具有更大的主动性:人们可以在伴随技术发展的过程中自觉调整与技术的关系模式,并在这种关系中主动承担起对自身及他者的责任,进而实现伦理主体的自我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