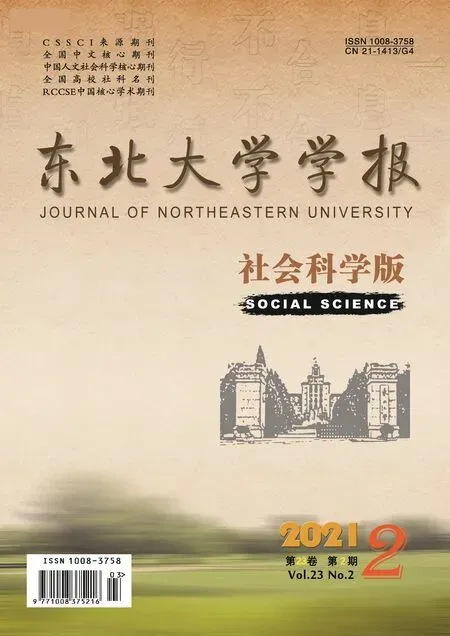《白噪音》中后现代声景的环境伦理思考
黄佳佳, 谭琼琳
(1. 湖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2; 2. 上海财经大学 外国语学院, 上海 200433)
“声音景观”(soundscape)源于“景观”(landscape)一词,意为“声音的风景”或 “听觉的景观”,简称为“声景”或“音景”。尽管“声景”与“音景”为同义词,在汉语表达上仍有一些细微的差别。“声”字从“耳”,“殸(磬)声”,本义为音波,包括乐音、话语及耳朵能辨别的所有听觉信息[1]695;而“音”则从“言”,“生于心,有节于外”[1]149,意指说出的话及话语中包含的心声。英语中的sound与voice也存在着差异,sound指的是声音、响声、声响[2]1988,而voice指的是嗓音、看法、呼声等[2]2326-2327。在意义上,前者比后者显得更宽泛。基于此,在大多数情况下,本文将soundscape译为“声景”,包含声音的自然属性与文化属性。
20世纪60年代末,加拿大学者雷蒙德·默里·谢弗(Raymond Murray Schafer)在其世界声景项目(The World Soundscape Project)中首次将“声景”作为研究对象,并将“声景”作为学术概念提出。谢弗认为,声音环境一般指客观环境或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或社会环境相对。这一观点在艾米丽·汤普森(Emily Thompson)的著作《现代性的声音景观》(TheSoundscapeofModernity,2004)中受到了质疑:汤普森将“声景”定义为“有关听觉感知或听觉的景观。像风景一样,声景同时也包括物理环境和感知环境的方式;它既是一个世界,也是一种为理解这个世界而构建的文化”[3]。她的这种论述主要源自阿兰·科尔班(Alain Corbin)对声音的研究。在《乡村钟声》(VillageBells,1998)一书中,科尔班结合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因素对19世纪法国农村的听觉变迁史进行梳理,深入探讨了钟声的文化意义[4]。随着声景在文化研究中的兴起,文学领域也开始关注声音描述或听觉感知,这使得听觉叙事、声景解读成为文学批评的一个新的视角。通过听觉的介入,读者可在视听感知平衡与统一中加深对文本深层含义的理解,从而实现更全面、更立体的文学解读。国外在这方面最早的研究来自加拿大学者梅尔巴·卡迪-基恩(Melba Cuddy-Keane),他曾创造性地将声学知识与叙事理论相结合,对20世纪英国现实主义和女性主义的先锋代表人物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1882—1941)小说中的听觉叙事进行了翔实的研究,指出“耳朵可能比眼睛让我们对世界有着更全面的了解,尽管它感知的是同一个现实。这种具有不同感知的优势在于两者互为相助”[5]。国内学者程虹曾在《自然之声与人类心声的共鸣》一文中探讨了美国自然文学中的声景,强调声景中自然之声与人类心灵进行沟通的特征[6]。傅修延则是从“听觉叙事”的角度提出将声景引入叙事研究的可行性和重要性[7]。
基于声音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各种声音成为作家们在构建环境,呈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时不可或缺的元素。他们试图通过“声音”这层面纱,揭示出不同历史时期人类生存空间的状况,引发人们对于环境与社会伦理的思考。美国后现代小说家唐·德里罗(Don DeLillo, 1936—)的成名之作《白噪音》(WhiteNoise,1985),正是通过描写后现代社会中的各种噪音来揭露科技与人类文明对生态环境以及人类身心的伤害,呈现出人类在死亡、信仰、灾难和暴力面前的恐惧,警示人们对于噪音与环境问题的思索。后现代社会也称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等,它指的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科技革命和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推动下,西方社会进入一种集知识、信息、高科技、消费、媒体等文化特征为一体的社会形态。本文拟从“声景”的视角,结合叙事学、生态学及伦理学的相关理论,通过分析《白噪音》中的听觉叙事和声音景观的建构来探究后现代社会中人们对于异化消费及环境伦理的思考。德里罗指出,白噪音不仅对后现代社会生存环境造成声音污染,还潜在地影响人们的消费观念和环境意识。他试图借“白噪音”以及文中各种声音的描写提醒人们关注声音与消费、声音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唤醒人们的环境伦理意识,寻找后现代社会中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方式。
一、 声景中的异化消费
雅克·阿塔利(Jacques Attali)在《噪音:音乐的政治经济学》(Noise:ThePoliticalEconomyofMusic,2009)开篇提到,“我们的科学总是希望监测、测量、抽象和阉割意义,却忘记了生命本身充满噪音,唯有死亡才是寂静的,如工作噪音、人类噪音和野兽噪音。噪音是可以买卖或禁止的。没有噪音,这一切皆不会发生”[8]。聆听噪音,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人类千百年来对环境所造成的破坏,并知晓这样的错误将引导人类走向何方;更重要的是,它有助于了解人类的未来和希望所在。《白噪音》这部小说向我们呈现了一个充满噪音的后现代社会。小说中的主人公杰克·格拉迪尼(Jack Gladney)是铁匠镇“山上学院”(College-on-the-Hill)希特勒研究系(the Department of Hitler Studies)的系主任,他与其第五任妻子芭比特(Babette)及各自之前婚姻中的几个孩子住在一起,生活平凡而琐碎。然而,一起突发的化学品泄漏事故打破了他们宁静的生活,引发了一系列家庭变故:孩子们不同程度地受到事件的影响;妻子因死亡恐惧铤而走险,通过“性交易”换取抑制死亡意识的药片;而杰克,因在毒雾中暴露,生命受到威胁,最终卷入诱骗妻子的格雷先生的谋杀事件。整本书中,作者一边叙述故事,一边用细腻的笔触向我们描述生活中的各种噪音,如家庭噪音、街道噪音、商场噪音等,这些噪音使人物的听觉感官积极参与了文化空间的营造,呈现出校园、家庭、郊外、超市、商场等日常生活空间中的社会关系。同时,作者对于“偶听”(overhearing)、“灵听”(weird hearing)、“幻听”(auditory hallucination)等听觉感知方式的灵活运用,使人物自然而然地被纳入了其所构建的社会关系网中,引发读者对现代人都市生活境况和伦理道德的思考。
《白噪音》发表于1985年,当时美国社会正处于消费文化的空前繁荣阶段,传媒的发展、科技的进步都为消费主义的盛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然而,人们在尽情享受着消费带来的刺激与快感的同时,也逐渐呈现出主体性消失的不安与焦虑,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眼中的“单向度的人”[9]12,即在现代工业化文明中被物质欲望所支配的、异化的人。他们陶醉于经济繁荣的景象之下,沉迷于物质财富的追求与享受,最终导致消费行为也被“异化”。《白噪音》中的杰克夫妇就是这样“单向度的人”。妻子芭比特总是不停地购买各种“不需要”的产品回家,等到商品过期后将其扔掉,然后再进行下一轮采购。杰克也觉得买回一大堆东西可以表明他们富足,光彩夺目而体积巨大的包装能让他们感到“昌盛繁荣”,“这些产品给我们的灵魂深处的安乐窝带来安全感和满足----好像我们已经成就了一种生存的充实”[10]21。小说中,白噪音主要指的是“消费文化的白噪音”,“作为现代科技产物的商品所发出的噪音”[11],而超市及商场则是其主要声源所在。杰克曾这样描述某个超市的噪音,以及深藏于其中的一种令人难以捉摸的声波:“购物车轮滚动时刺耳的吱吱声,扩音喇叭声和咖啡碾磨机的嘎嘎声,儿童们的哭叫声。在一切声音之上,或在一切声音之下,还有一种无法判定来源的沉闷的吼声,好像出自人类感觉范围之外的某种形式的密集群居生物”[10]38。这种噪音不仅让人有种无处不在的沮丧感,还有一种暴力和死亡的恐慌感。在另一处,这种感觉得到了回应。当他们一家走进“中村商城”(Mid-Village Mall)时,杰克感到“一种巨大的回荡着的喧闹声----好像是在灭绝一种野兽----充斥了这里广阔的空间”[10]92,“灭绝野兽”与“密集群居生物”一词遥相呼应,且更带有一种暴戾和血腥的感觉。事实上,生活中人们“血拼”促销产品时那种激情万丈、血脉偾张的场景同样不乏暴力和冲动。这一声音的描述,言简而意深。
杰克付款的时候碰到了同事,对方称他“不戴墨镜,不穿袍子,看起来就不一样了”[10]92。墨镜和袍子是杰克为打造自己希特勒专家这一形象而特意设计的“服饰符号”,就像他名字里额外加上的“J.A.K.”字母组合,虽然是随意杜撰的,但“使他的名字好像穿了一件借来的外套”,“暗示着尊严、重要性和声誉”[9]17。当同事的言辞点破他形象上的“不符”,他立马感觉到自己的大学教授、希特勒专家身份变得虚妄起来。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只要是身份,无论它们是指社会上的身份,还是家庭中的身份,学校中的身份等,都是伦理身份”[12]265,而伦理身份的确立则是“道德行为及道德规范的前提,并对道德行为主体产生约束”[12]264。杰克无法容忍自己的伦理身份遭到质疑,急需通过某种方式找回其主体性,于是便想到了购物。在《白噪音》所描绘的后现代社会中,符号的社会性已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商品消费领域。消费者的消费目的发生了质变,即由使用价值变为依附在商品上的符号价值。杰克必须通过符号消费来证明自己的身份。他开始“满不在乎地纵情购物”,“为购买而购买”;通过消费,他感到“开始在价值和自尊上扩张”,“发现了自己新的方面,找到了自己已经忘却的存在过的一个人”[10]94。这种消费不再是为了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而进行的活动,它被赋予了更多的意义;或者说,它满足的是消费者的心理欲求,从而导致人在消费活动中主体地位和理性精神的丧失,使人的本质异化到消费品上的人的物化状态。因此,它被学者们定义为异化消费。文本中,杰克的异化消费冲动明显是受到同事的话语(声音)刺激而产生的。此时,作者又一次对商场喧哗的声景进行了描述:“一支乐队正在现场演奏米由扎克背景音乐。说话声从花园和散步的小道上升腾十层楼,其中夹杂了各层楼面的噪音、噼啪的脚步声和敲击的钟声、电梯的嗡嗡声、人们吃东西的声响、人类进行交易的又生动又愉快的噪杂声,所有这些声音形成一股吼声,在宽大的柱廊里回响和盘旋”[10]94。这里所描绘的“脚步声”、“电梯声”和“吃东西声响”都是运用“灵听”,“即灵敏至极之听手法”[13]。这是作者特意赋予人物的一种“异能”,在特殊环境下对极其细微声音的感知,从而让读者能通过听觉感受其内心世界,理解作品的主题。这里所描述的各种声音以及“噼啪”“嗡嗡”等拟声词,说明主人公对声源的聆察非常仔细,对音质的辨析极为清楚,而一句“又生动又愉快”则交代了杰克聆听细致的原因,即消费带来的满足感和愉悦感。米由扎克(Muzak,又译为谬扎克)是一种在机场、旅馆、商店等公共场所连续播放的背景音乐,一般曲调比较安详平稳,能给顾客带来愉悦的购物心情,并使顾客随着音乐节拍而放慢脚步,延长购物时间。“中村商城”用乐队现场演奏米由扎克,让消费者流连忘返,实现更多的商品消费。因此,杰克一家的疯狂消费不仅来自同事的刺激,也来源于商场中现场演奏的米由扎克。聆听这种音乐,使敏感而细心的杰克心情愉悦,更加享受因消费而带来的身份自信和自我认可。
在后现代消费社会,由于消费主体的目的和心理的异化,消费客体的内容和形式也相应产生异化,从而转向主体的对立面。《白噪音》中的杰克经历过一次客体异化的消费。受同事默里(Murray)之约,他们去游览了名为“美洲照相之最的农舍”(the most photographed barn in America)的景点,那里竖着许多关于农舍的标示牌,簇拥着带相机的游客们和出售农舍照片的人。“听着快门不停的咔嚓声和卷胶片的手柄簌簌作响”,默里沉默不语,随后一针见血地指出,“没人看见农舍……我们到这儿不是来捕捉一种形象,我们之所以在此是来保持这种形象。每一个照相的人都强化了这儿的气氛”[10]12-13。在人们的镜头下,作为消费客体的农舍已被它的形象所代替,而这种形象是一种没有本源的复制,也没有任何指涉物或指涉意义的“仿像”(simulacrum)。有着标示牌的介绍,参观者主动放弃了对农舍的想象,它的过去、特征和功能都不及“照相之最”带来的视觉冲击,人们“所见的仅仅是旁人之所见”,积极参与的是“一种群体感”,成为“集体感觉的组成部分”[10]13。而这个部分的叙述在声景的设计上颇有特点,呈“无声”状态。首先,杰克的失语。自始至终都是默里在发表看法,即便中途默里问到杰克的感觉,他也没有回应。其次,默里多次长时间的“沉默”。美国心理学家保尔·古德曼(Paul Goodman)曾提出著名的“沉默定律”,即沉默可以调节说话的节奏,它在谈话中的作用,就相当于零在数学中的作用。尽管是“零”,却很关键。人在沉默时,可能正在体验某种情绪,或者正处于一种积极的自我探索。默里的沉默体现了他的思考和观察,也是对这种“美国式的魔力”的迷恋[10]19。从叙述者杰克的失语到默里的沉默,作者旨在突显这幅声景中的主调音(keynote sound)----“快门的咔嚓声和卷胶片手柄的簌簌响”[10]13,它确定了整幅声景的调性,即它支撑起或勾勒出整个音响背景的基本轮廓。在农场这样风光旖旎的田园风景中,作为主调音的咔嚓声格外引入注目,它如同白噪音般的存在,让真正想要欣赏农场风景的人们被迫屈从拍照的群体效应,眼中只剩下“仿像”的影子。默里恰到好处的解说,便成了个性鲜明的信号音(signal),充分引起了杰克和读者的注意和思考,让“仿像”这种异化的消费客体,以及人们趋之若鹜的消费态度更加深入人心。
二、 声景中的环境意识
消费异化是一种物化的文化形态,它造成了人们对物质的极度崇拜以及全社会形成的奢靡浪费之风,导致人们价值观的错位,更对环境造成了极大的污染和破坏。为了突出这个主题,德里罗在小说中花了大量笔墨去描绘各种形式的白噪音,并试图通过人物的听觉感知来表现他们在生态灾难前的惶恐、无措和绝望,从而唤醒读者的环境意识和生态责任。
在《文学理论》(TheoryofLiterature, 1984)一书中,勒内·韦勒克(Rene Wellek)与奥斯汀·沃伦(Austin Warren)指出,“一个‘意象’可以被转换成一个隐喻一次,但如果它作为呈现与再现不断重复,那就变成了一个象征,甚至是一个象征(或者神话)系统的一部分”[14]。由此可见,如若一种听觉意象在文本中总是被作者在各种声景中使用,那么它必然与作者意欲表达的主题思想有着重要的联系,形成一种象征意义。贯穿整部小说的“白噪音”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对于“白噪音”,德里罗有过两种解释:一种是由特别声音设备所发出的“全频率的嗡嗡声,用以保护人不受诸如街头吵嚷和飞机轰鸣等令人分心和讨厌的声音的干扰或伤害……‘白噪音’也泛指一切听不见的(或“白色的”)噪音,以及日常生活中淹没书中人物的其他各类声音----无线电、电视、微波、超声波器具等发出的噪音”[10]4。对于白噪音的描写,书中既有对无线电波、电话、电视、汽车声等多次概略的侧面描写,又有对超市、商场中喧嚣噪音的详细的正面描写。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噪音“在一切声音之上,或在一切声音之下,还有一种无法判定来源的沉闷的吼声”[10]38。这些充斥在后现代社会中的白噪音都来自于人们亲手研制的科技之物。作者通过“白噪音”这一听觉意象提醒人们在享受科技带来的舒适之余,也要清醒地意识到他们对于人与自然平衡关系的打破,对于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同时,书中人物对于“白噪音”的听觉感知也揭示了人们在后现代繁华物质掩盖之下精神的焦虑与惶恐,以及内心深处的茫然和无措。在书中,“白噪音”还被赋予了更深层的象征意义,即人们用以抵制死亡恐惧的一种力量。
谢弗在《声景:我们的声音环境以及世界的调音》(TheSoundscape:OurSonicEnvironmentandtheTuningoftheWorld,1994)一书中曾提及,“声景是任何声学领域的研究。我们可以称一个音乐创作为一个声景,或者称一个电台节目为一个声景,或者称一个听觉环境为一个声景”[15]7。因此,德里罗在《白噪音》中每一个听觉环境都可视作一个声景,它们都是由特定情境中诉诸人类听觉的意象组成的。谢弗认为,声学意义上的声景包括三个层次,即主调音(keynote sound)、信号音(signal)和标志音(soundmark),它们引起的关注度不完全相同。在同一幅声景中,呈现在景观最突出位置的声音和潜藏在深处的声音之间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关系,在不同的情节需求中,主调音和信号音可以相互转换,以此方式构成声景的“景深”(perspective)。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谢弗还借用了视觉感知中的一对概念即图(figure)和底(ground)来进行说明。根据格式塔心理学家的看法,图是兴趣的焦点,底是背景。后来在此基础上,他又增加了第三个术语,场(field),意即观察发生之地。现象学心理学家指出,被感知为图或底的东西主要由场和主体与场的关系决定[15]152。在这三个术语中,“图”对应于信号音或标志音,“底”对应于周围的环境声音,通常为主调音,而“场”对应所有声音发生的地方,即声景。
在小说第二部分“空中毒雾事件”(the airborne toxic event)中,杰克一家为躲避毒雾的侵害,深夜驱车逃往指定安身之所,在逃亡的路上听到收音机里的汽车喇叭声“以急促紧迫的调子不停地响着,在这暴风雪的夜空中,传递出一股野兽的恐惧感与警告”[10]172。在这里,“急促”(rapid)、“紧迫”(urgent)、“警告”(warning)三个词勾勒出汽车喇叭声传出时的听觉环境,在“暴风雪夜空”的背景下,这响声会立刻吸引所有人的关注,因此属于信号音。这是危险步步紧逼的信号,作者以此来表现汽车喇叭声带给逃难者的惊恐和慌乱,增强了此声景的紧张感。而接下来一个瞬间,直升飞机的声音将“我们”的视线转移,在光秃秃的树枝间,在直升机煞白的灯光下,“一个翻滚着的、状如鼻涕虫的膨胀的毒雾团”[10]172出现在“我们”眼前,它“巨大得几乎不可思议,超过了传说和谣言。它好像在生成它自身内部的风暴。可以听得见阵阵爆裂声和噼啪声,看得见道道闪光,以及一长串环状的化学气焰。汽车喇叭一阵吼叫,一阵呜咽”[10]172。在直升机声音的引导下,叙述者将毒雾的“神秘面纱”揭下,它翻滚、膨胀、庞然大物一般,视觉的画面已然令人惊悚,作者再适时添上声音效果,“阵阵爆裂声和噼啪声”(cracklings and sputterings),视觉和听觉效果并置,一种凶神恶煞、波谲云诡的恐怖气氛向读者扑面而来,让人浑身战栗。此时声景中的汽车喇叭声便不再像刚才那样“凸显”,它让位给毒雾的“阵阵爆裂声和噼啪声”,喇叭声变成“一阵呜咽”的背景音,这也就是谢弗所说的“图”变成了“底”。谢弗还指出,“当声音的力量强大到足以覆盖住一个大的平面,我们也可称其为帝国主义……因为他拥有一种力量,可以打断和主宰临近空间内的其他声音活动”[15]77。在这幅声景画面中,毒雾的爆裂声和噼啪声显然是充当了声音帝国主义的角色,它的出现令周围的直升机声、汽车喇叭声转眼变成了背景音。如果汽车喇叭声象征的是人类的科技产物,那毒雾爆裂声象征的则是遭受人类破坏而失控的大自然,它所爆发的力量让人造物不寒而栗、束手无策。通过此处声景的景深变化,作者隐喻地表达了他对工具理性和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批判:人类总为自己巨大的创造力而感到自豪,总觉得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牺牲他者的利益是理所应当的,可在充满灵性智能的大自然面前,所有的科技和人类力量都不堪一击。
在《白噪音》中,德里罗真实地记录了后现代社会中的各种听觉意象,向读者呈现了一个充满人造音的世界。在整本小说中,作者对于“人声”(包括情绪声、喧哗声、声调等)描写有近40处,对于“物声”(包括汽车声、电噪音、电视、收音机、电话铃、警笛、扩音喇叭等)描写有近100处,而对于“自然之声”(风声、毒雾响声、动物声等)的描写却不足10处,这说明在后现代“低保真”的声音环境中,“人造物”所产生的噪音已牢牢占据“声音帝国”的位置,而自然界的声音则越来越被人们忽略。另外,在“物声”的听觉意象中,电噪音被提及58次,频率最高,其中媒体(包括电视和收音机)的声音被提及38次,其次是汽车声,被提及20余次,再次是警笛和扩音喇叭,被提及18次。从数据中可以看出,电噪音是我们生活中最普遍却最隐形的噪音,它们几乎无时无处不在。最常见的电视声和收音机声,总是在故事叙述中随意地插入进来,虽然有时会打断叙述的连续性,但也恰巧说明它们存在的真实性,“在某种程度上,媒体为芭比特和杰克提供了一种舒缓的背景噪音,让他们在下意识中能感觉到自己正与无数其他听众关联在一起”[16],由此对媒体产生强烈的依赖性。芭比特好似总也听不够收音机里的访谈节目;海因利希(Heinrich)宁可相信收音机里的天气预报也不相信眼前看到的事实[10]22-25;杰克家所有的信息来源都依靠电视或者收音机,家庭的凝聚力也试图通过“观看电视”这种颇有仪式感的活动来获得[10]16,听完“客机遇险”经历的孩子认为“媒体报道”才是使这段经历有意义的方式[10]103。媒体的声音霸占着听觉的空间、钳制着人们的思想,因而更加模糊人们对现实的认知。在“人声”的听觉意象中,描述次数最多的是“喧哗”的声音,超市的嘈杂声、商场的喧闹声是杰克生活的铁匠镇即一个美国中部小城镇的标志音。这种标志音也间接说明了人们对于消费的狂热,它不仅产生了大量污染环境的垃圾,而且制造了一种消费噪音,给人们带来了无尽的焦虑和烦恼,污染着人们的视听环境。
“自然声景”的静默是这部小说一个很有特色的设计。作者在小说中提及“镇上……没有令人留连忘返的天然场所或迷人景色”[10]65,仿佛是为后面不多的自然声景描写埋下了伏笔。傅修延曾指出,“音景不光由声音构成,无声也是音景不可或缺的成分”[7]。无声的音景可以寄托哀思、省察内心,更能引起读者的特别关注和深层思考。小说中有一段古墓地的描写,“我站着倾听。我远离了车辆的喧闹、河对岸工厂的阵阵震动……这里有一种不为一切所动的静谧。空气冷得刺骨。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等待着感觉应该降临死者的和平宁静……我站在那里倾听。风吹落了树枝上的积雪。雪随着涡流和阵风从林子里刮来……当空中再次安静时,我又走在墓石之间……然后我站着倾听”[10]109。在这段描述中,作者用了三次“倾听”(listened),可听到的却是“静谧”(a silence)、“和平宁静”(the peace)和“再次安静”(still again)。墓地是生命终结的地方,这里的安静包含着对死者的尊重和对死亡及生命的敬畏之情。其次,这里的“安静”也是主人公内心中对宁静生活的向往,在喧嚣的城市中,这样的“安静”既是难能可贵的,又是极其可悲的,因为它暗示着正是人类的入侵才让原本生机勃勃的自然变得死气沉沉,最后还被人们无情地遗弃。于是,一种讽刺之意油然而生。因此,这段独特的无声描写是作者特意在这曲沸沸扬扬的《白噪音》中插入的一个“休止符”,它的音乐停顿让读者不禁去反思生命的意义、道德的力量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真正做到“无声胜有声”。
三、 结 语
书如其名,《白噪音》这部小说仿佛是一曲融合各种织体、节奏及旋律的无调性交响,错综而庞杂。但恰恰是凭借对声音环境如同“复制”般地逼真呈现,德里罗成功地唤起了读者对后现代社会生存环境恶化的关注。同时,通过揭示声音背后人们的消费理念与环境意识,他试图表明,后现代社会中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及相互作用逐渐呈现区域化和国际化的趋向,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伦理道德关系需要得到高度重视。书中人物的悲剧性结局旨在提醒读者,面对后现代生存环境恶化的严峻局面,逃避不是最好的方式;只有树立生态整体观意识,营造积极健康的社会生态环境,才能更好地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社会与自然之间和谐的多层次立体交叉关系,从根本上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