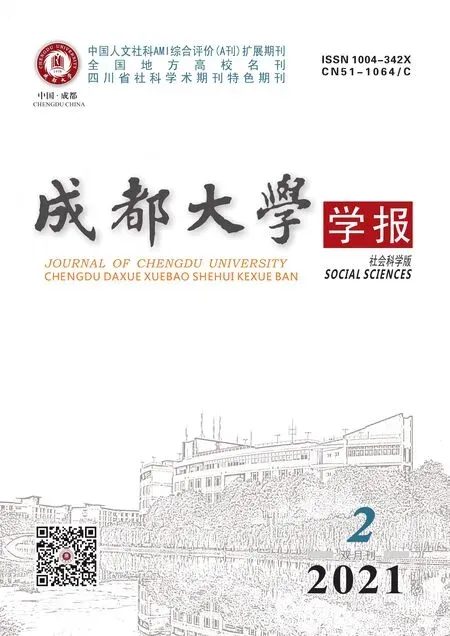史前蜀地农业的起源与早期发展考察*
辛 艳
(重庆医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400016)
蜀地早期历史与中国古史传说中的黄帝、颛顼、大禹等英雄人物密切相关。
本文从族群迁徙与文化互动的角度,探讨黄帝族群、禹羌族群对于推动蜀地早期农业的起源、初步发展的重要贡献,以求教于方家。
一、巴蜀农业的自然生态环境
农业是通过对动植物的人工培育,实现能量转化,取得农畜产品的社会生产部门。因此,农业既是一种经济的再生产过程,同时也是一种自然的再生产过程。农业的这种特点,决定了农业生产依存于特定的自然环境。本文探讨蜀地农业起源与发展,首先需要对巴蜀农业发展的自然生态环境作一介绍。因为巴蜀地区是作为一个完整地理单元存在的。
巴蜀地区地处我国内陆,地形地貌复杂多样。纵观全境,地势西高东低,东西两部分地貌截然不同。西部为山地、高原,是青藏高原的东延部分;东部地势相对较低,为四川盆地及其环绕周围的山地。四川盆地自西向东又由盆西平原(成都平原)低山区、盆中丘陵低山区、盆东平行岭谷区构成。[1]而素有“天府之国”美誉的成都平原是由发源于平原西部山地的多条河流的山前冲积扇组成,是典型的复合冲积扇平原,其面积达1.2万平方公里。平原内河流密布、土壤肥沃、土质疏松,非常易于农耕。盆中丘陵面积辽阔,土地平敞,土质深厚,河流纵横,适合发展农业;盆东平行岭谷水源丰富,其间分布有一定的河谷平原,但面积都不大,主要还是以丘陵、山地为主,农耕条件显然不如盆西平原和盆中丘陵地区。这种自然环境往往适合发展粗耕农业和与渔猎采集相结合的复合型经济。自然环境的差异对先秦两汉巴蜀地区各个族群的生业活动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
巴蜀地区地形地貌的差异,导致境内气候复杂多样。从气候带看,除热带外,盆地从南至北,依次是南亚热带、中亚热带、北亚热带、暖温带、温带,寒温带和亚寒带,无不齐备。东部为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温暖湿润,降水充沛,为水稻等农作物的生长提供了良好条件;西部山地高原以温带、寒温带季风气候为主,干湿季节交替明显,气候垂直变化显著,有利于农耕、畜牧等多种经营。
巴蜀地区地域辽阔,不仅地形地貌、气候复杂多样,而且具有复杂的成土条件和丰富的土壤资源,土壤种类繁多。具体包括川西高原森林土区,川西山地草甸土区,川西高山峡谷褐土及棕壤土区,盆地丘陵紫色土区,川西南山地及山间盆地红壤、褐红壤土区,盆地边缘山地黄壤区、黄棕壤区,以及盆西冲积平原、残丘及台地潮土性水稻土、黄泥土区,从亚热带到寒带的土壤应有尽有。复杂多样的土壤为农耕、畜牧等综合发展和多种经营提供了良好条件,而农耕大致又分为稻作与粟作。
巴蜀地区是我国西南的腹心地带,地处长江上游,地理位置特殊。它不仅可以通过长江三峡与广大的中下游地区相联系,而且也可以通过源于青藏高原东延的岷江、雅砻江、金沙江上游河谷与黄河上、中游广大地区发生联系。特别是四川盆地以西的川西高原历来是中国南北文化交流、民族迁移的一条重要走廊,被民族学界视为“藏彝走廊”核心地区之一[2],也是童恩正先生揭示的从中国东北到西南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重要组成部分[3]。由于这些地理特征,巴蜀地区也就成了东西南北文化交流融汇的重要津梁,在中华文明起源中占有重要地位。这就使得黄河流域的粟作农业和长江中下游的稻作农业都可能在很早就影响并传播到巴蜀地区。
二、黄帝族与蜀地粟作农业的起源
国际著名农史学家瓦维洛夫的名著《育种的植物地理学基础》指出,中国是世界八大农业起源中心之一[4],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区域即巴蜀。张光直据瓦维洛夫“经典著作”指出:
瓦维洛夫主张:上述八大起源中心中,最大最早的中心是中国中部、西部的山区以及附近低地。所指即鄂西到川西的山区及附近的低地。他根据现在的野生植物的分布推测:最早在中国由野生到家生的植物有粟、黍、高粱、大豆、红豆、山药、萝卜、白菜、芥菜以及各种的竹子,等等。[5]
本土学者蒙文通先生提到巴蜀农业起源也引述指出:
近时有研究中国农业史的科学家认为,中国农业在古代是从三个地区独立发展起来的,一个是关中,一个是黄河下游,在长江流域则是从蜀开始的。[6]
按以上两位学者的观点,巴蜀农业的起源极可能是独立的或原生的。由于此种认识形成的时间早,目前还缺乏考古学证据。然而,倘若从古代农作物品种本身的多样性而言,如上述瓦维洛夫所列“粟、黍、高粱、大豆、红豆、山药、萝卜、白菜、芥菜以及各种的竹子”等等,其中某些品种则完全有可能是直接从巴蜀地区野生作物驯化而来的。同时,巴蜀地区农业的发生是否为独立或原生固然还有疑问,但这绝不意味着巴蜀地区农业的发生就一定很晚,因为即使它是次生的也未必就晚。综合文献记载与考古材料,蜀地农业的发生,至迟可以上溯到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即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晚期。
位于长江上游地区的古蜀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起源地和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最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单元。史载古蜀很早就与华夏族群发生了互动关系,其间有着密切联系和经济文化交流。我国现存最早的地方志《华阳国志》是记载东晋以前我国西南地区的历史、地理的典籍。其云:
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颛顼;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武王伐纣,蜀与焉。[7]97
常璩将蜀地文明史追溯到了中国古史传说的“三皇五帝”时代,将蜀地的区域历史整合到华夏史体系中,这显然是受华夏正统史观的影响。蜀之开国于“三皇”之一的“人皇”,这是汉晋之际颇为盛行的华夏文明史起源的说法。[8]人皇的相关史迹,多见于谶纬书籍,并无严谨而可称道者流传下来。五帝时代,蜀人便与黄帝族群建立姻亲关系。“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这是蜀地土著居民与华夏族群发生互动的最早传说。太史公司马迁对此记述得更为详细。《史记·五帝本纪》云:
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是为帝颛顼也。[9]10
司马迁此记主要是出自《世本》和《大戴礼记》的《帝系姓》《五帝德》。上引文献提到的地名“西陵”,据考证,实为“蚕陵”之误,汉代其地置有蚕陵县,故地在今岷江上游茂县叠溪境内。蜀山,即岷江上游的岷山。江水指今岷江,若水指今雅砻江,皆在蜀中。黄帝娶于西陵氏、昌意复娶于蜀山氏,以及青阳、昌意二子降居蜀中的古史传说反映了黄帝族群从西北高原辗转南徙到川西地区,并与蜀地土著西陵氏、蜀山氏族群进行政治联姻的跨血缘的地域性族群重组的史实。黄帝族支系与蜀地土著族群进行融合、重组,使不同族群之间超越血缘纽带,结成早期地域性联盟。此种社会组织的形成无疑促进了古蜀早期文明因素的发生与发展。
近年来,岷江上游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也反映该区域族群文化与黄帝族群密切相关的马家窑文化、仰韶文化有一定联系。考古工作者在岷江上游以及支流黑水河和杂谷河的河谷地带调查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多达82处,其中茂县营盘山、波西、哈体都遗址等若干规模庞大者揭示了该区域史前社会颇为繁荣的状况。营盘山遗址地处岷江东南岸二级台地上,年代距今5500—5000年。遗址平面约成长方形,东西宽约150—200米,南北长约1000米,总面积近10万平方米,是岷江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大型中心聚落遗址。[10]遗址出土的彩陶为红胎黑彩,与西北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彩陶相似;出土的泥质磨光红褐陶碗与折腹钵、陶瓶腹部的双耳、陶器流等其他陶器,和磨制穿孔石刀,都具有马家窑文化特征。整体上看,营盘山遗址以本土文化因素为主,同时吸取了马家窑文化若干因素。波西遗址位于岷江西岸二级台地上,时代略早于营盘山遗址。其文化内涵与营盘山遗址有一定的联系,同时也显示出其具有庙底沟文化因素。[11]遗址G1出土的细泥红陶弧边三角纹彩陶敛口曲腹钵与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仰韶文化的A3碗、A10g盆等风格相似。且共存的双唇式小口瓶、尖唇敛口钵等其他陶器,以及细泥红陶及线纹所占比例最多的特征均属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晚期。而川西高原的另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大型聚落遗址——马尔康哈休遗址,位于大渡河上游,年代距今5500—5000年,与营盘山遗址年代相当。[12]其文化内涵包括了本土土著文化、仰韶晚期文化、马家窑文化等因素。出土的陶尖底瓶,陶双唇口式、平唇口式小口瓶,细泥红陶直口碗,泥质红陶卷沿盆,以及弧边三角纹、变体鸟纹、勾叶状纹彩陶等具有仰韶晚期遗存同类陶器的特征。而饰平行线条纹的喇叭口彩陶瓶、折腹陶钵、泥质陶敛口碗以及磨制穿孔石刀又与马家窑文化相似。以上诸遗址除了本土文化因素外,还受到黄帝族故地西北甘青地区古文化的强烈影响。此种情形,无疑揭示了川西高原族群文化来源的多样性,这正是不同族群之间跨血缘的以地域性联系为纽带结成的社会共同体的反映,是文明因素孕育的条件。
从生业方式看,黄帝族群无疑是以农耕经济为主要生业。就族源而言,黄帝与炎帝同源,均出自羌族。《国语·晋语四》云:“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13]西汉初年贾谊的《新书·制不定》也云:“炎帝者,黄帝之同父母弟也。”同书《益壤》亦云:“黄帝者,炎帝之兄也。”[14]足见,炎、黄二帝的同源关系。史载炎帝居姜水,并以“姜”为姓。上古时期“姜”“羌”关系非常密切,《后汉书·西羌传》:“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15]2869说明羌族是出于姜姓的支系。从古文字角度分析,“姜”从羊从女,“羌”从羊从人。二字乃意近通用之形旁,是代表性别的民族同义字,其字义同出一源。“姜”到“羌”的演变,反映了远古时期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历时性变迁。“姜”“羌”从羊之会意字,说明该族群是以牧羊之畜牧为主要生业,故《说文解字》解释“羌”为“西戎牧羊人”。这是否说明羌人自古就是以畜牧为主要生业呢?按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农业发生普遍要早于畜牧业,畜牧业是从农业中脱离出去的。后起的“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15]2869的游牧氐羌,是从早期农业部族中分化出去的。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形成游牧经济以前,都普遍经历原始农业阶段,游牧民族的形成是很晚的事情了。[16]姜姓炎帝,因教民耕农,故号曰“神农”,是我国传说中的农业始祖。姬姓黄帝也是以农业著称。从考古学上看,羌人故地西北甘青地区考古发现的大地湾文化、马家窑文化揭示当地居民的经济生活主要是以经营粟作农业,说明羌人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就进入农耕时代了。
川西高原地区的考古材料反映该区域持续受黄河上游粟作农业文化的影响,新石器时代晚期便开始了以农业为主,辅以渔猎采集的生业活动。营盘山、波西、哈休等诸遗址发现有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类似的彩陶与磨制石器并存的现象揭示,岷江上游地区农业起源很早的史实。营盘山遗址出土的磨制石器是以石斧、石锛、石凿为组合的农业生产工具为主,而作为专业性较强的特化谷物收割工具——穿孔石刀的发现,则说明农业生产技术有了较大进步。[17]营盘山遗址植物遗存浮选结果也显示,当地先民已经开始了原始种植业,是以种植粟和黍旱地农作物为主。[18]此外,营盘山先民还学会了驯养家畜。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遗骸中,属于家养动物的有猪、黄牛、狗等。家畜特别是家猪成为当时主要的肉食来源。[19]上述材料说明了营盘山先民是以农耕业为主要生业,辅之以渔猎采集经济。此种情形在大渡河上游的哈休遗址也得到反映。考古学者对哈休遗址灰坑进行浮选,发现有粟、黑麦等作物品种,据此推测,哈休遗址的居民主要栽培植物是粟等旱作谷物。[12]显然,川西高原的粟作农业是受黄河上游炎黄族群故地甘青地区古文化的影响所致。
三、禹羌族与蜀地早期农业的发展
继黄帝之后,中国古史传说里的另一位英雄人物大禹,与蜀的早期历史也有极为深厚的关系。作为黄帝族后裔的禹族早期曾生息于岷江上游地区,这些已为先秦以来的传世文献、考古学、民族学所证实。战国晚期的《荀子》说:“禹学于西王国。”[20]《史记·六国年表》明确记载:“禹兴于西羌”,此条下《集解》引皇甫谧曰:“《孟子》称禹生石纽,西夷人也。”[9]686此说当为《孟子》佚文,不见于今本《孟子》。西汉陆贾《新语·术事篇》也明确记载:“大禹兴于西羌。”[21]西汉桓宽《盐铁论·国疾》也说:“禹出西羌”。[22]可见,“大禹兴于西羌”是先秦以来普遍认同的说法。西羌的分布范围颇为辽阔,“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赐支者,《禹贡》所谓析支者也。南接蜀、汉徼外蛮夷”[15]2869。其主要分布中心在黄河上游甘青地区,还南及岷山之域。无论从地理上还是文化上看,岷山山区与西北甘青地区都是连为一体的。由此看来,禹羌族的地域范围大致在西北甘青地区和岷山一带。
此外,《孟子》佚文还将大禹出生地具体到一个叫“石纽”的地方。对此,蜀地文献有颇为详细的记载。旧题西汉扬雄所著《蜀王本纪》云:
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生于石纽,其地名痢(或作刳)儿畔。[23]
《蜀王本纪》取材于蜀地世代相传的旧说或广为流传的旧史而成书,将大禹的出生地锁定在川西地区的汶山郡广柔县,当有所据。后世蜀地学者也普遍认同这一说法。《三国志·蜀志·秦宓传》云:
禹生石纽,今之汶山郡是也”,裴注引谯周《蜀本纪》:“禹本汶山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其地名刳儿坪。[24]
《华阳国志》也载:
(禹生石纽)夷人营其地,方百里不敢居牧。有过,逃其野中,不敢追,云畏禹神;能藏三年,为人所得,则共原之,云禹神灵祐之。[7]562
郦道元《水经注》亦有类似的记载。上述文献提到的“夷人”泛指羌族。汉晋之际,岷江上游的氐羌族群对大禹顶礼膜拜,奉为神明,反映了大禹在当地深厚而久远的影响。
汉晋时期的广柔县管辖范围很广,包括现今汶川、理县、北川诸县以及相邻的茂县,以及都江堰市等部分地区,均有以“石纽”命名,并有禹生于此的相关传说。这一带主要位于岷江上游,是禹族生息繁衍的中心地区。禹生于石纽的传说,与羌族白石崇拜的古老习俗相关,“作为自然崇拜的主要崇拜对象之一的石崇拜,历来较完整保存在羌族的原始宗教信仰中”[25]。
禹兴于西羌,生于石纽的传说,得到了近年来考古材料的印证。2004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峡考古队在重庆云阳旧县坪发掘出土了一通东汉巴郡朐忍令景云碑,此碑铭文记述了有关“禹生石纽”的材料。碑文说东汉朐忍县令景云为大禹后裔,“先人伯杼,匪志慷慨,术禹石纽、汶川之会。帷屋/甲(怅)帐,龟车留遰,家于梓潼,九族布列,裳絻相龙,名右冠盖”[26]。这段碑文的意思就是说景云先祖为禹后七世孙、少康之子的伯杼,伯杼为遵循“禹石纽、汶川之会”的遗训,曾甲帐龟车,巡狩回蜀。可见,东汉时期大禹后裔便认为大禹不仅兴于西羌,而且还在汶川石纽组织过盟会。
禹羌族对蜀地早期文明的卓越性贡献在于,在蜀地取得的治水经验和水利技术有力地促进了本区域的开发与早期文明的繁荣,更为后世举世闻名的开明氏、李冰领导的水利活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当然,其更大的贡献在于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
禹羌族早先居息于川西北的岷江上游地区,其治水活动也是开始于长江上游江源地区(古人认为岷江是长江的正源)。大禹在总结其父鲧以“湮塞”“壅堵”的方式规避水患的传统治水经验的基础上,转而采取以“疏导”的方式消除水患,无疑是水利技术史上的重大进步。《尚书·禹贡》云:“岷山导江,东别为沱。”[27]152反映了禹羌族群在岷江上游的治水活动。大禹导江,即是从岷江开凿一条人工河道,分引岷江洪水,这条人工河道称之为“沱”。根据《尔雅》和《说文解字》的解释,出于江又还于江的水道叫“沱”。大禹导江目的在于解决成都平原水患问题。素有“天府之国”美誉的成都平原,在先秦时期则经常遭受洪水袭击。成都平原是由发源于川西北高原的岷江、沱江等多条河流山前冲积而成冲积扇平原。平原地势平坦,呈西北向东南微倾,海拔500-750米,地面平均坡度约4‰,地表相对高差都在20米以下,虽然有着天然的舟楫灌溉之利,然而也时常遭受岷江洪水的侵害。大禹“东别为沱”就是根据四川盆地地势西北高、东南低,以及天然水系的分布也多为西北东南流向等自然地理条件,将分洪水道巧妙地设计在平原中偏北,方向与天然水流交叉,采取自西往东的方向,以顺应地势与水情。沿程拦截暴雨径流,向东集中排到沱江金堂峡这个口门泄走。[28]大禹根据蜀地地势与水情设计的治水方案,为后世蜀地水利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禹羌族的治水足迹不止于岷江流域,而是遍布整个“梁州”之域。《尚书·禹贡》说:“华阳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艺,沱潜既导,蔡蒙旅平,和夷厎绩。”[27]150沱,即沱江;潜,一说即今渠江,一说即今广元东北的潜溪河,说明大禹治水活动已到达了嘉陵江流域。《尚书·禹贡》又说:“嶓冢导漾,东流为汉”;“浮于江、沱、潜、汉,逾于洛,至于南河”。[27]152江、沱、潜、汉即为岷江、沱江、嘉陵江和汉江,构成了长江上游的主要支流,也是梁州境内的主要水系。这些流域尤其是岷江流域是上古时期长江上游最早开发、最为繁荣的地区。正如蒙文通先生所言,禹羌族所在的岷江上游河谷地区是最早开拓的地区,蜀地农业就是开始于岷山河谷的。[29]47-48,75-82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的繁衍,加之距今4000多年的灾变气候,禹羌族主要支系在传说中的“五帝”时期发生了东渐北上黄河流域的历史性迁徙,但也在岷江流域和成都平原留下了一些氐羌支系。这些氐羌支系与来自东南方向的濮越系族群成为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以降的古蜀文明的主要创造者,持续推动了蜀地这一区域文明的繁荣。
综上所述,史前川西高原由于持续受到黄帝族群故地黄河流域尤其是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影响,粟作农业有了初步发展。大禹在蜀地取得的治水经验和水利技术更是有力地促进了本区域的开发与早期文明的繁荣。这为进入文明时代以后的蚕丛、柏灌、鱼凫时期蜀地农业发展与区域文明繁荣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