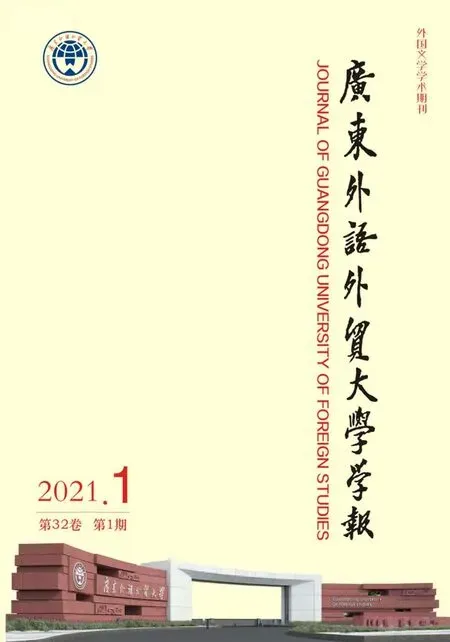为了被遗忘的过去:《查克·莫尔》的叙事策略研究
胡秋香
引 言
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Carlos Fuentes)是当代拉美文坛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与胡安·鲁尔福(Juan Rulfo)和奥克塔维奥·帕斯(Octavio Paz)并称为20世纪下半叶墨西哥文学的“三驾马车”。他的作品不仅在拉丁美洲广为传阅,在世界文坛上也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1954年,富恩特斯出版了他的第一部作品:《戴面具的日子》 (LosDíasEnmascarados)。《戴面具的日子》由六篇短篇小说组成,其中最出名的就是《查克·莫尔》(ChacMool),它也是该小说集中唯一一篇被富恩特斯选入1972年出版的文选《身体与祭品》(CuerposyOfrendas)中的小说。富恩特斯把《戴面具的日子》称为他以后作品的“祖先(el antecedente)”(García,2000:18),其风格、人物形象、氛围、主题等均在后续的作品中有所体现,所以《查克·莫尔》的研究对更好地理解富恩特斯的其他作品具有重要意义。
1910年墨西哥爆发了大革命,这场声势浩大、时间持久的革命结束了迪亚斯(Porfirio Díaz)的独裁统治,建立了立宪共和国。虽然革命并不彻底,但推进了墨西哥的民主化进程,唤醒了墨西哥人对自我身份的追问。他们需要为自己的存在寻找一个定义,确认自我身份,但是直到20世纪中期这个定义仍然悬而未决:“墨西哥人既不想是西班牙人,也不愿是印第安人,更不愿意是二者的后裔” (Paz,1950: 78)。所以他们称自己为自身形成的混血儿(mestizo), 是抽象概念中的“一个人(un hombre)”, 是“虚无 (Nada)”的儿子(Harss,1968:338)。从大革命以来,在墨西哥的现代文学中,对民族文化意识的探讨以及对自我身份的追问就一直是一个重要主题,而最典型的当属富恩特斯的作品。从《戴面具的日子》到涵盖墨西哥大革命各个阶层状况的恢宏叙事长篇小说《最明净的地区》(LaRegiónmásTransparente),再到描写乱世枭雄克鲁斯(Artemio Cruz)一生的《阿尔特米奥·克鲁斯之死》(LaMuertedeArtemioCruz),还有从虚伪、残酷、荒诞等各个角度来展示墨西哥面貌的短篇小说集《盲人之歌》(CantardeCiegos),都在探讨墨西哥这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古老而又年轻的国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如何去平衡传统与发展的关系,如何去发掘“墨西哥主义(mexicanismo)”的真正内涵。
作为富恩特斯早期的作品,《查克·莫尔》的研究相对他的其他作品而言研究成果较少。有的将《查克·莫尔》与科塔萨尔(Julio Cortázar)的《被占的宅子》(LaCasaTomada)做比较,重点分析原住民神祇形象(Martínez,2006);有的研究其与埃莱娜·波尼亚托夫斯卡(Elena Poniatowska)的《科亚特利库埃》(Coatilicue)之间的连续性,表明阿兹特克人的历史和神话构成了墨西哥民族身份的基础 (Ignacio,2017:530);有的则认为《查克·莫尔》是一种对话性的叙述,是两种意识形态、两种信仰和两种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展开的对话(Camacho Quiroz,2011:159)。《查克·莫尔》虽然是富恩特斯初期写作的尝试,但已经初现富恩特斯的创作风格:双重的叙事结构、带有神话色彩的叙事内容、交错的时间线,还有出其不意的结局、象征手法的使用等。因此,本文以《查克·莫尔》的叙事策略研究为出发点,借此揭示富恩特斯作品中对墨西哥民族文化意识的探索和对墨西哥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进程关系的思考。
双重叙事:两个声音、两条时间线
在叙事学领域,文本中的时间有两类:文本时间和故事时间,两者的重合只在理想状态中存在(李晓珍, 2020: 90)。《查克·莫尔》中的两个叙事声音:一个是以第一人称叙事的“我”,即菲利韦托(Filiberto)的朋友,“我”在小说中承担着全知叙述者的角色;一个是以日记形式叙事的菲利韦托,在小说中承担着人物叙事者的角色。“我”在菲利韦托被淹死后,去阿卡普尔科(Acapulco)把他的尸体运回墨西哥城,并送回他家。在收拾他的遗物时发现了他的一本日记本,于是在运送尸体回墨城的途中,“我”开始阅读他的日记,由此也慢慢解开了菲利韦托之前的一系列怪异举动和他的离奇死亡之谜。而当“我”将目光转移到日记上时,读者的阅读内容也转到日记上,视角进行了转换,“我”变成一个阅读者,菲利韦托开始扮演叙述者的角色。这时,两个叙事的声音和两条时间线出现:“我”阅读菲利韦托的日记内容对应当下“我”将他的尸体运回墨城的时间;菲利韦托在日记里记下他的经历对应过去他与查克·莫尔相识和相处的时间。这种双重叙事使读者能够从双重的角度了解事件发生的过程,从而既能够把自己带入故事中来,好像自己是一个参与者,同时又是一个旁观者,和故事保留一定的距离。这种在参与感和明晰度之间恰到好处的平衡给整个故事更添了一份神秘的色彩。通过双重叙事的策略,《查克·莫尔》的表层文本得到最大限度地表达。
“我”作为讲述者的视角下,一开始就交代了菲利韦托的死。把菲利韦托的死亡设置为小说的开端,即为故事设下了悬念。“悬念是一种具有高度张力性质的叙事技巧,使读者全神贯注于正在发生的事件及其未来发展,由此激发了读者对故事版本的多重想象”(尚必武,2013:132)。故事因此使读者产生了情感上的张力与期待,读者自己提出诸如“菲力韦托是谁?”“为什么会死?”“怎么死的?”等一系列问题,从而顺理成章地引出下文。另外,叙述者菲利韦托的朋友是以第一人称 “我”出现的。“我”作为一个全知叙述者,带着客观、冷静的态度来观察整个事件,就像是作为旁观者的读者一样,这就鼓励读者能够认同“我”的叙事,并且在“我”身上看到他们的影子。
接下来,“我”作为菲利韦托的朋友,对他做了简短的介绍:他留给“我”的印象仅限于每年去德国小旅馆、圣周六去跳舞、年轻时会游泳,除此之外,没有特别之处,是一个渺小、平庸的小人物。他的死亡也表明他的可悲:没有人在意他的死亡,也没有人会再去提起他,就像他不曾出现一样,“一脸惨白躺在盒子里的菲利韦托为了等早班车,在各种背篓包裹陪伴下度过了新‘生’活的第一夜”(富恩特斯,2019: 2)。他就像是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任何一个墨西哥人一样,也正因为如此,他不仅是他自己,也是大部分墨西哥人的写照:在现代化的社会里,已经失去了自己的特点,变得默默无闻,例行公事,没什么目标,好像一个工具人。
“我”的声音一共两次打断过菲利韦托的日记叙事。第一次是因为观察到他的笔迹有所不同,像小孩的字一样,“费劲地把每个字分开,有些又显得紧张”(富恩特斯,2019:11),不仅如此,日记还断了三天。这是发生在菲利韦托觉察到查克·莫尔雕像正在变成人的时候,他感觉到它躯干仿佛有某种肌肉质地,好像有东西在雕像内流动,而且雕像的手臂上开始长出汗毛。异常的字迹表明菲利韦托内心的混乱,日记的间断说明在语言中他已经没办法找到一个参考物来记叙自己所经历的一切,因为它是理性所无法解释的,是无法言说的。第二次“我”打断菲利韦托的叙事是当他讲到查克·莫尔完全变成人的时候。“我”回忆起菲利韦托的种种怪异举动:文书处理得乱七八糟,问水有没有气味能闻见,还主动申请去沙漠降雨。日记并没有说服“我”查克·莫尔存在的真实性,就像还不足完全说服读者一样,“我”还在为菲利韦托的举动寻找合理的解释:或许是夏天的雨太多让他脑子进了水,或许是老房子阴郁的环境让他抑郁了。“我”的叙事的插入一方面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菲利韦托的日记内容,在他身上确实发生过奇怪的事情;另一方面,“我”又是一个冷静的旁观者,一直在用理性为菲利韦托的日记内容寻找合理的解释,读者也不知不觉跟着“我”的行动走,也对查克·莫尔存在的真实性犹豫不决,故事的紧张感逐渐上升。
至此,一直到最后一篇日记“我”的声音才又开始出现,叙事又回到回墨城的旅程中来,并且“我”仍然在努力寻找菲利韦托“发疯”的合理解释:工作太忙或者还有点心理问题, “我”仍然没有承认查克·莫尔的存在。小说的最后部分,“我”来到菲利韦托的家,还没插钥匙一个印第安人就把门打开了,好像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一样,还没等“我”讲完,他就告诉“我”他什么都知道了。小说在印第安人的一句“我什么都知道” (富恩特斯,2019:20)中戛然而止。虽然故事并没点明,但可以推测出全知全能的印第安人,毫无疑问,就是查克·莫尔。由此可看出,“我”的叙述在整篇小说中非常简洁明了,重在展示事件的发展,几乎不带有感情色彩,显得沉着冷静。这与菲利韦托充满感情的叙述互为映衬,因而,从“我”看似波澜不惊的客观叙述中,更能感受到发生在菲力韦托身上事件的神秘性,增强故事的紧张感。“我”的叙述也是对菲利韦托日记内容的一个补充,“成为一个参与事件的见证者”(García,2000:26), 使小说故事情节更加完整。
小说的第二个叙事声音是菲利韦托的日记。日记是一种直观、有效的叙事方式,与其他叙事不同,日记是用来记录自己的所见所闻,是写给自己看的,而不是给别人看或者用来说服别人的,所以在日记中菲利韦托可以尽情地无顾忌地述说自己的种种体验和感受,无需对事件进行编造、掩饰或者夸大。日记是菲利韦托内心真实想法的反映,小说中把事件用日记的形式展现出来,显得十分真实而可信。在日记中,时间具有重要意义,它是记叙者将来阅读日记来回忆往事的一个参考物。但是在《查克·莫尔》中的菲利韦托的日记里面却找不到具体的日期,只有“今天”“一早”“星期天”“旱季”等抽象的时间词。具体时间的缺失表明菲利韦托无法再回去翻阅自己的日记,去回忆过去发生的事件,也暗示菲利韦托死亡的结局。
第一篇日记是菲利韦托在咖啡馆里回忆往昔,感慨当下。他想起昔日的好友,如今已经飞黄腾达,看到满是霓虹灯的城市以及装有自助饮料机的咖啡馆。好友、咖啡馆、城市“用一种跟我不同的节奏逐渐雕琢着自己”(4)①。这是现代工业社会的节奏,他们抛弃了过去,适应了现代化,并融入其中,成为其中的一部分。但菲利韦托不同,虽然也身处其中,却并没有完全融进来,在内心深处他并没有遗忘过去,甚至对过去还带着某种怀念,这也为后面他收集墨西哥原住民“小雕像、神像、盆盆罐罐”(6)的爱好以及和查克·莫尔的见面埋下伏笔。在朋友佩佩的介绍下,菲利韦托来到拉古尼亚(La Lagunilla),找到一尊查克·莫尔的雕像,他把雕像安放在自家的地下室里。从第三篇日记开始,记叙的重点逐渐转移到查克·莫尔身上。
查克·莫尔的变化是循序渐进的,而对它变化的描写也是遵循着线性叙事的结构,层层递进。首先是家里一系列怪事的发生:水管坏了,厨房水漫了一地,半夜听到让人毛骨悚然的痛苦呻吟,水管修好后又坏了,查克·莫尔长满了青苔,“全身像中了绿色的丹毒”(9)。 情景的渲染,为查克·莫尔增加了一层神秘的色彩,气氛也开始变得紧张起来。在《查克·莫尔》中,从第十三篇日记的描写开始,雕像开始变成肉身,“每摸过一遍石料就变软一些”(11),“躯干有某种肌肉的质地”(11),“有汗毛”(11),“呼吸声”(12),“脚步声”(12),“面带微笑”(13)。从日记中可以看出菲利韦托对这些变化也是难以相信,“我得去看医生,问问是我想象力太丰富还是神志不清或者别的什么”(11)。他虽然没有完全抛却过去,但是前哥伦比亚的文明毕竟太遥远,对生活在20世纪现代工业文明社会的他而言就像是一个传说,对于过去他也只是有一种朦胧的怀念,这种感觉并不强烈。所以面对眼前震撼的场面,菲利韦托感觉到的只是害怕、怀疑,并没有激动和惊喜。
查克·莫尔的第二阶段的变化是从肉身变成凡人。在《查克·莫尔》中,从第十三篇日记开始讲述查克·莫尔逐渐接触现代社会的产品,习性也逐渐趋向于凡人:“Sapolio皂” (15),“睡到我床上” (15),“穿上了我的衣服”(16),“把我晨衣的绸子摸来摸去”(19),“让我教他用香皂和乳液”(19)。查克·莫尔一步步陷入人世的诱惑,他的神力也慢慢消散,失去了降雨的能力,脸上呈现某种老态,头发变得灰白,身子浮肿。曾经威严的雨神已经变成一个也要经历生老病死的可怜的凡人,他已经无法再让菲利韦托感到敬畏,就连最开始的好感和朦胧的怀念也完全消失,相反他对查克·莫尔只剩下恐惧与厌恶。在最后一篇日记中,菲力韦托写道,自己想要逃掉,并且期待查克·莫尔死去。
作为人物叙述者的菲利韦托,其叙述视野和叙述范围是受到严格限制的,他只能说出他所经历的、所看到的、所感受到的。他没办法去讲述他未曾看到、经历到和感受到的种种。 因此,“我”的出现承担了菲利韦托死后的叙事者角色,去完成他所无法完成的叙述任务。也就是说,《查克·莫尔》的双重叙事中,菲利韦托的日记是整篇小说的核心内容,“我”的叙事则是小说情节的补充,全知叙事者和人物叙事者的完美结合共同将故事推向高潮。此外,小说双重叙事的策略让故事颇具“奇想文学”的特征。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在其论著《奇想—一个文学样式的结构研究》(TheFantastic:AStructuralApproachtoaLiteraryGenre)中指出,奇想(the fantastic)源于读者的一种犹豫感: “首先,文章必须让读者把人物所处的世界看成真实的世界,在所描述的事件的自然和超自然的解释之间犹豫不决。第二,作品中的人物也感觉到这样犹豫,犹豫从而成为作品的主题之一” (Todorov,1973:33)。这种犹豫感首先体现在小说人物“我”的身上,“我”作为一个现代文明社会的人,总是试图用理性为菲利韦托的异常举动和突然死亡寻求合理的解释,但菲利韦托的日记又让“我”想到也许真的存在某种超自然的存在,“也许查克·莫尔是真实的,也许只是菲利韦托精神错乱的产物”(Martínez,2006)。读者因为对“我”有着高度的认同感,也在这两种解释之间犹豫不决。其次,犹豫感还体现在菲利韦托身上,一开始他对查克·莫尔变成人也带着怀疑的态度,因为这种犹豫感的存在,鼓励读者继续往下读,一探究竟,从而赋予作品更强大的生命力。因此小说的表层文本通过双重叙事的策略,全知视角和限知视觉的转换以及在过去时间线和现在时间线交织中得到充分的展现。
象征手法:墨西哥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在拉丁美洲,虚构的文学作品常被批评为逃避文学,因为它并不总是根植于社会政治现实,相反还具有某种刻意避开现实问题的趋向。但是对富恩特斯来说,想象不是逃避现实的手段,而是“秘密潜入它、揭露它新的维度的方式”(Duncan,1986:131)。在一篇访谈中,富恩特斯说自己是塞万提斯式的作家,“用想象反对现实,把想象变成对社会的批评”(奥特加,1991:153)。 在《查克·莫尔》这篇充满想象的奇想小说中,富恩特斯运用象征的手法,将自己对墨西哥遗忘过去,迷失在现代工业社会的现实进行揭露和批判,一针见血地指出墨西哥确立自我身份的急迫性。通过象征的手法,小说的深层文本得到表达,而小说中的象征手法主要体现小说的人物上。
小说中的主人公之一查克·莫尔是前哥伦比亚时期阿兹特克文明的雨神,象征着墨西哥被遗忘的过去。“查克·莫尔”并不是雕像的本名,而是被发掘者命名为“查克·莫尔”,发掘者勒普隆荣(Le Plongeon)也并不是墨西哥人,而是英国人。被埋在土里的雕像是墨西哥被抛弃的古老文明,被重新命名的“查克·莫尔”则是被西方文明重新定义的墨西哥传统文化。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认为,话语从来就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它是人为构建的结果,是权力的产物和权力斗争的工具(Foucult,1981:55)。查克·莫尔失去了自己的话语权,不能言语,被现代工业文明塑造成血腥、残忍的形象。所以在现代墨西哥人的心目中雨神是令人害怕的、嗜血的,商店老板为了迎合浅薄无知的审美,还往他肚子上抹番茄酱。因此查克·莫尔不仅是被西方文明打败了,而且是被售卖了,并且心灵上也被背叛了:它被商业化,被划入自己根本就不属于的人为建构中,被用来强化别人感兴趣的印象,即文明的现代人和血腥的印第安人。当查克·莫尔变成能够用金钱来衡量的商品后,也就失去了它原有的价值。于是本可以成为民族身份表达的查克·莫尔被捏造成一个装饰品。被刻意扭曲的查克·莫尔因而变得不可接近,不可能再次成为墨西哥人的信仰,基督教成为“土著信仰一种新奇但又自然的延伸”(富恩特斯,2019:6)。西方文化取代了印第安土著文化成为墨西哥的主流。
查克·莫尔变成人则象征着古老的印第安文明在工业社会里腐化的过程。神话是属于原始社会的,神是从先民眼中变幻无测的大自然中衍生而来,与大自然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可是查克·莫尔现在所处的是现代工业社会,已经远离了原始的自然,地下室不是神庙,菲利韦托也不信仰他,更加不存在节日去纪念他。作为一个神,他离开了与自然的联系,没有了祭祀他的场所,没有信徒,更加没有供奉他的祭品。所以查克·莫尔失去了他的身份,必然变成一个普通人,甚至更加糟糕。在古老的文化和20世纪的现代文化中,他并没有从两者中获益,相反接受了两者最糟糕的部分, 变成一个不伦不类的“混合体”(Duncan,1986:132)。 “穿着家居服,戴着围巾。他的样子恶心得不能再恶心了,廉价花露水味儿,扑了厚厚一层粉想掩盖皱纹,嘴上拙劣地抹了些口红,头发像是染过”(20)。 查克·莫尔的装扮正呼应了小说集的名字:《戴面具的日子》。墨西哥大革命后,民族意识开始觉醒,但年轻的墨西哥还没有形成自身的民族文化意识体系,只好“匆匆忙忙地临时画了个脸谱戴上,转向印第安人的过去”(刘长申,1997: 88)。 又为了能够有现代的东西,从欧洲搬来了“乌托邦主义”。查克·莫尔正是大革命后被匆忙用来充当墨西哥民族传统的印第安文化,糟糕的妆容则代表胡乱嫁接在印第安文化上的西方现代文明,两者都没有经过筛选就被潦草地、乱哄哄地用来组成“墨西哥主义”。很明显,富恩特斯对待这种做法是持强烈的批判态度的,他用“恶心得不能再恶心(su aspecto no podía ser más repulsivo)”(富恩特斯,2019:20)来形容化妆后的查克·莫尔,揭示出这种行为的可笑和荒唐。
其实,富恩特斯在小说中还提到过去在现在的墨西哥社会存在状态的另外一种可能。查克·莫尔也并非一直遭到菲利韦托的厌恶,菲利韦托曾说他“笑容也更加和善”,“还是可以相处的”(富恩特斯,2019:12-14),他还给菲利韦托讲述神奇的故事,这些都曾让菲利韦托对他产生过好感。直到他开始接触现代工业社会的商品后,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越来越难以让人忍受。因此,如果过去能够在现在的墨西哥社会中保持它的纯粹,不故意迎合现代商业社会给它贴上的标签,过去就可以让墨西哥人接受,从而唤起墨西哥人内心深处的民族认同感。
小说的另一个主人公菲利韦托是一个典型的现代社会里的小人物,象征着墨西哥的现在。他生活在现代工业社会,但又不能完全跟上社会的节奏,显得有些落伍,只能在咖啡馆里回忆辉煌的过去。墨西哥也是如此,有着灿烂古老的印第安文明,但眼下很明显没能跟上全球现代化发展的节奏。菲利韦托对过去是带着眷恋的,因此他不愿意离开父母留给他的老宅子,老宅子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祖上显赫的见证。他怀旧的感情依旧是朦胧的,他收集墨西哥原住民艺术品,但更多的是出于爱好,他不关心查克·莫尔雕像的真假,只是觉得它好看而已,所以他并不了解也没有兴趣去了解土著文化,他已经感觉不到连接他与查克·莫尔的精神纽带。现在的墨西哥也是这样,对过去印第安文化的理解肤浅,内心深处并不认同它,更不承认自己是印第安人的后代。
菲利韦托父母过世,独居老宅,没什么朋友,写日记是他表达自我的唯一方式,也是他孤独的写照。地下室的收藏品是他的精神依托,对查克·莫尔雕像的渴望由来已久。菲利韦托寻找雕像喻指墨西哥人对自己民族身份的寻找。长久以来,墨西哥被西班牙占领,本土文化在西方文明到来之后被取代、被遗忘。墨西哥独立后,他既否认印第安人是祖先,也拒绝称自己是墨西哥的西班牙人。墨西哥似乎成了一个无根的民族,孤独感油然而生。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曾说,“墨西哥的历史就像一个人寻找他的祖籍和出身的历史”(Harss, 1968:340)。对身份的渴求几乎是出自潜在的本能,菲利韦托自己并没有强烈的意识,只当作满足好奇心,但他没有意识到这种对好奇心的满足正是出自自己本能的需要。这种需要就像是水管中的水,虽然有了水管的包裹而不被察觉,但一直在流动,在等待时机从水管中爆破而出。在日记中菲利韦托写道:“另一种真实昭示出来,虽然从前也被感知,但一直无主似的游荡,现在重来震撼我们,试图恢复生机和话语”(富恩特斯,2019:12)。菲利韦托终于意识到并且承认过去的存在,那些被遗忘的,终有一日会被重新记起,恢复生机。
但这还远远不够,另一个问题随即出现:该带着怎样的态度去对待过去呢?在小说中,菲利韦托对查克·莫尔的态度也反映出现在的墨西哥人如何面对和逃避过去。受到文明社会教育的现代墨西哥人早已不再信仰雨神,强加在雨神身上的血腥、残暴的话语也被他们作为事实接受。印第安文明被贴上“残暴”“野蛮”“未开化”的标签,墨西哥人从而拒绝接受自己是印第安人的后代,但他们需要找到一个寄托来证明自己过去的存在,所以墨西哥人对待过去的情感是矛盾的:既眷恋又逃避。菲利韦托的死则表明墨西哥亟待采取正确的态度来对待过去。为了逃避查克·莫尔,菲利韦托来到阿卡普尔科,却淹死在那里。在小说中,水既代表着生命,即对查克·莫尔来说是它力量的来源;同时水也代表着死亡:菲利韦托在水中淹死。富恩特斯借此来表明在民族意识模糊、各种思潮纷乱的墨西哥,如果不能够采取正面的态度来面对过去而一味选择逃避的话,所面临的民族文化意识危机将会让墨西哥迷失在飞速发展的现代工业社会。
小说的另外一个角色即“我”,从某种意义上说象征着墨西哥的将来。整篇小说中,对于“我”的描写屈指可数,我就像是一个透明人一样,几乎不被察觉,因为未来是没有人经历过的,也是当下无法感受到的。“我”通过菲利韦托的日记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就像对过去有所了解,经历过现在的将来的墨西哥,因而“我”的思维更加清晰,不像菲利韦托那样慌乱,也比菲利韦托更加有经验,能够用更加睿智的态度去面对过去。“我”和菲利韦托一样都生活在现代工业社会,都带着现代社会的特征,在小说最后一部分富恩特斯制造了“我”与查克·莫尔的见面,暗示墨西哥必须解决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才能在此基础上确立墨西哥的民族身份。小说开放性的结局也是富恩特斯对墨西哥将来的期盼,将来是不确定的,但是富恩特斯对“我”仍带着期许与希望。
结 语
《查克·莫尔》在表层文本的表达上采用双重叙事的策略,人物叙述者和全知叙述者结合,保证故事情节的完整性。全知视角和限知视角的转换又避免了小说叙事的单一乏味,增强故事的紧张感与神秘色彩。面对思想纷乱、民族意识模糊的墨西哥,富恩特斯用象征的手法将墨西哥的过去、现在、将来联系起来,展示出作品的深层文本。墨西哥拥有辉煌灿烂的过去,但自被征服以来,过去的辉煌被掩盖、被遗忘;又在西方话语的影响下,过去被扭曲,墨西哥人转而轻视和否定自己的过去,严重阻碍了墨西哥民族身份的形成。富恩特斯借此表达出对墨西哥面临的民族意识危机现状的担忧。过去是真实存在的,不能一味地否定或者逃避,但也不能全盘照搬。对待过去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如何协调传统与现代在墨西哥民族身份构建中的关系是墨西哥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双重叙事策略和象征手法的结合使作品的表层文本和深层文本得到巧妙地表达,使作品的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达到有机统一。
富恩特斯一生著作颇丰,他的作品不仅在拉美影响广泛,对世界文学界也有较大影响。富恩特斯被认为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但是他的许多作品仍然是立足于墨西哥的状况。在目睹了欧美国家发达的经济、科技和文化之后,也观察到拉美落后的状况。这让他不仅从政治、经济体制上寻找原因,也从文化的传承、传统和现代的关系、民族文化等方面去思考两者差异的根源。“换句话说,他是站在西方发达国家的高度观察自己的祖国的”(赵德明,2003:506)。他抨击社会的腐败、道德的丧失,也看到人性的善良、美好的一面。在追求物质生活的今天,富恩特斯的作品仍然具有较强的研究价值和意义。目前,国内对富恩特斯作品的研究相对缺乏,其作品内涵也有待深入挖掘。
注释:
①原文出自卡洛斯·富恩特斯.2019.戴面具的日子[M].于施洋,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此后仅随文标注页码,不再评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