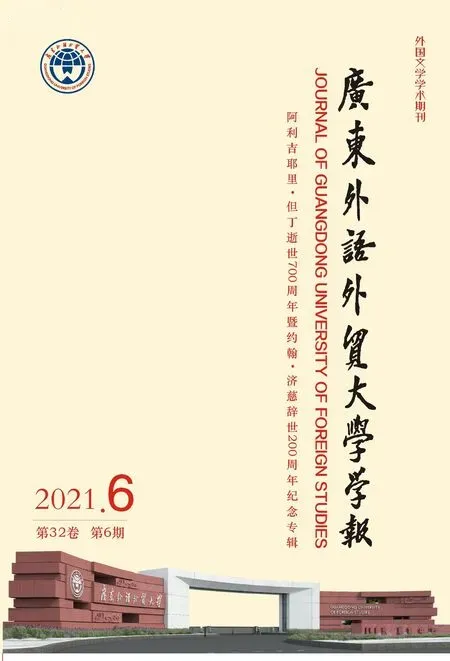诗歌中的脸:形象的遮蔽性
陈永国
引 言
脸是身体的一部分,是一种存在,但却是一种特殊的存在。脸作为表象,作为模样,作为形象,是给人看的,却又是不透明的,不可识别的,甚至是不可确定的。对于西苏来说,脸是崇拜的对象,是阅读的文本,是一个结构空间;它充满了神秘,因为一张脸究竟有多少副面孔实在难以预测,而即使只有一副面孔,其含义也不止一个(Cixous, 1991: 1-2)。对于德勒兹来说,脸不是脸,脸是面具。脸是“一个被结构的空间组织”;它把头遮蔽起来,因此头(以身体形式呈现的动物精神)便只能依赖于身体,因此也可以说,对立于头的脸并不属于身体。然而,通过擦拭和洗刷,脸的组织被解构,最终还是被头所替代。因此,在培根的肖像画中,脸只是幻象,作为附属物而存在(Deleuze,2003:20-21)。幻象一旦得以消除,作为动物之精神的头便可显现出来了。此外,在培根的肖像画中,面目的微笑如同里尔克诗中的夜风,可以消蚀脸;眼睛和嘴可以消解脸。于是,脸就成为既可以掩盖又可以被掩盖的图像,并由此而产生无尽的想象。在这个意义上,脸变成了图像,变成了面具本身。
在诗歌中如在肖像画中,脸也作为图像而存在,只不过其形象不是通过色彩,而是通过词语来再现的。由此,肖像画中脸的可视性就变成语言的隐喻性,其可视性下隐藏的神秘性就变成语言的不可译性,而其被图像所取代、被面具所掩盖的真实的面孔也只有在列维纳斯所说的“面对面”的对视中才能被揭示出来。这是因为绘画或雕塑所呈现的物本身之“自在”的存在只有通过鲜活的语言表达和深度的思想诠释才是可理解的。于是,在诗歌中,脸要么被呈现为庞德诗中模糊而不可辨认的“千人一面”,要么在惠特曼的诗中成为被众多面孔所遮蔽的“背后的究竟”,要么就是里尔克诗中只有通过死亡才能揭示其真实意义的被夜所消释的脸。而这一切都需要读者透过脸的表面而深入到物的深层才能见其本来“面目”。
庞德和惠特曼诗中遮蔽性的群脸
人群中这些幽灵般的脸
湿漉漉黑色枝条上的花瓣(庞德,《在地铁车站里》)
乍一看,庞德似乎在地铁车站上看到了五种因素,并将其汇集成诗:人群、脸、幽灵、枝条和花瓣。诗的第一行显然是描写地铁车站这个现实世界,甚或是现实中某个特定时间点的世界(比如下班时的城市地铁车站)或长途旅行后聚集在地铁车站里急于回家的人群。不过那些现实中的人脸却与另一个不同的世界关联着,即幽冥界,说明这些脸既是人脸又不是人脸,或者说既是人脸又是鬼脸,这可以根据真实世界中地铁车站人群的脸来判断,那是可以用焦虑、焦急、疲乏、饥饿、困倦、怠惰、苍白、无精打采、面无血色、形容枯槁、行色匆匆等形容词来描绘的毫无生命迹象、却在行走着的死者,一如所说的“行尸走肉”。于是,脸就扮演了两个完全不同的角色,但也是完全相同的角色,即生的世界中的人脸与死的世界中的鬼脸。也许二者本来就是没有分别的,因为诗人是把“人群中的这些脸”称作“幽灵”的,非常具体地反映了现代社会中的人千篇一律的面相。第二行意象突转,人群似乎被转喻为“枝条”,于是,那些面无血色、形容枯槁、行色匆匆的脸便被“湿漉漉(的)黑色枝条”串联起来,成为一体,那阴冷潮湿的感觉恰恰是地狱般的情形,使本来就苍白得令人骇然的幽灵显得更加可怕,仿佛人的世界真的变成鬼的世界。然而,最后一个意象“花瓣”的出现表面上似乎扭转了这个阴森黑暗的场面,把地铁车站里拥挤的人鬼难辨的脸瞬间变成了(想象中色彩缤纷的)花瓣,给潮湿阴冷的幽冥界带来了一线明亮的生机,读者一下子就被从痛苦的、疲乏的、无望的感觉中拉了回来,回到花的世界,脸也随之变成拧在一个枝条上的花瓣,脸变成花瓣。然而,我们大可不必如此乐观,因为这“花瓣”无论如何也不能帮助我们提炼出一系列表示欢乐的、艳丽的、色彩缤纷的形容词,来与上面的那个系列形成鲜明的对比,即使“花瓣”真的光鲜靓丽,因为它们结在“湿漉漉(的)黑色枝条”上而无法让观者高兴起来。进而可以下结论说,诗人庞德在地铁车站里的瞬间内捕捉到生活的真实,即海德格尔所说的作为存在者之整体的真实,并把这个真实用复杂的印象、深远的修辞、明了的语言和极简的形式置入诗中,以诗人特有的意象表达出来,但同时也藉此用这印象把那真实遮蔽了起来。因为,我们还是不确知那些都是什么样的脸,哪些具体的人的具体的脸,或究竟是表现哪种表情的脸(读者就仿佛但丁在维吉尔的引导下,游历了地狱和炼狱,最后在天堂的入口戛然止步)。
我们暂且放下庞德的诗,看看另一首也是描写人群中的人脸的诗:
在大街上徘徊,或者骑着马在乡村的小道上驰过,
看哪,这么多的人脸!
…… ……
这样在大街上徘徊,或者横过不断来去的渡船,
这么多的脸呀,脸呀,脸呀。(惠特曼,1987:859-865)
且不论庞德与惠特曼两人在时间维度和地域上的偏差,就空间而言,惠特曼带我们走出英国阴冷的地铁车站,在美国的大街上漫无目的地徘徊,或者在明亮的乡间小道上策马驰骋,又或在往来不断的渡轮上观看那“不断来去”的脸。所不同的是,庞德那毫无表情的印象式描述在惠特曼这里变成了一种真挚得甚至有些幼稚的惊叹:“看哪,这么多的人脸!”“这么多的脸呀,脸呀,脸呀。”相较之下,惠特曼比庞德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观察得非常仔细,即使脸拥挤不堪,也能够分辨出不同表情的脸:“友爱的、严正的、深思的、和蔼的、理想的脸;有精神预感的脸、总是受欢迎的普通的仁慈的脸”;甚至能识别出从事不同行业的人的脸:律师和法官的脸(他们后脑广阔)、猎人和渔人的脸(他们前额突出)、正教市民的脸(他们胡子剃得干净)、艺术家的脸(他们的表情是“纯洁的、夸张的、渴求的、疑问的”)、孩子的脸(圣洁的)、母亲的脸(发光的)、音乐家的脸和爱恋者的脸(模样未曾明确)。最重要的是,惠特曼甚至能分辨出“某些包藏着美丽的灵魂的丑陋的脸”和“漂亮的被憎恨或轻视的脸”,“表示尊敬的脸”“如同梦一样的脸、如同坚定的岩石一样的脸、完全隐去了善与恶的脸、被阉割了的脸”。从空间场所上看,惠特曼把城市的、乡间的、水路上的脸尽收眼底,而且,在情感上“所有这些脸都使我很满足”。
显然,在方法上,我们前面用来解读庞德诗的方式,即试图把诗打碎以见其根底,将瞬间呈现的永恒化为碎片,似乎不适合用于惠特曼的诗,因为惠特曼呈现了一幅不但完整而且细腻的人脸的图像,不但看到了脸的表象,还看到了这个表象背后所隐藏的东西,如丑陋的脸包藏着美丽的灵魂,而漂亮的脸却遭到憎恨或轻视。实际上,在看似完整的图像上,诗人已经把脸分割了,解构了,使其破碎了,甚至让读者看到了一反常态的现象:面目丑陋但心灵美丽;脸蛋漂亮但遭人憎恨。于是,我们对诗人在第一节中提出的“所有这些脸都使我很满足”这一说法不得不产生怀疑,也许正因如此,诗人才在第二节一开始就问:“你想假使我以为这些脸就表示出它们本身的究竟,我对于它们还会满足么”?原来这些令他满足的脸仍然没有“表示出它们本身的究竟”!所以,所谓的满足只是表面上的、虚假的、并非真心的。脸纯然成为图像、面具,背后竟掩盖着不令人满足的东西!所以,他要费一番气力探个究竟。在庞德那里,“探个究竟”是留给读者的;诗人只把那些脸组构成一个画面,一个印象,而且是模糊的、隐喻式的,即用一连串的意象呈现出关于脸的印象,并未像惠特曼那样将其一一详叙,尽管那个画面里一定藏有惠特曼所未曾看见过的脸。
可以说,庞德的诗以其浓郁的象征性隐藏起脸的个性和真实性;惠特曼的诗则以真挚的抒情性凸显出脸的个性和真实性。抑或可以说,惠特曼用在大街上、田野里和渡轮上看到的具体的脸弥补了庞德在地铁车站里看到的那些模糊的“花瓣”,虽然有时空的距离,但也完全可以在“穿越”的意义上说,庞德和惠特曼所看到的脸虽不完全一致,却也大同小异。其最大的共同点就在于,它们都只是一般地呈现,都只停留在作为以语言呈现的一般图像,如同已被置入存在者之整体真实的艺术品,因此仍有解蔽的可能性。于是可以说,庞德的诗也是抒情的,只不过那抒情是抽象的、凝练的、寓言式的隐喻和印象式的意象;它考验人的智力,不像惠特曼的诗一下子就把读者引向现实的具体,即使是被隐藏的“它们本身的究竟”,也是诗人自己拖曳出来去蔽的,即在那些不会令他满足的脸上,看到了“卑贱下流的虱子在上面苟且偷生,长着乳白色鼻子的蛆虫在上面蠕动蛀蚀”,那些脸上长着“一只嗅着垃圾的狗的突鼻,毒蛇在它口里面做窝”,那些脸是“比北极海更凄寒的冷雾,它的欲睡的摇摆的冰山走动时嘎吱作响”。此外,还有那些“苦刺丛的脸”“呕吐者的脸”“像药棚、毒剂、橡胶或猪油的脸”“癫痫病者的脸”“为恶鸟和毒虫咬伤了的脸”“一种不停地”敲着丧钟的脸。而即使你“皱纹满面”,面孔“和死尸一般苍白”,那也“欺骗不了我”。因为“我”能看穿“那滚圆的永远抹不去的暗流”,“能看透你那张失智的鄙陋的伪装”。不管你怎样扭曲、虚晃,“我”都会揭开你的假面;“我”都能看见“疯人院里最污垢的满是唾沫的白痴的脸”,“我”还知道他们所不知道的东西,那就是10年、20年后,这里的垃圾将被清除,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如同我自己一样的美好”。
将被清除的垃圾和最近将来的美好,这是在庞德的诗中所看不到的,甚至感觉不到的。拥挤的地铁车站、幽灵般的人脸和“湿漉漉(的)黑色枝条”,这无论如何也不会让庞德看到惠特曼心中的“旗帜和战马”“先驱者的高冠”,听不到那“凯旋的鼓声”,更难以想象那“不论睡着醒着都证明是神自身的子孙”的“威严的长着浓髯的脸”“健康的诚实的青年的脸”“盛开的百合花的脸”以及“有很多孩子的母亲的年老的脸”:
这大地柔美的性格,
这哲学不能超过也不愿超过的完美的境界,
这人类的真正的母亲。(惠特曼,1987:859-865)
大地的脸、母亲的脸、哲学不愿意逾越的完美的脸,这是惠特曼以其炽热的浪漫情怀和人文精神所极力歌唱的自然、民主和自由。无论如何,这些脸,即便是福柯所说的“沙滩上的脸”,即便是牛顿的沉默的数学的脸,或者异常平坦、宛如阳光下的满月、不曾为人与人之间的视线所捏塑、不曾见识过电石流火之力量的盲人的脸(马瑟, 2013:162),也都与庞德笔下模糊的甚至无形的脸,或惠特曼笔下有形的甚至轮廓清晰的脸一样,都是具有无限的指涉、具有无限的生成性的意义组合,而这些组合总是指向一个更高的能指,那就是脸的实质性表达,德勒兹称其为“脸性”(faciality)(Delauze & Guattari, 1987:115)。所谓“脸性”,就是马瑟所说的“藏于内心的”真正面容,我们从未曾见过的藏于假面背后的真面孔(马瑟, 2013:162),或惠特曼所谓脸的“本身的究竟”。所谓“脸性”,就是海德格尔经过去蔽而展示的脸,或德勒兹所说的经过解域而延展的场域:意指符号从这里产生、释放,声音从这里发出、传播,但它也是解域的极限,有再度被辖域化的可能,因此也可能被再度遮蔽。然而,既然是能指发放的场所,它就能赋予能指以内容,引发阐释,并通过阐释赋予脸以本质,使脸的特征发生变化,显露出它们“本身的究竟”。这就是说,“脸性”控制着意义的生产,主宰着脸的变化,最终赋予脸以归属。庞德赋予地铁车站里的脸以“幽灵般的”或犹如“花瓣”一样的“脸性”,籍着这“脸性”,我们抹掉本来就模糊的“脸”,改变面部特征或使其消失,然后进入另一个领域,“更令人哑言、更加不可识别的领域,那里在秘密地进行着生成的动物,生成的分子,夜间的解域从意指系统中溢出”(马瑟, 2013:115)。这里最重要的是“夜”的意象。夜的领域是漆黑的,神秘的;生成性的解域在这里隐蔽地进行着,从已然的意义系统中创造出逃逸线,但这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在另一位倾心于描写脸的诗人里尔克看来,夜正“携满宇宙空间的风”,“耗蚀着我们的脸庞”(里尔克,2009:41)。
里尔克诗中被夜风腐蚀的脸
在里尔克的诗中,“夜”给脸秘密进行的解域运动提供了场所和空间,因此我们更难以面对“脸”。但是,诗人立意要保护脸,保护“自己流逝的美”,用“明镜”“重新汲回自己的脸庞”(里尔克,2009:44);他“十指交叉”,用手掌庇护“被风蚀的脸”,因为这样它会“给我一丝感觉”(里尔克,2009:45);他“等待着,我把我的脸的自愿观望/执入白日的风中,/不抱怨黑夜……/(因为我看见夜已知晓)”(里尔克,2009:126)。然而,即使黑夜已经过去、白昼已经到来,他仍然“不要这些半虚半实的假面,/宁愿要木偶。实心的木偶。/我愿意忍受填塞的身躯,牵引线,/给人看的脸”(里尔克,2009:51)。里尔克宁愿做木偶,忍受被填塞、被牵引的痛苦,也宁愿把脸给人看,而不想要有表情的、能够虚掩着的、甚至可以“含羞试探的脸”。这是因为脸上的表情不是真实的,其内在是空洞的,形式是虚设的,最终将化入宇宙空间,将失身于母亲的躯体,并在那里被“蚀为平面”(里尔克,2009:55),或被化为乌有。有时,他真想让“流泪的脸庞”“如花开放”,“增添我的光彩”(里尔克,2009:75),但问题是,他不知道脸究竟归属于谁:
脸,我的脸:
你是谁的?对什么样的物
你是脸?(里尔克,2009:75)
我的脸是我的吗?针对谁而言,针对外部还是内部,我的脸才是脸?“你怎能是脸——对这样的内心,/那里面开始常与/逸散结成某物。”于内心散发出来、释放出来而结成某物,那是脸吗?树林、山峰、岩石、大海、天空,它们不都是没有脸吗?(树林可有一张脸?/大山的玄武岩不是/无脸却依然屹立?/大海不是/没有脸/从海底升上来?/天空不是映在海上,/没有额,没有嘴,没有颏?”)世间万物的存在似乎不需要脸,不需要什么遮蔽物,因为一切都是光明磊落的,一切都具有赤裸的物质性,谦卑、丑陋、美丽、厚重、粗大、纤小、有形或无形,它们实实在在地存在着,本身就是惠特曼所要追寻的那个“究竟”。甚至连动物也觉得这脸、这面具、这遮蔽毫无用处:“有时候动物给人一种感觉,/不是吗?似乎在请求:拿走我的脸!/它们觉得自己的脸太重,/并把自己渺小的灵魂/随脸一块太远地伸入/生命之中。而我们?”动物因着渺小的灵魂而不想要脸,因为它们进入生命的内部,与生命合为一体,因此就不再需要脸的遮掩了。而我们这些拥有“灵魂之动物,迷惘,/因心中的一切,还没准备好/趋向虚无,我们,吃草的/灵魂,/我们不是在夜里/向赐予者乞求非-脸,/它属于我们的幽暗?”(里尔克,2009:122-123)人类因着灵魂的牵引反倒迷惘,没有准备好走向虚无,不能坦然地面对死亡,因而在夜里祈求属于“幽暗”的“非-脸”。更何况,脸的表现不是真实的,表情是虚假的,它们作为图像都在遮掩着真实的存在。于是,庞德笔下“湿漉漉黑色枝条上的花瓣”就自然而然地被里尔克夜里的宇宙的风蚀化为“非-脸”,而惠特曼的那些具体的脸也就成为遮掩其“本身的究竟”的图像了。三位不同国族、不同时空、不同思想倾向的诗人就在“脸”的“脸性特征”上走到了一起。
然而,里尔克提出的一系列问题都是基于对死亡的深度思考。当你看到医院里的人批量地死去,甚至不再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死,因而也不再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生,死亡已经变得“平淡无奇”,这时,脸也就随之而变得毫无意义了,脸及其归属就将成为一种消逝的记忆(贝尔廷, 2017:120)。在里尔克看来,脸不是脸,脸是非-脸;而作为非-脸,脸可以是任何东西,唯独不是脸(这里,诗人里尔克和哲学家德勒兹再一次走到一起)。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一个人拥有许多张脸。脸作为器物、工具、面具,可以随时随地随意撕下一张,然后换上另一张,如同变换角色。人学会了换脸、变脸、扮脸(如同川剧中的变脸);学会了用脸扮演角色,也因此学会了制造和使用脸,于是脸变成了面具。在表演中,面具与角色是浑然一体的。角色在,则面具在(如同京剧中的脸谱);当角色不复存在时,面具也变得百无一用;当需要撕下面具时,脸也要一起撕下来,然后再换上另一张。于是,便有了描绘的肖像和雕塑的塑像,图像的艺术出现了。脸也通过艺术作品留下了生命的痕迹:“刻画在脸上的生命就像表盘上的指针一般清晰可辨,与时间的关联历历在目”,成为了历史的组成部分。在其反面,是雕塑的身体;身体在抗拒着“人们期望它所扮演的角色”(贝尔廷, 2017:123)。这意味着,脸“作为外在形式从不与身体浑然一致,而是试图呈现为一种不同于身体的东西”(贝尔廷, 2017:125)。或像德勒兹所说,它与身体相对立。这是因为雕像上的脸一旦被固定下来,成为“僵滞的面具”,它就是死亡的瞬间留下的模样,不具有生命的脉动,抑或就是死亡本身。而“真实的脸上呈现生命的流动。在生命进程中,脸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既指向它所走过的来路,又预示了死后将被戴上的那张面具”(贝尔廷, 2017:127)。脸在历史或生命进程中担任许许多多的角色,只有死后才凝固成“僵滞的面具”。而与面具相当的是文学的语言,文学语言能够编织各式各样的群脸或千人一面的单脸,而它们所承载的却不是物,是诗(马瑟, 2013:124)。之所以是诗,是因为脸与语言一样具有遮蔽的功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勒兹才说“脸是表指指意王国的正当的肖像,是这个领域内指意性能指固有的再辖域化”(Delauze & Guattari,1987:115),即脸是能指进行辖域化和再辖域化的场所;它引发阐释,改变意义,进而赋予脸以新的脸性。因此,德勒兹说,面具并不遮蔽脸,面具本身就是脸:它在遮蔽的同时引发新的阐释。
作为面具而遮蔽真实自我的脸
那么,庞德诗中作为面具的“花瓣”都承担着或遮蔽着哪些角色呢?惠特曼诗中具体的脸扮演的众多角色是否也变成掩盖真相的面具呢?它们与里尔克所说的“非-脸”又有什么关联呢?其诗性在何处?其“脸性”又在何处?如果我们把庞德诗中的群脸看作“现代人脸上那种屡见不鲜的千人一面”(贝尔廷,2017:124),那么,惠特曼诗中的众多角色是否就是用来抗拒死亡以便还原真实的脸的“自我”再现,或是当代文化中刻意提倡而流行的“一人千面”呢?它们又与里尔克的“终结的脸”“消溶的/包含夜的脸”“逸散的脸”“古老的上帝的古老的脸”“惯于理解的脸”有什么区别呢?从庞德到惠特曼,从惠特曼到里尔克,“哦,从脸到脸/何等的提升”(里尔克,2009:146)。提升到哪里?我们迄今仍然只是在言说,我们在对诗人口中的脸进行各种描述和阐释时,不过是在进行一种器具的转换,即由生命的面具——脸(图像),向生命的符号——语言(再现)——也即与面具相当的文学语言的一种转换,于是,里尔克这一讽喻性的感叹所指的根本就不是真正的提升,不过是从面具到面具的转换而已,因为语言不过是与脸相同的另一种面具。
我们只是嘴。但就在一瞬间,
那巨大的心跳悄悄把我们突破,
令我们哭喊——
我们这才是本质,转折,脸。(里尔克,2009:185)
所不同的是,从脸向嘴(言说)的转换或许是一种突破,是从心的跳动到本质的呼喊(哭喊),这是在瞬间内完成的。“心跳”恰如培根画像上的微笑,或蒙娜丽莎的含笑,或拉奥孔的嚎啕,突破了“脸”,突破了“嘴”,以“哭喊”的声音表达了“本质”,即那不可见的“自我”。只有在这时,“脸”才能通过“哭喊”转化为“诗”,脸背后“本身的究竟”才有可能被接近,正如在对诗的语言的解码中,只有打破诗之“言”(像)的部分,我们才能进入其未言(意)的部分,进而揭示语言背后的存在本体,接近物之物性。
诚然,“自我”、存在本体以及物之物性是可以通过多种形式表现出来,以多种面貌呈现出来的,因此其所承载的“意”也必然不是固定同质的,而是异质多变的。正如栾栋(2012)指出的那样:这里说的存在不是认知意义上的存在,而是一个以这种存在为出发点同时也以这种存在为归宿的完整的意义实在,同时也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宇宙实体。这是因为语言中的词就如同“脸”一样,总是被摆置的。“脸”诉说,词言说。脸用表情、目光、形态即其变形作用于对象,与其他的“脸”发生交流。同理,任何一个鲜活的词,都必须在一个弹性语境里与其他许多相异的词相互作用,才能在偶然的碰撞中产生“心跳”,令人“哭喊”,发生灵魂碰撞。但脸的交流是极其有限的、肤浅的,甚至是虚假的。纯诗是诗人们价值补偿的手段,它的意义不在于它的价值有多少真实性,而在于能够持续给诗人带来一种存在的优越感,一种心理的安慰(李国辉,2020: 49)。只有当“心跳”突破脸的外貌、从内心里发出“哭喊”的声音时,本质的交流才真正开始,因为脸作为易于腐朽的面具(即使上帝古老的脸也不例外)无法表达不可见的自我的灵魂,后者的不死性不会随着脸的僵滞而消亡,而且,哭喊或任何其他声音毕竟与语言是近邻。因此,肖像和雕像(脸和图像的艺术)不过是有限的交流手段,语言——以及由语言创造的文学作品(语言的艺术),“哭喊”或是由心灵呼啸而出的召唤——即便能够表达思想,却也未必是真正的自我精神的流露。于是,脸和声音的本质不在于交流,而在于阻碍交流;脸和声音的本质不在于感人,而在于阻塞/遮掩内心的呼唤。
那么,脸、声音及其艺术(绘画和图像艺术)所遮蔽的、或诗歌中借以用作面具的语言所遮蔽的“本身的究竟”究竟是什么呢?按惠特曼(1987)的说法,这“究竟”要么是“丑陋的脸”遮掩的“美丽的灵魂”,要么是被脸“隐去了(的)善与恶”。它或可体现为庞德诗中隐喻般的幽暗印象所遮蔽的现实世界,或可在里尔克笔下被夜消融却又包含着夜的生命之流的涌动。脸之“脸性”就是这个被遮蔽的“本身的究竟”,它具有无限的生成性,因而其意义(如果有的话)也不是由其表面所能推断出来的。如是,脸的“意义”似乎也因此被分为两个维度:一为显在,指可被言说的脸的意义,即其物质存在;如果它是丑的,其“本身的究竟”却未必丑。二为隐在,指脸被遮蔽或不可言说的意义,必须深入内部才能见其“本身的究竟”。中国古代玄学曾有“相由心生”之说,所谓“心者貌之根,审心而善恶自见”。说的是“貌”之根在心,只有深入内心才能见其善恶,但未必是相丑心必恶(“相由心生”的另一种解释)。这意味着,善恶并非是泾渭分明的对立面。苏格拉底相如森林之神,但五官背后深藏着内在的智慧和善;伊索相貌丑陋,但其美丽的灵魂中还隐藏着高尚的智慧;《巴黎圣母院》中的卡西莫多相貌丑之又丑,但心灵中却深藏着世间最大的爱。
在巴塔耶看来,文学的本质固然在于交流,而其最高价值则是表现恶(巴塔耶, 2006:24)。这不是说诗人喜欢作恶,描写恶,或宣扬恶;而是说恶对于诗人具有魅力乃至魔力。他要通过呈现真正的恶实现他所向往的善,一如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因为并非由于一味地宣传善、鼓励善、教育善,善就会普济众生,美就会自行到来,真理也会自动展示。善通过对恶的展示而被揭示;美通过对丑的展示而被显现;真理通过对虚幻的展示而被澄明。对于诗人来说,在思的某一阶段,美与丑、善与恶、生与死、真实与虚幻、言与不言、脸与心,都不是作为纯粹对立面出现的,而作为一物对另一物的遮掩而存在,而一物与另一物的关系却不必是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而是东方哲学中生生相克的化解。这又一次证明我们对待事物的态度以及籍由此而产生的思想无非是由习惯而养成。《爱丽丝漫游奇境》中的狮鹫曾说过,从来没听说过丑术!但我们都知道美术是什么!这是就西方人的认识方式而言的。古希腊哲学和艺术懂得高扬美,道说美,描摹美,但并非置丑于不顾,在建构美的话语时用美遮掩了丑,或只以丑作为美的参照,将丑弃置于边缘,或将其遮盖,于是就有了惠特曼所描述的被美所遮盖的丑恶的灵魂,或霍桑笔下披着宗教外衣而内心黑暗(黑暗得十倍——麦尔维尔语)的牧师,或马克思所透析的被镀成金色却使世界充满伪善和不幸的货币。换言之,被理性之美所遮蔽了的丑只有在被置入文艺作品时才有得以展示的机会,即在文艺作品敞开的世界里得以展示出来,并因之而存在。
结 语
通过脸、诗歌中的脸、文学中的脸和艺术中的脸,我们看到人的世界是想象的和虚构的,是图像的世界。它就像脸一样永远都在遮蔽、掩盖、躲避;但与此同时,也在解蔽、揭露、参与。这个发现既是令人惊奇的,也是令人不安的。脸本身无法解蔽、揭露、参与,它用目光穿透面孔、穿透面具而直视真实世界(正如萨特笔下3个互为地狱的人)。它用目光注视他者以消解我与他者(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界限。一句话,它用目光沟通。诗歌要么沟通,要么就什么都不是。信息时代的人沉浸在沟通之中;信息时代的人无时不在极端的孤独之中进行连续不断地沟通。于是,人成为语言。人存在就是为了沟通而使用语言,就是为了理解他人而注视外部的目光,而脸(图像)为着这种沟通和理解提供了令人痉挛和狂笑的场所,一个难以参透的世界,它本身就是由无数难以理解的甚至难以容忍的面相构成的。然而,人要掌握自己的命运,要享受自在的生存,要获得物的存在,就必须面对脸,面对那匆忙的、呆滞的、毫无表情的、甚至是丑陋的和恶毒的脸:庞德的群脸、惠特曼的无数个体的脸、里尔克的被夜风消蚀的脸,或者圣像中的脸、肖像中的脸、魔鬼的脸、怪物的脸、男人的脸、女人的脸、雕刻的脸、描摹的脸以及各种被书写的脸。为了自在的生存,人必须面对自己的脸和他人的脸,并消解二者之间的界限,这样,生与死、实与虚、美与丑、善与恶、昔与今、高与低、言与不言,便都可能不再是矛盾的了,而图像则是所有这些二元对立的最大调解者。